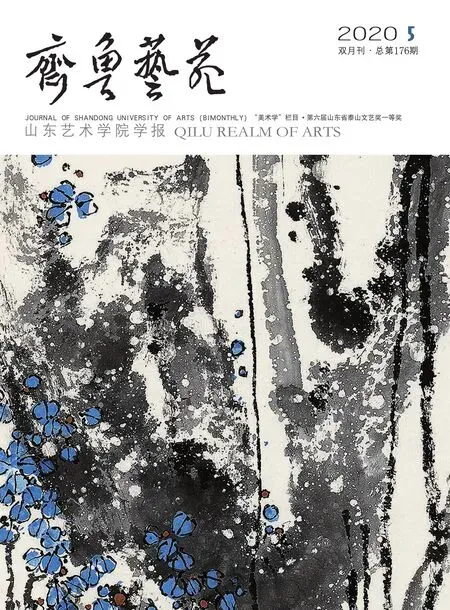《疯狂的外星人》:国产科幻电影的本土意识
李 宁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北京 100875)
2019年,《流浪地球》与《疯狂的外星人》两部科幻电影的风靡,使得这一年成为中国科幻电影创作历程中毫无疑问的里程碑式年份。巧合的是,上述两部同日上映的影片皆改编自作家刘慈欣的科幻小说;不同的是,二者的改编采取了相异的路径,并最终呈现出截然有别的影像风格。如果说郭帆执导的《流浪地球》较为忠实地延续了原著的故事架构,且在视觉效果、叙事模式等方面有意借鉴好莱坞式科幻电影的工业化、类型化经验,那么宁浩执导的《疯狂的外星人》则对原著《乡村教师》进行了改头换面式的重新演绎,并流露出强烈而独特的本土意识。两部影片的差异化路径对于中国电影产业而言是颇有启示意味的:一个良性的电影产业体系应该既能够生产出优秀的全球化、工业化产品,也能够彰显出独特的本土化、作者化特色(1)强调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的本土气质,并非否认它在工业化方面的探索。实际上,整部电影制作投资达到4亿多人民币,其中特效成本占比达到50-60%,片中外星人形象所依赖的生物表演类特效,还特地邀请国外顶尖特效团队。参见公众号“综艺报”2019年2月22日发表的《<疯狂的外星人>导演宁浩:拍美国人拍不了的科幻片》一文。。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疯狂的外星人》虽然在票房收益与受众影响层面,难以与《流浪地球》相颉颃(2)电影《流浪地球》的票房为46.8亿元,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的票房则为22.1亿元,两部影片分列2019年国产电影票房排行榜第2、6位。票房数据参见刘汉文,陆佳佳. 2019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J]. 当代电影,2020,(2):15-26.《流浪地球》在豆瓣网、猫眼电影上的评分,分别为7.9分(评价人数为1532828人)、9.2分(评价人数为245.8万人),《疯狂的外星人》在豆瓣网、猫眼电影上的评分则分别为6.4分(评价人数为567057人)、8.5分(评价人数为101.9万)。数据统计截至2020年6月6日。,但对于中国科幻电影而言同样意义不凡。正如陈旭光所指出的那样,“《疯狂外星人》呈一种‘中度工业美学’走向,在‘本土化’、现实性、‘作者追求’、荒诞喜剧风格等方面为中国特色类型杂糅的科幻喜剧片探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1](P113-122)。
发表于2001年的短篇小说《乡村教师》讲述了一个乡土文明与宇宙文明相接触的荒诞故事:身患肝癌的乡村教师李宝库,为了教化偏僻乡野的蒙昧孩童而鞠躬尽瘁,银河系中的高等外星文明碳基联邦,为防御星际战争而构筑隔离带,并对隔离带中不符合文明等级的恒星进行摧毁,前来甄别地球文明等级的碳基联邦,偏偏选中了李宝库的几位学生,而他们则凭借老师临死前传授的“牛顿第二定律”意外拯救了地球。小说表面上是一首对于乡村教师群体的颂歌,实际上是以鲁迅的“铁屋子”比喻为核心,建构起的一则批判蒙昧和崇拜科技的启蒙寓言。
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只保留了原著的荒诞色彩,而彻底更改了故事情节:自诩高等文明、原本要同地球建交的外星人,意外坠落中国某地世界公园,并由此在外星人、以耍猴人耿浩为代表的中国底层、C国特工为代表的外国势力之间,上演了一出你争我斗的喧哗闹剧。那么,与好莱坞式科幻电影相比,《疯狂的外星人》是如何构建起显著的本土意识的?接下来,本文将把影片放置在宁浩作品序列和国产科幻电影发展链条中,尝试从“混杂性”“作者性”“传统性”“世俗性”四个方面,进一步阐释其独特的影像风格及其在当前时代语境下的产业与文化意义。
一、混杂性:类型杂糅、话语狂欢与文化碰撞
类型电影作为一种强调商业实践与大众趣味的惯例系统,往往在故事情节、视觉图谱、人物形象等方面形成较为程式化的特征。如果从类型电影的视角考察, “科幻电影”(Science Movie)虽然和其他类型片一样都并非一成不变的分类系统,但整体上看还是有较为统一的观念与范式,例如对于未来世界的想象、对于科学技术的观照、对于视觉奇观的呈现等等。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显然并非一部典型的科幻类型片,而是一出混杂了纷繁元素的喧哗闹剧或曰癫狂喜剧,在类型元素、叙事手法、文化背景等诸多方面体现出强烈的混杂性。
影片的混杂性首先体现为科幻为辅、喜剧为主的类型杂糅特征。自2006年凭借《疯狂的石头》一鸣惊人后,宁浩的电影创作几乎都专注于喜剧片领域。经过此后的《疯狂的赛车》(2009)、《黄金大劫案》(2012)、《心花路放》(2014)等影片的历练,他逐渐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喜剧风格,尤其擅于展现底层小人物的悲喜人生。《疯狂的外星人》实际上延续了宁浩的喜剧路径,与其说是一部科幻片,不如说是一部披着科幻外衣的喜剧片。影片中科幻元素的运用,主要体现在“外星人接触”“外星人降临地球”这一故事背景的设置,以及外星人、外星飞船等形象的刻画,尽管其视觉特效耗资不菲。类型电影的惯例系统随电影工业演进与大众审美变迁发展至今,已经越来越体现出类型杂糅的趋势,类型元素的糅合最终往往形成一种混合类型样态。不过,混合类型中往往也会存在主类型元素与次类型元素之分。与《流浪地球》较为纯粹的科幻片样式相比,《疯狂的外星人》可以说是以喜剧为主类型元素,以科幻为次类型元素。
《疯狂的外星人》的这种混合类型样态,自然与宁浩本人深耕喜剧片有关。不过,如果将这部影片放置在中国科幻电影发展史链条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其与此前中国电影创作传统的深层次关联。长期以来,中国电影生产格局中缺乏类型片意义上的科幻电影。在科幻电影大幕初启的20世纪80年代初,尽管张鸿眉执导的《珊瑚岛上的死光》(1980)以可圈可点的类型水准投石问路,但随后中国科幻电影创作却在“科文之争”(3)所谓“科文之争”,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中国文学界、科学界等掀起的科幻文学应该归属于科学还是文学的论争。这场论争反映出科幻文学等科幻文艺长期以来的特殊处境:作为儿童文艺而在文艺界难登大雅之堂,同时其作品中科学幻想的科学性又备受质疑。“科文之争”诞生于新时期现代化进程重启的特殊语境下,并很快与1983年发起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合流,许多科幻作家被质疑宣扬伪科学、传播不良思想而备受批判,导致“科文之争”从学术论争上升至政治批判,并由此致使中国科幻文学的发展之路大为延宕。、电影创作的想象力匮乏、电影工业水平的落后等多重因素的制约下迅速陷于沉寂。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虽然也涌现出诸如《错位》(1986)、《男人的世界》(1987)、《霹雳贝贝》(1988)等多部带有科幻元素的电影,但上述作品只能视为寄生于喜剧片、悬疑片、儿童片等样式中的“准科幻电影”。例如,黄建新执导的《错位》就借助主人公赵局长制造仿生机器人以代替自己应付文山会海的故事,批判了官僚主义与形式主义,可谓中国电影史上最早的披着科幻外衣的荒诞喜剧电影。王为一执导的《男人的世界》同样也是借助科幻设定构想了一个没有男人的未来世界,整个故事的基调也颇具荒诞喜剧色彩。由此可见,《疯狂的外星人》的科幻为辅、喜剧为主的类型杂糅特征并非孤例,早已是中国科幻电影创作的一种传统。
其次,影片的混杂性还体现在巧合、戏仿、恶搞等手法的大量运用所形成的话语狂欢特征。狂欢化叙事向来是宁浩喜剧电影的显著特质。本文所谓的“狂欢化叙事”,其理论资源主要借自巴赫金的狂欢化诗学,指的是一种大众化的、戏谑式的、无拘束的话语模式。不过《疯狂的外星人》既没有重复《疯狂的石头》《疯狂的赛车》的多线“烧脑”路径,也没有重复《心花怒放》《无人区》的公路片模式,而是重点营造一种自由平等的狂欢氛围。影片设置了大量的巧合片段,例如外星人恰巧坠落至世界公园,又意外被误认为低等灵长类动物、外星人恢复超能力但又因醉酒而意外法力尽失、C国特工来袭但外星人又碰巧被泡酒等等。诸如此类巧合桥段的设置不断打破受众的期待视野、强化影片的黑色幽默色彩,也不断颠覆和重构影片中诸多人物形象之间的关系。影片还频繁运用“戏仿”的手法,例如对《E.T.外星人》(1982)、《战狼》(2015)、《邪不压正》(2018)等电影的有意“戏仿”,就形成了有趣的文本互文关系,令观众会心一笑。此外,影片的“恶搞”手法更是无处不在。与“戏仿”手法强调对源文本的滑稽模仿不同,“恶搞”手法的否定性、反讽性更强。《疯狂的外星人》中,外星人沦为猴戏表演者与泡酒药材、C国特工被猴子所假扮的外星人戏耍等桥段,都是以“恶搞”的方式颠覆观念认知与情节走向。正是在上述“巧合”、“戏仿”与“恶搞”等诸多段落的混杂下,影片的话语狂欢特性表露无疑。
再次,影片的混杂性还体现在多重文明的交织和碰撞。影片设置了外太空文明、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三大文化背景,外星人/C国特工的闯入意味着异质文明对本土文明的冲击。可以说,影片所要探讨的一大问题就是异质文明之间该如何共处,其多重文明的交织尤其体现在叙事空间的设置上。除了外太空、海外空间等多样空间之外,影片的主要叙事空间是中国某市颓败的“乐华世界公园”。作为微缩与混合景观的世界公园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涌现出的独特产物。从北京世界公园、深圳世界之窗到长沙世界之窗,这类主题公园在20世纪90年代接连出现,无一不以集中复制世界著名地标性建筑的方式展现中国走向世界的冲动、展现国人对于神秘外部世界的向往。不过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外交流日益密切,世界公园这种独特的人造景观也逐渐边缘化,在失去原初的文化与审美功能的同时,日益演变为一种带有特定历史感的文化符号。可以说,世界公园在一定程度上可谓福柯所描绘的“异托邦”(Heterotopias),它既是与虚无缥缈的乌托邦不同的现实空间,又是与其他现实空间不同的异质空间或他者空间。影片将叙事空间设定在这样一个独特的混杂空间中,更进一步强化了历史与现实、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张力关系。
二、作者性:荒诞风格与解构主义
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在类型元素、叙事手法与文化背景等方面表现出的显著混杂性,显示出创作者并不想单纯创制流水线上的大众化产品,而是试图形成独特的个人风格,传递某种特殊的价值理念。宁浩自己就曾鲜明地表示:“我不想拍‘爆米花’电影,不想拍这种流程的电影”[2]。可以说,《疯狂的外星人》是一部有意识凸显“作者性”的电影,因此从类型电影理论的角度来观照该作品,多少会有些削足适履,而从“作者电影”/“作者论”的角度加以阐释,就显得更为恰切。如果说“类型电影”强调的是大众欣赏趣味,那么“作者电影”凸显的便是审美风格创新。如同巴赞所言,“作者论”“是关于辨别艺术家的建树的价值体系,即在影片主题和技术成本之外,风格先于个人”[3](P44-49)。
《疯狂的外星人》的作者性,首先体现在影片所流露出的鲜明荒诞风格。从狭义上讲,“荒诞”(Absurd)实际上是西方现代化进程导致人类精神异化的语境下,所产生的一个独特的哲学与美学范畴,主要指代的是个体在现代化世界中的精神困境。不过,如果从广义上看,“荒诞”强调的是一种人与人、人与世界之间的非理性、不协调状态。如前所述,影片虽剥离了原著《乡村教师》的基本情节走向,但是却保留了其荒诞内核:宇宙高等文明与地球低级文明的意外接触。影片中,不同文明和物种之间在最初大抵构成了“外星文明——西方文明——中国文明(马主任—大飞—耿浩)——动物(猴子欢欢)”的等级体系。但不同形象之间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和等级,在影片中一次次地被嘲弄与颠覆。严肃的星际外交场景,被C国宇航员的社交自拍所破坏、最高等的外星人沦为最低等的猴子、目中无人的C国特工被无情戏耍、中国酒桌文化意外拯救地球文明,诸如此类不合常理的桥段,更进一步加剧了影片的黑色荒诞意味。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中国喜剧电影创作中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荒诞喜剧的大量涌现。尽管早在20世纪80年代,黄建新的《黑炮事件》(1985)、《错位》(1986)等影片就在荒诞喜剧领域投石问路,但整体上看中国长期缺乏荒诞喜剧电影诞生的文化土壤。但在21世纪以来,随着宁浩的《疯狂的石头》等影片的带动,荒诞喜剧电影小成气候,接连出现了《斗牛》(2009)、《杀生》(2012)、《驴得水》(2016)、《一出好戏》(2018)、《无名之辈》(2018)等代表性作品。荒诞喜剧电影的特质在于寓真实于荒诞之中,这类影片“注重展现人物之间或人物与世界之间的不协调、非理性,常常呈现出悲喜杂糅的风格,在反常悖谬事件的叙述中,流露出强烈的哲理化、寓言化气质,并在超现实意味的影像中,表现出鲜明的现实主义指向”[4](P69-73)。
《疯狂的外星人》的荒诞风格中,同样蕴含着强烈的哲理化、寓言化气质,这也是影片的“作者性”的第二个体现:以彻底的解构主义反思人类的等级秩序、英雄崇拜、霸权主义等价值理念。
影片的解构主义首先体现在对于社会地位、文明层级等等级秩序的解构。导演宁浩在接受采访时就指出:“这部电影谈的是一个歧视链问题,主题上不是讲善恶的,是告诉观众别骄傲、别自大、别瞧不起别人”[5](P97-102)。影片中,主人公耿浩作为耍猴为生的传统艺人,不仅要在民间艺术濒于灭绝的境遇中求存,更不得不面对自我社会地位边缘化与底层化的现实。片中多次出现的“臭耍猴的”一词,是他摆脱不掉的社会底层身份标识。面对来自外星人、世界公园领导、猴戏观众等不同主体的不解与歧视,他多次表达自己的鲜明立场:“咱这国粹不也得人人平等不是”“咱靠手艺吃饭,咋就低人一等了”“你们外星人也得讲究个人人平等”等等。不过,看似处于等级体系与鄙视链条低端的他,在耍猴表演或驯顺外星人的过程中,其实时刻在彰显自己作为人类驯化者的优渥感。耿浩尚且如此,拥有超能力的外星人、不可一世的C国特工等,更是表现出根深蒂固的高人一等的意识。影片有意不断打破不同主体之间先在的等级秩序,以此来彰显平等兼爱的重要性。
在解构等级秩序的基础上,影片其次体现出对于英雄和崇高的解构。影片中有这样一个颇为有趣的段落:国外的戒酒互助会上,一个身穿美国队长T恤的亚裔青年男子,宣称可以从超级英雄T恤中汲取能力,以帮助自己完全戒除酒瘾,但却被在场的C国特工约翰无情嘲讽和打击。在这一段落中,约翰亲自解构了好莱坞电影中所塑造的超级英雄的崇高形象,但符合好莱坞电影中特工英雄形象的惯例书写,而他在接下来执行寻找外星人任务时,很快就成为被解构的对象。影片用了戏弄同事、肆意杀戮等诸多细节,来刻画这一人物嚣张跋扈的性格,但他的英雄形象,不仅在世界公园照片的误导下一次次弱化,并最终在舔舐带有排泄物的基因球时,被无情戏耍和彻底瓦解。
《疯狂的外星人》解构等级,所要解构的根本上是等级差异带来的霸权,这种霸权既有微观的生活与身体层面,也有宏观的国际文化与政治层面。影片用了大量的笔墨展现主人公是如何按照驯顺猴子的程序来训练外星人的,并反复提及指代条件反射定律的“巴普洛夫原理”。实际上,整部影片的反思与解构基本都建立在“耍猴”这一仪式之上。“耍猴”的过程具有霸权性与戏耍性的双重特点,它既是一种戏耍表演,同时也是一种权力关系的展现。耿浩作为耍猴人对于猴子的训练,所要追求的是一种“驯顺的身体”,追求的是等级差异带来的权力快感。这一场景鲜明地体现出了福柯所谓的权力对身体的规训:“肉体也直接卷入某种政治领域;权力关系直接控制它,干预它,给它打上标记,训练它,折磨它,强迫它完成某些任务、表现某些仪式和发出某些信号”[6](P27)。
“耍猴”这一微观仪式场景中所蕴含的权力关系可以进一步扩展至其他领域。影片中,C国作为世界大国屡屡践踏他国主权,在他国领土上肆意展现自我霸权,却最后机关算尽、颜面尽失,其大国沙文主义受到了无情地戏耍与嘲讽。影片后段有这样一个颇有意味的段落:外星人的灵魂借助猴子的身体复活,发现自己的身体在经历泡酒后已经僵硬,盛怒之下,他扬言要清除人类垃圾文明,并将象征人类文明的世界公园破坏殆尽,不过在一番强力反抗与反击之后,他又出人意料地败给了敲锣和香蕉带来的生理上的条件反射。在这一段落中,外星人/猴子的合体,要反抗耿浩/C国特工所代表的人类霸权,但外星人的超能力所带来的统治地位,又被后者所戏耍与消解,这可以说点明了整部影片的主题:消解一切不平等,反抗一切霸权。正是通过荒诞风格下的解构主义,影片体现出了一部“作者电影”所独具的审美创造精神与文化反思精神,也由此体现出了它不同于好莱坞类型电影的独特本土文化身份。
三、传统性:文化符号的调用与改写
考察《疯狂的外星人》的本土意识,一个不可或缺的视角是影片中所蕴含的驳杂多样的传统文化元素与价值理念。对此宁浩就曾表示,“想拍一部只有在中国文化背景下才能拍出来的电影”[7](P97-102)。由于拥有悠远的历史和文化传统,与好莱坞科幻电影相比,中国科幻电影创作,更易于调用各类传统文化符号来为我所用。以上世纪80年代科幻电影为例,电影《错位》就在主人公的梦境里构筑了老子的形象,建构了荒原之上象征传统和中国的老子与象征现代和西方的电视机对坐的独特景象;电影《霹雳贝贝》的结尾,影片选择让主人公贝贝在万里长城这一重要的建筑空间与文化符号之上,等待外星人降临并助其从超能人变回常人,以此表达创作者解构偶像崇拜的深层意图。而在《疯狂的外星人》中,创作者正是将方言与英文、传统民族音乐与西方演奏方式、民间猴戏与星际外交等加以混搭,从而形成了土洋结合、中西混杂的独特风格。当然,影片中传统性最为显著的体现,在于对猴戏、孙悟空、火锅、酒这几种文化符号的调用或改写。
首先,影片将民间猴戏与孙悟空这一家喻户晓的神话人物及其故事相勾连,在神话挪用中巧妙彰显主旨。在中国文艺创作中,恐怕很少有神话角色可以像孙悟空一样不厌其烦地被不同时代的创作者们所挪用与改写,不断以新的故事与形象来承载不同的创作意图、展现不同时代的国民心理与感觉结构,最终构成了“一则光谱丰富的‘中国故事’”[8](P46)。当然,尽管故事纷繁多变,但孙悟空的“反抗者”形象却几乎稳固不变、深入人心。电影《疯狂的外星人》同样挪用了孙悟空“金猴奋起千钧棒”的反抗精神,但却将其移植到了一个中国、西方与外星球等多元文化相交织的特殊语境中。影片将主人公耿浩耍猴的场地,命名为“花果山大舞台”,大舞台的主背景是一座硕大无比的五指山,这种空间上的象征意味再明显不过:它指代着耍猴人/高等级与猴子/低等级之间的关系是如来与孙悟空之间的关系。外星人在影片中反复被戏耍,甚至最终沦为泡酒药材,而在忍无可忍之下,他的精神和猴子的身体共同化身为孙悟空形象,反抗五指山背后等级森严的权力关系。不过,影片改写孙悟形象的独到之处在于并没有仅仅强调其反抗的一面,而是建构起了反抗者/被反抗者两位一体的形象,以此达到前文论及的解构一切等级、崇高与霸权的目的。
无独有偶,在2019年,还有另外一位同样以“反抗者”形象家喻户晓的神话英雄被改写,那就是哪吒。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不仅高居该年度内地电影票房榜次席,更以面目一新的哪吒形象引发全民热议。将该作品对于哪吒的改写与《疯狂的外星人》中对于孙悟空形象的挪用进行对比不难发现,它们的“反抗者”形象与此前文艺作品中的形塑大有变异,且不约而同地映射出了当下这个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在人物形象上建构了哪吒/敖丙同根同源、你中有我的镜像结构,并将此前哪吒反抗父亲及其代表的父权社会与既有社会秩序的故事,改变为反抗虚无缥缈的、形而上的命运。《疯狂的外星人》虽然借助孙悟空的形象,反抗了具体微观的权力关系和不平等状态,但反抗者最后摇身一变又化为被反抗者,解构代替反抗成为故事的内核。可以说,两部影片中的反抗故事,对应的是“冷战”终结后阶级政治日渐式微以及社会反抗失去共同前景的时代大背景,彰显的是后阶级时代的身份政治。身份政治强调的是“对自身独特的文化身份的特殊性认同,不仅是自我认同,而且要求得到他人的承认,从而获得平等的对待与尊重”[9](P71-81)。而这种身份政治的诉求,正是《疯狂的外星人》所力图传递的核心理念。
除了挪用神话之外,《疯狂的外星人》还通过对于火锅、酒等饮食文化及其背后文化精神的书写,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性。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中,饮食活动往往都不仅是一种生理需求,而是沉淀文化精神的重要象征资源。尤其在饮食礼俗繁多复杂的中国,饮食活动往往作为一种仪式,在家庭伦理与社会交往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以火锅与酒为例,它们在深层次上都展现出国人在为人处世、治国理邦等方面追求调和、中庸、平衡的“和”文化。当然,这种“和”文化是建构在上下有别的等级秩序之上的,尤其体现在社会交往功能凸显,但又不乏糟粕的酒桌文化中。影片中有这样颇为怪诞有趣的一幕:恢复超能力的外星人傲慢地端坐火锅桌前,与卑微敬酒的大飞和表演杂耍的耿浩形成了有趣的对比,三人间的权力关系可谓一目了然。《疯狂的外星人》里对于火锅和酒的呈现,最终是为了展现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同化能力。影片中大飞将外星人泡在酒缸中是一个非常直观的象征场景:作为中国代表性传统文化符号的酒,将对地球文化一无所知的外星人完全浸染,这种浸染不仅是身体层面的,也是精神层面的。值得指出的是,影片并未对这种具有高度濡染性的传统文化的好坏与否,给出一个简单的立场或判断,而是较为客观地展现出来,供观众自己去体味与反思。
四、世俗性:日常、底层与现代性焦虑
火锅与酒作为一种文化符号,体现出了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浓厚的传统性,与此同时它们作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也体现出了影片的另外一重本土意识:强烈的世俗性。本文所谓的“世俗性”,是相对于“超越性”而言的,强调日常性、现实性与实用理性,而非强调对现实的超越。总体来看,好莱坞科幻电影可以说以“超越性”为显著特征,它们往往与现实保持一定的距离,在超越现实的基础上去畅想未来。而中国以往的科幻电影探索,总是难以摆脱现实的束缚,观照现实的冲动常常挤压了自由构想未来的空间。
当然,好莱坞科幻电影虽以“超越性”为显著特质,但并不代表它们就将现实议题束之高阁。许多好莱坞科幻电影所发挥的功能,可以说是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所说的“未来考古学”的方式,其“多种模拟的未来起到了一种极为不同的作用,即将我们自己的当下变成某种即将到来的东西的决定性的过去”[10](P379)。简而言之,好莱坞科幻电影擅于从遥远未来回过头来反思现实,而中国科幻电影则就扎根在现实土壤之中。正如有论者所言,中国的科幻电影创作“在实用主义观念的导向下,倾向于借助科幻形式外壳来反映现实社会中的问题,特别是反映在社会思想转型期,人们对传统与现代价值观态度的暧昧和焦虑”[11](P93-97)。
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的世俗性,首先体现在非常显著的日常生活叙事。为了将外星人坠落地球这一事件表现得更具反差性,影片让外星人深入中国小城,体验了火锅、杂耍、酒、拔罐等各式各样的环节。在耿浩与大飞在街头与江边追逐试图逃跑的外星人一场戏中,创作者们为我们生动展现出了一个由快递、出租车、鞭炮声、杂货店、露天集市等构成的典型而真实的平民生活场景。让不久前还在从事星际外交的外星人忽然置身于这样一个全然陌生化的场景中,更添几分荒诞之感。
具体来说,电影《疯狂的外星人》的日常生活叙事所着力建构的是一个以耿浩为代表的底层平民的生活空间。宁浩的喜剧电影总是善于描画耿浩式的小人物,无论是《疯狂的石头》里的保卫科科长和小偷团伙,还是《疯狂的赛车》里被终身禁赛的自行车手耿浩,他们都作为微不可见的浪花,在时代洪流中挣扎与沉浮,上演各自的悲喜人生。从这个层面来说,《疯狂的外星人》的世俗性,还体现在对底层人物的持续关注。影片中,作为继承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的耍猴人,耿浩的社会地位正如鲜有问津的花果山大舞台一样,是时代的边缘者与多余人。面对众人对于其身份与职业的鄙夷,他一次又一次地忍气吞声,直至最后奋起反抗。影片结尾,面对外星人对自己的一再贬斥,他不顾能力悬殊驾车试图与其决一生死,这是底层小人物的尊严之战。不过颇为值得思考的是,为了更明确地表达解构一切等级与歧视这一主题思想,《疯狂的外星人》并未将耿浩塑造为纯粹的小人物,也展现了他在身处统治地位时,身上所流露出的狂妄狡黠的权力欲望。这种处理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消解了这一人物带给观众的认同感,降低了令人共情和共鸣的程度。
从更深层面上来看,影片对于底层人物的书写,折射出的是中国当下现代化进程中如影随形的现代性焦虑。毫无疑问,四十余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疾如旋踵、翻天覆地的社会进程,随之而来的不仅是经济能力与生活方式的变更,还有文化与精神层面的变化。电影《疯狂的外星人》中,面对准备将花果山大舞台改造为火锅城的马主任,耿浩费劲口舌想要以改造舞台来吸引观众,却被前者无情奚落。在这一段落中,马主任用“你下去”的话语,指使耿浩到许愿池里捡拾硬币,并嘲笑他的猴戏挣得还没有许愿池多。而在许愿池旁边,一个硕大的“日进斗金”的钱币样式的雕塑分外显眼。这一个场景浓缩了整部影片对于现代化进程的思考:马主任与耿浩一上一下的空间位置,折射了他们的社会地位,而马主任对于经济效益的追逐与“日进斗金”的雕塑,显示出这是一个经济逻辑全面压倒精神追求的时代。猴戏的没落与火锅的兴盛,则表明这是一个浅薄的追求口欲的消费主义时代。正是在这种对比中,《疯狂的外星人》表现出了对当下社会伦理秩序失范、传统文化失落的忧思,从而进一步强化了影片的本土意识。
结语
在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日趋成熟的今天,如何在吸收外来技术与经验的基础上,走出一条独特的本土化道路,创制出别具一格的民族电影?电影《疯狂的外星人》是一次很好的示范。混杂性、作者性、传统性与世俗性的融合,使得影片具备了强烈而自觉的本土意识,形成了与好莱坞式科幻电影泾渭分明的影像风格与文化身份。这种本土意识,既是宁浩为首的创作团队的有意追求,也是中国科幻电影创作传统的一次延续,值得借鉴与思考。
此外不得不说的是,《疯狂的外星人》试图消解一切等级差异,试图构筑美好平等的人际关系,但故事并未到此结束。影片结尾的彩蛋展现出了无情的现实:在酒企的销售会上,经历过外星人事件后,被称为“西南猴王”的耿浩正意气风发,当大飞将其介绍给公司徐总时,他伸出手想要握手,却被对方无情地忽略。这个段落里,徐总的豪车、傲慢、西装革履与耿浩的运动装、手足无措形成了鲜明的等级差异。影片选用这样一个彩蛋作为终结,再一次说明喜剧的背后是悲剧,而电影往往只是现实的一种想象性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