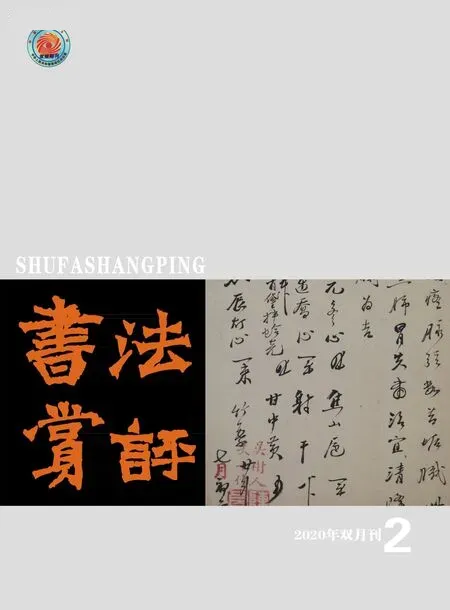山堂梦里频携手:读朱琪《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
付 豪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灿烂,艺术门类也纷繁众多。若推其中最具民族特色者,则非书法莫属。世界诸民族文字种类多矣,然而能独造艺术之境者,则唯独汉字之书法。篆刻与书法向称姊妹艺术,与书法有着千丝万缕之联系,却少见精彩的史论研究佳著。事实上依愚拙见,篆刻理论研治之难,更难于书法理论研究。具体来说,约有如下数种情况。
其一曰文献难以掌握。文献之难于掌握,在于两端。一端是存世文献过于丰富,一端在于其中有用文献太少。文献学家杜泽逊教授曾经说过,先秦的书可以读完,这费不了几年;两汉的也可以,魏晋南北朝的也行;唐朝就不一定了,宋朝就不可能了;元明清,那连门都没有。而篆刻艺术之自觉、文人篆刻之繁盛,恰恰就是在这“连门都没有”的几个朝代中。据知仅有清一代,存世图书就得超过二十万种(这还不计版本差异)。想竭泽而渔占有全部文献是不可能的,想从如此众多的文献当中蒐拾出有用的资料,亦难矣哉!而传统士大夫非儒林中人,即文苑中人,书法尚属余事,遑论篆刻。故而专以篆刻擅名者,多不能闻达于文化界之主流,甚至难免有“匠人”之讥。篆刻文献因得不到足够重视而失坠者不可胜数。清代印学名家汪启淑,曾因进献图书受到清高宗褒奖并得御笔题诗,一时声名大噪。他一生制作印谱据闻有二十七八种之多,而于今能复见于人间者,不及此数之半。如此名家已然如是,何况类似蒋仁这种孤高冷淡的印人?
其二曰文献难以复制。古代没有影印技术,拥有名家真迹的往往是少数财大气粗的收藏家,书法只能依赖碑拓、刻帖才能得到相对广泛的传播。然而,刻手有精粗之别,即便如启功先生所说的“即使精绝之刻技,碑如《温泉铭》,帖如《大观帖》,几如白粉写黑纸,殆无余憾矣。而笔之干湿浓淡,仍不可见”。[1]这般精工的刻手,也绝对无法传达出墨色的浓淡、纸质的精粗,更不必说那些连形貌也不能相符的拙劣之作了。书法一旦通过传统手段进入复制流程,其大量的信息损失决不可避免。而篆刻文献的复制,更有难于此者。篆刻是方寸间的艺术,其巧妙尽在于精微处(特别是善于使用细碎切刀的浙派篆刻)。原钤名家印谱流传不广,且也无法像刻帖一样复制后广为流布:刻帖细节不存,或尚可存其间架章法,不失为一种参考;而印章一旦失其精微,则徒留皮相之复制几乎毫无意义。即使以今天的影印技术,究竟能为印蜕留真几分,还需打个问号。笔者早年所购之《西泠八家印谱》(西泠印社影印出版)收录钱叔盖“大小二篆生八分”印,点画甚为粗壮,以为浙派朱文中之异类,故于此印印象极深。去岁春游沪,于上海博物馆见此印及印蜕,点画居然细如平常,方晓今是昨非。更有甚者,即便同一印章,所用印泥不同,钤印之效果也不能划一。印面钤盖之难如许,边款拓制其难亦可知矣。
其三曰文献难以甄别。文献难于甄别,亦可分为两端,一端曰文字资料良莠不齐,一端曰实物资料真伪混杂。对于篆刻家之地位,前文已经有所涉及。正因篆刻家地位不高、篆刻学科不显,故使得主流文献中难有篆刻的一席之地。而文献之可靠性,又常常是偏重主流文献的。以史籍论,正史之可信度高于方志;以方志论,省志之可信度高于县志。盖方志往往出于乡儒之手,或因桑梓情深,难免夸耀;人情世故,往往避讳;见识浅陋,率尔操觚……如此种种,不一而足,故而前人曾云:“方志之为书,善者少而不善者多,故学者恒蔑视之。”[2]然而许多篆刻家作为地方乡贤,其身世资料之保存,往往依赖方志。但方志之说,如有其他文献足以印证,尚可庆幸;如无可为佐证者,真可谓“死无对证”了,如何取舍,极费斟酌。而其余乡间文人遗文可信度究竟有几分,则更得打个问号。文献如此,实物尤难。书画作伪,古即有之,印章亦难于幸免;而因篆刻艺术的物质载体与书画有异,故其鉴定之难,往往倍于书画,又非深于此道者不能为也。
朱琪先生多年来著意西泠八家研究,所获颇丰,而此《真水无香:蒋仁与清代浙派篆刻研究》(以下简称《真水无香》)即其一端也。今岁拜读新著,颇有耳目一新之感。
蒋仁大名不必多说,然其行迹却如华表之鹤、岭上之云,难于追蹑。朱琪先生此著条分缕析,举凡蒋仁家世、生平、交游、思想、书法、篆刻、诗文无不该涉,于文献资料更有一网打尽、竭泽而渔之势,确如林乾良先生所誉“立马吴山”之作。是作独得之处,以后学拙见,约有如下数端。
其一曰重视印人人格形象的还原。艺术史研究,重视作品者有之,重视史实者有之,重视授受源流者亦有之。唯独于艺术家本身形象,往往缺乏关注。艺术家之人格思想是其艺术发端的重要基础;甚至说,真正的艺术家,他的人生本身也是一场行为艺术。就如前人论诗说,作诗时才有诗的决不是诗人,真诗人不作诗时也有诗。我们平时的目光,往往只流连于朱白之间,斤斤计较于刀法、字法、章法。但在《真水无香》一书中,可以看到作者勾勒出的一个篆刻艺术之外的蒋仁形象:他清贫孤高,柴门长掩,懒于交接,知己三五,以至于最后潦倒终身。倘若我们对蒋仁作为“人”的本身能够多加了解,他的人格形象也更加能够和他的篆刻艺术相印证,让我们得到更多篆刻之外的东西。
后人审视古人,难免有种“隔帘望月”的朦胧感,产生各种先入为主的偏差。“西泠八家”作为浙派篆刻的领军人物,我们往往只留意到他们的艺术取向大略相似,却很少考虑各自人生际遇以及人格形象的不同。黄小松和蒋山堂年龄相仿,交谊颇深,乃至互有印章酬赠;但是实际上,黄易对于入仕为官是持积极态度的,他的官员身份也为他的金石学活动(主要是碑刻寻访、拓片搜求)带来了极大便利。见识益广,学力益深,更兼生活顺遂,不必为生计发愁,故而所作深醇典雅,一派学人气象。但是,诚如蒋仁所云,篆刻之道,不尽关乎学力。所以尽管蒋仁布衣终身,懒于交接,不仅生活潦倒,见闻也远不如黄易。但是,他的篆刻依然取得了极高的成就。我们不得不说,他作为清逸出尘的文人品格,在极大程度上外化为高超的篆刻艺术。当认识到这一点后,或许我们会更加认识到蒋仁篆刻艺术的可贵。
其二曰重视印人创作心路的探求。学术研究需要严谨客观,这固然不错。然而文学艺术的研究,又难免具有主观性。因为无论是文学艺术的创作还是解读,总会有个人感情因素掺杂其中。但这并非不严谨,因为否认文艺研究还原作者创作心路的正确性,实际上就是否认文艺学科相对于自然科学的特殊性。文艺研究者不能只懂历史、懂文献,还应当了解文艺创作本身。《真水无香》一书中,作者特地拈出“真水无香”一印,试图还原蒋仁创作此印前后的心路历程,可谓是难能可贵的。作者在对蒋仁印章边款的研究中,又特地拈出“雪”“醉(酒)”“雨”等关键词,揭示出雪景、美酒、雨天往往成为蒋仁代表性作品的催化剂。这些关键词给人的感觉,又恰恰与蒋仁及其篆刻艺术的精神气质若合符契,这就不能不令人钦佩作者对于印人心迹的捕捉了。而作者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和他本人对于篆刻艺术(尤其是边款艺术)的深刻理解是密不可分的。
其三曰重视印章边款的综合价值。边款除了作为印章本身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外,其本质上是一种“文本”(text),其中常常既有客观史料,又有作者本人自述甘苦的内容,弥足珍贵。读《真水无香》一书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于蒋仁印章边款的利用可以说是全方位的。行迹交游这样的客观考述自不必论,而对于印章边款的文学价值以及其中承载的创作心理的认识更为引人瞩目。
作者对于印章边款价值的重视,还有一篇《消逝的维度:印章实用功能的消解与当代篆刻边款叙事功能的式微》可供读者诸君参阅。[3]当代篆刻边款叙事功能衰落的原因是多方位的,但最为根本的原因还是当代篆刻创作群体文化修养水平的不足,这使得边款艺术走向了以夸耀技术为目的的极端。现如今篆刻创作者在边款上下的不是“内容”(“文本”)的功夫,而是“形式”的功夫,但是边款的目的不仅仅应该是夸耀刀法或者 “书此以记岁月”。事实上苍白的时间是没有生命的,因为我们无法透过这些时间窥探到作者的内心世界,这种“匠化”倾向,是值得当代篆刻警惕的地方!
朱琪先生这部《真水无香》借蒋仁所言,未必尽关学力。雅逸的文人情怀,高超的篆刻实践水平,扎实的文献资料功底,共同造就了这部流派印史研究的佳作。其中虽偶有手民之误,[4]然终属白璧微瑕,不碍是作之必传也。
谨以自撰七绝二首为赞:
旧事西泠又几秋,微茫华表鹤难留。山堂梦里频携手,异代知音亦可求。
印人心迹杳如云,印学消磨賸几分。赖有江南朱司马,[5]积年故纸扫沉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