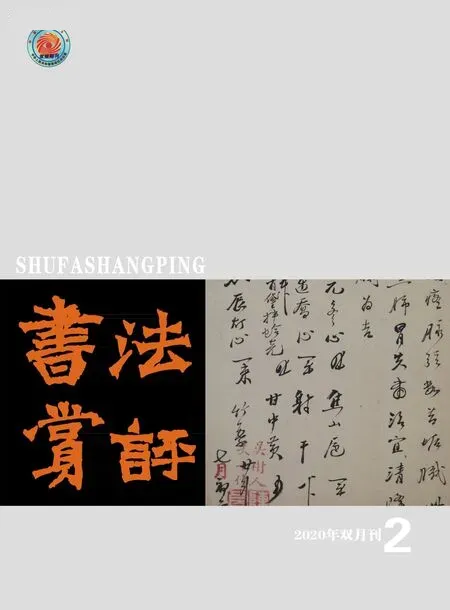李瑞清“兰亭观”的转变及缘由探析
朱 琳
导师评述:
朱琳目前是杭师大美术学院美术学专业(书法篆刻史论研究方向)的二年级学术硕士生,她在研二上学期完成的这篇论文经过多次修改得以刊发,是对她前一阶段学习和思考的一个肯定。虽然论文尚有不足,偏于稚嫩,但我非常乐意就此做出评述和推介。主要原因在于以下三方面:一、该研究基于作者的学术兴趣点,有较明确的问题引领。二、有较扎实的文献梳理和解读,前期的学术训练和研究铺垫起到了支撑作用。三、研究具有较好的持续性,由点至面再至立体,逐步深入。这三方面的看法,当然并非只建立在这单篇论文的基础上。朱琳自入学不久,即显现出格外勤奋好学和善于思考的品质,课外我经常被她“拦截”追问,并不时收到她“塞”过来的额外论文,因此交流更为频繁。
作者对于晚清民国时期的书法教育一直存有浓厚的兴趣,试图梳理此期有代表性的书法教育者及其教育理念、书学思想。前期她在撰写另一论文《李健<金石篆刻研究>中的“古器物图”探析》时,对李健与李瑞清的师承、渊源关系已有一定的认知。李瑞清身为两江优级师范学堂督学,是晚清民国书法教育史上的关键人物,其门人胡小石、姜丹书、李健后来也都身肩上海、南京、杭州等各地教职,因此追索李瑞清的教育理念及书学思想成为下一个目标。作者认为,李瑞清的“兰亭观”虽是其书学思想的一个局部,但先聚焦于这个“点”,进而将视野扩展,探究李瑞清对古代碑帖经典的观念及促成因素,是一个可行的研究路径,有助于全面、系统地把握李瑞清的书学思想,乃至更大范围的晚清民国时期书家的思考和选择。因此,她对《清道人遗集》中的碑帖题跋进行了较细致的解读,又对李瑞清与同时代书家的交游和学术大环境加以考察,最后得出的观点便聚结为这篇论文。朱琳在撰写这篇论文期间,正是学位论文的开题阶段,经过反复验证,她将选题和研究方向仍锁定于“晚清民国书法教育”,因此前期的这些点滴或片段思考,与后期的研究必然有紧密的联系,我期待她能够不断推进,对这一时期的书法史、书法教育史逐步建立起更为立体、深厚的学术认知。
研究生的教学和培养,涉及很多层面的问题。从长远来看,硕士生阶段是进入专业领域、从事学术研究的“起点”,而学术论文的写作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环节。这一环节中,尤其需要培养的,一是问题意识(学术敏锐度和思辨能力),二是文献能力(对文献史料的收集、解读和运用能力)。我作为导师,理当与学生共同努力、不断锤炼。
导师:徐清(杭州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
20世纪初,新、旧学术思想相互交汇,书家、学者的书学观念亦体现出这一时代的印记。李瑞清(1867-1920)作为晚清民国书法史上“金石派”的代表人物,[1]其独特的书画造诣早已为书法界、美术界所关注,其作为金石学家、书学教育者的身份及与此紧密相关的学术思想也受到了学界的重视。以往研究者对李瑞清及晚清民国书家的探究已取得诸多成果,但是仍有值得继续推进的空间。笔者试以李瑞清有关《兰亭序》的题跋为基础资料,对其“兰亭观”加以分析,借此梳理其帖学观念及促成因素,以期更全面深入地理解李瑞清的书学思想和书学教育理念,进而窥知晚晴民国时期书学发展的特质。
一、李瑞清“兰亭观”的转变
李瑞清早年受翁方纲、阮元、何绍基等前辈金石学家的影响,从事金石拓本的搜集与考订,并据拓本观察古代书体与风格的历史变迁,尤其青年科考时期,对阮元的碑学思想较为推崇。[2]根据夏寿田的记述:
“岁戊戌复相遇京师。余赁庑晋阳寺,髯与清道人同居临川馆。髯与清道人至相得,约为兄弟,朝夕龂龂论书家南北宗,又各出唐宋人画相夸诧,髯得意时,辄声震屋瓦。”[3]
可知,李瑞清在赴京师科考(1898-1899)期间,曾与曾熙反复讨论阮氏的南帖北碑论。李瑞清的《玉梅花庵书断》中,也有与阮元南帖北碑论相近似的言论:“书学分帖学、碑学两大派,阮云台相国元以禅学南北宗分之,帖学为南派,碑学为北派。何谓帖学?简札之类是也。何谓碑学?摩崖碑铭是也......碑学之中兴,自阮相国始,以南北分宗,其论甚辩,然究不确。阮既倡碑学,至邓石如、包慎伯是其后劲,今之书家,莫不人人言碑矣。邓书全从碑入,包则手写帖而口言碑,然著有《艺舟双楫》,于碑学颇多发明,不能谓为无功也。”[4]他又论说道:“南朝士大夫雅尚清淡,挥塵风流,形诸简札,此帖学之萌芽也。唐太宗好《兰亭》,于是又唐一代书家,无不学王者。苏灵芝欲展《兰亭》为碑,此以帖入碑之始。其书实伤婉丽,所谓俗书之祖也。”[5]这表明李瑞清早年颇受阮元书论及碑帖发展观的影响。而对于《兰亭序》,李瑞清在阅读了阮元以及光绪学人李文田(1834-1895,字仲约)的考证、著述后也深有感触,《兰亭序》文本内容和文字书写的真实性一度成为他关注的重点。
李瑞清《跋自临兰亭序》(1912年后)云:
“余生平不解《兰亭》,颇为沈乙盦先生所诃。然不能违心随声雷同以阿世。顺德李仲约侍郎,有三可疑之说,如道人胸中所欲语。今世所传《兰亭》与《世说新语》所载多异,‘莫春’作‘暮’,‘禔’作‘禊’,‘畼’作‘畅’,唐以来俗书也,晋代安得有此?此余所大惑也。”[6]
李文田曾在《兰亭序跋》中,从文本角度指出《兰亭序》有三个可疑之处:一是《兰亭》用笔与现存的晋碑不同,唐以后《兰亭》并非是梁以前的《兰亭》;二是《兰亭》的篇幅比《金谷序》的较长,应是隋唐人根据晋人偏好而任意添加;三是《兰亭》与《世说新语》的注所引不同,且与王羲之文集不相应。[7]李瑞清不仅对李文田的质疑表示认同,还进一步举证了“暮”“禊”“畅”三字,认为它们是唐代以后出现的俗字,不符合东晋的字形写法,因此《兰亭序》的真实与否令人疑惑。
然而,李瑞清在鬻书沪滨期间(1912-1920)对《兰亭序》的态度已开始产生变化,他并不一味地纠结于《兰亭序》的真或伪,而是逐渐倾向于从更宏观的书法史层面,对其书学地位和价值加以认知,并以自己的理解来临写《兰亭序》。
这种变化是逐渐产生和深化的,在上文引述的这段李瑞清《跋自临兰亭序》中,他还说道:“顷见曾季子、郑苏戡所临《兰亭》,郑则自运,尽变其面,曾则以率更法为之,‘定武’嫡派也。余则略参以篆隶笔作此。”[8]李瑞清看到曾熙临《兰亭》得欧本笔法之精妙,而郑孝胥则完全改变了《兰亭》原貌、纯出自运,因此他也尝试以另样的方式来写兰亭,即参用篆隶笔法。1914年,李瑞清在跋《定武兰亭肥本》时,强调了《兰亭序》的笔意古法:
“自来言帖者莫不首推《兰亭》,宋时士大夫家刻一石,游丞相一人刻五百之多,故以定武石刻为第一,以为不失古法,而肥本最为难得。此本墨色黝古,用笔浑厚,犹有钟元常风度,如‘欣’字末画翻落,章草笔也。‘向’‘因’‘固’诸字,汪容甫先生谓似《始平公》,非得此本,何以证其言之非诬。”[9]
李瑞清称赏《定武兰亭肥本》保留了钟繇的笔法风貌,收笔的翻出体现了章草笔法。此后,李瑞清在1915年《跋兰亭六种影印本》中,又对《兰亭序》存世版本有所梳理和探讨:
“《兰亭》为书道一大关捩,茧纸既入昭陵,‘定武’欧模耳,只能以之求《化度》,右军真面不可复见,仍当于唐贤中求之。唐人摹《兰亭》者以欧、褚最称于世。余曾见虞摹于徐叔鸿丈斋中,薛摹素未之见。薛本自褚出,而此本独凝静绝,无褚法,于此或反可以想象右军‘玉枕本’实从‘定武已损本’出。‘颖上本’世传为褚书,与‘神龙本’殊,然有烟霏雾结之妙,可宝也。”[10]
李氏认为:学书者可从唐代书家的模本中,窥探右军书法面貌,其中尤以欧阳询和褚遂良的临本最为著称;“玉枕本”虽然没有体现褚遂良的笔法,但体现出笔法的凝静,应是出自“定武已损本”。
1915年,曾熙在题跋中提及:他与李瑞清“共几研廿有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见,今则服膺予论”。[11]曾熙认为书学应沟通南帖北碑,他的书法善用汉隶圆笔、融合方圆,故自称南宗。这条记录也佐证了这一时期的李瑞清已由服膺阮氏的南帖北碑论,转为认同曾熙的观点。曾熙在《跋清道人节临六朝碑帖》中,也针对阮元南帖北碑论提出过自己的见解:
“《晋书》《南北史》皆唐人所修,阮于《北史》所称崔悦、卢谌等善隶工草,则信为有家法,右军传中善篆隶书为古今之冠则疑,援史品题,谓世不传右军隶法则可。至疑右军不能为隶,大令不解榜书,所谓非惑也,乃谬也......阮氏执南宋以来辗转勾抚,真伪混杂之阁帖,几疑江左风流,尽出渡江衣带一帖,何异见今日僧子诵经,即奉为如来法耶......近敦煌石室经卷,见有北朝书章草,以证沙简中晋人手札,并可悟南北行草同源之妙,惜阮氏不及见也。”[12]
曾熙指出:阮元因时代局限,未能对新材料进行研究,对王羲之认识存在缺憾,南北碑帖论也多有偏颇。这样的见解和认识,对李瑞清原有的碑学观念有所撼动。
李瑞清在《跋裴伯谦藏定武兰亭序》中,更直接地表明了自己对《兰亭序》的肯定:
“有唐书家无不宗右军者,犹宋书家之无不学颜,国朝书家之无不学董,其风尚然也。虽时代递嬗,所师各殊,然无不推右军为不祧之祖。右军行书于世者,无丰碑巨碣,但有笺简、尺牍之属。其最著者,世称《兰亭修禊帖》,其时欧、褚诸家均有模本。欧模极近右军,今所谓‘定武本’是也,历代书家无不宝之,奉为模范。余学北碑二十年,偶为笺启,每苦滞顿。曾季尝笑余曰:‘以碑笔为笺启,如载磨而舞,所谓劳而寡功也。’比年以来,稍稍留意法帖,以为南北虽云殊途,碑帖理宜并究......论古今书法之源流变迁,使知此帖为古今书学一大关键,要非阮芸台奋其私说所能革命也。”[13]
李瑞清认识到:虽然时代递嬗,但王羲之书法依旧是书家学习和继承的“不祧之祖”;结合自身二十年的学碑经验来看,纯以碑派笔法书写简札,容易板滞,因此临习法帖、碑帖兼涉,方是通途;《兰亭》是书法发展史的关键节点之一,其价值绝不是阮元北碑南帖论可以抹杀的。这段题跋也印证了曾熙所说,李瑞清对阮元北碑南帖论的前后态度发生了转变,由服膺转为质疑和反思,对帖学标杆《兰亭序》的态度也因此随之转变。
综上,李瑞清在1912年鬻书沪滨后,没有将《兰亭序》的研究内容局限在单一的考证层面,对《兰亭序》的态度也不再是单纯的质疑真伪,而是转从书法源流发展史的研究角度出发,以书法史观念重新看待《兰亭序》的传承脉络,肯定《兰亭序》的历史地位和价值,并提出要以篆隶笔法临写《兰亭序》的见解。
二、内因:李瑞清对书学源流发展的再认识
在阮元、何绍基南北书派论的影响下,李瑞清与其他的金石学家前辈一样,在研究中注重字义的考证、名物的解释,以及拓本校对、考证;与前人不同的是李瑞清更为注重对书法史源流的考述,[14]这也成为促使他日后能够反思、修正碑帖观念的契机。且李瑞清在南京任两江师范学堂监督时(1903-1911),与端方交游圈中的金石学家、碑帖收藏家颇多交游,有机会寓目并参与校对大量的拓本,饱览端方、杨守敬、王孝禹等人丰富的收藏,[15]为其书法史源流的考述提供了大量的资料,拓宽了其学术视野。
自19世纪末起,甲骨文、西北简牍等新材料的陆续出现,引发学界的髙度关注,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收藏家、学者的图录、研究著作相继出版,这些成果同样引起李瑞清的关注。[16]
出于梳理书学发展史的契机,以及朴学家整理古代文献的促动,李瑞清对所见到的古代文字、图像材料进行整理比对,即:对商周甲骨文、金文,秦汉篆隶、六朝隋唐楷书进行追本溯源、划分流派;并将研究范围拓展到钱币、砖瓦、镜铭、度量、权衡、陶器等器物上,对阮元的关于古代书体、风格考据式的研究范围进行拓展,至尚未得到充分关注的商周青铜铭文也成为书法研究的内容,尤其是新发现的文字材料如甲骨文、西北简牍也被他及时纳入到观照的系统中,这为李氏在阮元的研究基础上进行推进和反思,提供了新的佐证材料。此后,李瑞清对商周迄于隋唐的书体与书法风格,进行大量深入的分析,并将此研究方式延伸至唐宋以至于清代的书法墨迹中,使其在研究的范围和方法深度上,都对于阮元的相关论述有了更进一步的拓展和深入,[17]为自身客观认识《兰亭序》的书学地位和价值,提供了可能性。
李瑞清在进行书法史源流考述的过程中,对商周迄于清代的书体与书法风格,进行分析和梳理派别,注重对钟繇和“二王”书迹的推研,提出:“《宣示》《力命》平实微带隶意,皆右军所临也,无从窥太傅笔意。”[18]并在1918年李瑞清《跋曾农髯夏承碑临本》时言:“有晋王逸少世所号书圣者也,王师钟繇,钟实出中郎,是中郎为学书祖。”[19]可知李氏认为:钟繇下启王羲之,而师承蔡邕,王羲之楷法师法钟繇,实则是学习蔡邕笔法,王羲之书法师承蔡邕传袭隶法。在李瑞清《匡喆刻经颂九跋》中,也曾提及:“‘字似欹而实正’,此唐太宗赞右军书也。其实亦从商、周钟鼎中来,此秘惟《鹤铭》《龙颜》、郑道昭、《张黑女》及此石传之,其要在得书之重心点也。”[20]李氏将王羲之书法可得唐太宗称赞,归因为字的欹正关系处理取法于商、周钟鼎,得书之重心点的正确方法,再证王羲之楷法上承篆隶的主张。王羲之作为“二王”书法群体的开派者,李瑞清对其楷法溯源,实源于对整个“二王”帖学系统梳理的需要。《临右军帖》言:“世之言草书者称二王,实大令支流耳。大王法孙过庭,后惟赵子昂略涉其藩,世传但素师派也。”[21]并在《临大令送梨帖》中补充:“大令草出于篆,然其纵者已开唐派,余独憙此。”[22]由此可证,王献之草书出于篆,取其变化纵式的怀素开唐派草书。这一观念的产生,促使李瑞清将“二王”帖学取法上溯篆隶,置于书法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此外,李瑞清在1912年后,以遗老身份蛰居海上,鬻字卖画为生。初至上海时生活频遇窘境,[23]为鬻书糊口满足时人的购书需求,多取法“二王”书迹。[24]此时期对“二王”书迹的大量临摹,对其客观定位《兰亭序》有一定促动性。
三、外因:时代观念促使与交游学者影响
李瑞清“兰亭观”转变的缘由,与其对新材料的关注有密切关系,[25]同时也因受到沈曾植、曾熙和郑孝胥等人碑帖观念的影响。20世纪初期,随着甲骨文和《流沙坠简》等书法新材料的出土,使得书家对书法史发展研究进入更深层的领域。郑孝胥曾言:“自《流沙坠简》出,书法之秘尽泄,使有人发明标举,碑学者皆可循之以得其径辙,则书学之复古,可操卷而待也。其文隶最多,楷次之,草又次之,然细勘之,楷即隶也,草亦隶也。”[26]并题唐临绢本《兰亭序》曰:“米老所称‘转折毫芒备尽,与真无异,非深知书者所不能到’或指此本。唐人一代笔法不能越此。若更欲向上,需从隶草中求之矣。”[27]可见《流沙坠简》的出现佐证了郑孝胥楷、草书溯源隶法,于隶草中求古法临《兰亭》的观点。李瑞清在《跋自临兰亭》中,也提及观看郑孝胥所书《兰亭序》,故其参篆隶笔法临《兰亭序》,且此时期,郑孝胥与李瑞清的交游较为频繁,尝共宴、论书画文字源流发展,[28]可见二人在《兰亭序》的研究方面互有参照。
沈曾植较李瑞清年长,对碑帖皆有研究,处于清末书坛,深受阮元重碑抑帖,以及康有为贬卑唐碑的思想影响。1913年底或1914年初,沈曾植曾写给罗振玉的信中提及:“汉竹简书,近似唐人,鄙向日论南北书派,早有此疑,今得确证,助我张目。”[29]新材料的出现,引发沈曾植对阮元南北书派论的反思和研究,促其开始重新审视书法源流和传统书学理念,尝试将碑与帖进行融合,成为这一时期“碑帖融合”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30]李瑞清在《跋自临兰亭》曾言:“余生平不解《兰亭》,颇为沈乙盦先生所诃。”[31]从沈曾植对于李氏的批评,及沈增植不采用南北书派论的明显界定和尊卑态度来评价鉴赏兰亭,并认为《兰亭序》有风骨神采,可借《兰亭序》从唐人模帖中追溯晋人书风等观念,皆佐证沈增植对《兰亭序》的认同。[32]李氏曾言:“年来避乱沪上,鬻书作业,沈子培先生勖余纳碑入帖......酷暑谢客,乃选临淳化秘阁、大观、绛州诸帖,不能得其笔法者,则以碑笔书之,不知他日沈、秦两先生见此,如何论之?必有以启余。”[33]故在李氏居于上海期间,沈曾植作为书学前辈对李氏给予相应指导,其碑帖融合的观念对李氏产生了一定影响。
曾熙是促使李瑞清“兰亭观”转变的重要推手,除前文中有关阮元南帖北碑论偏颇的论述外,曾熙尝与李瑞清、谭延闿等书家学者共同赏定《兰亭》诸本,曾熙善比较不同版本之优劣,论其存本源流。[34]据李瑞清1915年《跋兰亭六种影印本》中,版本分析的详尽程度可知,此期间与曾熙的探讨,使李氏对《兰亭序》的认知逐步深化。同年十一月,曾熙云:“共几研廿有四年,前道人尚有南北之见,今则服膺予论,因书其后。”[35]在此后李瑞清的论帖题跋中,也流露出与曾熙相近的学术思想。种种皆表明,在曾熙对于阮元南北碑派论的否定下,李瑞清形成了新的碑帖观念,也使其对《兰亭序》的书学地位给予肯定。
在20世纪初新、旧学术思想相交汇的特殊历史时期,新材料与新视角的出现打破了碑帖间的界限,从而将研究者从碑与帖何为上的纠结挣扎中解放出来。客观而言,李瑞清受所处时代对《兰亭序》研究材料和方法的局限,其“兰亭观”也并非完美,但体现出李瑞清对书法史源流研究的高度重视;代表了同时代书家对于《兰亭序》的认识变化,暗含着书学者对碑帖关系的新审视,以及关注新材料所带来的书学研究群体性变化。李瑞清的“兰亭观”虽只是其书学思想的一部分,但作为一个重要的聚焦点,有助于我们更系统、深入地把握李瑞清的书学思想,乃至更大范围的晚清民国时期书家的思考和选择。
注释
[1] 《<清道人遗集>前言》,(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6页。
[2] 王东民:《以古为新—金石学传统下的李瑞清书画研究、创作与教育》,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56页。
[3] 夏寿田:《题曾熙山水册十二帧》,王中秀、曾迎三编著:《曾熙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版,第50页。
[4](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56-157页。
[5] 同上,第157页。
[6] 同上,第150页。
[7] 李文田:《兰亭序跋》,水赉佑编:《<兰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第826页。
[8](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50页。
[9] 李瑞清:《题定武兰亭肥本》,水赉佑编:《<兰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第824页。
[10] (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49页。
[11] 王中秀、曾迎三编著:《曾熙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页。
[12] 同上。
[13] (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73-74页。
[14] 王东民:《以古为新—金石学传统下的李瑞清书画研究、创作与教育》,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52页。
[15] 同上,第54页。
[16] 李瑞清《题跋》中对石室经书及《流沙坠简》等有所论述,详见(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33-165页。
[17] 王东民:《以古为新—金石学传统下的李瑞清书画研究、创作与教育》,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7,第62页。
[18] (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52页。
[19] 同上,第146页。
[20] 同上,第142页。
[21] 同上,第153页。
[22] 同上,第153页。
[23] 同上,第38页。
[24] 同上,第126页。
[25] 《玉梅花庵书断》:“近出龟版牛骨,实为殷墟文字,至可宝贵,睹之其派,最为明显。从前殷代文字,但于殷器中见一二象形字,不足成立,今殷墟之龟版牛骨,其文字虽不全,可以灼然知其一代文字之派矣。”(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59页。
[26] 郑孝胥:《题庄繁诗书陶诗序》,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印刷,第944页。
[27] 郑孝胥:《题唐临绢本<兰亭序>》,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1995年印刷,第1004页。
[28] 崔尔平选编点校:《明清书法论文选》,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年版,1995印刷,第958页。
[29] 沈曾植:《海日楼遗札》,《同声月户》,1944年第四卷第二号,第94页。
[30] 刘星振:《清代书家对<兰亭序>解读立场分析,《书法》,2018(06),第61页。
[31] (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50页。
[32] 沈曾植有关《兰亭序》题跋,详见水赉佑编:《<兰亭序>研究史料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年版,第634-644页。
[33] (清)李瑞清著,段晓华点校整理:《清道人遗集》,合肥:黄山书社,2011年版,第155-156页。
[34] 《谭延闿日记》中,多次谈及与曾熙、李瑞清等人共同赏定《兰亭》诸本,探讨书画文字源流。详见王中秀、曾迎三编著:《曾熙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版。
[35] 王中秀、曾迎三编著:《曾熙年谱长编》,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6年版,第19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