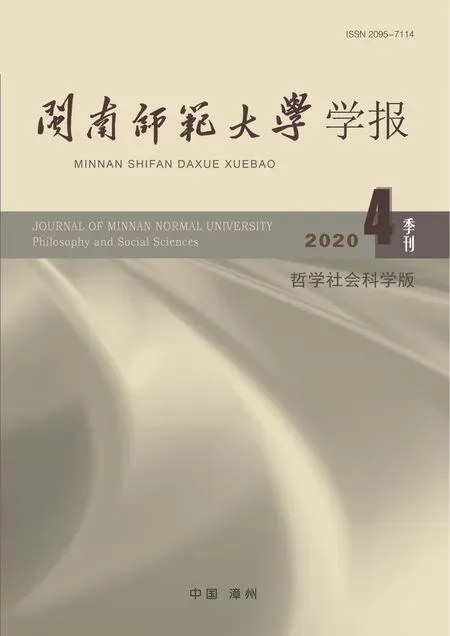《开元四部录》考辨
王照年
(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漳州 363000)
《崇文总目》作为专门收录宋仁宗景祐至庆历初(1034-1041年)馆阁(即弘文馆、史馆、集贤院和秘阁)藏书的官修解题类目录,是由当时的馆阁文士奉旨集体编纂而成,先后参与编纂者主要有张观、宋庠、王尧臣、聂冠卿、郭稹、吕公绰、王洙、刁约、欧阳修、杨仪、陈经、王从礼等人。由于编纂过程中仿照《开元四部录》(又称《开元四部书目》《开元四库书目》),应在体例和结构上有明确的参照对象,故成书虽经众人之手,但最终所成不失为一部编纂体例完备、整体结构严整的解题目录。也正因为如此,在《崇文总目》成书之后,作为一部官修目录书,既能够方便查阅当时的馆阁藏书,又能够便于读者迅速了解每一部藏书的基本信息。在实际应用中,不仅取代了之前《开元四部录》在宋代馆阁中承当检阅藏书的功用,成为当时官修目录类中极具实用价值的目录书;而且影响到自此以后官修目录、史志目录、私家目录等的编纂体例。至今依旧被学界推崇,素有“宋朝的官修目录以仁宗时所修《崇文总目》为最著名”[1](P178)的称誉。
按常理而论,《崇文总目》能够成为一部颇具影响力的官修目录,并在后世具有很高的关注度,应当会有学人对该书编纂过程中所仿照的《开元四部录》也予以更多的重视,方是合情合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与《开元四部录》相关问题的探讨却一直被学界忽略了,以至于北宋编纂《崇文总目》时所仿照的《开元四部录》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目录书?鲜有人追究。如在来新夏《古典目录学》一书中,起先有“官修目录”,列有《中经》至《天禄琳琅书目》的历代书目共十七部,其中见列“唐《群书四录》”“唐《古今书录》”和“宋《崇文总目》”[1](P23-24),而未见有《开元四部录》(或《开元四部书目》《开元四库书目》)之类的目录书;然后有“私家目录”,分为两种七类,凡所列举者亦未见之,当为不属于私家目录之故。但再至该书后文论及《崇文总目》编纂时称:“并命王尧臣、欧阳修等仿照唐代《开元四部书目》的体例,‘加详著录’,于庆历元年十一月撰成,赐名为《崇文总目》。”[1](P29-40)继而提到《崇文总目》的四部分类时,又称:“计经部九类,比《开元四部书目》少图纬、训诂、经解三类;史部十三类,删起居注、旧事、谱系三类,增实录、氏族、岁时三类;子部二十类,增类书、算术、艺术、卜筮、占书、通书、释氏七类;集部三类,删楚辞,创文史一类。”[1](P179)显然,在此突然出现之前公私目录中并未言及的“《开元四部书目》”,并引以为据,既没有注明撰者,也不见其引文来源,俨然《开元四部书目》是一部众所周知的唐开元年间编纂的目录书,足以影响到北宋馆阁文士编纂《崇文总目》时不得不借鉴和参照。可是,据本文考辨的结果表明:来氏所引证的“《开元四部书目》”,宋人又称“《开元四部录》”[2](P75),实为唐人毋煚的《古今书录》。
这一结论的确立,首先是肯定了流传至宋代的《古今书录》被称为《开元四部书目》或《开元四部录》,并非唐代殷践猷等撰成的《群书四录》,更非除此之外的其它目录类著述。其次是确定了影响北宋编纂《崇文总目》最为直接而深巨的目录书,其实就是众所周知的《古今书录》。最后是理清了宋代前后解题类目录的编纂体例前后承继的演进轨迹,这对学界整体推进解题类目录的纵深研究至为重要。
一、与《开元四部录》相关的《群书四部录》《古今书录》
若要深入了解与《崇文总目》相关的编纂情况,就必须先得明确编纂是书所仿照的《开元四部录》的真实情况。从现存文献记载可知:应该在北宋编纂《崇文总目》之前,曾有一部编纂于唐代开元年间的《开元四部录》,其在当时的作用和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是馆阁屡次搜访遗书的参照依据,如据《麟台故事》残本卷三中《书籍》载,宋太宗太平兴国九年(公元984年)正月,向天下颁布求书诏曰:
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举列其名,于待漏院出榜告示中外,若臣僚之家有三馆阙者,许诣官进纳。[2](P254)
二是日常检阅馆阁藏书的依据与最终编纂《崇文总目》所仿照的直接对象,如据《麟台故事》辑本卷二《修纂》载,景祐年间(1034—1038年)整理馆阁藏书时称:
景祐中,以三馆、秘阁所藏书,其间亦有缪滥及不完之书,命官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著为《总目》而上之。[2](P75)
不过,据现存《崇文总目》记载的情况来看,当时馆阁藏书中至少有十九部书目,然而其中并不见载有《麟台故事》所谓的“《开元四部书目》”和“《开元四部录》”之类的名目。对比之下,与之最为接近者,也仅存一条记载:“《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原释阙(见天一阁抄本)。”[3](P122-125)如果这一条记载与宋人编纂《崇文总目》所仿照的《开元四部录》无关,则实难找出值得可信的理由来说明一个很显然的问题:馆阁文士为何不著录当时馆阁中一直收藏并使用的《开元四部录》或《开元四部书目》?再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等相关书目的记载来看,更是不见与《开元四部录》,或称《开元四部书目》《开元四库书目》等与之名目相近的著录。如此一来,就不得不让人质疑:唐代的开元时期是否出现过这样或有类似名目的一部书目?
首先,依据史籍记载,唐玄宗开元年间确实整理过中央政府的藏书,这应是毫无疑问的史实,书名中含有“开元”二字者,应当顺理成章地想到的便是《群书四录》,这是因为该书又称《唐群书四录》《群书四部录》《开元群书四部录》①据武秀成《唐〈群书四部录〉撰者“王仲丘”辨误》有“《群书四部录》,又名《群书四录》《开元群书四部录》,凡二百卷,是唐代开元年间编撰的一部重要的朝廷藏书目录,也是古代卷帙最大的藏书目录之一”(详见《文献》2012年第4期,第163页)。可见,《群书四录》《群书四部录》《开元群书四部录》与上文所述及的《开元四部书目》,或《开元四部录》是有区别的,前者应是唐玄宗时朝廷所编《群书四部录》,后者应是毋煚依据《群书四部录》所编定的《古今书录》。等名称。
其次,从当时编纂出的目录书作为最终结果来考察,则与书名称“开元四部录”关系最为切近的目录书应该有两部:一是《群书四录》,唐殷践猷等撰,已佚,共二百卷,属于官修目录;二是《古今书录》,唐毋煚撰,已佚[1](P17),共四十卷,属于私家目录。既然是北宋馆阁所藏所用的是开元年间的目录书,那么初步可以肯定是其中之一,至少也是与其中之一的关系最切近。
再次,按照《群书四部录》与《古今书录》成书的先后经过来看,二者必定不可能会混同为一部书。如据《旧唐书·艺文志》载,《群书四部录》成书于开元九年(公元721)十一月,而《古今书录》是在此基础上节略成书的,时间本就有先后,即称:“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刘仲等重修成《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右散骑常侍元行冲奏上之。自后毋煚又略为四十卷,名为《古今书录》,大凡五万一千八百五十二卷。”[4](P1962)
最后,《群书四部录》的成书是编纂《古今书录》的前提,也是基础,二者虽有各方面的承继关系,但彼此之间存在的差异表明:根本不可能会混同为一部书。现今《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虽早已亡佚,但据《旧唐书》所载尚可推断:长达二百卷的《群书四部录》,真可谓浩繁卷帙,该书若能有幸存留后世,其体量实可与清代四库馆臣编纂的二百卷《钦定四库全书总目》相当,正如来新夏所言:“在目录书中除了《群书四录》有二百卷外,别无他书,而《群书四录》久佚,难得其详,所以《四库全书总目》可以说是古典目录书中篇幅最大的现存的唯一巨著。”①此处所谓“《群书四录》”,实乃《群书四部录》之简称。详见来新夏著《古典目录学浅说》,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8页。而况《群书四部录》出自众人之手,自然会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体例驳杂不一、内容难于周全等的问题。因此,仅以目录需要简明实用的标准来衡量,《群书四部录》确实不太合适,可以推广使用的范围也肯定不会太大。这从当时参与《群书四部录》编纂过程的重要人物毋煚所持态度和认识来看,也是如此:先是毋煚对刚成书的《群书四部录》很不满意,并持有“曩之所修,诚惟此义,然礼有未惬,追怨良深”[4](P1964)之类的怨言;而后是毋煚据实而论,直陈该书存在着“事有未周”“理有未弘”“体有未通”“例有所亏”“事实未安”[4](P1964-1965)等五个方面的重大缺失。也正是由于毋煚对《群书四部录》“追怨良深”,且指出的问题确凿而无不切中该书所存在着体例驳杂、内容纷繁、主旨不明、卷帙浩繁、不便使用等方面的弊端,所以才会最终出现毋煚在《群书四部录》已成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整理出四十卷的精简本目录书,另名《古今书录》。因此,仅从当时已经编纂出《群书四部录》作为前提和基础的承继性而言,可以将《古今书录》这一结果视为《群书四部录》的节略本。不过,毋煚之作,既远追《史记》《汉书》《七略》《七志》乃至《隋书·经籍志》的经籍分类著录之法,又近遵已经成书的《群书四部录》按照典籍收藏的库存秩次甲、乙、丙、丁排序的四分法,更是充分尊重当时朝廷图籍分四部收藏的实况与出现编目需求的情况,故所确定的图书著录之法与以往有着很大的不同:不再是按照典籍以所藏库存秩次的甲、乙、丙、丁四库排序的四分法,而是将相应典籍依据其所属学术性质分为子、史、经、集四部排序的四分法,即明确的是四部的部次,而非四库的库次,这不能不说是目录学在确定分类上的一个重大进步。再加上《古今书录》在编纂体例与主旨、呈现内容与卷帙等方面的明显差别,即便流传至宋代也不可能将其与《群书四部录》混同为一部书。
总之,《古今书录》与《群书四部录》虽然渊源极深,但自《古今书录》成书之后,就取代了《群书四部录》,二者不可能是同一部目录书,诸多情况均表明后世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会出现混同为一、不分彼此的情况。尤其是《古今书录》将释、道之书另列于四部之外,“别作目录十卷,名为《开元内外经录》”[4](P1965),即当时毋煚所做成的目录书有《古今书录》和《开元内外经录》两部分,表明在形制上与《群书四部录》更有着很大的不同。尽管这并不排除二者在书名上均冠以“开元”二字的可能,但是据实际应用情况来看,当时也只是在《古今书录》的后一部分释、道之书名曰“《开元内外经录》”。那么,流布至后世,将其四十卷的前一部分顺理成章地晚唐之北宋时期的人相应地称之为《开元四部录》、或《开元四部书目》、亦或《开元四库书目》,当属最为合情合理之事。
二、与《开元四部录》相关的新旧《唐书》著录
我们明确上述《群书四部录》与毋煚《古今书录》(包括《开元内外经录》在内)之间不可能会出现混同为一本书的情况后,接着需要更进一步梳理至清的关键问题是:自北宋初以来,从搜访遗书到编修《崇文总目》的过程中,诸多文献记载都是以《开元四部录》(或《开元四部书目》)为参照标准,而宋人所据《开元四部录》是与《群书四部录》关系最近,还是与《古今书录》关系最近呢?我们唯有在理清这些关系的前提下,才能够更进一步准确地界定出北宋编纂《崇文总目》时所仿照的《开元四部录》究竟是何典籍。
(一)与《开元四部录》相关的《旧唐书·经籍志》著录
据《旧唐书·经籍志》载,只是在其史部目录类之下见有“《群书四录》二百卷(原注曰:元行冲撰)”[4](P2011)的著录,并不见有《古今书录》和《开元四部录》之类的著录。这只能表明:在唐代开元九年(721)十一月之后的一段时期内,应在乾元殿确实藏有殷践猷、毋煚等奉诏修撰的《群书四部》二百卷。这一点再据《群书四部》成书之后,又由毋煚在该书的基础上,按照实际情况的需求精简缩编成《古今书录》四十卷,亦可得以印证。及至后来,《群书四部录》是否能够传至宋代,由于史料记载的缺失,实难考证。然而,目前依据史实推断,应当没有可能。其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
一是《群书四部录》自成书后绝少传世而最终散佚。因为在《群书四部录》成书之后,很快就出现的《古今书录》,既简便规整,又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其结果自然会更能实现原本编纂《群书四部录》的目的,进而也就逐渐取代了之前编纂成《群书四部录》作为唐代中央政府藏书目录书的地位和功效。于是《群书四部录》自此罕有人问津,以至于传播世间的可能性绝少,最终因无人问津而散佚。
二是几经祸乱之后的《群书四部录》几乎难以幸存。先是在唐代经历过被称之为“藏书之厄”[5](P61)的安史之乱和黄巢之乱,正所谓:“禄山之乱,两都覆没,乾元典籍,亡散殆尽。……及广明初,黄巢干纪,再陷两京,宫庙寺署,焚荡殆尽,曩时遗籍,尺简无存。及行在朝诸儒购辑,所传无几。”[6](P228)尤其平常典籍,更是“世莫得闻”[6](P228)。继以五代更迭、干戈纷争,都城又屡经战火,藏之于中央政府的典籍更是难以幸免。况且《群书四部录》作为一部目录书,不仅存在诸多弊端,而且卷帙浩繁而不便于使用,又很快被《古今书录》取代而废置。于是处在如此状态下的一部目录书,即便当时在西都和东都有正副本保存,可在几经祸乱之后,最终能够传至后世的可能性渺小至极。实如后晋宰臣赵莹初领监修国史之职而参与修纂《旧唐书》时所奏:“自李唐散乱,迨五十年,四海沸腾,两都沦覆,今之书府,百无二三。”[6](P228)后至后晋刘昫等进行到最终编纂《旧唐书·经籍志》时,仍旧是缺乏与之相关的材料,故不得不以传世较广的《古今书录》为蓝本节略而成。可见,早在五代时就已经看不到的中央政府典籍,至宋代能够看到的机率自会更小。更何况宋代所据《开元四部录》为四十卷本,是屡次搜书能够使用的,也是编纂《崇文总目》可以参照的传本,肯定是全本无疑。这足以表明:《开元四部录》只能是《古今书录》,而不可能是《群书四部录》。
另外,《旧唐书·经籍志》不见著录《古今书录》的原因在于:既然学界早已论定《旧唐书》的《经籍志》“实为《古今书录》之节本”[7](P217),那么按照常理而言,起初唐人毋煚在编纂成《古今书录》时,当然不会出现将自己编著的《古今书录》著录到本书中的情况;再至后晋刘昫等编纂《旧唐书》的《经籍志》时,又是依据《古今书录》节略而成,自然也就忽略了本该在《旧唐书》的《经籍志》中极有必要著录《古今书录》的情况。
(二)与《开元四部录》相关的《新唐书·艺文志》著录
据《新唐书·艺文志》载,先是在其史部目录类之下见有一条记载:“《群书四录》二百卷。”①此载之下有原注曰:“殷践猷、王惬、韦述、余钦、毋煚、刘彦真、王湾、王仲丘撰,元行冲上之。”(详见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五十八《志第四十八·艺文二》,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498页)注文中“刘彦真”原作“刘彦直”,盖欧阳修等为避宋真宗讳而为之,据﹝后晋﹞刘昫:《旧唐书·经籍上》作“刘彦真”,故改之。此外又有二处问题:一则《新唐书·艺文志》所载《群书四录》撰者有王仲丘,却无刘仲;且前已云“元行冲奏上之”,即不在撰者之列,可在后又云“元行冲撰”,以至于前后不一,自相抵牾;然详考之下,当以前者为准。二则《旧唐书·经籍上》所载《群书四录》撰者有刘仲,却无王仲丘。二者之间有出入,故存疑。相比之下,很明显的不同在于:《新唐书·艺文志》此载的原注比《旧唐书·经籍志》更为详尽。这应为欧阳修等在《旧唐书·经籍志》的基础上进行增补的结果,应属编纂者确实未曾得见《群书四录》而增补的内容。若不顾及这一增补结果,则《新唐书·艺文志》此载实与《旧唐书·经籍志》所载一样,仅能证实唐代确有《群书四部录》一书,并不能确证该书传至宋代而藏于馆阁而被欧阳修等据实著录。
然后据《新唐书·艺文志》另有一条记载:“毋煚《古今书录》四十卷。”[8](P1498)则正是《旧唐书·经籍志》本该著录却被忽略而不见载的内容。此载不只是表明欧阳修等在编纂过程中增补了《旧唐书·经籍志》所缺,而更重要的信息乃是:当时馆阁的确藏有唐人毋煚编纂的、书名为《古今书录》的、卷数为四十卷的书目。这与开元年间出自众人之手的《群书四部录》二百卷不可能会混同为一部书,也不是《开元四部录》《开元四部书目》《开元四库书目》等名目,且还不包括毋煚编纂的《开元内外经录》十卷在内。可见,这应当是当时参与修史的馆阁文士欧阳修等得见此书,才能够在《新唐书·艺文志》如此清晰地增加此条著录。
不过,为何《新唐书·艺文志》又同《旧唐书·经籍志》一样,仍旧不见有《开元四部录》的著录?难道唐代原本就没有这一部书目?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开元四部录》应当与前后出现的《群书四录》《唐群书四录》《群书四部录》《开元群书四部录》《开元四库书目》之类的众多名目,有一定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尤因唐代《群书四录》确实并没有传至宋代,传下来的应是在该书基础上成书的《古今书录》,故又可以进一步做出这样的推断:此类众多名目,应是《古今书录》在不同时期、不同文献记载中出现的别称,实即同一本书而已。
三、与《开元四部录》相关的《崇文总目》著录
据现存宋人当时编定的《崇文总目》卷二十三《目录类》所著录的十九部目录类书,以及清人钱绎对此所作考释的具体情况来看:当时整个北宋馆阁中所收藏的目录类著述实有十九部之多,除《符瑞图目》为南朝梁陈人顾野王所撰、《学士院杂撰目》为宋初馆阁文士所撰之外,其余都是唐人著述;著录在内的十九部书目的总卷数实为一百八十六卷,故从卷数上判断,当时馆阁确实不可能存有较为完整的《群书四部录》二百卷。再以所列十九部书目的名目来看,既不见有《群书四部录》之类的著录,也不见有毋煚《古今书录》的著录,只有“《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3](P122-125)一条著录,在名称上似乎与《群书四部录》比较接近,而在卷数上实与《古今书录》完全一致。既然我们已经论定《群书四部录》几乎不可能传至宋代,那么,至今出现在宋人文献中的、自宋初以来馆阁搜访遗书到编纂《崇文总目》所用的“《开元四部录》”或“《开元四部书目》”等书名,实即《崇文总目》中著录的、当时存于馆阁中的“《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而这也正是毋煚依据《群书四部录》而做成的《古今书录》四十卷。
尤其是这一点,还可据《宋史·艺文志》史部目录类之下,仅有“毋煚《古今书录》四十卷”[9](P5146)一条著录的情况得以证实。这是因为,在此著录之外,既不见有《群书四录》《唐群书四录》《群书四部录》《开元群书四部录》等名目的目录书著录,也不见有《开元四部录》《开元四库书目》《开元四部书目》等名目的目录书著录,此则足以证实:北宋馆阁所藏《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应当就是毋煚《古今书录》四十卷。再据今人研究表明:《崇文总目》,正是修撰《宋史·艺文志》所依据的四种书目之一①据周勋初先生《唐诗文献综述》一文中考其所依据的四种书目为:《崇文总目》《秘书书目》《中兴馆阁书目》《中兴馆阁续书目》,另还添入《宋中兴国史艺文志》中著录的一些典籍,成《宋史艺文志》八卷。详见《周勋初文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28-329页。,故而从《崇文总目》所载“《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到《宋史·艺文志》所载“毋煚《古今书录》四十卷”之间的这一变化,则正好说明二者实为一部书,只是在实际应用中的称呼与书目类文献中著录书名有别而已。而事实情况也只有如此:原本编纂《群书四部录》的作用和功效最终被《古今书录》取代后,才有可能凭借其自身的优势流布较广,因后世传播途径不同产生不同的名称,及至宋代,则出现将称其为《开元四部录》《开元四库书目》《开元四部书目》等的复杂情况。
四、与《开元四部录》相关的《通志》著录
鉴于要了解《崇文总目》的编纂之深受《开元四部录》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了解其深受毋煚《古今书录》的影响。之所以出现这一切混乱,均因文献本身在后世流布的过程中,不同时期可能会有不同的名称所致。不过,目前得出这一结论,也还是存在着一个难于周全的疑惑之处,即在南宋绍兴年间成书的郑樵《通志》中,先后有四条与《开元四部录》相关的著录:
《四部书目序录》三十九卷(原注曰:殷淳撰)。
《唐群书四录》二百卷(原注曰:殷践猷等撰)。
《古今书录》四十卷(唐毋煚撰)。
《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9](P1595)
以今观之,郑氏之书晚出于《崇文总目》百余年,其所录四部目录类书目已经不可能与《崇文总目》求得一一印证。特别是郑氏所列以上四部唐代的目录类书目,总卷数共三百一十九卷;而北宋编定《崇文总目》时所如实收录的、馆阁藏书中见在的、应为唐代的目录类书目,总卷数尚不足二百卷;二者在总量上的出入相差接近一倍,显然在此不能以郑氏之书直接为证,更不能以郑氏所载来准确反映北宋前期中央政府藏书的实际情况。此外,还需进一步说明四点:
一是郑氏所载殷淳虽有过编纂《四部书目》之实,但其为唐前之人,故与本文所探讨的问题无甚关联。
二是以上述所论《群书四部录》存世的实际状况来看,郑氏是否确实得见过其所著录在内的《唐群书四录》二百卷,还需详加斟酌,当不可尽信。另据与郑樵同时代而较早的宋人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中著录《崇文总目》时称:“《国史》谓书录自刘向至毋煚所著皆不存。”[11](P402)晁氏所谓“国史”,为北宋馆阁修纂的当朝史,且均有《艺文志》,如吕夷简等修《三朝国史》一百五十卷,王珪等修《两朝国史》一百二十卷,李焘、洪迈等修《四朝国史》三百五十卷》,记载的均为能得见的由北宋所编史实,能著录的也是当时以馆阁为主的中央政府藏书。可见,郑氏所举如此之多的书目,并非据实著录。
三是郑氏所著录的《开元四库书目》四十卷情况,又与《崇文总目》分毫不差,同样不注明撰人,让人难以否定《开元四库书目》与《古今书录》原本不是一部书的状况,当然也就会影响到难以肯定二者同为一部书的结论。
四是郑氏此载,确属特例,目前还没有足够的证据予以完全否定,同样也没有足够的文献材料以证其所载属实;特别是从《崇文总目》到《宋史·艺文志》,再到《四库全书总目》等一系列官修书目的著录中,也再无与郑氏此载相接近者;同样自宋代以来,诸如深受《崇文总目》影响的《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遂初堂书目》等一系列私家书目的著录中,也是如此。
通过以上考辨的结果可知:在《崇文总目》编纂的过程中,所仿照唐代《开元四部录》实际上就是毋煚的《古今书录》,尤其是编纂体例确实深受《古今书录》的影响。尽管目前我们看不到《古今书录》的全貌了,“但其所著录的唐开元以前的五万多卷古籍全部为《旧唐书·经籍志》照录,而且《旧唐书·经籍志》的分类体系、类目设置等大旨,一如《古今书录》,可以说,没有《群书四部录》和《古今书录》,也就没有我们今天可以见到的历史上第三部史志目录《旧唐书·经籍志》了”[12](P51)。因此,通过保存在《旧唐书·经籍志》中的《古今书录》四部书目及其相关序释,便可大体得窥其编纂体例之概貌。然而,为了确证此上考辨结果的重要性,我们还需要明确以下三点:
首先,现今存留于《旧唐书·经籍志》中的、处于毋煚《古今书录序》之前所罗列的、为了以彰显开元时期艺文之盛的、所谓“今录开元盛时四部诸书”[4](P1963)的四部分类标准,以及其下分别所著录的典籍,实乃沿袭开元时朝廷编纂《群书四部录》所用部类划分及其著录典籍的基本概况。
其次,现今存留于《旧唐书·经籍志》中的、处于毋煚《古今书录序》之后所罗列的、以四部分类为标准及其所著录的典籍,实乃以《古今书录》为蓝本的节略和补充,应该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古今书录》部类划分情况的旧貌。
最后,对于朝廷编纂《群书四部录》和毋煚编订《古今书录》而言,影响至为深远的四部分类法虽已由来即久,但最大、最直接的应当是唐初魏征等所撰《隋书·经籍志》。于是,从《隋书·经籍志》到《群书四部录》,继而又到《古今书录》,表面上虽是一个从官修目录书到私家目录书的演变过程,但从《古今书录》再到《崇文总目》,进而推演到之后的北宋《秘书省总目》、南宋《中兴馆阁书目》及其《续书目》、明代《永乐大典目录》、清代《四库全书总目》等官修书目的发展情况来看,实际上又是一个既相递承继而又各有因革的官修目录书的发展过程。因此,期间所出现的每一部书目,不只是越来越具有合理而严整的编纂体例,又始终不失其为目录书所必须具备实用之功效,而且还能够藉此清晰地反映出当时国家藏书的真实状况和体现出当时国家文化事业发展的整体水准。毋庸置疑,北宋编纂《崇文总目》所仿照的《古今书录》,肯定也是如此,理应在这一整体发展过程中起到过承前启后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