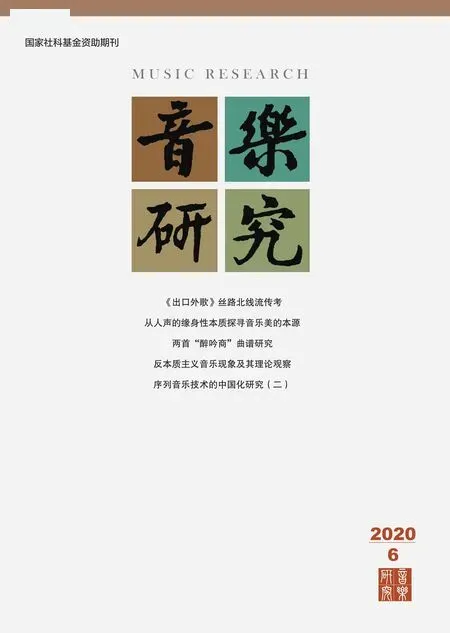孙继南音乐史学思想研究
文◎冯春玲
引 言
孙继南(1928—2016)先生,是我国当代著名的音乐史学家、音乐教育家。他的音乐史学研究与其音乐教育实践紧密相连,特别是他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学堂乐歌,以及黎锦晖、李叔同等音乐家的研究,均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其“学风之严谨,史料之翔实,评价之公允,在近现代音乐史学界有口皆碑。”①杨成秀《孙继南学案》,《天津音乐学院学报》2005 年第1 期,第71 页。综观孙继南的音乐史学成果,可以发现,虽然他未曾就音乐史学研究的元理论问题做出过专论,在涉及相关问题的访谈中也没有展开过具体的阐述。但是,作为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大家,其学术研究必然蕴含着丰富的史学思想。因此,对孙继南的音乐史学思想加以深入的学习与总结,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史料为本的音乐史学观
史学观,是史家对史学的根本认识,那么,音乐史学观,是音乐史学家对音乐史学的根本认识。音乐史学家具有怎样的音乐史学观,通常会对其史学实践产生深刻影响。从孙继南的自述可知,他的音乐史学观,深受傅斯年“史学即史料学”思想的影响。他在一次访谈中曾坦率地说:“我很赞同傅斯年‘史学就是史料学’的观点。”②曲文静《史料是史学的精髓——孙继南采访录》,《中国音乐学》2015 年第3 期,第5 页。
将史学定位为史料学的观点,在今日的史学研究中已不为学界所完全赞同,但是,“史学即史料学”的治史观念,却指出了史料在史学研究中无可替代的价值。没有坚实史料基础的史学研究无疑如空中楼阁。孙继南也正是从这一角度,强调了史料在音乐史学研究中的首要意义。因此,对于傅斯年、梁启超和胡适等人注重史料的史学研究,孙继南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和认可。他结合自身的音乐史学研究提出,“史料意识”是历史研究者必须具备的史学观念,翔实的史料是史学研究最为关键的基础,是否具有史料意识和辨别史料真伪的能力,往往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成败。③参见注②,第5—11 页。事实上,他在许多文论中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这一史学观念更是在其史学论著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笔者将孙继南的这一史学观总结为“史料为本的音乐史学观”。但是,这种以史料为本的音乐史学观,并非仅是史学思维上的理论认知,只有通过艰辛的研究实践——史料的发掘、考证、辨析、运用,才能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印证与统一。纵观孙继南的治史实践,史料为本的史学观念与治史原则,始终贯穿于他的音乐史学研究当中。
孙继南在音乐史料发掘与考证方面所做的努力与贡献,可以从他的研究经历和研究成果来略加感受。比如,他经过长达十余年的搜寻,终于将登州文会馆志中刊载的十首乐歌完整地呈现给音乐史学界,改写了学堂乐歌的历史;④孙继南《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 《音乐研究》2006 年第2 期。经过他的费心和努力,1984 年日本友人实藤惠秀将李叔同1906 编的《音乐小杂志》复印本赠予中国学界;通过他的细心考证,使我们得以了解清末官修乐歌教本——1907 年《乐歌教科书》的面貌,这本目前所见最早的官修乐歌教科书,包括与杨荫浏所填岳飞词大致相同的乐歌《满江红》;⑤孙继南《中国第一部官方统编音乐教材——〈乐歌教科书〉的现身与考索》,《音乐研究》2010 年第3 期。经过他的执着查寻、严谨考证,李叔同创作的两首歌曲《厦门大学运动会会歌》《诚》,得以拂去历史的尘埃,重新走进人们的视野;⑥孙继南《音乐史料之疑、考、信——以弘一法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考为例》,《中国音乐学》2013年第3 期;孙继南《〈诚〉:李叔同百年乐歌新发现——兼及周玲孙唱歌教材与李叔同歌曲史料研究》,《音乐艺术》2016 年第2 期。经其详加查证李叔同的传世之作《送别》,使我们认识到,《送别》经历了从“一瓢浊酒”,到“一斛浊酒”,再到“一壶浊酒”的长期讹误,以致被传唱为“一壶浊酒”。⑦孙继南《还历史歌曲以原貌——〈渔光曲〉、〈送别〉词曲辨正》,《中国音乐教育》2000 年第4 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编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一书,从初版到增订本,再到新版,经历了一个史料不断丰富与充实的过程。该书最后一版(新版)共编写条目850条,图片202 帧,后附史料选录、条目索引、人名索引和图片索引,可谓史料宏富翔实、图文并茂,是一本不可多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工具书。本书从初版问世以来,泽被学界众多从事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学者与莘莘学子,其学术价值熠熠生辉,可谓功德无量。
为了搜集史料,孙继南不但自己处处留意,辗转各处;同时,还经常拜托学界友人代为查阅一些难以亲力亲为的音乐史料,对此他总是要在相关文章中记下史料的来源并致以谢忱。更令人感佩的是,孙继南从不把史料作为私藏品,而是经常慷慨地提供给有需要的人。笔者十余年前撰写硕士论文研究黎锦晖的流行歌曲创作时,孙先生曾在史料线索方面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并且,他还主动将自己发现并查阅到的有关济南“五三惨案”的新史料提供给冯长春教授,于是才有了笔者与冯长春合作完成的《勿忘〈国耻〉——关于“五三”惨案的几则音乐史料》一文。⑧冯春玲、冯长春《勿忘〈国耻〉——关于“五三”惨案的几则音乐史料》,《中国音乐学》2014 年第3 期。
对于音乐史料的处理,孙继南是将其置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学学科发展的高度来加以审视的。他在一篇有关“重写音乐史”的争鸣文章中指出,学界关于“音乐史料学”的讨论“少之又少,不无遗憾”,继而结合自己的音乐史学研究指出:
经过长期音乐资料的搜集、整理和应用,笔者愈益深刻地认识到:“史料”不等同于“资料”。亦即“资料”在未经考证前,一般不能作为严格意义的“史料”,它需要一个先“疑”、后“考”、再“信”的过程。考证之初,多出于怀疑;考证翔实,方具可证性,用之于史学研究,才会有“信史”产生。⑨孙继南《音乐史料研究之疑、考、信——以弘一法师〈厦门市运动大会会歌〉版本考为例》,《中国音乐学》2013 年第3 期,第6 页。
在《佛曲〈三宝歌〉源流始末考》一文 中,孙继南又对史料的考订提出了“细”和“精”的要求:
所谓细,是指条分缕析,细节不惑;所谓精,是指考据精深,源流分明。⑩孙继南《佛曲〈三宝歌〉源流始末考》,《音乐艺术》2015 年第4 期,第11 页。
这短短的几行文字,可视为孙继南治史观念的浓缩,也概括了他由音乐史料学构筑而起的音乐史学观之根本。不管音乐史学获得怎样的发展,这一朴素却具真知的史学观念,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失去其理论指引的力量,反而历久弥新。
郭树群先生通过深入解读孙继南着重史料考证的部分论文,认为孙先生提出的音乐史料工作之“疑”“考”“细”“精”“信”的要求,可谓“五字箴言”,“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11]参见郭树群《几个学习有得的中国音乐史史料研究个案》,《中国音乐》2016 年第4 期,第63 页。刘再生先生在论及孙继南的治史贡献时则这样写道:“先生史料之扎实功底,史观之独立精神,史识之卓越超群,在老一辈近代史学家中极为少见。”[12]刘再生《低调人生学界楷模——孙继南学术人生追思录》,《人民音乐》2017 年第2 期,第26 页。可见,孙继南对音乐史料发掘与研究的贡献与卓见,得到了同人们的高度评价与认同。
二、人本主义的音乐史观
郭乃安先生的呼吁—“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至今犹在耳畔。这一呼吁,不仅意味着对过去音乐学研究中见“物”不见“人”之现象的批评,同时,也意味着音乐学研究由视角转换而带来的某种学术转向。因为“人是音乐的出发点和归宿”,“把目光投向人,不仅意味着在音乐学的研究中关注人的音乐行为的动机、目的和方式等,还意味着在各种音乐事实中去发现人的内涵,或者说人的投影”。[13]郭乃安《音乐学,请把目光投向人》,《中国音乐学》1991 年第2 期,第16 页。笔者以为,这样一种基于人本主义的音乐史观,在孙继南的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中,也得到了极为鲜明的体现。这样的音乐史观,完全不同于以往建立在阶级分析方法基础上审视音乐与音乐家的历史观;而是通过对音乐家及其音乐行为的全面考察,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将音乐家与音乐还原到特定的历史阶段与文化语境,并结合当代人对历史音乐文化的理解与阐释,对音乐家及其音乐行为做出实事求是的历史评价;其核心思想是对音乐家主体性的充分肯定,对音乐家艺术劳动的充分尊重。因此,这一带有鲜明人本主义色彩的音乐史观,进一步提升了音乐史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价值。人本主义的音乐史观,贯穿于孙继南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全过程,其中,关于黎锦晖和李叔同的研究,最能体现这一音乐史观。
众所周知,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黎锦晖在音乐史上的形象一直是“黄色音乐”创作的代表人物。由他创作的那些引领一代时尚的“流行歌曲”,长期遭到批判和禁止。这些使他曾经享有无上风光的歌曲作品,成为他后半生难以抹去的“不光彩”标签。“谈黄色变”的惯性思维,也使有关黎锦晖的历史研究也变得复杂而敏感。回到20 世纪30 年代初抗日救亡和左翼“新兴音乐运动”的历史语境,当然不难理解对黎锦晖的批评与责难。但是,黎锦晖创作那些“摩登曲”“家庭爱情歌曲”等时代曲的初衷,是为了追逐商业利益而丢却了艺术情操的不齿之举吗?他的大量爱情歌曲是否具有“黄色音乐”的内容与形式呢?
孙继南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样的答案,并非只是他站在今天五花八门的音乐环境中,对黎锦晖的流行歌曲加以比较后轻易得出的历史宽容;而是建立在对黎锦晖音乐人生,“时代曲”之时代的音乐观念冲突,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的反思等多方面,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之上;其中所表现出的史识、史德与学术勇气,令人感佩。这也正成就了孙继南对黎锦晖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从20 世纪90 年代初的《黎锦晖评传》[14]孙继南《黎锦晖评传》,人民音乐出版社1993年版。,到21 世纪初的《黎锦晖与黎派音乐》[15]孙继南《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上海音乐学院出版社2007 年版。,两部敢为学界之先的姊妹篇著作,不仅展示了黎锦晖及其“黎派音乐”得以正名的史学历程,同时,也反映了孙继南人本主义音乐史观逐渐明晰、确立的心路历程。《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一书,除了更为充盈的史料和更为全面的音乐分析之外,最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对黎锦晖历史形象做出的有血有肉的塑造和刻画。这种塑造和刻画,当然不是文学性的笔法,而是建立在对他的艺术人生、音乐创作、音乐观念等进行全面研究的基础之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黎锦晖关于救亡歌曲创作的深入论述,是以往有关黎锦晖音乐创作的研究中所很少见到的,该著对他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的贡献,给予了合乎历史的定位与评判,让世人重新认识到,近百年前的黎锦晖,就是高举“平民音乐”大旗,在音乐创作的内容与形式等诸多方面,都留下了深深探索印记的先行者。从“黄色音乐”和“黄色音乐的鼻祖”的贬斥否定,到“流行歌曲”和“流行歌曲创作的先驱”的高度肯定,这两种天壤之别的历史评价,体现了一位严肃而又充满人本主义情怀的音乐史学家忠实于历史的高度责 任感。
需要指出的是,孙继南对黎锦晖的历史评价,绝非为了“拨乱反正”而走向另一个赞美的极端,他深知“棒杀”和“捧杀”都是不符合唯物主义史学观的。因此,《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一书,没有回避对黎锦晖人性弱点、历史局限的评说,不虚美,不掩恶,如其所说“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显示了作者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学术品格。正如项阳先生在书评中所言:“对他(黎锦晖)的争议,究竟是他自身的问题,还是时代的问题,间或是社会的问题,透过孙先生的书,都一一给出了答案。”[16]项阳《黎锦晖:时代弄潮与世纪悲情》,《中国音乐》2007 年第4 期,第60 页。
在《黎锦晖与黎派音乐》一书结尾,孙继南不无欣喜地写道:“一位历史真实的黎锦晖,正在向我们走来。”[17]同注[15],第243 页。笔者相信,认真读罢此书的读者,亦会有相同的体会,一定会真切地感受到:一位历史真实的黎锦晖,透过一位史学家栩栩如生的音乐叙事,正在向我们走来。
弘一大师李叔同及其音乐创作与活动,也是孙继南用力最多的研究对象。很多人未必知道,李叔同在日本创办的中国第一本音乐期刊《音乐小杂志》,得益于孙继南的执着与努力,日本学者才赠予复制的珍贵音乐文物—那幅由李叔同亲自绘制的、令人过目难忘的彩色封面,才能走进中国音乐学者的视野。如前所述,孙继南研究李叔同的文章,都在史料的挖掘、考订方面做出了令人赞叹的努力。如果我们更为深入细致地研读这些文字,就会发现,这些文章仿佛是孙继南与弘一大师的一种历史“对话”。正是在这种充满人文情怀的历史研究中,弘一大师那超凡而又入世的历史形象才被勾画得血肉丰满,李叔同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生、绚丽多彩的艺术创作、悲欣交集的心灵体验,才得以清晰体现。作者对弘一大师人格的敬仰,并没有因为研究对象的宗教色彩而发生改变,这也反映了人本主义音乐史观对作者的深刻影响。
三、视域融合的历史认识论
“视域融合”,是德国哲学家、美学家伽 达 默 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提出的,有关艺术理解与历史阐释的阐释学理论。伽达默尔认为,艺术的意义在于理解,而理解既包括了带有“前见”的历史上的理解,也包括当下的新的理解,这特别体现在具有“再创造”特点的音乐艺术当中,因此,音乐的意义是向着未来敞开的。伽达默尔特别指出,“每一时代都必须按照它自己的方式来理解历史流传下来的文本”,因此,“理解就不只是一种复制的行为,而始终是一种创造性的行为”。将历史视域和当下视域相互融合,即他所谓的“视域融合”。基于这样一种关于艺术本质的认识,伽达默尔提出了一个根本的历史认识结果——“效果史”:“历史学的兴趣不只是注意历史现象或历史流传下来的作品,而且还在一种附属的意义上注意到这些现象和作品在历史(最后也包括对这些现象和作品研究的历史)上所产生的效果。”[18]〔德〕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真理与方法——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年版,第385 页。
孙继南并没有关于历史认识论的专门论述,也从未表明其治史过程中受到伽达默尔阐释学思想的影响。但细读他的音乐史学论著可以发现,他对历史人物的理解,对历史音乐的赏鉴,都带有比较鲜明的“视域融合”特点。他对黎锦晖与“黎派音乐”的研究尤其体现出这一特点。
如前所述,长期以来,关于黎锦晖及其音乐创作的历史评价,一直延续了20 世纪30 年代带有“左翼”特征的历史观点,这可谓是历史视域中所谓的“前见”。孙继南在论述黎锦晖研究的历史发展时,对这种历史视域给予了充分的理解,指出这既是由黎锦晖音乐创作的自身特征所决定,也是当时思潮涌荡时代引发批评的必然:
黎氏在创作实践中,虽有追求“雄壮”“热烈”“开展”之意,却不脱“黎派音乐”固有创作思想及艺术形式、风格之局限,随着全国人民抗日救亡热情的高涨,那种“轻歌曼舞、婉丽和谐”已不合时宜,尤其那些与救亡无关的软性歌曲依然流行于社会,因而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界的批评与指责。[19]同注[15],第221 页。
立足当代,孙继南之所以为“黎派音乐”正名,又是由于他对黎锦晖时代曲的历史评价融入了新时代的理解与阐释。以歌曲《毛毛雨》为例,孙继南认为,《毛毛雨》在当时遭到批评,与黎明晖的演唱水平亦有关系,1926 年初出茅庐的黎明晖演唱艺术尚不成熟,1934 年的录音版本就反映出更高艺术修养的表现。因此,他强调:“时代曲‘二度创作’对其风格情调的影响很大,此乃音乐艺术本身所决定,一切音乐作品莫不如此”。孙继南认为: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毛毛雨》,其中“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心”的立意,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五四”女性突破长期封建思想的觉悟。……由于歌曲本身就是“旧的音乐形式”、民俗小调,又是尝试之作,艺术、格调都未尽完善,各种不同的评议,见仁见智,并不异常。但若将其视为“淫靡”之作,则未免有失偏颇,何况这首歌曲毕竟具有自身的艺术价值。[20]同注[15],第160 页。
上述的中肯评价,相较于以往的种种贬斥与否定,不可同日而语。这种对历史音乐的批评与新的认识,无疑带有视域融合的特点。笔者相信,只要我们对当代音乐生活中令人眼花缭乱的流行音乐现象,与黎锦晖当年的“时代曲”稍作比较,就会发现,所谓“黎派音乐”与“黄色音乐”,没有任何实质的相同,新的音乐创作与审美体验,一定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人们对历史音乐的认识和评价。这样一种视域融合的历史评价并非个例。无独有偶,缪天瑞先生在谈到黎锦晖的流行歌曲创作时曾不无感慨地说过:“那个时候很多人都批判黎锦晖,认为他的音乐形式是黄色的,还有演唱的声音方面……其实现在看来不是什么黄色音乐,《毛毛雨》那首歌一点儿都不黄,比现在的好多流行歌曲健康多了。”[21]冯长春《口述音乐史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研究》,《艺术论衡》(中国台湾)复刊第9 期,2017 年11 月,第60 页。毫无疑问,当年也曾批评过黎锦晖的缪天瑞,他对《毛毛雨》的新的理解和历史评价,同样带有鲜明的“视域融合”特点,与孙继南的历史认识可以相互呼应。
笔者认同音乐研究中“视域融合”及“效果史”的历史认识观念。孙继南音乐史学论著中自然呈现出的这一历史认识论思想,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历史音乐和音乐家研究的认识与理解。
四、历史断代带来的思考
最后,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孙继南在新版《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中,将此前两版书名中的“近现代”改为“近代”,一字之差,反映了怎样的音乐历史观呢?作者在“新版补记”中曾一笔带过地提及该版的修订与“易名”之事,但并未交代易名的原因及相关学术理念论述。在为《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而作的一篇书评中,书评作者写下了带有猜想色彩的一句话:“进入新世纪之后,学界有人主张把整个20 世纪称为近代,看来不无道理。可能出于这种原因,作者把第三版《纪年》中的‘现’字去掉了。”[22]林寅之《钩沉辑佚自辛勤——读〈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一、二、三版》,《人民音乐》2012 年第8 期,第77 页。
限于眼界,笔者对于“学界有人主张把整个20 世纪称为近代”的观点无从查证,但以治学严谨著称的孙继南,在新版《中国近现代音乐教育史纪年(1840—2000)》中,将自鸦片战争以降至20 世纪末的音乐历史统称为“近代史”,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长期以来,关于“中国近现代音乐史”的历史分期一直存在几种不同的划分,常见的几种是:其一,1840—1919 年为近代史,1919—1949 年为现代史,1949 年至今为当代史;其二,1840—1949年为近代史,1949 年至今为现代史;其三,1840—1949 年为近代史,1949—1978 年为现代史,1978 年至今为当代史。此外,亦有学者以“新音乐”的诞生与发展作为历史主脉,将近代以来的音乐历史称为“新音乐史”。上述种种不同历史分期的观点,见诸大量的学术论著,此不一一举例。但是,如上所述,将鸦片战争后至整个20 世纪统称为“近代”者,音乐学界目前只见孙继南一人。他在晚年对近现代音乐史断代的观念更新,是否引起学界的认同抑或质疑,尚不得而知。笔者的理解是,作为音乐史学家,更由于《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在学界所产生的重要影响,或许孙继南将历史的眼光投向了长远的将来,也许在历史转折的某一时刻,以往的“现代”与“当代”都将成为后来人的“近代”。至于他对近现代音乐史的断代是否另有深意,现在我们无法确知,也无需做过多揣度。总之,孙继南先生在晚年以一字之变带来的新的历史观念,值得后来人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