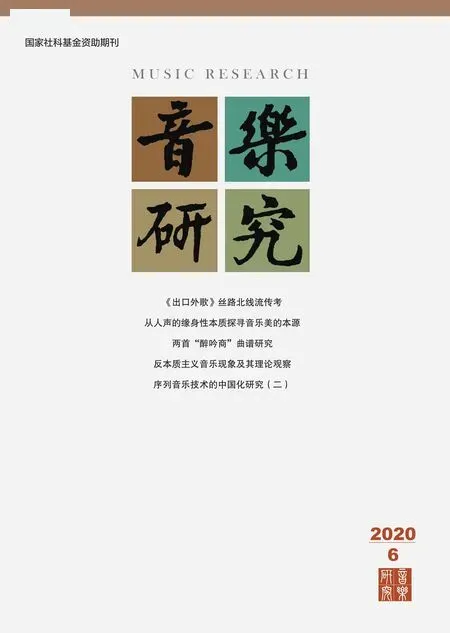三种伴奏形式与三种表述模式
文◎张振涛
在戏曲乐队待了六年,还真没把伴奏这档子事儿往深里想。“跟腔包调”“托腔保调”天天讲,好像无甚大道理。戏曲、曲艺,莫不如此。大学期间为管弦、声乐弹钢琴伴奏,接触了一批协奏曲、奏鸣曲及艺术歌曲、歌剧选段。这让笔者深感钢琴伴奏与戏曲伴奏的差异。西方伴奏独立性强,许多部分简直就是独奏曲。第一次为圣-桑小提琴《引子与回旋随想曲》弹伴奏,老师对我大声嚷嚷:“这段钢琴是独立的,你自己弹,不用顾小提琴”。这使我一下子回过神来,原来我不是伴奏,是主角。笔者真正把中西伴奏当作一个问题来思考,是在从事民族音乐学的田野调查之后。河北省保定市涞水县南高洛音乐会有种念诵方式称“对口”。所谓“对口”,就是笙管乐与诵经(文坛)的两拨人“口对口”。其实,旋律一模一样,按西方说法,管子和嗓子同声同律,是大齐奏。但乐师认真地讲,笙管是“伴奏”。这让笔者意识到,乐师所说的“伴奏”,是指以“经文”为主、笙管为辅的主从关系,其定位根本不在音乐上。中国伴奏与西方伴奏,传统伴奏与现代伴奏,各有定位。中国的托腔保调与西方的并驾齐驱,传统的主客分明与现代的互为主从,是两股道上跑的车。
世界音乐让我们遭遇到另一类“伴奏”——共鸣弦——嗡嗡作响,持续弥漫,浑然一体,妙不可言。将其比之中国烘托则不恰,喻之西方多声又不宜。其特点是既全面覆盖,又不求独立;既吞没主弦,又突出旋律。这是否可以称为“伴奏”或者根本不是我们定义的“伴奏”?三厢比较,中国伴奏之辅助性,不言自明;西方伴奏之独立性,不喻而立;共鸣弦介于两者之间,亦不立而成。“发现他者才能看清自己”。三个触点,让我们获得了一个更大也更有理趣的话题。
一、戏曲伴奏
1971 年,笔者进入山东省吕剧团乐队演奏小提琴。1949 年前,吕剧伴奏只有一把坠琴。50 年代“戏改”,吕剧成功上演了影响全国的《李二嫂改嫁》,一跃成为全省第一剧种;鸟枪换炮,加进二胡、琵琶、扬琴成“四大件”,配置来自梅兰芳的京剧改革模式,更大改观,始自移植“样板戏”。各地剧种无不搬用“钦定模式”,乐队标配—弦乐器:第一小提琴(4),第二小提琴(3),中提琴(2),大提琴(1),贝 司(1);木管:长笛(1)、单簧管(1)、双簧管(1)、巴松(1);铜管:圆号(2)、小号(1)、长号(1)。
乐队是皮,配器是瓤。交响之门开,主弦之声塞。若非政治挂帅,难免不发生“是以音乐为主还是以观众听戏为主”这一持续不休的论战,自然也会引发一小群“落伍”艺人与新型乐手之间的对垒。具体说,演奏坠琴的年轻主弦,适应新体制,幕间曲、前奏与较长间奏,停下来,听乐队造势;唱腔开始,与演员同步进入,或者说为“找不到调”的演员提供“扶手”。年纪较大的主弦,难以适应,乐队一起,找不到入口。主弦跑调,演员找不到北,乱成一锅粥。多亏指挥连比画带敲打谱台,老人家“连滚带爬”才找到入口。这类情况时常发生,惹得乐手直撇嘴。从此,配器再不敢把坠琴写得太独立。坠琴进入时,乐队拖长音或干脆停下来,免得麻烦。
更难适应的是演员。老式伴奏成长起来的演员,哪里驾驭得了大乐队,乐队一响,根本找不到调,迎面相撞,人仰马翻。原来是演员想什么时候开腔就什么时候开腔,想拖多久就拖多久,节奏是根“猴皮筋”,由着性子来,主弦跟着就行。这与杨荫浏回忆天韵社吴畹卿教授昆曲伴奏的方式是一样的。①杨荫浏《吴畹卿先生小传》:“吴畹卿在教学中,对于唱曲和伴奏,极为重视,学生学到一定程度,就要他们学会‘脱本’随着唱者的歌唱进行伴奏。他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充分发挥乐器的表达能力,依唱腔的高、低、迟、速,自如地进行托腔,使伴奏与歌唱丝丝入扣、融为一体。”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编《杨荫浏全集》(第4 卷),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年版,第17 页。
现在,天翻了,不是乐队听演员,而是演员听乐队,乐队让你进,你才能进。记得一位老演员,记不住复杂过门,乐队全奏,犹豫不决,入不了戏。乐队哄场,他急得脸红脖子粗,怒目开骂。指挥耐着性子,哄大家一而再再而三地练习。残酷现实,逼着老戏骨习惯新方式。不光样板戏令演员不敢说三道四,一大沓工工整整的总谱更让不认识谱的演员心生敬畏。面对政治、权威、现代、科学,高压重重,谁敢反抗?找不到调,敢怒不敢言,面对一大堆常常叫错名的西洋乐器,惶悚难辨!文明冲突,让艺人分裂!
新型配器,一言以蔽之,就是尽量不与唱腔相同。一班人马,步调一致,既烘托主旋律,又不尽一致。管弦乐使地方戏音乐获得音效。唱词有风吹草动,长笛走句;剧情有行军打斗,小提琴快弓;一号人物深思远虑,大提琴独白;他(她)心潮起伏,竖琴滚滚而来;他(她)豁然开朗,乐队全奏。凡此种种,皆有法可依。从样板库存中抽取、对号,是图解音乐的极端形式。不能否定现代京剧的乐队写法,这是熟悉传统的作曲家把京剧与现代管弦乐结合从而获得奇效的新路子。其中并非没有漂亮音响,也并非没有丰满配器。《智取威虎山》杨子荣唱段《打虎上山》前奏,《红灯记》李玉和主要唱段《雄心壮志冲云天》伴奏,《龙江颂》江水英唱腔《细读了全会公报》,《杜鹃山》柯湘唱段《家住安源》《乱云飞》的配器等,效果非凡,渲染气氛,铺陈意境,已可独立成篇。如果不是编排于特定剧情,如果可以删除“不合时宜”的唱词,这些作品均可列入经典。我们不会退化到脸谱时代,学术评判也不再囿于涂脂抹粉或胡乱抹黑。不能不说,那些唱段让音乐家十分振奋。
必须说明,一般人从收音机听到的唱腔,是经过处理的,唱词清晰,主次分明。乐队只在过门、间奏才放开音量。实际效果,远非如此。笔者在北京“人民剧场”看过北京京剧院演出的《红灯记》,主要演员浩亮(李玉和)、刘长瑜(铁梅)和高玉倩(李奶奶),都是一流好嗓子。但现场唱词,远没有收音机清楚。笔者怀疑,观众若无基本背得过的前提,头一回看,能否听清?这应了民谚“弦裹音,听不真”。这是现代与传统的最大矛盾。乐队压唱词的案例到处可寻。
1952 年,上级给定县秧歌团派来了作曲人员,帮助定县秧歌改进戏曲音乐,还给增设了乐器。但直至20 世纪90 年代,秧歌戏的演出进入高潮时,演员和观众双方还都要求抛掉乐器,直嗓大喊。这时,台上唱词的人和台下听词的人,都尽情尽兴,如醉如痴。艺人说:“乐器治嗓子”,意思是跟着乐器正规演唱,限制了他们的即兴发挥。观众说:“乐器一响,听不见词”,意思是加了乐器,听不准艺人的真嗓清唱,这不合乎原来的口耳交流习惯。②董晓萍、〔美〕殴达伟(R.David Arkush)《乡村戏曲表演与中国现代民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8 页。
老百姓可不管什么音乐独立与不独立,他们听的是唱词,虽然现代戏并不在乎能否获得老百姓作粉丝。上述案例,有典型性,老百姓听的是戏文,而非这里加一句长笛,那里进一段竖琴的“美容”音效。专业音乐家觉得好的,老百姓觉得花里胡哨;老百姓认可的,专业音乐家觉得单调。乡村草台上唱“姹紫嫣红”,不如说“花红柳绿”更让乡民明白!再说,民间剧团也没有财力置办那么多乐器。如同《红楼梦》大观园的赵嬷嬷所说:“谁家有那些银子买这个虚热闹去”。
此类“矛盾”的田野报告很多。广西来宾市兴宾区壮族师公戏伴奏,就是一把二胡,专业音乐家觉得单调,加入大乐队,却发现观众根本不买账,于是又恢复单调。伴奏本是扶助的小我,突变大我,必遭唾弃。20 世纪末,乡土模式正以极快速度全面颠覆音乐家自50 年代以来努力了60 多年的戏改成果。乐队保持自主权,是戏改主要内容之一。尽管以演员为主的体制在现代戏中被有目的地抑制,但在乡村依然受喜欢。这个话题在样板戏退场、老戏恢复后,差不多又回到原点。
二、钢琴伴奏与歌剧伴奏
西方伴奏大致分两类:一部分与中国相似,称“主调音乐”;一部分与中国不同,称“复调音乐”。扼要叙述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或教条化,但我们只能扼要叙述。
“主调音乐”,旋律为主,伴奏烘托。古典音乐基本属此类。典型的如舒伯特《小夜曲》、埃尔加《爱的礼赞》、莫扎特歌剧《女人善变》。莫扎特《圆号奏鸣曲》的钢琴伴奏,基本是固定音型打拍子,强拍处垫和弦。引子间奏,偶尔突出一下,转折过渡,如同戏曲过门的“镶边”“填空”,不喧宾夺主,中国人较习惯。
“复调音乐”不同,艺术歌曲的钢琴伴奏独立性很强。如舒伯特《鳟鱼》(后改为《A 大调钢琴五重奏》),钢琴六连音与八度跳跃,塑造鳟鱼形象,与独唱旋律完全不同。声乐套曲《美丽的磨坊女》的伴奏与歌唱也多有不同,《死神与少女》钢琴在低音区敲打,描述死神形象,阴森可怖。在和声框架下,声乐和钢琴各行其是,这是艺术歌曲的特点。
更典型的是歌剧,如《艺术家的生涯》咏叹调《冰凉的小手》《为艺术为爱情》的伴奏完全独立。习惯于“主调音乐”的声乐学生,没有提示音,一张口要准确唱出伴奏,非经训练,根本难以做到。笔者为他们弹伴奏时,最头痛的是弹了十遍八遍他们也找不到入口,甚至找不到音高,笔者只能死记暗藏内声部的音高,而且还要特别弹响一点。这让学生备尝辛苦,也让笔者懂得,歌剧艺术非经长期训练难以应付,找不到调的背后是中国人难以适应但必须适应的依靠伴奏的习性。
第三种类型,介于两者之间,如法国作曲家儒勒·马斯奈歌剧《泰伊斯》主题《冥想曲》(也译为《沉思曲》)。少年时演奏过单独抽出来的小提琴独奏,也弹钢琴伴奏,分解和弦,从低音涌向高音。2018 年,笔者第一次在国家大剧院看实况《泰伊斯》,了解到原来主题贯穿整个后半场。一首歌既可以独奏呈现(第一遍为小提琴独奏,竖琴伴奏),又能作为不同于独唱声部的伴奏存在(类似古诺在巴赫《C 大调前奏曲》上衍生出《圣母颂》),还能相互交叉,分镳并辔,真是绝妙无比。这让笔者对早年熟悉的独奏延伸出的“副产品”刮目相看。马斯奈充分发挥了一支好旋律的势能,生发出多重意境。
瓦格纳时代,乐队进入乐池,音量尽量不掩演唱,主腔之外,还留有巨大空间,充分表达器乐音效,这成为瓦格纳巨型乐剧不同于一般歌剧的突出看点。他笔下的乐队,时而伴奏,时而主奏,无终旋律,并行交替,很难再用主旋律、伴奏概念划分了。
2014 年9 月21 日,笔者在国家大剧院歌剧厅看了中央歌剧院演出瓦格纳歌剧《齐格弗里德》,2017 年看了《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2018 年又看了《纽伦堡的名歌手》,深切感受到歌唱家的专业化水准,在乐队全无提示的地方,歌唱家也能脱口而出,毫无障碍。
伴奏差异,反映观念。独立精神是西方艺术形态的支撑,不为伴奏而伴奏。“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布鲁尔(Brewer)提出的“最佳特性理论”认为,集体认同源于“个体的包容需要”和“个体的异化需要”两种相反动机的平衡机制。“个体的包容需要”,即个体期望成为集体一员并获得同化的需求;“个体的异化需要”,指个体渴望与他人不同的特殊需求。西方伴奏呈现的,即是该理论所解释的两种并行不悖的需求。
三、没有任何乐器以这种方式垄聚焦点
初听印度音乐,为共鸣弦的奇特效果啧啧赞叹。指板一侧,安装一排烘托衬垫的辅弦,明弹一弦,阴持数韵,延音余韵,繁复多端,既烘托旋律,又不干扰旋律,浑厚丰满,轰然作响。这是南亚、阿拉伯地区音乐的突出特征,说和声不是和声,说非和声又是和声,完全不同于“主奏是主奏、伴奏是伴奏”的划分。
印度西塔尔琴(Sitar)的底部有两个巨大葫芦型共鸣箱,宽大琴颈上有20 多个可移动的环形金属音品,上层系6—7 根旋律弦,4 根主弦,3 根共鸣弦,下层系13 根共鸣弦。低音维纳琴(Veena,或萨拉斯瓦蒂·维纳Sarasvati Vina)系列,是印度弦乐的庞大家族,两只(有的三只)巨大葫芦形共鸣箱,震震而动,复层共鸣。更令人震撼的是,演奏组合中,在维纳琴侧后方,一定要配备一件坦布拉(Tambura,一种长颈弹拨乐器)。两根弦或四根成双的坦布拉,通颈无品,不奏旋律,自始至终,拨弦共鸣。这种固定搭配,把嗡嗡作响的音效发挥到极致。
蒂莫西·赖斯《保加利亚音乐》一书描绘了东欧的“加杜尔卡”:
“加杜尔卡”为短颈梨形体,由一整块木头制成,宛如一把大汤勺。一块薄的木质音板黏合在中间碗状挖空的琴体上。用以演奏旋律的三根粗钢丝从颈头部的木质音栓穿过琴马直到系弦板。大约八根更细的琴弦位于三根演奏弦之下,调音位主要的旋律音高。这些弦并不被直接拨动,而是与演奏音高同时振动,这极大地增加了音量、共鸣和乐器音色的丰满度。③〔美〕蒂莫西·赖斯著,张玉雯译,管建华审校《保加利亚音乐》,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2016 年版,第39—40 页。
乌克兰标志性乐器“班杜拉琴”(或译“班德拉”Bandura,俄文бандура),有50—60 根竖系共鸣弦,初看像竖起来的扬琴。左臂抱琴,左手探到琴头外,如同弹竖琴,右手拨动琴板上琴弦,反手拉动粗弦以作共鸣。
北印度弓弦乐器萨朗吉(Sarangi),前排3 根主弦,下置10 根共鸣弦,指板左侧16 根共鸣弦。伊朗热瓦普(Robab),4 根主弦,12 根辅弦。西奥伯琴(Theorbo)在常规琉特琴上附加超长琴颈,排列20 余根共鸣弦,单独发展为长双颈琉特琴。西腾琴(Cittern),也是数轴杆侧,悬弦如绳。
多一根是一根,多一声是一声,一排不够,再加一排,弦外之音不但占有一席之地,而且成为缺不得、少不得的音响主体。笔者于2010 年在布鲁塞尔乐器博物馆,2011 年在法国巴黎音乐城,2017 年在日本浜松乐器博物馆,2018 年在牛津人类学博物馆,2019 年在圣彼得堡、莫斯科国家音乐博物馆,看到铺天盖地的共鸣弦乐器,品种之多,超出想象。若再把遍布欧洲的风笛持续音,以及延续至西方作曲家作品中的持续音划入视野,会看到了一个分布于中亚、南亚、欧洲的庞大家族。同类异域,迹同事殊,音响形态完全颠覆了我们的伴奏观念。
四、多余的一组弦
有篇散文题目叫“多余的一句话”,不妨改为“多余的一组弦”。它的确不是中国意义上的伴奏,也不是西方意义的和声。近年来,蒙古双声得到学术界广泛关注。马头琴、弓弦潮尔和库姆孜,都有低音弦,持续作响,形成实音弦主奏附加合音共鸣的音效。徐欣、萧梅的研究,让合音现象获得了跨境的景深。萧梅谈道:
比如形制为两根五度定弦关系的主奏弦与6—12 根辅弦的哈密艾捷克;以一束马尾弦主奏,另外张10—12 根钢丝共鸣弦的刀郎艾捷克;一根主奏弦与9—17 条辅弦的萨它尔;还有弹拨乐器热瓦普和弹布尔等都具有相同的主奏+辅弦结构。它们尽管各具特点,但其辅弦的功能皆与主奏弦构成相对固定的和音,因此更准确地说,它们并非辅弦,而是共鸣弦。有意思的是,上述艾捷克与萨它尔与蒙古族弓弦潮尔的追求类似,即以丰富的泛音与基础音结合。有意思的是,在有关艾捷克和热瓦普的资料中,亦可见关于它们从伊朗等地传入后增加了共鸣弦的记载。如马成翔在对清代史料的梳理中,指出艾捷克最早起源于伊朗,公元14 世纪以前传入中亚,流传在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以后传入喀什,增加了共鸣弦,形成了有共鸣弦的艾捷克形制。尽管我们现在在十二木卡姆的乐队中看到的艾捷克,是近代以来改良了的去掉共鸣弦,而将主奏弦增加为4 根的乐器,但刀郎艾捷克和哈密艾捷克却保留了清代以来的形制。刀郎热瓦普也有早期两根皮弦弹奏、后发展了共鸣弦的经历。④萧梅《文明与文化之间:由“呼麦”现象引申的草原音乐之思》,《音乐艺术》2014 年第1 期,第46 页。
以此而论,汉族弹拨乐器同样可以找到共鸣弦痕迹。如南音琵琶、苏州评弹琵琶、陕北说书琵琶和云南洞经琵琶,它们的第四根弦基本不弹,其中同样隐藏了中亚乃至风靡地中海文化的共鸣弦痕迹,其遗风遗绪,依然可辨家族身影。置而不弹的孤悬之弦,终于对接到广阔的共鸣弦世界,充满疑惑、不敢妄下结论而悬着的心,也落到了肚里。如此连接,令学术界冒出来许多要说的话。夏凡在博士论文中提到共鸣弦的地方有数处,她描述道:
如热瓦普的共鸣弦。以喀什热瓦普为例,第一根外弦为旋律弦,紧挨的第二根弦也可当旋律弦,也可当共鸣弦,之后五根都是共鸣弦。传统喀什热瓦普为五根弦,热瓦普演奏家达吾提·阿吾提(1939—)在此基础上加入两根共鸣弦,喀什热瓦普变为七根弦,定弦顺序为:C4—G4—D4—A4—E4—B4—F4。两根共鸣弦加入,与演奏曲目有关,古典热瓦普终止音,常落在#F 和B 上,加入#F 和B 共鸣弦,变得明亮。如《卡迪尔·麦吾兰》,终止音为B,若无共鸣弦B,完全不同。可见,共鸣弦不仅起到改善音色作用,还能改善延续局限性,“民族味道就出不来”。⑤夏凡《有品乐器律制形态研究》,中央音乐学院2011 年博士学位论文。
“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⑥刘勰著,周振甫注释《文心雕龙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版,第518 页。。共鸣弦定弦,一般为主弦五八度,主属基频,恒定敏捷。一般人不在意也不关注定律问题,虽然听的、唱的、弹的无不与此有关。热瓦普、艾捷克、萨它尔,大名鼎鼎的冬不拉,须臾不离的卡龙,孤悬之弦都有预设。对普通人来说,音乐是个数字有限且因为有限而有点幼稚的世界。持续振荡、折腾得热热闹闹的数十根弦,靠什么规律发挥音效,无人深究,宁愿相信“闲置”的弦无关痛痒。其实,共鸣弦必须经过计算,才能如人所听的那样和谐悦耳。夏凡提供了共鸣弦定音与实践挂钩的例证。
是什么促使了地中海文化圈五弦里拉发展到60 余根弦共鸣弦的雪球效应?这不能不让人注意到该区域音乐文化占主导地位的宗教性。宗教仪式需要迷幻声响,共鸣弦混响,余音袅袅,洋洋盈耳,作用于人耳的感受,就是让聆听者超越世俗世界。主弦以少为多、辅弦以弱为强的过人之处,就在于提供了宗教所需的声景。朦胧造境是其存在理由。如此看来,信仰沉迷与共鸣弦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笔者禁不住把这类音效与“非遗”展演上的木卡姆表演联系起来。弹拨尔、都塔尔、卡龙,在一群来自南疆莎车、身强体壮的老头手中爆发出巨大感染力;表演者或盘腿而坐,或屈膝而跪,昂头闭目,放声高歌,如处无人之境。活力无穷的维吾尔族老汉,与中国音乐研究所乐器陈列室简其华拍摄于50 年代的图片相接续。那组悬挂图片中,一位跪坐拉奏艾捷克的维吾尔族老人,凹进去的深目和囧囧发光的眼神,令笔者至今难忘。粗糙的手,就是琴弦上急速如飞的手,就是唱到兴头上抹抹嘴再端起“葡萄美酒夜光杯”的手。诸弦复合、轰鸣大作的音效,正是文化现场所需要的。
我们习惯于音响的清晰度,乃至怨怼某些乐器的致命“弱点”是余音不能立刻“停摆”。中央民族乐团排练过程中,笔者听过几位指挥抱怨坐在前排的扬琴音响,形容其音响太“脏”。尽管改革扬琴可以加踏板,但手脚并用,难以普及。话说回来,扬琴若不嗡嗡作响,就没了特点,然而,一旦进入乐队,优点变缺点,扰乱纯净,令众人不得安宁。这一度令指挥们进退忧虞,欲舍之不取,则虑其怀怨;欲待之合势,则苦其稽延。如果把此点作为一个不同文化体相互适应的问题看待,就深刻地反映出古老的共鸣弦乐器与现代乐队追求之间难以弥合的矛盾,并从中窥探大量附带共鸣弦的弹拨乐器被排除于现代乐团之外的根结。一件乐器能否进入现代管弦乐团,能否成为总谱中的一个声部,已经成为行情、等级以及社会认可度的标志,也成为该类乐器在现代命运中通蹇祸福的标志。
我们基本上属于不懂伊斯兰音乐文化的人。谈起欧洲音乐,笔者凭借少年时拼命学西方乐器的一点底气还能多少说几句;谈起印度、伊斯兰乐器,根本说不出什么道理,甚至观念中隐含着对不“干净”音响的敬而远之。从小种下的嫌弃共鸣弦“脏”的音响观念,难道不是单一文化观与西方中心主义的余音袅袅?即使在民族主义越来越淡,世界文化越来越普及的当代,这样的观念依然存在。我们曾以学习钢琴、小提琴作为一种值得自豪的身份,但如今,单一实践已经成为我们身上的“负资产”。从来不曾碰过甚至不曾见过的印度与阿拉伯乐器,使我们对其音响难以解读乃至产生亲切感;看到印度音乐家拉维香卡双目紧闭的陶醉及其家班的其乐融融,我们只能随心向往之,却完全不懂。不懂语言,无论我们花多少精力关注博物馆的印度与阿拉伯乐器,都没有能力解读既不懂演奏也不懂理论的共鸣弦世界。
大部分中国人对伊斯兰文化的认知,明显比不上佛教文化或基督教文化,这不完全是“偏见”,更主要的是“无知”。而这,与我们的博物馆数量太少,且视野狭窄不无关系。⑦陈平原《大英博物馆日记》(外二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 年版,第88 页。
关键时刻、关键会议,发挥了作用。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琉特琴专题会议,带来了许多信息。陈自明《世界民族音乐地图》(2007),也提供了大量资料。如果多一些像上海音乐学院召开的琉特琴会议,多一些像萧梅、陈自明一样开启新知的朋友和老师,如果早一点具备人类学知识,那么,学者的听觉会发育得更全面一点。
结语:三种伴奏、三种模式
伴奏在一个层次上是音响,在另一个层次上是行为,在更高层面上则是处理主属关系的准则。伴奏与其说是三种事实,不如说是三种文化模式的表述形式。保腔不只是伴奏,更是文化观念和社会结构的反映。托腔、包腔、裹腔,讲究的是与主旋律步调一致。如同戏曲剧团“鼓老”嚷嚷的:“另立门户,找死呀!”什么叫主旋律,什么叫烘托,什么叫红花,什么叫绿叶,主辅分明,植根于中国观众获取信息的基本习惯,更根植于中国人讲究秩序的伦理观念。“统帅专一,人心不分,
号令不二,进退可齐,疾徐如意,气势自壮。”⑧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6,中华书局1956 年版,第7545 页。整齐寓意,深意存焉。如此看来,伴奏就成了解读集体无意识的绳结。开始并未打算将伴奏确立为某种模式,却无意间看到了三种法度。此前未及感悟,盖因不具备世界视野和成论理据,而新的理据也可以把早年经历变成叙述资源。
康拉德《什么是全球史》⑨〔德〕塞巴斯蒂安·康拉德著,杜宪兵译《什么是全球史》,中信出版集团2018 年版。概括道:新的全球史是将现象、事件和进程置于全球脉络中,超越民族主义和欧洲中心论。他提出三种全球史:作为万物历史的全球史;作为联系史的全球史;以整合概念为基础的全球史。
人类学从微小入手,开膛破肚,探视艺术形态背后的社会类型。汉族以整齐划一为核心,西方以并行不悖为核心,印度、阿拉伯地区则以众筹共振为核心。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观中国伴奏,则觉世界所长与所阙;观世界伴奏,则觉中国所长与所阙。上览欧洲体制以为则,下观共鸣弦体制以为律,中国形态不言自明。标本的意义在于醒目,别殊类,序异端,“抒意通指,明其所谓,使人与知焉,不务相迷也”⑩同注⑧卷3(一),中华书局1956 年版。。将对立坐标,纳入阐述,就能对跨文化解读提供基料,或许这也算新型全球史的微型切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