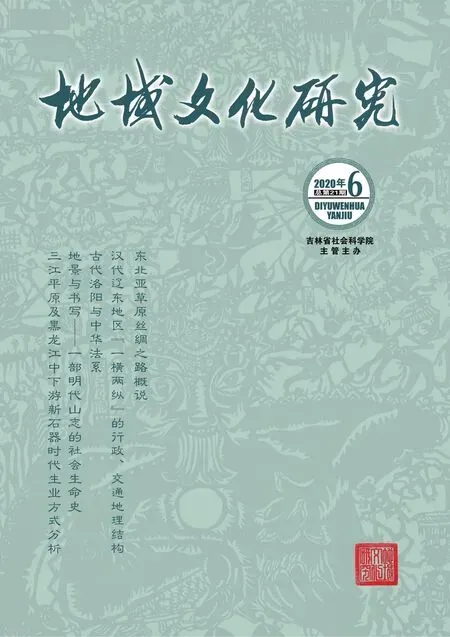今佚宋元佚文三则辑考及其中所见吴越社会生态
姜复宁 周琦玥
方志被誉为地方史料的渊薮,其中收录了大量的地方文献,历来为总集编纂者所推重。志书编纂者所搜罗的地方文献,往往来自于当地的金石碑刻,章学诚曾指出“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人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①(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20页。,将其提升到重要历史文献的地位。并进一步从方法论的层面指出,在纂修史志时“至墓志传赞之属,核实无虚,已有定论,则即取为传文”②(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820页。。其论继承“写远追虚,碑诔以立”的传统,又发现了碑刻文献在史志书写中的渊源,为后人重新思考碑刻文献的史学价值提供了启发。与着眼全国情势的正史相比,碑刻文献多为邑人所记当地事迹,更为注重乡邦耆献。因此许多为正统史家扬弃,或未为正史作者寓目的地方性史料,都在方志中得到载录。特别是宋代之后的志书,更是记载详细,恰如张国淦先生所言:“方志之书,至赵宋而体例始备。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③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页。,具有极强的史料价值。
自远古时期长江下游地区人类社会初现雏形,吴越两地便开启了各具特色而又相互交融共鉴的独特文化发展历程。周太王之子太伯、仲雍南奔荆蛮,“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余家,立为吴太伯”,可见吴地先民也即“荆蛮之人”,早在远古时期就已在此休养生息,而后在太伯、仲雍时代逐步成为共同体。《史记》记载了周武王封周章为吴君一事:“是时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后,得周章。周章已君吴,因而封之”。①(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446页。越国则为姒姓方国,“越王勾践,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②(汉)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1739页。吴越两国虽然始于不同的部落联盟,其考古文化谱系亦不相同,但由于两国地理位置相近,且两国之间交流频繁,因而在文化上有着诸多相同特质,这也成为两国文化可以在较大区域内呈现共性与融合的内在基础。
吴越文化形成的外在重要原因则是春秋晚期两国连绵不断的交战。吴越两国在春秋晚期国势均臻于强盛,吴国寿梦于此时称王,“寿梦立而吴始益大,称王”。《史记》认为这是吴国强盛的发端。《左传》记载了寿梦此时的攻伐:“吴始伐楚、伐巢、伐徐”,“蛮夷属于楚者,吴尽取之,是以始大,通吴于上国”。③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835页。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记·伍子胥列传》中对吴国对外战争的记载,称其“西破强楚,北威齐晋,南服越人”,明确指出了吴越两国的征战。而越国至勾践时兴盛,吴越两国开始了长时间的争霸战争,最终吴国为越国所灭。这些旷日持久的战争,使得在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状况、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诸多相同特质的两国在文化上相互交融,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吴越文化。
地域广袤、水网密布、土地肥沃的特殊自然环境为吴越地区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兼之历史上长期广泛在其疆域内存在的故国文化气质遗存,吴越两地的文化事业得到长足发展,表征之一即地志勃兴。这些地志多是地方官吏或当地知识阶层中对地域文化抱有热爱者,游历山川,踏访古迹,采摭旧闻而成。因其成书时代与记述时代相合,所记载的又是身在吴越之人所记的当地之事,因而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也为后人所推重。但部分吴越地志或囿于作者声望寂寂无闻,或限于所载地域过于狭窄,抑或因刻印数量较少,因而未能得到广泛流布。其中所保存的文学史料,往往有溢出文学总集之外者,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全宋文》《全元文》在编修时,对地方文献给予了高度重视,征引大量方志、碑刻资料。然而,总集的编纂要求“巨细兼收,义取全备”,实际上很难真正达到囊括无遗,往往存在漏辑之文,尚俟进一步填补。今就平日读书所得,对部分吴越地区方志文献著录而全集失收的宋元佚文予以补辑,为吴越文化,特别是宋元时期吴越社会生活风貌研究提供可资参考的材料。
一、今见三则宋元佚文辑录
流传较稀,鲜见今人提及的两部吴越地区旧志《蒲岐所志》《白石山志》,对地方文化,特别是当地的文学创作给予高度重视,广收艺文、碑铭,保留了一批宝贵的文学文献。同时,两书虽成书于清季,但均具有明显的承嗣性特征。如《蒲岐所志》卷首的“凡例”中明言“旧志创自明弘治年间陈公载旧稿也”,而后明人朱声振,清人胡光仁、倪启辰对此书予以“增修遗迹”,最终撰成今本《蒲岐所志》。④(清)倪启辰著,邹星伟、崔宝珏校注:《蒲岐所志》,收入乐清文献丛书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327页。《白石山志》的成书情况与之类似,据戴咸弼为此书所作序言可知,“盖施君六洲旧编,而陈君璞生重为增辑者也”,而“施君六洲”也即施元孚在“旧编”的序言中称“遍寻幽崖绝壑,剔断碑之斑藓,刮摩崖之层苔。既又博稽典故,旁采传文,取旧志修饰之”,可知施元孚的创作也是有明人原作作为底本的。①(清)施元孚著,邹星伟、崔宝珏校注:《白石山志》,收入乐清文献丛书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9页。两书的底本均为明人所作,与宋元时期相去不远。后世增辑重订者对前代著作的承嗣,使得志书具有了层垒性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明人著述的原貌。因此,现在看到的清本方志中对宋元旧文的记载实际源自于“去古未远”的明人记载而非清人重辑,具有较高的可信度,可以资补辑宋元佚文。现将其中所收录的三则宋元佚文以时间顺序辑录于下,并略加申说。
(一)真德秀《太医院大承德璠陈公碑》(作于1216年)
陈公璠者,其先闽之长溪人也。祖安道公徙居乐清岐山已三世矣。公之为人,博学好问,不拘小节,将拟大展底蕴。适遘金元迭起,志勿获伸,深怀愤叹,不复仕进。精炎帝岐伯之道,急于济人,不以贫富二其心。庆元六年夏五月,光宗皇后有疾,太医院束手无策,诏求天下良医。公时年四十有一矣,有司敦礼肃请,于是应诏而起,抵京见上。上甚礼遇之,宣入宫,诊既毕,出便殿。帝问卿:后疾尚疗否?公对曰:臣诊后疾,脾脉极虚,见是泄泻二疾作楚。帝善之曰:太后尚由坐蓐患脾泄,每至产月,旧疾必作,但未有若是之甚,餐粥半月不入汤药。今卿得其精,治之必有良剂矣。公曰:不难。用蜜半斤、姜三两、人参三两、木香二两调和,得所以进,服后七日觉必思粥。服之,不久乃醒,果然思粥。自是调理渐瘳。帝嘉之,厚以金帛,擢太医院大丞。嘉定乙亥四月初七日丑时卒于京。距生绍兴乙酉五月十八未时,享年五十有一。配甄氏。子二,长应镝,娶李氏,次应锷,娶金氏。女二,长适姚玘,次适孙文。御赐归葬。冬十月乙酉,二男奉柩归葬于岐山郡马垄侧。值予入京言事,二子泣血乞志铭于余。余尝获公祛除呕恙,未遑报答,爰慰志铭之请,因书其概而铭之曰:
陈氏之先,大舜之裔。自胡公满,传四十世。有公特达,无书不纪。精于医道,由仁由义。御葬岐山,古今隆遇。冀佑后人,绳绳勿替。
嘉定丙子三月十五日,江东转运使副使撰。丞务郎李天休书丹并篆额。
按:本文见《蒲岐所志》卷下《金石》,无署名。②(清)倪启辰著,邹星伟、崔宝珏校注:《蒲岐所志》,收入乐清文献丛书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439-440页。但文中“嘉定丙子三月十五日,江东转运使副使撰”,提示其作者信息。嘉定丙子为嘉定九年(1216),《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五》载嘉定九年(1216)“二月二日,权发遣宁国府张忠恕与宫观。以江东运副真德秀言其曩寸灵川,污秽无检,为宪臣所劾”③(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079页。,“六月二十一日,知广德军魏岘与宫观,先是,知广德军魏岘言本军教授林庠不职,得旨放罢。既而江东运副真德秀复言:乞将臣并赐镌斥,以惩差委失当之罪,臣见今待罪。寻诏真德秀无罪可待,魏岘与宫观”。④(清)徐松:《宋会要辑稿》,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第4080页。《宋史》在记载真德秀生平时提及其外任江东转运副使时称“时史弥远方以爵禄縻天下士,德秀慨然谓刘爚曰:‘吾徒须急引去,使庙堂知世亦有不肯为从官之人。’遂力请去,出为秘阁修撰、江东转运副使。”⑤(元)脱脱:《宋史》,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59页。真德秀《江东漕谢到任表》记述“臣已于二月初一日就本路信州永丰县界割职事讫者”⑥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1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144页。,而魏了翁为真德秀所作《真公神道碑》载“八年春,始领漕事”,综合可知真德秀于嘉定八年(1215)二月正式就任江东转运副使一职。嘉定十年(1217)冬季,诏除右文殿修撰知泉州,真德秀不再担任江东转运副使一职,刘克庄《真公行状》记载真德秀在江东任职时赞其“江东二年,凡下车例册及台阃戎司之馈,以至太夫人诞日诸司所奉寿礼,皆不入私囊,专储之以助赈施”。①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26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57页。行状中所称“二年”,恰与嘉定八年(1215)春到嘉定十年(1217)冬的时间相合,可知真德秀在江东转运副使任上的具体时段。则嘉定九年(1216)二月至六月,江东转运副使均为真德秀。此文作于嘉定九年(1216)三月,恰在此时间区间内,可知此文作者为真德秀。
《全宋文》卷七一三五至卷七一六〇收真德秀文数百篇,但均为拟诏、奏札之类公文,失收此篇。②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1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23-451页。此文为真德秀应陈璠之子所请而作的墓志铭,记载了陈璠的医术。同时,此文也是目前所见为数极少的真德秀文学创作,对于研究其文学创作有所裨益。且文中提及“冬十月乙酉……值予入京言事”,也保留了一条不见载于史籍著录的真德秀行迹。由文末所署时间,可知此文作于宋嘉定丙子年,即宋嘉定九年(1216)。
(二)卢祖皋《钱文子圹志》(作于1221年)
公姓钱氏,讳文子,字文季。其先居晋陵,后徙钱塘。五世祖尚,端州司理参军,自钱塘徙温之乐清。曾祖洁,祖忠卿,皆不仕。考朝彦,累赠至朝散大夫。妣孙氏,赠宜人。公生于绍煕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淳煕十四年补太学生,绍兴二年上舍释褐两优,授文林郎、吉州判官。任满,改宣教郎,知潭州醴陵县。入朝为太学博士。出知台州,改常州。罢归主管台州崇道观。除潼州路提点刑狱,未上,改成都府路转运判官,迁湖北路提点刑狱。被召,除吏部郎官,迁宗正少卿。乞补外,除直显谟阁,知太平州。寻改淮南路转运副使,兼提点刑狱,提举常平茶盐铁冶。升直宝文阁,复知太平。累乞致仕不允,遂乞待阙州郡,改知宁国。及期,又力辞。主管成都府玉局观、亳州明道宫。有旨转朝散大夫,守宝文阁致仕。嘉定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终,享年七十有三。娶吴氏,封宜人。子释之将受公遗泽。女嫁宣教郎卢祖皋。孙男岩,女一人。明年十月十七日葬于所居白石岩北灵山之源,是为铭,以纳诸圹。祖皋谨识。
按:本文见《白石山志》卷之末《附金石》,署名“宋卢祖皋”,为卢祖皋为其岳父钱文子所作的墓志铭。③(清)施元孚著,邹星伟、崔宝珏校注:《白石山志》,收入乐清文献丛书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229-230页。《全宋文》卷六九一二收卢祖皋文一篇,失收此篇。④曾枣庄、刘琳:《全宋文》第302册,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440页。据《白石山志》载,此刻石“在白石赤水洋灵山,碑石高二尺二寸,阔二尺五寸。志文共十八行,行二十字,末行六字。每字径八分,皆完好,楷书”。⑤(清)施元孚著,邹星伟、崔宝珏校注:《白石山志》,收入乐清文献丛书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230页。明人傅传就曾关注此刻石,并指出刻石中所载的卢祖皋与钱文子的翁婿关系值得注意,前代史书记载卢祖皋时,“并不言文子之婿,此志可补其阙”。
卢祖皋向以《蒲江集》名世,对其散文的探讨则因囿于材料之限而鲜见论述,此文可资参考。由文中“明年十月十七日葬于所居白石岩北灵山之源,是为铭”,可知此碑铭作于钱文子去世第二年,即宋嘉定十四年(1221)。
(三)冯福京《旌忠庙记略》(作于1304年)
有元统一天下,诏忠臣孝子之庙有司修理,所以隆节义、励风俗也。乐城旧有节毅侯庙,岁久倾敝。大德甲辰间,父老相与葺而新之。惟侯以忠贞遗烈,贻福乡民,旱涝疾疫,靡祷弗应。祭法所谓以死勤事,御灾捍患则祀之也。或曰庙宜于死之地,不宜于生之乡。予以为侯英爽,生死不二,无在不在。昔伍子胥生楚死吴,而吴楚皆有子胥庙;关云长生河东,死荆州,而河东荆州皆有云长庙。可举一而废百耶!
余有感焉:侯生于今,百有余年,庙又几五十年,而邦人共事,罔敢不恪,是区区者诚使之。以是知忠毅之节,著于人心者,万世一日也,徼福云乎哉。因作迎享送神之诗,使岁时歌之。侯姓侯氏,讳畐,字道子,号霜崖,著有《霜崖稿》。元大德甲辰九月既望。
按:本文见《蒲岐所志》卷下《艺文文外编》,署名“邑侯冯福京”,注明引自《侯氏谱》。①(清)倪启辰著,邹星伟、崔宝珏校注:《蒲岐所志》,收入乐清文献丛书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381页。《全元文》卷一〇二八收冯福京文十篇,失收此篇。冯福京“历庆元府学副教授,元贞元年(1295),以登仕郎遣昌国州判官,后兼巡捕司”。②李修生:《全元文》第32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05年,第275页。此文为冯福京为当地百姓重修旌忠庙而作。据《蒲岐所志》卷上《叙山》可知蒲岐城西龙穴山“上建旌忠庙,祀宋节毅侯侯畐公”。③(清)倪启辰著,邹星伟、崔宝珏校注:《蒲岐所志》,收入乐清文献丛书第二辑,北京:线装书局,2013年,第335页。由文末所署时间,可知此文作于元大德甲辰年,即元大德八年(1304)。
二、由方志佚文中窥见的宋元吴越文化特征
两部方志在空间上均属乐清,长期受到吴越文化影响。虽然两志最终成书的年代存在歧义,但却可以相互赓续,成为连续的链条。因而两志可以作为具有共同文化特质和密切关联的方志予以考察。通过对两部志书中所载录的宋元佚文进行考察,可以窥见当时的吴越文化特征与社会风貌,也是一种将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和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尝试。
(一)由墓志书写看吴越文化的史传文学传统
重视史传文学与乡邦史实,向来是吴越地区知识阶层的文化传统。“赵晔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晔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④(宋)范晔:《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337页。。早在汉代,赵晔就已编联钩稽吴越地区史实,形成《吴越春秋》以记其事。嗣后的《越绝书》赓续这一创作特色,将历史事实与文学创作有机融合起来,形成了吴越地区别具特色的史传文学传统。“史者,使也,执笔左右,使之记也”,“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⑤(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6年,第69-70页。这种兼通文史的史传书写使得吴越地区的文学作品往往记载史实翔实可信,保存了诸多历史资料。
《太医院大承德璠陈公碑》《钱文子圹志》均为碑记,通过记述逝者生前的事迹以表追思之意。“夫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⑥(唐)刘知几著,(清)浦起龙通释:《史通通释》,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第14页。,早在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几便对史学作品中的叙事极为推崇。章学诚更是敏锐地指出“古文必推叙事,叙事实出史学”①(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55页。,认为叙事文学的发轫与繁盛均与史学息息相关。以这样的视阈考察上述佚文中的两则碑记不难发现,在重视文学性的同时,两则碑记更带有明显的史学意趣。无论是《太医院大承德璠陈公碑》对陈璠诊疗过程中言辞问对记载之详细,还是《钱文子圹志》对钱文子一生历任官职及数次辞官归道时间的确切记载,无不跳出了空谈义理的藩篱,通过选取有代表性的事例作为碑传创作的主体与立足之本,使文学作品带有浓厚的纪实性特征。这种通过典型故事的典型细节,对传主进行深入刻画的写作手法,继承了吴越文化区一贯重视史实的传统与学风。
(二)由家风承嗣看吴越文化的家学渊源
江浙地区高度重视家族、世系的凝聚与传承,“昔者, 越之先君无余, 乃禹之世, 别封于越, 以守禹冢”②(汉)袁康、吴平:《越绝书》,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17页。,“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 乃封其庶子於越, 号曰无余”。③(汉)赵晔:《吴越春秋》,台北:世界书局,1980年,第35-36页。而吴越地区同时又自古尚文,家族观念与尚文传统的融合,恰如陈寅恪先生所言“学术中心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④陈寅恪:《隋唐渊源制度论稿》,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7页。,最终熔铸成了吴越地区学术家族勃兴、家学渊源深厚的文化色彩。这种重视家族文脉传承的特质,在方志记载中亦展露无遗。
真德秀对陈璠后人谆谆教导,期望“冀佑后人,绳绳勿替”,传承“有公特达,无书不纪”的家学渊源。由卢祖皋对钱文子家世的记载更是可以看出,钱氏家族累世以读书为志业,钱文子的道德文章自不待言,而其“子释之将受公遗泽,女嫁宣教郎卢祖皋”,其子继承父志,女儿亦嫁于诗礼人家。这些个案所投射出的恰是宋元时期吴越一带“文教渐摩之久……惟其所谓尚礼、敦庞、澄清、隆洽之说则自若,岂诗所谓美教化、移风俗者欤”⑤(宋)范成大:《吴郡志》,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页。,高度重视家风传承与家学渊源的社会风尚。
(三)对忠义传统与儒家信仰的高度认同
《旌忠庙记略》所记百姓捐资重修旌忠庙,“父老相与葺而新之”的史实,对侯畐抗击叛军的忠义气节给予高度赞扬,并说明了时人对“忠臣孝子”“忠贞遗烈”的赞颂,体现着儒家忠孝节义的道德理想,投射出吴越地区民众对前代忠烈之士的精神认同。
而冯福京作为深受吴越文化影响的当地士人,其创作目的在于“因作迎享送神之诗,使岁时歌之”。早在上古时代,文学的教化作用和治世功能就展露出来,并被运用在教育活动之中。《尚书·舜典》记载了舜帝对夔的政令:“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孔颖达认为这样做的用意在于“能教正直而温和,宽宏而能庄栗”,“诗言志以导之,歌咏其意以长其言”,“八音能谐,理不错夺,则神、人咸和”。⑥(唐)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收入(清)阮元《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106页。这种重视文学教化作用的传统在后世不断深化发展,文学的治世功用最终臻于“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地位,也成为儒家诗教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重视文学教化作用的传统为后世学者所承嗣,此处冯福京将“文以载道”之心倾注于碑记之中,欲使百姓铭记侯畐忠烈事迹,借以为儒家信仰张目,也体现出儒家信仰在当地广为流布的地域认同。
(四)民间信仰发达与宗教融合日趋紧密
吴越地区为中国先民筚路蓝缕,开创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这种与上古史的同声相应,使得吴越文化中往往保有多神信仰的遗存,也为后世民间信仰的发达提供了思想史的土壤。以儒家思想为统摄的冯福京《旌忠庙记略》,并未将民间信仰斥为“怪力乱神”,而是记载了民众自发修筑旌忠庙,“惟侯以忠贞遗烈,贻福乡民,旱涝疾疫,靡祷弗应”,将忠烈之士神化为具有当地文化色彩背景地域护佑者的民间信仰特征,具备一定的民俗与地域文化研究价值。
此外,宗教融合的日渐紧密也是吴越文化发展过程中值得关注的思想轨迹。卢祖皋《钱文子圹志》,其中所记述的主人公钱文子,以科举登第,是儒家思想的信徒。但纵观其一生,数次罢官而归,“主管台州崇道观”,“主管成都府玉局观、亳州明道宫”,在道观中任事。这种游走于儒道之间的人生轨迹,恰是钱文子自幼所处的以开放包容为主基调的吴越文化内在影响的外化。同时这也为我们考察宋代道教与儒学的融合共鉴提供了第一手材料,对研究吴越地区道教史具有一定的资料价值。
结 语
以上三则佚文对断代文学总集进行补充,可以收到扩充宋元作家序列、增加宋元文学作品数量之效,具有一定的文献学价值。同时这些来源于地方志所收录的文献,多保留文章的原始面貌,而其作者亦多为当地文士,往往可以代表一时一地的文化特质。这些材料对我们研究宋元社会生活,特别是江浙一带民众的生活状态所反映出的吴越文化特征大有裨益。同时这也是中国古典文献学、历史学研究与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尝试。
此外值得我们关注的另一个问题在于方志文献中所载录的众多地方文献的来源。本文所辑考的三则文献中,《太医院大承德璠陈公碑》一则由其命名便可以明确看出乃是碑文。而《钱文子圹志》则是为钱文子所作的镌刻于石上,随其棺椁葬于地下的一种特殊墓志,也可以归为金石文献。至于《旌忠庙记略》,由文中所载“父老相与葺而新之”的时间为“大德甲辰间”,而其后的落款也与此相同。古代兴修庙宇往往撰写碑记,勒石记事,因此这一篇纪文当为旌忠庙的记碑。综合来看,这三则佚文其实最初均存留在碑刻当中,嗣后为地方志编纂者采撷入志,可谓是金石材料的纸面化改写。
金石史料较之纸质文献,“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词当时所立,可信不疑”①(宋)赵明诚撰,金文明校正:《金石录校正》,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85年,第1页。,因其载体的特质而具有更强的真实性。同时以“写远追虚,碑诔以立”为刊刻旨归的金石碑刻,因其不可移动性和碑文或署刊刻年代,或署有刻工名号可资系联断代的特点,往往具有时间与地点的确定性,也即往往能提供很具体确切的时间、地点等。这种特质使得金石碑刻在中国史研究领域久为人推重,“至坛庙碑铭,城堤纪述,利弊论著,土物题咏,则附人物产、田赋、风俗、地理诸考以见得失之由,沿革之故”,甚至可以作为史传书写的重要立论依据。由此来看,在文化史研究领域,金石考证、方志著录的诸多金石文献的重要性不容小觑,值得我们予以充分重视。
但目前在考证地方文化时,对方志文献中所载录金石碑刻等内容的重视尚俟加强,对新材料的发掘也存在着诸多短板。总体来说,目前所能见到的对新材料的介绍与考释还是较少的,以金石文献作为研究材料进行研究时,往往仅以诸如《金石萃编》《山左金石志》《八琼室金石补正》等金石文献总集作为材料来源,这在提高了研究效率的同时,也带来了忽视新见材料证据的风险。因此研究者应充分重视文献材料在地域文化研究中的地位,孔子就曾指出“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可见文献材料在文化研究中的基础性作用。以辑佚为基础,以传统文献学的考据方法为主,间以现代的文化学、民俗学研究理论为参照的研究,一方面具有文学文献学的价值,对于推动断代文学图景的勾勒和中国文学发展史、文学思想史的研究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又颇具文化学,特别是地域文化研究的价值,佚文虽常常是片羽吉金、鸿爪雪泥,但却往往保有值得重视的第一手材料,值得在辑佚完成之余,充分考虑其在相关学科研究中的意义与价值。同时,以方志所载佚文作为地域文化研究的材料,也凸显出地方志作为历史资料渊薮的重要价值,对地域文化研究中资料的搜集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提示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