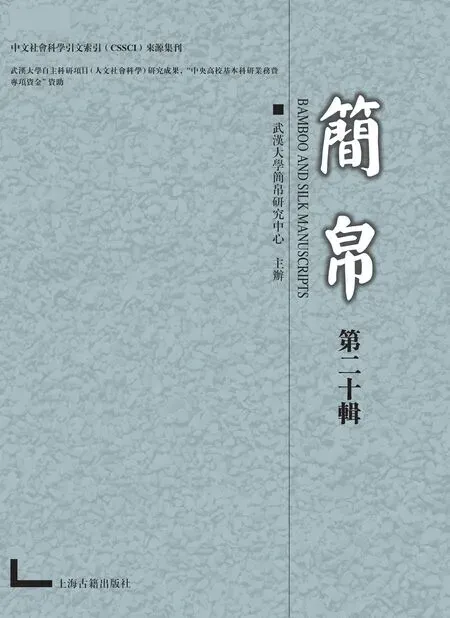吕后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發覆
——兼談漢初的刑罰序列
宋 潔
關鍵詞:三族罪 妖言令 夷三族之令 辛垣平 刑罰序列
《漢書》所載吕后元年“除三族罪妖言令”的問題,一直以來受到中外學者的關注。該問題的複雜性在於吕后所除的“三族罪”“妖言令”,在其後不久的文帝時期又再次廢除,這就造成了短時期内重復廢除的問題。針對這一重復廢除的問題,學者提出了各自不同的看法。因此,有必要先對過往研究做一梳理分析。
一、吕后“除三族罪妖言令”問題之回顧
先看“妖言令”的問題。漢文帝二年(前178),詔除“誹謗妖言之罪”。《史記·孝文本紀》云:
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賢良?其除之。
可見,在文帝剛登基不久就廢除了“誹謗妖言之罪”。其與吕后元年(前187)“除妖言令”相隔僅九年。針對這一現象,諸學者提出了各自的看法。顔師古認爲吕后與文帝之間曾重設“妖言令”;①師古曰:“高后元年,詔除妖言之令,今此又有妖言之罪,是則中間曾重復設此條也。”《漢書·文帝紀》,中華書局1962年,第118頁。梁玉繩、大庭脩認爲文帝詔文所説“誹謗妖言”中的“妖言”二字爲衍文;②“《漢書》紀、志高后元年正月詔除妖言令,而此又有妖言之詔,師古以爲中間曾重復設之。然詔中無一語及妖言,《名臣表》止言除誹謗律,景帝元年十月詔,歷敘孝文功德,但云除誹謗而亦不及妖言,則師古重設之説未確,疑‘妖言’二字是羨文。”梁玉繩:《史記志疑》,中華書局1981年,第258頁;大庭脩著,林劍鳴等譯:《秦漢法制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4—95頁。張建國、高敏認爲吕后並未廢去“妖言令”。③參見張建國:《夷三族解析》,《法學研究》1998第6期,第143—157頁;高敏:《〈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諸律的製作年代試探》,《史學月刊》2003第9期,第32—36頁。案:需要注明的是,張先生認爲吕后所除妖言令僅是“事涉三族罪的那一件妖言令”,而其他“妖言令”並未廢除,所以才會有文帝的復除。
再看“三族罪”的問題。“三族罪”首先涉及到“三族”之所指。《史記集解》引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也。”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也。”
“三族”在法律範圍指父母、妻子、同産。這是學界主流觀點。最直接的證據可見《墨子·號令》:
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産皆斷。左右知不捕告,皆與同罪。以城爲外謀者三族。
岑仲勉云:“‘以城爲外謀者三族’句,即前‘若欲以城爲外謀者父母妻子同産皆斷’之複出,余前文謂三族是父母、妻子及兄弟,得此益足證實。”④岑仲勉:《墨子城守各篇簡注》,中華書局2004年,第124頁。確定了“三族”的範圍之後,再看《漢書·刑法志》所載文帝二年之詔:
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産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
這説明文帝二年之時,“三族罪”依然存在。正因此,學者就吕后元年到文帝二年之間“三族罪”的情形發表了各自的看法:閻若璩認爲吕后到文帝之間曾重設過“三族罪”,只是史料缺載;⑤參見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95頁。張建國認爲吕后根本没有除去“三族罪”,所除去的是“三族罪中的妖言令”。⑥參見張建國:《夷三族解析》第156頁。
自從2001年《二年律令》刊佈之後,該問題更爲複雜。《二年律令·賊律》簡1-2云:
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及守乘城亭障,諸侯人來攻盜,不堅守而棄去之若降之,及謀反者,皆要斬。其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其坐謀反者,能偏捕,若先告吏,皆除坐者罪。①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著:《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四七號墓〕》(釋文修訂版),文物出版社2006年,第7頁。
該律文所誅殺的父母、妻子、同産,正是“三族”的範圍。而《二年律令》中因有吕后元年所封其父的謚號——吕宣王,故可以肯定《二年律令》曾針對吕后元年所下達的詔令進行過相應的律文修訂。正因此,這便與吕后元年“除三族罪”産生了矛盾,因爲“三族”既然指“父母、妻子、同産”,那爲何吕后元年“除三族罪”之後的《二年律令》中依然是“父母、妻子、同産”呢?按理,是不應該再有此“三族”的。針對這樣的矛盾,高敏認爲“所謂‘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妖言令’,已直接爲抄録於吕后二年的《二年律令》中的《收律》所否定,故到文帝二年還有‘議除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及收’的必要”。②高敏:《〈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中諸律的製作年代試探》第36頁。邢義田認爲吕后“詔除三族罪,事實上並未真廢,或甫廢即恢復,故仍見於《二年律令》”。③邢義田:《張家山漢簡〈二年律令〉讀記》,《燕京學報》2003年新第15期,第2頁。宫宅潔認爲“吕后詔書的實際效力乃至史實本身都令人懷疑”。④宫宅潔著,楊振紅、單印飛等譯:《中國古代刑制史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第140頁。可見,三家都以《二年律令》質疑了吕后“除三族罪”的真實性。
此外,最近的成果當屬水間大輔的研究。水間氏認爲吕后二年的《二年律令》中之所以還存有“三族刑”的規定,是因爲“三族刑廢除後,若立刻從法文集删除三族刑,則不能參閲並確認如何處理在廢除前犯三族罪的人的三族”。⑤水間大輔:《漢初三族刑的變遷》,《厦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年第6期,第67頁。即認爲詔令所廢除的法規,在法文集中還需要保存一段時日。這一觀點的提出,大輔本人似乎也有一絲猶豫,畢竟“高后元年追尊曰吕宣王”一事已反映在了《二年律令·具律》之中。並且,《秦律十八種·尉雜》簡199云:“歲讎辟律于御史。”説明相關人員每年都要到御史處對律令進行校對。《具律》中“吕宣王”内容的出現正是這一規定的寫照。所以,吕后元年“除三族罪”的詔令未反映在《二年律令·賊律》之中,當有其他原因。
水間大輔並不否定吕后“除三族罪”這一記載,故在此基礎上着手找尋“三族罪”被重新制定的原因,提出“吕后八年吕后死後,太尉周勃與朱虚侯劉章等對吕氏政權發動政變,將吕氏男女全部抓捕,‘無少長皆斬之’。‘無少長皆斬之’這一表達很相似於《二年律令》第1-2號簡的‘其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①水間大輔:《漢初三族刑的變遷》第67頁。故水間大輔認爲“三族罪”再次制定於吕后八年。
水間氏將“三族刑”重新制定的原因解釋爲吕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這似乎是一個較爲合理的解釋。不過,《史記·吕太后本紀》云:“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吕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這實際上已經超出了“父母、妻子、同産”的三族範圍,可視爲一種敵對集團間應急性的措施。當然,此事件之後,是否通過正規立法程式重設“三族罪”,僅從當時功臣們考慮新皇人選、等待新皇到來的緊張局勢來説,似乎無暇或無必要在新皇來臨之前去制定一個“三族罪”。何況,如果真是吕后八年由功臣們再次制定“三族罪”,那文帝在剛登基、帝位不穩之時,就敢直接否定諸功臣的舉措?且諸臣在后少帝當位之際,滅吕氏,廢立后少帝、文帝,其本身就有謀反夷族之嫌,實無必要重設“三族罪”。
實際上,水間大輔所提出的解釋還需要面對一個更大的問題。這就是文帝二年不僅廢除了“三族罪”,還除去了“妖言罪”。既然以誅滅吕氏一事來確定“三族罪”的再實施,那又以何事來確定“妖言”在文帝二年之前的再制定呢?可見,脱離“妖言令”而談“三族罪”就會受到限制。
水間大輔的這種解釋雖然讓人不安,但他此前曾提出、其後又放棄的一個看法,卻值得重視。他曾認爲:“吕后元年廢除的是施以‘黥’‘劓’與‘斬趾’等附屬的肉刑後處以死刑這一三族刑的執行方法,而三族刑本身没有被廢除。”此觀點的意思是,“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這一行刑方式被廢除了。對此,宫宅潔指出有此可能,但又指出:“如果吕后改革並非要廢除緣坐本身,而衹是想改變它的處刑方式的話,那麽《刑法志》將這一改制稱作‘除三族罪、妖言令’顯然是誇大其詞,問題仍無法解決。”②宫宅潔著,楊振紅、單印飛等譯:《中國古代刑制史研究》第139頁。宫宅潔的意思是,如果僅僅只是廢除夷三族的酷刑,吕后或者班固不會説成“除三族罪”,因爲“三族罪”不僅牽涉到“酷刑”,還涉及到“父母、妻子、同産”的緣坐。這一詰語,被水間大輔所接受,並進而改變了觀點,提出了上述所説的法文集删除的滯後性以及吕氏被殺後重新制定三族罪的觀點。
二、吕后“除三族罪妖言令”之含義
筆者接下來在水間大輔所放棄觀點之上,來作出一些證明。我們還是要回到文獻上,去瞭解班固到底所要表達的意思。《漢書·刑法志》云:
【1】漢興之初,雖有約法三章,網漏吞舟之魚。然其大辟,尚有夷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祅言令。【2】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産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産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收之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爲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爲暴者也。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
此記載可分爲兩段,全是講述漢初三族之法的經歷。先看第一段中的“三族罪”,宫宅潔認爲“三族罪”要包括緣坐,實則未必。《漢書·高后紀》云:“除三族辠。”“罪”“辠”有學者做過考釋:“‘罪’原作‘辠’,‘辠’原指以刑具加於人身,先指割鼻之劓刑,後引申泛指各種刑罰。‘罪’本指以羅網捕飛鳥,引申爲捕罪人或監禁罪人。無論是‘辠’還是‘罪’,原義均不是指‘犯罪行爲’,而是對待犯罪人的措施,即刑罰。”①劉志松:《釋“罪”》,《江蘇警官學院學報》2008第4期,第105頁。冨谷至也指出:“秦簡中‘罪(辠)’除了犯罪的意思外,還有刑罰的意思……‘罪’一詞具有‘犯罪’和‘刑罰’兩種含義,説明罪(crime)的概念和與其相對應的罰(punishment)的概念没有被嚴格地區分開來。至少在秦律中,還没有把罪和罰加以區分的意識……對於‘加罪’,首先要指出的是,秦律中的‘罪’是刑罰的意思,就是説‘加罪’是加罰即附加刑罰的意思。”②冨谷至著,柴生芳、朱恒曄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9—20頁。由上可見,“三族罪”可指“三族刑罰”。
冨谷至和劉志松對“罪”字已做了詳細的説明,其説當可采信。在此基礎上,再舉幾例。《韓非子·説難》云:
衛國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刖。彌子瑕母病,人聞,有夜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孝哉!爲母之故,忘其犯刖罪。
“罪刖”“刖罪”之“罪”用的是“刑罰”之義。又如賈誼《新書·鑄錢》云:
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錢,敢雜以鉛鐵爲它巧者,其罪黥。
再如青海大通縣上孫家寨漢墓木簡中記載:
諸誅者皆劓之,以别死辠。①國家文物古文獻研究室、大通上孫家寨漢簡整理小組:《大通上孫家寨漢簡釋文》,《文物》1981年第2期,第25頁。
此“死辠”之“辠”正是“刑罰”的意思。通過以上兩例,我們更加肯定“罪”所具備的“刑罰”義。
正因此,“除三族罪”按照“犯罪”“刑罰”兩義,便只能理解爲“除三族刑罰”與“除三族犯罪”。“三族犯罪”在《二年律令·賊律》中包括“謀反”“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等行爲。吕后肯定不會除去“謀反”“以城邑亭障反”等罪名,故“除三族罪”反而只能理解爲“除三族刑罰”。
既然“除三族罪”是指“除三族刑罰”,那結合上引《漢志》第一段内容,也便明白“夷三族之令”中的殘酷刑罰恰好與“三族罪”互爲關聯。《漢志》在描述了“夷三族之令”“具五刑”之後,緊接着就提到“除三族罪妖言令”,其間關係不言而喻,指的就是吕后廢除的是“具五刑”之刑罰。
緊接着的一個疑問是:爲何在全段表述“三族刑”的時候要將“妖言令”放進來?實際上,理解了“三族罪”也就理解了“妖言令”。看“夷三族之令”中的一句話:“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這應就是“妖言令”的内容。“妖言令”與“三族罪”一樣,皆是事關“夷三族”處刑方式的一個法令。
既然我們提出“妖言令”是指“夷三族之令”中的“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那麽,至少應該讓“妖言”與“夷三族”或者“誹謗”或者“詈詛”建立聯繫,這樣才能認定“妖言令”並非唐突出現於《漢志》對夷三族的介紹之中。下面對四者之關係,做一些論述。
“誹謗”與“妖言”往往難分。賈誼《新書·保傅》云:
故今日即位,明日射人,忠諫者謂之誹謗,深爲之計者謂之妖言,其視殺人如艾草菅然。豈胡亥之性惡哉?
又《漢書·路温舒傳》云:
臣聞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正言者謂之誹謗,遏過者謂之妖言。
“遏過”“深計”有指斥過誤、言辭情感深切的意思,故表達上强於“正言”“忠諫”。或者也可看成互文:忠諫者、深計者謂之誹謗妖言;正言者、遏過者謂之誹謗妖言。正因爲誹謗與妖言較難區分,所以,沈家本認爲“秦漢之妖言,乃誹謗之類”,①沈家本:《歷代刑法考》,中華書局1985年,第1860頁。韓國磐也指出兩者性質相同。②韓國磐:《中國古代法制史研究》,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80頁。因此,如果誹謗都能適用夷三族,那麽妖言當也能適用夷三族。《史記·高祖本紀》云:
還軍霸上。召諸縣父老豪桀曰:“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誹謗者族,偶語者棄市。”
又《史記·秦始皇本紀》云:
丞相李斯曰:“……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制曰“可。”
兩相比較,劉邦對父老豪傑所説的“偶語者棄市”,即爲李斯向始皇提議的“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而劉邦所説的“誹謗者族”也應當是李斯所説的“以古非今者族”。誹謗的手段有不同,通過托古以攻擊當朝便屬其手段之一。如《韓非子·忠孝》云“爲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表達了今不如古。此即爲“以古非今”。韓非子對此視之爲“誹謗其君”。當然,就算劉邦、李斯二人對此所指不同,也至少説明了秦法中的“誹謗者”和“以古非今者”是會遭受族刑的。“誹謗者”或“以古非今者”有被夷族的情形,故妖言者也當有被夷族的情形。
“以古非今”不僅被視爲誹謗,也有被視爲“妖言”的情形。《史記·秦始皇本紀》有李斯説“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黔首”與始皇説“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妖言以亂黔首”。李斯所説是焚書一事,始皇所説是坑儒一事。此處“妖言”是否指“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從“亂黔首”的影響來看,似乎當爲同指。另外,後世將被坑殺的人理解爲“儒生”,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基於太子扶蘇所説的一段話:
“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爲訞言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始皇使人廉問“諸生”,扶蘇爲“諸生”求情。太子規諫之語中所提及的“諸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説明始皇已經對“亂黔首”的儒生展開了懲治,而誦法孔子的儒生的輿論武器,莫過於借詩書以評論時政,所以,只能説諸生確有違反焚書時所規定的“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的禁令。换言之,被坑殺的諸生“爲訞言以亂黔首”當屬於“語詩書、以古非今”的情形。《嶽麓秦簡(伍)》簡1017規定:
【●】自今以來,有誨傳言以不反爲反者,輒以行訞律論之。①陳松長主編:《嶽麓書院藏秦簡(伍)》,上海辭書出版社2017年,第42頁。
該法開始將“以不反爲反”的虚假傳言都納入到“行妖”之中,可見秦律對“妖”的認定是比較寬泛的。而“以古非今”是用切實的語言攻擊、反對當朝。所以,“以古非今”視爲“妖言”當在情理之中。這裏需要指出的是,“諸生”的懲處似乎並不符合“以古非今者族”的規定。對此,我們認爲需要考慮“坑殺”並非法定刑的性質。“妖言”行爲的認定是有據可依的,如“行訞律”中當囊括諸多“妖”性質的行爲,可作爲判定“妖”的依據。但在處罰“諸生”時,卻並未遵照法定刑的規定,而是改用了“坑殺”這一法外刑,且無法得知是否牽連了家人。所以,我們不能通過法外刑去判斷諸生“爲妖言”並非“以古非今”。史書中所載詔獄,往往任皇帝喜怒,死罪不殺,活罪不饒,罪刑不對等。
綜上可知,“誹謗者”“妖言者”“以古非今者”皆可適用族刑。三者有時候可同指互用。②筆者曾撰文指出“妖言罪”的特徵不易理解的原因:“以爲和‘妖言’概念的模糊及其詞性有關。‘妖言’主要是從言論所具有的性質來認定的。我們知道,‘誹謗’一詞一般是作爲動詞使用,其後賓語一般是人或事,如:‘今乃誹謗我’‘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誹謗政治’;而‘妖言’卻主要用作名詞,一般作爲賓語,如:‘妄作妖言’‘爲妖惡言’‘謂勝爲妖言’,包括我們所能見到的最早對‘妖言罪’有明確界定的《唐律疏議》,都是提出的‘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揆之常理,罪名的認定,一般是以犯罪嫌疑人的行爲、動作來判定,如誹謗罪、殺人罪、盜竊罪等等;而‘妖言’作爲一名詞,表述的是行爲動作所具有的一種性質,而不同的行爲都可能産生出一種‘妖惡’‘不祥’的性質,如‘以古非今’算妖言,‘妄説天道’可爲妖言。所以,‘妖言’一詞可以涵蓋許多具體的行爲。不同類型的言論都可能冠以爲‘妖言’。”拙文:《兩漢“妖言”與“祝詛”關係探析》,《湖南大學學報》2014年第2期,第21—22頁。需要指出的是,並非所有的誹謗、妖言行爲都會遭受族刑。從上文可知,誹謗、妖言中的“以古非今”的行爲可適用族刑。
既然“妖言令”和“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中的“誹謗”建立了聯繫了,那麽“詈詛”是否也能和“妖言”確立聯繫呢?“詈”有辱駡之意,不好判斷與“妖言”的關係。“詛”往往與“祝”連用。③“祝”有“詛”義。《後漢書·賈逵傳》云:“逵薦東萊司馬均……均字少賓,安貧好學,隱居教授,不應辟命。信誠行乎州里,鄉人有所計争,輒令祝少賓,不直者終無敢言”。李賢注:“祝,詛也。《東觀記》曰:‘争曲直者,輒言“敢祝少賓乎”?心不直者,終不敢祝也。’”文帝除誹謗妖言詔中就直接用的是“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筆者曾針對文帝詔文中所説的“祝詛上”與“妖言”的關係進行過比較,認爲其“妖言”包括“祝詛上”。《孝文本紀》記載爲:
上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其除之。民或祝詛上以相約結而後相謾,吏以爲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爲誹謗。”
此“妖言”與“祝詛上”之關係,筆者之論述,撮其要,是以《睡虎地秦簡·封診式》中的一則“毒言”爰書展開,先通過《論衡·言毒》所云“太陽之地,人民促急,促急之人,口舌爲毒”,能用來“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延疾”“愈禍”等;再繼之以《論衡·訂鬼》所云“天地之氣爲妖者,太陽之氣也。妖與毒同”“天地之間,妖怪非一,言有妖,聲有妖,文有妖。或妖氣象人之形,或人含氣爲妖。象人之形,諸所見鬼是也;人含氣爲妖,巫之類是也。是以實巫之辭,無所因據,其吉凶自從口出,若童之謡矣。童謡口自言,巫辭意自出”。可見,“毒言”爲“妖言”,而“祝詛上”正可視之爲“毒言”“妖言”。①參見拙文:《兩漢“妖言”與“祝詛”關係探析》第21—23頁。
“毒言”的“祝樹樹枯”“唾鳥鳥墜”確在漢宫施用。《史記·外戚世家》有載:“長公主怒,而日讒栗姬短於景帝曰:‘栗姬與諸貴夫人幸姬會,常使侍者祝唾其背,挾邪媚道。’”此中“祝唾其背”,正是“祝樹樹枯”“唾鳥鳥墜”在人身的施展。
通過以上論證,我們建立了“妖言令”與“夷三族”“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三者之間的聯繫。
另外,文帝時期又有除“妖言”之舉,文帝詔文説“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此“妖言之罪”當與吕后所除“妖言令”無關,而關乎《嶽麓秦簡(伍)》簡1017“有誨傳言以不反爲反者”之類的言語之罪。我們知道“令”有補充“律”的功能,正如“夷三族之令”只規定行刑的過程,而“夷三族”的具體罪名是分設在“律”之中的,《二年律令·賊律》簡1-2就有謀反、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等夷三族的罪行或罪名。所以,我們結合“令”的功能以及“夷三族之令”與《二年律令·賊律》的關係,可以推斷“妖言令”是對“妖言律”的部分補充。而文帝所除的“妖言之罪”應該指的就是“妖言律”中的内容。
以往可能也忽視了“三族罪妖言令”與“夷三族之令”的關係。其實,“夷三族之令”並非具體的“令名”,用現在的話解釋就是“夷三族的令”,屬於一個概括性的説法。我們所知道的具體“令名”,譬如“津關令”“功令”“金布令”“田令”等等,都不會有“之”字。
“夷三族之令”既然作爲泛指,那應該有具體的“令名”與之相對應。結合上下文語境,若有所悟,這應是指“三族罪妖言令”。“三族罪妖言令”一般被理解爲“三族罪”與“妖言令”。實際上,“夷三族之令”應該至少包含兩個以上的“令”,才采取了泛指的説法。“三族罪妖言令”最好的理解應該是分爲“三族罪令”與“妖言令”。這在文法上也是成立的。“三族罪令”的“令”字因“妖言令”的“令”字而省去,兩者共用一個“令”字。譬如,《二年律令·秩律》簡441云“丞相、相國長史,秩各千石”,便指丞相長史、相國長史,共用“長史”二字。此類例子甚多,不贅舉。因此可以説,班固是將事關三族酷刑的兩條“令”,即“三族刑罰令”與“妖言令”合併論述而稱之爲“夷三族之令”。
“除三族罪妖言令”實際上是漢惠帝的動議。《漢書·高后紀》云“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辠妖言令,議未決而崩,今除之”。可見吕后只不過是在完成兒子意願。惠帝是一個遭受過巨大心理創傷的皇帝。《史記·吕太后本紀》載:
太后遂斷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居數日,乃召孝惠帝觀人彘。孝惠見,問,乃知其戚夫人,乃大哭,因病,歲餘不能起。使人請太后曰:“此非人所爲。臣爲太后子,終不能治天下。”孝惠以此日飲爲淫樂,不聽政,故有病也。
惠帝見“人彘”後,因病“歲餘不能起”,言語中“此非人所爲”“終不能治天下”,足見其對酷刑的痛恨。而“三族刑”與“人彘”可算是“異曲同工”。這有助於我們理解吕后所除“三族罪、妖言令”背後的動機及含義。
接下來分析第二段的内容。第二段是關於漢文帝廢除對“父母、妻子、同産”的收坐,以及漢文帝因“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的事情。此句意思需留意,“復行三族之誅”是側重於“三族”二字,表示重新將“三族”納入到了誅殺範圍,但卻並非恢復“三族刑罰”。文帝所做的只不過是自己廢止“三族緣坐”,又自己再次恢復而已。
事實上,“夷三族”之法包括三個要素:罪名、罪刑、坐罪範圍。謀反等“罪名”肯定不會被廢除,故而,能廢止的也就只會是“罪刑”與“坐罪範圍”。文帝二年詔文是將親屬收坐予以廢除,並不關涉主犯的“罪刑”,文帝後元元年(前163)“新垣平謀爲逆,復行三族之誅”之後,《史記》《漢書》除了“腰斬”之外,再也見不到關於“具五刑”的記載。有學者認爲“具五刑”的終止是因爲漢文帝十三年(前167)除“肉刑”的緣故。①張建國:《夷三族解析》第149頁。但是,肉刑的廢除只包括黥、劓、左右趾,而“三族酷刑”中所剩下的笞、梟其首、菹其骨肉、斷舌等刑罰無法被廢除。所以,廢肉刑肯定不是三族酷刑被廢除的原因。又由於文帝二年詔文並無一語涉及到主犯的“罪刑”的問題,所以,“具五刑”的消失與漢文帝無關。這説明“罪刑(具五刑)”的廢除早於漢文帝。所以,“罪刑”的廢除只能是吕后二年“除三族罪、妖言令”的結果。
正是因爲文帝“復行三族之誅”,所以,新垣平之後的晁錯就逃脱不了“三族”被誅殺的厄運。《漢書·晁錯傳》云:
“錯不稱陛下德信,欲疏群臣百姓,又欲以城邑予吴,亡臣子禮,大逆無道。錯當要斬,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臣請論如法。”制曰:“可。”
可見,文帝如果未“復行三族之誅”,晁錯的“父母、妻子、同産”都將會因爲文帝“盡除收律、相坐法”而倖免。但是,“復行三族之誅”後,“父母、妻子、同産”的緣坐誅殺被再次啓用,又恢復到了《二年律令·賊律》簡1-2所規定的“皆要(腰)斬。其父母、妻子、同産,無少長皆棄市”的情形。晁錯及家屬也正是按照此律文被處決。
三、“三族罪”與漢初的刑罰序列
上文反復論述了吕后“除三族罪”並非是“罪名”的廢除,因爲其下統攝了諸如謀反、降諸侯、以城邑亭障反等等多種罪名。而這些罪名,吕后是不可能廢除掉的。在這種認識之下,我們再轉到“罪”所具有的“刑罰”義來做延伸理解。我們先看幾條史料。《周禮·秋官·司寇》云:
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殺罪五百。
這是説墨罪之下有五百條或者五百罪名,劓罪之下有五百條或五百罪名,宫罪、刖罪、殺罪也皆如此。這些都是以“刑罰”作爲標準統攝衆多法規。再如《後漢書·陳寵傳》所載陳寵上奏:
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
這也可看到漢人在對律令統計時,有以“刑罰”爲統計標準的。以上都是依照不同的“刑罰”來分類統計律令。
結合“刖罪五百”“劓罪五百”的分類標準,“三族罪”似也可理解爲“刑罰”標準下所包含的諸多罪名與行爲。打個比方:“三族罪五百”。
綜上,“除三族罪”不能簡單地與“除誹謗罪”“除妖言罪”等具體罪名比較,而應該用“除刖罪”“除黥罪”“除殺罪”去理解更爲穩妥。在“刖罪”“黥罪”之下包括諸多罪名。如果是“除刖罪”“除黥罪”,那肯定不會是廢除“刖罪”“黥罪”之下的全部罪名,而應該理解爲是廢除“刑罰”。原刑罰廢除之後,罪名將采用其他的刑罰來懲處。如漢文帝“除肉刑”就是最好的例證。肉刑改革之前,時人正有“黥罪”的叫法,賈誼《新語·鑄錢》“愿民陷而之刑僇,黥罪繁積”“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當肉刑改革之後,“黥罪”所屬的罪名便會轉移到其他刑罰之下。所以,當我們看到“除某某罪”之時,還是需要甄别的,畢竟有的是刑罰,有的是罪名。
在“三族刑罰”的理解之下,似乎可以引申出一個問題,值得今後進一步討論。這就是律令的分類可以按照行爲的性質分爲“賊律”“盜律”“囚律”等,也可按照“刑罰”如黥、劓等的不同來劃分。“三族罪”按照“刑罰”的標準來統攝諸多罪名,這便與上引《周禮》及陳寵所述漢律的情形相一致。因此,在這樣情況下,我們是不是能在漢初的刑罰序列中增添一個“三族罪”?换言之,在吕后廢除三族酷刑前的漢初,“殺罪”之上是否還有一個“三族罪”呢?
吕后“除三族罪”後,“具五刑”等酷刑不再出現。故主犯所受的“三族刑”便轉入“死刑”(腰斬)之中,其刑罰序列中的最頂端便也消失。
“三族罪”取“刑罰”義,也可稱之爲“三族刑”。該刑的特點在於,“三族刑”的主犯雖然最終也是一死,但其“殺之”只是整個刑罰的一個中間性環節。我們將《二年律令》與“三族刑”作一比較。《二年律令·具律》簡88:
有罪當黥,故黥者劓之,故劓者斬左止,斬左止者斬右止,斬右止者府之。
此刑罰序列是黥刑→劓刑→斬左趾→斬右趾→腐刑。腐刑之後往往就是死刑。再比較“三族刑”:
“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其誹謗詈詛者,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
此句慣有的斷句爲“笞殺之”,筆者曾指出應改爲“笞,殺之”。“笞”在整個執刑過程中屬於替代刑,因爲符合《二年律令·具律》簡91、122云:“及老小不當刑、刑盡者,皆笞百。”①彭浩、陳偉、工藤元男主編:《二年律令與奏讞書: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出土法律文獻釋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27、141頁。由於腐刑只針對男子且不便,故而三族刑中的女子在“斬右趾”之後就屬於刑盡,所以,“笞”在整個三族刑中屬於替代刑,是替代腐或宫刑的。①拙文:《“具五刑”考——兼證漢文帝易刑之前存在兩個“五刑”系統》,《中國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63—73頁。其後的文帝肉刑改革也是以笞替代黥、劓、斬趾。因此,通過比較,“三族刑”主犯生前所遭受的刑罰正與《二年律令·具律》所記述的一致,需要將法定的刑罰序列過一遍,再執行死刑;而死後又要遭受梟首、菹醢。因此,“三族刑”應區别於單純的“死刑”,似乎可以加入到漢初的法定刑罰序列之中。即:
三族刑→(殺之)死刑→腐刑→斬右趾→斬左趾→劓刑→黥刑……
或稱之爲:
三族罪→殺罪→腐罪→斬右趾罪→斬左趾罪→劓罪→黥罪……
“三族刑”的特點,並非單純以殺死爲目的,而是還包括身前與身後的刑辱以及對他者的警示。《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云:
譽適以恐衆心者,翏。“翏”者可如?生翏。翏之已,乃斬之之謂殹。
斬殺之前的“生戮”,目的就是刑辱罪犯;而死後的梟首、菹醢,更是對罪犯的殘酷侮辱以及對他人的威懾。因此,“三族刑”具有與單純死刑迥異的刑辱震懾意圖在其中。
四、結語
通過上文分析之後,再回顧吕后到文帝之間的情事,也就自然清晰了。吕后元年所廢除的“三族罪妖言令”是“三族之刑”,並不涉及“父母、妻子、同産”,更不涉及到廢除“謀反”等罪名,故而行用於吕后二年的《二年律令·賊律》中出現“父母、妻子、同産”等字眼也就不足爲怪。到了漢文帝二年,文帝通過對“收律、相坐法”的廢除,讓“父母、妻子、同産”免於“夷三族罪”的牽連。結合《二年律令·賊律》1-2簡,可推知“以城邑亭障反”“降諸侯”“謀反”等罪將僅止於自身腰斬,家屬不必受牽連。其後,文帝因新垣平一事,恢復了對“父母、妻子、同産”的誅殺,但三族之酷刑並未被恢復。漢初“夷三族”之法的變遷大致如此。這不僅將傳世文獻之間的問題疏通了,也化解了與出土文獻之間的矛盾。所以,我們也就明白了漢文帝爲何會有另一次對“妖言罪”“三族法”的廢止舉措,因爲,文帝所廢除的和吕后所廢除的完全是兩個不同性質的事物。其實,結合《漢志》的前後文語境,不去假設吕后與文帝之間有過重設“三族罪”“妖言罪”的行爲,再加之以《二年律令》中“三族”的記載作爲輔助,足可知道吕后、文帝所除不同。可以説,班固的表述是連貫而完整的,並無缺漏,只是因爲後人在理解上出現了偏差,故而才有了各種彌縫之論。
附記:本文得到了諸師友及匿名專家的幫助及寶貴意見,謹表謝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