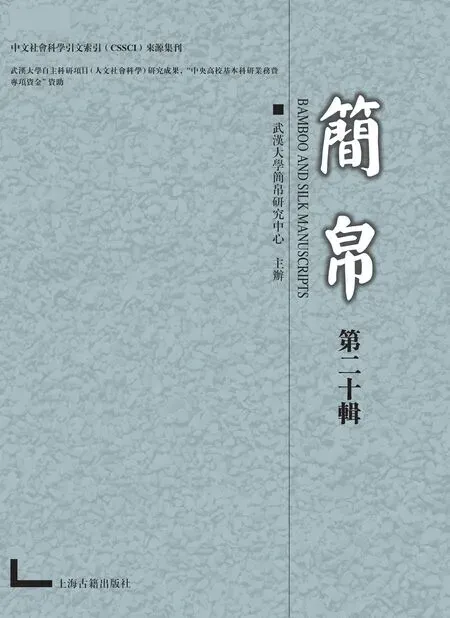“黄豆瓜子”何以支付“地下賦”*
——從《泰原有死者》、馬王堆遣策看東漢張叔敬鎮墓文
蔣 文
關鍵詞:鎮墓文 泰原有死者 馬王堆 黄豆 黄圈
一、引言
1935年春的山西忻州,在同蒲鐵路建設的過程中出土了一件朱書陶器,原器不知下落,器形、大小皆不明。①馬鏡清稱之爲“瓦盆”,摹本亦作侈口深腹的盆形(馬鏡清:《漢張叔敬墓避央瓦盆文(附考釋)》,民國雙色印本。轉引自陳直:《漢張叔敬朱書陶瓶與張角黄巾教的關係》,《文史考古論叢》,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90—392頁;李明曉:《山西忻州熹平二年(173)張叔敬鎮墓文集注》,簡帛網2016年3月20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2508);陳直稱之爲“陶瓶”“陶缶”;郭沫若稱之爲“瓦缶”(郭沫若:《蘭亭論辯》,文物出版社1977年,第32頁)、“瓦盆”(郭沫若:《奴隸制時代》,《郭沫若全集·歷史編》卷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92頁)。幸運的是,器物上的朱書文字有馬鏡清摹本留存於世,研究者多稱之爲“熹平二年張叔敬鎮墓文”或“熹平二年張叔敬墓券”。全篇釋文如下:①最早的釋文爲馬鏡清釋文(轉録於陳直:《漢張叔敬朱書陶瓶與張角黄巾教的關係》第390—392頁)。除陳直外,較早的引用張叔敬鎮墓文的學者還有郭沫若(郭沫若:《蘭亭論辯》第32頁;郭沫若:《奴隸制時代》第92、94頁)。較晚近的收録研究張叔敬鎮墓文的論作如:黄景春:《早期買地券與鎮墓文整理與研究》,博士學位論文,華東師範大學2004年,第125—127頁;張勳燎、白彬:《中國道教考古》,綫裝書局2006年,第160—162頁;劉昭瑞:《漢魏石刻文字繫年》,新文豐出版公司2001年,第202—203頁;吕志峰:《東漢熹平二年張叔敬朱書瓦缶考釋》,《中文自學指導》2007年第2期,第19—23頁;李明曉:《山西忻州熹平二年(173)張叔敬鎮墓文集注》。本文所引釋文主要據李明曉文。
熹平二年十二月乙巳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張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塚丞塚令、主塚司命、魂門亭長、塚中游擊等:
這是一篇較爲典型的東漢鎮墓文,其中提到爲讓死者張叔敬在陰間過上好日子、不再糾纏牽連生人,埋入各種“復除之藥”,包括代替“生人”的“上黨人參”、代替“死人”的“鉛人”,以及死人用以交付“地下賦”的“黄豆瓜子”等。“人參”“鉛人”亦數見於其他鎮墓文,然“黄豆”頗爲罕見,“瓜子”迄今僅見此一例。前人在談及張叔敬鎮墓文時,似均未深究“黄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一句的涵義。“黄豆瓜子”所指爲何?爲什麽可以支付“地下賦”?這些問題有待解釋。本文將結合北大藏秦牘《泰原有死者》、馬王堆遣策等材料對此進行探討。
二、“黄豆瓜子”並非以實物形式繳納之賦
要理解“黄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最直接的思路當然是——“黄豆瓜子”是以實物形式繳納的“地下賦”。衆所周知,古人事死如事生,對陰間制度的想象多參考陽世,如果地下賦可直接徵收黄豆瓜子,想必也是現實世界賦税制度的映射。那麽在現實世界中,生人可用“黄豆瓜子”繳納地上之賦嗎?
漢代賦税大體可分爲租、賦、税三宗:租指田租(即地税),徵收實物(穀物、芻稿);賦指諸賦,按人或户徵收,形式是貨幣;税大致指按行業或地區徵收的雜税,形式以貨幣爲主。從文獻來看,“賦”既可泛指各種租、賦、税,也可專指按人或户徵收的、以貨幣形式繳納的諸賦,但以後者爲常,前一種用法較爲罕見。①馬怡:《漢代的諸賦與軍費》,《中國史研究》2001年第3期,第27—37頁。
能够影響到喪葬習俗的必然是陽世普遍通行的情況。由於漢代“賦”絶大多數情況下專指諸賦,張叔敬鎮墓文之“賦”大概率是專指;又由於諸賦的徵收形式是貨幣,便不太可能以實物“黄豆瓜子”納賦了。漢代確實也偶見以實物“叔(菽)粟”納賦的情況。《漢書·昭帝紀》載昭帝元鳳二年“三輔、太常郡得以叔粟當賦”,又載元鳳六年昭帝昭令曰:“夫穀賤傷農,今三輔、太常穀減賤,其令以叔粟當今年賦。”表面上看,這兩條材料似表明至少豆類(菽)是可以直接納賦的,但是我們必須考慮到“叔粟當賦”並非常態,只是於局部地區施行的臨時性政策,並且這些“叔粟”其實也是在充當貨幣的替代品(顔師古注:“諸應出賦算租税者,皆聽以叔粟當錢物也。叔,豆也。”)。因此,作爲特例的“叔粟當賦”恐怕不太可能影響到喪葬習俗。
以上討論是基於“賦”爲專指的情況,退一步説,如果張叔敬鎮墓文之“賦”泛指租賦税呢?即便如此,以實物“黄豆瓜子”納“賦”的可能性恐怕也不高。以實物繳納的主要是田租,而田租所徵收的穀物主要是粟、黍之類的糧食,“黄豆”作爲豆類尚可計入,“瓜子”則不是一般意義上可以果腹的農作物,很難計入其間。
總之,根據漢代賦税制度,陽世間的生人恐怕不太可能以實物“黄豆瓜子”繳納“地上賦”;相應地,陰間的死人應該也不會用“黄豆瓜子”來繳納“地下賦”。那麽張叔敬鎮墓文何以言“黄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呢?
三、“黄豆瓜子”爲黄金之替代物
我們認爲,張叔敬鎮墓文中用以繳納“地下賦”的“黄豆瓜子”其實是作爲黄金的替代物。這類觀念在時代更早的出土文獻中有痕迹可尋。
(一)《泰原有死者》“黄圈以當金”①姜守誠亦將《泰原有死者》“黄圈以當金”與張叔敬鎮墓文“黄豆瓜子”聯繫,但他認爲“黄圈”是大豆黄芽,“黄豆是可以視作冥界貨幣、錢財、資費而使用的,乃財富的象徵”(姜守誠:《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考釋》,《中華文史論叢》2014年第3期,第167—168頁),與我們的看法有所不同。我們認爲“黄圈”是豆而非豆芽,“黄豆瓜子”也並非僅是籠統地象徵財富,詳見下文。
最堅實的證據來自北京大學藏秦牘《泰原有死者》:②李零:《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簡介》,《文物》2012年第6期,第81—84頁;圖版見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北京大學藏秦簡牘概述》,《文物》2012年第6期,第71頁。本文的釋文與原釋文不完全相同,與相關研究論著中的釋文亦有差異,不一一注明,與本文討論關係較大的釋文改動將在注釋中説明。
泰(太)原有死者,三歲而復産(生)。獻之咸陽,言曰:
死人之所惡┗:解予死人衣,必令産(生)見之;弗産(生)見,鬼輒奪而入之少内┗。死人所貴:黄=圈=(黄圈,黄圈)以當金;黍粟,以當錢;白菅,以當〈緜〉。③李零讀“”爲“紬”。姜守誠認爲“”當讀爲“繇”或爲“繇”之訛字,表徭役(姜守誠:《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考釋》第153—154頁),不少學者持類似觀點。陳劍指出:“”當爲“縣(緜)”之誤;“白菅”與“緜”形貌相似,故以“白菅”充死人之“緜”;漢代西北簡及山東鄒城邾國故城遺址所出新莽“貨版”證明“緜”與“貨幣、財富”存在關係。詳參陳劍:《據出土文獻説“懸諸日月而不刊”及相關問題》,《嶺南學報》第10輯,2018年,第71—72頁。女子死三歲而復嫁,後有死者,勿并其冢┗。祭死人之冢勿哭,須其巳(已)食乃哭之。不須其巳(已)食而哭之,鬼輒奪而入之厨┗。祠毋以酒與羹沃祭(?),而沃祭前┗。收死人勿束缚,毋決其履,毋毁其器,令如其産(生)之卧殹(也),令其(魄)不得若思┗。黄圈者,大叔(菽)殹(也),(熬)去其皮,④“”,原形作。李零隸作“”,認爲當讀作“”意爲割,研究者未有異議。我們認爲,此字左上部不是“未”而是“”,全字當釋作“”,讀爲“熬”。“”的上部在秦漢文字中可寫作三重,亦可寫作兩重或一重。比如,馬王堆一、三號墓遣策出現了大量的“熬”字(後接“豚/兔/鳧/雁/鷓鴣/鵪鶉/雀/雞”等),絶大多數時候寫作、這類形體,但有時亦寫作(一號墓遣策簡69),同時,馬王堆中“熬”字也寫作(《五十二病方》行61)。馬王堆《陰陽五行甲篇·上朔》中的“敖”字就寫作,與之當爲一字,只不過左上部寫法略有訛變。如果仔細觀察還會發現,左上部的起筆其實並不是一横,而是左右各兩小筆,而這也正符合秦漢文字“熬”“敖”中“”的起筆特徵。“去其皮”當讀爲“熬去其皮”,指用乾炒、乾煎的手段去掉黄卷(大菽)的皮。豆類炒熟後略加搓揉,很容易去皮。馬王堆《五十二病方》行300有“取大叔(菽)一斗,熬孰(熟)”之語。置於土中,以爲黄金之勉。
《泰原有死者》中“黄圈”前後出現了兩次。整理者李零認爲“黄圈”即《神農本草經》等本草書中記載的“大豆黄卷”,是用大豆發出的黄色豆芽,研究者似皆從之。此外,前人在討論“黄圈”時,亦多聯繫遣策中的“黄卷”。漢代遣策“黄卷”數見,包括:馬王堆一號墓遣策簡161“黄卷一石,縑囊一笥合”,三號墓遣策簡148“黄卷一石,縑囊今笥”,一號墓45號簽牌、三號墓2號簽牌“黄卷笥”;鳳凰山八號漢墓遣策簡139“黄卷囊二,錦”、簡140“黄卷囊一,白繡”、簡141“黄卷囊一,赤繡”;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遣策簡6“黄卷□一,棺中”、簡8“黄卷一囊”。研究者皆將遣策中的“黄卷”和《本草綱目》《黄帝内經》《神農本草經》《金匱要略》等中的“大豆黄卷/豆黄卷/黄卷”等同,認爲黄卷指一種大豆生芽而成、可以入藥的食品。①例如,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文物出版社1973年,第143頁;田河:《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遣册補正》,《社會科學戰綫》2010年第11期,第86—87頁。
我們認爲,《泰原有死者》“黄圈”、遣策“黄卷”可能並非指大豆所發之蘖芽,恐怕就是大豆之别稱。證據有二:一是《泰原有死者》明確説“黄圈者,大叔(菽)殹(也)”,而非“大菽之蘖也”之類;二是馬王堆三號墓2號簽牌上書“黄卷笥”,發掘整理者認爲當繫於東97笥,東97笥内現存大豆。②湖南省博物館、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二、三號漢墓》,文物出版社2004年,第188、200頁。除此之外,馬王堆一號墓45號“黄卷笥”簽牌,發掘整理者描述説:“出土時與‘黄頪笥’木牌同在353號笥上,該笥盛梨,而其南側的355號笥缺木牌,與實物對照,可能屬之。”③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第117頁。按:353號盛梨之竹笥位於西邊箱下層,355號同樣位於西邊箱下層,内存“絹質藥草袋6個”,將45號簽牌附於355號笥未必合理;與此同時,西邊箱中層的341號竹笥現存“黄絹袋内盛黑、白豆等”,而341號竹笥尚未找到對應簽牌。④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第118頁。我們懷疑45號簽牌本繫於中層的341號竹笥,後掉落至下層的353號竹笥之上,若這一猜測符合事實,則爲“黄圈/黄卷”指豆又添一條證據。
總之,如果抛开出土文獻的“黄圈/黄卷”與本草書中的“大豆黄卷/豆黄卷/黄卷”所指必定相同的成見,僅從《泰原有死者》文本本身及馬王堆簽牌所對應之實物出發,會發現“黄圈/黄卷”更可能指大豆而非大豆所生之芽,“黄圈/黄卷”與本草書中的“大豆黄卷/豆黄卷/黄卷”或許名同實異。雖然《泰原有死者》末句“以爲黄金之勉”的意思暫時尚難確定,但“黄圈以當金”這句足以證明大豆可作黄金之替代物。
(二)馬王堆遣策“彩金如大菽”
大豆當金的觀念不僅見於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在時代稍晚的馬王堆漢墓遣策中亦有反映:
菜(彩)金如大叔(菽)者千斤,一笥。
(一號墓遣策簡296)
(三號墓遣策簡302)
唐蘭認爲“菜即彩字,疑是土質畫彩的金幣”。①唐蘭:《長沙馬王堆漢軑侯妻辛追墓出土隨葬遣策考釋》,《文史》第10輯,1980年,第55頁。按:唐説大致可從。“菜”用爲“彩”的用字習慣馬王堆遣策内部數見。一號墓遣策簡217、三號墓遣策簡274“木五菜(彩)畫并(屏)風”、一號墓遣策簡232“布檢(奩)五菜(彩)文一合”,皆爲“菜”讀爲“彩”之例。依馬王堆遣策記載,下葬的“菜金”數量巨大(“千斤”“五百斤”),在墓中卻没有發現相應之實物,可判定“菜金”並非不腐朽之真金。②周世榮認爲“菜金”當讀爲“采金”,爲真金(周世榮:《西漢長沙國貨幣新探》,《中國錢幣論文集》第3輯,1998年,第188—189頁),恐不可從,但謂“作顆粒狀、粗細如豆,當屬顆粒狀的自然金塊或顆粒”(第189頁),有一定啓發性。馬王堆遣策還記載了其他金錢珠寶的仿品,所記數量亦驚人:一號墓遣策“土珠璣一縑囊”(簡294)、“土金二千斤”(簡295)、“土錢千萬”(簡297);三號墓遣策“土錢百萬”(簡301)、“土金千斤”(簡303)、“土珠璣一縑囊”(簡304)。一號墓中出土泥郢稱三百餘塊、泥半兩四十簍(每簍約二千五百至三千枚)、盛於絹袋之中的泥丸,發掘整理者認爲分别對應於遣策之“土金”“土錢”“土珠璣”。③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第126頁。雖然這些“如大菽”的“菜(彩)金”因爲某種原因不見於墓中(至少是不見於發掘報告中),但它和“土金”“土錢”“土珠璣”性質相同當無問題。
馬王堆遣策中“如大菽”的“彩金”就是狀如大豆的表面塗色的土質之物,④“泥郢稱”等也是塗彩的。馬王堆一號墓報告謂“泥郢稱”係“泥模板製成後,在字面上塗一層黄粉,再經火燒,以象徵金版”(湖南省博物館、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第126頁)。它和《泰原有死者》“以當金”的“黄圈”實質相同——皆爲黄金之替代物。之所以要將這種土質塗色之物製作成大豆的形狀,正是爲了盡可能逼真地模仿可以代金的大豆。《泰原有死者》以真的大豆(“黄圈”)象徵黄金,“黄圈”是“僞黄金”;馬王堆則用土質塗色的豆狀之物仿擬大豆(“大菽”,亦即“黄圈”),繼而象徵黄金,可視作“僞黄圈”或“僞僞黄金”。
綜上所述,《泰原有死者》和馬王堆遣策表明在秦漢人觀念中大豆(“黄圈/黄卷”“大菽”)可以代金,這完全支持了我們的觀點,即張叔敬鎮墓文“黄豆瓜子”中“黄豆”實係黄金之替代物。“瓜子”代金目前雖然還没有到見到直接的出土文獻證據,但從情理來説也是頗爲合適的,詳見下節。
四、“黄豆瓜子”與黄金形貌相似,故可爲黄金之替代物
要論證“黄豆瓜子”實係黄金之替代物,還需要回答一個關鍵的問題:爲什麽“黄豆瓜子”可以作黄金替代物?
“黄豆瓜子”之前的“上黨人參九枚,欲持代生人”“鉛人,持代死人”兩句,爲解答這個問題提供了重要參考——“人參”“鉛人”之所以可用來替代生人死人,關鍵在於它們具有人形。
人參具有人形當無疑。而且從其他鎮墓文來看,人參不僅如張叔敬鎮墓文所言可以代生人,其實也可以代死人。熹平四年胥氏鎮墓文“大(泰)山將閲,人參應□”(按:“應”後之字當是“之”),説的是泰山長檢閲時人參會替代死者去應答。①漢魏鎮墓文在强調生死有隔時,多有“生人屬西長安”“死人屬東泰山”一類語,可見在人們的觀念中,人死後魂歸泰山。鎮墓文多見“泰山長閲,死者某某自往應之”之語,如:建興四十六年傅女芝鎮墓文“太(泰)山長閲,死者傅女芝自往應之”,咸安五年姬令熊鎮墓文“太(泰)山長問見,死者姬令熊自往應之”(按:“問見”可能當作“閲見”或“閲視”),甘肅敦煌新店臺阿平鎮墓文“太(泰)山長[閲],死者阿平自往應之”。可推知熹平四年胥氏鎮墓文中的“人參”是作爲死者的替身去應對泰山長的檢閲。换言之,不管是生人還是死人,人參皆與之形狀相似,皆可替代。鉛人具有人形當然更容易理解。漢魏南北朝墓葬中隨葬鉛人的例子有不少(有時鉛人内置於陶瓶之内,陶瓶上或書有鎮墓文)。這些鉛人往往是由很薄的鉛片製成,有的做得比較逼真,甚至還有男女之别。②劉衛鵬、程義:《漢晉墓葬中隨葬陶瓶内盛物的初步研究》,《江漢考古》2008年第3期,第78—85頁。除張叔敬鎮墓文明確提及鉛人是死人之替身外,其他鎮墓文對鉛人代人還有更具體的描述。建和元年加氏鎮墓文:“故以自代鉛人,鉛人池池(佗佗),能舂能炊,上車能御,把筆能書。”可看出鉛人在地下代替死者從事各種雜役。又,建興九年張雪光鎮墓文:“謹以桐人、鉛人,廣肩大背,可以自代。”栩栩如生地强調鉛人身强力壯,足以替代死者進行勞動。此外,漢魏南北朝鎮墓文亦見“蜜人”(熹平四年胥氏鎮墓文“蜜人代行□作”,蜜人可能由蜜蠟製作)、“木人”(河南郾師正始五年鎮墓文)、“柏人/松人/松柏人”(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藏建興廿八年松人解除簡),此外文獻亦見“錫人”(《赤松子章曆》),時代更晚的鎮墓文中還有“石人”等。
總之,無論是天然具有人形的人參,還是使用各種材質製作的人工製品,都是因爲具有人形,所以可代人。“黄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既與“上黨人參九枚,欲持代生人”及“鉛人,持代死人”並舉,其背後的邏輯很可能是一致的。那麽,“黄豆瓜子”很可能與所替代之物在外形上存在某種聯繫。
“黄豆瓜子”的形貌和黄金有相似之處嗎?答案是肯定的。
自然金或産自砂礦或産自脈礦。金礦石露出地表,長期風化侵蝕後碎裂成顆粒、碎屑等,又經風力、流水等外力的搬運和分選,沉積於山坡、河床、湖海濱岸等處,便形成了砂金礦床。由於開採較易,早期採金都是開採砂金,開採脈金則是較晚時候的事情。秦漢時人們所能見到的自然金也應該是砂金。從文獻記載的一些對砂金形狀的描述來看,在古人眼裏砂金金塊可與大豆、瓜子形狀接近:①以下所引關於自然金形狀及顔色的文獻記載,多據夏湘蓉、李仲均、王根元:《中國古代礦業開發史》,地質出版社1980年,第298—299頁。均已核對原始出處。
凡金不自礦出,自然融結於沙土之中。小者如麥麩,大者如豆,更大如指面,皆謂之生金。昔江南遺趙韓王瓜子金即此物也。
(〔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金石門·生金”)
廣西諸洞産生金,洞丁皆能淘取。其碎粒如蚯蚓泥,大者如甜瓜子,故世名瓜子金。其碎者如麥片,名麩皮金。
(〔元〕周密《癸辛雜識續集》“金紫銀青”)
麩金出五溪、漢江,大者如瓜子,小者如麥。
(〔明〕李時珍《本草綱目》“金石·金”)
山石中所出,大者名馬蹄金,中者名橄欖金、帶胯金,小者名瓜子金;②此處“瓜子金”應是脈金。不過此亦反映出古人常用“瓜子”來描述自然金的形狀。水沙中所出,大者名狗頭金,小者名麩麥金、糠金;平地掘井得者,名麪沙金,大者名豆粒金。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五金·黄金”)
“黄豆瓜子”與天然的砂金形貌相似,可能不僅體現在形狀上,亦體現在顔色上。文獻關於自然金的顔色有如下描述:
麩金即在江沙水中,淘汰而得,其色淺黄。
(〔宋〕寇宗奭《本草衍義》“金屑”)
其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爲足色金也。
(〔明〕曹昭撰〔明〕王佐增《新增格古要論》“金”)
金有山金、沙金二種,其色爲七青、八黄、九紫、十赤,以赤色爲足色也。
(〔明〕宋應星《天工開物》“金石·金”)
由此可知,包括砂金在内的自然金,其色並不全然爲黄,根據純度的不同,會呈現出青、黄、紫、赤等不同的色彩。“黄豆瓜子”之黄豆當然是與“八黄”的砂金最爲相似(《泰原有死者》的“黄圈”也最可能象徵黄色的砂金);馬王堆遣策的“菜(彩)金”則有可能外塗了不同的顔色,以象徵各種顔色的天然砂金。
總之,自然産生的砂金與黄豆、瓜子在形狀和顔色方面皆有相似之處,故“黄豆瓜子”可爲黄金之替代物。①可補充的是,《泰原有死者》説“黍粟”“白菅”可分别代替錢、緜,恐怕亦與其形貌和錢、緜相似有關。上引文獻有“麩麥金”“糠金”之名,可見在古人看來糧食穀物的形狀和金錢存在相似之處,如果是一堆穀物和一堆金錢,則總體感官上更爲接近;白菅和白緜皆爲白色綫狀物,若皆捆紮爲一卷,則更爲相像。東漢靈寶張灣楊氏鎮墓文有言:“謹以鉛人、金玉爲死者解謫,生人除過。”“鉛人”與“金玉”並舉,此亦可與張叔敬鎮墓文對讀,佐證我們的觀點。
五、結論及餘論
本文觀點可大致總結如下:東漢熹平二年張叔敬鎮墓文有“黄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之語,我們認爲,“黄豆瓜子”實係黄金之替代物,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黄圈以當金”、馬王堆遣策“彩金如大菽”皆爲大豆代金觀念的反映,支持了這一解釋;黄豆、瓜子與天然的砂金在形狀及顔色方面皆相似,故可代金,繳納地下賦。
最後需補充的是,東漢魏晉南北朝鎮墓文、買地券中出現的各種“豆”,其性質並不單純,大致可分爲四系:
一、張叔敬鎮墓文“黄豆瓜子,死人持給地下賦”爲一系,“黄豆”是代金納賦之物,最終達到“復除”即解除重復的目的。②廣義的“重復”指死者返回陽世作祟的各種形式。關於“重復”,可略參黄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以買地券、鎮墓文、衣物疏爲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97—111頁。
二、“焦大豆”爲另一系(見於光和二年王當買地券、光和五年劉公則買地券、景元元年張氏鎮墓文等),“焦大豆生”常和“鉛卷(券)榮華”“雞子之鳴”並舉,它們是故意設置的陰陽往來的前提條件,是絶無可能實現的,從而達到隔絶生死的目的;③可略參黄景春:《中國宗教性隨葬文書研究——以買地券、鎮墓文、衣物疏爲主》第111—124頁。又,建興十三年自芝鎮墓文有“鉛人能行,人參能語,黑豆生英,桃李生莇,瓦狗能吠,五穀自甌”之語,“黑豆生英”爲“焦大豆生”之變體。
三、還有一系“豆”是較爲籠統的解除重復的法物,如:“今下斗瓶、五穀、黄豆、荔子、鉛人,用當重復生人”(永興三年趙詡鎮墓文、永興三年缺文鎮墓文);“今下斗瓶、黑豆、離子、五穀、鉛人,用生者當重復,死者解除憂”(建興十九年李興初鎮墓文)。在這裏,“黄豆/黑豆”和“斗瓶”“五穀”“荔子/離子”“鉛人”並舉,①舊將“荔子”讀爲“荔枝”或“梨子”;“離子”舊或釋爲“雞子”。按:疑“荔子”“離子”皆讀爲“藜子”,藜子爲穀物。是解除重復的法物,“黄豆/黑豆”的這種法力,很可能源自大豆的代金功能,也可能源於“焦大豆生/黑豆生英”,或二者兼有。
四、鎮墓文中的“豆”也可以只是單純地作爲穀物糧食。建興廿四年周振鎮墓文“送死人周振、阿惠:金銀錢財、五穀糧食、荔子黄遠、牛羊車馬、豬狗雞雛、樓舍惟(帷)悵(帳)、桮杅槃案、彩帛脂粉,諸入什物,皆於方市買賈。”這裏的“黄遠”當讀爲“黄卷/圈”,②“荔子黄遠”顯然可與上文所引“黄豆、荔子”“黑豆、離子”對讀,故“黄遠”當讀爲“黄卷/圈”。已有學者提出“黄遠”指黄豆,見寇克紅:《高臺駱駝城出土簡帛考釋二則》,簡帛網2008年11月18日,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897。應是最普通的、作爲穀物糧食的豆,似乎不承擔什麽額外的功能(至少没有直觀地反映在鎮墓文的敘述中)。又,光和□年王氏鎮墓文有“……五穀黄豆,□酒馬賄……”,這裏的“黄豆”有可能也是穀物之豆。總之,這兩篇鎮墓文中的“黄遠(卷/圈)”“黄豆”,應與前引馬王堆、鳳凰山、張家山遣策簽牌中的“黄卷”一樣,都是指作爲穀物的豆。
附記:本文基本觀點(即張叔敬鎮墓文“黄豆瓜子”當與《泰原有死者》“黄圈以當金”、馬王堆遣策“彩金如大菽”聯繫,“黄豆”爲代金之物)成形於2010年11月,當時曾草撰一稿。2012年《泰原有死者》正式公佈後,我對初稿進行了修改並作爲課程論文提交,論述粗淺,未敢示人。2017年初,爲參加芝加哥大學顧立雅中心舉辦的“Prayer,Sacrifice and Funerary Documents of Ancient China”會議,我將主綫觀點撰成“To Turn Soybeans into Gold:a Case Study of Mortuary Documents from Ancient China”一文,後發表於BambooandSilk第2卷第1期,但囿於自身的英語水平,加之英文論文的信息承載量有限,一些枝節問題無法納入。今以舊稿爲基礎,參考近年學界的相關研究,在結構、材料、論證各方面進行了相當幅度的增補和調整,重新撰寫了本文。請祈讀者師友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