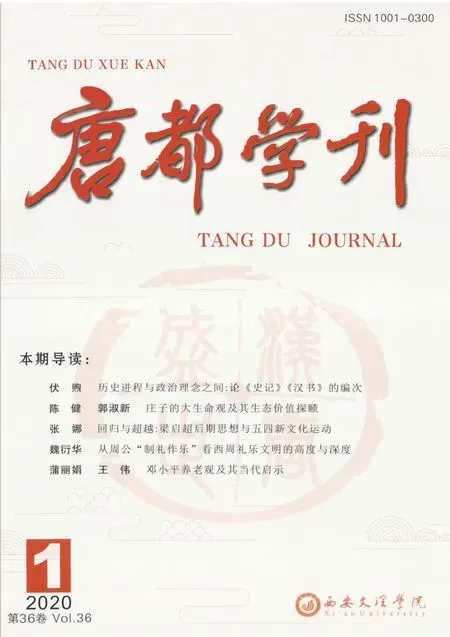女性、知识与权力
——《源氏物语》中的《史记》出典研究
刘佳琪,郭雪妮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西安 710119)
有关《源氏物语》学习、征引《史记》的研究,大体可以追溯到《源氏物语》早期的注释书,如《明星抄》认为《源氏物语》流畅优美的文体模仿的是《史记》笔法,各卷的安排与设计,也有《史记》影响的痕迹[1]95。此外,四辻善成《河海抄》、一条兼良《花鸟余情》等注释书都从不同角度论及《源氏物语》与《史记》的关系,大体涉及主题思想、人物形象、结构安排等多个方面,可谓极其详尽。近年来学界多从情节构思(1)参见田中隆昭《〈 源氏物语〉 里的孝与不孝——从与〈 史记〉 的关系谈起》,载于《天津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 年第6 期;高文汉《试析中国古代文学对〈 源氏物语〉 的影响》,载于《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1 期。、人物塑造(2)参见陈明姿《〈源氏退居须磨记〉 对中国史书及文学的受容》, 收入叶国良, 陈明姿编《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文学篇》,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年版, 第39 页。劳模《日本平安朝女作家与中国文学—一以紫式部为中心》,载于《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1 期。、语言、风格(3)参见覃启勋《〈史记〉 在日本》,载于《文史知识》,1988年第12 期。和结构(4)参见高文汉《试析中国古代文学对〈 源氏物语〉 的影响》,载于《日语学习与研究》,1991年第1 期。等方面入手进行探究。
但是,在对《源氏物语》学习、征引《史记》展开研究的同时,《源氏物语》创作的文化背景、作者的女性身份及其征引《史记》典故的方法却没有引起研究者充分的重视。因此,本文拟在对平安朝《史记》主流接受情况考察的基础上,重点分析《源氏物语》征引《史记》典故的方法,进而探讨紫式部如何以知识参与权力与话语建构。
一、《史记》在平安朝的讲读与接受
《史记》自随第一批遣隋使传入日本后,逐渐受到日本贵族知识分子的尊崇。根据史料记载,早在奈良时代,《史记》就已经成为日本大学的史学教科书。《续日本纪》天平宝字元年(757)11 月条记载孝谦天皇的敕命:“敕曰:如闻。倾年诸国博士、医师,多非其才,托请得选,非唯损政,亦无益民。自今已后,不得更然,其须讲经生者三经。传生者三史。”[2]243敕命明确规定“传生者”所学为“三史”,即《史记》《前汉书》《后汉书》。而在平安时代,《史记》则成为天皇、贵族的必读书目。《三代实录》就有大量关于天皇阅读《史记》的记载,日本清和天皇贞观十七年(875)4 月28日记载:“是日,帝始读《史记》。参仪从三位行左卫门督兼近江权守大江朝臣音人侍读。”[3]361
从奈良时代被作为大学教科书,到平安时代成为天皇、贵族的必读书目,呈现出《史记》逐渐被日本男性贵族世界广泛接受的进程。紫式部写作《源氏物语》时的10 世纪末11 世纪初,汉文学整体上虽不再像奈良时代和平安前期那样炽热,但《史记》仍是天皇、贵族的学习内容之一。《源氏物语》“少女卷”中有这样一段:
他打算将应读之书尽行读完,早日加入群臣之列,立身用世。果然只消四五个月,已经读完《史记》等书。
夕雾现已可应大学寮考试了。源氏内大臣先叫他到自己跟前来预试一下。照例召请右大将、左大弁、式部大辅及左中弁等人来监试。又请出那位师傅大内记来,叫他指出《史记》较困难的各卷中考试时儒学博士可能提到的各节来,令夕雾通读一遍。但见他朗声诵读,毫无阻滞,各节义理,融会贯通,所有难解之处,无不了如指掌。其明慧实甚可惊。监试诸人,都赞叹他的天才,大家感动流泪。[4]361
夕雾对《史记》的融会贯通得到称赞,这说明《史记》作为大学寮考试的必考科目,是当时贵族文人必备的修养,足见《史记》学习的确是贵族生活中的重要部分。然而,平安朝的整体文化环境,正如加藤周一指出的:“公家的汉文与私家的和文的区别,与男女的区别重叠在一起”[5]182,汉文是与公家、男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于男性而言,汉文书籍的学习关系到考试、立身、扬名、宫廷交际、官场应酬等,汉诗文水平的高低与身份、修养息息相关,但于女性而言却并非如此。《源氏物语》“雨夜品评”一段中,左马头在定义女子品级时有言:“一个女子潜心钻研三史、五经等深奥的学问,反而没有情趣。”[4]33所谓有“情趣”,即是本居宣长所概括的《源氏物语》一书宗旨——“知物哀”。“知物哀”就是对“世上万事万物,形形色色,不论是目之所及,抑或耳之所闻,抑或身之所触,都收纳于心,加以体味,加以理解”。有情趣、知物哀的女子,会用自然的人性、人情去体察身边的一切,既体现家世教养,又富有风流雅趣。因此,当时女性的主要学习内容,“第一要习字,其次要学七弦琴,注意要比别人弹得更好,还有随后《古今集》的歌二十卷,都要能暗诵,这样的去做学问。”[6]22这样的“女性学问”自然不会包含充满政治、道德意识的《史记》在内。女性修习弹琴、习字与咏歌,增加自己的情趣是表层目的,深层目的则在于促进与男性的交往,通过具有浓烈游艺色彩的“学问”迎合男性审美,最终得到美满的婚姻与归宿。
二、《源氏物语》中的《史记》出典
《紫式部日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那个叫式部丞的人,在一旁读《史记》时,听了又听,只是不懂,又记不住。我倒出奇地很快听懂了。对汉文典籍很有研究的父亲时常叹息说:‘可惜不是男儿, 真不幸啊!’”[7]355窃以为,这段话至少包含了两个信息:其一,紫式部虽然身处热衷学习汉文书籍的社会,但由于性别原因,紫式部没有像式部丞一样学习《史记》的“合法性”;其二,尽管没有学习的“合法性”,但书香之家的耳濡目染,还是足以让紫式部积累了深厚的汉文修养。这种汉文修养的直接体现就是《源氏物语》对汉文典籍的大量征引,其中,数量最多的是《白氏文集》,其次当属《史记》。
《源氏物语》多处征引《史记》典故,由于篇幅所限,本文选定其中最重要的五处作为讨论范围。现以典故在《源氏物语》中出现的顺序排列如下,并作简要分析:
第一,《杨桐》卷引戚夫人的典故:
她回想桐壶院在世时对她无微不至的宠爱以及恳切的遗言,觉得现今时世大变,万事面目全非。我身即使不惨遭戚夫人的命运,也一定作天下人的笑柄。[4]196
此处,作者让藤壶皇后自比戚夫人,但通过“即使不……也……”这一句式(5)原文作“戚夫人の見けん、目の樣にはあらずとも、かならず、人笑へなる事は、有りぬべき身にこそあめれ”,参考自《日本古典文学大系14:源氏物语》(第一册),山岸德平校注,岩波书房1958 年版,第388 页。,说明藤壶皇后此时之所以对自己的处境担忧,一方面是因为掌权的弘徽殿太后有可能因桐壶帝生前对自己和皇太子的宠爱而施加报复,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受源氏纠缠,担心与源氏私通的“恶名”泄露于世。也就是说,对藤壶皇后而言,“沦为天下人的笑柄”是足以与“戚夫人的命运”相比的可怕之事。戚夫人的典故,见于《史记·吕太后本纪》[8]897。戚夫人在刘邦生前可谓是集万般宠爱于一身,刘邦甚至有意立其子刘如意为太子。但在刘邦去世后,戚夫人却遭到吕后的报复:先是被砍去手脚、剜去双眼,继而被用药熏聋耳朵,灌了哑药,最后被扔入厕中,称为“人彘”,受尽折磨而死。此处引戚夫人典故,将两者相提并论,无疑传达出与源氏私通一事,着实给藤壶皇后带来了极重的心理负担。
第二,《杨桐》卷引“白虹贯日,太子畏之”的典故:
弘徽殿太后的哥哥藤大纳言的儿子头弁,自从祖父右大臣专权以来,变成了一个青年红人,目空一切。此时这头弁正前往探望其妹丽景殿女御,恰巧源氏大将的前驱人低声喝着,从后面赶上来。头弁的车子暂时停住,头弁在车中从容不迫地朗诵道:“白虹贯日,太子畏之!”意思是讥讽源氏将不利于朱雀帝。[4]200
“白虹贯日”是指形如白色的长虹穿日而过,这种大气光学现象被古人视为君王丧命之象,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凶兆。但是,从相反的角度看,如果统治者是暴君,那么“白虹贯日”则会被当做吉兆,出自《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8] 2470中的“白虹贯日,太子畏之”即是一例。“白虹贯日,太子畏之”的意思是,尽管天空出现预示君主殒命的白虹贯日之象,可是燕太子丹仍然担心荆轲不能顺利刺杀秦王嬴政。在典故中,此句出于邹阳之口,邹阳忠心耿耿却因羊胜等人的谗言被梁孝王下到狱中,因此,感叹“白虹贯日,太子畏之”是意在说明自己有着像荆轲一般“为君所疑”的苦楚。反观《杨桐》卷,从头弁的角度讲,虽然他引用的是“白虹贯日,太子畏之”整句话,但其实他的意图只在征用前半句“君王丧命”的征兆意义来表达对源氏的猜忌和厌恶,“太子畏之”的意义是缺席的。
第三,《杨桐》卷引“文王之子,武王之弟”的典故:
诸人皆极口赞誉源氏大将,或作和歌,或作汉诗。源氏大将得意之极,骄矜起来,朗诵“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这自比实在很确当。但他是成王的何人,没有继续诵下去,因为只有这一点是疚心的。[4]208
典故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诫子伯禽日:“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于天下,亦不贱矣。”[8]1518周公旦是西周开国重臣,曾辅佐武王战胜殷纣。武王死后,周公担忧天下人听说武王死而背叛朝廷,遂替幼小的成王代为处理政务,主持国家大政,但此举却招来管叔等人的嫉妒。其子伯禽代其到曲阜就封时,他对伯禽说了这段话,意在告诫伯禽不要因为自己身份高贵就轻慢于人,要谦虚待人,才能不失贤士归心。《杨桐》卷中,“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换在源氏身上,就置换成了——桐壶之子、朱雀之弟,身份的确如同周公一样高贵。然而,紫式部却并不是为了显出源氏的高贵或者谦虚才让他说出这样一句话,此处的重点恐怕在于“但他是成王的何人,没有继续诵下去,因为只有这一点是疚心的”这一句。《史记》中的成王,在《源氏物语》中与此时的皇太子、后来的冷泉帝形成类比关系,但冷泉帝名义上是源氏的弟弟,实际上却是源氏的儿子。因此,紫式部让源氏说出这样一句话,不仅刻画出源氏此时春风得意的样子,而且暗指了他与藤壶皇后的私情,可谓一举两得。
第四,《须磨》卷引赵高指鹿为马的典故:
源氏公子兄弟辈的诸皇子,以及向来与公子亲善的诸公卿,起初常有书信寄须磨慰问,并且有富于情味的诗文互相赠答……弘徽殿太后听到他们同他唱和,很不高兴,骂道:“获罪于朝廷的人,不得任意行动,连饮食之事也不得自由。现在这个源氏在流放地造起风雅的邸宅来,又作诗文诽谤朝政,居然也有人附和他,像跟着赵高指鹿为马一样。”[4]235
典故见于《史记·秦始皇本纪》:“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乃先设验:持鹿献于二世曰:‘马也。’ 二世笑曰:‘丞相误耶,谓鹿为马?’问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马’以阿顺赵高。”[8]273《须磨》卷中,弘徽殿太后将源氏比作只手遮天的权臣赵高,无疑传达出她对源氏极度的反感,厌恶之情溢于言表。
第五, 《新菜续》卷引“百步穿柳叶”的典故:
有人说道:“承蒙诸位夫人送来这许多华丽的奖品,美意诚可感谢!单教百步穿柳叶的能手欣然享受,未免太杀风景了。本领差些的人应该也都来参与竞赛。”于是大将及以下的人都走下庭中去。[4]586
“百步穿柳叶”见于《史记·周本纪》:“楚有养由基,善射者也,去柳叶百步射之,百发而百中之。”[8]165紫式部引用养由基的典故,不仅说明“能手”本领高超,可与在射艺上出类拔萃的养由基作比,而且客观上反映出中国游艺项目射艺传入日本后,在贵族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这一历史事实。
三、女性意识的反叛与妥协
据上文对《源氏物语》中《史记》出典的分析来看,上述典故征引均着眼于套用原典的人物故事,或传达人物感情,或表露作者倾向,或塑造人物形象,或丰富情节内容,体现了紫式部对《史记》的谙熟。男性依靠对《史记》的学习参与生活,紫式部则借用《史记》来文饰自己的作品,描写并解释生活。这种文饰不仅体现了不低于男性的汉文实力,同时,由于假名书写的物语本身的私家性质,当《史记》典故作为纯粹的叙事融入《源氏物语》时,《史记》就有了“私家”的存在方式,这在客观上构成了对《史记》的男性话语身份的消解。男性依凭知识权威划定的《史记》接受边界,就这样被紫式部通过文体跳脱了。并且,诸如“作者乃一女流,不宜高谈国事。记此一端,亦不免越俎之罪”[4]189,“作者女流之辈,才疏学浅,不宜侈谈汉诗。为免烦琐,一概从略”[4]361之类的解说,在《源氏物语》中不胜枚举。可见紫式部在使用《史记》构筑女性物语世界时,对自我女性身份与汉文世界的对立有足够的认知。因此,对《史记》的征引就不单单构成了对《史记》公家身份的消解,更意味着以知识构建权力,从而对根基深厚的男性文化意识进行反叛。这种反叛,不仅建立在对男性世界知识掌握的基础上,也来源于对自我价值认知的渐趋明确。
《源氏物语》在诞生之初,尽管是作为“‘聊以’消遣的娱乐性读物”[9]103与“和歌咏唱指南”存在的,但并不代表紫式部对自我所作物语的定位也仅限于此。紫式部在第25卷《萤》中借人物之口发表了对物语的认识,如“不看这些故事小说,则日子沉闷,无法消遣。而且这些伪造的故事之中,亦颇有富于情味,描写得委婉曲折的地方,仿佛真有其事。所以虽然明知其为无稽之谈,看了却不由你不动心”[4]435。又如“虽然并非如实记载某一人的事迹,但不论善恶,都是世间真人真事。观之不足、听之不足,但觉此种情节不能笼闭在一人心中,必须传告后世之人,于是执笔写作”[4]436。这体现了紫式部对自己所写所作的肯定,并试图在理论上为其提供支持。不过,很难想象紫式部在创作伊始就预见自己的作品会获得巨大成功。《源氏物语》共54 卷,《萤》卷处于中间的位置,这并不是偶然的。只有在写作与传播的过程中得到藤原道长的资助和天皇的喜爱之后,她对自己所写物语的价值才表现出了肯定。关于物语的讨论就是其女性意识的佐证——是那个时代有才能、但又畏于身份的限制、畏于当时阶级环境所限制的一位女性通过文体所作的、对于男性话语体系的反抗。
但是,由于时代环境限制与个人心理影响,紫式部对男性话语体系的反抗也体现出了矛盾与局限。紫式部创作《源氏物语》时,是身处封闭的宫廷社会之中的女官。处在这样一个小集团中作者和读者本身就缺乏距离感,且《源氏物语》是写好一回便传阅一回的,因此,书写过程就极易受到读者评论影响。而从《紫式部日记》中,不难看出紫式部是一个相当敏感的人,很在意其他人的看法和议论。《紫式部日记》中记录了一段紫式部家中侍女的议论:“汉籍读得多了,才会薄幸,为什么身为女子却要读汉文呢。从前的女子,就连阅读经书都要被禁止的呀。”[7]352因为受到这些议论的影响,紫式部便决定“连一个汉字也不写了”。在家中尚且如此,更何况在女官云集的后宫中,处世似乎并不是很顺利,因此更是步步小心。诸如“作者乃一女流,不宜高谈国事。记此一端,亦不免越俎之罪”等评论干预,正是紫式部与评论背后读者的普遍认知做出的调和,以此来达到与读者的价值相合。
至于对《史记》这一汉文典籍的征引,虽有《紫式部日记》的佐证,可以确定紫式部是通过阅读《史记》通晓这些典故的,但这些典故的传播渠道并非就是《史记》,这些故事基本在《艺文类聚》中均有收录。《艺文类聚》成书于唐高祖武德七年(624),至迟在淳和天皇时期(823—833)已在日本广泛传播。虽然与《史记》同为汉文书籍,但由于其类似于故事集的性质,内容较《史记》更易传播。《史记》虽然作为汉籍不在女性学习的范围内,但《史记》中的故事通过《艺文类聚》这类类书传播乃至运用到日常会话中确有可能。对紫式部的读者而言,《源氏物语》中的《史记》典故的汉文身份很可能并不十分明显,而只作为故事存在,因此并没给紫式部带来许多她所“在意的评论”。
而且,对于家中侍女关于阅读汉籍会“薄幸”的议论,紫式部虽然并不全然认同——“迷信哪些东西真的会长命无恙吗?没有人见过,也无法证实呀”,但却紧接着又说,“侍女们说的或许真的有点道理”[7]352。可见,这些时时萦绕于耳畔的男性话语,其实已经渐渐地内化于紫式部的意识中,并无形中成为她前进的阻力。此外,紫式部在日记中针对清少纳言写汉字发表的一段评论,也可以作为她对汉籍看法的佐证:“清少纳言是那种脸上露着自满,自以为了不起的人,总是摆出智多才高的样子,到处乱写汉字,可是仔细一推敲,还是有许多不足之处。”这说明紫式部本人对汉籍的认识是充满矛盾的。尽管紫式部在对《史记》典故的征引中得到了自我价值的确认,但由于他人乃至本人共同构成的社会意识的施压,紫式部的反叛与动摇并存,她不得不一再退缩,重新进行身份认同。
综上所述,尽管紫式部对所作物语的价值有充分的认知,并主动征引男性汉文世界的《史记》来文饰自己的叙事,客观上表现出对男性话语体系的反叛,但并不能因此认定其对自我价值的认知已经上升到成熟女性意识的层面。紫式部的女性意识中呈现出的更多是矛盾:一方面,她在无形中已经接受了男权体制下的种种规约,并以男性愿望所要求的方式看待自己;另一方面,自身的想法与需求自然会不断地与这种规约和方式发生冲突,而为了迎合男性的文化借以使自身获得认可,又故意对自己的想法和需求视而不见,继续用男性的标准压抑、克制自己,从而加剧了冲突。这种女性意识萌发之初的样态,也见于平安朝女性文学的另一经典之作——《枕草子》中。首先,《枕草子》同样征引了《史记》典故,分别是“女为悦己者容,士为知己者死”“孟尝君鸡鸣度关”与“项庄舞剑,意在沛公”,这三处典故的征引不仅体现出清少纳言如紫式部一般不凡的汉学修养,征引方法也与《源氏物语》如出一辙,即用《史记》来文饰自己的作品。其次,《枕草子》的作者对“女性”的认识同样充满了矛盾。《枕草子》第二〇段“女人的前途”一节,先是说“没有什么希望,只是老老实实地守候仅少的幸福,这样的女人是我所看不起的。有些身份相应的人,还应该到宫廷里出仕,与同僚交往,并且学习观看世间的样子”,同时又表示同意有些男人所认为的 “出仕宫廷的女人是轻薄不行的,那样的人最是可厌”的观点,继而又为出仕的女人辩解,“有过出仕宫廷的经验,那就不会像乡下佬的样子,把有些不懂的事情去问别人的必要了。这也就是很是高雅的事情了。”[6]24可以说,这种女性意识萌发之初的矛盾,构成了平安朝女性文学的共性。一方面,她们认识到了自己所写所作是有意义的,产生了流传后世的想法;另一方面,又因为女性身份而自卑,只能怯怯地与男性的世界对抗,呈现出一种极其复杂的形态。但是,她们的女性意识毕竟已经显现——《源氏物语》征引《史记》典故的方法,提供的正是窥见一斑的窗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