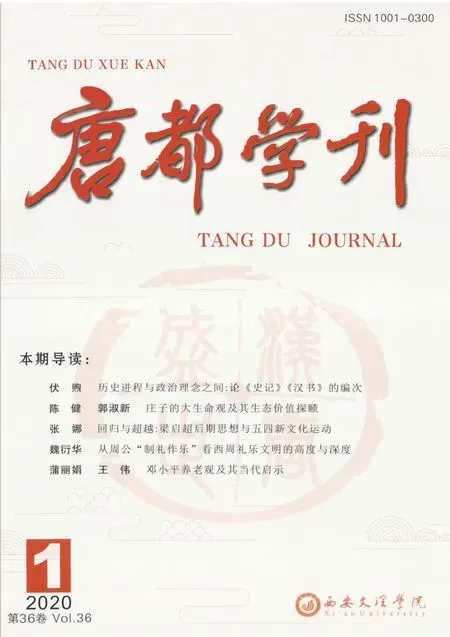历史进程与政治理念之间:论《史记》《汉书》的编次
伏 煦
(山东大学 文艺美学研究中心,济南 250013)
自然时间对于历史和历史书写而言皆是最重要的维度,编年体史书的体例便以时间作为最基本的标准组织历史事件,《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所以纪远近,别同异也。”[1](杜预《春秋左氏传序》)但是比起“系日月而为次,列时岁以相续”[2]25的编年体史书,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正史,历史时间虽然在使用编年体写作的帝王本纪、诸侯世家与年表之中依然占据者主导地位,但不再作为影响史书体例的唯一标准,单纯地按照时间排列事件,必然无法全面反映历史本身的进程以及史学家对于当时政治秩序的理解,本文将以作为通代与断代纪传体正史首创之作的《史记》《汉书》的编次问题为例,来讨论自然时间之外的两个维度,即历史进程与政治理念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史书体例与历史书写。
一、《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世家中的西周春秋诸侯史
对于纪传体史书而言,历史进程首先是以自然时间来推进的,大部分本纪、年表、世家、列传的编次都遵从自然时间所确立的秩序,以《史记》三十世家为例,《吴世家》第一至《郑世家》第十二,是西周春秋的十二世家;位列十三至十五的是瓜分晋国的赵、魏、韩三世家,第十六是取代姜氏的田齐,以上是战国四世家;第十七位是孔子,“仲尼悼礼废乐崩,追修经术,以达王道。匡乱世反之于正,见其文辞为天下制仪法,垂六艺之统纪于后世”[3]5219-5220,孔子有德无位,以其学术文化上的功绩和对于后世的深刻影响,故入辅弼天子的诸侯之列;第十八位是陈涉,“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3]5220,陈涉首倡反秦,功大而入世家;第十九位是西汉前期后妃(除吕后入本纪),作为西汉帝王之母妻,她们以合传的形式集体入世家,并且排列在《楚元王世家》《荆燕世家》与《齐悼惠王世家》这些汉初宗室之前;汉初宗室三世家之后,分别是萧相国、曹相国、留侯张良、陈丞相、绛侯周勃等西汉开国功臣,继而司马迁以文帝子梁孝王、景帝十三子(五宗)、武帝三王次于其后,是为三十世家。
上述《史记》三十世家的编次自然是符合历史时间的,然而若详细追究,我们或许会产生这样的疑问,其中最大的一组,即西周春秋的十二世家内部,又遵从了一个怎样的标准?历史时间是唯一的因素吗?司马迁以吴、齐、鲁、燕、管蔡、陈杞、卫、宋、晋、楚、越、郑之次序排列春秋十二世家,为什么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的十三国次序非常不同?《十二诸侯年表》以周为先,鲁次之,以下是齐、晋、秦、楚、宋、卫、陈、蔡、曹、郑、燕、吴[3]896。通过仔细分析与对比,窃以为《史记》的西周春秋十二世家的次序反映了西周分封诸侯所建立的政治秩序,司马迁基于对这种周王室政治理念的认同,以此为标准安排了春秋十二世家的次序;而《十二诸侯年表》的次序,是春秋时代诸侯力政、弱肉强食的历史形势的反映,则是以实际的历史进程为标准。
首先来看西周春秋十二世家的情况,有论者指出吴太伯为首反映了太史公自身所认同的道德观念:“《伯夷列传》和《吴太伯世家》分别被置于‘列传’和‘世家’的第一篇,显示了司马迁的尊重让国、让天下之义举的价值观。这与《五帝本纪第一》有关禅让的记事也有着联系。”(1)(日)今鹰真《关于〈史记〉的编次——特别是关于〈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分别置于“世家”“列传”第一篇的意味》,载《司马迁与史记论集》第3 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191页。吴太伯作为周文王的长兄,其事迹当在周灭殷商之前,故列其于世家之首,不仅与伯夷列于七十列传之首的意味相似,都是推崇廉让之节,而且符合实际的历史时间顺序。《吴太伯世家》以降的诸篇,可以大致分为三组,其一是《齐太公世家》《周公世家》和《燕世家》,太公望“文武是师”,被尊为“尚父”,其位在周初崇高,后代桓公又有“九合诸侯”之功,故其位列西周立国后诸位同姓诸侯之前;紧跟其后的是周公、召公所分封的鲁、燕世家,两人作为武王母弟,辅弼成王,安定周室。第二组四世家皆与周初安抚前代的政策有关,《管蔡世家》的主角管叔鲜与蔡叔度亦是武王母弟,“二人相纣子武庚禄父,治殷遗民”,然管蔡“疑周公之为,不利于成王,乃挟武庚作乱。周公旦承成王命,伐诛武庚,杀管叔而放蔡叔,……从而分殷余民为二。其一,封微子启于宋,以续殷祀。其一,封康叔于卫君,是为卫康叔”[3]2252(2)《管蔡世家》亦交代武王其他几位母弟的分封情况,排行第六的曹叔振铎附后,行七的成叔武与最小的冉季载其“后世无所见”,霍叔处行八,其国灭于晋献公,卫叔封行九,入《卫世家》。从这个意义上看,《管蔡世家》亦可看作武王母弟的合传。。卫国与宋国分列第七、第八位,是因管蔡之乱后分封,时间上晚于绍帝舜之后的陈国与绍夏禹之后的杞国。
第三组是晋、楚、越、郑四国,其中,晋国始于成王之弟唐叔虞,时间上亦晚于周初封建的诸侯。次于《晋世家》的,是同样受封于成王之世,且被视作南蛮的楚国:“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3]2473-2474。春秋中后期,吴越两国亦始通于中原并参与争霸,吴国作为太伯之后位居世家之首,越国登上历史舞台较晚,根据《越王勾践世家》的记载,越国亦是夏禹之苗裔,勾践先人乃“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后二十余世,至于允常”。 允常乃勾践之父,之前越国的世系失载[3]2252-2553,便只能次于楚国之后了。郑国始于周宣王庶弟友,“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3]2584,此时距离周幽王被犬戎所杀仅有三十五年,分封时代较晚,而且春秋中期之后,郑国处于晋楚争霸的夹缝之间,艰难生存,国力亦有限,故而以郑押尾。
相对于《史记》十二西周春秋诸侯世家的编次而言,《十二诸侯年表》的排列体现更多的是西周共和年间(前841—828)之后历史进程的实际情况。年表首行为周,尊崇天子之意,次为鲁,《春秋》以鲁君系年,故而周、鲁为先,与世家的排列相似,是政治理念的反映,也可视作提供了一个历史时间的坐标。以下齐、晋、秦、楚、宋五国,在春秋中前期依次称霸,很明显是依据实际的历史进程而建立的秩序(3)近代学者刘咸炘在《太史公知意》中认为:“(《十二诸侯年表》)本以鲁为主,而齐、晋、秦、楚四大国次之,余则威服于四大国者也。”载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49页。;之后的卫、陈、蔡、曹四国,虽然都是春秋时期的小国,但立国较早,十二西周春秋世家中的管止于管叔鲜本人,杞国更是“杞小微,其事不足称述”[3]2291(4)太史公在此之后总结了“唐虞之际,名有功德臣也”之后代在西周的分封情况,其中,“滕、薛、驺,夏、殷、周之间封也,小不足齿列,弗论也。”可见,极为关心三代帝王名臣之后的太史公,时常将历史的实际情况作为更加重要的因素。,故而不入年表;卫虽小国,亡于战国末年,故次序早于陈(灭于哀公十七年)、蔡(灭于春秋后二十三年,晚于陈三十三年)、曹(灭于哀公八年);郑国立国较晚,故又次于这些春秋小国之后,燕国虽然立国很早,而且始祖召公作为辅弼成王的重臣,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然而燕国在春秋时代默默无闻,其国世系纪年虽然清楚,但纪事最早见于《春秋·襄公二十九年》“齐高止出奔北燕”[4](5)之后北燕在《春秋》的纪事依然极少,《昭公三年》记“北燕伯欵出奔齐”,《昭公六年》记“齐侯伐北燕”。《左传·昭公三年》记载的出奔国君是燕简公,而《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与《燕世家》记载的是燕惠公,昭公六年齐侯伐北燕的目的,《左传》与《史记》皆记载是纳燕出奔之君,《史记》记载燕惠公于归国之次年卒,而《左传》未提及。一事,其国流传的事迹极少,对春秋时代影响亦小。吴国作为春秋末期之霸主,在春秋末期国家实力和国际影响远高于燕国,然而吴王寿梦(寿梦元年是鲁成公二年)以前虽有世系而无系年,故无法编入年表,只能在《吴太伯世家》中述之;类似的越王勾践之父允常以上,先代世系纪年皆无考,亦无法编入年表。
我们可以看出,《十二诸侯年表》的编排,主要原则是诸国在西周末年至春秋时代的实力和影响,作为西周初年分封的管、杞并未列入其中;客观原因还有史料的齐备和缺失:燕国因为世系和系年的完整,列于失载春秋中前期系年的吴国之前,而越国的西周春秋世系整体缺失,故而无法编入年表。
通过以上对《史记》十二西周春秋诸侯世家与《十二诸侯年表》编次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太史公在建立《史记》西周春秋史书写体例的时候,存在着两种标准:一种是西周初年周王室通过分封诸侯所建立的政治秩序,司马迁认同这种政治理念,因而十二西周春秋诸侯世家的编次呈现出现在的面貌;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在某种理念的支配下进行,历史进程的展示也是史学家的基本任务:“幽、厉之后,周室衰微,诸侯专政,春秋有所不纪,而谱牒经略,五霸更盛衰,欲睹周世相先后之意,作《十二诸侯年表》第二。”[3]5209
这两种标准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同时历史时间作为一个始终产生影响的因素,亦在两套不同的秩序中有所反映:十二西周春秋诸侯世家的排列亦大体按照历史时间次序,晋、郑等后封的诸侯国亦编于靠后的位次;另外,吴太伯是武王的伯父,周公、召公以至于卫康叔,皆是武王的母弟,唐叔虞是武王的儿子,西周初的同姓诸侯王的次序依照的是家族的行辈,这也是时间顺序的体现。在《十二诸侯年表》中,周、鲁居前,周为天子,本不在十二诸侯之列(6)《十二诸侯年表》实际上记叙了十三个诸侯国的世系及大事,时培磊《试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之“篇言十二,实叙十三”问题》,《唐都学刊》,2010 年第3 期。时文认为,“十二诸侯”的名称并非学术史上所认为的那样,去掉秦、吴、鲁等某一个诸侯国,数字只是虚指,十二诸侯之数的确立和《史记》各体例之数相合,十二本纪取法《春秋》十二公。;而《春秋繁露·三代改制》云:“故《春秋》应天作新王之事,时正黑统,王鲁,尚黑。”[5]在《春秋》公羊学的理论体系中,“王鲁”之说具有重要的地位。《十二诸侯年表》将鲁次于周,列于“春秋五霸”之前,以是出于政治理念而不是历史进程的考量。两者合而观之,展示了春秋时代诸侯国力的升降对西周初期分封制度的破坏,司马迁创制的书写体例,实际上继承了《春秋》的批判精神。
在两种原则交织的影响下,太史公建立了一个相对严密的书写体例,一方面是他自己认同的西周初期的政治秩序及其理念,另一方面是春秋之后时势的变化发展,这一过程既非单纯的建构,亦不是对客观事实不加整理的接纳。在《太史公自序》中,太史公声称“余所谓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3]5203但他亦以“作五帝本纪第一”等百三十篇,表达了自己通过绍续《春秋》以“成一家之言”的志向。可见太史公自身的定位,是在“述者”与“作者”之间的。
二、“光汉”:《汉书》对西汉前期历史秩序的重构
与《史记》类似的是,《汉书》在建构文本秩序的过程中,亦存在历史进程和政治理念的纠葛。班固在《汉书·叙传》中声称:
汉绍尧运,以建帝业,至于六世,史臣乃追述功德,私作本纪,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太初以后,阙而不录,故探纂前记,缀辑所闻,以述《汉书》,起元高祖,终于孝平王莽之诛,十有二世,二百三十年,综其行事,旁贯五经,上下洽通,为春秋考纪、表、志、传,凡百篇。[6] 4235
《史记》原名《太史公书》,尚有诸子遗意,司马迁个人对历史总趋势的看法尽可以表达,不必为一朝一姓而作;而《汉书》作为“汉室之书”“断自高祖,尽于王莽,……勒成一史,目为《汉书》。”[2]20“班氏不满史公将汉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故特以前汉为起讫,称为‘汉书’,以与唐虞三代之书,争光并美;其意在于尊汉,为汉代之统治者而著书,绝无标榜断代之意。”[7]287在了解《汉书》“尊汉”与“光汉”的著述目的的前提下,我们就不难理解,班固虽然声称《汉书》百篇为“述”(7)《汉书·叙传》依次罗列百篇之目录,“述《高纪》第一”等;这与《史记·太史公自序》“作五帝本纪第一”等截然不同。刘咸炘认为:“(班固)改言述,盖避作者之谓圣,而取述者之谓明也。”见氏撰《汉书知意》,《汉书知意》为札记体,在每篇之下多有对《汉书》题目编次的解释。参见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233页。,并且几乎全盘接受了《史记》的文字,然而在书写体例的建构方面,我们可以看出班固“重构”西汉前期历史的意图。
首先是在“传”的题目上,《汉书》取消了世家,故而《史记·陈涉世家》以降的汉初后妃、宗室诸王、皇子与开国功臣等,在《汉书》中只能入传;项羽亦不可能与汉代皇帝并尊,只能与陈涉合传,居于列传之首。《汉书》列传前四(8)《汉书》前四篇传,正是徐冲所谓的“开国群雄传”“其书写对象是与王朝‘创业之主’之间不存在原初性君臣关系的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其在纪传体王朝史中的位置则通常被置于本纪之后,诸臣传之前。”对于《汉书》而言,“与王朝‘创业之主’之间不存在原初性君臣关系的前代王朝之末世群雄”这一定义,无法涵盖《汉书》卷三十一至三十四的专主身份,这四卷传记似乎是“开国群雄传”“开国功臣传”与“异姓诸侯王传”相互混杂的产物。见氏撰《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单元二“开国群雄传”第一章《“开国群雄传”小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年版,79-81页。,只有《张耳陈余传》第二的安排,与《史记·张耳陈余列传》第二十九相合(此前为先秦及秦代人物),《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和《韩彭英卢吴传》第四是汉初异姓诸侯王传记,实际上重新整合了《史记》的《魏豹彭越列传》第三十、《黥布列传》第三十一、《淮阴侯列传》第三十二、《韩信卢绾列传》第三十三和《田儋列传》第三十四。关于《魏豹田儋韩(王)信传》第三的安排,刘咸炘认为:“班断代为书,分详则伤烦,故合列三人,以其皆六国之后,意见赞中”[8]196。徐复观先生虽然指出“《汉书》则魏豹、田儋、韩王信为合传,因为这都是六国余荫的异姓之臣。在形式上,《汉书》的排列似较合理。”但通过分析《史记》将魏豹、彭越、韩(王)信、卢绾合传的原因,以及彭越、黥布、韩信对于西汉开国的重要地位,便进一步得出“在问题的实质上,则史公的安排为不可易”的结论[7]317-318(9)徐先生认为,班固“对于有损刘氏庄严的异姓功臣的诸记录,他在良心及事实上不能不承认,但在承认中也做了技术性的处理,以减轻他们的分量,亦即所以维护帝统的庄严。”。
如果我们从建构文本秩序的角度看,史学文本秩序所折射的,一方面是撰述者的政治理念,另一方面则是实际的历史进程,《汉书》为光大汉室而作,自然要以更加规整而严密的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确立政权本身的合法性,故而实际的历史进程是在政治理念的支配下进行的。有趣的是,在这一调整过程中,《汉书》传记的题目中加入了许多在司马迁看来无足轻重、事迹附他人传记而传世的人物。如汉初唯一善终的异姓诸侯王长沙王吴芮,《史记》仅在《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中为其国留有一席之地,而《汉书》将其列入汉初异姓诸侯王专传之末,虽然吴芮事迹无多,亦无奇行,班固的目的在于完整地呈现汉初国家机器的构成,自然不会遗漏任何有一定政治地位的人物,使得自己精心建构的秩序留有瑕疵。
同理,这种建立完整秩序的“重构”活动,还见于《高五王传》第八、《张陈王周传》第十与《张周赵任申屠传》第十二。“高祖八子,二帝六王。三赵不辜,淮厉自亡,燕灵绝嗣,齐悼特昌。”[6] 4248其中,对于淮南王刘长,因其子谋反不得善终,《史》《汉》皆单独立传,齐悼惠王一支在铲除诸吕之时颇有建树,故《史记》以《齐悼惠王世家》纪其事,而并未给三位赵王和燕王四王立传(10)徐复观先生认为:“《史记》‘高祖八子’之名,及齐悼惠王肥、赵隐王如意、赵幽王友、赵共王恢等的遭遇,因系吕后专制,大发其毒狠之私的结果,而诸人又无独立行谊可述,故《史记》皆附见《吕后本纪》。……在形式上,(《汉书》)较《史记》为整备;但不仅在内容上无所增益,且史公由诸王之遭遇以集中写出吕后的凶残成性,借此以暴露此段历史之真相的用心,反因之模糊消失。”《两汉思想史》(第三卷),314-315页。。实际上,班固的做法,与《史记》立《管蔡世家》《陈杞世家》有类似之处:管叔鲜因作乱废死,曹叔振铎亦无甚事迹,杞国小微而无足称道,然而他们或是文王嫡子,或是先代帝王之后,《史记》为其立世家,亦是政治理念与相关历史事实的反映,刘咸炘在《太史公知意》的“管蔡世家”条指出:“此篇承太公、周、召之后,收拾文王诸子,下则列三恪及卫,次第甚明白,……曹国非重,岂宜独夹于三公、三恪之间哉?且此篇虽题管蔡,实总叙文昭,曹亦文昭,故叙于此,犹《万石张叔列传》后叙周、赵、任、申屠,史公篇题本不取该备也。”[8]76从这个角度看,吴芮、高祖诸子进入《汉书》列传的意义,与《史记》西周春秋诸侯世家亦是相似的(11)《汉书》改《史记·梁孝王世家》为《文三王传》亦是同理,刘咸炘认为:“马之《梁孝王世家》实文三王世家也,班详其标目。”参见《刘咸炘学术论集(史学编)》,202页。。
《史记》为萧何、曹参、张良、陈平、周勃各立世家,凸显五位开国功臣对于汉初政局稳定所做出的贡献,不得不说,《汉书》将其压缩入《萧何曹参传》和《张陈王周传》,且置于汉初宗室、皇子之后,至少没有特别表彰五人的意图。其中,萧何和曹参是高祖和惠帝之时的丞相,陈平是卒于文帝初年,周勃继任。其中,曹参去世后,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任左丞相(12)高后元年,王陵为太傅,陈平为右丞相,吕后亲信审食其任左丞相,见《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表》,752页。,《史记》将王陵附于《陈丞相世家》,并未单独立传,《汉书》将其列入具有丞相传性质的《张陈王周传》,实际上肯定了王陵“任气,好直言”的品行,反对吕后立诸吕为王[6]2047;不仅如此,王陵的加入也使得《汉书》列传第九、第十更加完整,通过诸丞相的事迹反映了汉初的政治结构。同样,《史记·张丞相列传》实际上是汉初御史大夫传,后附周昌、赵尧、申屠嘉之传,《汉书》将三位列入题目,不单单是承认他们的历史地位,更是完整地呈现汉初国家机器运作的需要。从这个角度看,班固的调整不能简单地看作“点鬼簿”,即史料的堆砌、人物的罗列,他需要完整地展示西汉初期的政治秩序,国家机器如何通过某一职位上的个人得以运行。
与《史记》相比,《汉书》在编次上亦有一重大调整,那就是作为后妃合传的《外戚传》极其靠后,位列第六十七位,其后只有《元后传》(汉元帝王皇后)和《王莽传》(13)徐冲认为,《汉书》最后三篇的安排,“当反映了班固及其背后的东汉朝廷对于西汉王朝之终结的历史认识”,关于汉代的外戚问题,亦可参考徐书《中古时代的历史书写与皇帝权力起源》单元三“外戚传”与“皇后传”第一章《汉代的“外戚传”与外戚权力》,127-141页。。刘知几在《史通·编次》批评《汉书》“后外戚而先夷狄”,是以后世的史学观念论之,班固的编次反映的是对西汉历史的认识,西汉亡于王莽篡汉,王莽身为孝元王皇后弟子,其权力来源于西汉一朝对外戚地位的认可,“及王莽之兴,由孝元皇后历汉四世为天下母,享国六十余载,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6]4035因此,《元后传》列于《外戚传》与《王莽传》之间,三者皆在汉代诸臣及四夷之后,实际上反映的是西汉政权如何转移到外戚之手,最终导致了王莽篡汉的历史后果,正所谓“明以王莽之势成于元后,史家微意寓焉”。[9]
《元后传》有相当篇幅记录了王氏兄弟子侄政治发迹之事,尽管这与《外戚传》以后妃为主、其家附传的结构类似,然而卫、霍等功业显著的外戚中有专传,西汉中后期的宣帝祖母史氏、母家王氏与哀帝祖母傅氏之外戚,亦有合传《王商史丹傅喜传》。“《外戚传》实以后妃与其亲属同叙,《元后传》亦王氏传也。王氏传本当在《外戚传》中,以其事多而别开之,……《莽传》本应连元后,元后本应在《外戚》,故并《外戚》移后,而抽出元后、王莽别开专篇也。”[8]228
到了《三国志》《后汉书》以降,《皇后传》或《后妃传》的名称代替了《外戚传》,并且列于列传之首(14)《史通·题目》篇云“马迁撰皇后传,而以外戚命章。案外戚凭皇后以得名,犹宗室因天子而显称,若编皇后而曰外戚传,则书天子而曰宗室纪,可乎?”《史通通释》,85页。,实际上亦是继承《史记·外戚世家》的位置(《外戚世家》实际上是西汉世家之首),故而我们不难理解刘知几的批评。有趣的是,后世有人特意改动了《汉书》的安排,《梁书·刘之遴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
时鄱阳王范得班固所上《汉书》真本,献之东宫,皇太子令之遴与张缵、到溉、陆襄等参校异同。之遴具异状十事,其大略曰:“……又今本《外戚》在《西域》后,古本《外戚》次《帝纪》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杂在诸传秩中,古本诸王悉次《外戚》下,在《陈项传》前。”[10]
《梁书》中所提及的“《汉书》古本”,从编次看应该出于后世观念。不仅是《外戚传》的次序,皇子作为同姓诸侯王,其传记一般都按照时代散入诸臣传记之中。正如刘咸炘在《汉书知意·高五王列传》的批评:“史篇次序,本非朝仪,传以释纪,当依时叙。诸王既不别为世家,则与诸臣杂编,固其宜也。萧子显、魏收始聚宗室于首,他家犹不尽从,奈何谓班氏已如萧、魏乎?”[8]198-199“古本”的编者将其依次列于《外戚传》之下,强行按照政治地位而非历史进程重新编次《汉书》,当然不可能如流传至今的版本符合实际的历史进程。有论者指出正史编次中政治地位代替时间顺序的过程:“就二十四史的范围来看,列传编次原则的定型化约在南朝前期。沈约《宋书》的列传大略可见是以时代、政治地位编排,唐初所修五史,列传的政治因素十分鲜明,这种标准在此后也得到延续。沈约《宋书》与唐初五史的另一共同点是,它们形成的漫长过程基本都限定于官修史体系之内,……呈现‘兼顾’的过渡状态的正史(《三国志》《后汉书》与唐修《晋书》的西晋部分),是混合了官修史的编次思路与受《史记》传统影响的私人史家的编次思路所致。因此,这种‘过渡’不是在体条发展线索内的编次思路的逐渐变化,而是两条线索即两种编次思路所形成的文本的影响力此消彼长。”[11]可见,以南朝之后流行于官方史学的意见,来“重构”所谓的“古本《汉书》”,便是用单一而僵化的标准,抹杀了《汉书》本身在多重考虑之下做出的合理安排。
三、结语
无疑,《史记》《汉书》具有不同的撰述目的与历史观念,但作为纪传体史书创体阶段的著作,在以编次来构建文本秩序的过程中,尚有比较大的发挥空间,本文所强调的历史进程和政治理念两个因素,对《史记》《汉书》文本面貌的影响表明了司马迁和班固并没有秉持单一的标准,而是综合各种因素,包括充分考虑时间顺序本身,尽量做出合理的、符合更多标准的选择。在分析《史记》《汉书》编次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发现,实际的历史进程与政治理念之间相互交织,比如西周与西汉开国初年对功臣的封赏,就是在历史进程之中确立本朝的政治秩序,后世史家出于这种秩序的认同而形成特定的政治理念,也正是两者之间一表一里的共同作用,使得中国传统的史学呈现出复杂而生动的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