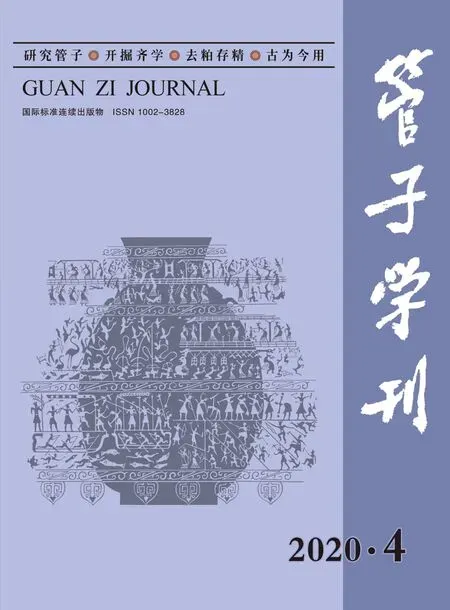《春秋》“夫人何以不称姜氏”笔法新释
——兼议春秋初期齐、鲁之关系
陈豫韬
(南京大学 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春秋时期鲁闵公二年,鲁国陷入了一场巨大的政治内乱。宗室中的公子庆父杀死了当时继位不到两年的君主鲁闵公启。作为这场政治阴谋参与者的鲁国夫人,同时也是鲁闵公名义上的母亲哀姜,在这场内乱后逃往了邾地,而后被自己的母国齐国执拿并杀于夷地,仅以尸体归鲁。此事被记录在《春秋·僖公元年》中,文云:“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正是在这一段文字中,出现了“夫人氏”这一在《春秋》中十分少见的称谓。这种单称“夫人”却不言姓的笔法。在《春秋》中还有过一次,即《春秋·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这件事情发生的前一年是鲁桓公十八年,鲁庄公的母亲文姜与齐襄公私通,鲁庄公的父亲桓公因此事而被齐国公子彭生谋杀。之后或者是不容于鲁国的舆论压力(1)顾炎武著,黄汝成释:《日知录集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83页。,文姜遂逃往齐国。巧合的是,这两次事件都关系到鲁国的君主被杀,两次弑君事件的发生都与鲁国夫人有关,而两位鲁国夫人又同样都来自齐国。那么,这种笔法的改变是否与齐、鲁之间的关系有关呢?在长期以来对于《春秋》的研究里,这个问题一直吸引着学者们的广泛关注,却从未获得过统一的意见。因此,有必要对此事的史实重加梳理,并重新加以讨论。
一、“贬笔”说——《春秋》经学视角下的义理阐释
在漫长的《春秋》研究史中,围绕着《春秋》本身“一字褒贬”与“断烂朝报”性质的争论从未间歇。自孟子提出孔子作《春秋》,以今文学派为代表的一种具有强烈功利性质的“微言大义”《春秋》阐释学体系被建立起来。而在这种具有逻辑一贯性的阐释学体系之下,以《公羊》《谷梁》两传为代表的经说在汉代被立为学官,并确立了其学说在后世的重要地位。针对本文中的变例问题,《公》《谷》二传的解释有着其独特的理论特征。
鲁庄公元年,庄公之母文姜自鲁往齐,《春秋》经文记载此事曰:“三月,夫人逊于齐。”对此,《春秋公羊传》曰:“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2)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224页。而《春秋谷梁传》则曰:“不言氏姓,贬之也。”(3)范宁集解,杨士勋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379页。鲁僖公元年也使用这种逻辑。僖公之母哀姜的尸体自齐返鲁,《春秋》经文记载此事曰:“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而《春秋公羊传》曰:“夫人何以不称姜氏?贬,曷为贬?与弑公也。然则曷为不于弑焉贬?贬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丧至也。”(4)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247页。《春秋谷梁传》则曰:“其不言姜,以其弑二子,贬之也。或曰:‘为齐桓讳杀同姓也。’”(5)范宁集解,杨士勋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谷梁传注疏》,第2391页。
从以上所列《公》《谷》二家对《春秋》这种行文变例的解释可以看出,双方都相对直接地将此归为一种价值判断。两处变例的主角,其中《庄公元年》的夫人文姜是鲁桓公的配偶,《僖公元年》的哀姜是鲁闵公名义上的母亲。《公羊》和《谷梁》都认为她们因涉及弑君事件,而被《春秋》史官去掉姜氏以示贬称。但这种结论虽然有了形式上的统一,其逻辑内核却显得支离而难以自洽。例如在《公羊传·僖公元年》中,由于将不称姜氏作为哀姜弑君的贬笔,但在弑君事件与“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之间却有“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一段没有作贬笔处理的记载,这便出现了矛盾。为此,《公羊》传虽然给出了所谓“贬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丧至也”的说法,但是毫无旁证,过于牵强。为了完成其学派逻辑的自我建构,东汉时期的何休对《公羊》的说法作出了进一步的诠释:“刑人于市,与众弃之。故必于臣子集迎之时贬之。所以明诛得其罪。因正王法所加,臣子不得以夫人礼治其丧也。贬置氏者,杀子差轻于杀夫,别逆顺也。”(6)公羊寿传,何休解诂,徐彦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第2247页。通过何休的解诂,我们可以进一步将《公羊》学派说法的依据归纳为三点:一是称“夫人氏”,是出于对哀姜参与弑君事件的贬笔;二是“贬必于重者,莫重乎其以丧至也”,因为哀姜尸体自齐返鲁之时,鲁国臣子集而迎之,所以这个时候公开贬之,王法得正;三是文姜弑夫,故去氏而贬称为“夫人”,哀姜杀子,罪不及文姜,所以留“氏”以示轻重。后世赞同《公羊》之说者不乏其人,如刘敞、洪咨夔、陈深、高闶、方苞等人皆持此说。但各家虽有发挥,基本也都是沿何休解诂《公羊》的说法加以衍说。
为什么要在“丧至”时作贬笔?《公羊》传的解释又是否成立?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在于看相同的历史语境下其逻辑是否具有一贯性。先以《庄公元年》“夫人孙于齐”为例。文姜虽然没有“丧至”之事,但自其于庄公元年称“夫人孙于齐”以下,至庄公二十二年“葬我小君文姜”而上,指代文姜的“夫人姜氏”这个称谓出现了十二次,这其中既有薨、葬之事,也有文姜屡次前往齐国私通齐襄公的记载。而依照何休解《公羊》的逻辑,在文姜逃往齐国这一时期我们找不出任何时间上的特殊性,在此时将之贬称也无法获得“明诛得其罪”的效果。孔颖达《正义》就曾直斥《公羊》之非:“案礼之成否,在于薨、葬,何以丧至独得为重?丧至已加贬责,于葬不应备文,何故葬我小君,复得成礼?正以薨、葬备礼,知其无所贬责。”(7)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90页。
其次,《春秋》经文没有直接揭示出哀姜在僖公元年的死因,而是记作“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依照三传、《史记·鲁周公世家》及《列女传》的记载,哀姜是被其母国的国君,同时也是身为春秋霸主的齐桓公杀死的。值得怀疑的是,按照《公羊》的逻辑,齐桓公以当世霸主的身份诛杀哀姜,其行为显然具有充分的正义性,既然《春秋》要以褒贬彰显大义,为什么经文此处不写明哀姜的死因呢?正如孔颖达云:“然既讳其杀,不宜有贬。”《谷梁》虽有“为齐桓讳杀同姓”之说,但从春秋大义的角度出发,以齐桓公霸主的身份讨哀姜,实属名正言顺,无需史笔代为之“隐”。正如刘敞在其《春秋权衡》中所说:“夫人挟小君之尊,而杀二子,鲁人终不敢讨也。桓公为伯主,疾祸乱之所生,岂得顾同姓哉?此非春秋所耻也,非春秋所耻,则亦非春秋所讳矣。”(8)刘敞:《春秋权衡》,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9页。将之与《公羊》《谷梁》所举的其他讳例相比,也有明显区别,如《谷梁传·僖公十七年》:“夏,灭项。孰灭之?桓公也。何以不言桓公也?为贤者讳也。”《公羊传·庄公三十年》:“秋七月,齐人降鄣。鄣者何?纪之遗邑也。降之者何?取之也。取之则曷为不言取之?为桓公讳也。”灭人之国,取人之城,在行为上具有非正义性,言为贤者讳,尚可以理解。如果将齐桓公处死哀姜视为正义的行为,又因为是杀同姓而代为之讳,岂不成为显小节而灭大义吗?实际上从鲁国立场出发,《左传》的意见相对较为中允,谓“君子以齐人之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9)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791页。这就是说齐国虽然是哀姜的母家,但女子嫁人则从人,桓公是不应代鲁国杀人的,应责而不应代为之“隐”,鲁史没有为齐桓公“隐”的动机。
最后,倘若经文此处是以“贬”为直接目的,在记载手法上何以要隐去“姜”字而不隐“夫人”,隐去“姜”字可以达到降低其身份地位,彰显其罪恶的效果吗?这同样是不合逻辑的。就如顾奎光《春秋随笔》所说:“以去姜为贬,则有不可通者,贬当先去夫人,不当去姜氏。文姜哀姜俱乱鲁,不绝之于鲁,而绝之于齐,此何意乎。”(10)顾奎光:《春秋随笔》,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8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71页。凡此三点,都是历来持“贬笔”说的立论者无法解释的问题。起码在这个问题上,勉强地运用微言大义理论套用,人为地赋义与建构,与《春秋》经文本身将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因此,研究者需要重新寻找更为合理的解释。
二、阙文说、省文说与文本的再审视
《梦溪笔谈》记载宋绶的一则故事,其谓:“宋宣献博学,喜藏异书,皆手自校雠。常谓校书如扫尘,一面扫,一面生。故有一书,每三、四校,犹有脱谬。”(11)沈括:《梦溪笔谈》,长沙: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91页。经典文本在流传过程中具有不可靠性,像《春秋》这样古老的文献,不可否认其物理载体变化过程中所引起的文本差异,这也是校勘学需要解决的问题。那么同样,将文姜与哀姜的称谓问题视作古书的讹脱自然是最为简单直观的处理办法。最早提出阙文说法的是魏晋时期的杜预。针对《僖公元年》的变例情况,他说:“僖公请而葬之,故告于庙而书丧至也。齐侯既杀哀姜,以其尸归,绝之于鲁。僖公请其丧而还,不称姜,阙文。”(12)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790页。孔颖达的《正义》亦持此说。这种意见在对《公》《谷》之“贬笔说”纠正的同时,也解释了为何“夫人氏”的说法独阙一“姜”字的问题。以“阙文”说立论,确实可以避免许多出于笔法考虑而产生的问题,是以后世从此说者亦不在少数,如黄仲炎《春秋通说》、赵鹏飞《春秋经筌》、程端学《春秋本义》、王介之《春秋四传质》等。当然,各家为自证其说,论证角度也不相同。如湛若水《春秋正传》:“《礼》曰:‘为伋也妻,则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则不为白也母。’今哀姜虽身犯大恶,而庄公生时未出之也,是犹为鲁君母也,义当从人,则齐人当归之,鲁侯当受之,葬以小君之礼也,盖名分未绝,则义亦未绝也。”(13)湛若水:《春秋正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9页。这是尝试以礼为出发点解释鲁僖公行为的正当性,并引《礼记》为其说立据。以“不丧出母”的规范来看,哀姜当时并未被出,母子名分未绝。那么鲁史就不会擅作加工,应当衷实地书上“夫人姜氏”才符合礼节。王樵《春秋辑传》则认为鲁国“今乃请而还之于鲁,以小君之礼,大义灭矣。春秋详书之,所以深著鲁君臣之罪也。”认为鲁国史官在此处应该是写有“姜”字,以此来昭示鲁君臣之罪。其立论点虽然与湛说相反,但结论却又相同,都以有“姜”字为当。
由于杜预所提出的“阙文”说缺乏必要的证据,是以后世虽不乏为其辩护者,但质疑和反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刘敞《春秋权衡》曰:“春秋之义,以一字为褒贬,苟所不通者,则谓之阙文,春秋何文不阙也。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亦阙文邪?”(14)刘敞:《春秋权衡》,第204页。廖平《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证》云:“不称姜,绝之。不称姜氏既为例,则不称姜亦例矣,岂可以为阙文?”(15)廖平:《春秋左传杜氏集解辨证》,《续修四库全书》第12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78页。从校勘学的原则上来说,虽然阙文不似衍文需要以讹误痕迹为据,但仍需要遵守一定的原则。文姜、哀姜的文法变例都是春秋笔法诸家争论之处,且两处脱文都处于同一个位置上,恰好脱去了“姜”字。那么杜氏直接以阙文说以解《僖公元年》的变例,就会显得非常草率。奇怪的是,在面对《庄公元年》文姜“夫人孙于齐”的变例时,杜预却采取了与哀姜完全相反的处理方式,其谓:“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姜氏齐姓,于文姜之义,宜与齐绝而复奔齐,故于其奔去姜氏以示义。”(16)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762页。可以看出,对于两个相同的变例提出不同的解释,杜预的诠释未能获得逻辑上的统一。对于《春秋》经文将文姜记作“夫人”,杜预认为这是史官的一种处理方式,即文姜作为鲁国夫人,在齐国杀死鲁国国君时应与齐国撇清干系;而当《春秋》将哀姜记作“夫人氏”时,杜预则认为是阙文,而且没有说明“夫人”与“夫人氏”的区别,这使人怀疑杜预说法的正确性。后人如湛若水等为之解说,亦不可视为的论。若依湛说,文姜当时也没有被出,难道“夫人孙于齐”也是“夫人姜氏孙于齐”的阙文吗?为什么相隔甚远的两处文本如此巧合,偏偏都在同一处位置脱落文字?王樵之说亦臆解太甚,试想鲁国的史官不去贬责参与弑君的哀姜,反而去贬责请还小君尸体的鲁国君臣,这难道不是彰小疵而隐大恶吗?史官何不于前写明齐桓以大义杀哀姜呢?这样不就更能起到显明桓公大义且深罪鲁君臣的用意吗?
出于对杜预说法的修正,又有学者提出了“省文”的说法。如陆淳《春秋集传微旨》云:“不言姜,犹一事再见卒名也。”(17)陆淳:《春秋集传微旨》,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6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59页。又如吕大圭《春秋或问》云:“或者例以为阙文。然以鄙意思之,若以是为阙文,则春秋之可以阙文言者固多矣。奚独此哉?窃意此年‘夫人孙于齐’不书姜氏者,盖前年书‘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则今年孙于齐者,即如齐之姜氏也。僖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盖前年书‘夫人姜氏薨于夷’,则其所谓夫人氏之丧至者,即薨于夷之姜氏也。此盖蒙上文而书之。若夫‘夫人孙于邾’,则上无所见,故不得不以姜氏称也。”(18)吕大圭:《春秋或问》,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7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540页。吕大圭认为庄公元年“夫人孙于齐”乃是前接桓公十八年之“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僖公元年“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乃是前接本年“夫人姜氏薨于夷”。按照这种逻辑结合《春秋》前后经文来看,省文的地方应该不在少数。但以文姜称谓为例,庄公四年有“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齐侯于祝丘”,庄公五年有“夏,夫人姜氏如齐师”。庄公七年,“夫人姜氏会齐侯于防”,“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谷”,先后相接,《春秋》何故不省文?是故方苞《春秋直解》云:“赵氏(19)赵汸:《春秋师说》,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4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66页。谓文姜孙齐,不称姜氏,哀姜丧归,不称姜,皆承前文而联为一事,非也。宋华元出奔,宋华元自归于宋中无间事,犹再书宋华元,安有阅月踰时而去姓氏,以联为一事者哉。”可见省文说在逻辑上完全不能自圆其说,不足取信。
清代皮锡瑞《春秋浅说》云:“考襄二十六年传,对曰,君夫人氏也。则夫人氏当时本有此称,不得谓不得去姜存氏也。其去姜字,当如贾侍中说,文姜杀夫重,故贬去姜氏,哀姜杀子轻,故但贬去姜。杜以爲阙文非是。”皮锡瑞这里乃是出于反对杜氏的“阙文”说而提出的观点,虽然他也赞同贾逵注关于为何文姜逊齐称“夫人”,哀姜丧至则称“夫人氏”而提出的弑父、弑子有别说,但其关于“氏”字的存否问题又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证据,即“夫人氏”是当时的既有称谓。近人杨伯峻先生亦持相似看法,其《春秋左传注》云:“杜注以为‘氏’字上应有‘姜’字,不称‘姜’为阙文。但‘夫人氏’、犹隐公三年之‘君氏’、《诗·邶风·凯风》之‘母氏’,并非阙文。”(20)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277页。但这种说法的证据力仍显不足。从杨伯峻先生所选例证看,隐公三年有鲁隐公的母亲声子称为“君氏”,但《左传》另有阐释:“不称夫人,故不言葬,不书姓。为公故,曰‘君氏’。”可见,因为声子并不是鲁惠公夫人,所以此处既不书“夫人”,也不书其父家的姓氏。而襄公二十六年传的“君夫人氏”弃,我们可以根据《左传·襄公二十六年》的记载来判断这里称谓是否具有特殊性,其文云:“初,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弃诸堤下,共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弃。长而美。平公入夕,共姬与之食。公见弃也,而视之,尤。姬纳诸御……”夫人既然被宋芮司徒遗弃而名为“弃”,那么也就意味着这位弃夫人没有父家,自然不具备使用芮司徒姓氏的权力。不书姓氏是因为无姓氏可书,这显然也是一处特殊的个例,远不足以将“君夫人氏”视为春秋时期的通用称呼,更不足以解释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故而仍需要更为合理的解释。
三、还《春秋》以《春秋》——由史笔看春秋前期齐、鲁关系
相对于《公羊传》与《谷梁传》的史官贬笔说法,另一部《春秋》三传的《左传》并没有对庄公元年与僖公元年的两处称谓变例进行一体诠释,但在庄公元年的解经语中明确地提出了一个“绝不为亲”的说法,即《左传·庄公元年》:“三月,夫人孙于齐。不称姜氏,绝不为亲,礼也。”《左传》的这个说法,在后世主要有两种解释:
第一种认为“绝不为亲”说的是文姜与齐国断绝关系。如《正义》云:“言于夫人之义,宜与齐绝,不复为亲也。姜氏者,齐之姓也。《礼》:‘妇人在家则天父,出嫁则天夫。为夫斩衰三年,为兄大功九月’。今兄杀已夫,于文姜之义宜与齐绝,姜意不与齐绝而复奔之,故于其奔也特去姜氏。”(21)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762页。苏辙《春秋集解》云:“齐人杀哀姜,而以其尸归,绝之于鲁。僖公请而葬之,不称姜氏,何也?文姜之孙也,不称姜氏,以为义当绝齐也。哀姜之死,齐既自绝之矣,是以不称姜也。”(22)苏辙:《春秋集解》,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8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3页。但将这种说法套用在《僖公元年》时,由于哀姜是与庆父合谋杀死了鲁闵公而自己被齐桓公杀死,便会变得同苏辙的说法一样形成两种逻辑。
第二种看法认为“绝不为亲”是鲁庄公与文姜断绝母子关系。如陈傅良《春秋后传》:“此文姜也,曷不称姜氏?绝之也。吾君父不良,死于齐。而文姜犹孙于齐,庄公不可以言人子矣。绝文姜,所以恶庄也。”(23)陈傅良:《春秋后传》,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51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617页。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绝不为亲者,以文姜有杀夫之罪,庄公宜恸父之被杀而绝母子之亲,《说苑》所谓‘绝文姜之厉,而不为不爱其母。’”(24)杨伯峻:《春秋左传注》,第157页。那么以这种说法,问题就变成了鲁国自己内部的矛盾,但如果说鲁庄公与文姜断绝母子关系,为什么经文要削去其父家的“姜氏”,而不削去代表鲁国身份地位的“夫人”呢?换之《僖公元年》则理亦同。对两处变例的解释仍然无法形成统一的逻辑。
或是受到《左传·庄公元年》说法的影响,后世有的学者也用这种“绝亲”理论来解释《僖公元年》的变例,认为《左传·僖公元年》之“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乃是齐国绝断和哀姜的亲属关系,收回其“姜氏”的使用权。如黄正宪《春秋翼附》:“去其姜者,齐恶而削之也。齐曰夫人氏,则鲁使亦曰夫人氏。史官亦书曰夫人氏。圣人仍旧史之文耳,不然夫人尊号且存之也。而独去一姜字谓之何哉。”(25)黄正宪:《春秋翼附》,《续修四库全书》第135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38页。姜宝《春秋事义全考》:“不称姜,盖齐绝之不许氏其姓尔。”(26)姜宝:《春秋事义全考》,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69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79页。但这种说法于《庄公元年》又全不可通,因为文姜逃往齐国时,在位的是与之私通的其兄齐襄公,齐国不可能断绝与文姜的亲属关系,彼处的“绝不为亲”说的是文姜应与齐国绝亲。如果依照上述解释,同样会造成《庄公元年》与《僖公元年》两处变例无法形成统一的逻辑。那么“绝不为亲”之说如何同时适用于两处变例,可先从比较文姜称“夫人”、哀姜称“夫人氏”这两个称谓变例的文本本身及其背后具体的历史背景谈起。
在文姜称谓发生变例之前,经文记载:“(桓公)十有八年春王正月,公会齐侯于泺。公与夫人姜氏遂如齐。”(27)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759页。而后才有《庄公元年》的“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孙于齐”(28)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762页。。哀姜的情况同样与之类似,其变例出现前的经文是“秋八月辛丑,公薨。九月,夫人姜氏孙于邾”(29)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787页。。在此之后的《僖公元年》:“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丧至自齐。 ”(30)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790页。
通过上文的比较首先可以注意到,两处称谓变例的相同点在于句中都存在一个“齐”字。而进一步整理这种称谓变化与二人所涉及到的弑君事件的关系又可以发现,文姜称“夫人”在庄公元年,前一年即桓公十八年春,桓公携哀姜入齐。同年夏,其夫桓公为齐襄公使彭生所杀。于是庄公元年三月记载“夫人孙于齐”。从桓公被杀到此,文姜确实是首次出现。而哀姜称“夫人氏”在僖公元年,前一年即闵公二年秋八月,闵公为庆父使卜齮所杀。此后,经文中哀姜首次出现在同年九月,经文称“夫人姜氏孙于邾”,第二次出现在僖公元年七月,经文称“夫人姜氏薨于夷”,第三次出现在僖公元年十二月,至此经文才称“夫人氏之丧至自齐”。也就是说,其称谓变化与哀姜所参与的弑君事件的联系其实并不紧密。其实,两处变例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变例出现之前,齐国都对鲁国的国家利益有所侵犯;而两处句中同时出现的“齐”字,则是这种变例出现的直接原因。而所谓的“绝不为亲”,其实是鲁国要表明绝齐亲的态度。细究这两处称谓变化背后的历史原因,分别是因为齐国杀死了鲁桓公与哀姜,这对鲁国的国家利益、国际声誉是一种极大的侵犯与损害。所以《左传·僖公元年》云:“夫人氏之丧至自齐。君子以齐人杀哀姜也为已甚矣,女子,从人者也。”可以发现,此处传文虽然没有像《庄公元年》那样对“夫人氏”进行直接的解释,但却同样表明了鲁国对齐国的谴责态度,即哀姜虽然有罪,但是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哀姜身为鲁国的国君原配夫人,齐国不应该擅自杀掉哀姜,其态度与《左传·庄公元年》是统一的。是以针对哀姜的称谓,同样不应当是齐国绝哀姜之亲,而是鲁国绝齐国之亲。以往的学者往往无法厘清这其中的具体关系,如孔颖达的《正义》虽然在《庄公元年》赞同“绝不为亲”是鲁国史官在撇清文姜与齐国的关系,但出于“疏不破注”的局限,在《僖公元年》却没有采用这种说法,而是赞同了杜预的阙文说。同样,苏辙在面对《僖公元年》哀姜的称谓问题时,又认为是齐国绝断和哀姜的亲属关系,与他在解释《庄公元年》文姜变例的说法截然不同。相同笔法作两种解释,不仅使得问题复杂化,逻辑上也难以使人信服。
我们已经得出结论:鲁国史官的笔法是为了断绝与齐国的亲属关系,以表示对齐国公然侵犯鲁国利益的抗议。那么剩下的问题只有两个,第一是《僖公元年》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齐人以归”句有“齐”字而不去“姜”字的问题,这个问题其实通过《春秋》的记载可以发现,“薨、葬”的格式属于行文的定例,自隐二年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至昭十一年五月甲申夫人归氏薨,《春秋》经文在记载小君“薨”时,对于其“夫人某氏”之称始终不变,于葬时称“葬我小君某某”亦不变。正如苏辙所言“薨葬尽礼,虽欲去之而不可得。”第二是两处变例,为什么文姜称“夫人”,而哀姜称“夫人氏”,是不是如贾逵所云“杀子轻,故但贬姜”呢?其实并非如此。贾逵论点成立的依据是鲁国史官的史笔,而其史笔所针对的主要目标在于文姜与哀姜,这与我们认识的针对齐国的结论并不一致。产生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夫人”或“夫人氏”都不是当时标准的称谓方式,加之从庄公元年到僖公元年的这两处记载时间相差三十余年,所负责的史官在行文习惯上有所差异,故而一为“夫人”,一为“夫人氏”。正如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隐公四年》云:“推寻经文,自庄公以上,诸弑君者皆不书氏,闵公以下皆书氏。亦足明时史之异同,非仲尼所皆刊也(31)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第1725页。。虽然这并非完全相同的例子,但也可以看出,庄公时期与僖公时期的记载存在一定差异,这确实是《春秋》中存在的现象。本题两处异文的重点仍然在于“去姜”而不在于“存氏”。
春秋早期,随着齐、鲁两国力量悬殊日益增大,两国的关系也面临着重大转折。鲁隐公十一年,鲁国公子翚弑君而立鲁桓公,或许是出于得位不正的考量,鲁桓公继位后三年选择与齐国联姻。在此之后的过程中,历史的天平越发朝着齐国一方倾斜。鲁国的历代国君,包括庄公、僖公、文公、宣公、成公等都娶了齐国的女性作为自己的国君夫人。而反观齐国,则没有迎娶鲁国夫人的情况,由这种联姻关系就能够看出两国之间的不对等关系。又通过上文的考证,我们可以将本文所讨论的两种称谓的变例与当时齐、鲁之间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鲁桓公的死,表面上看是因为文姜与齐襄公的通奸,但由齐、鲁此时的关系来看,这次偶然事件却像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政治谋杀。虽然齐、鲁两国在齐襄公时期存在联姻,但是两国在对待纪国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的矛盾。齐国试图吞并纪国的企图由来已久,而鲁国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则不愿意齐国将纪国吞并。以至于在桓公十三年,由鲁国、纪国、郑国的三国联军打败了齐国、宋国、卫国、燕国所组成的四国联军。次年,齐襄公继位。桓公十七年春,鲁国、齐国、纪国会盟于黄,鲁桓公试图调解齐、纪之间的矛盾不成,于是夏天鲁国与齐国又在奚地交战。十八年,鲁桓公携同夫人文姜到齐国去与之修好,随即遭到齐国的杀害。因此,不能将这一事件简单地解读为充满道德隐喻的修辞。而哀姜的死,同样也是齐国出于国家利益考量作出的决定。本来鲁庄公死后,继位的公子般的母亲是鲁国大夫党氏的孟任,假如公子般继位成功,那么齐国对于鲁国的政治影响将会被削弱。而恰巧鲁国公子庆父作乱杀掉公子般后选择逃往了齐国,回国之后又立了齐叔姜的儿子鲁闵公,这背后很难说没有齐国的暗中控制与授意。第二次作乱杀死持亲齐立场的闵公时,庆父逃往莒国,哀姜逃往邾国,也显然因为两人的阴谋侵犯了齐国的利益不敢再次前往齐国寻求庇护,之后齐桓公将哀姜杀死也即为此。虽然鲁国在春秋前期尚属较有实力的国家,但在与齐国的来往中却仍然处于下风。通过这两处称谓变例,可以看出虽然鲁国受限于实力看似毫不作为,但其中却隐藏着鲁国在其国家舆论与外交层面对齐国所持的激烈的谴责态度,也反映出当时齐国对鲁国的政治压迫与鲁国的现实窘境。这便于我们更为深入地了解当时齐、鲁之间的政治、外交等局势。
还需要认识到的是,对于历史材料的解读需要从编撰者的立场出发,也需要其具体的历史背景作为支撑。在此我们可以借用李剑鸣教授的“语境主义史学”的概念,即对于过去的人与事不可随意解释,不能用今人所掌握的知识、信息和价值观念来评价过去人的行为和想法,而必须把它们置于具体的“语境”中,并尽可能地从当事人的角度出发考察,非如此不足以了解其本来的面目和意义(32)李剑鸣:《历史语境、史学语境与史料的解读——以弗吉尼亚州批准美国宪法大会中一条材料的解读为例》,《史学集刊》2007年第5期。。借用清人章学诚的观点:“是则不知古人之世,不可妄论古人文辞也。知其世矣,不知古人之身处,亦不可遽论其文也。”(33)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8页。明白了这一点,就能够对《春秋》此处鲁国史官的义例获得更深层次的认识与结论。在这种认识下,不论是持“贬笔”说还是“阙文”“省文”说的研究者,其问题都在于只注意到了主体意识与主体语言同文本之间的关系,而没有注意到它们与客观历史的关系。任何熟悉海登·怀特《元历史》理论的研究者都会注意到,由于事件与故事之间存在着不同维度的差异性,试图使一种价值判断或逻辑规律贯穿于事件始终的尝试都会受到这样或那样的限制与约束。当然我们也应当承认,既不能将历史编纂视作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也不能在历史编纂的研究中完全借鉴哲学“语言学转向”的概念。这就意味着,在区分历史真实与史学家主观的问题时,我们往往需要借鉴二元甚至多元的诠释方法,以求在当代视角下的文本解构能够向着历史事件与历史真实本身进行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