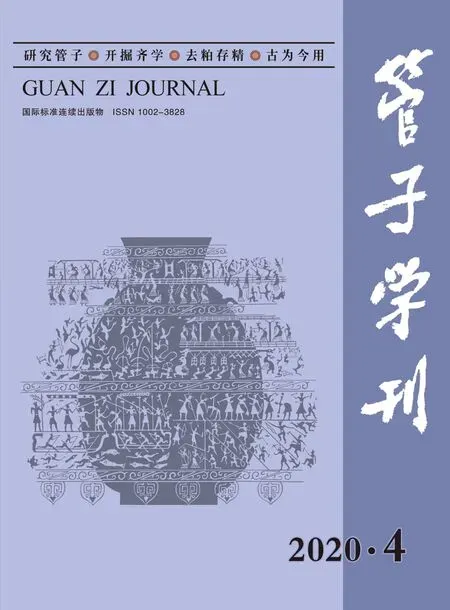论管仲形象的政治伦理意义
——以朱子《论语集注》中对管仲的评价为中心
游 森
(同济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092)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说:“宋贤不善读之,乃鄙薄事功,攻击管仲。……专重内而失外,而令人诮儒术之迂也。岂知孔子之道,内外本末并举,而无所偏遗哉!”(1)康有为:《论语注》,《康有为全集》第六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92页。那么宋儒是否如康氏所指责的“鄙薄事功”“攻击管仲”“专重内而失外”呢?本文以朱子为例探寻其对孔子的管仲评价的解读,说明其中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意义,以期澄清所谓“鄙薄事功”“攻击管仲”“专内失外”等误解。
《论语》上记载孔子与学生间议论管仲的话语有4条,于《论语》中所占比重不可谓小,足见孔子对管仲的重视,分别为《论语·八佾》第22章、《论语·宪问》第9章、第16章、第17章。在此4条中,孔子对管仲有褒有贬。贬其不知礼等行径,褒其相桓公一匡天下、存续华夏文明的功绩。朱子就《论语》关于管仲诸条的注解梗概分别如下:
器小,言其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局量褊浅、规模卑狭,不能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愚谓孔子讥管仲之器小,其旨深矣。或人不知而疑其俭,故斥其奢以明其非俭。或又疑其知礼,故又斥其僭,以明其不知礼。盖虽不复明言小器之所以然,而其所以小者,于此亦可见矣。故程子曰:“奢而犯礼,其器之小可知。盖器大,则自知礼而无此失矣。”此言当深味也。苏氏曰:“自修身正家以及于国,则其本深,其及者远,是谓大器。扬雄所谓‘大器犹规矩准绳’,先自治而后治人者是也。管仲三归反坫,桓公内嬖六人,而霸天下,其本固已浅矣。管仲死,桓公薨,天下不复宗齐。”杨氏曰:“夫子大管仲之功而小其器。盖非王佐之才,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其器不足称也。道学不明,而王霸之略混为一途。故闻管仲之器小,则疑其为俭,以不俭告之,则又疑其知礼。盖世方以诡遇为功,而不知为之范,则不悟其小宜矣。”(2)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67-68页。
盖桓公夺伯氏之邑以与管仲,伯氏自知己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穷约以终身而无怨言。(3)《四书章句集注》,第152页。
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4)《四书章句集注》,第154页。
程子曰:“桓公,兄也。子纠,弟也。仲私于所事,辅之以争国,非义也。桓公杀之虽过,而纠之死实当。仲始与之同谋,遂与之同死,可也;知辅之争为不义,将自免以图后功亦可也。故圣人不责其死而称其功。若使桓弟而纠兄,管仲所辅者正,桓夺其国而杀之,则管仲之与桓,不可同世之仇也。若计其后功而与其事桓,圣人之言,无乃害义之甚,启万世反复不忠之乱乎?如唐之王圭魏征,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可谓害于义矣。后虽有功,何足赎哉?”愚谓管仲有功而无罪,故圣人独称其功;王魏先有罪而后有功,则不以相掩可也。(5)《四书章句集注》,第154-155页。
根据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朱子观点及其解释特点:
第一,朱子置管仲的人品、事功于《大学》的义理脉络里,进而呈现出管仲形象缺失“正身修德”的一环,致使他无法“致主于王道”。质言之,“器小”表面上是指管仲奢侈、犯礼诸方面,实质上体现的是他不知大学之道。第二,承认管仲的仁功,但否认其为仁人。第三,沿袭程子以齐桓为兄、子纠为弟,以兄当国合法的说法,从而认为管仲改事桓公无罪。
下面笔者将分别围绕这三点展开本文内容,以见朱子以上观点的政治伦理意义。
一、大学之道与王霸之辨——朱子对孔子的管仲评价的解读
对“器小”的看法,皇侃《论语义疏》引孙绰云:“功有余而德不足,以道观之,德不曰小乎?”(6)皇侃:《论语义疏》卷二,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73页。是就功德两个角度对管仲进行评价,事功方面管仲之成就绰绰有余,然而德行则不称其功。这一评价体现功德一致的评价标准。由“器小”的注解可以看出,尽管也是承袭对管仲德行不足的批评,但不同处在于朱子的话语里有《大学》义理作为参照系统。概言之,朱子此时是以“大学之道”衡定人物。在朱子的话语中有个关键的内容——“致主于王道”,换言之,管仲未能引导桓公当于王道,朱子把原因归结为管仲自身“不能正身修德”。因此可以看到,朱子实际已将管仲置于“大学之道”中,依据大学的义理对管仲进行审视和评价。朱子视“大学之道”为致治之法,作为臣的管仲本当依循“大学之道”正身修德,以辅佐作为君的齐桓公实现王道;然由于管仲不知“大学之道”,以至“局量褊浅、规模卑狭”,最后“虽能合诸侯、正天下”,却因“其器不足称也”仍然不足以当仁。
与朱子从《大学》语境来看待管仲不同,《论语义疏》引李充云:“齐桓隆霸王之业,管仲成一匡之功,免生民于左衽,岂小也哉?然苟非大才者,则有偏失。好内极奢,桓公之病也。管生方恢仁大勋,弘振风义,遗近节于当年,期远济乎千载,宁谤分以要治,不洁己以求名,所谓君子行道忘其身者也。漏细行而全令图,唯大德乃堪之。季末奢淫,愆违礼则。圣人明经常之训,塞奢侈之源,故不得不贬以为小也。”(7)《论语义疏》卷二,第76页。李氏认为管仲的行为是在为君分谤。联系《论语·述而篇》第29章,陈司败向孔子询问昭公娶同姓是否知礼的问题,当时孔子则回答为“知礼”的情形,反映出孔子为先君昭公隐讳。据此看,李氏认为管仲奢侈、犯礼构成以分谤方式为齐桓公隐讳嫌疑也是合理的,也能解释通。
但是这一解释方案无法协调孔子本人对管仲所下“不知礼”的断语。无论管仲是由于不知礼而犯礼,还是出于为君分谤的动机故意为之,管仲无礼为既成事实。孔子分明说管仲不知礼,那么无论其动机如何,就孔子给管仲的定性来看,朱子的解释应该说更为符合孔子的意思。
在朱子看来,管仲的器小乃是由于其不知“大学之道”,进而仅致主于霸道,未能更进于王道,由此说明王霸可以依循“大学之道”来作为区判标准。我们可以借助朱子和陈亮的王霸之辨的讨论,进一步了解朱子的这一理路。陈龙川正式与朱子展开王霸之辨始于《甲辰秋书》,此书作于淳熙十一年。这年陈龙川出狱,朱子致信慰问劝说其“以醇儒之道自律”,放弃“义利双行、王霸并用”的主张(8)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二),《朱子全书》第2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581页。,故陈龙川作此书为自己辩护。陈龙川认为,“义与利不是截然对立的,三代之君是王霸并用,汉唐的皇帝也并非只用霸道而不用王道。”(9)耿振东《〈管子〉学史》,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284页。汉唐绝非全是人欲,其本领极大,若是没有兼具仁智勇,绝不可能担负起天下之责。
朱子的回复,主要表现在严格区分心术根源于“天理”还是“人欲”,以分判王霸方面。朱子指出“不必求之于古今王霸之迹”,只需要“反之于吾心义利邪正之间”,通过“察其心”来识别汉高、唐宗“果出于义耶,出于利耶?出于邪耶,出于正耶”?在朱子看来,汉高、唐宗“直以其能假仁借义以行其私”,而当时与其争天下者,“才能智术既出其下,又无仁义之可借,是以彼善于此而得以成其功耳”。汉高、唐宗的成功仍然奠立在仁义之上,哪怕其所作所为假仁义之名。但就亘古今、常在不灭的道,朱子质问:“汉唐所谓贤君,何尝有一分气力扶助得他耶?”(1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二),《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2-1583页。
陈龙川在后来的前后两封《乙巳春书》以及一封《乙巳秋书》中,谈到“心之用有不尽而无常泯、法之文有不备而无常废”(11)陈亮:《陈亮集》,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45页。,认为“惟王为能尽伦,自余于伦有不尽,而非尽欺人以为伦也。惟王为能尽制,自余于制有不尽,而非尽罔世以为制也”(12)《陈亮集》,第345页。。在他看来,“三代做得尽者也,汉、唐做不到尽者也”(13)《陈亮集》,第348页。而已。汉唐虽然杂霸,但是“杂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14)《陈亮集》,第340页。。由此可见,陈龙川认为霸道实质上根据于王道,或者说霸道是王道的部分开展。但是朱子认为汉唐所作所为只是“暗合”于道,根本上“所以为之田地根本者,则固未免乎利欲之私也”(15)《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二),《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87页。,他们心术的真相仍然是人欲。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朱子和陈龙川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并不一样,两人所用原则分别基于各自对“王道”的理解。尽管陈龙川讲王霸杂用,但是他所谓的霸道其实乃是王道的部分开展,从本质而言,王霸并没有不同。所以他说:“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岂其于本质之外换出一般以为绝世之美器哉。”(16)《陈亮集》,第346页。在他而言,王霸不是分别由天理、人欲这组对立的概念决定的,事迹本身与心迹具有内在的相关性。如果说霸道驳杂,但是以其事迹而言,其中定含“真心”,关联着王道。朱子则一定要深究心迹是否纯粹符合天理,将被评价的人物置于《大学》义理参照中。从心迹而言,看其心是否无人欲;从事迹而言,是否由义理心导源出来。朱子认为王道与霸道根本不是一回事,他提出“察其心”的方针,其实既已按《大学》的视线进入政治伦理生活,其意义绝非是要停留在历史中,“若夫点铁成金之譬,施之有教无类,迁善改过之事则可;至于古人已往之迹,则其为金为铁固有定形,而非后人口舌议论所能改易久矣。今乃欲追点功利之铁以成道义之金,不惟费却闲心力,无补于既往;正恐碍却正知见,有害于方来也”(17)《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二),《朱子全书》第21册,第1591页。。可见对当代的关注才是朱子的重心。如果承认了陈龙川的王霸逻辑,那么势必会造成对现实政治伦理生活的侵害。最后会演变为追求事功时,只看结果。如此心术势必被导向外在性的维度,以功利逻辑建构人的行为。对朱子而言,王道根于天理,而天理发生于无人欲之心。朱子是以内在性管摄外在性,用天理来确保事功的发生。
但是正如在评价管仲时,承认他的仁功,却否认其为仁人一样,尽管可以不认可霸道,但是始终无法否认它在事功层面有缔造仁功的可能,如管仲以霸道辅佐桓公,而行尊王攘夷之道,最后孔子也不得不称许他有仁功。陈龙川即是抓住这点,认为仁之功用与心相应,其区判应当以事迹为依据。单就这点来看,朱子对管仲的评价也必须依据管仲生平事迹,从此便不难看出陈龙川和朱子仍然存在共同点,他们都需要把握史事。然而依据史事,儒者对管仲的评价却分歧更甚。
二、有罪还是无罪?——经学、史证、理学间的管仲
(一)“三归”
检诸朱子《集注》之前的文献,除《说苑》认为“三归”为台名以外,绝大多数文献认为“三归”与三娶相关。如《公羊传》:“三国来媵,非礼也。”(《春秋公羊传·成公》)《左传》成公八年《经》,杜注:“古者诸侯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国,国三人,凡九女,所以广继嗣也。”(18)李梦生整理:《春秋左传集解》上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353页。是诸侯娶三同姓之国为礼。照这样理解,娶三姓的下大夫管仲实属僭礼。毛奇龄从文献考证的角度,否定了朱子释“三归”为台名的说法。他在《论语稽求》中说道:“旧注引包咸说,谓三归是娶三姓女,妇人谓嫁为归。诸儒说皆如此。朱注独谓三归是台名,引刘向《说苑》为据。则遍考诸书,并无管仲筑台之事。即诸书所引仲事,亦并无有以三归为台名之说,刘向误引。”(19)毛奇龄:《论语稽求篇》,《毛奇龄全集》第14册,北京:学苑出版社,2015年版,第208-209页。通过否定刘向《说苑》三台的说法,从而使朱子的解释失去合法的文献根据。另外,《群经平议》:“就妇人言之谓之归,自管仲言之当谓之娶,乃诸书多言三归,无言三娶者。……朱注据《说苑》‘管仲筑三归之台以自伤于民’,故以三归为台名。然管仲筑台之事不见于他书。《战国策·周策》:‘宋君夺民时以为台,而民非之,无忠臣掩盖之也。子罕释相为司空,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齐桓公宫中七市,女闾七百,国人非之。管仲故为三归之家以掩桓公,非自伤于民也。’《说苑》所谓‘自伤于民’者疑即本此。涉上文子罕事而误为筑台耳。古事若此者往往有之,未足据也。然则三归当作何解?”该书据《韩非子·外储说》所载管仲有三处家第而释“三归”,认为“是所谓归者,即以管仲言,谓管仲自朝而归,自家有三处也”(20)俞樾:《群经平议》,《春在堂全书》第1册,南京: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489页。。程树德在《论语集释》当中认为“此以三归为家有三处,较旧注、朱注义均长,似可从”(21)程树德:《论语集释》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第273页。。
针对“三归”取“三台”的说法,朱子有自己的考量:
或问三归,曰:“《说苑》谓‘管仲筑三归之台’,而韩非亦曰‘桓公使管仲有三归之家’是其证也。”曰:“旧说妇人谓嫁曰归,三归云者一娶三姓,而备九女,如诸侯之制也。且虽台名,安知不以处是人而名之乎?”曰:“若此则为僭上失礼,与塞门反坫同科矣。今夫子但以为不俭,则亦但为极台观之,侈而未至于僭。”(22)朱熹:《四书或问》,《朱子全书》第6册,第671-672页。
可以看出朱子在给出“台名”的解释之前,已经考虑到前人娶三姓的说法,然而由于孔子的话语之中,并没有指责管仲僭越礼制,只是提到其不俭约,最多认为他因“不知礼”而犯礼。从动机而言,刻意僭越礼制,本质构成对君权的挑衅,如果是这样的话,孔子定不会仅仅说管仲“不知礼”。如孔子对季氏僭礼的批评便相当严厉:“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由此再比较对于管仲的评价,便可以推知,孔子很可能只是认为管仲奢侈、不知礼。那么如果依据这个看法的话,“三归”无论解释为“台名”还是“家有三归”,其实都只是关系奢侈而不牵涉僭越礼制方面。
钱穆先生在《论语新解》里认为:“三归谓其有三处府第可归,连下文官事不摄,最为可从。”(23)钱穆:《论语新解》,《钱宾四先生全集》第3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版,第105页。也是同意释“三归”为三处家第。程树德《论语集释》还引了其他几个说法:1.三归为三牲。2.三归为藏货财之所。3.三归为地名。三种说法都有文献依据,此处不一一列举。
上面不同的考证结果,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奢侈但并不僭越礼制型;第二种僭越礼制背离臣道型。在每种类型下所展现的管仲形象是绝不相同的,其意义也是差别巨大。前者使管仲以“不知礼”的奢侈形象示人,后者则使其成为了专权的僭越者。朱子的“台名”观点属于第一种,也意味着朱子对管仲的看法,毫无疑问但以“不知礼”看待他的。
(二)桓公与子纠的关系
关于桓公与子纠谁才有继承权,我们先看看《公羊传》的说法:“其称子纠何?贵也。其贵奈何?宜为君者也。”(《春秋公羊传·庄公》)《谷梁传》也如此认为,其言“言子纠者,明其贵,宜为君”(《春秋谷梁传·庄公》)。然而考诸三传文本,其实并没有明确指出桓公与子纠是哪种亲属关系,谁是兄谁是弟,甚至说两人到底是不是兄弟,都没有明确交代过。《公羊》《谷梁》是明言认为子纠拥有合法的继承权。相比之下,《左传》其实并没有讨论合法性的问题,唯独杜预在注的时候以子纠为桓公庶兄(24)《春秋左传集解》上册,第77页。,而这一点并不足以说明谁更有继承权。
元儒程端学《春秋或问》有云:
或问曰:“公伐齐纳子纠,齐小白入于齐。先儒或以子纠为兄,或以小白为兄,何也?”曰:“各有其说,而未可以片言决也。谓子纠为兄者,《公》《谷》之意,而孙氏、胡氏、刘氏邦衡莘老、东莱诸儒宗之;谓小白为兄者,程子之说,而康侯、朱子、张氏诸儒宗之。然各无明文可考。孙氏诸儒谓子纠为兄者,以《春秋》书法有‘子’字故也,据经论理者也。然朱子则谓《公》《谷》之经无‘子’字而小白为兄。程子意不特以《公》《谷》无‘子’字,亦以《论语》孔子许管仲之仁之事,信之也。但程子于管仲之事以大义推之,而知其为兄耳,非有所据也。今以《春秋》所书‘齐小白入于齐,与齐人取子纠杀之’之文观之,则子纠为兄之说似有理。盖齐小白入于齐有篡位之辞。齐人取子纠杀之,三传同有‘子’字,固不可以《公》《谷》前无‘子’字为疑也。”(25)程端学:《春秋或问》卷第三,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本,第10a-10b页。
通过程端学,可以看到关于宋儒历来对桓公和子纠兄弟关系的讨论,依据的是《春秋》笔法。程子由《公羊》《谷梁》“公伐齐,纳纠”无“子”字,判断桓公为兄。由此,理学内部从胡安国、朱子、张栻等以来便尊程子说,以桓公为庶兄。更为关键的一点则是程端学指出,程子以桓公为兄的真实用意其实源于《论语》孔子赞许管仲仁功,换句话说,程子欲要协调《论语》中孔子关于事功与义理间的关系,而这个考量才是促使程子持桓公为兄这一观点的决定因素。正为此,历来不信《春秋》一字褒贬的朱子,才会取程子以一字定夺桓公和子纠兄弟关系的说法。
理学内部一直沿袭程子的说法,直至王船山才明确打破历来理学在兄弟意义上看待桓公和子纠关系的观点。他在《春秋稗疏》中提到历来关于桓公和子纠关系的看法有以下几种:1.子纠为兄、桓公为弟。2.桓公为兄、子纠为弟。3.桓公为叔、子纠为侄。第一种观点的代表有杜预,第二种观点的代表有程子,第三种观点是船山自己的看法(26)参见王夫之:《春秋稗疏》,《船山全书》第5册,长沙:岳麓出版社,2011年版,第35-36页。船山认为管仲既有功又有过,不必从中调停,是采程子功过不相掩的说法。在《读四书大全说》船山又持桓公为兄、子纠为弟的观点,并且认为:“齐之难,起于襄公之见弑,则为襄公之子者,俱有可反国以存社稷之义,非国家无事,长幼有定序,而纠故作逆谋以争兄位也。”见《船山全书》第6册,第805-806页。船山对经典的解释多随文就义,故而前后观点有差异,甚至矛盾者时有。。船山的叔侄说,干脆只接受孔子称许管仲事功的说法,以子纠拥有优先的继承权,言外之意即取管仲功过不相掩的说法。但是在《读通鉴论》里,船山又说“管仲,齐之臣,齐侯其君也”,“仲之事子纠,齐侯命之”(27)王夫之:《读通鉴论》卷二十,《船山全书》第10册,第750页。,又以君臣未定来看待管仲与子纠的关系,以此说明改事桓公无罪的观点。
为什么桓公和子纠属于哪种亲属关系会被如此看重?除了桓公与子纠到底是哪种关系,将引发出关于桓公继承是否合法的问题外,还将牵扯出“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非但不死,反而改事桓公这个仇人,此行径是否合于君臣之义的问题。后者关系着儒者理解孔子对待事功和义理以及两者关系的态度问题。
如果照《公羊》《谷梁》之说,子纠贵当立为君,那么桓公杀子纠的性质就成了弑君,随之管仲改事桓公便为事仇。这样的话,等于证明管仲悖逆臣道。如此一来,在称许管仲事功时,孔子岂不是不顾其乱君臣大义的罪,但以结果论英雄?这样将使孔子所言的仁人与仁功间不必关联起来,从而开了一道罅隙使乱臣贼子一旦有仁功便能一洗前罪。
可见,程子确实如程端学所论,别有用心。以桓公为兄的话,那么首先确定了其拥有优先的继承权,相比子纠而言更具合法性,因而管仲改事桓公便只能算作改正,仍然不失君臣之义。所以朱子说“管仲有功而无罪”。同时引“唐之王圭魏征,不死建成之难,而从太宗”为例,以说明王、魏改事太宗,害于君臣之义,原因即在于建成继承君位的合法性已定,太宗弑杀建成就是篡位。如此在君臣名分之下侍奉建成的王圭、魏征改事弑其君的太宗,无论之后的功绩有多大,两人始终有罪于君臣之义。
从上文看出,无论对“三归”还是兄弟关系的解读,朱子对文本的诠释有两个原则,以管仲为例,朱子在诠释文本时,始终在强调仁功与仁人两个层次的区别,有仁功者不等同于就是仁人。但更为根本的目的,则是为了维护君臣之义,以德收摄、引导事功。本来仁功并不必要牵涉桓公与子纠关系类型的问题,相对而言君臣之义是否能够得到维护,却与之关系重大。处理好了,就君臣关系而言,管仲是无罪的。这样,才能实现义理在政治伦理的秩序建构中的合法化。
三、“致主于道”——修德与王道秩序的建构
(一)德尊于势——孟子对管仲的评价
在《孟子·公孙丑上》第1章中,公孙丑问孟子,如果他当权齐国,是不是能复兴管仲、晏子的事功?孟子回答说:“子诚齐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孟子轻视管仲诸人,并引曾西“管仲得君如彼其专也,行乎国政如彼其久也,功烈如彼其卑也”的话,以说明管仲不足效法,此亦可视为孟子对管仲的评价。《孟子·公孙丑下》第2章表达了德尊于势的思想,其所举管仲事例亦表达了孟子对管仲的评价。其言:“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故汤之于伊尹,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王;桓公之于管仲,学焉,而后臣之,故不劳而霸。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认为德为治理天下的利器,是天下得治的必要条件之一。与爵位、年齿并立,三者分别在权力秩序、人伦社会、国家治理层面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即便在权力秩序层面,德依然不可或缺,它是获得秩序的保证。如果国家治理无法实现,那么权力的系统一定会出问题。管仲在孟子的话语下,以霸道秩序的构建者形象出现在与构建王道秩序的伊尹形象所形成的对比图景中,不仅形成了王霸规模上的落差,而且将德的意义通过两人共同的君师身份凸显出来,以说明德在秩序构建中所具有的巨大效果,更彰显出管仲不足为法。
在孟子的叙述中,德为致治的构成因素,有德者才能实现王道秩序。有德者蕴含有道之义,孟子分明有抬高道之地位的意图,使道尊于势。此处亦透露出孟子的君臣观:1.道尊于势,有道的人可为君侯之师,君臣以道合;2.君臣皆为爵位,并不具有绝对伦理的关系(28)孟子这些观点直接影响黄宗羲,他在《明夷待访录》里提到君臣名异而实同,即名称虽然不同,但是从为天下、为百姓的目的而言两者并无不同。参见《明夷待访录》的《君道》《臣道》两篇,收录于《黄宗羲全集》第1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以上可见,孟子对管仲的评价并不与孔子一致。因此,朱子需要对此作出说明,否则四书系统内部便会产生不协调,甚至会牵连朱子的道统说(29)朱子的“四书”体系即是建立在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的道学传承谱系上。换言之,如果朱子无法做到四者间的协调,那么这个系统自身便无法获得自我的统一性。,使其受到质疑。
朱子在《读余隐之尊孟辨》里谈到:“夫子之于管仲,大其功而小其器,邵康节亦谓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知此者可与论桓公、管仲之事矣。夫子言‘如其仁’者,以当时王者不作,中国衰,夷狄横,诸侯之功未有如管仲者,故许其有仁者之功,亦彼善于此而已。”(3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27页。点明《论语》中孔子以仁功称许管仲。那么朱子在触及孟子的评价时,又是如何理解的呢?
朱子从两个方面来理解孟子的评价:第一,“至于语学者立心致道之际,则其规模宏远,自有定论,岂曰若管仲而休耶!曾西之耻而不为,盖亦有说矣”(3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27页。。从规模而言,管仲立心便未致道天下,所以规模狭隘,不见宏远。第二,“李氏又有救斗之说,愚以为桓公、管仲救父祖之斗,而私其财以为子舍之藏者也。故周虽小振,而齐亦寝强矣,夫岂诚心恻怛而救之哉”(3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27页。。管仲无诚心恻怛救周,仍是一番功利之心,是动机出于人欲。至于孟子轻薄管仲事功,朱子说孟子所处的时代天命已改,与“齐桓之时,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革命之事未可为也”(3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28页。相比,齐宣王可以王天下,并指出孟子微言所在,“孟子言以齐王犹反手,自谓当年事势,且言己志,非为管仲发也”(34)《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五),《朱子全书》第24册,第3528页。。孟子对管仲的评价,在朱子看来,既考虑到时代天命已改的情势,又依据道以德行的原则。朱子后学真西山在《大学衍义》中说道孔孟差异:“若管仲者,孔子盖尝以‘如其仁’称之,孟子学于孔子者也,何其言之异邪?曰孔子之称,称其攘夷狄而尊中夏也;孟子所讥,讥其舍王道而用霸术也,所指固不同矣。然孔子虽称其功,而器小之讥,不知礼之讥,固未尝略;况世变日下,使孟子而不复议其舍王用霸之罪,则人将靡然趋于霸矣。”(35)真德秀:《大学衍义》卷十四,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旨在说明时代天命已改这一点,即沿袭朱子意思。
(二)“修身以道”——工夫论视域下的王道秩序
朱子认为管仲不知“圣贤大学之道”,故不能通过“正身修德以致主于王道”,这点前文已明。朱子对管仲的评价是以《大学》义理为参照,其目的要以修身所根循的道德法则为王道秩序奠立根基,以统一天理与事功,使事功的发生根源于德性,从而解决仁功与仁人的断层。从这点而言,朱子强调称许管仲“如其仁”时,孔子的意思乃为:“如其仁,言谁如其仁者,又再言以深许之。盖管仲虽未得为仁人,而其利泽及人,则有仁之功矣。”以仁功消除掉管仲为仁人的诠释余地,区分开仁功和仁人,以见管仲的事功原理与仁人所具备的天理不同。但由此是否会开启只需要追求仁功,而不必同时为仁人的逻辑可能呢?
其实朱子视仁功和仁人为连续的整体,仁人对仁功而言具有奠基性,而且这种奠基性应当通过《大学》来看。
李从之问:“‘壹是皆以修身为本’,何故只言修身?”曰:“修身是对天下国家说。修身是本,天下国家是末。”(36)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十五,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07页。
或问:“《大学》之书,即是圣人做天下根本?”曰:“此譬如人起屋,是画一个大地盘在这里。理会得这个了,他日若有材料,却依此将去,只此一个道理。明此以南面,尧之为君;明此以北面,舜之为臣也。”(37)《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50页。
所谓规模之大,凡人为学,便当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及“明明德于天下”为事,不成只要独善其身便了?须是志于天下,所谓“志伊尹之所志,学颜子之所学也”。所以《大学》第二句便说“在新民”。(38)《朱子语类》卷十四,第260页。
据以上三则材料,可做几点说明和总结:第一,修身是天下国家的根本。朱子以本末关系对待修身和天下国家,即知从逻辑而言,修身为天下国家的前提。第二,《大学》是“圣人做天下”的根本,也是“做天下”的蓝图。第三,修身的立意中包括“志于天下”的环节。
由此,可见《大学》义理是由“内圣”而“外王”的构型,以工夫论路径拓向天下国家秩序,使之与心灵秩序同构发生。
王船山先生在《读四书大全说》云:“曾西之所以下视管仲者,正在诚意正心之德。”(39)《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船山全书》第6册,第621页。也是通过《大学》义理看待管仲。并说:“《大学》之道,天德也,王道也;显则为《周官》之法度,微则为《关雎》《麟趾》之精意也。”(40)《读四书大全说》卷四,《船山全书》第6册,第621页。更为鲜明地点出“大学之道”就是“王道”这一点。
另外,通过朱子的政治实践活动,可以更加清楚地看清“诚意正心”在秩序建构中的地位,尤以朱子所上三封《封事》为代表,其中“大学之道”以近于“帝王之学”的面貌被呈现出来。
朱子《壬午应诏封事》是在绍兴三十二年宋孝宗即位时(1162年)应诏而上的。其中言:“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纤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41)《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572页。孝宗淳熙七年(1180年)上《庚子应诏封事》,有言:“臣尝谓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若夫治军省赋以为恤民之本,则又在夫人君正其心术以立纲纪而已矣。”(42)《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581页。孝宗淳熙十五年(1188年)上《戊申封事》,有言:“天下之大本者,陛下之心也。……臣辄以陛下之心为天下之大本者,何也?天下之事,千变万化,其端无穷,而无一不本于人主之心者,此自然之理也。故人主之心正,则天下之事无一不出于正;人主之心不正,则天下之事无一得由于正。……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宫之中,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窥者,而其符验之著于外者,常若十目所视、十手所指,而不可掩。……所以正吾此心而为天下万事之本也。”(43)《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一),《朱子全书》第20册,第590-591页。无不以“诚意正心”为根本,纳之为“帝王之学”的核心要旨。其所涉的学问以《大学》为结构,更见“修身以德”在秩序建构中的奠基地位。
结语
朱子不仅依据《大学》义理评价管仲的人品及事功,并且还据之对经史中分歧的管仲事迹作出某些取舍。比如取《说苑》台名的说法释“三归”,乃是为证明管仲因不知“大学之道”才有奢侈、犯礼、无法“致主于道”等“器小”之讥;又结合理学的君臣观念,取程子桓公为兄、子纠为弟的说法,以证管仲无罪于君臣之义。于是,构建起管仲“有功而无罪”的形象。通过展现管仲这个止步于霸道的有仁功者的不足,与不能正身修德间的因果关系,说明惟有根循“大学之道”才能导引出完美的王道秩序图景。其中所蕴含的政治伦理意义,表现为历史政治的当代化、当前化,它不仅寄托了理学家的政治和人格理想,同时也是对现实政治的关注方式。
历史并不是作为过去而存在于文献、记忆或者口述里;相反,历史是在当下生活中被思想不断激活的,成为生活的部分并继续推动实际的发展。管仲形象的积累与演变是在政治伦理的建构中发生的,它随着儒者“治天下”的关怀而释放其“当代”意义。史学大家顾颉刚曾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他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以尧舜禹为例说明层累现象:“《论语》中两次连称尧舜,一次连称舜禹,又接连赞美尧舜禹,可见当时确以为尧舜在禹之前。于是禹之前有更古的尧舜了。但尧与舜、舜与禹的关系还没有提起……在《论语》之后……有了《尧典》、《皐陶谟》、《禹贡》等篇出现。……于是尧与舜有翁婿的关系、舜与禹有君臣的关系了。”(44)顾颉刚:《古史辨自序》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6页。其实史学的层累是经学诠释过程中的产物。如朱子在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注重普遍和超越的价值维度,让历史随着这些价值的关注而再现于“当代”。管仲形象即是在这些价值的关注中被探讨和再现的。
当康有为指责宋贤“轻薄事功”“攻击管仲”“专内失外”时,暴露了他两个问题:一是忽略了“内”“外”并举的问题。朱子对孔子的管仲评价的解读,正是为了使“内”“外”并举,同时给出一条由“正身修德”而及“治天下”的“大学之道”的实现路径;二是就朱子而言,义理与事功乃是本末关系,是一体的两面,并不存在“专内”的意思。
正如历史学家克罗齐所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并且认为思想创造了历史。那么据之,可以说思想对现实的关怀注定要使历史当代化。 由此而言,在理学家的经世关怀中所展现的历史,本身即是思想的现实反映(45)参见[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2页。克罗齐的话,原本是针对旧的编年史而言。他认为编年史,使历史成为了“死”材料,成为过去而失去在场性,致使难以为当前思想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