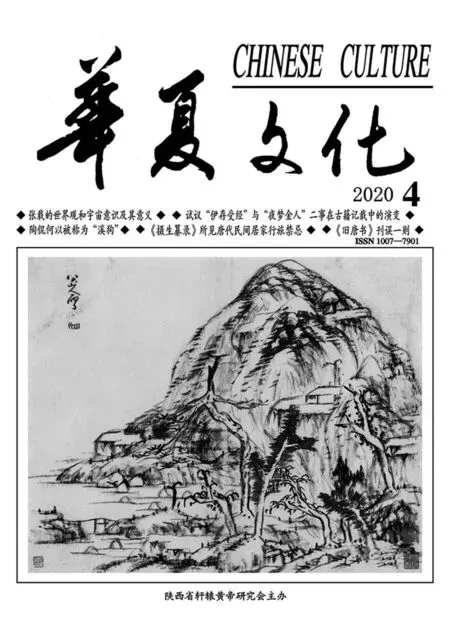金岳霖《中国哲学》述评
□窦 渊
金岳霖先生于1943年在昆明撰写《中国哲学》一文,原文用英文撰写,首次公开发表于我国1980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创刊号,由其学生安徽大学哲学系的钱耕森先生翻译为中文,另有王太庆先生负责校对。金先生的这篇著名论文思想深邃,颇有见地,兼之文风畅快,内容深刻,对初学中国哲学者大有裨益。
谈中国哲学,那就不得不先谈谈超越了国别的“哲学”的概念——哲学是什么?这是一个大问题,一个高深的问题,一个或许复杂也或许简单的问题。我认为哲学就是“思维的科学”,这里的“思维”指“思想”加“维度”,不光要有“思想”,还要有“维度”,也就是说不是一种思想或一类思想,不是专制的、绝对的思想,不是静止的、孤立的、片面的思想,而是复杂的、变化的思想,是既矛盾又协调的,是有生命的、多层次的、联动的思想。哲学没有那么高深,谈不上境界,也犯不上一本正经地去谈什么境界,哲学就是讲思维,它和每个活人相关,严格地讲是和所有活过的人都相关。例如存在着或存在过一个叫张三的人,他丢了钱包,然后他安慰自己吃亏是福,这样的思维其实就是哲学,“吃亏是福”就是一种“福祸相倚”,事物相反相成的哲学思维。哲学就在日常生活之中,它渗透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它从未脱离人们的生活,只是有些专业的人将它从中总结和凝练了出来,发展成了一门系统的科学。成为系统的科学固然有其好处,但也不乏弊端。好处是哲学成为一门系统的科学之后能得到专门的、细致的研究,且这样的哲学看起来似乎更符合所谓科学的定义;弊端在如此为之似乎就挖掉了哲学的根柢,切断了哲学的生命力,哲学就真的成了一门冰冷的、没有人情味儿的,和正义、希望这些人类共同美好愿景无关的纯粹科学了。这样的哲学就产生了职业的哲学家,而“往日的哲学家从来不是专职的。职业哲学家的出现可以对哲学有些好处,但是对哲学家似乎也有所损伤。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中国哲学》)。
但这到底只是我个人的看法,谈不上成熟,也远不够深刻。想要把“哲学”的概念弄得更清楚一点,还得看看一些大家的看法。胡适先生曾说“哲学是研究人生切要的问题,从意义上着想,去找一个比较可普遍适用的意义。”(《东方杂志》第20卷23期)而“因为人生切要的问题不止一个,所以哲学的门类也有许多种”,进而胡适先生在其《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将哲学门类分为六种:
一、天地万物怎样来的?(宇宙论)
二、知识、思想的范围、作用及方法?(名学及知识论)
三、人生在世应该如何行为?(人生哲学,旧称“伦理学”)
四、怎样才可使人有知识,能思想,行善去恶呢?(教育哲学)
五、社会国家应该如何阻止,如何管理?(政治哲学)
六、人生究竟有何归宿?(宗教哲学)
胡适先生在上个世纪将哲学分类为如此六种,可谓是颇有见地的,涵盖方面也很广泛,甚至涉及了教育哲学。虽说在如今这种分法并不完全适合现代哲学体系,但先生之见亦不得不称之为高见。
而英国大哲学家罗素在其著作《西方哲学史》的美国版序言中曾说“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而哲学的人生观与世界观是两种因素的产物,“一种是传统的宗教与伦理观念,另一种是可以称之为‘科学的’那种研究,这是就科学这个词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的。”罗素亦在其《西方哲学史》的绪论中有一段关于对“哲学”理解的集中表述,即在说明哲学是介乎科学和神学之间领域的东西。
接下来再结合金岳霖先生《中国哲学》的这篇文章来谈谈中国哲学。当世有三大主流哲学思想,分为印度哲学、希腊哲学、中国哲学,而对应的就有梁漱溟先生在其《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中提出的“人生三路向说”。“在三大哲学思想主流中,人们曾经认为印度哲学是‘来世’的,希腊哲学是‘出世’的,而中国哲学则是‘入世’的”(《中国哲学》)。但是,在金先生看来,“哲学从来没有干脆入世的;说它入世,不过是意图以漫画的笔法突出它的某些特点而已”(《中国哲学》)。所谓“入世”“仅仅是强调中国哲学与印度、希腊的各派思想相比有某些特点”“它的本意大概是说,中国哲学是紧扣主题的核心的,从来不被一些思维的手段推上系统思辨的眩目云霄,或者推入精心雕琢的迷宫深处”(《中国哲学》)。这就是中国哲学的本质特点。
不论是印度哲学、希腊哲学,还是中国哲学,其与理智的关系都是同样密切的。因为“正象工业文明以机器为动力一样,哲学是由理智推动的”“而在理智方面,中国哲学向来是通达的”(《中国哲学》)。
谈到中国哲学,“人们习惯于认为中国哲学包括儒、释、道三家”(《中国哲学》)。其中儒、道二家是中国固有的,是本土文化的产物。而释家则是从印度传入的,但“无论如何在早期是受到中国思想影响的”(《中国哲学》),其受到道家思想深刻影响的实例就是“格义”。南北朝时期多有以庄学讲佛学者,如《高僧传》中记载慧远“引庄子为连类”以讲“实相义”,也不乏僧人如道安、支道林等,讲佛经时亦常以“三玄”之言比附。
金岳霖先生在文中还谈到了中国哲学的四个特点,其一是“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其二是“天人合一”;其三是“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其四是“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一)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
有不少人指摘中国哲学没有逻辑,甚至说中国哲学不以认识为基础,事实上这种指摘和认识是很荒谬的。金先生讲“我们并不需要认识到生物学才具有生物性,意识到物理学才具有物理性。中国哲学家没有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轻易自如地安排得合乎逻辑;他们的哲学虽然缺少发达的逻辑意识,也能建立在以往取得的认识上”(《中国哲学》)。先生的这番话掷地有声,不仅准确地阐述了中国哲学关于逻辑和认识论方面的特点,事实上也回答了中国究竟有没有哲学的问题。
上个世纪出现了影响深远的“西学东渐”思潮,导致中华文化出现了文化自卑现象。当时一大批人觉得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无比优越的乃甚是完美的,认为我们应该摒弃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因为中华文明是落伍的、腐朽的、失败的。当时这种西方美而中国丑,“外国的月亮比较圆”的荒谬论调甚嚣尘上,甚至于有一批人宣称应该废掉中国的汉字而使用西方的字母。随着这些现象的产生,中华文化的方方面面都遭受了挑战,也就真的竟有不少人怀疑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甚至就直接认为中国是没哲学的了,而直到今天,也仍有人在持着这种观念。这种怀疑实在无趣,因为答案是——中国当然有哲学。
“中国有无哲学”的这个问题其实也是由金先生提出的,即“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历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这是关于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也就是著名的“金岳霖问题”。事实上,在金先生那里,给出问题的同时也给出了答案。就像金先生讲的,我们不需要意识到生物学才具有生物性,不需要意识到物理学才具有物理性,也不需要意识到哲学才具有哲学性,或者说不需要意识到西方所谓的那种哲学才具有哲学性。中国哲学是自成体系的,它不需要西方体系承认方可存在,无论西方认可不认可——中国哲学就在那里。不能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非西方的存在,至少不能拿来衡量一切非西方的存在,比如中国就是这样的存在。
所谓“意识到逻辑和认识论,就是意识到思维的手段”(《中国哲学》),但这种意识又很容易被人贬为“诡辩”。以前还流行过一阵庄子学说是诡辩的说法,但现在这种说法已被拨乱反正了。庄子学说自然不会是“诡辩”,在被那些人称之为“诡辩”背后的实质,“其实不过是一种思想大转变,从最终实在的问题转变到语言、思想、观念的问题”(《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在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不发达,也在另一方面成就了中国哲学。如金先生认为“也许应该把庄子看成大诗人甚于大哲学家。他的哲学用诗意盎然的散文写出,充满赏心悦目的寓言,颂扬一种崇高的人生理想,与任何西方哲学不相上下。其异想天开烘托出豪放,一语道破却不是武断,生机勃勃而又顺理成章,使人读起来既要用感情,又要用理智。”“他那里并没有训练有素的心灵高度欣赏的那种系统完备性”(《中国哲学》)。
正是中国哲学在逻辑和认识论的意识上的不发达,才成就了像庄子这样的哲学家,才成就了像庄子哲学这样的哲学体系。一种观念并非是被编制得越严密、安排得越完备,就越是完美的。事实上,“安排得系统完备的观念,往往是我们要么加以接受,要么加以抛弃的那一类”(《中国哲学》)。一种观念愈是完备、愈是分明,就愈不具有暗示性。而中国哲学向来是并非如此的,中国哲学是“言近旨远”、“言有尽而意无穷”的。金先生讲“中国哲学非常简洁,很不分明,观念彼此联结,因此它的暗示性几乎无边无涯”(《中国哲学》)。而中国哲学的这种特点就决定了“中国哲学是特别适宜于独创的思想家加以利用的,因为它可以毫不费力地把独创的思想纳入它的框子”(《中国哲学》)。
(二)天人合一
初学中国哲学的人,甚至是对中国哲学接触不是很多的人,在谈到中国哲学的特点时,恐怕都会讲个“天人合一”出来。的确,“天人合一”算得上中国哲学最突出的一个特点。而“天”的涵义其实是不容易把握的,但“如果我们把‘天’了解为‘自然’和‘自然的神’,有时强调前者,有时强调后者,那就有点抓住这个中国字了”(《中国哲学》)。
“天人合一”之说确实无所不包,“最高、最广意义的‘天人合一’,就是主体融入客体,或者客体融入主体,坚持根本同一,泯除一切显著差别,从而达到个人与宇宙不二的状态。”(《中国哲学》)
在这方面,西方对待“天”的态度和中国迥然不同,“西方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中国哲学》)。西方主张将自然和人分离开来,这种看法也就随之带来了所谓的“人类中心论”,而这种论调直到今天都在给人类带来着巨大的磨难。随着人类工业文明的兴盛,损害的是整个地球的自然环境,现在直接的恶果就是全球气候变化的问题。部分沿海国家已经因为气候变暖所导致的冰川融化及海平面上升而不断丧失国土,位于中太平洋南部的岛国图瓦卢(Tuvalu)已成为第一个因国土丧失而进行举国搬迁的国家。随着人类科技文明的进步,对自然破坏的能力越来越大。2020年7月下旬,日本轮船“MV Wakashio”号在毛里求斯海岸附近搁浅,随后泄露了上千吨石油,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毁灭性的摧残。西方所谓的“人类中心论”最后只能毁灭人类,而且人类别无出路——只有被毁灭。
我们或说人类不应将也不能将人与自然分割开来或对立起来,我们应该做的是“自然的合乎自然,或者满意的心满意足”(《中国哲学》),也就是说要“合乎道而止于道”,也就是中国哲学的重要内核——天人合一。
(三)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
在希腊哲学和中国哲学中,都强调个人不能离开社会而生活。“从苏格拉底到亚里士多德,无不特别强调良好政治生活的重要性。这些学者既是政治思想家,也是哲学家。他们的基本观念看来是认为个人要得到最充分即最‘自然’的发展,只能通过公道的政治社会为媒介”(《中国哲学》)。
而“中国哲学毫无例外地同时也就是政治思想”(《中国哲学》)。儒家思想毫无疑问是政治思想,因为它倡导“内圣外王”,这“内圣”和“外王”同样重要,只不过有的时候囿于时局“外王”难以实现,那就只能致力于“内圣”之学,即所谓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而不少人怀疑道家思想究竟是否也是政治思想,其实这种怀疑是大可不必的。“道家的政治思想是政治上自由放任,它的消极意义仅仅在于谴责政治上过分硬扣的做法,并不在于不采纳任何政治目标,道家和儒家一样有自己的政治理想。我们可以把那种理想描述为可以在卢梭的自然状态中达到的自由平等境界,再加上欧洲人那种自然而然的不屈不挠的精神”(《中国哲学》)。
儒家思想在政治方面的确比道家思想积极得多。孔子本人就不仅是哲学家,还是政治家,其实也可以将孔子描述成“新儒家”,因为“他十分明智地不当独创的思想家,宣称自己只是宪章文武,祖述先王之道”(《中国哲学》)。孔子建立的这种儒家思想就在不自觉间带上了一种继承传统的客观意义,其特色就很鲜明,就成了独一无二的中国思想。“在政治上不出现倒退的时候,它大概能够引导中国思想沿着它的轨道前进,在政治上出现倒退的时候,它也很容易把后来的思想捏进它的模式。”(《中国哲学》)这样的儒家思想几乎可以做到无所不包,无可不包,无论在历史的发展中遭到如何的危机,遇到别的理念的如何挑战,它总能倔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以一种“旧瓶装新酒”的模样重新绽发光彩。纵观儒学发展史,可见儒家思想的这种本领确实十分了得,而儒家思想的这种模式就是“哲学和政治思想交织成一个有机整体,使哲学和伦理不可分,人与他的位分和生活合而为一”(《中国哲学》)。
布拉德雷讲“人人各有其‘位分和生活’,其中有他的自己的自然尊严”,那“既然见到人各有其位分和生活,一个人就不仅对于自然安于一,而且对社会安于一了”(《中国哲学》),而这种“伦理与政治合一,个人与社会合一”自然也是“天人合一”了。
要之,关于这种独一无二的中国思想,金先生认为:
儒家政治思想与哲学家及其哲学都有内在联系。儒家讲内圣外王,认为内在的圣智可以外在化成为开明的治国安邦之术,所以每一位哲学家都认为自己是潜在的政治家。一个人的哲学理想,是在经国济世中得到充分实现的。……一位杰出的儒家哲人,即便不在生前,至少在他死后,是一种无冕之王,或者是一位无所任的大臣,因为是他陶铸了时代精神,使社会生活在不同程度上得到维系。因此人们有时说中国哲学家改变了一国的风尚,因此中国哲学和政治思想意味深长地结成了一个单一的有机模式。(《中国哲学》)
综上,可知在中国哲学中个人和社会的合一性与和谐性。
(四)哲学家与他的哲学合一
关于哲学家和他的哲学合一,也就是一个学者论道、践道的合一,这方面古希腊哲学家是做得不错的,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但当代的西方哲学家则做得远远不够。作为哲学家,古希腊的那些哲学家们并不超脱于自己的哲学,他们推理、论证,并且传道;而当代的西方哲学家们,“就或多或少超脱了自己的哲学。他推理、论证,但是并不传道”(《中国哲学》)。
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应该说是时代的问题,在当代西方是很困难甚至不会再出现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式的人物了,“从斯宾塞起,我们已经意识到应该明智一点,不必野心勃勃地要求某一位学者独立统一不同的知识部门。每个知识部门都取得了很多专门的成就,要我们这些庸才全部掌握是几乎不可能的”(《中国哲学》)。科学的体系经过漫长时间的发展,已经比两千多年前复杂得多,要求出现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几乎是不可能的,现代西方人的求知更倾向于一种分工的办法,但“在某种意义上,苏格拉底式人物一去不复返则是更加值得惋惜的”(《中国哲学》)。
而且现代西方人的求知“还有一种训练有素的超脱法或外化法。现代研究工作的基本信条之一,就是要研究者超脱它的研究对象”(《中国哲学》)。如现代的宗教学的研究学者,无须有宗教上的信仰对象,而且在某种意义上,只有超脱了这种对象,对客观真理的感情盖过了其他有关研究的感情,才能更好地推动现代的科研工作。但这种超脱倾向就会导致一些十分严重的问题,在这种超脱之下而诞生的专门的哲学和职业的哲学家,就对哲学和哲学家有所损伤,因为这样造就的哲学家“他懂哲学,却不用哲学。”而且“哲学一超脱,就成了一条迂回曲折的崎岖道路,布满技术性的问题,掌握它需要时间,需要训练,需要学究式的专一,在全部掌握之前往往会迷失方向,或者半途而废”(《中国哲学》)。
在西方当代所呈现出的哲学家与他的哲学无法合一的这个问题,在中国当代就没有那么难以解决甚至无法解决。“中国哲学家到目前为止,与当代的西方哲学家大异其趣。他们属于苏格拉底、柏拉图那一类”(《中国哲学》)。
金先生在文中指出:
其所以如此,是因为伦理、政治、反思和认识集于哲学家一身,在他那里知识和美德是不可分的一体。他的哲学要求他身体力行,他本人是实行他的哲学的工具。按照自己的哲学信念生活,是他的哲学的一部分。他的事业就是继续不断地把自己修养到近于无我的纯净境界,从而与宇宙合而为一。(《中国哲学》)
的确,真正的中国哲学家向来是论道和践道合而为一的,他和自己的“道”是不可分的,以至于他成了他“道”的一部分。无论是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如老子、孔子、墨子、孟子、庄子等,都是人道合一、以身践道的;还是中国现代的哲学家,陈寅恪先生、金岳霖先生、胡适先生等,依旧是如此的。这似乎就是中国哲学和哲学家们的传统了。
在金先生看来,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如此的:
在认识上,他永远在探索;在意愿上,则永远在行动或者试图行动。这两方面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在他身上你可以综合起来看到那本来意义的‘哲学家’。……在他那里,哲学从来不单是一个提供人们理解的观念模式,它同时是哲学家内心中的一个信条体系,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以说就是他的自传。(《中国哲学》)
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应该是“合道”的,也就是说他和他的哲学是真正合一的,他的“道”不仅是做学问的标准,同样也是做人的尺度。
陈寅恪先生在对冯友兰先生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版的《中国哲学史》上册的审查报告中曾说道:“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这是陈先生对于研究古人学问所提出的要求和标准,即需具备一种了解之同情。自然地,“了解之同情”不只是研究别人的学问应有的要求,做个人的学问也当有这种“了解之同情”的基本要求,自己的学问和这学问的立说之人即自己应“处于同一境界”,这也就是强调做学问的人和学问应该是合一的。
哲学家和他的哲学也是不可分割的,“哲学家与哲学分离已经改变了哲学的价值,使世界失去了绚丽的色彩”(《中国哲学》)。若研究一种哲学,抑或做一种学问,不是解决人类何从何往的问题,不是探究人类如何更好地生活的问题,不是致力于世界更加美好的问题,反而使得人类加速消亡,万物失去平衡,人心更加浮躁,世界更添灰暗,那这种哲学或学问真是可恶!
读金岳霖先生这篇《中国哲学》的文章,不难发现先生对于真正哲学的向往和欣喜。先生做学问,切合实际,从生活而起,又致力于探求哲学的真正价值,力图为世界再添几缕绚丽的色彩。这实在是了不起!从先生身上,大抵是明白如何做学问和做人的。我笔下有山河万千,人间百态。提笔话江山,我定要这人间再多出几束光来,这是一个哲人或文人做学问该有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