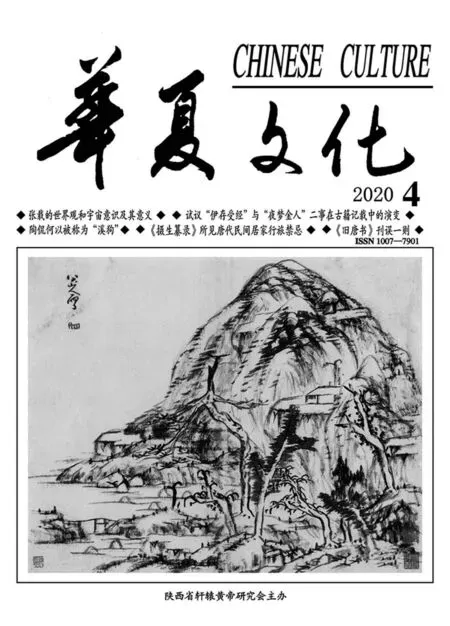《论语》“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章探赜
□程泽阳
《论语·先进》有一章:“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在此章中,孔子不同意子路推荐子羔出仕,而子路应之以“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由此出发,对于孔子何以批评子路,为学、读书、出仕之间是什么关系以及相关问题,都值得深入探讨一番。
一、子羔为宰之地考
子羔,原名高柴,又作子皋、季羔、季子皋、高子皋。《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高柴字子羔,少孔子三十岁”。又说:“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比《先进》篇所记多一“郈”字,东汉王充《论衡·艺增》也作“子路使子羔为郈宰”,由此生出异说。刘宝楠引戴望的观点:“《史记》‘费’字后人所增。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释郈在郓城宿县,未言费所在,知所见本无费字……子路以堕郈后不可无良宰,故欲任子羔治之。”他不仅断定高柴所任为郈地宰,还点出了子路任职时间在孔子“堕郈后”,并加按语认为“戴说颇近理”。(刘宝楠:《论语正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2页)。但是笔者认为此种说法并不合理。首先,戴望根据《史记正义》此处只释郈不释费,断定“费”字为后人所增,此观点就站不住脚。因为在《史记》其他出现费地之“费”的地方,如《孔子世家》“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等处,《史记正义》都是不释费,只释郈,则可知《正义》默认“费”字不出释文,戴望所认为的不释“费”字则本无“费”字的观点不成立。并且根据日人水泽利忠的考证,南化本、枫山本、三条本、梅本四种宋元版《史记》校记都“无郈字”(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四,广文书局,第2410页),却没有校记说无“费”字的。
其次,王充《论衡·艺增》云:“子路使子羔为郈宰,孔子以为不可,未学,无所知也”,此一处虽作“郈宰”,但记载十分简略。而《问孔》、《量知》、《正说》三处均记载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并且引用得比较详细,其中《正说》篇所引与《论语》相差无几。虽然黄晖《论衡校释》认为正作“郈宰”,凡作“费宰”皆后人据今本《论语》而改。可是他的说法也有不合理之处:第一,若是后人据《论语》妄改“郈”为“费”,何以独《艺增》篇未改?第二,《问孔》篇引文作“有社稷焉,有民人焉”,而《正说》篇却作“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前后不相统一,若经后人窜改,必严丝合缝,无此纰漏。所以这些纰漏恰恰证明应是王充凭自己记忆所写的“传闻异辞”。同时代的《白虎通义·社稷》引用此段,亦作“季路使子羔为费宰”;刘宝楠又说“《论语集解》亦不释郈,则包、周、马、郑诸家所据本皆作费”,则同一时代诸家与王充《论衡》所本相同,都作“费”。
最后,仔细品味此章语气,子路使子羔为邑宰似乎颇为容易。再参之以《论语》:《雍也》篇“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子罕》篇“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子张》篇“孟氏使阳肤为士师”。在这几例中,“使……为……”均表示前者对后者拥有某种指派、任命的权力。但是“仲由为季氏宰”,子路是季孙氏的“总管”(杨伯峻语),而郈地却是叔孙氏十分重要的采邑,是“三都”之一,那么即使子路在“堕三都”之事中再有功劳,也不可能很轻松地以季孙氏家臣身份指派子羔做叔孙氏重要都邑的邑宰。又根据《论语》记载,叔孙氏这一代家主叔孙州仇,即叔孙武叔,他曾多次诋毁孔子,意必之前对孔门弟子无好感,不会任用孔子门人。事实的确如此,《左传·哀公十七年》云“公会齐侯盟于蒙,孟武伯相……武伯问于高柴”,《礼记·檀弓下》“子皋将为成宰”、“季子皋葬其妻,犯人之禾……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可见高柴是受到孟孙氏的重用,当过成宰(成即郕)的,所以有理由认为《仲尼弟子列传》中“子路使子羔为费郈宰”的“郈”是“郕”字之误。
二、出仕、为学与读书的关系
子路举荐子羔当邑宰,孔子以为不可。子路说:“有社稷焉,有民人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王充《论衡·正说》云:“五经总名为书。”子路认为为学不一定只是读《诗》、《书》等典籍,治民、事神亦是为学。而孔子说:“是故恶夫佞者”。梁章钜注曰:“佞是口才捷利之名,本非善恶之称。”程树德说:“自夫子恶夫佞者,而佞乃为不美之名。”孔子为什么批评子路“佞”?为学与读书是何关系?
据余英时考察,春秋末期,宗法分封制度被破坏,社会阶层的流动——即上层贵族的下降和下层庶民的上升,使得处在“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的士阶层人数大增,士出现了从最低层的贵族到最高级的庶民的转化。瞿同祖也认为,处于四民之首的士民是士的预备阶级,他们以学问为事,不耕不作,“学未成不为官,便是庶民;被擢用时,便可进而为士”。因此,私人讲学的风气在此时十分兴盛,儒家、墨家都大规模的收徒讲学,传授士民做官的知识。《论语·为政》“子张学干禄”,《卫灵公》“学也,禄在其中矣”;《墨子·公孟》:“子墨子曰:‘姑学乎,吾将仕子。’”而不经过学习则不能出仕,《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子皮想要让尹何主管一邑之地,在管理中学习,而子产说:“侨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若果此行,必有所害。”《新序》也记载:“鲁哀公问子夏曰:‘必学而后可以安国保民乎?’子夏曰:‘不学而能安国保民者,未尝闻也。’” 为学熟习成为了出仕必不可少的条件。因此当子路让子羔出仕去当邑宰时,孔子认为子羔“学未熟习”,会害了子羔。
在《论语》的记载中,孔门对“学”是非常重视的。《论语》开头就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子自述“十有五而志于学”、“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孔子对季文子、颜回的评价也都是“好学”,其他关于学习方法、学习意义的论述也比比皆是,兹不赘言。既然学是为了出仕做准备,那么所学、所教就十分重要。首先应当是学习各种实用技能——即“艺”。孔子也说:“吾不试,故艺。”艺指多才能,大体是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官吏的常用技能。《左传·昭公七年》记载“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于是临终时使其子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是贵族不知礼而向孔子请教;《论语·子罕》云:“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是孔子曾致力于乐;同篇又云:“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是孔子娴熟射与御;孔子又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程树德《论语集释》考证“古谓字书为史”,是孔子对书有研究;《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贫且贱。及长,尝为季氏史,料量平”,是孔子于数亦能“会计当”。因此当季康子问子路是否可以“从政”时,孔子说:“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掌握“艺”是庶人为“士”最基本的要求。
若只是要学会一项或数项“艺”,自然不一定要学于“仲尼之门”。而孔子之所以为孔子,亦不仅仅是因为他教授弟子射、御之技能,更在于他教授与传承礼乐文化的典籍。《述而》篇说:“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这是有关孔子教人最直接的表述。《先进》篇则将孔门高弟按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分为四科。北宋刘敞《公是弟子记》将二者对应起来:“文,所谓文学也。行,所谓德行也。政事主忠,言语主信。”他还认为:“古之教者,《诗》《书》、礼、乐。至仲尼,益之以《易》《春秋》,乐自此没矣。礼者,徳行之本也;《诗》者,言语之本也;《书》者,文学之本也;《春秋》者,政事之本也。”又将孔子四教与儒家典籍联系起来。《史记·孔子世家》亦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此处的“六艺”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诗》、《书》等典籍在春秋时代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宗庙会同、诸侯朝聘,还是劝谏君主、贵族宴饮,这些场合都需要赋《诗》、引《书》来表达意见,或为自己的观点提供依据。据统计,《左传》中引诗、用诗多达一百多处,孔子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这些都是重视《诗》交际功能的体现。
但是也有不同观点,元代《四书辨疑》引王若虚云:“夫文之与行固为二物,至于忠、信,特行中之两端耳,又何别为二教乎?”将“忠、信”纳入“行”中,把孔子所教归为“文”和“行”两类。事实上,这种看法才是比较全面的。随着王官之学失守,“道术将为天下裂”,士阶层不仅娴熟于赞礼、治政等具体技能,还掌握了传承礼乐文化的上古典籍。他们面对礼坏乐崩、“肉食者鄙”的现实局面,要求改变,并以“道”自任,“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自觉地承担起了弘道的责任。因此,一部分人为学不再是为了出仕、求禄:“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论语·雍也》)颜回好学,却未曾仕进,而是“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士志于道”、“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君子谋道不谋食”成了更高层次的要求。因此“为学”内容的本末就发生了变化,具体技能的掌握、《诗》《书》等典籍的讽诵固然重要,但对“道”的践行、传承才是为学的终极目标。而儒家的“道”是仁、是孝悌,都是侧重于“行”。故而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在“文”和“行”的关系中,孔子认为学文是“行有余力”才可以从事的,先“行”而后“文”,这一思想在孔门后学亦引起了讨论。有若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子游批评子夏的门人只能“洒扫应对进退”,有末而无本。为学次第、本末的争论已经有了分歧。
至此,对孔子批评子路“是故恶夫佞者”可以全面地理解:子羔“学未熟习”,对典籍的理解、应用不够,自然不可以出仕;但子路之言若单独拿出来亦无不当,为学当然不仅仅只是读书,至少包括力行;所以孔子只说他“佞”,而对他的意见并没有正面否定,此处的深意值得注意。
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的后世影响
自子路以“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应孔子,此语很长一段时间都用作掩饰不读书的遁辞,如《魏书·伊馛传》崔浩云:“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卫青、霍去病亦不读书,而能大建勋名,致位公辅”。及至宋代,学术风气大变,心性之学兴起,子路之言才又被置于学术讨论的语境之中。
“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从范围上讲,是说为学不仅仅包括读书;从为学次第上讲,则是认为读书不在为学之前,不是为学所必备的。因心学一派主张“心即理”,认为为学应当“发明本心”,先立乎其大,故而主要从为学次第的层面上理解此语。如陆九渊说:“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又说:“学者须是打叠田地净洁,然后令他奋发植立。若田地不净洁,则奋发植立不得。古人为学,即‘读书然后为学’可见。然田地不洁净,亦读书不得。若读书,则是假寇兵,赍盗粮。”(《陆九渊集》,中华书局,1980年,463页)与陆九渊来往密切的曾丰亦有诗云:“……心融口笑先儒泥,一万余言解三字。粹精还我闻未闻,糟粕从渠味无味。悬知书者古之余,稷契皋夔读何书?犹期立脚群贤上,更请回头万物初。”(《题李师儒上舍稽古堂》)明代陈献章更说:“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陈献章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0页)这引起了朱熹学派的极大反对,鹅湖之会上朱熹与主张“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的陆九渊激辩;王应麟考证稷契皋夔之时,亦有书可读;明儒黄佐批评说:“学必读书,然后为学,问必听受师友,然后为问。驾言浮谈,但曰‘学苟知本,则《六经》皆我注脚’,则自索之觉悟,正执事所谓野狐禅耳。”(黄宗羲,《明儒学案》卷五十一)但正如全祖望所说,陆王之学并不教人不读书,而是“深戒学者骛高远而不览古今”,他认识到“陆学精处,正在戒学者之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学者可不戒乎!”黄宗羲也说:“然阳明亦何尝教人不读书?第先立乎其大,则一切闻见之知,皆德性之知也”。他们的思想对于转变繁复的章句训诂之学自有其积极意义,只是流弊以致“世之谈道者,每谓心苟能明,何必读书”,亦非象山、阳明所知也。
心学发展到后期,出现了“未尝读书而索之空寂杳冥”、“人人禅子,家家虚文”的局面,儒生对于经史典籍早已束书不观,只致力于与帖括之文有关的程、朱注疏。随着明朝灭亡,有识之士如王夫之、颜元等人认识到这种空疏的学风与之有莫大的关系。颜元说:“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所以他认为为学不仅仅是读书,甚至不是读书,“道不在诗书章句,学不在颖悟诵读”,力主实行、实干之实学。他解释此章云:“‘贼夫人之子’,盖谓道未明,德未立……非谓必使之先读书也”,又说:“读书愈多,愈惑,审事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将读书视为“吞砒霜”。他重新诠释儒家之道与学:“盖吾子之所谓道,即指德行兼六艺而言;所谓学,即指养德修行习六艺而言”(《颜元集》,中华书局,1987年,第222页),要求儒生躬行“六府、六德、六行、六艺之事”,身习“礼、乐、射、御、书、数以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之属”,为有用之学,做有用之人。
陆王心学赞同“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而反对陆王心学的颜元亦赞同此语,这种现象值得更加深入地探讨。在今天,我们对于子路“何必读书,然后为学”之语仍要作辨证地理解,即既要广泛地读书、博览,又不可只将读书看作为学而钻入故纸堆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