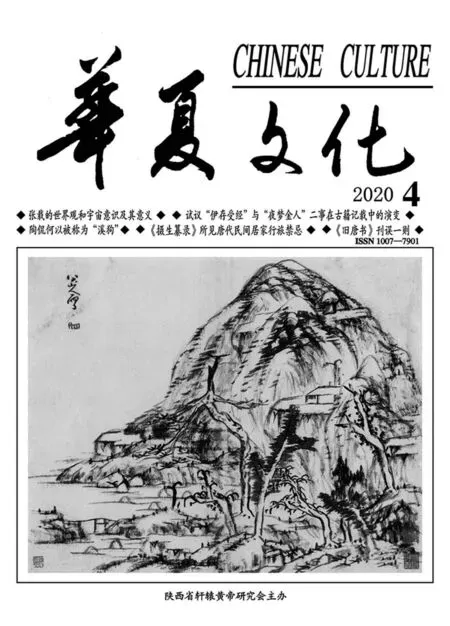论慎子的“制法”思想
□张涵毅
比之战国其他法家人物,慎子显得相当特别,他强调法治,却不唯法是从;看重君权,却从不以君为尊。他的思想有别于其他法家思想,这与其成长于三晋、游学于稷下的学术经历不无关系,这也使得慎子能够主动地吸收并融会先秦诸家学说,自成一派。学界对于慎子思想的研究,主要文章有《慎子法治思想概述》(刘斌,《管子学刊》,1998年第1期),《慎子学术思想刍论》(范国强、田一颖,《陕西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06期),《论慎子的学术思想》(李延勇,《西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5期),这三篇文章主要集中在对慎到学术思想的总结概括,并对道法关系,慎到“势治”思想等内容做出了一定程度的讨论。本文拟从法治运行主体这一角度来重新考察慎子的“法”思想,以期获得新知。需要说明的是,《慎子》传世本的部分篇章和真伪问题在学界有着巨大争论,本文拟就《慎子》整体文本进行分析与梳理,这样的方式虽具有冒险性,但诚如史华兹所认为:思想史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冒险事业,相对于目前证据并不坚实的真伪考证,这也不失为一种谨慎理性的研究态度。
一、定法者、司法者与役法者
在慎子看来,法治作为国家政治管理的手段,要让法在国家行政领域、世俗生活领域中顺利运行并产生作用,就缺少不了三个主体的努力,这三个主体便是:“以力役法者,百姓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以道变法者,君长也。”(《慎子·逸文》)。慎子认为,百姓、司法者(官吏)以及君主,他们构成了法治运行的三个必要主体。百姓遵守法律,拥戴法律;执法官吏严格执法,以身作则;统治者根据国情、民情、世道变化来制定合适的法律,那么国家便会得到大治,有道社会的理想便能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百姓,司法者,统治者虽然是自下而上位处于社会的不同阶级,但法治地流通运行,并不只是相邻的两个阶级互相影响与渗透。慎懋赏在注慎子时解释道:“百姓畏法,故能趋而使之;有司执法则事治,而百姓安也;随时变法而不失其道,人君之所以宰治万民也。”(《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78页)慎懋赏在注解这段文字时,将“役”翻译为驱使,差遣的意思。这种解法本无问题,但细究全文语境,便会发现此处“役”译作“驱使”会有问题。将“役”译为驱使,那么“以力役法者,百姓也”,百姓便成为了此句的主语,不过是被动主语,意为百姓被驱使,但看余下两句译文都并未有被动语态,所以按照并列的关系,第一句也不应该翻译为被动句。《说文解字》上对“役”有如下解释:“戍也。依韵会订。戍,守边也……殳所以守也。故其字从殳。引伸之义凡事劳皆曰役。”由此可见,将“役”翻译为守护,捍卫的意思会更贴近于原文。那么结合慎懋赏的注解,也就更容易理解君、吏、民三者在社会法治系统中的相互关系。这三个主体如同三极一样,相互影响且不能分割。君与吏之间:统治者设定出一套适用于社会的法律,并根据社会形势的变化适时做出相应的调整,再通过自己手下的官吏完成法条政令的宣传和执法任务。吏与民之间:官吏有义务向民众宣传和普及政府颁发出来的律令,同时也要以身作则,严格执法。民与君之间:在慎到看来,好的律法,再加之负责任的官吏,这样的治理是完全贴合人情,符合百姓利益的,本着趋利避害的人性特征,每个百姓都能够衷心护法,保护自己现有的利益成果。因此,在慎到的眼里,法治社会下的百姓并非完全是惧法畏法因此不敢成为乱法之徒,而是守法护法的一大力量。由此,可以更进一步看出,慎到认为君、吏、民三者之间他们的利益是一致而非相对的。慎到认为,君主虽然高高在上,但只有施行有道之政,才能得道多助,集众人之资,共同维持国家政治的清明:“大君者,太上也,兼畜下者也。下之所能不同,而皆上之用也。是以大君因民只能为资,尽包而畜之,无能去取也。”(《慎子·民杂》)这也是慎到区别于商鞅、韩非子思想学说的一大不同。商鞅认为:“今世主欲辟地治民而不审数,臣欲尽其事而不立术,故国有不服之民,主有不令之臣;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以乐成。”(《商君书·算地》)而申不害任术,则是要调和君臣之间的矛盾,以防大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有其民而取其国矣。”(《申不害·大体》)韩非更不必说,他认为:“大臣苦法而细民恶治也。当今之世,大臣贪重,细民安乱,甚于秦、楚之俗,而人主无悼王、孝公之听,则法术之士,安能蒙二子之危也而明己之法术哉!”(《韩非子·和氏》)所以,慎到不同于其他法家,在他看来,作为法治运行的三大主体:君、吏、民,他们之间并未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相反这三者必须紧密配合,天下才能够得到大治。
二、定法者:因道全法,立天子以为天下
在法家的眼里,“治术”永远都是他们最关注,最热衷的话题。无论是治政,还是治民,商鞅、申不害、慎到、韩非他们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观点,并且这些观点也实实在在地影响到了后代的政治构建。他们观点各有不同,但出发点总是一样,那就是统治者到底要怎样才能更好地继续自己的统治。而慎到最重要的观点就是:因道全法。
慎到认为,一个好的统治者,需要做到两点:一为无为,一为因循。与道家出世的无为观不同,慎到作为法家是积极入世的,他只是借用黄老道家的“无为”概念来解释自己的学说。慎子对“无为”有这样的阐释:“天有明,不忧人之暗也;地有财,不忧人之贫也;圣人有德,不忧人之危也。天虽不忧人之暗,辟户牖必取己明焉,则天无事也;地虽不忧人之贫,伐木刈草必取己富焉,则地无事也;”(《慎子·威德》)关于这段话,慎懋赏这样解释:“天之明无私照,而何忧于暗,地之利足以养民,而何囿于贫。”(《慎子集校集注》,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4页)按照慎到的说法,天有日月星辰,能普照万户;地有草木虫鱼,能滋养众人,那统治者有什么能够国治民安?答案显而易见,那就是靠刑名法术。反过来讲,慎到认为万事万物如果没有可靠的凭借,就不能取得成功,慎到自己也举例:“毛嫱、西施,天下之至姣也。衣之以皮倛,则见者皆走;易之以元緆,则行者皆止。由是观之,则元緆色之助也,姣者辞之,则色厌矣。”(《慎子·威德》)就算自己是西施,没有好看的衣服穿在身上,那也不能吸引行人驻足观看。这也就说明了统治者只要依靠法术,就可以无为而治,坐享太平。慎子对此有一大段总结的话,可以完整地表达出此种观点:“古之全大体者,望天地,观江海,因山谷。日月所照,四时所行,云布风动。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不洗垢而察难知,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不急法之外,不缓法之内。守成理,因自然。祸福生乎道法,而不出乎爱恶。荣辱之责在乎己,而不在乎人。故至安之世,法如朝露,纯朴不欺,心无结怨,口无烦言。故车马不弊于远路,旌旗不乱于大泽,万民不失命于寇戎,豪杰不著名于图书。不录功于盘盂,记年之牒空虚。故曰:利莫长于简,福莫久于安。”(《慎子·逸文》)当然,慎子认为要实现无为而治,君主所倚靠的法必须是善法。
定法者如何才能制定出善法,或者说什么样的法才能成为统治者统治的利器呢?慎到认为法是客观自然的东西,是人类社会实践的产物,它取之于人也用之于人,受到自然客观规律地约束:“法非从天下,非从地出,发于人间,合乎人心而已。”(《慎子·逸文》)慎到认为,这样的法必须因循天道:“天道因则大,化则细。因也者,因人之情也。人莫不自为也,化而使之为我,则莫可得而用矣。”(《慎子·逸文》)值得注意的是,慎到所言的“天道”不同于儒家心性论中所言的“天道”,也并非“赏善罚恶”的意志之天,而是指类似于昼夜更替,四季变换的自然规律。慎到认为,因循天道的政治实践就体现在制定合乎世俗人情的法律上,他认为:“故用人之自为,不用人之为我,则莫不可得而用矣。此之谓因。”其次,慎到还认为善法不仅要因人情,还要因国情,根据不同时期的需要来修改和更新法律:“故治国无其法则乱,守法而不变则衰,”这一点看法在所有的法家思想者那里其实都有所体现,《商君书》中就有:“治世不一道,便国不用法古。”(《商君书·更法》)之说;《韩非子》中也有云:“世异则事异。”(《韩非子·五蠹》)审时度势,强调效用,这几乎是所有法家思想家的“通识”。
总而言之,慎到认为,作为定法者,要顺天应时地来制定法律,只有上合于国家利益,下合于风俗民情的法,才能成为统治者所能倚靠的统治利器,实现政治的无为而治,社会的长治久安。
三、司法者:执法严格,立公废私
司法者,在这里不仅仅是指掌管法律和刑讯审问的官员,还包括全部的行政官员和地方具有管理任务的族长等。相比于申不害和韩非,慎到似乎对政府官吏的关注并不那么热衷,在统治者该如何处理与大臣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和统治者应当如何正确使用官吏的问题上并未作深入的讨论。究其原因,主观上慎到作为法家“势”治说的代表者,其关注点在于君主如何借助“势”来有效地管理国家,而官吏管理则属于“术”的范畴,慎子的关注点并不在这里。客观地来讲,由于《慎子》一书在历史流传多有遗失,完整性的欠缺也导致我们很难一窥慎子思想的全貌。但这并不代表慎子没有关于吏治的观点,从现今能看到的《慎子》一书中,慎子的吏治思想也不容忽略。
首先,司法者的任务,慎子认为有二:其一为以身作则,依法办事;其二便是宣传,引导,教育百姓知法、守法。关于以身作则、依法办事这一方面,体现在慎子彻底、完善的法治观上。慎子认为上至天子,下到黎民百姓,都应该受到法律的约束和制约,反对法外开恩,这样法治的适用范围和约束力才能有明确的界限。举国上下,一断于法,举国官吏,依法办事,这样法治才能真正具有严肃性和神圣性,不惧任何势力的挑战。慎子云:“故智者不得越法而肆谋,辩者不得越法而肆议,士不得背法而有名,臣不得背法而有功。我喜可抑,我忿可窒,我法不可离也;骨肉可刑,亲戚可灭,至法不可阙也。”(《慎子·逸文》)便是说明了官吏具有以身作则、依法办事的责任。其二,慎子也注意到了,法条政令自上而下传入社会,必须经过官吏们的普及与引导,让民众能够知法守法,继而成为民众的日常行为准则。道家思想家们曾对慎到这样的行事准则做出了评价:“推而后行,曳而后往。若飘风之还,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全而无非,动静无过,未尝有罪。”(《庄子·天下》)这也从侧面论证了慎到“徐徐图之”的思想风格,慎到显然意识到在法令颁行之初,如果不加考虑雷厉风行地进行社会法治,便会有很多人因为不熟悉法律而受到刑罚的处罚,这是不得民心的策略,不利于法治的稳固建立,为了更有效率地建成法治社会,官吏们便担负起了宣传引导的责任。
其次,司法者的目标,便是通过执法建立起“立公废私”的群体意识。慎到认为当今乱世,混乱的根源就在于社会缺少标准,在标准的缺失下社会公平便不能得到保障,从而激起社会动荡,威胁到君主的统治。而有道之法能够撑起这一标准,官吏可以成为一盏天平,依据法的标准将民与民之间的利益公平化,在平等的“公”之外,任何人的“私”都不能得到满足。慎到云:“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慎子·威德》)公正,公信,公审,公义,构成了慎到理想中的法治社会样貌,成为国家政府司法者们的最终目标。
四、役法者:趋利避害,护法成势
役法者,便是黎民百姓。同儒家人性善恶之争不同,法家在对人性的讨论中并未提及过人性的善、恶问题。即便是上世纪谷方、张申等学者所倡导的法家“自然人性”论,也未在法家典籍中有过只言片语的记载,法家思想家们似乎都在刻意地回避这种带有强烈儒家色彩的思考模式和价值判断。对人性的考察,法家探讨最多的,还是在跳出善恶纠缠的人情问题上,慎到也不例外,他对趋利避害的人情有着深刻的认识:“人,莫不自为也。”慎到认为利益主导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世间人情,千变万化,始终都难逃一个“利”字,即便是血肉之亲,兄弟之情也不例外:“家富则疏族聚,家贫则兄弟离,非不相爱,利不足相容也。”(《慎子·逸文》)但是,历史上舍生取义的人大有人在,针对这样的人,慎到认为:“能辞万钟之禄于朝陛,不能不拾一金于无人之地;能谨百节之礼于庙宇,不能不弛一容于独居之馀。盖人情每狎于所私故也。”(《慎子·逸文》)在慎到看来,做出舍生取义行为的人,只是暂时地压抑住自己的好利之心,但其本身绝不是不好“利”之人。慎子虽然列举出了这种残酷的现实来论证人情好利的观点,但与儒家不同,他未有对这种唯利是图的人情做出价值判断。慎到认为趋利避害人情的存在本就合理,人人都好利恶害,但每个人却善恶各有不同,这之间并未有直接的关联,慎子举例说:“匠人成棺,不憎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慎子·逸文》)做棺材的工匠并非真的想人死,而是有人死他才能把棺材卖出去,不能因为工匠做了棺材就把他当做恶人。通过这个例子,慎到说明了“逐利”本身是不具有善恶性的。如何利用“趋利避害”的人情来管理百姓,治理国家,才是法家最关注的话题。慎子认为,人情不能改变,因此必须“贵因而忌逆”:“寄治乱于法术,托是非于赏罚,属轻重于权衡。不逆天理,不伤情性。”(《慎子·逸文》)通过法治,用利来驱动百姓,用刑来禁止百姓,这样全国上下令行禁止的同时,各方的利益才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
慎子还注意到,君民之间从社会安定的角度来说,利益是一致的。天下平民众多,如果没有一个人能够发号施令,统领百姓,那社会必将一片混乱;反之,统治者在领导众人,设计一套合乎民情的法令,法令保护百姓利益,也维护统治者自身统治,社会便能安定,民众因为新法能够合法地保护自己的利益,安居乐业。民众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能够成为当前法治的拥护势力,这样无形中也能让君主之“势”得以壮大。慎子云:“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利一人也。曰:天下无一贵,则理无由通,通理以为天下也。故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立官长以为官,非立官以为长也。法虽不善,犹愈于无法,所以一人心也。”(《慎子·威德》)便是这样的道理。
慎子从定法者、司法者、役法者三个主体来设计出一套理想法治社会的蓝图,这三者互相影响,缺一不可,如果能各自安守其职,那么国家政治便能有序运转。慎子思想中的“人情自为”、“立公去私”、“执法必严”等思想体现了他积极的、彻底的法治观。需要注意的是,慎子言“势”最多,认为天子之势取之于民,所以要立天子以为天下,也肯定“法”的作用,却唯独对后世不断诟病法家思想中的帝王之“术”讨论最少。这也使得慎子思想在先秦法家各派中积极意义最大,其思想不仅成为日后韩非集法家思想之大成的养料,也在以后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应当给予充分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