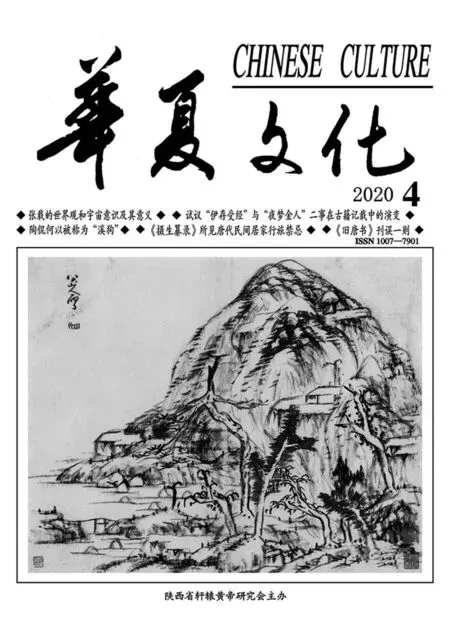张载的世界观和宇宙意识及其意义
□谢阳举
张载是北宋伟大的新儒家学者,从范畴史角度来说,宋明理学本质上是研究“天道性命”的学问的。作为置身于二十一世纪的后来人,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天道性命”的学问?
笔者以为,这种学问的核心相当于今人所谓的世界观哲学。作为一位返本开新的儒学思想家,张载面临的首要课题就是要驳难佛、老并弘扬儒学固有的世界观。这套世界观的基础就是所谓“乾坤之道”,为此就需要重构切合于时代需求的新儒学世界观。
在“北宋五子”中,张载最独特的贡献就是针对释、老简明而精要地阐述和重演出理学家眼中的世界观,这在《西铭》和《正蒙》中得到高度浓缩的体现。《西铭》是从其殚精竭虑的代表作《正蒙·乾称》的首章析出成篇的,可谓张载的得意之作。张载将其抄录、张贴在西窗之上,名之为《订顽》,后来程颐将其改称为《西铭》。《西铭》一篇,区区三百字,一般被认为是张载思想的精髓所在。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它集中地反映了张载的宇宙意识和有机主义世界观。与同时代的理学家二程兄弟相比,张载不持绝对主义的天理观,没有将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没有落入禁欲主义伦理观的窠臼,保持了原始儒家立足于人文价值准则的基本特色。与原始儒家相比,他在批评释、老的过程中,上溯中国古老易道的天地人三才统一的思辨原理,发展了《中庸》将本体、性命、认识和伦理贯通起来的有机世界观。张载的世界观坚持以天道、气化为本源,属于朴素的唯物论,其意在扫尽“空无”,反对所谓老子的“有生于无”,又拒斥佛教的因缘幻化色彩,首次在气论与“二端”辩证法的基础上重新统合了世界、认识、伦理和人心、性命等等,搭构出多维度统合、庞大深密的新儒家世界观。根据张载的诠释,这个世界观的纲领在于理一分殊、穷理尽性、参赞化育。
今天我们读《西铭》,不难发现,它的逻辑结构包含两部分:其一,论宇宙变化之道,识万物之性,《西铭》称之为“穷神”、“知化”;其二,论“与天为一”,成性成身,《西铭》称之为“善述其事”、“善继其志”、“存心养性”。后者的完成被张载称为配称为“天地的孝子”的充分且必要的条件,这是《易传》所言的“大人之德”的另一种表述,也正是正统儒家历来标榜的效法天地、参赞化育、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中国文化根本精神。严格说来,这些观点在先秦就被分散地提出来了,因此并不属于原创性思想,可以说是对《周易》、《中庸》之学所蕴含人文理念地激活和某些诸子思想片断地整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是张载使它们清晰化并具有了应对佛老的文化力量。在当时,这对诊治文化上三教冲突和中国士大夫文化心理上的“世界观紊乱症”(借用荣格语)起到了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儒家创始人孔子赞成子产“天道远、人道迩”的说法,立足于人伦秩序或曰先王礼道展开思考,其学术的主导特色是直接亲证的人伦本位意识。到了张载,由于释、老有关生死、本体思想的交侵,新儒家必须拿出更为高远有效的论证,这就是张载从宇宙意识开始运思的原因。张载自己说过:《订顽》之作“只欲学者心于天道,……”(《语录》上),“理不在人而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如此观之方均”(同前)。《西铭》指出:人是渺小的,也很幼稚,表现在他们不知道自己与万物浑然联系的实况。这就为突破人的有限性,从更广的范围来解决人世、人道的问题埋下了伏笔。从这个出发点看,张载或许可谓他所批评的老氏(老子)、庄生(庄子)的后代。儒道会通是以“天人之际”为重要媒介的,两家交叠有个共同归趋,都希望认识天人的相关性,都渴望统一天道和人道这对深层矛盾。当然,张载是回到《易传》、《中庸》的儒家标志性立场。他创造性地解释说《系辞》的“系”字反映了三才之道的内在贯通,“系之为言,或说《易》书,或说天,或说人,卒归一道,盖不异术,故其参错而理则同也”,因此在他看来,“老子言‘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此是也;‘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此则异矣。圣人岂有不仁?所患者不仁也。天地则何意于仁?鼓万物而已。圣人则仁尔,此其为能弘道也”(《系辞》上)。张载正是站在原始儒家的立场上吸收释、老的思辨以反对释、老,重建新儒家的世界观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张载所辟的并非真释、老,例如,他批老子的世界观错在主张“有生于无”,这是贵无论玄学歪曲诠释老子思想的结果;他批释家障于心法、鼓吹万物虚幻,也是受到当时简单化地批判佛学的影响所致。
张载从易理出发,贯通天道人心,邃密地构建了他的物质和精神相协调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和《易》一样,是无穷变化的世界观,是始终“有人”的世界观。他说:“不见易则不识造化,不识造化则不知性命,既不识造化,则将何谓之性命也”?“易乃是性与天道,其字日月为易,易之义包天道变化”(《系辞》上)。为辟佛老,他力主返回易学,要求用虚实、形上形下范畴代替有无这对范畴,希望从思维方式上返归儒家精神。他断言“无”中不能生“有”,即变化不是生灭,变来变去都是“气”的变化。从直观上看,这难以回答宇宙生成这种类型的变化和通常所见的普通事物变化类型的不同。为此,他从逻辑上提出,不论虚空、气体还是一切有形事物都是气的不同形态而已。气本身也是有分别的,一是太虚之气,它是自为根本的,所以叫“气之本体”,由阴阳未分的气组成,是处于完美和谐状态下的和气一团。易理有“太极”,是无体之体,张载将其改造为“太和”,认为它是万物本源。太和也就是“太虚”之气,张载强调太虚是不能理解成绝对无气的虚空的。二是分阴分阳、阴阳比例不同的气。张载认为气有一个根本的特点,就是阴阳消长、运动不息,他叫“气化”,气化的形式表现就是道。世界肇始于太虚,最终不出乎返回太虚罢了,这是“不得已而然”(《正蒙·太和》)的。关于世界是动态世界的根本原因,张载认为是由于气本来就有复杂的相互作用态势,“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缊、相荡、胜负、屈伸之始”(《正蒙·太和》)。阴阳相反相成的作用是气运的核心形式,张载称之为“有对”(同前),这是世界变化的最基本原因,也是世界变化的微妙所在,“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两故不测。两故化,推行于一”(《正蒙·参两》);“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两体者,虚实也,动静也,聚散也,清浊也,其究一而已”(《正蒙·太和》)。张载所说的“神”不是鬼神的神,而是指气固有的运动属性,其实就是变化莫测的意思。根据这些论述,张载认为,万物虽多,“其实一物”,不出乎阴阳二端之理(《正蒙·太和》);“无所不感者虚也,感即合也,咸也。以万物本一,故一能合异;以其能合异,故谓之感;若非有异则无合。天性,乾坤、阴阳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万物,所受虽不同,皆无须臾之不感,所谓性即天道也。感者性之神,性者感之体。惟屈伸、动静、终始之能一也,故所以妙万物而谓之神,通万物而谓之道,体万物而谓之性”(《正蒙·乾称》);天地间“物无孤立之理”(《正蒙·动物》),世界是以气化感应相互作用的互联网络关系体。
宇宙意识开启了张载的物质世界观,后者又充实了其宇宙意识。正是基于对世界深层气化运动之道的认识,张载说:“明天人之本无二”,“天人异用,不足以言诚;天人异知,不足以尽明。所谓诚明者,性与天道不见乎小大之别也”(《正蒙·诚明》)。显然,使张载认为自己突破了老庄提出的天(道)人(道)关系哲学之谜的原因就在于,张载自认为真正识得了气化之道,也就是“性”这个万事万物、一切变化的共同本质,“性者万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君子所性,与天地同流异行而已焉”(《正蒙·诚明》)。《西铭》对人与他者关系的概括就是:“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这可以说将思孟学派“尽心知天”、诚明呼应的观点落到了实处。张载称这个宇宙意识的扩充为“大心”,与释、老不同,他主张“人本无心”,真正的心就是“合天”的过程,“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物有未体,则心为有外。世人之心,止于闻见之狭。圣人尽性,不以见闻梏其心,其视天下无一物非我,孟子谓尽心则知性知天以此。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这是具有相当深广度的超越之心。在思孟学派和《易传》那里,“天”带有很强的外在目的论、道德价值论色彩,这使得早期儒家伦理似乎多少有点有用无体,经过张载的改造后,天人关系向着心性论化的道学转变,认识论的色彩明显得到深化,这就巩固了儒学所肯定的人的内在价值论的原则。《西铭》之后,程颐、朱熹曾经偏向于沿着儒家宗法伦理诠释张载的文字。在笔者看来,“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八个字,蕴含了一种自我超越、拥抱世界万物的伦理觉悟,它标志着新儒家世界观和宇宙意识的成熟,今天仍然具有积极价值。在笔者看来,儒学和理学如果大兴于未来,还应该回到张载再出发,起码张载是绕不过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