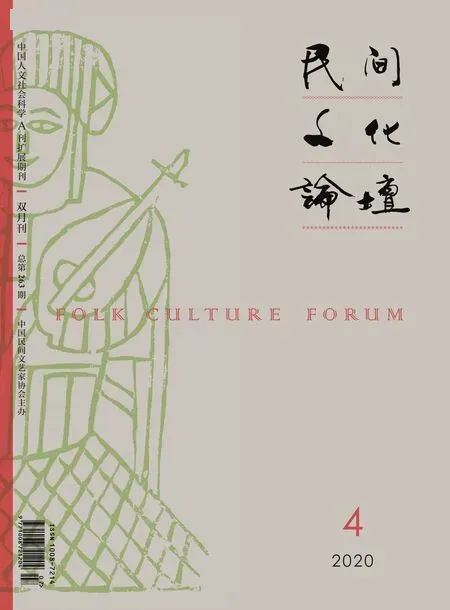新文艺•民族遗产•学术研究
—— 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三重旨向
漆凌云
一 、 民间文学价值新定位:“搜集整理”论争溯源
“搜集整理”研究是十七年时期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热点话题a相关论著详见刘守华:《1949—1966:中国民间文艺学》,《通俗文学评论》,1996年第3期;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施爱东:《民间文学:向田野索要什么》,《中国民间文化的学术史观照》,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71—206页;毛巧晖:《民间文学批评体系的构拟与消解——1949—1966年“搜集整理”问题的再思考》,《西北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等等。。从现有资料看,王国栋1935年发表的《谚语的搜集和整理》b王国栋:《谚语的搜集和整理》,《师大月刊》,1935年第22期。是民间文学领域最早关于搜集整理的讨论。他主要从民间文学学科视角讨论谚语的整理问题,但并未在学界产生较大影响。如何搜集?为何整理?如何整理?是十七年间“搜集整理”论争的关键。从民俗学学术史来看,忠实记录是民俗学人一以贯之的要求。周作人1914年的《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要求:“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童话可以文言叙说,但务求与原本切近,其中语句有韵律如歌词者,仍须逐字照录,如蛇郎之宁可吞爹吃,不可嫁蛇郎等是。”a周作人:《征求绍兴儿歌童话启》,《绍兴县教育会月刊》,1914年第4期。周作人主张的“须照本来口气记述”“务求与原本切近,其中语句有韵律如歌词者,仍须逐字照录”与1950年代搜集整理讨论中关于忠实记录的本意大体相近了。1918年《北京大学日刊》上发布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亦注明“歌辞文俗,一仍其真。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改为官话。”b《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9月21日第5版。可见保留民间文学的“原汁原味”是民俗学人的共识,《歌谣》周刊的发刊词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c《<歌谣>周刊发刊词》,《歌谣》,1922年12月17日第1版。。刘枝后来对民间故事的采录过程进行详细阐发,“不能听人家说一句,你写一句;等你写完了,或是说一句一停,人家再说,要是叫人家说一句你停一句,这事恐怕除了你自己的老婆或亲人外,人家没这工夫耐这麻烦!要是听一句写一句,除非先学会速记,后再搜集故事不可;况且说者看你在旁写他所说的,他又不好意思说了,听完了再写,又恐不免有遗漏和谬误的地方……故事虽不能听一句写一句或是叫说者说一句一停;但可当他说时执笔记其大概,或者避免说者看你写他所说的嫌疑,索性等他说完你再写,怕说完又遗漏和谬误的地方,不妨多校正几次。”d刘枝:《对于搜集民间故事的一点小小意见》,《歌谣》,1924年第54期,3—4版。董作宾在《征求民间文艺简章》中进一步指出“记录的方法,韵语如歌谚等,须一依口语写出,其中方言俗字,可用罗马字或拼音字母,注明其音韵,宜详释其意义,勿随意改成国语或文言;散文如神话童话等,则以宜质朴的国语传写之,遇有韵语处,仍当尽量保持本色。又该材料采自何处,通行于何地,并须一一注明。”e《征求民间文艺简章》,《民间文艺》,1927年第2期。
忠实记录是学术研究的基本要求,但不同的学科专业,记录的水平各有差异,大体形成三种模式:一种是民俗学模式,以《歌谣》《民俗周刊》登载作品为典型;另一种是人类学模式,如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报告》f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陈志良的《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g陈志良:《广西特种部族歌谣集》,《说文月刊丛书》,桂林:科学印刷厂,1942年。;最后一种是语言学模式,如李方桂的《龙州土语》h李方桂:《龙州土语》,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年。李方桂在序言中介绍了采录方法:“这些故事中的第1、3、4、5、11是先用Fairchild记音机记在铝片上,然后再让发音人一句一句地慢慢说出来用笔记,回来又重新听写改正。其余只是发音人一面说,著者一面笔记。有些字发音人认为龙州乡下常用的字而城里不大用的,我也都注下来……这些故事可以供留心民间故事的人参考。”中记录的民间故事和歌谣均配有国际音标。学者们的讨论也大多集中在如何做到忠实记录,并未涉及如何整理的问题。i万建中、李琼:《20世纪民间故事书写研究评述》,《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搜集整理问题论争实践源于延安时期对民间文学社会价值的新认知。
民间文艺自晚清以来就受到政治人物的关注,如晚清改良派和革命派均曾借助民间文艺形式宣传政治主张。j详见钟敬文:《晚清革命派作家对民间文学的运用》《晚清改良派学者的民间文学见解》,《钟敬文文集》(民间文艺学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259—352页。中国共产党历来对民间文艺的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青睐有加。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注意到民间文艺是宣传发动群众参与革命的有力工具。k郑长天:《毛泽东与民间文学》,《湘潭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1938年4月,他在鲁迅艺术学院发表讲话时说:“到群众中去,不但可以丰富自己的生活经验,而且可以提高自己的艺术技巧。夏天的晚上,农夫们乘凉,坐在长凳子上,手执大芭蕉扇,讲起故事来,他们也懂得胡适之先生的八不主义,他们不用任何典故,讲的故事内容却是那么丰富,言辞又很美丽。这些农民不但是好的散文家,而且常是诗人。”a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24—125页。作为政治领导人的毛泽东对民间故事的讲述者给予了“散文家”“诗人”等崇高评价,这在中国文学史上并不多见。毛泽东还将民间文艺视为民族文化遗产、新民主义文艺创作的重要宝库,“对于中国和外国过去时代所遗留下来的丰富的文学艺术遗产和优良的文学艺术传统,我们是要继承的,但是目的仍然是为了人民大众。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但这些旧形式到了我们手里,给了改造,加进了新内容,也就变成革命的为人民服务的东西了。”b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艺论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7页。毛泽东格外重视民间文艺的社会价值,视为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号召知识分子深入群众,学习老百姓的语言,借助旧形式(民间文艺)发挥社会动员作用为政治服务。《讲话》发表后,民间文学采录工作在延安广泛开展,成果有《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陕北民歌选》《刘志丹的故事》,等等。c详见贾芝:《延安文艺丛书·民间文艺卷》,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8年。
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学人对民间文艺的认识大多是从文学价值、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展开论述,毛泽东则进一步将其提升为中华民族的文学艺术遗产,还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他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赋予劳动人民以革命性和先进性的属性,把传统文化思想内容层面的“精华与糟粕”分别对应于劳动人民和封建统治者,明确提出:“把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通过“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从而建立起“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d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毛泽东的“阶级分析法”和“精华—糟粕”二元观对此后民间文学的采录和研究产生广泛影响e如延安文艺代表人物周文在分析四川机智人物张官甫的故事就指出,“在民间流传的故事,不一定全是从民间产生的。其中有许多固然是很好的,但有些却是不好的,反民众的,即是产生于统治者,或者受了统治阶级教养的人编造过传给民间的。”详见周文:《再谈搜集民间故事》,《大众文艺》,1940年第5期。。
延安时期的民间文艺采录者多为文艺工作者,如柯蓝、康濯、董均伦、李季等。他们实地采录民间文艺作品的目的在于通过思想内容和艺术价值的筛选,把具有教育宣传价值的作品加工整理后在民间推广,从而实现民间文艺的社会价值。如柯蓝采录的民间故事集《咱们的老高》中,十五篇是作者在陕北农村搜集民间故事的一部分,“(五篇)是收集现实材料,采用民间故事、传说的形式写出来的。其他十篇写的时候,连结构也经过了很大的改动,和原来的样子也大不相同。这便是我要把这十五篇民间故事收集出版的第一个原因。因为我这种尝试,是企图使新文艺与民间形式结合的尝试,是企图使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尝试,虽然这些尝试并不很成功。”f柯蓝:《咱们的老高》,上海:群育出版社,1949年,第1页。可见,文艺工作者采录民间故事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李束为也谈到整理民间文艺作品的必要性,“这些经过采集与整理出来的民间故事,(或说略加提高的故事),比起原来在群众中流传的未经整理的故事所起的影响大的多了。因为那些未经整理的故事是在一种自然状态下流传,想起什么故事就讲什么故事,并不一定根据当前工作与群众的目前的思想状况加以选择,同时所讲的故事也不一定都是有教育意义的。”a李束为:《民间故事的采集与整理》,《文艺报》,1949年第11期,第8—9版。尽管何其芳在《从搜集到写定》倡导忠实记录原则,“尊重老百姓和他们的作品。首先要忠实地记录。其次,民间文学既是在口头流传,就难免常因流传地区不同与唱的人说的人不同而有部分改变或脱落。我们在采录时,同一民歌或民间故事就应该多搜集几种,以资比较参照……至于民间故事,则因地区与说的人不同而变化更大,当然于一字一句保存原来面目,但也应基本上采取一种忠实于原故事的态度。若系自己改写,那就不算是地道的民间文学,而是我们根据民间文学题材写成自己的作品了。无论民歌、民间故事、民间戏剧,写定时都应附注流传于何地。普通不易了解的土语、事物,以及与之有关的一切也都最好加以说明,以便旁人阅读或研究。”b何其芳:《从搜集到写定》,《民间文艺新论集》,北京:中外出版社,1950年,第177—178页,该文写于1946年11月10日。但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采录民间文艺作品,一方面是学习民众的语言艺术,“直接地就必须从民间去获得,间接地就必须从民间文艺获得”;另一方面“利用旧形式并不是停止于旧形式,而正是要从思想上、艺术上加以改造,在批判地利用和改造旧形式中创造出新形式。”c周扬:《对旧形式的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中国文化》,1940年创刊号。,从而为政治服务。 可见,延安文艺工作者深入民间采录民间文艺作品重在为老百姓提供精神食粮,发挥宣教功能。
二、 加工取向与学术本位:新中国初期的搜集整理论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化政策的核心路线是围绕“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展开的。伴随着劳动人民社会地位的变化,民间文艺地位也发生反转,不仅是“新的人民的文艺”d周扬:《新的人民的文艺》,北京:新华书店,1949年。,还是“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e钟敬文:《口头文学:一宗重大的民族文化遗产》,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部,1951年。。1950年成立的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是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上的大事件。民间文艺研究会融合了延安和国统区的民间文艺学人,学术理念各有差异,但在资料搜集上达成以下共识。《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号召搜集民谣、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年画、弹词等文艺资料,要求搜集资料时注意:
“1. 应记明资料来源,地点,流传时期,及流传的状况等。2. 如系口头传授的唱词或故事等,应记明唱者的姓名、籍贯、经历、唱讲的环境等。3. 某一作品应尽量搜集完整;仅有片段者,应加以声明。4. 切勿删改,要保持原样。5. 资料中的方言土语及地方性的风俗习惯等,须加以注释。6. 美术品最好是寄原作,唯摄影图片或精确的复制品亦可。7. 搜集资料时,倘有何种重大困难,个人难于解决者,可向本会提出,本会当在可能范围内帮助解决。”f《本会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北京:新华书店,1950年,第105页。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征集民间文艺资料办法》不仅明确提出民间故事的采录要保留原样,还要注明资料、地点、流传时期、流传状况、唱讲的环境、保留方言土语及地方习俗。比延安时期的民间采录工作要求更为科学、翔实,关注到了民间故事的传承语境。新中国建立后,民间文学的采录取得重大成绩,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民委系统及各省市均有诸多优秀成果。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少数民族地区的作品得到挖掘,如《爬山歌》《天牛郎配夫妻》《白族民间故事传说集》《白族民歌集》《藏族民间故事选》《南北方民歌选》《召树屯》《阿诗玛》《娥并与桑洛》《刘三姐》《嘎达梅林》《格萨尔王传》《玛纳斯》《江格尔》,等等。a详见刘锡诚:《二十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14年,第640—658页。其中不少搜集成果后来成为少数民族文学经典,进入21世纪后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提出:“广泛的搜集我国现在及过去的一切民间文艺资料,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加以整理和研究。”b《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新华书店,1950年,第104页。这样的表述说明搜集、整理和研究是三项互相关联的工作。在当时的会领导人看来,民间文艺作品的采录主要还是为社会主义新文艺服务的。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提出“今后通过对中国民间文艺的采集、整理、分析、批判、研究,为新中国新文艺创作出更优秀的更丰富的民间文艺作品来。”c周扬:《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周扬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0页。郭沫若也主张“我们不仅要收集、保存、研究和学习民间文艺,而且要给以改进和加工,使之发展成新民主主义的文艺”。d郭沫若:《我们研究民间文艺的目的——在本会成立大会上的讲话》,《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1950年,第9页。《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也明确提出:“在搜集、整理和研究中国民间的文学、艺术,增进对人民的文学艺术遗产的尊重和了解,并吸取和发扬它的优秀部分,批判和抛弃它的落后部分,使有助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建设。”e《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章程》,《民间文艺集刊》(第一册),新华书店,1950年,第104页。也就是说,对采录到的民间文艺作品加以适当改造为社会主义新文艺服务,是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内容。当时采录、出版的民间故事科学性暂且不论,但社会价值显著,面向大众出版的具有鲜明人民性和艺术性的民间故事“将新的社会主义伦理价值扩散到全国各地域、各民族,加速社会主义‘新儿童’的塑造。”f毛巧晖:《1949—1966年童话的多向度重构》,《上海师范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
文艺创作取向与学术研究取向差异甚大,所以钟敬文对当时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中的任意改写情况提出了批评:
在记录和整理的方法上,也有些地方值得我们考虑。有些故事的记录者,拿当前的思想或政策去改串故事的意思和情节,拿现在流行的或个人爱好的文体去改变它固有的叙述,并且大都连一点声明也没有(有的歌谣的记录者也这样做,但是比较少数的)。记录民间故事、歌谣等,必须充分忠实于民众原有的思想和口吻,这是起码的规条。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劳动人民的固有创作(至少有些的创作),是有它自己思想上和艺术上的优点和特色的。一般记录、整理的主要目的,是供给文艺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研究、参考或学习的资料。因此,就必须尽量保持原来的精神和面貌。g钟敬文:《民间文艺学上的新收获》,《新建设》,1951年第1期。
但钟敬文的学术本位观点并未改变当时民间故事搜集整理中的改写状况,创作取向问题依然存在,并在1956年形成了一次大争论。
这场争论是在繁荣科学和艺术必须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背景下展开的,导火索是刘守华发表《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一文。此后朱宜初、刘魁立、巫瑞书、陶阳、毛星、贾芝等学者也纷纷加入讨论,董均伦、江源、陈玮君、张士杰等民间故事采录家也撰文回应,讨论成果汇集在《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h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搜集整理问题》(第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62年。中。刘守华对改写后选入初中语文课本的《牛郞织女》及李岳南所写的评论提出批评,指出:“由于我们许多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同志对这种工作采取了一种简单的、粗暴的态度,忽略了整理民间故事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即保持民间故事原有的风格和艺术特点”a刘守华:《慎重地对待民间故事的整理编写工作——从人民教育出版社整理的<牛郞织女>和李岳南同志的评论谈起》,《民间文学》,1956年第11期。李岳南随后撰文回应。陈纬君把整理和改编混同起来,发表《必须勇敢地跃进一步》,号召“(喜爱)民间文学的作者同志们,必须勇敢地跃进一步,从内容到形式、风格,要创作些新的来”b陈玮君:《必须勇敢跃进一步》,《民间文学》,1957年第6期。。
刘魁立1957年发表的《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对董均伦、江源夫妇在整理过程中只注重搜集反地主、反皇帝、反封建迷信题材的作品提出批评,指出记录民间文学作品总的原则是:“以珍惜尊重的态度对待每一篇作品、每一句话和每一个词。准确忠实、一字不移——这是对科学记录的第一个要求。不加任何窜改、歪曲、扩大或缩减,如实地全面地提供有关人民创作和生活的材料——这就是民间文学搜集者的基本任务。”c刘魁立:《谈民间文学搜集工作——记什么?如何记?如何编辑民间文学作品?》,《民间文学》,1957年第6期。刘魁立除了提出著名的“一字不移”论,还提出“活鱼要在水中看”的观点,注意“记录民间作品的‘生活’”,还结合自己在苏联采录民间故事情况,对在民间故事采录中如何记录讲述者的语言、手势、表情、异文等问题提出一套比较系统的操作方案。董均伦对刘魁立的“学院派”做法不以为然,结合自己的采录实践指出刘魁立的采录方法缺乏可操作性。
这场论争集中在两大群体间,一方是基层民间文艺采录者,一方是民间文艺研究者。一方侧重将民间故事视为文学作品,一方则视民间故事为科学研究资料,立足点不同,难以达成共识。刘锡诚、陶阳、张文、吉星、毛星、贾芝等民研究会学人都肯定了忠实记录的重要性,要求区分整理、改写和再创作的界限。但大多数还是以文学立场来看民间文学采录工作。毛星的《从调查研究说起》对此次论争做了较完整的学术总结。他肯定了采录民间文学作品的复杂性。
同样一个故事,各个人有各个人的讲法,除了巧拙的不同,对于那些已形成自己独自风趣的高明的故事家说来,各个人又具有各个人的讲述风格。而且,就是同一个人讲同一个故事,这次讲的和另一次讲的,也常常是不完全相同……心情好时,可以讲得眉飞色舞,讲得很细致;心情不好,或者不讲,或者就只讲一个大概,甚至三言两语就把一个故事“交代”了。面对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忠实记录或忠实的整理,很自然地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故事的讲述不那么固定,究竟忠实于一个人某一次讲述呢,还是要忠实于民间的这一个故事。我的看法是,两个都要,后者是目的,前者是基础。d毛星:《从调查研究说起》,《民间文学》,1961年第4期。
毛星结合具体的讲述情境对讲述人、讲述风格进行了较深入探讨,殊为不易。他有丰富的采录经验,认为民间故事的讲述文本尽管不是固定的,但忠实记录是基本原则。对于从事民间故事采录者而言,尽管逐字逐句记录困难,但“从事民间文学搜集整理工作的人,为什么不应该有记录故事的专门技能呢?”他对民间文学作品从讲述现场到写定过程进行较深入的学理分析,同时提出如何才能采录到“民间的这一个故事”。
只讲忠实于民间的这一个故事,不讲要一次次的忠实记录,这里所说的民间的这一个故事,岂不成为抽象的悬空的东西,而这里所说的忠实不是也就失去根据了吗?如果只有一次忠实的记录,就认为把这个故事的民间原貌完全记录下来了,也不妥当。因为除了故事讲述者的巧拙和所讲的粗细,还有这样的情况:讲故事的人由于记忆的错误或别的什么原因,或者把有的内容讲漏了,或者在一个故事中甚至可能把别一个故事误掺进来;而故事在流传过程中,剥削阶级把他们的某一些思想掺入故事中,也完全是可能的;甚至,可能这个讲故事的人,由于种种原因,比如或者他本人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或者他是从剥削阶级那里直接或间接听来的,因而所讲的故事的主题思想和情节内容,与一般劳动人民所讲的差异很大,立场观点和思想感情与一般劳动人民相违背。这样,这一次记录,对于这一个故事的民间原貌来说,它的忠实性就存在着疑问。
毛星指出民间故事的采录需要长时间的深入调查才能获取口承文艺的完整面貌,散发出浓郁的学术探索气息。但他主张的“民间的这一故事”多少带有完美主义色彩,侧重文学性和艺术性的统一,革命性和大众性的统一,剔除剥削阶级的影响。在他看来,“整理加工的目的,是力求最充分地显现出这个故事在民间的最完美的面貌,拭去其他阶级点染在它身上的尘污,集中可以集中的民间对这一故事的一切美的创造……民间的这一个故事,可能已有了比较固定和比较完整的讲述内容,而且存在于当前的一个或某几个故事家的口中。也可能本来有很完整的讲述内容,但现在已没有一个人讲得很完全,有的比较详细地记得这一段,有的则比较详细地记得另一段。另外的或较多的情况是:这个故事的主题思想和基本情节尽管已大致固定,但故事的细节描写,这样的描写的精华,则存在许多人的口中,有的把这一段讲得好,有的则对另一段有更完美的描述,或者这一段昨天还比较粗糙,今天有了新的细致的讲法。这样,这一个故事在现实生活的人民口头实际上并没有集中组织在一起,这就有待于搜集整理者的整理。经过艰苦的搜集整理,这一个故事才能真正成为一个。”a毛星:《从调查研究说起》,《民间文学》,1961年第4期。毛星所说的“这一个故事”应该属于恩格斯在谈典型人物塑造时引用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b李衍柱:《试谈黑格尔所说的‘这一个’》,《外国文学研究》,1978年第5期。恩格斯说:“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一个’,而且应当如此。”,具有典型性和完美性,需要严谨的综合整理才能实现。但就民间故事的讲述实际来看,要采录到完美的“这一个故事”是不大可能的,整理加工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事实上,此后成为民间文学经典的文本皆经过文人的反复加工,诸如《阿诗玛》《刘三姐》《召树屯》,等等。傣族叙事诗《娥并与桑洛》便是在8份原始资料基础上整理而成,“整理本只用了很少的诗行描绘沙铁家的富有;大力删除求神求佛生子的过程,剔除宣扬封建迷信的部分,又适当保留能反映出佛教对傣族人民生活产生过影响的部分诗句;削去对桑洛外貌美的不健康的夸张描绘;选取了桑洛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的情节。而摒弃了表现唯利是图的思想与主题无关的对经商情况的具体细微的描写。这有助于人物形象的完美、主题思想的深化,也符合傣族人民歌颂自己的理想人物的愿望。这无疑是做得正确而且必要的。”c刘廷珊、傅光宇、马永福:《对<娥并与桑洛>整理工作的一些看法》,《民间文学》,1962年第1期。
论争的最终结果体现在1958年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报告上提出的十六字方针:“全面搜集,重点整理,大力推广,加强研究。”d贾芝:《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1958年7月9日全国民间文学工作者大会报告》,《民间文学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96—100页。十六字方针体现了特定学术语境下对民间文艺的采录要求,注重民间文艺的政治教育功能,要求“在全面搜集的基础上,有重点地进行整理编选。先整理对建设社会主义帮助大的,富有教育意义的作品,例如目前的新民歌,优美的民间故事、在群众中流传最广的歌颂英雄人物的民间说唱以及优秀的长篇叙事诗,等等”e同上,第 97 页。。内容上对革命内容的强调,导致此后民间故事采录注重革命传说,忽略幻想故事等传统民间故事。同时要求采录时保留民众生动的语言。另外,也关注民间故事的科学研究价值,指出“首先强调忠实记录。民间文学工作需要树立科学态度、科学方法。因为把群众的作品忠实地记录下来,是一切工作的基础。”a贾芝:《民间文学论集》,北京: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99页。
尽管“忠实记录、适当加工”,既强调了民间文学采录工作的科学性,同时也强调了民间故事的教育功能。由于当时从事民间故事采录工作大多是缺乏专业素养的基层文艺工作者,对采录的故事作品进行或大或小的加工现象比较普遍。张士杰在介绍自己采录经验时谈到,“在开头老渔翁得宝的一段,讲者说的比较简单,我就把这一段做了详细的描写。我认为,这更能突出老渔翁的勇敢机智和‘宝贝不是凭空得到的’(原述时就说明这点,只是不突出)。在渔翁连钓金鱼、砸水珠、变金豆子一节中,讲述者只说渔童连钓带唱,我就根据这情况让渔童唱出了八句歌谣。我认为,故事本身就很优美,特别是在这一节里,如果要渔童唱起来,不就更加强效果了吗?我就给加了八句歌谣。”b张士杰:《我对搜集整理的看法》,《民间文学》,1959年第12期。所以就当时出版的民间文艺作品而言,忠实记录的作品并不多,但我们如果翻阅1960年代广西、湖南、云南、贵州等地由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民委等单位组织采录的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作品油印本资料,依然能看到“忠实记录”的鲜明印记。
三、“搜集整理”与中国民间文学集成
“搜集整理论”论争过后的1958年,全国各地兴起了“新民歌”运动,民间文学界呈现向主流文学挑战的“越界”现象。c毛巧晖:《越界:1958年新民歌运动的大众化之路》,《民族艺术》,2017年第3期。受此影响,民间文学界的搜集整理的“文学创作”取向愈发显著,出现全民创作的高潮,日渐偏离学术本位,直至改革开放时期才实现反转。
(一)确立学术本位:《泰山民间故事大观》的采录实验
1978年4月,钟敬文、贾芝、毛星、马学良、吉星、杨亮才等开始筹备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在民间文学采录实践中,忠实记录与慎重整理的尺度如何把握依然没有达成共识。1980年5月,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委派陶阳、徐纪民、吴绵三人在泰安地区进行“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一个实地试验,成果结集为《泰山民间故事大观》。陶阳等人的具体做法为:
(一)依靠地区文化部门的领导;
(二)全面搜集、全面调查(包括口头记录与查考历史文献);
(三)利用录音机,同时笔记;还要力求做到有闻必录;
(四) 记录同一母题故事的异文;
(五)研究每一尊神的来历,对故事的异文作比较研究和有关理论上的探索。d陶阳等:《泰山民间故事大观》,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3页。
他们以学术本位来采录,将采录到的故事分为“原始记录稿较完美的故事”“同一母题的异文与‘综合整理’的故事”“同一题目又各自独立的故事”,特意把录音记录稿同加工过多的整理稿做比较。如张建新讲述、吴绵录音的记录稿《吕洞宾给王母娘娘拜寿的故事》和搜集者加工稍多的整理稿《瑶池会》两相比较,“发现记录稿故事井井有条,层次清楚,易懂易记,有情趣 。而加工多的整理稿《瑶池会》则打乱了原来的叙述方式,把原来的述论式变成了吵架式。尽管文笔流畅,故事却大为逊色。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整理民间传说故事,还是尽可能保持原故事的结构和叙述方式为好。”a陶阳等:《泰山民间故事大观》,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第211页。因此,他们提出整理工作要注意保持“口头性”,录音稿优先。b同上,第 210 页。“泰山民间故事调查实验”注重查考历史文献记述,记录各种母题的异文,保留方言特色,通过注释和附记阐发讲述文本的相关信息,是当时“忠实记录”的样板,为此后进行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工作积累了有益经验。
(二)科学整理方法与原则的确立:《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的出台
1984年5月28日,文化部、国家民委、中国民研会联合发文编辑出版包括《中国民间故事集成》在内的三套集成。《中国民间文学集成》的编撰旨在“汇集和总结全国各地各民族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成果,保存我国各族人民的口头文学财富,继承和发扬我国各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让民间文学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同时也为民间文艺学和社会科学领域中有关学科的研究,以及文学艺术创作的借鉴提供较完整的资料”c《关于编辑出版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的意见》,《中国口头文学遗产数字化工程全纪录》,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4年,第62页。。编撰宗旨体现了民间文学采录的文化遗产保护价值、科学研究价值、文艺创作资料价值和社会价值,要求利用录音、摄像和录像技术进行采录,要尤其强调在普查基础上,“三套集成各卷本要严格注意科学性、全面性和代表性,选入的作品,一定要符合‘忠实记录、慎重整理’的原则,避免失真。要具有高质量,真正反映各民族劳动人民口头文学的原貌。”d同上。三套集成的编撰把科学性列为首要原则,但口承文艺是处于生活层面的演述,转换成书面文本需要经历寻找讲述人、建立田野关系、全面采录等多重程序,在具体实践中科学性的实施难免出现各种问题。为此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在1987年5月专门出台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对搜集的方式和方法、记录的原则和方法进行翔实解答,着重指出“民间文学作品一经采集和记录,就作品本身来说,便离开了口头讲述环境,进入了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另一种流传过程。这一流传过程,是以书面形式发挥它的资料和阅读作用。在这个从口头到书面的过程中,为使口述的原材料更好地呈现在书面上,就需要对原材料进行一定的整理工作。它同样是一件科学性很强的工作,需要严肃的科学态度。民间文学的整理,其性质是科学的性质,即通过整理的手段更好地再现出民间口述的原材料的本来面貌和光彩。整理者的责任,不是修正改变和拔高原作的主题、增加情节、改换语言,表现整理者的创造才华,而是不改变原作,忠实原作,更好地再现原作。”e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内部资料),1987年,第59页。《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从国家层面对以往的搜集整理工作进行了系统总结,明确了搜集整理的学术本位要求,并对此前在公众读物中常使用的综合整理法提出“能不用尽量不用”。整理稿是口头文学的书面定本,《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还提出采录过程中应加以检验和复核,“复核时可着重下列问题:对作品原貌体现如何?对原作主题、情节是否保持,程度如何?整理中可否有加工?有否添加情节、改换人物?有否整理者的语言?其程度如何?必要性如何?对原作的特色韵味有否体现?对原作品的语言体现如何?可否看出讲述人的特点?对原讲述风格体现程度如何?辅助材料(如讲述人、时间、地点、讲述环境、方言注释、必要的有关说明等)是否准确、清楚。”a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内部资料),1987年,第68页。
《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以学术本位为指导,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搜集整理工作的原则及操作实践进行了系统总结,吸纳国外的采录经验b如《手册》总结了定居式搜集和采录队搜集的方法,要求采录者关注被采访者的心境、忙闲、仪式过程及演述情境,注意讲述者的开头语、接续语、感叹词、语气词、方言、特殊用语,制定了三套集成的分类编码方案等。详见中国民间文学集成总编委会办公室编:《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手册》(内部资料),1987年。,具有“田野作业”特质,确保了中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的科学性,避免了胡乱加工现象。在三套集成的普查和采录实践中,我们充分利用延安时期和新中国初期形成的动员式采录机制,借助行政力量通过国家、省、地、县、乡的专业培训来实现普查目标,发动上百万人参与,共采录“民间故事184万篇、民间歌谣302万首、谚语748万条,总字数超40亿字”c季成:《任重行难 成绩斐然——全国民间文学集成工作已逾十年》,《民间文学论坛》,1997年第1期。,为中国民间文艺学人留下了一大批宝贵的研究资料和文化遗产,启迪了后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中国民间文学大系》出版工程。
结 语
“搜集整理”是独具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彰显了民间文学文艺价值、文化遗产价值、社会认同价值和学术价值的多棱面向。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文学成为“接驳国家话语的重要场域”d毛巧晖:《现代民族国家话语与民间文学的理论自觉(1949-1966)》,《江汉论坛》,2014年第9期。,建设新文艺强化对新政权的认同是首要目的,自然呈现重文艺价值和民族文化遗产价值而忽视学术价值趋向,但造就了《刘三姐》《阿诗玛》等文艺经典。改革开放后,学术生态得到恢复,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社会价值开始弱化,“改旧编新”论广受批评,民族文化遗产价值得到广泛认同,学术价值重迎生机。随着三套集成工作的铺开,“忠实记录”原则成为共识,“搜集整理”逐渐被“田野作业”收编,学术研究逐渐成为重要旨向,涌现出诸如“立体描写”e详见段宝林:《论民间文学的立体性特征》,《民间文学论坛》,1985年第5期。的本土学术话语,推进了中国民间文艺学的话语体系建设。可见,“搜集整理”折射的是不同历史时期民间文艺在“求真”与“致用”间的功能转换。最后需要指出的是,随着学界对“搜集整理”文艺创作价值的淡化,也导致民间文艺远离大众,社会影响日渐弱化,近年来出现 “重新改写中国民间故事”f刘守华:《论民间故事的“改写”》,《民俗研究》,2017年第1期。“超越语境,回归文学”g刘宗迪:《超越语境,回归文学——对民间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倾向的反思》,《民族艺术》,2016年第2期。的呼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