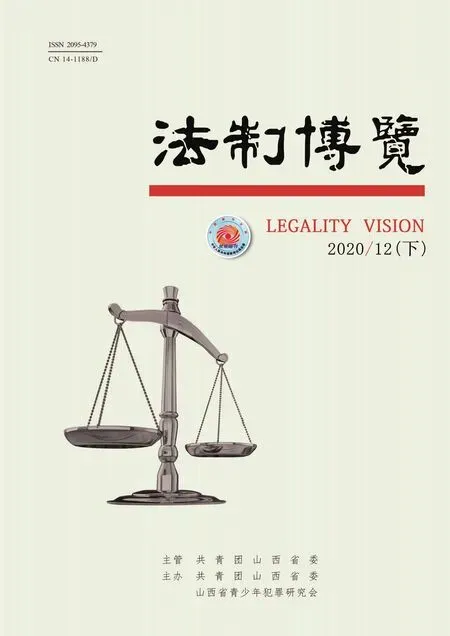合同诈骗罪与合同欺诈的概念和特征
康 希 丁 可
1.重庆市璧山区纪委监委,重庆 402760;2.重庆市彭水县人民检察院,重庆 402760
一、合同诈骗罪概念及特征
(一)合同诈骗罪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二十四条的规定,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采取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骗手段,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合同诈骗行为自有史记载以来就存在。新中国成立前的刑法均没有单独规定合同诈骗犯罪,均是以诈骗罪进行处罚。1997年通过的《刑法修正案》首次设立了合同诈骗罪,自此合同诈骗犯罪有了其独立的罪名。事实上,我国对合同诈骗罪的理论研究在1997年之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市场经济制度的迅速发展导致部分市场主体为获取利益而不惜违法甚至犯罪,学者们为此在这方面进行了专题研究。
(二)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
该罪的构成要件和特征如下:其一,犯罪主体包括自然人和单位,自然人是指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个人;单位是指公司、企业和其他组织。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针对那些专门从事非法活动的单位通过合同诈骗的方式获取非法利益,而且这些非法利益由单位中的个人获得的情况,不成立单位犯罪,而应当由个人来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其二,犯罪的客体对象复杂。侵权的对象包括公私财产的所有权,也包括市场经济中的诚实信用秩序。侵犯公私财产权会使得当事人一方失去对其所有财产的控制权;侵犯市场经济中的诚实信用秩序,就会破坏市场交易秩序与合同管理制度。其三,犯罪的主观方面是故意。为了实现非法占有财产,合同诈骗的行为人必须希望并积极追求这一结果的发生,不可能采取冷漠的态度去期待欺骗结果。因此,合同诈骗的意图是由直接故意的意图构成的。其四,时间条件是有限制的。法律明确了五种诈骗行为,而骗取他人财产意味着犯罪行为人的缔约当事人因为行为人的欺骗错误地进行了财产的交付。虽然是受害者“自愿”交付财产,但实际上并未成为受害者真正的意思表示,这种误解导致了财产的错误交付。
(三)时下观点评析
时下主流的观点认为,“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是法条竞合适用规则,是法条竞合情形下按照特别法处理的法律依据。学界对此存在的争议集中在此条文的真实意义上,如何谓“本法另有规定”,又何谓“依照”,是参照还是严格按照等。
学者孙海霞认为,“本法另有规定”是指凡是刑法分则条文中有其他与本罪相联系又区别于本罪的其他特殊罪名,就应当按照此特殊罪名的规定处理。即便是在根据一般法构成犯罪而根据特别法不构成犯罪,或者特别法明显比一般法要轻的情况下,也仍应当严格按照刑法的明文规定,按照轻罪甚至无罪处理。
学者余文唐认为,“本法另有规定”是指符合特殊法罪名全部的构成要件,也即只有在构成特别法罪名的情况下,才能够绝对排斥一般法罪名的适用。此种观点显然是从该规定的语义解释入手,企图通过赋予语句有别于通常理解方式的其他意义,以达到一般法条不被排斥适用之目的,其仅仅解决了“本法另有规定,依照规定”可能造成的特殊法犯罪行为被无罪处理的问题,却仍没有解决一般法与特殊法量刑轻重错位的问题,因而仍然算不上合理的解释。
学者王烁认为,所谓的“依照规定”表述不清,依照的意义不明,立法者的本意是要求在本法另有规定的情况下参照而并非严格按照特殊规定处理,但在制定该规则时犯了用语不当的错误,从而导致上述争议问题的产生。甚至有学者提出,“本法另有规定,依照规定”原本就属于提示性条文规定,不具备法律的强制性效力。故该条文不排斥一般法条的适用,旨在提醒司法人员在适用一般法条时还应考虑到特殊法条的规定。很显然,上述“参照论”与“提示论”的两种观点都违反了刑法的明文规定及其条文的基本含义,是对立法者立法本意和精神的曲解。
由此可见,合同诈骗与普通诈骗在构罪标准与行为人主观构成要件方面也有着明显区别。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普通诈骗罪的法律条文与行为模式无法完全包容合同诈骗罪,这是与法条竞合理论相违背的。
通过对上述批判观点之评析,我们不难发现,基于合同诈骗行为骗取的金额过小与过大之特殊情形下存在的某种现实问题,而将合同诈骗行为论证为想象竞合是不科学的;而仅仅通过通常的语义理解方式认为合同诈骗行为被包含在诈骗行为之内,从而将合同诈骗行为论证为法条竞合也难具有说服力。
事实上,以上论证都有其科学、合理的成分,但严格来讲,其论证过程并不细致严谨,也并不全面而深入。有学者主张,对于分别侵犯个人法益与侵犯国家、社会法益的具有法条竞合性质但其一般法条与特别法条出现轻重错位的几组罪名,如过失致人死亡与玩忽职守、交通肇事等罪,诈骗罪与合同诈骗、金融诈骗罪等罪,虽形式上具有包含、交叉关系,符合法条竞合条件的特点,但因其特别法罪名侵犯了新的法益,而应作为想象竞合犯择重罪处断。此种观点被称为“大竞合论”,即强调无须严格区别罪名之间的竞合形态,而直接按照重罪优先原则处断。笔者承认,“大竞合论”对于司法实践具有较强的指导性作用,但在法理研究的层面上,“大竞合论”似乎是在逃避相关问题,旨在将复杂的法学理论作简单化处理,且该论调明显违背了竞合关系的基本理论,笔者对此是极不赞同的。
故笔者认为,“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确实是刑法对法条竞合处理规则的设定,但因适用该规定产生司法困境的根源不在于该规定本身,而在于刑法分则对法条竞合下的各种特殊法罪名的量刑设定不合理。如上所述,合同诈骗行为侵犯的是双重法益,对比于普通诈骗行为,其显然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但就是在此基础上,合同诈骗罪的构罪数额标准明显比诈骗罪高。在犯罪数额相同的情况下,合同诈骗罪的刑期相较于诈骗罪明显偏低。这就是说,合同诈骗罪对比于普通诈骗罪而言是轻罪,这显然不利于打击社会危害性更大的合同诈骗行为,也有损于司法公正。笔者揣测,立法者可能是基于普通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比起合同诈骗罪的犯罪对象来说相对弱势,且合同诈骗犯罪的数额通常都比较巨大之考虑,故宁可弱化经济管理秩序的保护,转而强化对弱势群体财产权益的保护,因此才有此轻重错位之规定。再者,立法者不是万能的,刑法是立法机关制定的,但立法机关的组成人员并非都是刑法学家,在立法中出现某些违背法理常情的现象亦属正常,这是由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性等多种因素造成的,因此才有修改完善法律的必要。
二、合同欺诈概念及特征
(一)合同欺诈概念
弄清合同欺诈的关键点是理解欺诈的概念。根据我国合同的相关理论以及司法实践,不难找出对欺诈概念的明确定义,即“合同欺诈”一词指,缔约方在缔结或者履行合同期间实施的欺诈行为。欺诈行为的表现形式是多样的,行为人惯用的欺诈伎俩主要有编造虚假事实、故意告知对方当事人等几种类型。必须要明确的是,合同欺诈与合同纠纷之间存在本质的差别,从民事法理方面来讲,产生合同纠纷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合同欺诈。除此之外,还包括履行合约或者违反合约等形式。也就是说,二者存在一种包含关系,即如果某种行为属于合同欺诈,则当然也属于合同纠纷,反之则不必然成立。
(二)合同欺诈构成特征
1.从手段看,合同欺诈具有隐蔽性。根据上述关于合同对经济生活的广泛适用的论点,合同欺诈是多种多样的,并且难以完全描述的。但是不管欺诈者使用什么手段进行欺诈,比如不准确的告知合同履行情况,或者采用高科技手段隐藏合同履行情况等,都是把意图从表面隐藏到实质层面。在这个基本特征的作用下,对方误解了真实情况,基于这种认识,合同行为偏离了其原本的意思表示。
2.从范围上看,合同欺诈范围广泛复杂。目前,我国有关合同条款主要存在于《合同法》和《民法总则》,合同欺诈涉及几乎所有类型的合同。当然,还有一些合同没有被用来进行合同欺诈。因此,对于某些具有个人特征的合同,如领养合同,即使当事人在当时使用该行为进行欺骗,也故意将对方的错误情况通知对方或故意向另一方通报,也不能因为隐瞒真实情况而构成我们称之为合同欺诈的事实。因此,普通合同欺诈涉及到共同销售合同欺诈。
3.从目的上看,合同欺诈具有违约性和故意性。合同欺诈本质上是一种故意的行为。但如前所述,基于合同欺诈而签订的合同是表面合法的,它符合建立合同的一般要求。因此,从客观上看,合同欺诈确实属于某种意义上的违约。但是,不能简单地将合同欺诈确定为民事违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