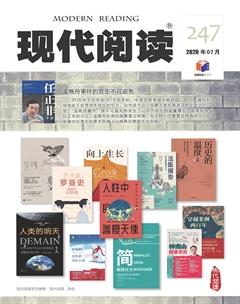宇宙学领袖人物安德烈?林德
约翰?霍根 孙雍君 张武军
安德烈·林德,1948年出生,美籍俄裔宇宙学家,现任斯坦福大学教授。他是最早提出暴涨宇宙学的学者之一,并修正了艾伦·古思的模型。他一直是宇宙学研究的领袖人物之一。《科学美国人》杂志资深撰稿人约翰·霍根通过采访,力求把真正的宇宙科学和这位真实的科学家普及给大众。
林德因其理论“变戏法”而出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使暴涨理论获得同行们的认可,这是一个从粒子物理学中推出的更为离奇的想法。暴涨的发明,一般归功于麻省理工学院的艾伦·古思,但林德帮助改进了这一理论,并使之得到公认。古思和林德提出,在我们宇宙历史的极早阶段,那时的宇宙比一个质子更小——引力会变成斥力。因此,他们认为宇宙经历了一次惊人的、指数增长的膨胀;而时至今日,宇宙则以一个低得多的速率膨胀。
古思和林德的观点建立在未被检验的——几乎肯定是不可检验的——粒子物理学统一理论基础上。不过宇宙学家喜欢暴涨理论,因为它能解释一些由标准大爆炸模型产生的扰人的问题。首先,为什么宇宙在所有方向上均表现出或多或少的相似性?答案是:与吹起一个气球时抹平了它的皱折类似,宇宙的指数膨胀使得它相对平滑。反过来,暴涨也解释了为什么宇宙不是一个完全均匀的、一锅汤似的发光体,而是以恒星和星系形式呈现的成团的物质。量子力学表明连真空也充满能量,这些能量不断地涨落,像风吹过湖面时湖面水波的起伏。按照暴涨理论,这些在宇宙极早期由量子涨落产生的波峰,在暴涨后会变得足够大,成为形成恒星和星系的引力种子。
暴涨有一些令人惊诧的含义,其中之一是我们通过望远镜所能看到的一切,都只代表在暴涨时产生的极大区域内的一个极微小部分。但林德并未就此止步,他进一步提出,甚至那个极大宇宙,也只不过是暴涨时产生的无限多宇宙中的一个。膨胀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它不仅产生了我们置身其中的宇宙——我们依靠望远镜能探索到的嵌满星系的领域,还产生了无数的其他宇宙。这个超级宇宙具有所谓的分形结构:大宇宙生出小宇宙,小宇宙再生出更小的宇宙,如此继续下去。林德把他的模型称为混沌的、分形的、永远自复制的暴涨宇宙模型。
在林德讲述他的经历时,很明显,焦虑乃至抑郁是激励他的重要因素。在他研究中的几个阶段,就在取得突破性进展前,他会对洞察事物的本质感到绝望。林德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就已经偶然得出了暴涨的基本概念,当时他正在莫斯科,但是他认为这个想法缺点很多,以至于无法继续研究。艾伦·古思认为暴涨能解释宇宙几个使人困惑的特征,比如宇宙的平滑性。这使他的兴趣再次被激起,但是古思的看法也有毛病。林德在思考这个问题时是如此入迷,以至于得了胃溃疡。好在他终归还是厘清了该怎样修正古思的模型,才能消除其技术上的问题。
但即使这个新暴涨模型,也还是建立在林德深感怀疑的统一理论之上。最终,在陷入忧郁以至于缠绵病榻一段时日之后,他确信暴涨能由约翰·惠勒首先提出的更一般的量子过程产生。据惠勒所云,如果谁能拥有一台比任何现存显微镜的分辨率强大亿万倍的显微镜,他就能看到时空由于量子不确定性而剧烈地涨落。林德认为惠勒所说的“时间泡沫”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暴涨所需的条件。
暴涨是一个自耗过程,即空间的膨胀使驱动暴涨的能量很快耗散。但是林德认为,一旦暴涨开始,由于量子不确定性,它将总是在某处继续进行(量子不确定性的一个特征)。在这个时刻,新的宇宙纷纷产生了,有些宇宙立即坍缩回去,另一些宇宙膨胀得如此之快,以至于物质没有机会聚合。一些类似于我们置身其中的宇宙安稳下来,以足够慢的速率膨胀,引力就使物质形成星系、恒星和行星。
林德有时将这种超宇宙比作无垠的大海。靠近看,这大海给人的印象是运动不息和变化不止,波浪起伏。我们人类,由于生活在这引起起伏的波浪之一中,会认为整个宇宙正膨胀着。但是如果我们能升到海面之上,就会认识到膨胀的宇宙只是一个无限大的永恒的海洋中一个微不足道的局部。林德认为英国天体物理学家弗雷德·霍伊尔早期的稳恒态理论在某些方面是对的,如果以上帝般的视角来看,超宇宙当然能表现出某种平衡。
林德并不是第一个假定存在其他宇宙的物理学家。虽然大多数理论家都将其他宇宙作为数学抽象对待,并对此感到困窘,但林德却喜欢推测它们的性质。例如,在说明其自复制宇宙理论时,他借用了遗传学话语,暴涨创造的每一个宇宙都生出另外的“婴孩宇宙”:这些后代中有一些会保持其先辈的“基因”,演化成类似的宇宙,有着类似的自然法则,也许还有着类似的土著居民。援引人择原理,林德提出,某种宇宙学版本的自然选择,会更倾向于让那些有可能产生智慧生命的宇宙永远存在。“在宇宙的某处存在着像我们一样的生命,这在我看来差不多就是板上钉钉的事实,”他说,“可惜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
像艾伦·古思和其他几个宇宙学家一样,林德也喜欢玄想在实验室中创造一个暴涨宇宙的可行性,但只有林德提出这样的疑问:为什么要创造另一个宇宙?它带有什么目的?根据林德计算,一旦某个宇宙工程师创造出一个新的宇宙,它会立即以超光速同其母体分离,不可能有进一步的通信。
另一方面,林德猜测,或许这位工程师能以某种方式精心处理暴涨前的种子,使它演化成为一个有特定的维数、特定物理规律和自然常数的宇宙。这位工程师会以上述方式将某种信息嵌在新宇宙的结构上。林德认为,实际上我们的宇宙很有可能就是另一宇宙的生物创造的,而像他自己这样的物理学家,在摸索着试图揭示自然规律的过程中,实际上可能正在破译来自我们宇宙母体的信息。
林德抛出这些观点时显得相当谨慎,同时观察着我的反应,只是在最后,大概是对我吃惊地大张着嘴感到很满意,他才让自己露出了一丝笑意。然而,当我想知道嵌于我们宇宙的信息可能是什么的时候,他的笑容消失了,郁郁地说:“似乎我们还没有成熟到能知道这些信息的地步。”当我进而追问他是否担心其所有的工作可能只是——我竭力想要找到一个恰当的词语——胡说八道时,他的脸色阴沉得都快滴出水了。
“在我消沉的时候,我的确会感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他回应道,“我思考的都是些相当原初的玩意儿。”他又补充说,他曾尽力让自己不要太沉迷于自己的想法,“有时这些模型相当奇怪,如果你对它们太认真,就有掉入陷阱的危险。我想这和在湖面薄冰上跑步相似,如果你跑得非常快,你可能不会沉下去并且能跑上一大段距离。可如果你只是站在那儿去思考是否跑对了方向,那无疑你就会掉下去。”
林德似乎是想表明,他作为一名物理学家的目标并不是去追寻解,去追寻“終极答案”或仅仅是追寻某个“答案”,而是要不断前进,不断向前滑行。林德对终极理论的想法感到恐惧,其自复制宇宙论要这样解读才有意义:只有宇宙是无限且永恒的,科学作为对知识的探求,也才会是无限且永恒的。但林德认为,因为物理学受制于这个宇宙,所以它不可能趋近终极。“例如,你没有将意识包括进去。物理学研究物质,而意识并非物质。”林德同意约翰·惠勒的说法,现实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参与现象。“在你测量前,没有什么宇宙,没有你能称作是客观现实的东西。”林德说。
就像惠勒和戴维·玻姆一样,林德似乎对物理学永远不会十全十美的前景,既满怀着神秘的憧憬,又倍感煎熬。他说:“理性的知识有一定局限。研究非理性的一条途径是深入其中思考,另一条途径是用理性工具研究非理性的边界。”林德选择了后者,因为物理学只是提供了一条研究世界运演的“不能说完全无意义”的道路。但有时候他承认,“当我一想到自己会像一个物理学家那样死去时,就会感到沮丧。”
(摘自清华大学出版社《科学的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