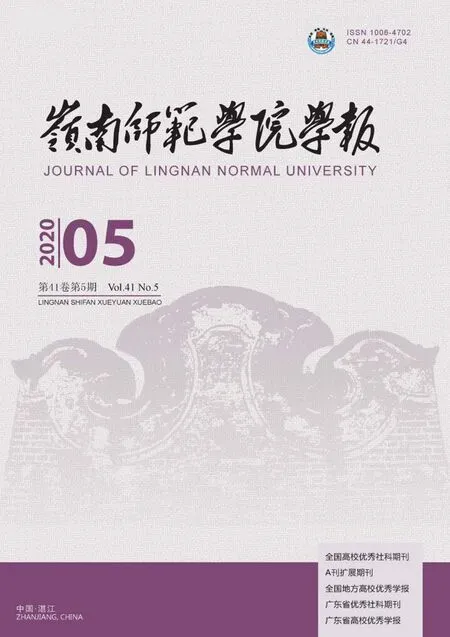潘玉良绘画作品中的女性符号探析
李 京
(淮南师范学院 美术与设计学院,安徽 淮南 232001)
每一个艺术家都有自己所钟爱的题材与反复描绘的对象,潘玉良作为民国时期的第一代女性画家,她画面中出现最多的图像就是女性符号。欧文·潘诺夫斯基(1)欧文·潘诺夫斯基(1892年3月30日-1968年3月14日),美国德裔犹太学者,在图像学领域做出突出贡献。认为,图像是一种意指,用来代表其他事物,或是表意的标识,具有符号与象征的功能,即可以理解为符号。因此,潘玉良绘画作品中这些女性形象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种艺术符号。苏珊·朗格(2)苏珊·朗格,美国符号学美学家,先后获哲学、文学博士,研究方向为符号学研究,主要美学著作有《感受与形式》、《艺术问题》等。指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她强调艺术表现的是人类情感而非艺术家个人的情感,艺术中使用的符号是一种暗喻,一种诉诸感受的东西,一种终极的、非理性和不可言传的意象,一种充满了情感的、生命的和富有个性的象征。潘玉良笔下的女性符号俨然不同于中国传统仕女图中为满足封建儒家思想的评判标准和审美趣味而出现的传统淑女,也不同于民国初年的月份牌中依照男性价值判断而塑造的妙龄女郎,她们有的气质温婉,表现了民国名媛特有的娴雅气质,有的热烈奔放,传达出现代女性关注自身与生命本体的叛逆与不羁,有的忧郁迷惘,暗示了画家对命运的叩问与对未来的困惑,有的温存典雅,散发出醇厚的母性光辉……潘玉良笔下这些具有特定含义的女性符号既寄托了画家心中的美好理想与自我期许,也传递出了她内心的缺失与迷惘,反映了她内心的情感与价值判断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
一、潘玉良以女性为符号作为绘画母题的缘起
(一)女权运动的兴起,女性艺术家开始把艺术创作的视角转向女性自身
潘玉良生活的20世纪的历史也可以被称为一部女性主义的运动史。民国初年,女性主义思潮由斯宾塞的《女权篇》的传播被介绍到中国,随之而来的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提出的“男女平等”的口号彻底改变了潘玉良的命运,潘玉良由一个在男权社会下被蹂躏被践踏被消费的女性客体渐渐成长为一名具有女性自觉意识与独立精神、能够把握个人命运与人生轨迹的艺术家,实现了自我价值,完成了救赎之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潘玉良本身就是一个女性符号,在她的身上,承载了多重的意义。潘玉良命运多舛,她跌宕起伏的人生际遇与风云变幻的历史时代环环相扣、紧密契合。她既是时代的经历者,也是一位时代的书写者与记录者,她把描绘的对象转向女性自身,她笔下的女性形象由千百年来男权视角下优美娴雅的审美客体逐渐转变为撕掉传统标签并自由地表达自我的主体符号,这些女性符号既是潘玉良理想化的自我期许,同时也倾注了她的自我反思与自我观照,她以自我图像的方法抵制男权社会的审视,同时也重构了女性的精神内涵。
(二)现代艺术的繁荣,符号的运用是现代艺术的主要特征之一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现代艺术思潮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各种艺术流派更迭变化,异彩纷呈。符号学、图像学等纷纷从不同的角度介入了绘画,并从作品的意义、意味或意蕴的层面去阐释绘画,对绘画作品中从属的、约定俗成的象征性内容进行确定,凸显画面的哲学性意味与精神性内涵。主观性、内向性是现代主义的重要特征,艺术家往往侧重于表现自己心理层面的真实,赋予画面主题以譬喻性、模糊性和多义性。当时身居现代艺术阵营中心,并作为“巴黎画派”一员的潘玉良自然也受到了这一时代精神与艺术思潮的感召,国内十年积累的心得,对中国传统绘画的反观与回归,使身处异域的潘玉良对自己的母体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体悟与认识,为了赋予画面更深层次的意蕴,她在画面中植入了既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特征同时也恰好契合了现代艺术精神指向的艺术符号,其中最值得探究的就是女性符号。
二、潘玉良画面中的女性符号探析
符号在绘画中的运用由来已久,在原始社会,人类就有把动物的图形刻在武器或器皿上、用符号传达人类情感和当时的社会活动的风尚,这些作为符号的图形不必肖似,它仅仅是一种象征性的功能。在20世纪的现代派绘画中,艺术家们更热衷于运用象征、譬喻、寓言、暗示、无意识、梦幻、荒诞、悖谬等探索方式和表现手段,来传递物象背后不可言传的意义,目的是在画面中注入更深层次的哲理内涵和尽可能多的信息量,从而启发观众去思考,去发现。其中女性画家也不乏其人,如同美国女画家欧姬芙常常以花卉作为隐喻性符号,赋予了她画面更多的女性意味与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潘玉良画面中的女性符号也值得我们去探究和解读。
(一)旗袍女子

图1 旗袍女子
苏珊·朗格提出“艺术是人类情感的符号形式的创造”,“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1]75。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或象征活动,只有解读作品中的符号,才能解读作品真正的内涵。不同时代不同民族的衣冠发式都具有极其强烈的符号意义,就像八大山人一直“戴斗笠”“著宽袍”、墨西哥女画家弗丽达喜欢描绘穿着波西米亚服装的自画像一样,潘玉良亦钟情于象征东方传统文化符号的旗袍女子(3)潘玉良一生钟爱旗袍,现安徽省博物馆馆藏的潘玉良的5件衣服均为旗袍,其中3件分别绣着具有中国传统符号意味的龙、凤与鹤的图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旗袍女子”是指画家作于1940年左右的穿着旗袍的自画像,然而又不仅仅是自画像(4)安徽省博物馆馆藏的这5幅潘玉良的自画像,除了两幅分别作于1939和1940年之外,其他3幅均未注明创作年代,但是根据绘画风格可以推断年代相近。。 熟悉潘玉良的人都知道,潘玉良并不具有传统审美意义上窈窕淑女的特质,她的学生郁风说:“她有男人的性格,像条汉子,很少流泪,并不柔软娇美,多愁善感;她说话很粗犷,为人豪放,不拘小节,有时不修边幅……”这一点在潘赞化1955年写给潘玉良的信中可以找到佐证,他说:“你一生不解(讲)究装饰,更有男性作风。少年骑马射箭,都是好手。为什么到老了,还要着嫁时少女花服,在古希腊罗斯荒岛古雕怪兽旁烈日之中照相与我呢?所以我诗云:‘容比当年尤妩媚,情愈曩昔更缠绵。温柔敦厚仍如昨,文采风流未减前’。”[2]23令人困惑的是,潘玉良笔下这些身着旗袍的画中人却妆容精致,仪态娴雅,神情幽然,颇有远意,似乎在向观者诉说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由此可见,这些自画像并不是潘玉良自身的真实写照,而是她内心理想的外化,是一个个具有象征性意味的符号,反映了潘玉良站在传统男性视角下的自我期许与自我塑造。潘玉良一生感念既是爱人又是知己的潘赞化,她这几幅颇具东方女子情韵的自画像是对远在故国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丈夫潘赞化的情感表露,也是“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的传统士人精神的具体体现。
(二)游乐的女子

图2 歌舞艳声
苏珊·朗格说:“以一种客观的符号将一个主观的事件或活动表现出来,任何艺术品都是这样一种形象,不管它是一场舞蹈,还是一件雕塑品,或是一幅绘画,一部乐曲,一首诗,本质上都是内在生活的外部显现,都是主观事实的客观呈现。这种形象之所以能够标示内心生活中所发生的事情,乃是因为这一形象与内心生活所发生的事情含有相同关系或成分的缘故”[1]8。潘玉良作品中有相当多的篇幅描绘了游乐的女子,她们郊游戏水、莺歌曼舞,沉浸在美好的春天里。潘玉良把这些青春女子潇洒旷达,放纵恣肆的生命状态与自然融为一体,讴歌了生命本体的野性与活力,表达出艺术家对自由与美好生活的向往,体现这一主题的作品从1941年到1959年一共有22幅之多,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春之歌》《郊外之春》《歌舞艳声》等。尤其是作于1956年的《歌舞艳声》这幅画,描绘了一群欢乐的女子,她们有的奏乐,有的舞蹈,肆无忌惮、旁若无人地沉醉在这潋滟的春光里,对不远处一个驻足观赏的男子视而不见。每一个艺术家从客观世界选取来描绘的对象都是用来传达内心意象的,画面中的图像是画家把内在的情感转化成的一种供人观赏的可见的形式,也是一种符号,潘玉良这张画中那些身着民族服装,欢乐而又自我沉醉的女子,传达的是画家对一种自由洒脱的生命状态的向往,也是一种人生理想。由此也可以看出,画家由最初孜孜于把自己塑造为一个传统男性审美判断下温良娴雅的女性形象并以此撕掉自己出身青楼的身份标签的意图逐渐转变为对这种自娱自洽、怡然自得,不再关注他人的目光而是自给自足的精神状态的追求,不得不说,这显示了潘玉良的自我成长与自我纳悦,是一次华丽的蜕变。
(三)女人体

图3 女人体
在西方绘画体系里,一直崇尚人体的美,女人体不但不污秽,反而象征着神圣、自由、脆弱和真理,虽然裸体在某种语境下也代表着肉欲,但是未经任何装饰的女人体常常被作为纯洁无瑕的象征。欧文·潘诺夫斯基在《弗洛伦萨与意大利北部法新柏拉图主义运动》一文中指出:“无论圣经还是以此为依据的罗马文学,裸体总是因表现贫困与寡廉鲜耻而一再遭人唾弃,在比喻性的表现中,裸体通常被视为曲折、欺骗或者外在表现的对立一方,等同于率直、诚实或事物本质。在神的眼里,一切都是赤裸而无法隐瞒的。”[3]158女人体一直是潘玉良热衷描绘的题材,尤其是中晚期,潘玉良用彩墨的方法表现了许多裸体的东方女子形象,她们或全裸或半裸,或斜倚或端坐,或读书或揽镜,呈现出一副怡然自得、岁月静好的样子。潘玉良笔下这些仪态万方、神情娴雅的裸体女子,除了一些素描与油画习作属于写生练习之外,其他的均不是写实意义的再现,而是一个个图式化、象征性的符号,是在西方语境下的“东方女性”的象征,具有特定的文化内涵。欧文·潘诺夫斯基说:“中世纪神学认为裸体具有四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导致谦卑行为,人类自然状态的(自然裸体);自愿身无长物,不要现世财产的(暂时裸体);作为纯洁象征(或称作因忏悔而获得纯洁)的(美德裸体);象征欲望、虚荣以及道德沦丧的(罪恶裸体)。但在美术作品中,四种类型最后那种裸体实际上被排除在外”[3]159。在潘玉良描绘女人体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以自己为模特画成的,画家在画中有意把自己真面目隐去,她们或背或侧,从不正面示人,只留给观者一个背影,一个遐想的空间。西方符号学的代表人物卡西尔曾提出“艺术是一种符号的形式”,当作品中反复出现某种符号,那么就得思考这些图像或符号背后的意义。卡西尔说:“只有把艺术理解为是我们的思想、想象、情感的一种特殊倾向、一种新的态度,我们才能把握它的真正意义和功能”[4]215,由此可见,潘玉良笔下的这些裸体女子形象完全不同于中国古代春宫图中的女性形象,她们不再是被男性消费与关注的客体,丝毫不带有色情的意味,而是画家自我摹写与自我叙述的方式,她用裸体的符号来象征自己的卑谦和纯洁,以及身无长物、孑然一身的洒脱与淡泊(5)潘玉良在法国被称为“三不女士”:不谈恋爱,不入法国籍、不和画商签订合同。,既表现出她与自己过往经历的和解,也传达了她对自我的坚守和对现实世界的反叛与不妥协。
(四)舞蹈的女子

图4 双人扇舞
在50年代中期,潘玉良的画面中一共出现了8幅舞蹈的女子的形象,这一类的作品,除了一幅《三人扇舞》作于1957年,两幅年代不详,其他5幅均作于1955年,在《双人扇舞》这幅作品里,潘玉良用极简的黑白赋色和具有中国民族意味的对称性图式来安排画面,很像中国传统的太极阴阳图。在画家这些描绘舞蹈的女子的作品中,都有着共同的特征:她们身着传统服装,梳着中式的发髻,有的手持折扇和面具,有的背景上会出现红色的中式灯笼,她们面目模糊,不求肖似,这些女子不是具体某个人的呈现,也不是对客观自然的模拟,她们或两个一组或三个一群地出现在画面里,和那些象征中国传统文化符号的元素组成一个共同的民族符号。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国内掀起了一场艺术民族化的热潮,毛泽东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进一步确认了他一以贯之的艺术要走“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的道路(6)毛泽东的这一艺术观念最早见于《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先在鲁迅艺术学院进行实践,1949年后则由中央美术学院(1950年在北京成立)进行推行。。从潘玉良的藏书中有多本毛泽东的著作可以看出,潘玉良对新中国的文艺路线是有所关注和践行的(7)在潘玉良的藏书中,有《祖国在前进》、《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等书籍。。据潘家后人徐永昇所述,潘赞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对新中国的成立充满期待与信心,毫无疑问,潘赞化的这一思想影响了潘玉良,她先后于1949年和1951年两次致信自己的丈夫要求回国但终未成行。由此推断,潘玉良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绘画上所进行民族风格的探索和尝试与当时国内的政治空气和艺术风潮是有一定关系的。这些“手之舞兮,足之蹈兮”的舞女形象既是潘玉良对国内的艺术民族化道路的积极响应,也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欢欣鼓舞的心情的一种表达。
(五)母性形象
每一个艺术形象,都可以说是一个特定含义的符号或符号体系,苏珊·格朗说:“艺术品是将情感(广义的情感,即人所能感受到的一切)呈现出来供人观赏的,是由情感转化为可见的或可听的形式。它是运用符号的方式把情感转变成诉诸人的知觉的东西。”[1]24在潘玉良的绘画作品中,有相当多描绘母与子的篇幅。仅在1958年,她就接连画了《哺乳》《母爱》《母与子》等多幅表现母爱题材的作品,那么这些作品中的母亲形象只是简单的写实意义的呈现吗?并不是这样,这些母与子的形象其实是寄托着潘玉良内心情感的象征性符号。我们想要了解艺术家作品的内涵,需要去解读这些作品中符号所表达的意义。众所周知,潘玉良本人不能生育,为了能给潘赞化延续香火,她特意把潘赞化的原配妻子方氏接到上海,生下潘牟,并视如己出,这在潘玉良早期反复描绘的作品《我的一家》中可见一斑,在《我的一家》中,潘玉良俨然以母亲的形象出现,画面中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生活场景既是当时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也是潘玉良心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景。关于潘牟的出生,潘赞化曾有信赞潘玉良入潘门四十多年后,有十件可记之事,其中第二条即“迎妇生子”,并有诗云:“几回青鸟使申江,避席亭间扫玉床。大礼躬行迎旧妇,天津牵遣小二郎”[2]22。从与潘赞化后人的通信中所传达出的情感也可以看出,潘玉良始终对潘牟一家怀有殷殷的关切之情,这种情感即使在她与潘家连接的纽带潘赞化去世之后也绵绵不绝,未曾间断,直到她在法国病逝。在最后留下的遗嘱中,她写道:“这是我的家信,如果我将来死在国外,烦请朋友们将这些信寄给小孙潘忠玉留为纪念……潘张玉良请求。”[2]28潘玉良一生辗转,多次搬家,但是家信一直珍藏在身边,由此也可以看出她对潘氏一家的深情。尽管如此,但终生不育也许是她一生中最难以言传的隐痛,所以母与子的形象才会作为符号在她画幅中反复出现,成为她吟咏讴歌的对象。显而易见,画中的母亲是潘玉良自己的化身,所表达的也是她内心隐秘的情感与无法实现的人生夙愿,就像墨西哥女画家弗里达因为车祸失去了生育能力却一直在自己的作品中反复描绘生孩子的场景;法国女画家卡萨特一生未婚,却热衷于描绘母与子的题材一样,潘玉良把母亲的形象作为一个符号反复描绘,又何尝不是对于其内心深处某种缺失与苍凉的补偿与慰藉呢?!
(六)占卜的女子
“一切艺术都是创造出来的表现人类情感的知觉形式,这种创造出来的形式是供我们的感官去知觉或供我们想象的,而它所表现的东西就是人类情感”。苏珊·朗格从符号论的哲学基础出发,认为艺术表现的正是艺术家所认识到的人类普遍感受,艺术抽象出的则是人类普遍感受的本质或概念,艺术是以人类精神为基础,是体现或象征人类生命感受形态的可感形式,因此,苏珊·朗格将艺术界定为人类感受符号的创造,认定艺术旨在表现人类普遍感受的符号形式。在潘玉良第二次去法国并旅居异域的40年中,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祖国,思念着家人,但是故国遥遥,归期无望,她不得不感叹自己命运的无常。自1939年以后,扑克牌就成为一个符号常出现在她的作品里,扑克作为在7世纪由吉普赛人流传到欧洲的一种游戏,具有占卜含义,而占卜也是西方绘画中常出现的题材,用来表达隐喻的意味,潘玉良在《占卜的女子》这张彩墨画里,画了一个穿着中式服装的女子,静静地坐在那里,她低眉垂目,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手里不停地把玩着扑克,似乎在占卜自己未知的命运。一般来说,画面图像所传达的内容往往与画家想要表达的情感有关,这个占卜的女子其实是一个艺术符号,具有象征的意义。艺术符号之所以能够传达内心世界,源于符号与画家内心情感有相通或相同的成分与缘由,“在艺术中,符号就是思想的具体感性基础的袒露”[5]485。《占卜的女子》作于1957年,当时潘玉良已经六十多岁了,在潘赞化的家书中,多次提到自己“齿落、溺多”的老境,而潘玉良的身体也有很多状况,家乡的亲人盼着她回去,她也归心似箭,可是一次次回国的申请均被法国当局驳回(8)1956年,潘玉良身体状况恶化,申请回国,但是法国当局不准带作品离境,只好暂时放弃。,贫病交加、生活困顿的她怎能不追问自己的命运呢?未来的无法预知使她产生了宿命的思想,所以她把这种难以言说的苍凉心境转化成一种优美的艺术符号诉诸笔端,借用占卜的女子这一形象表达自己当时身在异乡、孤苦无依时惶惑无助的心情,引人遐思无限,让人低回不已。
三、结 语
鲍列夫认为:“符号的功能造成了符号关系场,要领会一个符号,必须首先知道它所代表的那个对象(符号的对象意义)并理解符号本身的意义(符号的含义)。”[60]486潘玉良作为民国时代第一批女性画家,她画面中一系列的女性符号作为独特的视觉文本,由对传统男性视角下“被观看”的优雅娴静的淑女形象的塑造逐渐蜕变为在现代主义思潮下女性的自我觉知与自我纳悦,自我表达与自我书写,展现了中国女性从几千年来男权话语的审美观念下的自我意识薄弱的传统女性转化为独立与自主、自洽与自足的现代女性的轨迹。潘玉良作品中这些承载了时代风尚与文化含义的女性符号与她画面中的空间场景、装饰性的物件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严密的逻辑系统,共同记录了潘玉良作为一个女性符号在那个历史环境下的个人成长与思想变迁。
——潘玉良的艺术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