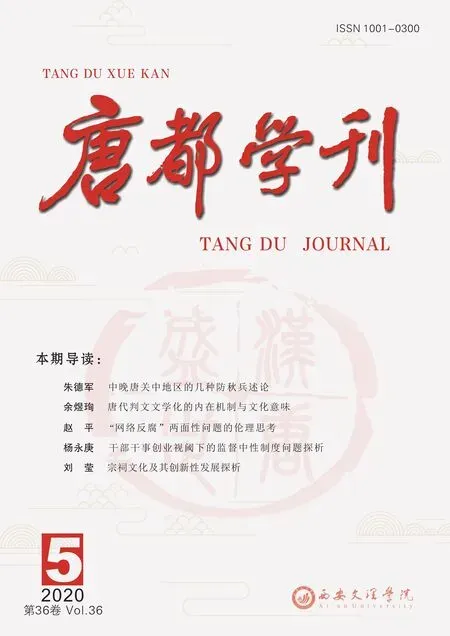从章太炎先生《新方言》等成果看陕西方言
孙立新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文学与教育学院,西安 712046;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学艺术研究所,西安 710065)
《章太炎全集·语言文字卷》[1]收录了章太炎先生《新方言》《岭外三州语》《文始》等成果。其中《新方言》包括刘光汉、黄侃两位先生的后序(跋),在该卷的起止页码3~151,96千字;《岭外三州语》起止页码155~172,12千字。以《新方言》之所论及与陕西方言关系最为密切,其次为《岭外三州语》。《新方言》《岭外三州语》均为著名语言学家蒋礼鸿先生校点。以下予以讨论,作为学习该卷的心得。
章太炎先生在其一生的革命和学术生涯中,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有很优越的条件调查到各地第一手方言资料。章先生以语言学家的眼光审视这些资料,条分缕析,深入讨论,形成了《新方言》《岭外三州语》等方言研究成果。《新方言》等成果绝大多数内容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的。如章先生指出“古人于大物辄冠马字”,即以“马”训“大”,可从陕西方言把大瓢叫作“马勺”,把大玻璃灯叫作“马灯”等得到印证。
一、从《新方言·释词第一》看陕西方言
《广雅》:些,词也……《楚辞·招魂》用之。今淮西黄梅语馀声犹多言些,扬州、杭州亦然;音如洒,或促如杀。些犹尔也,词之必然也。[1]15
其一,关中轻声调的“些”很普遍地用作表恳求的句末语气词,例如:“你赶快过来些|叫他走些!”孙立新《关中方言语法研究》[2]869-875对“些”字在关中方言里的语法语义特点及读音变体有比较深入的讨论。“些”字古音为[sia],今关中地区的长武、太白、扶风、千阳即读作[sia],不分尖团的西安、鄠邑等处读作[iɛ],分尖团的大荔、临潼、高陵等处读作[siɛ],泾阳、三原等处读作[siã](这是[sia]主要元音鼻化的结果),永寿、乾县、眉县读作[ia];宝鸡、凤县、凤翔、麟游、陇县读作[sa],这是[sia]减去介音的结果,宝鸡等处的读法对应着《新方言》里的“洒”或“杀”,“杀”在扬州、杭州等南方方言里是入声字,今关中方言没有入声;富县读作[s],这是[sa]元音高化的结果,富县“些”的音变轨迹为[sia→sa→s]。
其二,孙立新《陕南方言略说》描述了陕南表恳求的句末语气词,如留坝的“嗄[.sa]”和汉中的“噻[.sai]”,其实“嗄、噻”都是“些”的历史性音变;“嗄[sa]”是[sia]减去介音的结果,“噻[.sai]”是在[sa]的基础上又有增音,即增加了韵尾[i]。汉中“噻[sai]”的音变轨迹为[sia(些)→sa(嗄)→sai(噻)][3]。两处的例句比较如下。
留坝: 过来嗄! 对啦嗄! 你叫他回去嗄! 你先听我讲嗄! 你讲讲理好嗄!
汉中: 过来噻! 对啦噻! 你叫他回去噻! 你先听我讲噻! 你讲讲理好噻!
二、从《新方言·释言第二》看陕西方言
古人于大物辄冠马字,马蓝、马蓼……马蜩、马蚿是也。今淮南、山东谓大枣为马枣,广东谓大豆为马豆,通言谓大蚁为马蚁。[1]28
《辞源·下册》(修订本)“马”字条第三义项“大,《尔雅·释虫》‘蝒,马蜩。’注:‘蜩中最大者为马蜩。’《本草纲目》四六介二马刀:‘俗称大为马,其形象刀,故名。’”[4]3443“马”字训“大”可资印证的如普通话的“马路”指大路,而关中方言“马”字训“大”的例子比较多,如把大瓢叫作“马勺”,把大玻璃灯叫作“马灯”,把很大的乐器号叫作“马号”、很大的锣叫作“马锣”,把高大而有苦味的野生苜蓿叫作“马苜蓿”,西安一带把大个儿的黑色牛虻叫作“马虻噆”(把普通牛虻叫作“虻噆”)。按:以上章先生所写作的“马蚁”,后来大家都写作“蚂蚁”,因为“蚁”字是“虫”旁,“蚂”也类化成为“虫”旁。陕西方言把各种大大小小的东西叫作“尕大马细”或“尕细马大”,其中“尕、细”互训,“马、大”互训;“细、大”在此语境由去声变作阴平,分别如“搭、西”。
《方言》:杪,小也。木细枝谓之杪。江、淮、陈、楚之内谓之蔑。郭璞曰:蔑,小儿也。今杭州谓极小曰蔑,读如弥;宜昌谓小儿为蔑子。[1]28
其一,陕南柞水把树梢上端的细枝叫作“梢杪子”,如当地渔鼓歌词云:“梢杪子姜太公做了鱼竿”。柞水渔鼓以及镇安渔鼓均系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
其二,关中把极小的婴儿叫作“碎蔑蔑”,把单独的东西叫作“单蔑蔑”。
《汉书·西域传》曰:以金银为钱,文为骑马,幕为人面。如淳曰:幕音漫。[1]31
陕西方言把旧时的货币制钱叫作“麻钱”,麻钱有字的一面叫作“字”,无字的一面叫作“幕”且“幕”字也读如“漫”。陕西民间赌博恶俗中的押宝,有一种叫作“押字幕(=漫)宝”的,就是以字还是幕来决定胜负的。
《说文》:绰,缓也。《尔雅》:宽,绰也。今谓屋及器宽大为宽绰,人性奢泰为阔绰。言宽绰者,或转去声为操。[1]33
西安一带把“绰”字文读如“戳”,白读如“操”。鄠邑把绰号叫作“外号儿”,又叫作“妖绰”;其中“绰”字就读如“操”。
《士冠礼》注:杀犹衰也。《地官·廪人》注:杀犹减也。旧皆音所界反。《广雅》:杀,减也……今人谓水浆愈渴为杀渴,姜蒜除腥为杀腥气,义皆训衰训减。[1]39
陕西方言“杀”的“减,减去;去掉”义用法如“杀毒”即“减去毒素”,再如“杀腥气、杀膻气”分别指“减去鱼腥味、减去羊膻味”。鄠邑把一批货物很快被买光叫作“杀货”,例句如:这个地方的人有钱,杀货得很,一车苹果拉来不到两个钟头儿就卖完咧。
胡、倭、蛮,四裔之国也。今谓行事无条理、语言无伦次曰胡……凡专擅自恣者通谓之蛮。[1]46
我们认为章先生认定的用作副词的“胡、蛮”的语义是正确的,这在当初的确有汉族对少数民族的歧视因素。“胡”在官话如《新方言》里的用法可从《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第531~532页看到许多例词[7],陕西方言的用法可从《都市方言辞典》(陕西卷)第200~201页中看到许多例词[8],请分别参阅;这里补充一条陕西方言跟“胡黏面罐子”义同的惯用语“胡黏面馆子”,也是“胡说八道,胡搅蛮缠”的意思。陕西方言“蛮”有“鲁莽;语言难懂”等意思,请参阅《都市方言辞典》(陕西卷)第254页;再如关中平原地区的人把山里人叫作“山蛮子”,远离河滩的人把距离河滩很近的人叫作“滩蛮子”,旧时关中方言把豫剧叫作“蛮子戏”;再如商南人把赣语区移民的方言叫作“蛮子话”,商南方言的主体是“蛮子话”,这种叫法很可能是当地土著居民早先对赣语区移民方言的叫法。“蛮子”含有歧视因素和贬义。
《说文》:东,动也……自西安以至四川皆谓自作不靖曰东乱子,亦曰东祸。[1]78
以上章先生以阴平字“东”来表示“闯乱子”的语义最少不符合西安一带方言实际。西安一带把“弄脏”叫作“董”或“董脏”,把“闯乱子”叫作“董乱子”。其中上声字“董”可能是本字。清代小说《歧路灯》(作者李绿园,1707—1790,河南人)第26回:“后书房原叫戏子们董坏了,还得蔡湘着实打扫打扫。”第27回:“这事多亏我到,若叫你们胡董起来,才弄的不成事体哩。”第99回:“我不长进,董了个昏天黑地。”第102回:“像我这大儿子不成人,几乎把家业董了一半子。”清代关中渭南皮影戏作家李芳桂(1748—1810)剧作里把此字写作“挏”,例句如:“前日验尸挏成酱。(《香莲佩》第38回)”我们认为“挏”不是本字,音义均与陕西方言不符。“挏”在《广韵·上声董韵》[11]跟“动”同音,按照古今语音对应规律,普通话读作dònɡ,《说文解字·手部》:“挏,拥引也。”是“来回摇动、拌动”的意思[9],跟“董”在近代汉语及陕西方言的两个常见义项无关。李荣先生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第5册第4199页收录了河南洛阳方言的“董”,解释为“挥霍家业财产”,举例为“他把家业董了,到他这一辈算完了”[10],其语义与西安一带的“闯乱子”很近。
《墨经》:佴,自作也。字从声转作耳。《汉书·司马迁传》:而仆又茸以蚕室。《文选》正作佴。庾信谓随意自恣出入曰佴进佴出,即自作义。佴、茸皆耳声。[1]78
“佴”字普通话读作èr,关中方言例外地读如“耳”。关中中东部是“搁,搁置”的意思,西部是“扔掉,扔弃;丢,遗失”的意思。《说文解字·人部》:“佴,佌也。从人,耳声。”徐锴《说文系传》曰:“佴,此也。”[9]《广韵》反切为“仍吏切”[11]。《汉语大字典》(一)第144页第一义项为“相次,随后”[12],今关中方言的用法为引申义。“佴”字宝鸡一带及乾县、长武等处读作[⊂әr],鄠邑读作[⊂],洛川、宜君、铜川、耀州、白水、富平等处读作[⊂z]。
今直隶、淮西、江南、浙江皆谓寝曰困。[1]87
陕南方言区佛坪等处把睡觉叫作“困觉”,柞水凤凰镇把睡觉叫作“困醒”。
《庄子·外物》篇:螴蜳不得成。《释文》郭音陈惇;司马读曰沖融,言怖畏之气沖融两溢,不安定也。按:螴蜳犹言佂伀。淮南谓假寐暂觉为螴蜳,上音如沖,下音如惇。吴越曰打磕螴,音如沖。[1]87
如上章先生所讨论的实质上是“打盹儿”的叫法,章先生所写的“沖”的本字应是“舂”。陕南方言区石泉、镇坪、平利、白河、镇安、柞水把“打盹儿”叫作“舂瞌睡”,柞水曹坪镇叫作“舂瞌困”,商南叫作“舂颚”。
三、从《新方言·释亲属第三》看陕西方言
《方言》:崽者,子也。郭璞音宰,今通谓子为崽。成都、安庆骂人则冠以崽字,成都音如哉,安庆音如簪。[1]95
其一,关中人亲昵地骂爱捣蛋的孩子为“崽娃子”,其中“崽”字读如“哉”。例句如:这崽娃子心眼儿多得很|几个崽娃子劳神得很。《广韵·皆韵》:“崽,自高而侮人也。”[11]《汉语大字典》(一)第786页第三义项引用《天录识馀》:“崽,今北人骂顽童曰崽子。”[12]
其二,关中方言无“崽”读如“簪”的,而普通话ai韵母字读作an韵母可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副词“还”在华阴、合阳、宜川、黄龙、洛川、宜君、耀州、蒲城、白水、长武等处读如“含”;二是长武阳平字“排埋鞋台抬才(人才;时间副词)材豺柴呆(呆板)崖捱来”等读作an韵母。另外,长武“怀”字读如“环”。
四、从《新方言·释形体第四》看陕西方言
《说文》:颡,额也。苏朗切。西安谓头曰颡,开口呼之如沙。此以小名代大名也。[1]97
关中方言对于动物头的叫法可以鄠邑为例来说明:鸟、虫豸等多叫作“”,如雀儿(麻雀)、鸽鹁儿(鸽子)、鹌鹑儿、鸡(家禽也可以叫作“头”)、长虫(蛇)、虫儿(蚕);牲畜、野兽等多叫作“头”,如牛头、猪头、羊头、狗头、老虎头。但是,马头叫作“马”,有一条惯用语“鸡骨头(=独)马”,指乌合之众。

《说文》:脬,旁光也。今人皆谓旁光为脬。[1]102
关中很普遍地把膀胱叫作“尿(=脲)脬”(鱼“尿脬”的“尿”读如“虽”),其中“脬”读如“抛”。另外,关中把表示大小便频次的量词叫作“脬(=袍)”,如“尿了两脬(=袍)”。
《说文》:尻,从尸,九声。今山西平阳、蒲绛之间谓臀曰尻子,四川亦谓臀为尻子,音稍侈如钩,九声之转也。[1]103
关中许多人包括笔者曾经长期认为章先生所认定的读如“钩”的“尻”是当地指称屁股的本字,张振兴、张惠英先生《从“沟、溪”说起》认为“沟”才是本字[13],请参阅。
五、从《新方言·释宫第五》看陕西方言
《说文》:霤,屋水流也。《左传》:三进及溜。《释文》:溜,屋霤也。[1]107
孙立新《陕西方言纵横谈》第42页指出:鄠邑把山墙的“檐头”(即隔火墙)叫作“霤水”[14]。另外,鄠邑把“霤水”顶部苫盖的瓦叫作“霤水瓦”。
山西平阳言墙声在墙、序之间,转入近鹊。[1]107
章先生这里所讲的实质上是平阳方言“墙”字音近于“鹊”,关中东部韩城、澄城“墙”字读作[io]韵母,如澄城“墙”字读作[tshio24];澄城“墙”字跟“鹊雀[tshio21]”声韵一致。
六、从《新方言·释器第六》看陕西方言
《尔雅》:茅,明也。郭璞引《左传》前茅庐无杜解云:茅,明也。凡标识明目者皆得云茅,今语为苗,《土相见礼》草茅古文作苗,今人呼矛音亦如苗。[1]113
关中方言区很普遍地把“矛”字白读如“苗”,白读语境为“矛子”,指长矛;文读如“锚”。
《说文》:箸,饭敧也。今惠、潮、嘉应之客籍谓饭敧为箸隻。其余通谓之夬,读若快。[1]116
其一,关中多数方言点对筷子笼的叫法里用到“箸”字,如西安、临潼、洛南叫作“箸笼儿”,商州、丹凤、潼关、三原叫作“箸笼子”,泾阳叫作“箸笼罐子”,礼泉、蓝田、鄠邑叫作“箸笼”,宝鸡、咸阳一带叫作“箸篓罐”。
其二,关中通常把筷子还叫作“筷子”。章先生所写“快”,官话后来写作“筷”,张成材先生《陕甘宁青方言论集》对“箸”到“快”,再到“筷”有深入讨论[15],请参阅。
《说文》:鞔,履空也。母官切。《广雅》:鞔,补也。今人谓以革补履头为鞔鞋,张革冒鼓亦曰鞔鼓……《仓颉篇》云:鞔,覆也。《一切经音义》引。是鞔鼓义。[1]121
如我们对“鞔”的考据,《广韵》母官切:“鞔,鞔鞋履。”改革开放前,西安一带民间的丧葬习俗,孝子要穿白鞋,把白布缝在布鞋上叫作“鞔白鞋”或“鞔鞋”。假如父亲去世、母亲健在,必须把脚后跟留出来,忌讳“鞔”完;母亲去世后才可以“鞔”完。请详阅孙立新《户县人的“计较儿”和忌讳》[16]。
《吕氏春秋·开春论》:灓水啮其墓,见棺之前和。高诱曰:棺头曰和。今浙江犹谓棺之前端曰前和头,音如华。淮南谓题字于棺前端曰题和,音如壶。[1]125
七、从《新方言·释天第七》看陕西方言
今陕西、四川皆谓夏月暴雨为偏涷雨……亦曰白雨,广东谓之白撞雨。[1]131
关中很普遍地把夏天的暴雨叫作“白雨”,特别大的暴雨如瓢泼大雨叫作“大欻欻白雨”或“大漴漴白雨”;孙立新等《西安方言俗谈》对“漴”字的考据[19]如《集韵》平声江韵锄江切:“漴,雨急谓之漴。”[6]又,去声漾韵助亮切:“漴,雨疾下。”按:上文章先生论及“广东谓之白撞雨”,其中“撞”的本字很可能就是“漴”;如关中方言“创撞漴”声韵相同。
湖北谓雨而木冰为油光凌,读去声。[1]132
陕南镇安、柞水等处把冻雨叫作“油光凌”,其中“凌”字读作阳去调如“令”。
《说文》:凊,寒也。七正切。福州谓寒为凊,若通语言冷也。[1]132
陕西方言把食物凝固叫作“凊”,西安等处读如“庆”,例如:臊子凊住了;凊皮(稀饭表面凝固得像皮一样的东西)。《玉篇·冫部》:“凊,七性切,寒也,冷也。”[18]因为食物凝固一般都是寒冷导致的,所以,“凊”的“凝固”义是引申的结果。
今淮西、浙江谓日昃时为下昼,惠、湖、嘉应之客籍谓之下晡头,广州仍言下昼。[1]132
陕南石泉、白河、岚皋、柞水、商南把下午叫作“下昼”。
八、从《新方言·释动物第十》看陕西方言
《方言》:蛄,南楚谓之杜狗,今通谓蝼蛄为土狗,或云地狗。[1]139
陕南紫阳把蝼蛄叫作“土狗儿”,镇巴叫作“土狗子”。
《说文》:孚,卵孚也。亦书作抱。《方言》:北燕、朝鲜、洌水之间谓伏鸡曰抱。今自江而北谓鸡伏卵曰抱,江南或转如捕。[1]141
以上“孚、伏”今写作“孵”,“抱”实际上是“孚、伏”的古音。关中方言很普遍地把“孵”叫作“抱”,如西安一带“抱”跟“报暴爆豹”等同音。而关中不少方言点“孵”义的“抱”如章先生所说的转音(音变)如“捕”,例如:泾阳读如“怖”或“补”,咸阳北部读如“怖”,铜川、千阳读如“瀑”。另外,西安一带把抱窝鸡叫作“罩毛鸡”,“毛”字在此语境只有白读音[mu24],当地把抱窝叫作“罩毛[mu24]”。
九、从《岭外三州语》看陕西方言
《岭外三州语》是章先生对惠州、梅州、潮州客话(即客家方言)部分词语来源研究的成果,我们从中找到两条与陕西方言本字“厖、啗”有关的内容。
《尔雅》:厖,壮,大也。《方言》:凡物之大貌曰丰厖。三州谓人肥大曰厖壮,亦曰丰厖。[1]155
扬子《方言》“丰、厖”有所区别,章先生当作一个词来处理是不对的。扬子《方言》卷一:“凡物之大貌曰‘丰’;厖,身之大也。”“厖”的异体作“”,《集韵》[6]莫江切:“,身大也。”西安一带“厖”读作[ma31]。多指人、特别是小伙子的块头大:小伙子长得~得很;复合词作“厖壮”,还有“厖实”;蓝田、乾县等处把大块头牛犊叫作“厖厖牛犊”。
《说文》:啗,食也。以食食人亦曰啗。[1]159
陕西方言“啗”读如“旦”。“啗”有两个异体字:“啖”和“噉”。陕西方言把给牲口喂熬制的中药叫作“啗药”。章先生的释义是:自己吃叫作“啗”(自动),给别人(当然可以包括动物)吃(以食shí食sì人)也叫作“啗”(使动)。如右是笔者对“啖”字的考据,请参阅《陕西方言纵横谈》[14]40页:《说文解字·口部》:“啖,噍啖也。”《广雅·释诂二》:“啖,食也。”《山海经·海外东经》:“黑齿国在其北,为人黑,食稻啖蛇。”《史记·滑稽列传》:“啗以枣脯。”《汉书·王吉传》:“吉妇取枣以啖吉。”颜师古注曰:“啖,谓使食之。”《世说新语·任诞》:“籍饮噉不辍,神色自若。”李白《侠客行》云:“将炙啖朱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