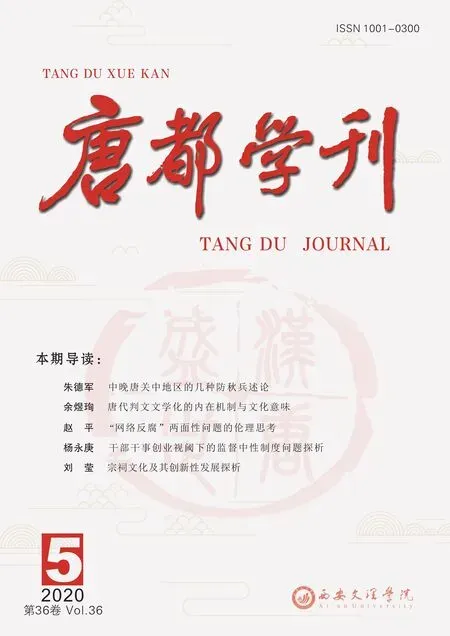唐代舍利瘗埋制度之“金棺银椁”探析
沈雅彤
(山东大学 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济南 250100)
佛教自两汉时期传入中国,舍利信仰便在这片文化土壤中发芽生根。中国的舍利信仰,一方面传承于印度佛教,历代宗师以佛经中有关舍利信仰的内容为参照如法供养,另一方面受到中国本土文化氛围的影响,人们以自己的生存境遇为标准有选择地接受舍利信仰。佛经传入中国的数量是浩瀚的,里面有关对舍利塔的记述十分丰富,不同思想体系对舍利塔的阐释是不同的,在历史的选择下,各个时代形成了特色鲜明的舍利信仰。在唐代舍利信仰中有一个创新性的举措,他们将棺椁元素添加在舍利瘗埋制度中。根据考古发现,舍利的瘗埋制度虽然在每个朝代都有些许的不同,但是他们的形制都是一脉相承的,唯有到了唐代“金棺银椁”因素创造性地出现在了舍利瘗埋制度中。
舍利与棺椁的结合之所以被称为创造性地碰撞,源于两者所内涵的思想本身是平行无交集的,两种思想的融汇势必会有耳目一新之感,不禁让人探求这一文化现象背后的深意。舍利作为佛陀解脱思想的象征,所表之法是超脱尘世思想和情感的,棺椁为礼法的象征,是世间制度表现之极致。在佛经里对舍利瘗埋的详细描述中明确表明棺椁与舍利之间的界限(1)参见释法显译《大般涅槃经》。,阇维之前涅槃后的法体被层层安置于金银铜铁的棺椁中,阇维之后舍利内金瓶中即起佛塔,“金棺银椁”的舍利瘗埋制度公然打破这一界限,直接以世俗表征浓厚的棺椁来供养舍利,这是否意味着当时佛教的神圣性与现实的世俗性之间的界限被打破了?透过现象看本质,作为佛教产物的舍利瘗埋之变异唯有从佛教思想史视角予以解读。舍利信仰按照印度的形制传入中国且发展至唐初都未有棺椁的身影,而武后改造原始形制以金棺银椁供养、瘗埋舍利,我们当然可以将其看作是一个偶然事件直接引导棺椁瘗埋舍利的蔚然成风,也可归因为审美、技艺、材质等诸多因素变化的结果,然而舍利瘗埋作为一种佛教的信仰形式,这一转变必然是以其背后佛教观念的转变作为支撑。通过从佛教思想史的视域下对棺椁瘗埋舍利现象的探因,为佛教研究提供了一种新思路,佛教物质文化与思想史之间是存在互证关系的,佛教思想可以解答现象的产生,同时现象也是思想特性之显发,佛教物质文化可以对佛教思想进行更多面的写照,更丰富地理解一个历史时段中的佛教。正如棺椁瘗埋舍利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唐代佛教荒诞而又真实的图景,这是理解唐代佛教的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对此现象的深刻解读可以看得到一个情理之中又意料之外更加活泼的唐代佛教。
一、唐代舍利瘗埋制度的形成
舍利瘗埋还要从舍利信仰说起。印度佛教中有一支思想体系是关于舍利信仰的。佛陀一生广转法轮,将自己菩提悟道的真理说予身陷苦海的众生,佛法真切触动人心,使佛陀有了一众追随者,他的教团越来越壮大,但是身处现世的佛陀总归要示现涅槃,对于这件事他的弟子都深感惶恐。为了让他所讲之法能够传承利益更多的人,也为了让弟子有一份情感的皈依处,佛陀为他们讲述了涅槃后的舍利信仰。《金光明经》中认为舍利“是无量六波罗蜜功德所熏”,“是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2)参见昙无谶译《金光明经》。,换句话讲舍利是佛陀修行成就之体现。它的存在一方面是对佛法的体现,在没有佛陀说教的情况下向众生继续示现佛法,另一方面给予人成佛的信念和希望,舍利代表了佛法的真实不虚,里面传递出佛陀的精神力量使人们坚定成佛的脚步。舍利在佛教语境下被赋予至高无上的意义,它与佛陀的地位相等自然也受人供养。“阿难!若佛灭后,若复有人,深心供养如来舍利四分之一、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百分之一、千分之一、万分之一、恒河沙分之一,乃至如芥子许,皆以深心供养、恭敬、尊重、赞叹;若佛现在,若复有人,深心供养、恭敬如來。如是二人,所得福德皆悉无异,其福无量不可称计。”(3)参见若那跋陀罗译《大般涅槃经后分》。供养舍利与供养佛的意义是相同的,都可以得到甚深利益。供养思想成为舍利信仰中的一部分,如何如法供养则成为舍利信仰中的重要表现形式。在《长阿含经》中,弟子阿难问佛,佛陀灭度后应该如何,佛陀回答:“阿难!汝欲葬我,先以香汤洗浴,用新劫贝周遍缠身,以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毕,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旃檀香椁次重于外,积众名香,厚衣其上而阇维之。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上天。”(4)参见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首先进行葬仪,待葬仪结束后将舍利收集起来,把他们带到四通八达的大路上建立塔庙,使行人都可以瞻仰到佛塔,从而思慕佛法,获得大利益。
佛经中有关舍利信仰的内容包括:舍利是什么、舍利的价值、如何供养舍利,起塔供养舍利是对舍利信仰描述的最后一步,但是在现实中却存在着入住佛塔后的舍利应以怎样的形式接受供养等问题。建于阿育王时期位于桑奇的三座佛塔,向人们展示了印度佛教中舍利在佛塔中是如何被供养的。桑奇的三座塔分别是大塔——据说用以供奉佛陀舍利、二塔——供奉阿育王时期十位长者的舍利、三塔——存放舍利弗与目犍连的真身舍利。19世纪初期桑奇三塔重新进入人们的视线,同时他们也遭到最野蛮的考古挖掘,在对存放佛陀舍利的大塔进行考古挖掘时,由于之前粗暴的行为甚至没有找到石质的舍利罐。虽然没有形象地看到佛陀舍利是如何被瘗埋在佛塔中的,通过另外两座塔挖掘后的联想和推测,舍利应该是被放入特殊设计的舍利圆罐中,埋藏在覆钵式佛塔的中心位置(如图1)[1]。当舍利信仰跟从佛教传入中国后,舍利存放的容器、瘗埋的形式、甚至是供养的佛塔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佛教传入中国后,供养舍利与舍利塔似乎成了同义词,只要有舍利定会起塔供养。据文献记载推测,早在三国时期便出现了舍利塔。南北朝是舍利塔和舍利瘗埋制度的发展时期,直到隋代实现了舍利塔的繁荣和舍利瘗埋全国范围内的统一。[2]10隋代的仁寿元年、二年、四年分别于三十一州、五十余州、三十余州建立舍利塔。“据王劭所记,仁寿元年天下各塔于十月十五日午时安入塔内石函;据安德王雄等记,二年于四月八日午时入函,礼式均极隆重。”[3]隋代的舍利瘗埋是在皇室的主导下进行的,不仅形式同一,而且对当时舍利瘗埋产生了直接影响,形成了一个正式且统一的标准。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受隋文帝主持建塔供奉舍利的事件影响,隋代舍利容器组合形成了较为统一和固定的模式[2]59。在《广弘明集》中的《舍利感应记》中记载,“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座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瑠璃各三十。以瑠璃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薰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5)参见释道宣《广弘明集》。隋代所确立的舍利瘗埋容器的基本组合为:函+瓶(如图2)[4]。通过考古发现,隋代的函为两重,即石函和容纳其中的铜函,而舍利瓶通常为琉璃瓶。唐代舍利瘗埋容器组合便是在这个基础上形成的。

图1

图2

图3
唐代舍利瘗埋制度是在隋代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直到唐初年间仍然延续隋代旧制,舍利瘗埋制度的转折为唐高宗、武后时期。唐初瘗埋制度虽然容器形式和质料多样,但是归根是对“函+瓶”制度的继承,万变不离其宗,然而唐高宗、武后时期出现了棺椁这种新型舍利瘗埋容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记载高宗显庆五年宫中将迎供法门寺的佛骨舍利,“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疋,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凋镂穷奇。”(6)参见释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这是文献中有关棺椁制度最早的记载,学界一般认为舍利的棺椁容器肇始于这个事件,武则天是棺椁瘗埋的发明者。
法门寺的舍利瘗埋制度应该代表了唐朝的最高水平。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基地宫是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大的,这与皇室关系密切,唐朝历代皇帝对寺中舍利青睐有加,对其进行最大程度的扶持和资助,这便增添了其皇家寺院的色彩,里面的设置也是当时寺院中的最高级别。当然从地宫中出土的文物也印证了这种说法。地宫中一共出土四枚佛骨舍利,除一枚佛骨舍利是存放在“檀香木函+鎏金四天王银函+素面银函+鎏金如来银函+六臂观音金函+金筐宝钿珍珠状金函+金筐宝钿珍珠状石函+宝珠顶单檐四门金塔”[2]164这种组合的容器中,其他三枚分别被存放于“汉白玉双檐灵帐+铁函+鎏金双凤纹银棺”“汉白玉彩绘阿育王石塔+宝刹单檐铜塔+迦陵频伽纹银棺”“铁函+鎏金金刚界大曼荼罗成身会造像银函+银包角檀香木函+嵌宝水晶椁子+玉棺”(如图3)[5]165这样的组合中。法门寺的实例说明棺椁已经成为当时主流的瘗埋容器。
唐代创造性地使用棺椁容器盛放舍利这种现象引发了笔者的思考,不仅是因为它的创新性,更大的原因在于棺椁本身的意义和其背后所隐藏的思想。隋代的瘗埋容器组合为“函+瓶”,在汉语语境中“函”是一种平常的容器,如“经函露湿文多暗,香印风吹字半销”中,函便是用来装载书籍的工具,而“瓶”也是一种日常容器,可以用来盛水或是酒等。两者是一种常见且常用的容器,他们本身没有特定的意义和指向性,但是唐代所启用的“棺椁”之所以引人深思,是因为这种容器的指向性非常明确。“棺椁”实为棺和椁,棺用以敛尸,是安放遗体的器物,而椁的意义相对宽泛,统指外面所加之物,但是与棺连用表示套于棺外的大棺。用以装载舍利的容器不断特殊化和指向明确化,意味着人们对舍利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不再笼统地看待它,而对其赋予某种特殊的意义。显然,用棺椁装载表明当时的人们更愿意将舍利当作佛之遗骨,由此对待舍利的情感也在向世俗化转变。
二、从金瓶到棺椁——舍利容器变化与意义变迁
以棺椁作为舍利容器是一种中国特色十分鲜明的舍利瘗埋制度,是舍利信仰来到中国后所进行的创造。回顾舍利瘗埋的原貌,它在佛经中呈现出与此迥然相异的形态。《长阿含经》中,“时,阿难复重三启:佛灭度后,葬法云何?佛言:欲知葬法者,当如转轮圣王。……佛告阿难:……阿难!汝欲葬我,先以香汤洗浴,用新劫贝周遍缠身,以五百张叠次如缠之。内身金棺灌以麻油毕,举金棺置于第二大铁椁中,旃檀香椁次重于外,积众名香,厚衣其上而阇维之。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上天。”按照佛的意图,在佛灭度后,按照转轮王的葬仪来安置,先将遗体放入金棺之中,再将金棺放入铁椁之中,铁椁之外再围旃檀香椁,这一切的准备都是为接下来的阇维(7)阇维:梵语,指往生后火化。意义同“荼毗”。做准备。阇维结束后便是舍利信仰的第一步和最重要的一步,即讫收舍利起塔供养。这个步骤在佛经中同样也有记载。在《大般涅槃经》中:“阇维既竟,收取舍利,内金瓶中,即于彼处,而起兜婆,表刹庄严……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上天。”舍利应收入金瓶中,随即起塔供养。棺椁只用于对佛陀遗体处理的阶段,舍利生成后便置于瓶中,放在舍利塔内进行供养。然而,唐代的舍利瘗埋制度,将棺椁应用于对舍利的装载,且供养于舍利塔内。装载舍利的容器发生了变化,这似乎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只要我们深入思考容器背后所隐含的意义,这一微不足道的变化就不是偶然,而是承载了当时人们对舍利信仰的思想变化和情感转向。
1.唐之前舍利装载容器:供养情怀、以奢为旨
也许是严格按照佛经中的规定,隋代的舍利瘗埋制度——“函+瓶”与前文佛经中所提到的“收取舍利,内金瓶中,即于彼处,而起兜婆”的形式相符,用瓶收取舍利在佛经中是一种普遍的现象,这种容器的本身并没有特殊的含义。如在《大般涅槃经后分》中,“尔时,四天王各作是念:我以香水注火令灭,急收舍利,天上供养。作是念已,即持七宝金瓶,盛满香水,复将须弥四埵,四大香洁出甘乳树,树各千围,高百由旬,随四天王同时而下至荼毘所。树流甘乳,注写香瓶,一时注火。注已,火势转高,都无灭也。尔时,海神莎伽罗龙王及江神、河神,见火不灭,各作是念:我取香水注火令灭,急收舍利,住处供养。作是念已,各持宝瓶盛取无量香水,至荼毘所一时注火。注已,火势如故,都亦不灭。”四天王与海神、江神、河神分别持七宝金瓶和宝瓶,内注香水以灭阇维之火。在这段经文中,瓶变为用于盛水的工具,由此可推测“瓶”在当时是一种常用且用途甚广的容器,它并非装载舍利的专属。瓶的广泛用途使得它的意义极为普通,仅仅为一种装载的容器,它与舍利之间也没有特定的关联,并不能给予舍利附加意义。
舍利的载体虽不挑剔但却十分庄严。如《大般涅槃经后分》中对讫收舍利的描述:“其城内人先已遣匠造八金坛,八师子座,各以七宝而为庄严,其七宝坛各受一斛,各置七宝师子座上。……尔时,世尊大悲力故,碎金刚体成末舍利,惟留四牙不可沮坏。……尔时楼逗与城内人涕泣盈目,收取舍利,着师子座七宝坛中,满八金坛,舍利便尽。尔时,一切天人大众见佛舍利入金坛中,重更悲哭,涕泣流泪,各将所持深心供养。”金坛也可以用来盛放舍利,只是金坛被进行了精心的打造,同时前文佛经中提到“收取舍利,内金瓶中”,此处也特地强调为金瓶。对容器的精美制作和高质料要求表现出人们对舍利的尊崇和供养情怀。《金光明经》云:“舍利是由戒定慧之所熏修,甚难可得,最上福田。”舍利作为戒定慧熏修之产物,似乎变作佛陀遗留在世间的真身,时刻提点世人坚守舍利中蕴含之正法,为众生增长成佛信心[5]。舍利容器的高规格,除了以崇敬之情对待佛陀于世间珍贵遗法的原因之外,还受到供养思想的影响。
“讫收舍利,于四衢道起立塔庙,表刹悬缯,使诸行人皆见佛塔,思慕如来法王道化,生获福利,死得上天。”(8)参见佛陀耶舍共竺佛念译《长阿含经》。对舍利的供养在佛经中有诸多论述,这段经文中表明,将舍利讫收于佛塔供养,生时可以有福德,死后亦可以早日摆脱轮回之苦。有现实利益和得解脱支撑着舍利供养的信仰,而其中更加重要的是解脱成佛。《大般涅槃经后分》中阿难的一段对佛陀的陈白详尽表达了供养佛陀的意义所在。“阿难白佛言:如来出世悲愍众生,显示十力、大悲、四无所畏、十二因缘、四谛之法、三解脱门,八种梵音雷震三界、五色慈光遍照六道,随顺众生心业所转,或得四果三乘所行、或证无漏无为缘觉之道、或入无灭无生菩萨之地、或得无量诸陀罗尼、或得五眼、或得六通、或脱三恶、或出八难、或离人天三界之苦。如来慈力清淨、如来解脱法门不可思议,乃至涅槃,一切世间人天四众起七宝塔,供养舍利得大功德,能令众生脱三界苦、入正解脱。以是因缘,佛般涅槃,一切世间人天大众,报佛甚深无量慈恩,起七宝塔供养舍利,理应如是。”佛作为大觉悟者,以将世界真相展现在众生面前为己任,他自身把对众生所说之法都修行到了极致,因此才会有赞叹性的语言来展示他的境界,如“显示十力、大悲、四无所畏、十二因缘、四谛之法、三解脱门”“八种梵音雷震三界、五色慈光遍照六道”“得四果三乘所行、或证无漏无为缘觉之道、或入无灭无生菩萨之地、或得无量诸陀罗尼、或得五眼、或得六通、或脱三恶、或出八难、或离人天三界之苦”等。信仰者认为佛陀的道路是根本的,毕生所愿早成佛道,唯有坚守佛之法门,赞叹佛之境界,在佛灭度后供养佛的舍利像供养佛一样,才能真正跟随佛陀的脚步,出苦海成佛道,从而获得“大利益”。所以供养舍利在修行成佛的过程中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供养的形式又常常表现在将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奉献于供养物,舍利容器是舍利供养的一个方面,因此佛经中表现出来对容器形式和质料的较高要求。
2.唐代舍利装载之棺椁容器:世俗情感的表征
佛经中不乏对棺椁的记叙,佛陀灭度后的仪式中棺椁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是佛经中也十分明确地说明棺椁应该在什么情况下使用,荼毗之前用棺椁,生成舍利后便要“内金瓶中”。经文中佛陀遗体和舍利所呈现出的气象是十分不同的,佛陀作为证悟者,虽然其遗体可被视为全身舍利,但是按照佛陀遗训荼毗是必不可少的过程,这是当时印度最普遍的一种葬仪形式,这个过程与世俗的做法并无二致,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如悲伤、沉痛等许多世俗的情感,棺椁即用于遗体荼毗的过程中。当葬仪结束舍利产生之后便出现了另外一番图景,怀着至诚、崇敬的情感顶礼舍利。舍利的出现是对葬仪的升华,人们寄托其中的是超越世俗的宗教情感。舍利摆脱生死离别的消极情感,而将自身升华为佛法之结晶,使得人们去崇拜、赞叹和供养。从棺椁到瓶的容器变化就可以感知到两者的性质转变。棺椁在世俗葬仪中使用极为普遍,是荼毗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之后出现的舍利其意义超越了整个世俗世界,棺椁已经装不下这种高深的意义,唯有用供养性质的容器才能与佛陀真身的象征和延续的意义相契合。然而,唐代将棺椁延续到舍利装载的环节,这金棺银椁居然可以“装得下”无上之舍利。佛经中舍利容器的日常性无法赋予它额外的意义,即不能从容器中解读出当时舍利信仰的独特之处和情感取向,只能从较高的规格体会到供养思想,唐代的舍利容器却总是给予我们更多的信息。
棺椁是唐代常见的葬具。唐代的等级制度十分明确,深刻地影响了葬礼甚至是葬具的选用。“考古发现的唐代石椁、石棺、石门、石棺床等的使用者身份多在三品以上,只有极个别的身份较低,说明以石棺作为葬具在唐代有严格的等级规定。”[2]168石质的棺椁已经被用于有一定的身份地位之人,更何况是金棺银椁呢!“金棺银椁”几乎将唐代的葬仪发挥到了极致。最高级别的葬具一方面说明他们将佛陀作为这世间最高贵的人来对待,以这种方式夸张地拔高,使佛有了至尊的意味,而另一方面葬具代表对离开世间人们的追悼,越是对现实有生死执着,越是将世俗的情感寄托在葬礼之上,再殊胜的葬具也无法改变其世俗意义的内涵。用棺椁装载的舍利不再意味着是对世间的超越和升华,而是佛陀现实中遗体的延续,他们将此生不能值遇佛陀的遗憾和佛陀灭度的悲痛寄托其上,更多的是对世俗情感的凸显而非关注出世的解脱思想。
在《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中武后提出以金棺银椁的形式供养佛舍利虽是棺椁瘗埋的肇始,然而棺椁瘗埋制度的出现并非武后一时兴起的偶然之举,它是在一个世俗超越神圣的时代背景下慢慢成形的。此时何以会出现装载舍利的棺椁容器呢?冉万里先生认为可从《全唐文》第九十五卷中《禁葬舍利骨制》中窥得一二,“释氏垂教,本离死生,示灭之仪,固非正法。如闻天中寺僧徒,今年七月十五日,下舍利骨,素服哭泣。不达妙理,轻徇常情,恐学者有疑,曾不谤毁。宜令所管州县,即加禁断。”[6]大致文意为:释迦牟尼佛本是教导人们脱离生死轮转苦海,佛陀示现的灭度并非究竟之法,如今听闻天中寺有僧人在七月十五下葬舍利,身着白色衣服伴随着悲伤的哭泣,形同世俗的葬礼,这种行为并没有通达佛教真正的法门,轻易地展现出世俗的情感,这样会使学佛之人产生疑问,难道不是毁谤佛法的表现吗?佛寺所在地的州县应该严加禁断。此事件从侧面说明唐代佛教中的世俗意味是极为明显的,人们尝试从世俗的处境和情感去理解佛教的事物。佛陀舍利本是佛陀灭度后出世佛法之象征,但是僧人们更愿意从熟知的现实去理解。舍利是佛的遗物,佛陀灭度如再生父母离我们而去,身心无所依怙,悲怆之情无法自已,哀伤之状无法自禁,舍利成为寄哀思的最好凭借,因此将舍利当做佛陀,在悲伤的情感中进行肃穆的仪式实在无可厚非。虽然武则天明令禁止这种仪式,认为这种行为使世俗情感掩盖了佛义妙理,无法通达佛教高深的境界,但是不可否认当时人们已经在舍利中注入了更多的世俗情感。人们更习惯于从自身的生存境遇去理解佛法,走上一条自下而上的超凡入圣之路。
三、“金棺银椁”制度探因
1.佛教中国化的开显
“金棺银椁”是佛教舍利信仰中的一个环节,这种新形式的瘗埋制度何以会出现,首先应该从佛教发展的角度去理解。经过汉魏两晋南北朝的发展,佛教在中国奠定了深厚的根基,进入唐代后佛教的发展更加繁荣,佛教理论深化且佛教宗派形成。如果说印度佛教传入中国犹如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播种下了一个种子,经过一段时间人们对它的接纳和在这个文化氛围中的自我改造,那么到唐代便是种子结出果实的时候,“中国佛教”完全真正地呈现出来。之所以被冠以“中国佛教”的名称,原因在于此时的佛教已不同于印度佛教,而包含了中国式的创新性思想。以在中国文化土壤中孕育出的佛教奇葩——禅宗为例。“禅”在印度佛教中除了“禅定”并无它意,而在中国却以“禅”创建了一个宗派,内里包括一套完整的成佛理论和修行体系。佛教中除了从印度传入的佛典被称为“经”,其他的著作便进不了“经”的行列,而禅宗六祖惠能之《坛经》成为在中国唯一被收录于“经”的著作,可见当时的禅宗已然进入佛教的主流且具有相当高的地位。禅宗并没有固守印度佛教的思想,“在惠能禅宗成立之前,传统佛教普遍重视禅定修习;包括达摩禅在内,所有禅法都没有脱离传统意义的禅定,未摆脱印度坐禅冥想修行的影响”[7]596,而惠能“彻底改变了人们对禅的传统认识,极大地开拓了禅者的视野,成为禅宗思想史上的重要转折。”[7]597禅宗对摒弃外缘收摄内心的禅法进行大胆发挥,认为本心即是“清净心”,不需要通过摒除妄心复归清净的方式达到一定的境界,这样反倒是对妄心和清净心都有执着。所以禅并非通过特定的方式到达一种较高的境界,而是体会当下这颗如如不动的本心,那么行住坐卧无非是禅。
通过解读禅宗的思想可知,中国佛教已经自成体系,宗派佛教的思想理论十分严密,创新性的特征非常明显。唐代的社会、文化、寺院经济等因素满足宗派佛教的形成,而宗派的形成又刺激着佛教思想不断深化和体系化。八个宗派的思想是在严密逻辑的基础上向前推进的,这种创新性是佛教思想在时代思潮处于领先地位的基础。唐代佛教沉浸在创新性的氛围中,因此“金棺银椁”这种革新的舍利瘗埋制度的出现便也无可厚非了。唐代具有从中国文化的角度去阐释佛教思想的大气象,宽容的氛围中滋生以世俗视角理解佛教,加之人们对佛经思想的解读已不拘泥于印度佛教,更何况是佛经中所介绍的宗教仪式。用传统的思维方式来看待舍利瘗埋不可避免地加入一些中国式情感,在当时的思想风气中这些世俗情感得以肆意发挥,“金棺银椁”的形式因此而被造就。
2.世俗化的崇佛走向
“金棺银椁”是世俗生活中一种极具身份地位象征的丧葬礼仪,所以探讨这种新型舍利瘗埋制度的出现不单要从宗教的角度,还应该探讨宗教与当时文化之间的关系。唐朝人对佛教的态度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可以通过“风向标”——唐代皇帝对佛教的态度来了解。唐代的历代皇帝,除了武帝发动“会昌法难”,其他均对佛教进行不同程度的扶持。无论这些皇帝自身在情感上是否信仰佛教,但他们对发展佛教的政策都是支持和提倡的。当然其中不乏有特别推崇佛教的领导者,这些领导者的风向标作用时刻感染着民众对佛教的态度。比如武后利用佛教论证其统治地位的合法化,她不仅亲自为佛经作序,而且积极推动法门寺佛骨迎奉活动,这些行为足以让民众对佛教产生起极大的热情,佛教信仰的潮流势不可挡。武则天在迎奉佛骨中有一个细节是将佛骨迎入宫中,置于明堂,《旧唐书》中记载:“夫明堂者,天子宗祠之堂,朝诸侯之位也。”“而武则天却将天子祭祀天地、祖先的圣堂用做用做瞻礼佛骨之所,其以‘佛’代‘天’的意图明矣!”[8]可见在世俗社会中,武则天已经将佛的地位上升到一个非常高的位置,可以与这个国家被推崇的最高价值等同。
佛教作为外来传入的宗教,在唐代宽容的文化环境中受到了各个阶层的推崇,最广泛的接纳便是世俗化的开端。一方面人们在情感上对佛教广泛接纳,另一方面佛陀的价值被拔高到极点,从这两点来说以“金棺银椁”礼遇佛陀舍利不足为奇,甚至是必然的。当时的社会依然秉持以礼为原则的社会秩序,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佛陀,必然会受到相应规格的安置,棺椁作为世俗之人最高的葬仪礼遇,“金棺银椁”用以配置佛陀舍利。社会对佛教的广泛接纳,对教理的理解也变得更加简单直接,“金棺银椁”是极高礼遇和人们内心尊崇之情的表现,同时也是更加贴近人们生活更加世俗的变现。
四、物质文化之于佛教思想史的重要意义
对佛教器物的研究,考古、文献、艺术、美学等学科在各自领域中的成果颇丰,对解读佛教发展之路做出了极大贡献,然而作为佛教物质文化之底色的佛学意识形态,学界鲜有从这一角度对佛教器物进行解读。佛学意识形态包括教义、仪式、宗教生活等,从宗教本身来解读佛教器物本应是最为核心的一步,而佛教物质文化一直游荡在佛教研究的边缘,其中的大部分未予以解读,他们内涵的价值对佛教研究的意义也未得以彰显。大多数的佛教器物从考古、文献、艺术等角度已经被进行了详尽的研究,他们的史实脉络清晰、形式特点清晰,对其彻底还原和解读奠定良好的基础的同时又差一步之遥,宗教视角是必然而又关键的一环。从宗教学视域对物质文化的解读不仅可以借助各学科之东风,将器物之原貌全然展现,而且最关键的是为宗教学本身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佛教器物是佛教生命力的体现,在这条生命线中的各个姿态又是佛教诸种特点的显发,那么从这个角度便能看到佛教在历史阶段中不同面貌的写照,更敏感地洞察到其历史特征。
舍利瘗埋的“金棺银椁”制度这一现象在考古界已被发现多年,它的存在如同定律一般无需多言且人尽皆知,而将其放于宗教学的研究领域它则更像是一朵奇葩,内涵无尽深意等待人们的关注。文章通过对“金棺银椁”现象进行历史爬梳、内涵解读、原因探析,使它在佛教思想史层面的样貌基本呈现,也为我们观测唐朝佛教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众所周知,唐代是佛教发展的繁盛期,宗派佛教争奇斗艳,而“金棺银椁”世俗化路径也是对繁盛期的另一种表现。在教界内部快速发展的同时,信众对佛教的接纳与理解也在持续上升,“金棺银椁”的普及意味着人们对佛教理解由圣入凡之风向,世俗化的走向虽不能算做宗教发展最理想的道路,但是理解的通俗性和接受的广泛性使宗教的民众基础持续增加,是佛教发展必不可少且实现跨越的重要一步。“金棺银椁”展现出唐代佛教繁盛时期之世俗化的一面,由此使唐代佛教的样貌更加丰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