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影成三人:论李渔《比目鱼》传奇中的“戏中戏”设置
《比目鱼》传奇是明末清初著名剧作家李渔的代表作品之一,该剧运用“戏中戏”的编剧技法,使全剧情节有机、紧密地联系起来,主题和人物性格得以彰显和拓深,舞台场面得到丰富和拓展,形成了虚实相生、精妙动人的独特观演效果,充分展现了李渔“结构第一”的整体戏剧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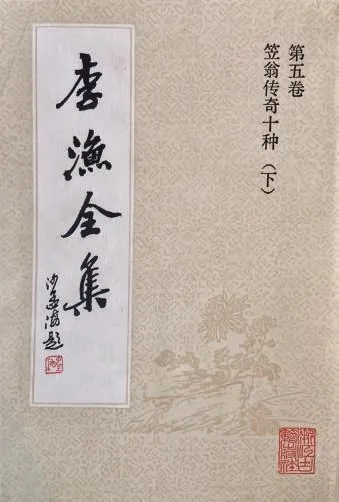
《李渔全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出版
一、从小说到传奇
“优伶”自古以来就是为世人所轻视、为写作者所忽视的群体。李渔移家金陵后,为了生计,常带着他的家庭戏班到各地达官贵人府上“打抽丰”,他不仅自己创作剧本,还要教育、训练演员,指导排戏,因而招来士林的不齿,“人以俳优目之”,他自嘲地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贱者居”。这些生活经历,使他对演员的生活状态和思想情感非常熟悉。
顺治十年左右,李渔创作了以演员为题材的小说《谭楚玉戏里传情·刘藐姑曲终死节》,他在文章开场中写道:“天下最贱的人,是娼、优、隶、卒四种,做女旦的,为娼不足,又且为优,是以一身兼二贱了。为甚么还把他做起小说来?只因第一种下贱之人,做出第一件可敬之事,犹如粪土里面长出灵芝来,奇到极处,所以要表扬他。”
小说讲述了贫苦书生谭楚玉因对女旦刘绛仙之女刘藐姑一见钟情,自降身份投身戏班学戏,如愿与藐姑做起了场上夫妻,不料绛仙贪图势利,逼女出嫁财主钱万贯,藐姑无奈之下,在一次演出《荆钗记》时假戏真做,投江明志,谭楚玉亦随之殉情,后幸得水神晏公、莫渔翁相助,两人死而复生,发达团圆。在叙事手法上,李渔以戏中人两次搬演南戏《荆钗记》写主人公一家之分离、团聚,形成了新奇巧妙的“戏中戏”结构,睡乡祭酒评曰:“令人自开卷称奇,直至终篇,无刻不欲飞欲舞。”
顺治十八年前后,李渔以这篇小说为蓝本创作了《比目鱼》传奇,传奇延续了小说“优伶有情”的主题,以谭楚玉和刘藐姑“初以目成,继以目语,而终以目比”的爱情故事为情节主线,歌颂夫妻之义,并在此基础上增设了君臣、义友的情节副线,使这部才子佳人戏增添了一些儒家治世、高蹈出世的复杂思想内容。在编剧技法上,“戏中戏”的运用仍是该剧的主要特色,在第十五出“偕亡”和第二十八出“巧会”中得到了充分展现,由于戏剧特有的剧场性情境和写作篇幅的扩展,比之小说更呈现出了多重“戏中戏”的特征。
二、“戏中戏”在《比目鱼》传奇中的运用
在《比目鱼》第十五出“偕亡”中,刘藐姑把《荆钗记·抱石投江》这出旧戏文改为新关目,借演戏痛骂土豪,陈情爱人,投水殉情。“偕亡”一出,实际上形成了三出戏的相互照映——演出人是一出戏(《比目鱼》),演的是一出戏(《荆钗记》),戏中还有一出戏(“藐姑做戏”)。
剧中,刘藐姑为了能顺利登场,先在后台演了一出“薄情寡义”的戏。她装出一副欢喜的模样,假意允诺钱万贯婚事,要他答应让她最后登一次台:“第一件,不演全本,要做零出。第二件,不许点戏,要随我自做。”谭楚玉误会藐姑变心,气得自认瞎眼看错了人,直感叹:“天地之间竟有这样寡情的女子?有这样无耻的妇人?”此处,藐姑扮演“无情”之人,以场下之“做戏”,埋伏接下来场上之“情真”;以场下之“无情”,埋伏其后场上之“痴情”。
接下来,藐姑正式演出《荆钗记》。《荆钗记》讲的是穷书生王十朋和佳人钱玉莲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王十朋才学出众,却家境贫寒,仅以荆钗为聘,娶得爱才不爱财的佳人钱玉莲为妻。春闱催试,王十朋上京赶考,和玉莲分开,他一举得中状元,却因拒绝丞相的招赘,被贬至偏远之地;其时,玉莲也因抵制继母逼其改嫁富豪孙汝权而投江自尽。后玉莲被人救起,这对节义夫妻最终团圆。无论是爱情的主题还是人物的命运,《荆钗记》和《比目鱼》都构成一种镜像式照映,在“抱石投江”这出戏中,藐姑演的是钱玉莲,唱的却是自己的心声:“遭折挫,受禁持,不由人不泪垂!无由洗恨,无由远耻,事到临危,拚死在黄泉作怨鬼!”宁死不嫁二夫的钱玉莲与刘藐姑,以角色之“痴情”,映射演员之“痴情”,以角色之命运,埋伏演员之命运。
先是“斥贼”,“钱玉莲”唱道:“我母亲,信谗言,将奴误。娘呵,你一心贪恋,贪恋他豪富。把礼义纲常,全然不顾!”玉莲所骂的“狠心的继母”,照映见钱眼开的刘绛仙。“钱玉莲”又指着台下观戏叫好的钱万贯骂道:“真切齿,难容恕!坏心的贼子,你是个不读诗书、不通道理的人。不与你讲纲常节义,只劝你到江水旁边照一照面孔,看是何等的模样,要配我这绝世佳人?”玉莲所骂的暗施诡计、强夺人妻的孙汝权,照映以财逼婚的钱万贯。

《李渔全集》,此图所述为“投江”剧情
然后是“诉请”。“钱玉莲”抱石投水前,回首望向后台的谭楚玉:“我那夫呵!你妻子不忘昔日之言,一心要嫁你;今日不能如愿,只得投江而死。你须要自家保重,不必思念奴家了!”“钱玉莲”嚎啕痛哭,谭楚玉亦哭。“伤风化,乱纲常,萱亲逼嫁富家郎。若把身名辱污了,不如一命丧长江!”她唱完此曲,霎时跳入滚滚江水。此时,刘藐姑与钱玉莲完全融为一体,戏与戏中戏融为一体,戏里戏外的人物命运也融为一体。
谭楚玉至此恍然大悟,在众人喧哗之际,他走到台前高叫:“刘藐姑不是别人,是我谭楚玉的妻子……他既做了烈妇,我不得不做义夫了。”“维风化,救纲常,害人都是这富家郎。他守节捐躯都为我,也拚一命丧长江!”亦急跳入江。此处,谭楚玉与王十朋完全融为一体,“殉妇”的动作,既是“抱石投江”这出“新编”关目的高潮,也是《比目鱼》剧情的高潮,场下喧哗呼救的观众,既是《比目鱼》剧中的“场下”人,又仿佛成为《荆钗记》戏中的“场上”人。戏与戏的照映,引出了演员与角色的照映,现实与戏剧的照映,命运与命运的照映,它们相互鼓荡,相互推动,相互映射,从而达到了人物动作的高潮,情感的高潮,情节的高潮以及主题的高潮。
再看《比目鱼》第二十八出“巧会”。戏一开场,谭楚玉和刘藐姑夫妇平安荣归,为了报答水神晏公救护之恩,要点戏为晏公祝寿,此处照映前文第十五出,戏班来此演戏也是为了给晏公祝寿。
谭楚玉派仆人去戏班打听,仆人回来说:“做戏的人,依旧是那班朋友,只换得一生一旦,做生的就是令堂。”此处照映前文因谭楚玉、刘藐姑投水,所以戏班生旦皆换。
谭楚玉得知刘绛仙在戏班顶替了“生”的位置,特意点名要刘绛仙演《荆钗记》中“王十朋祭江”一出,试其是否有悔过之心。谭楚玉点戏,派人要求刘绛仙“不做全本,只演零出”,“做完之后,再拿戏单来点”,照映第十五出中刘藐姑对钱万贯说的“不演全本,要做零出”,“不许点戏,要随我自做”。
接着是刘绛仙登场演《荆钗记》。“王十朋祭江”,照映前文“钱玉莲投江”,又照映刘藐姑投江;刘绛仙饰演王十朋,照映前文谭楚玉饰演王十朋。
刘绛仙睹物思人,祭的是钱玉莲,却哭起了藐姑:
我那妻呵!你为我完名全节,身葬波涛。如今做丈夫的,没有别样报你,只得这杯酒儿,求你再饮几口,(擎杯奠介)
【收江南】呀!早知道这般样拆散呵,谁待要赴春闱。便做到腰金衣紫待何如?端的是不如布衣,倒不如布衣!则落得低声啼哭,自伤悲!
(一面化纸,一面高叫介)我那藐姑的儿呵!做娘的烧钱与你,你快来领了去。(号啕痛哭,旦亦哭介)
【沽美酒】纸钱飘、蝴蝶飞。纸钱飘、蝴蝶飞。血泪染、杜鹃啼!俺则为睹物伤情越惨凄。灵魂儿您自知,俺不是负心的,负心的随着灯灭。花谢有芳菲时节,月缺有团圆之夜。俺呵!徒然间早起晚宿,想伊念伊,要相逢除非是梦儿里,再成姻契
刘绛仙悔悟,由戏中戏的“哭妻”转变为戏中现实的“哭女”,藐姑哭着答应,从舟中出来相见,原谅了母亲,一家团圆。此处,以“王十朋”哭妻之“真情”,照映刘绛仙此时之“真情”,又以刘绛仙此时之“真情”,照映她自己彼时之“无情”,照映谭楚玉、刘藐姑彼时之“真情”。无情者向有情者的转变,有情者对无情者的照映,使情真者愈见其真,“情义”的主题得以彰显。
两次“戏中戏”,成为推动人物关系和情节发展的重要关目:前一次戏中戏,谭楚玉夫妇投水,埋伏后文晏公等人之救护,钱万贯、刘绛仙之反目,刘绛仙之悔悟;后一次戏中戏,谭楚玉一家团圆,又勾连前文,使谭、刘之姻缘“因做戏而起,以做戏而终”。
两次“戏中戏”,角色和演员,戏剧和现实相互照映,使人物性格和人物关系彼此渗透,互相烘托。李白《月下独酌》诗云:“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比目鱼》中演员和《荆钗记》中角色的关系,恰如诗中的人、月、影——演员是实的,角色是虚的,虚实相生,如月如影。不写戏中戏,依然可写演员之“殉情”、“团圆”,犹如不写月、影,依然可写诗人之月下独酌,然而以戏中戏写“殉情”、“团圆”,因有烘托对比,情真者愈见其真,主题得以更加彰显,正如以月、影相衬,愈见诗人之孤独。

《李渔全集》,此图所述为“哭女”剧情
三、从“戏中戏”的运用看李渔“结构第一”的整体戏剧观
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提出,戏剧创作要以“结构”为第一,他认为:“至于‘结构’二字,则在引商刻羽之先,拈韵抽毫之始。如造物之赋形,当其精血初凝,胞胎未就,先为制定全形,使点血而具五官百骸之势。……工师之建宅亦然,基址初平,间架未立,先筹何处建厅,何方开户,栋需何木,梁用何材;必俟成局了然,始可挥斤运斧。”[2]从《比目鱼》的两次“戏中戏”可以看出,李渔“结构第一”的戏剧观念,不仅包含着一种系统性的意识,也包含着一种结构形式审美的意识。
首先,“戏中戏”的运用表明,戏剧创作不是从某一出、某一个具体情节开始,而是从整体构思开始的。从小说到传奇,“戏中戏”一直是这个爱情故事的重要结构,李渔在编剧第十五出的“戏中戏”时,已筹划好了第二十八出的“戏中戏”,在写后者时,又注意勾连前者,因而两次“戏中戏”的人物、情节乃至台词,都能前后照应,毫无疏漏,完整地体现主题。
其次,“戏中戏”的设置并非仅从情节结构出发,还包含着对舞台整体效果的考虑。李渔充分利用“戏场”、“戏中人”的概念,以精妙设计产生了多重“戏中戏”效果,这说明,李渔是把戏剧当做一个案头与场上并重的整体,来进行系统构思的,他注重剧场性,注重观众体验,追求统一的舞台艺术美,这和明人把戏剧当做曲词、文章来写的做法截然不同。
再次,两次“戏中戏”的镜像式对称,显示了李渔对形式审美的追求。对称设置,并非关目的简单重复,而是层层推进,层层照映,这样,各个部分不仅能严丝合缝,还能达到对称之美。这在明末清初,文人传奇普遍存在结构散漫问题的背景下,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注释:
[1](清)李渔:《李渔全集·笠翁传奇十种(下)》(第五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94页。
[2](清)李渔:《李渔全集·笠翁传奇十种(下)》(第五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9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