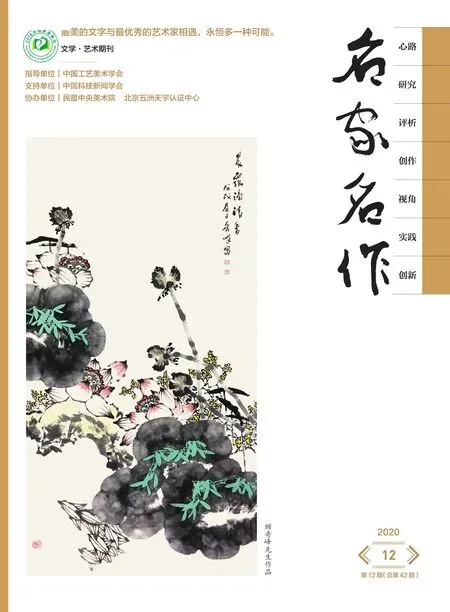小说叙述语言与作家族裔身份认同的建构①
——以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为例
任晓兵
蒙古族重要的民族作家玛拉沁夫在界定何为“少数民族文学”的时候,确定了“民族身份、民族题材、民族语言”这三个基本原则。玛拉沁夫阐述认为作家本人的少数民族族裔出身、作品描写的少数民族生活镜像、作品叙述使用的少数民族语言是界定少数民族文学范畴的基本因素。当然,这三个因素玛拉沁夫认为并不是完全并列的,其中作者的少数民族族裔身份应该是前提,即以作者的少数民族族裔身份为前提,加上民族生活的描写和民族语言的运用,或者两者之一,即少数民族文学。[1]在这个概念的描述中,作家民族族裔身份的确定是作家创作的文本是否可以被归为“少数民族文学”的基础和关键。
玛拉沁夫等20世纪五六十年代登上中国当代文坛的蒙古族作家,在他们那个特殊的风云岁月,玛拉沁夫等蒙古族作家自我的蒙古族民族文化意识并没有在小说文本中完全缺失,同样也表现出了对自我民族身份的强烈认同倾向。
一
民族认同是民族心理研究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近年来在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等领域被广泛关注的一个话题。作为一个概念,“认同”一词源于心理学。弗洛伊德是第一个使用这个概念的人,它指的是“个人与他人、群体或模仿人物之间的情感和心理趋同的过程”。[2]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这个概念在其他领域中应用的时候不断衍生出新的含义,但强调个人与群体,甚至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归属感是其共同的倾向。在民族学领域,民族认同是指“民族身份的确认”“是社会成员对自己民族族裔身份的认知和情感依恋”。[3]在文学批评的领域,它更强调自己的文化归属。
民族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国家认同的主观认识,体现为对自己的民族价值观、行为规范和文化传统的归属感,有很强的文化色彩”。[4]少数民族作家族裔身份的确定,也就是他们对其自我民族身份的“认同”过程。如何认知并确定自我的民族族裔身份,对于少数民族作家而言,他们往往会通过借助自我的文学创作实践来加以建构。少数民族作家借助文学想象表达对本民族文化、价值观念和宗教信仰的认同感,由此产生了以族属为中心的文学凝聚力。
“少数民族文学”文本中所具有的“民族自我认同”叙述一般体现在以下两个不同层面:显性维度与隐性维度。文本所叙述的情节内容、所表现的主题等是显性维度的体现;这个维度体现在文本中很容易被辨识。隐性维度主要指的是文本在叙述的语言、叙事的技法、形象的塑造等方面体现出来的信息。这个维度的信息往往是需要创作者和文本接受者的互动、文本接受者深层次地阐释解读,才能够加以明晰。本人重点阐述分析玛拉沁夫《茫茫的草原》一书中叙述语言与作家族裔身份认同建构的关联。
二
1951年的春天,时年二十岁的玛拉沁夫深入科尔沁草原体验生活,以牧民女青年塔姆的英雄事迹为原型,写作完成了短篇小说《科尔沁草原的人们》。小说的问世,预示着玛拉沁夫以少数民族作家的身份跻身当代文坛。从此以后,玛拉沁夫创作了一系列以内蒙古草原上蒙古族人民生活情境为内容的小说文本。这其中,以1957年出版、1963年修订后再版的《茫茫的草原》(上部)最为成功。《茫茫的草原》这部著作,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出现得最早的反映蒙古族生活镜像的长篇小说,它被认为是一部“在思想上和艺术上都取得了相当成就的好书”。[5]在这部“好书”中,蒙古族作家玛拉沁夫首先通过小说的叙述语言,完成了隐性维度上地对自我民族族裔身份的建构和认同。
安德森(Anderson, B)曾对“民族”(nation)做了一则著名的智性界定,民族是一“想象的共同体”——“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6]这个“共同体”的想象,“最初而且最重要的是通过文字(阅读)来想象的。[7]”“从一开始,民族就是用语言——而非血缘——构想出来的,而且人们可以被‘请进’想象的共同体之中”。[8]依托安德森的论述可知,语言是个体建构自身民族认同的最重要载体。
对于一位作家而言,母语写作带来的民族认同效果,需要作家本人的创作书写和文本接受者(指与作家同一民族的成员)的阅读体验来一并传达。但母语写作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作品的传播范围,比如蒙语写作的文学作品只是在蒙古族内部流传,没有蒙语语言基础的其他民族读者是无法阅读的。母语和民族文化相互依存的这种特定关系,使在民族文学的创作中单纯使用民族母语完成写作,这样建构出的民族认同效果带有不可避免的封闭性与狭隘性。在这种情况之下,非母语写作便应运而生。对于具有少数民族族裔身份的作家而言,非母语写作(主要指运用汉语进行写作)的民族认同效果肯定不及母语写作带来的效果强烈,但非母语写作却能唤起更广阔范围内的文本接受者,从而在更广阔的范围之内传达民族认同。
玛拉沁夫非常熟悉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情境,他对自己的故乡草原怀着炽烈的情感。玛拉沁夫跨越了内蒙古广阔的大草原,从本民族的传统文学作品中汲取了有价值的滋养,并且积极向广大牧民鲜活的口头语言学习,将其加工、提炼成为自己小说创作的书写语言。在《茫茫的草原》中,玛拉沁夫正是通过这种具有蒙古族“本色”和“基调”的“民族化”的“汉语”叙述,鲜明地表现了蒙古族浓郁的民族风情。蒙古族的民间谚语、格言、歌谣等,都是蒙古族的历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逐渐积累起来的智慧结晶。在《茫茫的草原》中,玛拉沁夫运用了大量的关于自己民族的格言、谚语、歌谣等这些民族文化信息。玛拉沁夫在运用这些因素的时候,它总是使它们与小说中描述的具体场景以及人物的思想感情相吻合,从而使作品具有更强烈的民族生活气息和地方特色。例如,文本中有这样的叙述:“马和歌声是蒙古人的两只翅膀”“额头上的皱纹擦磨不掉,心里的恶意掩盖不住”“狗走过的道上有尿迹,兔子走过的道上有屎堆”“狗不咬拉屎的,官不打送礼的”,等等。这些具有高度形象化、比喻性色彩的语言,都是蒙古族的劳动人民于长期的生产和生活中总结概括出来的。
在《茫茫的草原》中,玛拉沁夫一方面将这些具有民族色彩的民间谚语、俗语贴切圆润地加以运用,同时也在小说的叙述文字中穿插使用蒙古族的民间歌谣。蒙古族民间歌谣植根于蒙古族人民现实生存的沃壤, 渗透于蒙古族人民生产和生活领域中的方方面面。蒙古族歌谣的种类繁多, 在玛拉沁夫的作品中主要有赞美诗、祝福词、情歌、童谣、摇篮曲等形式,作者将这些民间歌谣运用得恰如其分。在整部小说的叙述中,共有二十处左右出现了歌谣。每一处的歌谣都和文本叙述的故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产生了特有的艺术效果,其中一种明显的文本效果就是加重了小说的民族特点和地域色彩。小说中有这样的叙述:当苏荣带领的工作队进驻特古日克村时,普日布打算给她一个下马威,其中很重要的一步就是让民间的“祝词家”来唱《赞马歌》,“它向前奔跑的时候,如同欢乐的彩鸾在空中飞旋;它纵身驰骋的时候,好像吃饱的玉兔在原野上撒欢……”(卷一·五章)[9]六首《赞马歌》从不同的角度颂扬了草原上奔腾的骏马,表现出了蒙古族人民对马的热烈情感,体现出了蒙古族人民的性情,创造出了浓郁的草原边塞情调。又如在小说的《卷四·四章》里,玛拉沁夫以这样一首蒙古族的童歌来表达蒙古族人民经历长久的雨雾天后渴望晴朗天气的心情:“云彩,云彩,远远地走吧,太阳、太阳,近近地照!/阳光、阳光,近近地照,云彩、云彩,远远地走吧!”[9]又如在《卷一·十章》里,玛拉沁夫让莱波尔玛唱了一首摇篮曲:“别人的孩子爱哭呀/呜……哎……呜……哎/我的宝宝爱睡呦/呜……哎……呜……哎。”[9]这些歌谣的运用,都彰显了玛拉沁夫对自我蒙古族族裔身份的建构和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