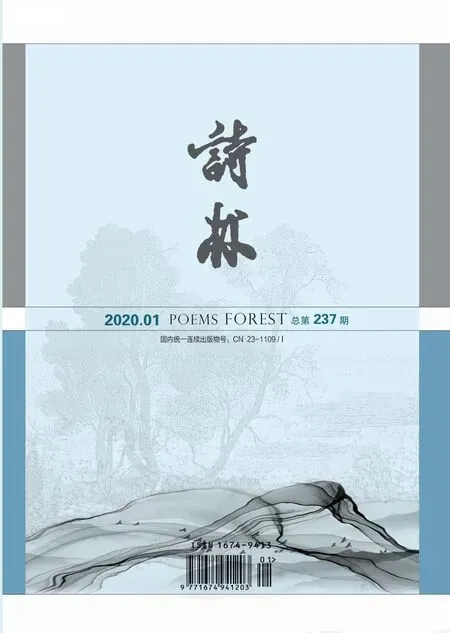城市规划师(组诗)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 宇舒 译
一个悲伤的孩子
你难过,因为你难过。
它是通灵的。关乎年龄。是化学的。
去看心理医生或吃片药,
或者像一个无眼玩偶一样拥抱你的悲伤
你需要睡觉。
好吧,所有的孩子都悲伤
但有些人克服了。
数一数你的幸福。甚或,
买一顶帽子。买一件外套或宠物。
跳舞来忘记。
忘记什么?
你的悲伤,你的影子,
无论草坪聚会日
当你被太阳晒红了脸
嘴里含着糖,
穿着有丝带的新衣服
涂抹着冰淇淋进来时,
你遇到了什么,
都在浴室里,对自己说,
我不是被偏爱的孩子。
我亲爱的,当这
恰好发生
光芒消失了,雾滚滚而来
你被困在你辗转的身体里
你的身体在毯子或燃烧的汽车下面,
红色的火焰从你身上渗出,
点燃了你头顶的柏油,
或者是地板,或者是枕头,
我们谁都不是被偏爱的孩子,
或者我们都是。
飞进你自己的身体
你的肺充满和扩展它自己
粉红血液的翅膀,而你的骨头
掏空它自己,变得空洞。
当你吸气的时候,你像气球一样上升
你的心也变得轻而巨大,
带着纯粹的喜悦,纯净的氦气跳动。
太阳白色的风吹过你,
在你之上什么也没有,
你看到地球现在像一颗椭圆形的宝石,
光芒四射,带着爱的海蓝色。
只有在梦中你才能做到这一点。
醒来时,你的心是一个颤抖的拳头,
一粒细小尘埃堵塞了你吸进去的空气;
太阳是一个炎热的铜重物
直直压在你头骨粉红色的外壳上。
总是在枪响前的时刻。
你一遍遍试着上升,但你不能。
自有人类社会以来,不论哪一种形态、哪一种类型的民主,不论其中“民”的范围有多大,一般都遵循三个重要原则。
规 定
我们该随身带些
什么?我们永远无法
决定;或者穿什么
或者该在
哪一年去旅行
所以我们在这儿穿着薄薄的
雨衣和橡胶靴
口袋里什么都没有
只有铅笔存根,两个橙子
四辆多伦多有轨电车车票
和一个有弹性的带子
绑着一捆小的白色档案卡
上面印有重要事实。
城市规划师
干燥的八月阳光中,
巡游这居住区的周日街道
冒犯我们的是
理智:
迂腐的一排排房子,干干净净
种着的树,断言着
表面的平整性,像在斥责
我们车门的凹痕。
这里没有喊叫,或者
玻璃碎片;最突兀的
也不过是沮丧的草丛中,电动割草机
切割出一条直带时的理性呜呜声。
但尽管车道整齐
甚至通过屋顶全部展示同样的倾斜度
避免戳到炎热天空
来回避歇斯底里,
仍有确定的一些事物:
车库里缠绕着油溢出的味道
一种隐隐的病,
砖头上溅的油漆像一块瘀伤令人吃惊,
乱七八糟的一卷中沉着的
一根塑料软管;甚至是宽大窗户太专注的凝视
让我们短暂地进入
石膏将裂的缝背后
或者下面的景观
当房屋倾覆时,会斜斜地
滑进粘土海域,像现在
没人注意到的冰川一样缓慢。
这就是城市规划师
带着阴谋家的疯狂面孔
散落的地方,在未经调查的
领土,相互隐瞒,
每个人都在他自己私人的暴风雪中;
他们猜测着方向,草绘
短暂的线条,线条死板如墙上
的木制边框,在消失着的白色空气中
在雪平淡无奇的疯狂中
追踪着郊区秩序的恐慌
夜晚的诗
没什么可怕的,
它只是正变成
朝东吹的风,只是
你的父亲是雷声
你的母亲是雨水
在这个水的国家
米色的月亮像蘑菇一样潮湿,
有淹死的树桩和游泳的
长鸟,苔藓在树木的
四面生长
你的影子不是你的影子
而是你的投射,
窗帘遮住门时
你真正的父母消失了。
我们是其他人,
是带着我们的黑暗之首
默默站在你床边的
来自湖下面的人。
我们来用红色羊毛,
用我们的眼泪和遥远的耳语
覆盖你。
你在雨的手臂中摇晃
你睡眠的寒冷方舟,
而我们等待你的夜晚
爸爸和妈妈,
用我们寒冷的手和已死的手电筒,
知道我们只是
一支蜡烛抛出的
摇摆不定的影子,在二十年后
你会听到的回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