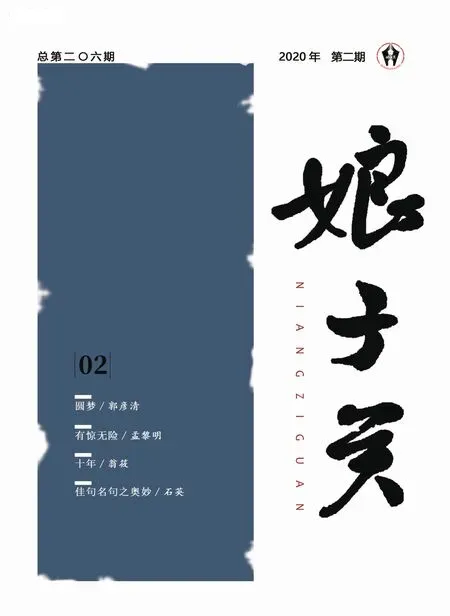终究,我们的眼睛里会有这条河流的反光
文 赵少琳(太原)
我不是拿起笔来就能写作的那种人,我在写作之前必须要有一些日子的宁静,在这些日子里,我把心头的杂事、烦躁、不安渐渐地滤掉,让自己不断地恢复和回到宁静。当然,在这样的日子里我还必须要紧紧地抓住书本,像僧人一样诵读着经卷,以滋养和增强我对语言的悟性。在我渐渐靠近语言的时候,我希望我的宁静能够保持下去,这样我写作的欲望就不会被破坏,否则的话,我写出的文字肯定是潦草和易碎的。
给人写评论,就像善良的郎中给人看病一样,药下得轻了,人家说不管用,药下得重了,人家又嫌涩苦,让人左右为难。徘徊中,直让那下药的郎中不好下方。
这不,建平的诗集《暖色调》即将付梓,让我说几句话,我怕说不好,便感到了常有的胆怯和心慌。好在建平给了我一些时间,让我靠近他诗歌的灵魂,靠近他诗歌的肉体,苦思冥想中,我便粗粗的有了以下想法,也不知道说的和他的诗歌是否还沾一点儿边了。我想,建平也是世面上的人,吃不吃我说的这一套,他定会有自己的判断。
选择具有文学性的语言
选择具有文学性的语言,或者准确地说是选择具有诗意的语言,可以看出一个诗人在语言面前所表现出的能力,什么是文学性的语言,就诗歌而言,就是要看一个字,一个词组的字形、字貌和词性是不是具有一定的弹性和韧性,是不是具有血肉和金属的分量,是不是稳重和具有神秘感。譬如:云彩和陶罐两个词组,前者显得轻肤,而后者显得凝重;譬如:小草和葵花两个词组,前者小草就显得单薄和虚弱,而后者葵花就显得壮烈一些和更有个性。再譬如:山河、红旗、努力、大道、欢腾、人生、情思、向前呀等等,这些浮躁的公共话语放在诗歌里确实让诗歌抬不起头来,而我们许多写作者常常意识不到这一点,这很可怕,作为一名诗人,在语言面前畏缩和妥协,只是轻率、盲从地和一些贫穷的语言缠绕在一起,缺少与语言的对峙,缺少向着语言冲锋,不能突破语言的障碍以及它的核心,这实质是表现出了一名诗人或是一个作者的弱小。在这本诗集中,我喜欢你写的《史蒂夫·乔布斯》:
那个缺口,在无数人眼中盛开/使一个远去的背影余温犹存/你纤瘦的像个果核/却掏尽毕生火焰/燃烧出一个新的世界//清晰,简约,特立独行/咬去那一口/把自己的魂黏合上去/一种唯美的完整//轻轻触摸你的激情/十分爱渴,一半愚痴/阴影,噪音,他人观念从不附体/创新的长调/回响着内心的呼啸/你似一道光,灵射硅谷/八十三亿美元的奖赏/耀眼了你匆匆的一生//谁说那个苹果/是图灵吃剩下的/谁说上帝的第三个苹果/幸运砸向了你/欲左右长空/必先左右自己/犀利超越,有因有果/你说想和苏格拉底/相处一个下午/而他说,想与你同行
——郭建平:《史蒂夫·乔布斯》
明显的,这样的诗歌剔除了日常低矮和带有惯性的语言,你所选择的语言正好能够柔韧地展示出其诗歌的肌肉,这让我们读这首诗时尝到了甜头,有了暖意。在写作上,我们就是要为每一首诗歌,找出所需不同的每一个词来:沉湎、追忆、联想、推敲、跋涉、颠覆、眺望、靠近、辗转……为一首诗能找到一个准确的词语去受苦、去受难、去创造一首诗的宫殿和魔方,是一个诗歌信徒应有的信念,也是一个诗人所应该铭记的心经。在当下,好些人的诗歌创作仍处于盲区,他们被大量泥沙俱下的诗歌所裹挟、所左右,被任性粗浅的诗歌所撩逗。从而,一次次掩埋了诗歌的真相、诗歌的籍贯。寡淡、虚弱、迷茫、莽撞、失血而成为一股股诗歌语言的流弊,让人不知所措和晕头转向。
我们缅怀上世纪80年代的诗歌创作,那是个屏声静气而又喜欢沉思的年代,那时的诗歌创作朴素而又确实让人心头发热,现在,我手头就有我省诗人潞潞发表在《人民文学》1982年第九期上的《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和发表在《山西文学》1983年第7期上的《南海,我把北方的风雪寄给你》,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返回到那时的诗歌现场,看看我们能不能在80年代的诗歌里取暖:
上海音乐厅。/圆形的拱顶,奶油色的墙壁,/小步舞曲加珍珠霜的幽香。/六角人民币和四十分钟排队的辛劳,/使我挤进这城市的高雅与堂皇。//管弦乐。独唱。小提琴五重奏。/报幕员的甜笑。起落的金属指挥棒。/而后是黑色额发一个潇洒的甩动,/崛起了小号,崛起一片广阔起伏的高原,野牛的/长鬃风一般飘扬……//这不是上海,分明是我的北方。/有着苍劲的群山,燃烧的落日,/有着白毛风、马群和男子气的北方。/金的号键,白皙的手指,/激情——突破上海。/勇敢的野牛之血呵!//文静中,感到速度,平衡里,感到癫狂,/温文尔雅接受着力的碰撞。/不可抑制的音乐厅,/腾起野牛疾驰而过的尘烟和轰响。/这是上海。/是一片湖蓝涂上山岩的褐色,/是幽静庭院风的光临、海的涌浪。/呵,年轻的小号冲决了堤坝,/压过来轰轰烈烈的北方——
——潞潞:《城市与勇敢的野牛之血》
这里是北方。雪,纷纷落着。/雪纷纷落着,已经三个昼夜了。/风也结伴而来,从遥远的西伯利亚,/甚至,更远的地方。/草原、大漠、森林被不可抗拒地逾越了!/到处是力的旋流,速度——/昂着头在奔跑!//于是,我想起了你,南海。/你以为我对你是陌生的,不。/你还是那样湛蓝吗?平静时,/像全神贯注的默想与思考。/你很深,翻滚着白色的浪花,/我不知道,那是由于鲸鱼还是爱情?/你还有海鸥,它不惧怕风浪,还有船,/鸣着汽笛,船头有着旗帜和年轻的海员。/你很骄傲,南海:/可我,一名北方人却为你感到遗憾。//你有着暴烈的风。那风/可以使你翻一个180度,使你呕吐,/使你的珊瑚和水草为之战栗。/但你有雪吗?噢,怎么会呢?/雪,可以使你凝固,使你封冻;/也能让你感受到春天里解冻的欣喜。/让你的椰林、你的土地落下一天飞雪吧!/你也燃起红红的篝火,煮沸一锅雪水,/你也穿起厚厚的皮大氅,背上猎枪,/骑着马,在雪原和密林里追逐熊和狐狸吧!/那样,你会更加勇敢,也更漂亮。//我把北方的风雪寄给你了!/每一枚洁白的、六角形的结晶体,/都是一篇美丽的童话,/它会向你叙述它奇妙的变幻,/见过的雪山、冰板以及黄河,/怎样曲曲折折地流着,高原一片空旷;/它也见过马群在飓风里跑动,咴咴长啸,/见过黄羊坚韧地刨着冰雪下的草根,还有/人们在风雪里开动油锯,满脸胡须结着银霜……/我把这一切装在一个蓝色的航空信封里,/连同北方冷峻的、粗犷的呼吸……//南海,在你收到我的北方之后,/请你回一封信吧,莫忘记/贴牢那张画着金色铁锚的邮票……
——潞潞:《南海,我把北方的风雪寄给你》
这是沉淀下来的诗歌,因它保持了诗歌的温度和理想,而正成为诗歌灵魂的一部分,这样具有碾压性的诗歌究其原因是立意的强大和想象力所赋予语言以锐气,从而,建立起了一座座奔放的花园,给读者以情感上的响应,让人长久地停留在这些诗歌的面前,而不愿意离去。
请不要说这样的诗歌已经过时,难道北岛的诗歌《回答》,梁小斌的诗歌《中国,我的钥匙丢了》,食指的诗歌《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江河的诗歌《太阳和他的阳光》,昌耀的诗歌《划呀,划呀,父亲们!》,杨黎的诗歌《冷风景》,欧阳江河的诗歌《玻璃工厂》,海子的诗歌《亚洲铜》等等都过时了吗?殊不知,这些诗歌都产生于上世纪八十年代,而敢于说这样的诗歌过时了的人,我看他们只是嘴巴子很硬,而笔头子却不坚挺,往客气里说,他们对中国的诗歌只是有着断崖式的理解,并没有看到中国诗歌生长的过程,这对以往中国优秀诗歌的繁衍造成了伤害。我注意到有这样一种现象,时下,当有人写出了这样的诗歌,立刻便引来了读者的惊呼,好像无意中捡拾到了一粒金子。
譬如有这样一首诗:
一枚螺丝,锈死在一块铁板上/看起来那么腐朽而寂寞。/我用扳手拧了几下,没拧动/它像仇人一样,咬着牙。/只好滴几滴机油,渗到螺母里去/一根烟的工夫,时间苏醒/我再拧,它尖叫着松开了手/与死爱的这块铁板一丝一扣地分离/在我使劲转动下/听见它撕心裂肺地喊疼。
——李伟:《拧螺丝》
读者比我们聪明,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不是很清楚吗?这样的诗歌出自真正的诗人之手,而这样的诗歌在上世纪80年代遍地都是,不值得大惊小怪。只是我们现在有些作者仍旧处在一种盲区里边,自娱自乐着,这让人感到了沮丧和焦虑。
建平,我举出以上的例子不仅仅是让你解渴,不仅仅是在为你的诗歌培土,而更多的是想让你增加一些想法,从而,在你的诗歌创作和心理上起到一些光合的作用。
用疾苦和肉体温暖你的文字
你写的《我想……》和《霍金》这两首诗歌,写的既有灵气又有底气,不妨,我们先把这两首诗歌抬出来,看看有没有眉眼,看看是不是你箱底里的东西。
“我不想因一次雾霭肆虐/就抱怨环保工作不力/但我想,纵横于雪域//我不想因一次透水事故/就对所有矿井安全心生质疑/但我想,不再出现悲剧//我不想因洪水泛滥/就冷眼江河的情意/但我想,请回李冰和大禹//我不想因个别不雅视频/就相信都是权钱色交易/但我想,与珠穆朗玛峰庄严并立”
这首直视现实的诗歌,从结构上来讲就颇有道法,从立意上来讲又颇有狠劲;核心稳定,语言先抑后扬,思想层层递进,段落起承转合,在我们读这首诗时不会影响我们的自尊而引起一些杂念。
这首诗好读,因为它含蓄而富有节奏地直指和活检着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和这首诗有了一种血亲的关系。有人抱怨说,我也有生活,我怎么就写不出这样的诗来。我想,作为一名诗人首先要忘记赞美和市井的喧哗,忘记物质对我们的勾引,而潜心地去成为一名时间的囚徒。形象地说,如果你还爱着诗歌的话,我想说,从明天开始,就让我们的手回到一支笔上来,就让我们的目光回到一张纸上来,就让我们的身体回到一对桌椅上来。种种:从明天开始,不去关心那些大佬们的车子、皮包和香水;不去关心他们所说的期货、证券和股指;不去关心灯红酒绿的街头……从明天开始,要远离那些瓦解你定力的鲜花、景致和酒桌……以及远离那些喧嚷与是非。你要埋头奔跑,在每一本书的站台和河流上,去寻找自己的故乡和渡口。这里,我亦欣赏你写的《霍金》一诗:
霍金,昨晚梦见你/站在广义相对论的阶梯上/给我阐释奇点定理/不行,我还是弄不明白/多想讨一杯成果充饥//轮椅上的梦在黑洞发酵/绽放了宇宙之谜/与你的名字连在一起/仿佛缩短了天地距离/命运对你悲惨的咒语/使泰晤士河/有了一个杰出的传奇//强大的思想徜徉在天域/仍像当年赛艇舵手一样/敞亮而积极/管它黑暗还是窒息/你成为一个符号/生命的质感/在时光本质中沉淀、增值/放射着深意/
读这首诗,使我想到了过去的一件事情:中国的紫砂壶在民间是受文人墨客喜欢把玩的器物,为了锦上添花,他们常常想让锔匠在紫砂壶上补上锔钉,而一把新的完好的紫砂壶是没有裂痕的,怎么办?如果用一把锤子去敲这把紫砂壶,敲地过劲了就敲碎了,敲地过轻了或许无济于事,不急,锔匠自有锔匠的门道。抬手间,锔匠把一把把豆子放进壶里,倒上水,然后把壶盖和壶身绑在一起,等待着那豆子在壶里膨胀。不用多久,渐渐膨胀的豆子就把那壶身挤裂了。之后,锔匠把那挤裂的地方锔上铜钉,使一把壶看起来更加的耀眼。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一首诗就是要有一把豆子的力量,给人鼓舞和投射出一束光线来,给人以前倾的信念。《霍金》这首诗就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在写这首诗时,作者或许也经历了波折与痛苦,就像一把豆子在苦闷中前行,而最终照亮了人们的脸庞。难道创作不也是这样的吗?写出一首好诗那是要经历泥泞和坎坷的,那是要经过阵痛的。在写作上,我们常常会败给一支笔;常常会败给一张纸;我们在一支笔前逃离,我们在一张纸前逃离,我们甚至会在一对桌椅前逃离,因为,在写作的途中会布满荆棘。从以上的诗中我可以看出你在宁静地写作,不急、不燥、不滥竽充数,使你的诗歌洋溢出了纯洁的温度和气息。建平,在你的诗歌里,我似乎不止一次地看到,你在黄昏里,怀着一颗悠久的心,向着悠久的诗歌,用疾苦和肉体温暖着你的文字。
想象和比喻与诗人是鱼水的关系
想象和比喻与诗人是鱼水的关系,没有想象和比喻的诗歌就好像鱼儿离开了水,那离开水的鱼儿,注定是一条死鱼。过去有个皇帝不是爱写诗吗,一生中写了四万多首诗,其中有一首写雪的诗是这样写的:一片一片又一片,三片四片五六片,七片八片九十片……这是诗吗?我看连儿童诗都不是。这首诗就是一条死鱼。这样的东西毫无诗歌的面孔和表情,最终被大家当成了笑话。是皇帝你就好好当你的皇帝罢了,作什么秀呢!在这里,我想提醒你的是,不要在这虚假的东西面前低头。即使皇帝写出来的诗,也不要被他的龙颜所吓倒。现在,让我们看看诗人海男在上世纪80年代写的一首诗歌《在你的手臂仍然孤独》,看看具有鱼水关系的诗歌是什么样子的:
生命的呓语发出请柬。我肩上披散的长发/目睹了无处归宿的长夜。/我们不再蒙蔽的时候,我的脸上/最后一滴泪水枯干。我抽回我的手/在坍塌中颤抖。我不是你/怀抱中那个永远安宁的信徒。/在剧痛中抽搐的是灵魂的病体。/我最后想告诉他/让黄蓝色在四野弥漫。/我什么时候/学会了荒诞地跪在你面前。我带着永久的哀伤/充满在你的手掌。我始终是一个/带着死亡的信息生存的幽灵。我却不知道/爱你奇特而沉思默想的渴望。我什么时候/让你在十二夜后染黑我的躯体和眼睛
——海男:《在你的手臂仍然孤独》
这种卓越的联想与比喻,让读者读的兴奋和有了醉意,这在当今仍然是一线的语言、比喻和想象,是现时疲软的诗歌所无法追赶的。如果我们把诗歌创作形象地当成一道佳肴去做的话,那我想,它应该所具备的条件是:立意+想象+比喻+动词等等。意识不到这一点,那我们的诗歌就会带有一些天生的缺陷。
无山可落时/就落水,落地平线/落棚户区,落垃圾堆/我还见过。它静静落在/火葬场的烟囱后面/落日真谦逊啊/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挑三拣四
——张二棍:《太阳落山了》
姑姑在剥洋葱/洋葱让姑姑流泪/洋葱因为开不出花委屈了一辈子//剥去旅居地、迁徙地、暂住地/姑姑要剥出洋葱的籍贯/剥去死掉的丈夫、打工的儿子/走失的狗/摔碎的鱼缸/姑姑要剥出洋葱的命运/一层一层,不停地/姑姑,像在掘开自己的坟/像要越来越快地/挖出自己//在这个村子里,这个午饭时辰/有多少人在剥洋葱?/有多少人像姑姑一样/不停地/流着泪
——唐小米:《剥洋葱》
每次剥轴子的时候/你都只剥一半/让剩下的一半/在妈妈的胎盘里/多睡一会儿
——灵鹫:《剥柚子》
我不住地往出打着手中的好牌,我不知道你是否领会了我打出每一张好牌的意图。从这些好牌里,你能不能看到诗歌的嘴唇,你能不能看到诗歌的眼睛,你能不能看到诗歌的面孔……如果你能看到这些,那你就不会在它们的呼吸和心跳里走丢。
不能不说的一些话语
当然,在你早期的诗歌里,我也曾看到过你一些涣散的诗歌,譬如:
似一道道长虹落地/把蠕动化为通达/老百姓心里的五色梦/重叠出座座立交桥的雄灿//远望,车流如一只只彩蝶/从不同方向/在视野中飞来滑去/行车千里任穿梭/红绿黄灯成看客//入夜,演绎闪亮的魔幻曲线/羞退了火红的晚霞/浅浅吟诵风景这边独好/使人荡气回肠/嗖嗖疾驰,吹着本质的口哨/现代版的激情荡漾在星空/宛若要摘下一颗/送给筑桥人//桥连桥,桥连路,桥连心/施施而行于桥畔/与之互诉衷肠/不用酝酿,内心的词如春风/早已浩浩荡荡/顺畅的呼吸,舒绿了田野/宽绰了希望
——郭建平:《桥之语》
在你的胸前徜徉/脑海中是你澎湃的形象/低着头施施而行/生怕惊扰你沉睡的梦乡/休眠上万年/你还是升腾时的模样//小沙弥平息了你暴躁的脾气/生成富晒的滋养/使脚下众生/找到了奋起的方向捡一小块你的遗存带走/不为镇宅,只想用它听到塞外人/“萱草无忧”的歌声/常在耳边回响
——郭建平:《火山群断想》
我必须要诚实地指出,这些诗歌语言软弱,公共话语强烈,感受肤浅而使诗歌处于一种低温的状态,以至形成了诗歌致命的内伤。挑剔的读者对这样的诗歌是抗拒的,是不会给好脸色的。就此,如果我遮遮掩掩、半推半就、吞吞吐吐地说出一些寡油淡水、应付差事的话,不去找出这些诗歌松软的部分,这无异于是在戕害和谋杀一个成长中的诗人。抚今思昔,或许我只是在杞人忧天。建平,你有能力去背叛这样的诗歌,因为你能够写出《史蒂夫·乔布斯》,你能够写出《霍金》,你能够写出《立冬,一个清瘦的名词》,你能够写出《我想……》等等,在螺旋式的上升中,你一定会改写自己,写出让读者点头的作品来。
或许,我们并不是轻易就能够到达一条河流的,在到达这条河流之前,我们饥渴、冥想、甚至还会虚脱,但我们的额头却可以将一根根的火柴擦亮。忘我中,我们在向一条河流靠近,终究,我们的眼睛里会有这条河流的反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