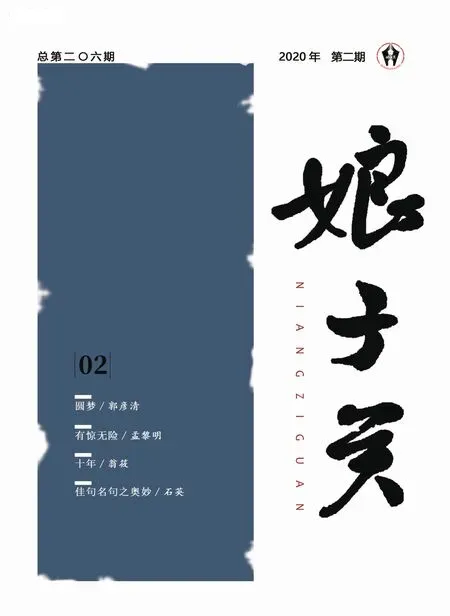佳句名句之奥妙
——诗文偶感
文 石英
我在解放区上初中时,尽管当时读书、教学的条件都十分困难,但每上语文课时,村镇里的“大饱学”战老师几乎总要强调作诗(旧体诗)、为文时炼字炼句的重要。必要时他能随便举出古人诗文中的一些佳句、名句来做示范。事情过了若干年,回想起来愈来愈能感到它的意义非同小可。
其实,我们许多人在提到古代的某首诗某篇散文,真正能丝毫不差地记得全篇文字者很少,大都是记住它们中间的某一两句,似乎也就把握了全诗或全文的精髓,如刚刚过去的丙申年中秋节,那几天电视台的主持人总在引用两句话——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但极少说出作者为谁,也多半不介绍全篇的题目;至于是诗是词,一般的听众也未必穷追,但大都能略知其寓意。很简单,因为过中秋节嘛!
但有的听众还是晓得的。“噢,引用的是苏东坡的《水调歌头》”,还有的内行和诗词爱好者想必也能知道是词的结尾两句。从一般意义上说,一首不短的诗词,一篇较长的文章,并非专家的普通读者能够记住其中的几句,也就无须自惭。从平时接触中我得出一个印象,有的名诗或散文名篇,大多数人其实就知道其中的最核心、最精粹、最富思想内涵的两句。如范仲淹的《岳阳楼记》,记住的就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两句,但已有资格说:我知道《岳阳楼记》,甚至还可以说:知道了这两句话,就知道了范仲淹。也就是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范仲淹这个人物的鲜明标志,或者干脆说,就是范仲淹。另如,知道了“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便知道了王勃和《滕王阁序》。可见真正的佳句、名句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一个作家和诗人来说有多么重要!
有一位诗人生前名声不显,只知道他是浙江龙泉人,连生卒年代都不具体,只知公元1224年(南宋)前后在世,但一首七言绝句《游园不值》,尤其是后两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便使他不能从宋诗阵列中除去,这位诗人就是叶绍翁。他的诗作中的名句更被后世人提摘出一个著名的成语——红杏出墙,意有别指,至今仍在沿用。类似的例子并非个别,如唐人许浑在当时并无太大名气,但他《咸阳城西楼晚眺》中句“溪云初起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却流传千数百年而生命力不减,而且早已越出本来景观气象,引申为一种紧张时势,近世常为政论文章中所借用。另如同为唐代的章碣,一生屡试不中,流浪而不知所终。然其七言绝句中语“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后被认为是经典,提示了一种时变势移的至理。以上之为位不显名不隆,却以句胜也。
佳句、名句之重要,有些情况下也离不开字的精致与讲究。北宋人宋祁《玉楼春》中“红杏枝头春意闹”之“闹”字,对于全句无疑生色不少,生动活泼,春意火爆。同是北宋词人之张先则以“云破月来花弄影”“无数杨花过无影”“帘幕卷花影”被誉为“张三影”,向以观察细致,意象精到而在宋词中独树一帜。在构句中某个字词的讲究,应做到新颖自然,酌奇而不失其真。过分雕琢死抠并非正途,必然消解了精妙中的活气。无论是古体诗还是新体诗文,皆不足取。
我对古典文学领域中的大家素来仰慕有加,在大学中学文学史,当时对唐诗中之李白、杜甫、白居易三位,往往冠以“伟大”的头衔,其他以“杰出”“优秀”等推定之。另有既无身份,又乏名气,作品遗存少而又少者则直列其作品,评价中往往无头衔称谓。但所幸编著者还算慧眼识珠,引其作品示于后人。这当中不只是拥有名句的作者,还有对整篇作品引录者。如唐人金昌绪所遗之五言绝句《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以戍边征夫之妻的口气,写出她渴望梦中与丈夫会面的心情。诗句近于直白,却深含情意,但对作者,编选者几乎一无所知,只是传说他曾在钱塘住过;至于其全部作品的写作情况,则皆无说有。
像这样命运蹇促的文人,或因志愿不遂,或因遗作太少,又无人推崇,故难入大家名家之列(凡大家、名家不仅应有值得称道之作,也要有相当可观数量之笔墨遗世),但我对这样生平可能“混”得不舒不展、有佳作却又不多的作家,一向抱有同情。斯人“身份”不重,不等于作品质轻;虽少而精到,亦应如实给以高分。客观地说,他们中有的人不是不能为名家乃至大家,境遇不佳有时可能被损耗、销蚀甚至吞噬,没有全被湮没,亦算不幸中之幸矣。
好在大家中有时也有头脑清醒者,当年李白登黄鹤楼,欲挥笔诗咏此景,忽然看到有崔颢之七律《黄鹤楼》,顿然自叹“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其实有关黄鹤楼的诗,李白还是写过的。笔者不想为尊者讳,相比崔颢的《黄鹤楼》,实在逊色不少,可见不论当时者还是后来人为大家加了多少“伟大”的头衔,但都无法使其篇篇“盖帽儿”,首首“拔尖儿”,真是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无论在任何时候,对于大家都不要迷信,既为大家,当然他的作品中肯定不乏佳句名句,但我在读诗文中,偶然发现另一些优秀的作家和诗人,尽管尚未被拥至顶尖,可他们诗文中的佳句妙语时能令人叫绝!这时我心中每每在想:这样的妙句李白、苏轼也未必写得出来,面对这类“硬件”真货,不禁心生敬畏之意:凡高级的艺术作品,有赖于世世代代有良知的识货之人。在艺术作品的“真理”面前,理应人人平等,不应因其当时境遇未达十分隆盛,身后又未加予“伟大、杰出”之殊荣而稍有不公正待遇。
古代为诗为文者中,确有少数既作品繁洁,质量又臻上乘,佳篇名句滚动于字里行间,辉映于鄙牖灯下。言及此,我又想到了陆游陆放翁。他一生留下诗词近万首,其中能为人熟知和记住的也占相当可观的比例,佳句、名句可谓举不胜举。这一点在古今诗人作家中真的是很不简单。否则的话,岂不是又超前出了另一个乾隆(乾隆留下的诗作达四万首之多,几无可圈可点之出彩之篇、精到之句)。而且,令人耳熟能详且经常引用之名句,许多人竟不知是出自陆公之手,如“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游山西村》)、“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临安春雨初霁》)、“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等。这充分说明,此公诗词中的佳句太多,以致读者们难以细辨了。其实,放翁诗词中的佳句还很多,如“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书愤》)、“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夜读有感》)、“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等,都是既有气魄又具深刻内涵的精句,足见作为大诗人的陆游精神世界是何等宏阔;另外,我读陆游诗词,还自然联想到他的作品对后世多方面的浸润和影响。如他的“小楼一夜听春雨”的情景和意境对某些影视作品的启示;他的咏物词的构思与后世某些新诗肖似;等等,都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创意的时空穿透力。
佳句、名句的形成当然不是仅靠凭空搜索枯肠刻意拼凑的产物,而是最璀璨的思想火花与诗艺灵感一见如故的理想对接。一个缺乏丰厚深刻思想熔炼和艺术造诣(包括文字的机智和灵动)的庸才,纵然竭尽艰涩制作效果也不会太好。应该说,那些出色的作者无疑都是那个时代很有思想和最聪明的人。且看: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过华清宫》)穷奢极欲,不惜代价地满足“最爱”的“舌尖”口福,同时便引来了胡人汹涌铁骑连锅端掉,付出也算“值”了。表面只是“一骑笑”,后果却无比沉重。小杜的艺术手法绝高,深刻!还是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由一个歌女仍在唱旧时陈后主作的靡靡之音,预示摇摇欲坠的唐王朝距离覆亡已相去不远,诗人的敏锐感觉由此可见。又如刘禹锡的“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西塞山怀古》),山形依旧,而朝代频繁更迭,人世倏忽令人无限感慨。“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乌衣巷》)借燕子飞来飞去的易主之象,寓任何煊赫之势亦难免转为衰败,又是刘禹锡式的深刻别致的哲思。而几乎人人能吟的李商隐的“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无题》),含蓄、内敛、深沉、绵密。无须细究是写个人情感经历还是喻人事政途际遇,仅将普通物象与这超事物本身的曲挚思想表达得如此精到这一点,即为千古难以逾越之名句矣。至于词,历来不乏名句。如南宋辛弃疾“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青玉案·元夕》)多年来,人们总是围绕究竟是个人的情感际遇还是寓壮志难酬的孤独心境争议不休;是“寻人”还是“被寻人”仿佛也成问题。其实都是都有又何妨?谁能说个人感受与社会感觉就那么全无联系。还是今人机灵,广告语中还在套用此句:“众里寻景千百度,蓦然回首,那景却在群山环绕处”。无论是雅是俗,是高洁还是实用,均可见名句的不衰生命力。
诗词的名句奥妙无穷、魅力无穷;而非诗的名句和名言也可能是时空无穷,威力无穷。非诗名句和名言的内涵在特定环境下也会发挥诗质的渗透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