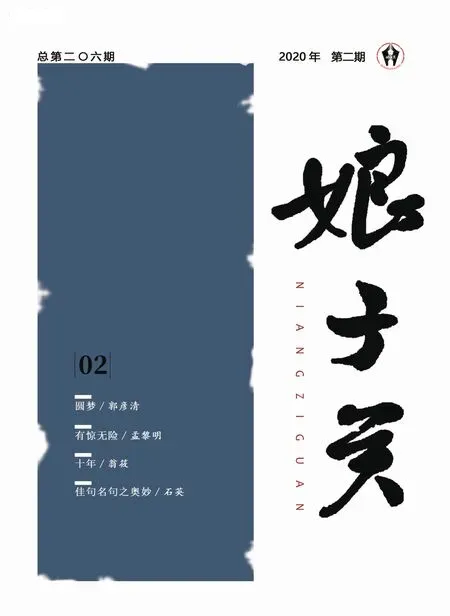行走在那年岁末
文 农荣思(云南)
那一个因年代久远而下落不明的早上,我兴奋得过早就醒来,漆黑的屋子没有一点光亮,我擦亮眼睛望上天窗,深邃的苍穹黑黢黢地覆盖着我的双眼,我陶净耳朵聆听,村中的雄鸡确实也还没有鸣叫着黎明,但我清楚地听到并联想到,村中的家狗在大路边狂吠不止,村中已经有人去赶集了。
我憋了一晚上的内急,掀开被子,准备起床,一阵寒风袭来,我打着哈欠连着喷嚏。我轻盈地跨过大哥的身体,蹑手蹑脚地下床。睡在我身边的大哥沉重地翻个身子,慵懒地说:“干吗呀你要?”
我兴奋地说:“哥,起床了,上街赶集去了。”
大哥似睡非睡地瞟我一眼:“你看天窗上面是什么?”
我相当马虎地穿好布鞋,急不可耐地向门口走去:“我管它是什么。”
大哥困顿地说:“妈还没起呢。”
我说:“我下楼去喊她。”
大哥打断:“这些天,妈妈每天都去挑柴,累得很,起不来……”
我摸黑到楼下的门边,阴冷的空气从门缝钻进来,我哆哆嗦嗦地拔开门闩,冷空气澎湃而来,强大的气流推动着木门缓缓敞开。小山村的黑夜总是很漫长,外面天色朦胧,还没显示出破晓的痕迹来。我蹿出门去,还没走几步,就扑在院子的泥巴地上,我明亮地发现,院子里的空地、破败的牛圈猪圈、木架阳台堆积着晶莹的白雪,这一夜,世间万物都花白了。
妈妈最终还是起来了,那得归功于我的助攻。我去打开了她床边的电灯,摇落了她睫毛上厚重的眵目糊,摇醒了她,她再不起来,我估计会把她的身子摇散架,像摇落寒冬风雪中的枝叶。可是我还嫌她起得太散漫,在那时候的我看来,她总是那样,做什么都磨磨蹭蹭,慢慢吞吞。大哥在妈妈起后也起了,他过早地被当成家里常住的男人,听着妈妈的吩咐去帮助村里人烧砖、烧炭、打瓦……这些天,他和妈妈到村子对面的麻栗坡去劈柴。麻栗树质地坚硬如生铁,历来是烧炭的优质木材,大哥一斧子下去,树没劈开多少,反而把自己给震倒了,一天累得他吃过晚饭,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便呼呼大睡,大腿压着我的小腿,被我踹了几个大脚也没踹醒。
我家在大路下面,赶集的乡亲们看到我们家亮起电灯,就会在他们的脚步声即将踏上我们家后屋时,扯起嗓子零碎地喊着妈妈结伴去赶集。可是妈妈对每一波的叫喊都回应说“刚起床,先去吧!……”脚步声渐行渐远,我听着就着急了,催着妈妈赶紧出门去赶集,妈妈在我咄咄地催逼之下,没来得及去吃热在锅中的过夜菜,急忙打包一坨冷饭,放在竹背篓里,背着背篓打着手电筒边出门边用围巾包裹头脑来抵挡冬天的寒气,踉踉跄跄地跟随在我和大哥身后。
二十年前的赶集总是在黎明之前就开始了,是一整天无比艰辛的漫长跋涉。那一次赶集发生在1998年,那年的冬天眼看着就要一步跨过去了,与新的一年只差一个赶集日。小年小节可过可不过,春节不可不过,妈妈艰难地下定决心,上街去赶集买年货,给我和大哥买新年衣服。那时候最让孩子开心的事情,是要过年了去赶集买套新衣服,毕竟一年也没几套衣服,怎么能不让孩子兴奋呢。
二十年前,我8岁半,矮小瘦弱,鼻子常常拖着一条清鼻涕。大哥11岁未满,虽然年纪小,但个子大,看着像个男人。妈妈33岁,正值壮年,但她身子癯瘦略显佝偻,就像历经沧桑一般,常年愁苦着爬着皱纹的脸。那时的我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孩子,活泼淘气,性急火燎,冲动莽撞,大哥恰好相反,他沉默,话少,加之他年龄比我大一点,更显沉稳懂事。从性情来看,村里人都说我们俩不是亲兄弟,但妈妈坚决给予否定,并坚称我们兄弟都是从她肚子的荒芜田地里生长出来的,品种来自同一个男人。妈妈呢,我有点说不清楚她那时候善变的复杂情绪和庞杂的情感网络,有时候像寡妇一样沉默寡言,隐忍涵豁,有时候像泼妇一样指天骂地,脾气易燃易爆。
性格迥异的母子三人从村边那棵古老的千年榕树前面小心翼翼地滑下去,山村小路被枯草封锁,窄小如线条一般。羊肠小路湿漉漉,滑拉拉,寸步难行。路边的枯枝荒草不时刮弹着路人的耳朵、头发、眼睛和衣服……覆在枯草上的雪片刷刷地落在路人身上,让人感受到一种刻骨铭心的寒冷。妈妈在后面打着电筒,一边走路,一边不停念叨着,“路滑……慢点走……”我跟着大哥走一段,跑一阵,我们两似乎放了猫眼,长了飞腿,冒着黧黑的黎明,一下子就走在前面,远远把妈妈甩在后头。“注意……看路,小心……树枝弹到……眼睛……”妈妈的声音像衣裳破烂从后面一丝一线地撕扯过来。
到了松林坳是平路,我和大哥先到,大哥依在一棵瘦弱的棵松下,跺着脚上的泥土说:
“休息一下,等等妈。”
我本来想一直走的,但是大哥说了等妈妈,我就不能走了。相比于妈妈,我向来更听哥哥的话。因为我在不听话的时候,妈妈只会唠叨,而哥哥会毫不留情地给我几个拳头。
我也依着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松树,不满地说“妈妈怎么那么慢啊!”
天色还是朦胧一片,松树林中一时阒寂无声。大哥不说话,安静地等着。我突然害怕起来,问大哥:“妈怎么还不来啊?”
大哥说:“妈妈昨天去砍柴累倒了,没休息好,走路慢。”
过了半炷香的时间,我听到脚步声从坡下传上来,看到手电筒的光柱在森林中闪闪烁烁,我兴奋地跟大哥说:“妈妈上来了。”
大哥听着脚步声,说:“不是妈妈”
我说:“是妈妈。”
大哥神色悠远地说:“不是妈妈。”
我急了,大声说:“是妈妈。”
从麻栗坡爬上来的是我们村子里的驼背单眼王大叔,他见到我们,急切地说:“你们两个在这呢,你们的妈妈在下面摔了一跤,手电都摔坏了。”
我气急败坏地说:“怪不得那么慢呢!”
大哥急切地询问王大叔:“我妈有没有受伤?”
驼背王大叔安慰我们说:“倒没受重伤,打滑时手撑着地,破了点皮,膝盖也擦着砂石,也擦破皮了,也快上来了吧。”说完他就先走了。
妈妈爬到山顶我们倚着的老松树时,目光茫然地看着我们两兄弟,压低嗓门说:“你们走路……小心啊,不……不要摔了”在她正面最近的我,明显得感觉到她气喘得很是粗重,她气息没呼匀,又急着说话,致使咳嗽连连,声音颤抖。
我不耐烦地说:“妈,你怎么那么慢啊!人家都走到前面很远了。”
大哥扶着妈妈的胳膊,语气略带抱怨:“妈,你自己小心点,别摔着了。”
“好……好,我们赶路吧……”妈妈欣慰地看着哥哥,没有咳嗽,声音却在颤抖。
松树林是一段平路,妈妈依然在后面念叨着:“刚上坡又走平路,特别容易腿软,一不小心就会崴脚”停了一会又说“晚上降了霜露雪,容易打滑……山里人走着这样坎坎坷坷的道路太久远了,在不好走的道路,你们要学会放慢脚步,小心谨慎地行走,这是农村里的常识。”
我最烦妈妈唠叨个不停,且走路还特别慢。我催动大哥走快点,于是才一下子,便又把妈妈甩在后面。
我们前后有村人在走着,打着光柱子在朦胧天地间摇晃摆动,脚步声掺和着说话声一路长鸣,把一座座山峰甩在后头,但却总觉得路比脚长,怎么走也走不完似的。
走过多时,大地呈现一个模糊的轮廓,这时的天空灰蒙蒙地亮起来,群山旷野白茫茫的。我们终于到了那一条长达11公里的水电站水坝的坝头,要去集市非得走完这条蜿蜒盘环的水坝不可。这条水坝是开发水电而建,由县里包括我们村在内的好几万人长年累月开凿而成,纯人工的血汗长堤。我们村子里便是接受这条水坝的恩赐,家家户户拉来了电线,得到了光明。
坝堤的墙面很厚,够两人并排行走,水坝的河水很深,枯水期也能没过一个成年人的胸腹。我刚走上堤坝的第一步,便又听到妈妈在后面絮絮叨叨地说:“走路小心呐,千万别掉到水里了。”语气颇为严肃和惊慌,大哥听到妈妈的话,就叫我在水坝的盖板上站着等妈妈。盖板上覆盖着厚厚的白雪,白雪中有一条混杂着黄色泥浆的路线,延伸而去,消失在眼光中的拐弯处。
我们仨在堤坝上前后走着,妈妈一路聒噪不停,要我们一路小心,她跟我们讲关于水坝子的故事:传说在这条水坝建成不久,我们村里的一个嗜酒的汉子到村外去喝喜酒,傍晚回来,醉醺醺地走过坝子,掉到水里淹死了。后来还有几个醉汉相继溺水而死,村里说这个蓝悠悠的水流坝子就受了诅咒。有死人的地方总是会留下心里阴影,就算不喝酒的人走坝子,都要格外小心,平时在坝上坝下耕作种植的时候,无论多热都不敢轻易下水。
我听完妈妈讲的故事,问妈妈说:“这么难走,那为什么非要走呢,就不能换条路吗?”
妈妈说:“有些路不能不走,不走不行。”
我有点呆愣:“为什么不走不行。”
大哥说:“因为这条近啊。”
妈妈说:“因为除了这一条,再也没有其他的路途。”
妈妈说完了,水坝也就走完了,也就出了我们村的地界。
2003年,我们村子开通一条风尘仆仆的黄土公路,2013年我们村铺上了顺畅的水泥路,去赶集用不到一个小时即可来回,人们都说那都是社会的进步。我长大后努力学习,才知道社会确实是在进步的。但那条至今还具备引流功能的水坝早已不具备通行的功能,被人们永远地遗忘在深山老林和历史的尘埃里。今年春节期间,我在农村待着无聊到处玩耍,我带着年轻的妻子和年幼的儿子去大坝上溜达,忽而想起妈妈二十年的对话,我知道我儿子年幼听不懂,但我还是要对他说:人人也都无可逃地要面对一条蹇足的路途,所以要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重新回到那一年的故事上来。尽管那时候的我一心想着要是像山中的老鹰一样,生出一双翅膀飞越万水千山,不用走路磨破脚就好了,但冰凉的现实就摆在我面前,我面前的路途同样是翻坡越岭,走山坳过谷口……走了不知多久才远远地看到在罗共村的水泥路上,有好多的三轮车跑着,来来往往地拉人,坐上三轮车半个钟头就可以到八宝镇上,走路还需一个多小时。走到水泥路的三岔口处,有个包子铺,正有赶集的人们买包子,我早上没有吃早点,肚子都饿坏了,走路也没力气,我看着人家吃包子,流着口水,红着脸对妈妈说:“妈妈,我肚子饿了……”
虽然天气寒冷,妈妈走路走得劳累,背着背篓,脸上还是汗津津、红扑扑的,她硬生生咽下口水,说:“买包子就不要坐车,坐车就不要包子,你要坐车还是要包子?”
我说:“我要吃包子,也要坐车。”
妈妈问大哥说:“你饿了吗……要坐车吗?”
大哥说:“妈你也饿了吧,我们要包子吧,四个包子才两块钱,坐车,我和弟弟小不算钱,你也要四块呀。”
妈妈看着大哥,目光温暖而柔和,说:“好,老大说的是。”妈妈要了四个包子,把两个给了我,她和大哥各吃一个……
当时,一辆新式的带篷盖的三轮车停在包子铺门前,一个冻得脸蛋通红的小女孩在她妈妈的搀扶下钻进车里,后面还有一个挑着黄豆来卖的老头,一对年轻的叔叔阿姨。上车的人我都看在眼里,我心里想着,那小女孩好像在哪里见过似的,我多想再看她一眼,于是不自觉地靠近那辆三轮车,妈妈非常敏捷地狠狠拖住我,三轮车分分钟就装满了人,从我面前摇摇晃晃地开走了,我挣脱妈妈的控制,追着那辆三轮车跑了一大截路,直到我跌倒在路上,也没追上快似流星的三轮车。事隔多年之后,我梦里时常出现雨雪天赶车的情景,大概源于这里的深刻而难忘的记忆。
按照每周一天的赶集,今天是年终的最后一次赶集。那时候,山高路长的,人们不常上街,非要等街天才去,而乡镇街道构造简单,一个镇子就那么几条街。每逢街天,人流拥堵,黑压压的人头,步步难行。大家都赶着置办年货,摆摊的货物也很多,商贩都希望年终前能把东西卖出去,安心地过个好年,勤快张亮的吆喝声此起彼伏,附加砍价的尖锐争辩声,过路的三轮车,面包车和小轿车一路长鸣的汽笛声环绕在大街小巷中。妈妈背着个比她身子大一圈的竹编背篓,一手拉着我,一手拨开人群,大哥则紧跟在我们身后,当我们在人海中历经漂泊,终于站在邮政所大门前时,看到的是紧闭的大门上张贴的公告。识字的哥哥看了看,跟我和妈妈说邮政局过年放假了。
大概已是正午,天空又飘着一些毛毛雨夹着雪丝。我们在邮电局的一个电杆边失魂落魄地呆站着,仿佛失去了人生的方向。那时候的我肚子正饿着,我认为饿了就要吃饭,渴了就该喝水,就扯着妈妈说:“妈妈,我饿了,我们吃饭吧。”
妈妈安慰我说:“儿啊,再忍忍,等一下再去吃好吗?”
大哥说:“弟弟,我也饿着呢,听妈的话,再忍一会。”
妈妈欣慰地看着大哥,转头迷茫地看着邮电局关闭的大门,跟大哥说:“街天不是全天都开着呢嘛,怎么就关了呢?”
大哥说:“过年放假了!”
妈妈拍了一下脑袋:“对呀,放假了,那怎么办,你爸爸寄来的钱怎么取,年货怎么办……”妈妈满脸通红,呵出冷冷的气息。
大哥无法回答妈妈的话,耷拉着脑袋望着我。我又拉着妈妈的手说:“妈妈,我饿了……”
我可怜巴巴地看着妈妈,妈妈可怜巴巴地看着我。大哥可怜巴巴地一会看我一会看妈妈。
妈妈带着我们转到另一条街去找一个远亲的舅爹。舅爹家就在这个镇子上,做建材生意。舅爹他身宽体胖的小儿子李进在邮电局工作,妈妈去舅爹家,寻找保全我们安然度过年关的一线生机。舅爹家的建材店门口有很多人,大多是来买年货的人停留休息的,妈妈把空得能装下整条街东西的背篓放在门口,叫我和大哥候着,她一个人进去找舅爹,我拉着她手不放,她没办法只能让我跟她进去,但她悄悄地告诫我一会儿不要乱说话。
瘦骨嶙峋的老舅爹在收银台边坐着烤电炉,妈妈喊了一声,舅爹看到妈妈,笑着脸说:“来赶集呢”说着从叠放的板凳里抽出一个木质四角凳,让妈妈坐着,妈妈站得恭敬,低声下气地说:“小进放假了吗?邮电局不开门了!”
舅爹说:“是啊,这不马上就过年了呢,他在楼上看电视呢,你上去找他吧。”
妈妈出来门口,跟大哥说,你再等一会儿,我上去就来,说完牵着我的手从门面的左侧铁门上楼去。
妈妈在二楼门口擦着布满黄土泥巴的鞋子,朝里面问候了一声,李进望过来喊了一声“姨”后,继续坐在沙发上跷着二郎腿看电视。
妈妈自觉进门来,走到李进跟前,站立着说:“邮电局放假了是吗?”
李进说:“是啊,放了几天了!”
妈妈说:“那就不能取钱了是吗?”
李进说:“是呢。”
妈妈说:“是这样的,你姨夫他在外打工,不回家过年了。他寄了一些钱来,要我们到邮政去领着过年,姨今天来呢,邮政局没开门了,孩子的新衣服,炮仗,对联……什么都没买……”
李进依然头也不转地看着电视,沉思良久说:“钱在邮政倒是跑不了,明年来取也行,就是……”
妈妈说:“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家……”
李进转头看了妈妈,妈妈低头望着自己尘土满面的布鞋。
李进见妈妈久久站着,他的眼珠转了半个地球,说:“要不这样,反正我在邮局上班,我先给姨一些钱,过完年上班就帮姨把姨夫寄来的钱取了,姨上街来,抵了我那一些钱后,还剩的给你,姨看怎么样?”
我妈妈高兴地说:“那样最好,就是麻烦你了。”
李进站起来,说:“姨,你先坐着,我去问爸爸要钱。”他刚要走出门口,忽而问起“姨,你吃饭了吗?”
妈妈说:“吃了吃了,你去吧。”
妈妈领着我们去乡村饭店吃卷粉。服务员端来两碗卷粉时,妈妈把从家里带来的冷米饭,放入了大哥和我的碗里,服务员最后端来妈妈那一碗时,看到妈妈正在往大哥的碗里放入白花花的米饭,她鄙夷一笑,走了。妈妈把粘在塑料袋的米粒抖落到她碗里。我吃得很快,一下子就吃完了,大哥跟妈妈一样,吃得很慢,不过也差不多吃好了,妈妈碗里似乎还是跟端来的时候一样少,没有吃得更少,她细嚼慢咽,像在品尝山珍海味一样。她吸了一口汤,手捂着右边脸,显得很痛苦的样子,我知道妈妈的牙齿疼痛着呢,妈妈小时候并没有刷牙,到了二十几岁才开始刷牙,33岁的妈妈牙齿已经被蛀掉了一大半,上门门牙还缺了一颗,说起话来似乎在吹风,口齿不清。后来我踏遍祖国的万里河山,吃遍祖国的八方美食,但我一直都只喜欢吃卷粉,其根源跟那次赶集不无关系,我也许并不是热爱卷粉,只是无论如何都忘不了那种穷苦饥饿的滋味。
从饭店出来,我们最先要去专卖衣服的那一条小街,那里的衣服大多是西装和军装,就是那个时候流行的童装。每个摊主看到妈妈领着我和大哥两个孩子过来,眼睛雪亮起来,大声吆喝着,像是有大生意要赚一样。我的性子急燎,都想买了走人,可是妈妈出了奇地缓慢,瞄了又瞄,摸了又摸,放了又放,从这条街的街头边看边摸边讲价,及至巷尾时,又返回来再看再摸再讲价,我不断地催她快买快走,不然回家太晚了,妈妈望着苍天,天上布满乌云,寒风轻轻吹着。
她下定决心走进一个本地口音的中年女人守着的摊点。摊主看到我们进来,抽出嘴巴滔滔不绝地跟我妈妈说东说西把我妈妈绕得南北不分。我一眼看中了那个男孩看中的军装旁边的西服,对妈妈说:“我要那一件。”同时,我听到那个男孩子的妈妈说:“不买这个了,上次赶集才买了跟这个一样的衣服。”
我相信妈妈也听到了,她慈善地说:“好,买,大姐,把那套衣服拿下来。”
那位大妈用木托子取下来,诡秘地笑说:“这套衣服你小儿子穿着准合身。”
妈妈把衣服往我身子前后比对,然后让我穿着上衣,在她面前走几步,她看了又看,满眼溢出喜欢。
妈妈问摊主:“店家,多少钱?”
摊主说:“哎呀,今年最后一个赶集日了,图个吉利,88块吧。”
妈妈不回答她,扭头问待在她后面的大哥说:“老大要买什么衣服呢?”
那位妈妈领着跟我一样大的男孩子和他的妹妹出去了,又有一位妈妈领着一个女孩进来,摊主又忙两头招呼。
大哥指着一边衣架上挂着的一件红色带帽衫,对妈妈说:“我想买那一件。”
摊主取下来,说:“这件两面穿的,有绒的,有防雨绸的,看天正反穿。”
大哥试穿了后,妈妈问摊主说:“多少钱呢?”
摊主说:“那件68块不讲价。”
妈妈盯着大哥试穿的那衣服,在帽子上发现有脱线的痕迹,线头没打好,还沾了点灰尘,她指着那个地方说:“你看这里,线头都没打好,灰尘也多。”
摊主贴近一瞥,往帽子轻轻一拍,把灰尘拍掉,说:“哎呀,这不影响,拍掉就好了。”
妈妈说:“一套西服和这件红衫125块怎么样?”
摊主说:“哎呀,145块不能再低了,已经是亏本价了。”
妈妈说:“你看嘛,我同时买了这么多,就不能多降点嘛。”
摊主说:“不能再低了。”
妈妈说:“那我们买不起了,走了。”说着就领着我和大哥要走了。
“行吧,125块就125块,赶着回家过年呢。”摊主急得本地口音说得都不利索了。
从那摊位出来,妈妈对大哥说:“你裤子就不用买了,去年买的那件黑色的裤子,太大没穿,放在箱子里也是新的,赶着今年穿着过节吧。”她又对我们哥俩说:“你们鞋子不用买了,妈妈都给你们做好了,每人两双布鞋,够你们穿一年了。”
街尾一家卖女人衣服的摊位面前,妈妈投入花白柳绿木棉红的目光,年深月久地凝望着,直到被身后尖锐的车辆喇叭声一惊,才梦醒了似的收回目光拉着我们走出这条街。
从卖衣服的这条街道出来,路过卖玩具的巷子,我看到摊上的玩具枪,赖着不走了。妈妈知道我的心思,用力拽着我的手去菜市场,在来来往往、形形色色的人群中,我虽然个头小,但瞬间力量却大得出奇,我用力一拉,妈妈就退步,我急着往回走,急转过头把在我后面一个彪悍的叔叔撞了个满怀,还把叔叔旁边的一个穿着绣花鞋的阿姨踩了一脚,她那双绣花鞋鞋背红火的石榴图蒙上一层湿泥土,她望着妈妈,白了我一眼,没说什么,提着一袋水果和那叔叔一起跟在稍微疏落的人群。妈妈为了避免我冲撞到人,只得放弃捕捉我,和大哥蹒跚地跟在我后面。我走到卖玩具枪的一个摊位,杵在那儿,目光锁定在那些玩具枪上,死活不动了。
卖玩具的摊主是个肥胖而高大的叔叔,他吐沫横飞地跟围在他摊子边的人介绍各种玩具枪的价格,我摸着摆在摊边的狙击枪,那把狙击枪手托和手柄是暗黄色,枪管和望远镜是黑色,枪管很长,望远镜还有红外线,那把枪深深地吸引我,前几天我在村子里看到邻居家的孩子拿着类似这把玩具狙击枪在他家木架阳台上射我家房顶上的麻雀,我也要买一支玩具枪,在我家阳台上用这把玩具枪去射他家屋顶上的麻雀。我坚定地认为不是我渴望玩具枪,是玩具枪诱惑我,就如我邻居家的那个小麻雀叽叽呱呱地诱惑着我。我发现大哥也被摊中间的一把黑色手枪诱惑着,不自觉地伸手去把玩,但他到底比我大一点,很快就放手了。
我指着那把枪,跟妈妈说:“我想要这把。”
妈妈一脸无奈,说:“儿啊,我们去买对联,香火……那些还没有买呢。”
摊主对我妈妈说:“嫂子,买了吧,就88块,便宜点,80块给你了。”
妈妈说:“80块,都够我孩子买一套衣服了。”
我乞求妈妈:“衣服已经买了,给我买枪吧。”
摊主见缝扎针,把摊中间那把大哥摸过的黑色手枪丢到我面前,说:“这把20块,收你15块,贱卖了,今年最后一次赶集日。”
妈妈的目光热辣地盯着摊主,摊主讪讪的笑容僵在臃肿的脸上,妈妈拉着我的手说:“我们先去买过年的东西,等会再过来,好不好!”
我甩开她的手,定在摊前,带着哭腔说:“妈,我就要买,我不走,你给我买。”
妈妈铁青着脸,被我甩开的手无处安放地瑟瑟发抖。她看着大哥,说:“老大,我们走,放他一个人在这里。”大哥看着摊上那把充满诱惑的黑色手枪,然后看了蓄势要哭的我,准备跟妈妈走了。我看着妈妈要走了,用力拉着妈妈的手,跺着脚,尖锐地痛哭,语无伦次地乱骂,众人甩来噼噼啪啪的目光打在妈妈充满汗液的脸上,几根斜刘海遮挡了妈妈灰白的脸,她带着一种恨铁不成钢的落寞神情钻进人流中,大哥白了我一眼,尾随妈妈钻进人流中,妈妈故作大步远走,但一步一回头,始终在我的视线范围之内。
摊主看我在他摊前哭闹影响他的生意,用嫌弃的目光说我到对面的路口哭去,我极不情愿地走到一个既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玩具枪,又不妨碍摊主做生意的不远不近的地方。街上的人们熙熙攘攘,这丝毫不影响我欣赏那把散发着神秘光芒的可以打死小麻雀的狙击枪,我给那把狙击枪取了个外号,叫小麻雀,来表示我对它的亲热。我看到一个胖小孩和他的胖老爸靠近那个摊点,胖老爸跟胖摊主有说有笑,胖小孩举起我那把小麻雀,用他的大眼睛对着小麻雀的望远镜,胖手指扣动机舌,对着街上一棵覆盖着白雪的桉树做瞄准发射的动作。
我看着胖叔叔不知何事,急急地跑进摊位里面的屋子,摊子瞬间无人站岗。我看到摊上的玩具,被雨打湿了,沾染着点点雨滴,我极力地用目光寻找我的小麻雀,但是没找到,我猜是那胖小孩拿走了。我灵机一动,找不到小麻雀,就拿刚才大哥看中的那把黑色手枪,趁着没人看店,我飞一般地跑过去,一把抓着那只散发着光圈的手枪,像一条鱼儿一样溜溜地钻进了人海中。
我找到了妈妈和大哥,他们站在那棵覆盖着白雪的桉树下张望着我。我不无兴奋地把那把枪藏在我腹部的衣服里面,玩具枪冰凉着我的皮肤。我无比雀跃地对他们说:“妈妈大哥,你们看。”
我慢慢地把那只散发着黑色光圈,像夏天的冰棍一样冒着冷气的黑色手枪掏出来,给他们看。妈妈脸色沉重地说:“枪从哪来的?”
我说:“从那个摊点拿来的。”
妈妈拉着我的手,矮下身来,抚摸着我单薄的身子和通红的脸庞,用一种异常平淡的口吻说:“孩子,妈妈跟你说过多少遍了,做人要堂堂正正,清清白白,不是自己的东西不能,不能偷……”
我把手枪晃在大哥的眼前,沾沾自喜。大哥定定地看着我,一言不发。妈妈说:“把手枪还回去,你还是妈妈的好孩子。”
我耍性子,置气着说:“妈,你不给我买,我自己拿回来,你还要我还回去。”
我直到现在都不愿回想那段不堪的往事,我也极度不愿意回去主演那一次赶集中最精彩最悲惨最难忘的重场戏。妈妈拉着我的手,到那个摊前,此时摊主已经回来,妈妈满含歉意地说:“大兄弟,我的孩子年纪小,不懂事,拿了你的东西,我也教育了他,也把东西还回来了,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妈妈说着夺去我手中的玩具枪,轻轻地放回了摊上。
那位叔叔耸动腮帮子,摸着那把散发着冷气的冒着寒光的手枪,用一种极其复杂的眼神看着我,平静地说:“嫂子,东西找得回来就没事。”
直到现在我都不能准确理解那眼神的全部含义,是失望,是愤怒,是恨铁不成钢,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我的品德的全盘否定?在以后的为人处世中,我一想起那个阴气逼人的眼神,就如锋芒在背,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仿佛经过了一个冬季,群山环绕的小镇中,有大雾气从山顶弥漫开来,把整个镇子包围起来,灰色的天空飘起了毛毛细雨。人们的视线只在一条街里,除此之外,看不到其他的地方。赶集的人也少了,没人会关心我一个失落的孩子。玩具枪还回去后,我还在原来那个不远不近的地方,站着哭着,眼睛须臾不离那把散发着冷气的冒着寒光的手枪。妈妈拗不过我,领着哥哥去买年货。天色渐渐暗淡下来了,要在集市散场前把年货置办齐全。
摊主守着摊位,天飘着雨夹雪的时候,他进房子里拿着一把大伞过来,张开大伞,覆盖着摊位。趁着他来来回回地出入房里,我突然故技重施,在他进屋子的瞬间,窜出来,伸手去拿那把枪。但这次却没有那么幸运了,我脏兮兮的小手还没碰到手枪,就被胖叔叔一把抓住,嘴里大声叫嚷着:“杂种……小偷……”然后一下把我摔到街边,我整个身子滚了两圈,脑袋撞到街边的台阶上破了一个洞,流出血来,身子像水牛在水坑打转似的,一片泥泞,滚成了个泥人。路人向我投来鄙夷的目光,我抱着脑袋,挛缩在地上。这时,人群中蹿出一个人来,一把把我抱起搂在怀里,泣不成声地哆嗦着,“儿啊,你怎……怎么样了,你……没事吧……你忍着……”
我知道我在妈妈的怀抱里,我哭着,妈妈也哭着,我们母子的哭声在拥挤肮脏的街道毫无归宿地回荡着。
妈妈近乎崩溃,呜咽地悲苦起来,雨雪落在我们身上、脸上,妈妈的泪水落到我脸上,就像雨雪一样冷,让我分不清是她的泪水还是雨雪。妈妈哭天抢地:“孩子他爹,你这个负心汉,一年半载不回家,留下两个娃,让我千辛万苦拉扯长大,抬头不见青天,低头不见你爹娘,你再不回家,这家不成家了,你知道村里的流言蜚语吗,你知道别人都说我什么吗,说我在村里找汉子啦,说你两个宝贝儿子不是你的种啦,不是你的,那是谁的啊?”
我妈妈撕心裂肺地哭着说:“儿啊,你脑袋流血了,你还好吗,我们去河边洗洗。”她抱着我,仰望苍天说:“孩子他爹,我们的孩子……”
我断气般一边哭泣一边说:“妈妈,那个胖子说我是杂种,是小偷……”
妈妈悲痛地啜泣说:“你不是杂种,你有爸爸,有妈妈,……你的爸爸出去打工,赚很多很多的钱,给你买很多好玩的玩具枪……你也不是小偷,你在妈妈眼中是最好的孩子,儿啊,等下妈妈给你买玩具枪,你别哭了好吗?”
我哭声渐息渐止了,妈妈的哭声缥缈遥远了,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故事讲到这里本该结束了,因为上述的真实而悲惨的经历魂牵梦萦般充斥着我的整个童年时代的记忆。但是为了让故事更加根深蒂固,枝繁叶茂,让往事更加有血有肉,有滋有味,我有必要进行下面的讲述,作为故事的结尾。
大哥遵照着妈妈的指示,买了年货,去街尾的榕树下守着东西,等待我和妈妈。妈妈拉着我的手从街道七拐八绕找到了大哥,我们三人相依为命,赶赴回家的路。返回的路上,如同是时间的轮回一般,让人觉得很多事情都可以从头再来。
从镇上到罗共村,几重山路,几重水路,还可以看到三三两两、成群结队的人们走在回环蜿蜒的小路上,过了罗共村,基本就没人跟在后面,本村的人因为旅途遥远,早去早回了,偶有一两家落在我们后头,不用多长时间也把我们超越了,翻过一座山岭,就不见人影,远远地把我们甩在后头。
天色一点一滴如下雨般地暗淡下来,水坝还没有走完,雨雪风还是一路相随,天彻底黑了,没有星星没有月亮的暗黑夜晚,群山影影绰绰,荒草小道两边的树木像无数个暗影,阴森恐怖。我夹在中间,打着电筒,照应前后,电筒突然卡的一声没了光亮,三人全部陷入漫无边际的黑暗中,妈妈着急说:“儿啊,怎么把电筒关了。”
哥哥战栗说:“弟,快打开手电照路。”
我惊慌地说:“我没关,它自己关的,会不会是早上妈妈把它摔坏了。”
坝里的水黑黝黝地汩汩流动着,泛起悠悠的声音和深谷的大河流水撞击石头发出的澎湃的声响混杂在一起,夹带着远近无人的暗淡恐怖。连绵的群山被疾风掠过,产生了无数个声音,像是樵声,像木鸟啄枝,像猿猴啼哭,野狼长嚎,又像山鬼嘶鸣……声音十分的神秘莫测,让我十一分的担惊受怕。
手电突然砰的一声亮起来,我们又恍恍惚惚,踢踢踏踏地迈开了轻声的脚步。我不知者无畏般高兴地说:“妈妈,还有人在砍树,还有人在我们后面。”大哥一向沉默寡言,他不接我的话,只顾认真走着。妈妈自顾着赶路,过了半晌,颤抖着说:“别说话,注意赶路。”
峰回路转之后,村边那棵古老的千年榕树已经近在眼前,我欢乐地对妈妈说:“到家了,为什么后面砍柴的人没跟上我们呢?”
妈妈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到了这里,我们才算是到家了。”
大哥对我说了一句:“弟弟,你觉得谁会在晚上砍柴呢?”
妈妈笑着说:“夜里砍柴的传说,我讲给你大哥听了,没跟你讲过,你不知道。”
妈妈双手顶着背篓的底部,耸耸肩膀,边喘着气,边娓娓地跟我们说那个故事。传说从前村里有个男人,为了寻找失踪的妻子,越过深谷里的大河,误入那一片后来村里人尽皆知的臭名昭著的原始森林,那片原始森林仿佛深渊一样幽僻孤寂,日照不进,人迹不至,充满古怪而神秘的气息。男人在林里迷失方向,走了方圆十几里,四周始终围着相同的却又似是而非的缠满藤枝蔓葛的参天大树。男人没有再出来,从此没人再敢进去那片树木成精的原始森林。男人失踪的那天黄昏,河中的秋水意外暴涨,乌黑的洪水席卷着断木,枯叶,破筏,滚滚而流,淹没了岸边的生灵。男人回不来了,家里人焦灼了一晚上,第二天约着全村人一起满山找了大半月,始终没找到,不久以后,村里人在初一,十五,三十这几天的晚上路过那片原始森林的对岸这一边大坝时,开始听到樵声阵阵,彻夜不绝,村民们说,那是男人在砍伐树木,开辟道路,寻找妻子……
我听了妈妈讲的故事,起了一身鸡皮疙瘩,幼小的心灵颤抖不已,被吓得要哭出来。每当我回想起村中那些至今无法理解的千奇百怪的事情都会神经错乱般不知所措,如同二十年前的我一样惊惶不安。
妈妈接着说:“刚才你说听到砍柴声的时候,你不知道妈妈有多惊怕。如果没有你们,妈妈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以为妈妈年纪比我大,人比我大,胆子也比我大,却也一样害怕,我说:“我最小,我最怕……”
妈妈说:“是人都会害怕的,都是人与人相照为胆,人与人相依为命。所以人为什么要成家立室,我和你们爹为什么希望你们快点长大,有出息,就是害怕有一天父母老了,不在了,你们有媳妇了,一起去面对让人害怕的事情的时候,才不会感到那么害怕。”
我和大哥似懂非懂地沉默不语。妈妈又说:“以后你们长大了,再大的风雨,也要记得回家。天底下的路有千万条,但回家的路只有一条,天底下的人千万个,父与母只有一个……”
过了那可棵被村里的年轻人看作是爱情的象征,被当作在仲夏月圆之夜幽会的固定场所的千年榕树,再走百来步,就到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