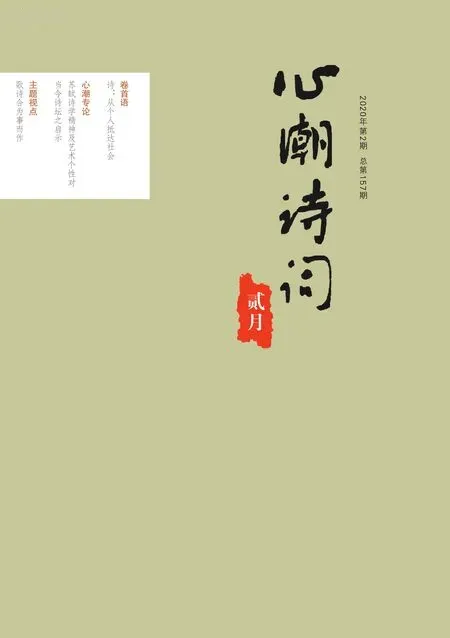对联是沟通新诗与诗词的桥梁
常 江
从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开始,崛起的新诗便和传统的诗词,形成尖锐的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了百年诗史。对立的结果,是各自为王,各领风骚。在中国作家协会的旗下,一个中国诗歌学会,管新诗;一个中华诗词学会,管诗词。赛诗,各有一套评审机制,各有一种批评原则,各有一支创作队伍,各有一批评审专家。你那里建立“诗词创作基地”,我这里聘请“校园诗人”。这两年的《中国诗词大会》,让诗词火了一把,很快被人议论“那是背诗的功夫”,火苗顿时低了不少;新诗百年,热烈庆祝一番,自称新诗也继承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化传统,很快有人议论,是继承西方文化传统一百年吧……
这是现状。就这样走下去吗?
有识之士提出,新诗和诗词要团结起来,互相学习。好主意。
怎么团结?怎么学习?这应该是我们认真讨论的事情。团结的手段,学习的措施,不是一种,哪种更有效,需要实践的检验。根据个人的创作和研究经历,发表意见,是当代诗人的历史责任。
几十年来,我写新诗,也写诗词。后来一心一意搞起对联,新诗和诗词都写得不多了。近几年来,我评对联,也评新诗,也评诗词,常常将这三者进行对比,逐渐地悟出点东西,所感所悟,又逐渐清晰起来,形成了我的这个观点:对联是沟通新诗与诗词的桥梁。
这个命题,首先是把我自己吓了一跳:天哪,对联有如此大的功德吗?仔细想想,这不是胡说八道,也不是开玩笑,还真有点靠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参与主编《中国对联大辞典》,第一次把对联知识、对联历史用词条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在写“五四运动对联”词条的时候,惊异地发现两个奇妙的现象。
其一,五四运动是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样大的历史事件,流传下来的文学作品却很有限:诗词和“孔家店”一起被“打倒”了,新诗也只剩下几声遥远的呐喊,能够沉淀下来至今还被人乐道的,竟然是对联!
五四对联,遍布学校、店铺,以至寺院,直接配合了学校罢课、商人罢市,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如:
四金刚捧日,的是可杀;
众商行罢市,尤须坚持。
五四对联,采用象征、借代、比喻、谐音、摹拟等多种手法,增强感染力,有高超的艺术性,如: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特别著名的是上海一鸟店所贴的:
三鸟害人鸦雀鸨(指烟、赌、妓);
一群卖国鹿獐螬(谐指陆宗舆、章宗祥、曹汝霖)。
其二,五四运动以后,新诗成为诗坛的霸主,诗词创作虽然有南社、漫社等一批文人坚守着,毕竟“大势已去”;但是,在这场大变革中,对联不仅毫发未伤,还不断形成高潮。1924年孙中山先生逝世,全世界的挽联铺天盖地,保守估计,也有50万副,在有些地方,写挽联的白布都脱销了。
对联能受到如此特殊的待遇,不被攻击,不遭反对,生命延续,生机旺盛,只有一个解释:对联是新诗和诗词共同的朋友。唯有这样,对联才能一手牵着新诗,一手牵着诗词,成为沟通二者的桥梁。
对这个新命题感兴趣的人会问,对联是怎么沟通的,换言之,对联与新诗及诗词有些共同的东西才能沟通。它们的共性在哪里?
我的看法,是三个方面,不妨看作是三座桥。
第一座桥,是“语言桥”。
对联和诗词的语言沟通,不成问题,本来它们就是在一个诗歌传统体系中。
对联有格调如诗的:
春风放胆来梳柳;
夜雨瞒人去润花。
(清·郑燮)
对联有格调如词的:
新相识,旧相识,春宵有约期方值,试问今夕何夕?一样月色灯色,该寻觅;
这边游,那边游,风景如斯乐未休,况是前头后头,几度茶楼酒楼,尽勾留。
(何澹如撰佛山赛会)
对联有格调如曲的:
出门一瞧,数十里图画屏风,请看些梵宇僧楼,与丹枫翠柏相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青的靛青,绿的碧绿;
归台再想,几千年江山人物,回溯那朱门黄阁,和白屋蓬扉接壤,名者争名,利者夺利,圣者益圣,庸者愈庸。
(山东济南千佛山北极阁)
对联的特色是雅俗共赏。“俗”的内容很丰富,其中一种就是白话。白话对联自古就有:
放开肚皮吃饭;
立定脚跟做人。
(某相国题)
“五四”期间,更有商铺贴出的白话对联:
学生一天不释;
本店一日不开。
有些对联,就和白话诗一样:
嫩头的绿叶,渐发芽了;
巧舌似黄莺,真好听呀。
(题音乐学校)
当新诗与诗词在“语言桥”上相会,便演绎出一个个精彩的故事:贺敬之的像格律诗,郭小川的像元曲小令……而聂绀弩的格律诗口语化,一批年轻诗人正在用当代语境创作……
第二座桥,是“对仗桥”。
对仗是汉字独有的存在方式,也反映了中国人思维的哲学意义,当然,对仗是对联的灵魂。诗词不以对仗为自己的基本特征,但在格律上离不开对仗:有些词,相邻的五字句、七字句是必须对仗的;律诗,中间两联也是必须对仗的。由于对仗,我们可以感到文字很美。这些都无须解释。
问题是新诗对仗吗?请看:
挽断白发三千丈,
愁杀黄河万年灾。
(贺敬之《三门峡·梳妆台》)
如果不那么严格要求的话,它们本身就是一副对联。郭小川“长吟大赋”式的诗作,以严格或稍为宽松的对仗为基本特色,如:
继承下去吧,我们后代的子孙!
这是一笔永恒的财产——千秋万古长新。
耕耘下去吧,未来世界的主人!
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人间天上难寻。
(郭小川《刻在北大荒的土地上》)
以写短诗见长的张志民,更是注重句子的凝练,离不开对仗:
亭亭座座珍珠塔,
层层叠叠翡翠楼。
(张志民《秋到葡萄沟》)
“五四”以来,不少诗人的探索,力图离古典诗词更远些,更自由些。但有个令人深思的现象,便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运用对仗,“流露”出一些对偶句来。即使主张句数不等、句式不齐,甚至不用标点的,也难以完全摆脱“对偶”。如:
伊犁苹果香又甜
鄯善的瓜儿甜又香
(艾青《垦荒者之歌》)
向昨天告别,
不需要用眼泪串成珠链。
向明天走去,
不需要用彩虹搭成长桥。
(罗洛《不需要》)
就是“五四”诗人,他们的“对偶句”也比比皆是。可以说,从每个现代诗人的作品中,都可以找出这方面的证据。那么,“现代派”诗人们,又怎么样?有趣的是,他们也并不那么讨厌对仗。以著名的引起过争论的这首《远和近》来看:
你
一会看我
一会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全诗六句,竟然有四句是相当于“对仗”的。这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现在,我们很难在各种新“派”、各种新“体”的诗里,找到对仗的例子,他们以“反传统”作为自己的旗帜,故意不去对仗,成心破坏对仗,以形成自己的“风格”。这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到桥上见面再说吧。
第三座桥,是“韵律桥”。
诗词的韵律,比较好理解,简单说,可以理解为格律。这种韵律,是古人长时期的经验总结,形成科学性的规律。平仄规律,是为了好读、好念、好吟诵,可以吟出高低起伏,可以吟出荡气回肠。律诗要求押平声韵,是为了能把声调拉长。为什么忌孤平,因为不好读。“红军不怕远征难”好读,远征改成长征,就没法吟诵。
新诗有押韵和不押韵的。汉语押韵体现了最好的韵律,有些诗人对于韵脚的字词选择十分讲究,比如郭小川。我们看他《祝酒歌》的前两节:
三伏天下雨哟,
雷对雷;
朱仙镇交战哟,
锤对锤;
今儿晚上哟,
咱们杯对杯!
舒心的酒,
千杯不醉;
知心的话,
万言不赘;
今儿晚上啊,
咱这是瑞雪丰年祝捷的会!
你看,这里的韵脚多么精细:第一小节,“雷”“锤”“杯”,都是平声字,而且都是阴平,第一声;第二小节,“醉”“赘”“会”,都是仄声字,而且都是去声,第四声。
不押韵的新诗,标榜“自由”,但“自由”的结果,总让人感觉是分行的散文。走在“韵律桥”上,新诗有了重大发现:哈!对联你也不押韵。
说得没错,对联是不押韵的。对联上联一般以仄声字结尾,下联一般以平声字结尾,一仄一平,当然不押韵;但是,这一仄一平,形成了韵律。不只在句脚,全部对联的文字都有平仄规律可循。
个别时候,对联也在本联中押韵,可以营造一种趣味,像梁章钜的作品:
客来醉,客去睡,老无所事吁可愧;
论学粗,论政疏,诗不成家聊自娱。
有的新诗,没有标点,不像《祝酒歌》那样,给读者许多提示。而且,看起来随意转行,也许当中有语气回旋、情感转折的韵律在。
语言、对仗、韵律,这三座桥上,来来往往的人越来越多。新诗走过桥来,会看到诗词的高妙;诗词走过桥来,会看到新诗的瑰丽。
我常常在这三座桥畔行走。我对写新诗的朋友说过,学点古典诗词吧,那里有我们民族自己的东西,有说不完的魅力,你会受益良多;我对写诗填词的朋友说,不妨向新诗学习,那里有新的立意,新的角度,更有接地气的当代语境;写新诗也好,写诗词也好,现在,我想对各位说,何妨多关注一下对联呢,那也是一座宝山,攀登者必定有不寻常的收获。
以上,我是从自身的角度谈看法,所说的话可能有偏颇之处,那就请多加原谅。为此,仿照苏东坡《题西林壁》改诗一首,来结束我的发言:
新诗成岭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诗坛真面目,只缘身在对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