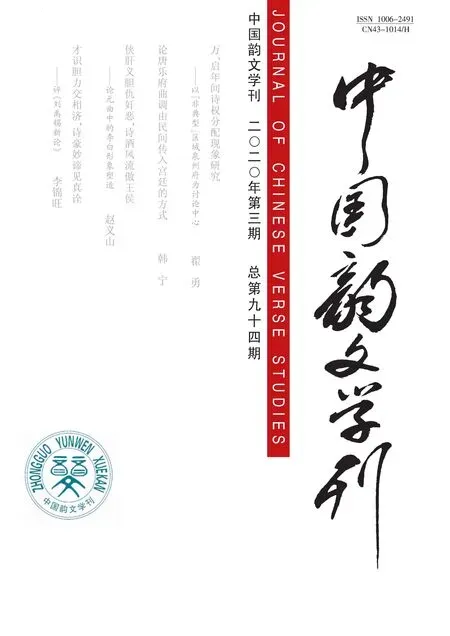濂溪诗与周敦颐“仙翁隐者”形象的塑造
——兼论苏轼、黄庭坚对周敦颐的推崇
许和亚
(浙江大学 中文系,浙江 杭州 310058)
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号濂溪,世称濂溪先生,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是宋代比较特殊的一个人物,他生前在政治、学术领域可以说寂寂无名,身后却享有极高的声誉。苏轼说“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并赞之以“全德”。[1](P1667)黄庭坚说:“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2](P1063)苏、黄素不轻许可人,却极力褒扬周敦颐的人品、境界之高。至南宋,经过湖湘学派的胡宏、张栻以及朱熹、魏了翁等理学家的推尊和建构,周敦颐“理学开山”“道学宗主”的形象逐渐树立起来,道统地位的合法性最终获得朝廷的认可。(1)有关周敦颐“道学宗主”形象、地位在南宋的建构过程及相关问题,学界已有一些研究成果。论文参看王丽梅《周敦颐理学宗主地位的确立——张栻在周敦颐理学宗主地位确立过程中之作用与意义》,《哲学与文化》2009年第11期;周欣《周敦颐道学宗主地位的确立》,《学海》2015年第4期;肖永明、申蔚竹《南宋湖湘学派对周敦颐的推崇及其思想动因》,《湖南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专著参看Joseph A. Adler. Reconstructing the Confucian Dao: Zhu Xi’s Appropriation of Zhou Dunyi,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14. 周建刚《周敦颐与宋明理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年版。同时,周敦颐在北宋当代的真实形象、本来面目随之遭到遮蔽和尘封,并逐渐湮没于历史的长河之中。然而,周敦颐的诗歌创作以及北宋人的濂溪和诗、题诗,为我们重新认识周敦颐的形象及其塑造问题提供一个重要的窗口,其中苏轼、黄庭坚的濂溪诗创作是关键的一个环节。本文试图回到北宋特定的历史空间和文学语境,呈现被建构成“道学宗主”之前的周敦颐形象,揭示其受到同时人尤其是苏轼、黄庭坚推崇的深层动因。可以说,探究周敦颐在北宋的真实形象及其塑造问题,不仅在宋代思想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是宋代文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具有重要的文学史价值和学术意义。
一 自认与他认:“仙翁隐者”形象的生成
关于周敦颐在北宋时的情况,朱熹曾说:“濂溪在当时,人见其政事精绝,则以为宦业过人;见其有山林之志,则以为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无有知其学者。”[3](P2357)在三十余年的仕宦生涯中,周敦颐基本在地方上为官,长期从事刑狱、司法方面的工作,虽然“为治精密严恕,务尽道理”(潘兴嗣《濂溪先生墓志铭》)[4](P186),但毋庸讳言他是个典型的地方官吏,政坛上的声望和影响十分有限。从宋代学术的发展历程来看,宋兴八十年,至“庆历之际,学统四起”[5](P251),“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实启宋代学术之盛的先河,同时及稍后的范仲淹、司马光、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相继而出。尽管周敦颐在同僚、亲友眼中“好学博通,言行政事皆本之六经、考之《孟子》”[4](P148)(孔延之《邵州新迁州学记》),“志清而材醇,行敏而学博,读《易》《春秋》探其原”[4](P168)(吕陶《送周茂叔殿丞序》),“尤善谈名理,深于《易》学,作《太极图易说》《易通》数十篇,诗十卷,今藏于家”[4](P186),但在北宋政坛、学界群星闪耀的夜空,他无疑是异常晦暗的那一颗,闪烁着微弱的光芒。诚如侯外庐先生客观指出的,周敦颐“在北宋当代,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都没有很高的地位”,并明确断言“其崇高地位多出于后人追拟”。[6](P502)可谓确论。
其实,周敦颐主要是因其“山林之志”形成的“襟袖洒落,有仙风道气”的人格魅力,为时人所瞩目。周敦颐对自我形象有清晰的认定,妻兄蒲宗孟所作《墓碣铭》记载他“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常以仙翁隐者自许”[4](P188)。作为宋代士人阶层的一员,周敦颐虽然具有“自其穷时,慨然欲有所施,以见于世”[4](P187)的入世精神和安民之志,具有“事冗不知筋力倦,官清赢得梦魂安”(《任所寄乡关故旧》)[7](P73)的责任担当和淑世情怀,但其仕途并不算顺风顺水。正如北宋末王庶所作《濂溪诗》说:“先生帝王师,韫椟求善价。连城既不售,抱恨归长夜。”[4](P174)中岁以后,即辞官退居庐山濂溪之上,“区区世路求难得,试往沧浪问钓船”(潘兴嗣《赠茂叔太博》)[4](P168),成为其由仕宦转向山林的准确预言和真实写照。
宦海浮沉,周敦颐践行“吏隐”的为官之道;退居濂溪,他保全山林之志、涵养仙风道气。“吏隐”唐代已有之,王维在经历“安史之乱”后,亦官亦隐,奉行“无可无不可”的处世原则,践行“长林丰草,岂与官署门阑有异”[8](P1095)的人生哲学。白居易亦是“有志于吏隐者”,秉持“官不官,系乎时也。适不适,在乎人也”(《江州司马亭记》)[9](P2733)的出处原则,并在“吏隐”的基础上发展出“中隐”的仕宦理念。至宋代,以隐者之心为官吏之事的“吏隐”,更加趋于普遍化、常态化。周敦颐曾对潘兴嗣言及出处的态度说:“可仕可止,古人无所必。束发为学,将有以设施,可泽于斯人者。必不得已,止未晚也。”[4](P186)吕陶也说周敦颐“常自诵曰:‘俯仰不怍,用舍惟道。行将遁去山林,以全吾志。’”[4](P168)典型地体现了“吏隐”的仕宦心态。随着仕宦的流离播迁,周敦颐对隐逸生活的向往与日俱增,中年遂决定辞官归隐,真正开启其“仙翁隐者”的生活模式。在他三十余年的宦游生涯中,“诗笔不闲真吏隐”(赵抃《寄永州通判茂叔虞部》)[4](P170),常借诗歌吐露其以“仙翁隐者”形象追求“山林之志”的真实心声。
据蒲宗孟所作《墓碣铭》,周敦颐“尤乐佳山水,遇适意处,终日徜徉其间”[4](P188),凡任官所到之地,常不辞高远,遍游山川名胜。嘉祐五年(1060)正月,时任合州判官的周敦颐与将士郎赤水令费琦游龙多山,有酬唱诗八首,刻石于“高崖危嶝斗绝荒阻之间”[4](P155)。嘉祐八年(1063)正月,周敦颐通判虔州任上游罗岩,作诗云:“闻有山岩即去寻,亦跻云外入松阴。虽然未是洞中境,且异人间名利心。”[4](P157)寄情于名山大川、云外松阴,往往成为他摆脱世俗名利牵绊的重要方式。《同石守游山》亦云:“朝市谁知世外游,杉松影里入吟幽。争名逐利千绳缚,度水登山万事休。野鸟不惊如得伴,白云无语似相留。旁人莫笑凭栏久,为恋林居作退谋。”[4](P157)与逐名争利的朝市相比,诗人感觉山中的野鸟、白云更加亲切自然,已萌生退隐山林的念头。然而由于缺乏必需的物质保障,只能在政事之余游历山川以寄寓情怀:“久厌尘坌乐静元,俸微犹乏买山钱。徘徊真境不能去,且寄云房一榻眠。”[4](P158)在道观的“真境”中暂时获得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慰藉。
通判虔州期间,周敦颐已萌生退居庐山之意。嘉祐八年(1063),因虔州民家失火,周敦颐受牵连对移通判永州,仕途偃蹇,使他归隐山林的念头更加强烈。治平二年(1065)前后,“湓浦方营业,濂溪旋结庐”[4](P171)(蒲宗孟《乙巳岁除日收周茂叔虞曹武昌书,知已赴官零陵,丙午正月内成十诗奉寄》其七),周敦颐在庐山置办田产,建濂溪书堂,为退居濂溪做准备。在之后长达近十年的宦海浮沉中,周敦颐时常将归隐之念寄托于对庐山濂溪的吟咏之中。其《思归旧隐》诗云:“静思归旧隐,日出半山明。醉榻云笼润,吟窗瀑泻清。闲方为达士,忙只是劳生。朝市谁头白,车轮未晓鸣。”[4](P158-159)周敦颐以“达士”自处,厌弃熙熙攘攘、争名逐利的仕途,思念濂溪闲适惬意的隐逸生活。《夜雨书窗》诗云:“秋风扫尽热,半夜雨淋漓。绕屋是芭蕉,一枕万响围。恰似钓鱼船,蓬底睡觉时。旧隐濂溪上,思归复思归。钓鱼船好睡,宠辱不相随。肯为爵禄重,白发犹羁縻。”[4](P159)亦是表达宦游中思归濂溪的主题。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周敦颐的这些诗歌“毫无理学的酸腐气,自有一种幽趣”[10](P123)。可以说,周敦颐诗歌所展现的“幽趣”,正是其“仙翁隐者”形象内在品格与洒落胸襟的外化。
不仅如此,周敦颐“仙翁隐者”的形象及其脱俗洒落的品格,也是时人所普遍认同的。赵抃《题茂叔濂溪书堂》称周敦颐“清深远城市,洁净去尘”,“主人心渊然,澄澈一内外”。[4](P170)周敦颐通判永州后,任大中作《江上怀永陵倅周茂叔虞部》诗云:“监州永陵去,远目立江干。烟浪三湘阔,风帆八月寒。不闻求进路,只见话休官。种竹濂溪上,归因作钓竿。”[4](P172)此时周敦颐对仕途已无求进之心。傅耆《周茂叔送到近诗数篇,因和渠阎、裴二公招隐诗》云:“三贤趋向一家同,不欲尘埃作苟容。明逸招归豹林谷,乐天邀入香炉峰。”[4](P167)种放,字明逸,《宋史》本传载其“与母俱隐终南豹林谷之东明峰,结草为庐,仅庇风雨”[11](P13422)。白居易任官江州期间,曾作《上香炉峰》《登香炉峰顶》等诗,表达摆脱“物役”“尘鞅”[9](P388)的愿望。傅耆将周敦颐视为种放、白居易的同道中人,指出他们在归隐的趋向上一致。周敦颐对山水之乐的热爱终其一生,蒲宗孟作《墓碣铭》描述说:“乘兴结客,与高僧道人跨松萝,蹑云岭,放肆于山巅水涯,弹琴吟诗,经月不返。及其以病还家,犹篮舆而往,登览志(忘)倦。”又说:“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常有高栖遐遁之意。”[4](P188)蒲宗孟是周敦颐的妻兄,所言大抵信实不虚。可以说,周敦颐的“孤风远操”“高栖遐遁之意”,正是其“仙翁隐者”形象最真切的反映。
二 互文与形塑:濂溪命名及濂溪诗创作的效应
因建构周敦颐“道学宗主”完美形象的需要,朱熹对濂溪命名进行了强制阐释,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对此有廓清的必要。其实,濂溪命名不仅蕴含着中国古代文学固有的隐性传统和互文特征,而且与周敦颐在北宋时的形象及塑造问题直接相关。此外,周敦颐的濂溪诗创作以及北宋人的和诗、题诗,使其“仙翁隐者”的形象、脱俗洒落的品格不断得到塑造和强化,最终获得“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的高度评价,并为后人所普遍接受。
关于濂溪的命名依据及旨趣,周敦颐在《书堂》诗中有明确的表达:
元子溪曰瀼,诗传到于今。
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钦。
庐山我久爱,买田山之阴。
田间有流水,清泚出山心。
山心无尘土,白石磷磷沉。
潺湲来数里,到此澄澄深。
有龙不可测,岸竹寒森森。
书堂构其上,隐几看云岑。
倚梧或欹枕,风月盈中襟。
或吟或冥默,或酒或鸣琴。
数十黄卷轴,贤圣谈无音。
窗前即畴囿,圃外桑麻林。
千蔬可卒岁,绢布足衣衾。
饱暖大富贵,康宁无价金。
吾乐盖易足,名溪朝暮侵。
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4](P158)
据潘兴嗣所作《墓志铭》,周敦颐“尝过浔阳,爱庐山,因筑室溪上,名之曰濂溪书堂。”[4](P186)此诗所咏即濂溪书堂,写出濂溪风景之美与书堂主人闲适自足的隐逸高趣。自何弃仲以“志乡关在目中”(《营道斋诗并序》)[4](P175)、邹旉以“示不忘本”(《游濂溪辞并序》)[4](P175)表彰周敦颐以濂溪命名溪流、书堂之后,朱熹从建构周敦颐“道学宗主”形象和地位的需要出发,赞同这一说法,并在《江州重建濂溪先生书堂记》《书徽州婺源县周子通书板本后》等文中予以高度肯定,影响深远,几为定评。不可否认,周敦颐以家乡道州营道县的濂溪村命名庐山家门前的溪流及书堂,从情感层面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然而,当我们追溯濂溪命名的影响渊源时,周敦颐的用意及其旨趣或许可以得到更加贴切的解释。
可以说,周敦颐对濂溪的命名无疑受到中唐诗人元结对瀼溪、浯溪命名的直接影响。元结《瀼溪铭并序》云:“瀼溪可谓让矣。让,君子之道也。”[12](卷六)其《喻瀼溪乡旧游》亦云:“尤爱一溪水,而能存让名。终当来其滨,饮啄全此生。”[12](卷三)其《浯溪铭并序》云:“吾欲求退,将老兹地。溪古地荒,芜没已久,命曰浯溪,旌吾独有,人谁知之,铭在溪口。”[12](卷六)证以上引《书堂》诗“元子溪曰瀼,诗传到于今。此俗良易化,不欺顾相钦”,可知周敦颐对濂溪的命名以及《书堂》诗的创作,直接启发于元结对瀼溪、浯溪的命名以及《瀼溪铭并序》《浯溪铭并序》等诗文的创作,典型地展现了中国古代文学蕴含的隐性传统及其互文特征。不仅如此,瀼溪与濂溪、元结与周敦颐之间存在重要的地缘关系:瀼溪、濂溪皆在九江,均属湓水;元结曾任道州刺史,周敦颐本是道州营道县人。同时,周敦颐、元结两人在为文上也有绝似之处,傅耆与周敦颐信中说:“兼承宠示《说姤》,意远而不迂,词简而有法,以之杂于元次山集中,能文之士观之,亦不能辨其孰周而孰元也。”[4](P151)再者,从精神层面观之,元结通过瀼溪、浯溪营造了一个“惬心自适,与世忘情”[13](P3883)的隐逸空间;周敦颐常以“仙翁隐者”自许,濂溪的命名不当与元结瀼溪、浯溪命名的精神相悖。其如北宋张舜民所作《濂溪诗》云:“洗耳褰裳本绪余,何须外物表廉隅。碧梧修竹藏丹凤,空谷生刍老白驹。水为不争方作瀼,溪因我有始名浯。北人要识濂溪景,请问江州借地[图]。”[4](P174)濂溪之于周敦颐的意义早已非“志乡关在目中”“示不忘本”所能概括,而是其处世品格、情怀高趣的外化形态,具有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周敦颐《书堂》诗中所说的“元子与周子,相邀风月寻”,当作如是观,方得其真意。
两宋之际的朱弁指出:“周茂叔,居濂溪,前辈名士多赋濂溪诗。”[14](P123)濂溪书堂建成后,围绕濂溪而进行的和诗、题诗活动在友朋、同僚间持续不断,赵抃、潘兴嗣、任大中、孔平仲等人皆有濂溪诗创作,南宋末刊本《元公周先生濂溪集》卷七中保存了不少这类诗歌作品。周敦颐去世后,其子周寿、周焘继承濂溪和诗、题诗的文学传统,经由苏轼、黄庭坚、贺铸等人的参与,濂溪诗创作在艺术成就和传播效应上皆达到新的高度。周敦颐“仙翁隐者”的形象和“光风霁月”的人格,正是通过这一传统不断得到形塑与强化。
周敦颐友人清逸居士潘兴嗣《和茂叔忆濂溪》诗云:
忆濂溪,高鸿冥冥遁者肥。
玉流来远不知源,源重山献翠深遮围。
试将一酌当美酒,似有泠然仙驭飞。
素琴携来谩横膝,无弦之乐音至微。
胡为剑佩光陆离,低心俯首随转机。
伊尹不忘畎亩乐,宁非斯人之与归。[4](P169)
潘兴嗣亦是一位由仕宦而退居山林的隐士,自称“清世之逸民”,辞官后“隐居豫章东湖上,琴书自娱”[15](P25)。潘兴嗣以《周易》“上九,肥遁,无不利”喻濂溪为隐居佳处,在其笔下,退居濂溪后的周敦颐是个像陶渊明、伊尹一样的隐士。又其《题濂溪》诗描述濂溪风光和周敦颐形象说:
鳞鳞负郭田,渐次郊原口。
其中得清旷,贵结林泉友。
一溪东南来,潋滟翠波走。
清响动灵粹,寒光生户牖。
峨峨双剑峰,隐隐插牛斗。
疏云互明晦,岚翠相妍丑。
恍疑坐中客,即是关门叟。
为歌紫芝曲,更击秦人缶。
窅然忘得丧,形骸与天偶。
君怀康济术,休光动林薮。
得非仁智乐,夙分已天有。
斫鼻固未免,安能混真守?
归来治三径,浩歌同五柳。
皎皎谷中士,愿言与君寿。
殷勤复恳恻,杂佩贻琼玖。
日暮车马徒,桥横莫回首。[4](P168-169)
“紫芝曲”即秦末汉初“商山四皓”四位隐士所作的《紫芝歌》,“三径”“五柳”代指陶渊明。此诗以商山四皓、陶渊明比拟周敦颐,歌咏了退居濂溪后的周敦颐闲适自得的隐逸生活和清旷豁达的出世情怀。赵抃《题茂叔濂溪书堂》诗云:
吾闻上下泉,终与江海会。
高哉庐阜间,出处濂溪派。
清深远城市,洁净去尘。
豪发难遁形,鬼神缩妖怪。
对临开轩窗,胜绝甚图绘。
固无风波虞,但觉耳目快。
琴樽日左右,一堂不为泰。
经史日枕藉,一室不为隘。
有莼足以羹,有鱼足以脍。
饮啜其乐真,静正于俗迈。
主人心渊然,澄澈一内外。
本源孕清德,游泳吐嘉话。
何当结良朋,讲习取诸《兑》。[4](P170)
描绘了濂溪书堂清深、洁净的生态环境以及书堂主人惬意、雅致的隐逸生活,并揭示出“主人心渊然,澄澈一内外。本源孕清德,游泳吐嘉话”的人格美感。孔平仲《题濂溪书院》亦是同题诗作:
庐阜秀千峰,濂溪清一掬。
先生性简淡,住在溪之曲。
深穿云雾占幽境,就剪茅茨结空屋。
堂中堆积古图书,门外回环老松竹。
四时风物俱可爱,岚彩波光相映绿。
先生于此已优游,洗去机心涤尘目。
樵夫野叟日相侵,皓鹤哀猿夜同宿。
方今世路进者多,百万纷纷争转毂。
矫其言行鬻声名,劳以机关希爵禄。
由来物役无穷已,计较愈多弥不足。
何如潇洒静中闲,脱去簪绅卧林麓。
先生此趣殊高远,不以寻常论荣辱。
奈何才大时所须,犹曳绯衣佐方牧。
鸾章凤羽出为瑞,未得冥冥逐鸿鹄。
先生何时归去来,古人去就尤宜速。
须怜溪上久寂寥,苍烟白露空乔木。[4](P173)
此诗作于周敦颐濂溪书堂建成之后、辞官退隐之前。在孔平仲笔下,与“鬻声名”“希爵禄”的仕宦之人受“物役”相比,周敦颐则优游于濂溪之上,“洗去机心涤尘目”,谋划着“脱去簪绅卧林麓”,过着潇洒闲静的生活。通过以上北宋时人的濂溪和诗、题诗创作,周敦颐的“仙翁隐者”形象不断得到塑造和强化,其飘洒脱俗的品格也得到反复展现和旌扬。
此外,由于濂溪成为周敦颐形象、品格的外化形态,时人还常将“廉”视作其品格的重要特征。任大中《濂溪隐斋》就说:“溪绕门流出翠岑,主人廉不让溪深。若教变作崇朝雨,天下贪夫洗去心。”[4](P172)其《再题虞部周茂叔濂溪》又说:
公廉如古人,禄利十钟疏。
照发一簪墨,乐归溪上居。
群峰插云秀,满眼如画图。
一瓮酒自足,数亩稻有余。
夜月摇吟笔,朝厨摘野蔬。
渴饮溪中水,饥不食溪鱼。
大溪深一丈,松筠自不枯。
公心保如此,真为廉丈夫。
廉名似溪流,万古流不休。
我重夷齐隐,日月光山丘。
夷齐魂若在,畅然随公游。[4](P172)
可以说,周敦颐“廉”的品格是当时人的普遍认知,“廉名似溪流”,符合周敦颐濂溪命名的旨趣和对自我形象的认定。再者,周敦颐《书堂》诗句“名溪朝暮侵”,一作“名濂朝暮箴”[7](P63),也许更接近周敦颐以“廉”喻“濂”之本意,正如元结以“让”喻“瀼”,以“吾”喻“浯”。杨杰《濂溪》诗也说:“山为羌仙传旧姓,溪因廉士得新名。愿持一勺去南海,直使贪泉千古清。”[16](P255)也即濂溪因周敦颐“廉”的品格而闻名。道潜《归周茂叔郎中濂溪》也说:“衣冠有旷士,眷此宜徜徉。乞身不待老,结屋栖其旁。高风慕箕颍,不羡尚书郎。松菊手自插,葱葱蔚连冈。了无川泽营,庶以廉自方。”[17](卷一)杨杰、道潜与苏轼交好,亦以“高风”“廉退”表彰周敦颐的精神形象和人格美感。
可以说,濂溪命名、濂溪诗创作以及周敦颐形象的塑造三者是紧密联结在一起的。濂溪命名的依据和旨趣,与元结瀼溪、浯溪的命名形成互文关系,是周敦颐“仙翁隐者”形象自我认知的直接反映。同僚、友朋的濂溪诗创作,不仅形塑、强化了周敦颐“仙翁隐者”的形象和脱俗洒落的品格,而且形成一种濂溪和诗、题诗的文学传统,并经由苏轼、黄庭坚等人的参与而得以发扬光大,影响深远。
三 苏、黄濂溪诗创作及其对周敦颐的推崇
南宋吴子良说:“山谷称周濂溪‘胸次如光风霁月’,又云:‘西风壮士泪,多为程颢滴。’东坡为濂溪诗云:‘夫子岂我辈,造物乃其徒。’盖苏氏师友未尝不起敬于周程如此。惜乎后因嘻笑而成仇敌也。”[18](P578)苏轼、程颐“因嬉笑而成仇敌”,引发蜀、洛两党之争,同时导致了所谓的“周程、欧苏之裂”[19](P17),也即在文学和思想领域形成“自元祐后,谈理者祖程,论文者宗苏,而理与文分为二”[20](P19)的文、道割裂局面。然而,在北宋诸多濂溪和诗、题诗中,尤以苏轼、黄庭坚的濂溪诗创作影响最大,流传最广,对周敦颐“仙翁隐者”形象、品格的塑造和推崇也居功最著。因此,探究苏、黄濂溪诗创作的相关问题,并揭示两人对周敦颐推崇的深层动因,在宋代文学史、思想史上皆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黄庭坚《濂溪诗并序》云:
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中岁乞身,老于湓城。有水发源于莲花峰下,洁清绀寒,下合于湓江。茂叔濯缨而乐之,筑屋于其上,用其平生所安乐,媲水而成,名曰濂溪。与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对茂叔之美。”虽然,茂叔短于取名而惠于求志,薄于徼福而厚于得民,菲于奉身而燕及茕嫠,陋于希世而尚友千古。闻茂叔之余风,犹足以律贪,则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二子寿、焘,皆好学承家,求予作濂溪诗,思咏潜德。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故余诗词不及世故,犹仿佛其音尘。[2](P1063-1065)
《濂溪诗并序》或创作于元丰四年至六年(1081—1083)黄庭坚为官太和时期。(2)南宋中期黄 《山谷年谱》将此诗附于崇宁元年(1102),疑误。黄庭坚元丰四年至六年任太和县令,其间周敦颐长子周寿(字元翁)任吉州司法参军,两人为同僚。元丰四年黄庭坚作《奉送周元翁锁吉州司法厅赴礼部试》,次年周寿中进士,六年黄庭坚与周寿、周焘兄弟多有诗歌唱和。又据《濂溪诗并序》说“二子寿、焘,皆好学承家,求予作濂溪诗,思咏潜德”,或可推断此诗作于黄庭坚为官太和时期。另南宋后期史季温《山谷别集诗注》也定为太和时期所作。郑永晓《黄庭坚年谱新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14页)、《黄庭坚全集辑校编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55页),皆定为太和时期所作。该序揭示了濂溪诗的创作缘由,濂溪“媲水而成”的命名由来,以及“足以律贪”的品格寓意。苏轼《故周茂叔先生濂溪》云:
世俗眩名实,至人疑有无。
怒移水中蟹,爱及屋上乌。
坐令此溪水,名与先生俱。
先生本全德,廉退乃一隅。
因抛彭泽米,偶似西山夫。
遂即世所知,以为溪之呼。
先生岂我辈,造物乃其徒。
应同柳州柳,聊使愚溪愚。[1](P1667-1668)
元祐三年(1088)正月,苏轼知贡举,周敦颐次子周焘为此榜进士。此诗应作于元祐四年(1089),苏轼刚从“洛蜀党议”的政争旋涡中抽身而出,以龙图阁学士除知杭州,此时周焘晋升两浙转运判官,同在杭州,故请求苏轼作濂溪诗。苏轼以“全德”“廉退”“造物乃其徒”表彰周敦颐品格、境界之高,视他如陶渊明、伯夷、叔齐这样淡泊名利的隐士。同时,柳宗元世号柳柳州,名愚溪而居,愚溪之于柳宗元即如濂溪之于周敦颐,是其形象的自我写照和品格的外化形态。苏轼、黄庭坚对濂溪的解读,遭到何弃仲、邹旉以及朱熹等人的批评,朱熹甚至批评周敦颐长子周寿“与苏、黄游,学佛谈禅,盖失其家学之传已久,其言固不足据”[21](P1836)。周寿“学佛谈禅”确实不虚,黄庭坚集中《答濂溪居士》即答复周寿学佛“蹊径”[22](P1038-1039)之问,而且周寿与僧人道潜也有交往。(3)濂溪居士的身份,学界尚无定论,甚至有研究者以此作为周敦颐与黄庭坚交往的证据,纯属臆测。今据道潜《参寥子诗集》卷七《规师方外停云斋》:“铭诗善摹写,居士亦风流。”自注云:“揭榜、作铭皆濂溪居士,居士即周元翁也。”(《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可断定濂溪居士即周敦颐长子周寿。然而不可忽视的是,黄庭坚、苏轼所赋的濂溪诗分别受周敦颐之子周寿、周焘的请求而作,苏、黄二人在作濂溪诗前应阅读过周敦颐之子提供的《墓志铭》《墓碣铭》以及前人所和、题的濂溪诗,也应该知道周敦颐的家乡是营道县濂溪村,而苏、黄诗中之所以仍旧标举“廉退”“律贪”,一方面应为周敦颐父子的共同认知,另一方面或受任大中等人所作濂溪诗的影响。周敦颐二子“好学承家”,继承濂溪和诗、题诗的文学传统,请求苏、黄作濂溪诗以旌扬乃父名节,因此黄庭坚在《跋周元翁龙眠居士大悲赞》中评价周寿说:“吾友周寿元翁,纯孝动金石,清节不朽,虽与日月争光可也。”[23](P1584)贺铸《寄题浔阳周氏濂溪草堂》诗也是受周寿的请求而作,其序云周敦颐“中年投节,退居湓城之南溪上,因名濂溪以自况。二子:寿,字元翁;焘,字次元,相踵第进士。丙子(绍圣三年)五月,余舣舟汉阳,始与元翁相际,求余赋此诗。”有诗句云:“濂溪之水清,未足濯公缨。平生抱苦节,成就此溪名。”[24](P193)周敦颐“中年投节”“名濂溪以自况”“平生抱苦节”,恰可以彰显其“廉”的精神品格。因此,南宋周以雅《濂溪六咏》其一说:“此心安乐莫非廉,媲水成名亦偶然。湓浦舂陵随地在,不应太史失其传。”[4](P181)太史即黄庭坚,苏轼、黄庭坚、贺铸等人与周敦颐之子周寿、周焘皆有交谊,所作濂溪诗不应偏离周敦颐濂溪命名的本意与旨趣。
周敦颐在北宋之所以被当代人尤其是苏、黄推崇,与其“仙翁隐者”形象以及“廉退”的品格息息相关。中国古代的隐逸传统源远流长,《周易》所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25](P71),即道出了古之隐者遗世独立的人格魅力。至宋代,士人对隐逸的看法相对辩证,“小隐隐林薮,大隐隐朝市。市朝心隐不隐身,山林未必忘名利”[16](P105)。此时,隐逸群体的生存状况、精神面貌较之前代已有很大的改变,他们大多不再以“不事王侯”高自标置、幽栖岩谷远避于世,而是自觉投身于学术研究、教育子弟或文学创作之中,如林逋、陈抟、种放、魏野、邵雍等人皆是如此。对于羁旅宦途、受名利牵绊的士大夫而言,隐君们“适意江湖,草芥功名,陶情畎亩,浮云富贵,咏诗于霸陵之乡,采药于武安之山。掷楯而叹,耻役亭长;解绶而归,羞为折腰”[26](P253)的隐逸生活和人格魅力具有天然的吸引力。然而,现实却是“诗人类以弃官归隐为高,而谓轩冕荣贵为外物,然鲜有能践其言者”[27](P266)。因此,宦途士子不仅普遍对隐者不吝褒扬,而且对弃官归隐行为以及恬退品格尤为叹赏。北宋刘恕的父亲刘涣就是一个由仕宦而归隐的典型个案。据载:“父涣,字凝之,举进士而颍上令,以刚直不屈于上位,即弃官而归,家于庐山之阳,时年且五十。欧阳修与涣同年进士也,高其节,作《庐山高》诗以美之。涣居庐山三十余年,环堵萧然,饘粥以为食,而游心尘垢之外,超然无戚戚之意。以寿终。”[28](P567-568)皇祐二年(1050),欧阳修作《庐山高赠同年刘中允归南康》诗,送别辞官归隐的刘涣,盛赞其“宠荣声利不可以苟屈”,“丈夫壮节”可与庐山比高。[29](P84)此诗一出便广为传颂,获得朝野名流的激赏。不仅如此,“方是时,学士大夫争为咏叹以饯之”[30](P258),形成了广泛的崇隐之风和社会影响。
在由仕宦而辞官归隐的路径和影响上,周敦颐与刘涣可谓如出一辙。周敦颐中岁辞官归隐前,已在庐山建濂溪书堂,并且作《书堂》诗以彰显己志。这在朋友、同僚间引起较大反响,潘兴嗣、赵抃、蒲宗孟、李大临、任大中、孔平仲等人皆有濂溪和诗、题诗创作,尤其到苏轼、黄庭坚的濂溪诗创作,才真正使周敦颐声名大振。周敦颐在北宋被推崇并赢得大名,固然与其子周寿、周焘请求苏轼、黄庭坚、贺铸等人创作濂溪诗有一定的关系,但更为根本的则是时代风气的产物,是宋初以来朝野上下崇隐之风的逻辑发展,根植于中国古代隐逸传统的文化心理之中。时人与后人对周敦颐“仙翁隐者”形象以及“廉退”“脱俗”品格的推崇,一定程度上源于自我心灵的投射。对于向往隐逸而未能付诸实践的士人而言,将对闲适生活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对隐逸之士的推崇和赞扬,或许不失为一条抒发宦游心绪的有效途径,尤其对深陷朋党之争旋涡的北宋士大夫而言更是如此。
同时,周敦颐“仙翁隐者”形象展现的脱俗洒落的人格美感,与苏轼、黄庭坚“不俗”的精神追求和理想品格相契合,这可以说是苏、黄二人极力推崇周敦颐的内在动因。潘兴嗣《赠茂叔太博》称赞周敦颐“心似冰轮浸玉渊,节如金井冽寒泉”[4](P168),何平仲《赠周茂叔》说他“冰壶此外更无清”[4](P171),以“冰轮”“冰壶”喻周敦颐品格之通透融明。赵抃《题茂叔濂溪书堂》说他“主人心渊然,澄澈一内外”,孔平仲《题濂溪书院》以“先生性简淡”“洗去机心涤尘目”称之,蒲宗孟《墓碣铭》描述他“生平襟怀飘洒,有高趣”,“其孤风远操,寓怀于尘埃之外”。黄庭坚在以上诸人的基础上,对周敦颐的形象、人品进行了高度的概括和提升,说他“胸中洒落,如光风霁月”。南宋理学家李侗、朱熹因此语“形容有道者气象绝佳”[31](P322),也给予了高度的肯定。不仅如此,为了与周敦颐的人格精神相契合,北宋濂溪诗的创作者们也主动以“脱俗”为艺术标准。傅耆在与卢次山的书信中说:“濂溪诗文,皆当世名公所为,自顾顽钝,未敢措手。或时强为,皆未能脱俗气,故迟疑蓄缩,久而未敢尘听也。”[4](P152)黄庭坚《濂溪诗并序》也指出:“茂叔虽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终在丘壑,故余诗词不及世故,犹仿佛其音尘。”其实,“脱俗”“不俗”本身也是苏、黄的人生追求和理想品格。苏、黄二人的诗文集中频繁提到对“俗”“世俗”“尘俗”的厌恶,对“不俗”的欣赏和追求。苏轼《於潜僧绿筠轩》说:“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1](P448)其《书林逋诗后》又说:“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1](P1344),对林和靖“神清骨冷”的“绝俗”气质表示神往。黄庭坚《寄题安福李令爱竹堂》说:“渊明喜种菊,子猷喜种竹。托物虽自殊,心期俱不俗。”[2](P838)其《书缯卷后》也说:“余尝为少年言,士大夫处世可以百为,唯不可俗,俗便不可医也。”[23](P1569)可见苏、黄二人对“不俗”品格的高度认同与一致追求,这与周敦颐“仙翁隐者”形象所展现的脱俗洒落的精神气质相契合。可以说,正是在这一维度上,苏、黄高度认同“仙翁隐者”形象的周敦颐,并创作出脍炙人口的濂溪诗,展现了对周敦颐的高度敬意与大力推崇。
四 结 语
自南宋张栻、朱熹等理学家从创立理学本体论和建构理学道统的需要出发推尊周敦颐以来,后人对周敦颐的认知多基于其“道学宗主”的形象和学术地位,其在北宋时的本来面目、真实形象则遭到严重遮蔽。本文致力于回到北宋时的历史空间和文学语境,揭开周敦颐“道学宗主”形象的面具,展现其在北宋时的真实形象、本来面目——“仙翁隐者”。周敦颐的“仙翁隐者”形象不仅出于自我认知,而且获得时人的普遍认可。周敦颐的濂溪命名受中唐诗人元结瀼溪、浯溪命名的直接影响,是周敦颐廉退品格、隐逸高趣的外化形态,展现了中国古代固有的隐性文学传统及其互文性特征。北宋时期围绕濂溪而进行的和诗、题诗活动,一方面形塑、强化了周敦颐“仙翁隐者”的形象及其脱俗洒落的品格;另一方面也形成一种濂溪和诗、题诗的文学传统,在周敦颐二子的推动下,经由苏轼、黄庭坚以及众多友朋的参与而得以发扬光大,并产生广泛的传播效应和深远的文化影响。虽然苏、黄二人是受周敦颐之子周寿、周焘的请求而作濂溪诗,但“造物乃其徒”“光风霁月”的评价可谓推崇备至。苏、黄等人对周敦颐的推崇,一方面与周敦颐“仙翁隐者”形象及其“廉退”品格息息相关,是宋代崇隐风尚的逻辑发展,根植于中国古代隐逸传统的文化心理之中;另一方面是由于周敦颐“仙翁隐者”形象展现出的脱俗洒落的人格美感,与苏、黄对“俗”“世俗”的厌恶以及对“不俗”“脱俗”的人生理念、精神品格的追求相契合。这是我们探究周敦颐“仙翁隐者”形象的塑造与被推崇的深层动因的重要维度,同时对理解北宋中期以来的“周程、欧苏之裂”乃至文、道之关系,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