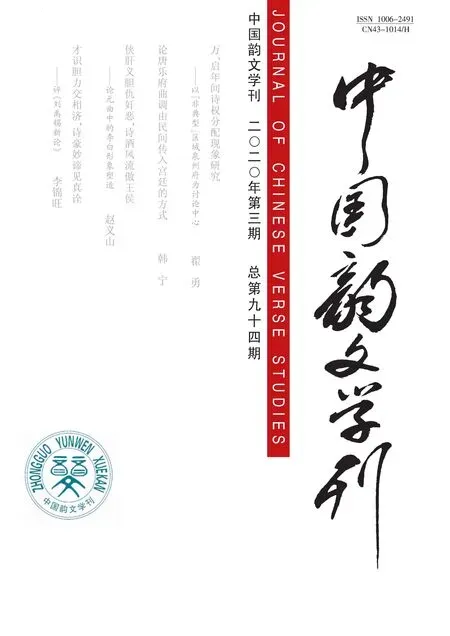《诗经·黍离》主旨辨正
杨淑鹏
(晋中学院 中文系,山西 榆次 030600)
《黍离》是《诗经·王风》的第一篇。根据《诗经》编排规律,一般排在每部分之前者,都是该部分中最主要的篇章,因此历代倍受人关注,异说自然也较多。20世纪的一批学人,则对传统的《诗经》诠释做出了全面颠覆,务求冲破“旧经学”的范囿,还《诗经》以文学的本来面貌,就诗论诗,各奋私智,故而在短短不到百年之间产生的新说,就远远超过了过去的两千年。郭沫若认为是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1](P208),蒋立甫认为实际是旧贵族“感伤本阶级的没落”[2](P73);陆侃如、冯沅君[3](P36),程俊英、蒋见元[4](P194)以为写迁都时心中的难受;余冠英[5](P72)、褚斌杰[6](P181)、金启华[7](P150)、李蹊[8]等以为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郭晋稀以为是卫人流滞王城者所作[9](P73);蓝菊荪认为是怨战之作[10](P215);叶知秋以为“为人类千古之问——‘我是谁’而作”(1)冯现冬《对生命本体存在的千古追问》(《名作欣赏》2016年第10期)也有类似的观点。[11];其他还有“情诗说”(2)许永强《〈黍离〉是一首爱情诗》一文中以为,“这首爱情诗分三章,皆以离离成行的黍稷起兴,写一青年因爱恋着一个姑娘而不可得的愁郁心绪”(《韩山师专学报》1993年第2期)。,“奴隶号叫说”[12],“失去土地的农民的哀号说”[13],“下层官吏怨刺说”[14]等。统纲这些新说,有其共同的时代特点:一、基本不考虑秦汉经师传说与史籍的相关记载;二、基本不考虑前贤的研究成果;三、唯创新是务,把标新立异作为追求的方向。这种风气风行百年,至今未沫。虽说20世纪的革命思潮,对于冲垮旧的学术格局产生了积极意义,推动了中国学术的迅猛发展,但毕竟也留下了诸多遗憾。要想对《诗经》做出合理的解读,还必须全面综合分析前贤的研究成果,从其所善,补其不足,从而做出新的探讨。故本文首先要对两千多年来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做全面的梳理。其次分析其得失,找出新解决途径,以求通过对《黍离》创作主旨的探讨,深化文本研究。
一 《黍离》主旨旧说十种
笔者详考两千多年来中日韩三国300余学者对《黍离》主旨的研究,特就其歧说缕析于下。
一、“闵宗周”说
此说首倡于《毛诗序》,其曰:“《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15](P5)孔颖达疏解其意说:“……周室颠覆,正谓幽王之乱,王室覆灭,致使东迁洛邑,丧其旧都,虽作在平王之时,而志恨幽王之败,但主伤宫室生黍稷,非是追刺幽王,故为平王诗耳。又宗周丧灭,非平王之咎,故不刺平王也……”[15](P5)这里重点强调几点:第一,创作时间在平王时;第二,创作事由为西周王室覆灭;第三,表达的情感是闵伤宗周,而非刺幽王,更非刺在朝天子平王。这一观点,基本上代表了汉唐持毛说的基本认识。历代注家遵从其说者最多,如苏辙、李樗、范处义、戴溪、许谦、梁寅及日本中村之钦、冢田虎、东条弘、安井衡等,李朝朴世堂、金钟厚、申绰等,皆从其说。有些学者在此基础上还做了细化研究,如魏了翁将“闵宗周”具体为“闵伤幽王”[16](P407),丰坊则说:“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洛,尹伯封过西都而伤之,赋《黍离》。”假托申培说,将行役周大夫确指实为“尹伯封”,行役事确指为“犒秦师”,“幽王伐申,申侯逆战于戏,射王,杀之。立平王于申,迁洛,命秦伯帅师逐犬戎于镐京。寻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师,过故宗庙宫室,咸生黍稷,闵王室之颠覆,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诗”[17](P647)。
二、伤时追怨说
首倡此说的是朱熹,是在“闵宗周”说的基础上滋生出来的。他以为此诗“既叹时人莫识己意,又伤所以致此者果何人哉!追怨之深也”[18](P42),即伤时与追怨双重主旨说。顺“叹时人莫识己意”思路,严粲《诗缉》做进一步发挥,确指“所伤”为时人浑然已忘亡国之痛的状态:“周东迁而遂微,置丰镐于度外,盖秋风禾黍之感不接于目,日远日忘也。”[19](P95)朱善《诗解颐》又进而从诗中纟由绎出了“怨时”的意义:“行役之大夫苟无所见则已,既已见之,而且忧之,且追怨之,岂容付之无可奈何而已邪?谓宜请于平王,泣血尝胆,号令诸侯,整师缉旅,克复旧业。”[20](P211)而依“追怨”说,谢枋得《诗传注疏》把“怨”“恨”的矛头对准了平王:“吾观《书》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以有为矣,所以训戒晋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国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兴废,悉置度外,文、武、成、康在天之灵必不乐矣!王畿乃天子自治之国,挈畿封八百里要地,悉付之他人”[21](P237),“秦人能以天王之仇为天下之同仇,平王不能以厥考之怨为一人之私怨,人之度相越如是哉!”而刘瑾直指褒姒母子:“然则《黍离》之感慨,有不待于大夫行役之时,而已兆于褒姒母子僭乱之日。大夫追怨之词有所归矣。”[22](P384)朱善又将怨恨指向平王时群臣:“为之臣者,又寂无一人以为言,则其偷安忍耻,颓堕委靡,岂特王之罪,亦群臣之罪。”[20](P211)曹学佺说:“诗人之追怨不但平王,而且及于幽王也,但不敢直指君父之恶耳。曰‘此何人哉’,又至再至三而曰‘此何人哉’,其意深矣。”[23](P16)沈守正《诗经说通》则说:“旧说:人兼幽、平说。胡休复云:‘东迁之祸,不在犬戎,而在艳妻煽处之日乎!’意更远矣。”[24](P42)显然,他们的关注点已不在“闵宗周”,而在致使宗周颠覆的根源。从经学意义上讲,这便大大前进了一步。
三、请秦归旧都于周说
宋王质《诗总闻》曰:“当是东周怀忠抱义之士来陈秦庭,以奉今主归旧都为意,或以尊王室制诸侯为辞。往往有怪其久留不去者也,徒隐忧难明告。”[25](P491)潘克溥《诗经说铃》亦引此说以广见闻。因此说有过多的猜测性,故从之者少。
四、伤周室不竞说
此说始于季本,其《诗说解颐》说:“旧说因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倾覆,彷徨不忍去而作。今以事理论之,似不尽然。当时周虽东迁洛邑,而岐周旧地尽封秦。假使故宫为其所毁,则都城之内宜为室庐,乃以黍稷为言,则当在野外之地,而岂可语于城内哉?且五谷者,民之所资以养者也,而称其黍稷之盛,则其民犹为勤力,似有叹羡之意,与言蔓草荆榛者不同矣。其必秦得歧周之后,务本力农,周大夫出过其地而见之,知秦地广民勤,将以富强雄天下,而伤周室之不竞乎!”[26](P91)季本以为《黍离》描述“黍稷”当为田中景,非废墟景,因此“黍稷”句为叹羡“秦民勤力”,以反衬周之不竞。何楷从是说。姚炳亦云:“当时平王以乱故徙居东都王城,及襄公讨西戎救周,乃以岐丰赐之秦,遂有宗周畿内之地。此本朝之赐,又未有数年,岂尽没其旧耶?故有谓与言蔓草荆榛者不同,其必为秦得岐丰之后,务本力农。”[27](P447)清李光地又演变出“周弱秦强说”,其《诗所》说:“周室播迁,以其地畀秦人,故曰彼黍之离离者如故,而稷且自苗而穗、自穗而实矣。古者尊黍而稷次之,于以见平王之不能复兴,而秦之渐强魄兆已见也。”[28](P29)
五、迁都说
以为《黍离》反映了平王为避戎寇,迁都洛邑的事件。宋张文伯《九经疑难》曰:“《黍离》述其迁都之迹也,戒后君不救先君之弊。《易》不云乎:‘有子考无咎。’有子,可托也。考无咎,得干也。宣、厉,其人也。宣为有子,厉全在雅。平同无子,幽平在风,戒也。处于《卫》下,何也?《郑》《卫》,亡国之音也。《郑》之上、《卫》之下,若曰《黍离》亦亡国之音也。”[29](P848)东迁而周室衰微,又有“闵东迁之失谋说”,朱谋说:“《黍离》,闵宗周也。何以闵?闵东迁之失谋也。西周政令所以能行乎诸侯者,非徒文、武、成、康之德,亦以地势险固,足食足兵,可以东制诸侯之命耳。幽王虽死骊山,犬戎无盘据丰镐之理,乃因一败遽尔东迁,有识之士于其行也,痛悼失图,故赋此诗:黍稷离离,下垂而硕,犹有忧者,中心思惟而倾其首也。”[30](P562)傅恒亦曰:“夫宗周者,是文、武所经营也,是成、康以来所世守也。宫庙陵寝皆在焉,土田上上,山川险塞,是天下之奥区也。犬戎作难,衅起一时,秦襄力战彼,亦自复其仇耳。为平王者,留晋文侯、郑武公夹辅周室,使襄公逐西戎而居之,则周可复兴,与宣王争烈矣!乃惧其侵暴而即安于东,举西京而畀之秦,异日者秦之代周实始于此。大夫行役兴怀,于彼黍彼稷者,伤周之物产而为秦之粢盛也,周之民人而供秦赋役也。呼苍天而问何人,盖叹平王君臣以国与人,不知谁实倡为此谋也,不然赫赫宗周,褒姒灭之,举世皆知而又何问人哉?”[31](P74)
六、卫寿闵兄说
刘向《新序·节士》曰:“卫宣公之子,伋也,寿也,朔也。伋,前母子也,寿与朔,后母子也。寿之母与朔谋欲杀太子伋而立寿也,使人与伋乘舟,于河中将沉而杀之。寿知不能止也,因与之同舟,舟人不得杀伋。方乘舟时,伋傅母恐其死也,闵而作诗,《二子乘舟》之诗是也。……于是寿闵其兄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32](P874)刘向诗学与鲁诗同源,故明清学者皆以此为鲁诗说。清儒治今文者多从其说。牟庭《诗切》言:“今以诗意求之,定从鲁诗说为是,但其诗非寿子所自作,盖诗人咏其事而吊之,且以刺宣公也。”[33](P700)冯登府《三家诗遗说》说:“本欲杀伋而杀寿,故以黍、稷同时以喻兄弟起兴,不敢斥言君父,而呼诉于彼苍,孝子之思深矣。”[34](P756)
七、伯封思兄说
《太平御览》九百九十三羽族部引陈思王植《令禽恶鸟论》说:“尹吉甫信后妻之谗,而杀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离》之诗。”[35](P316)曹植学《韩诗》,因此明清学者多以此为《韩诗》之说。范家相《三家诗拾遗》说:“如鲁、韩,则此诗皆弟忧其兄之词,事适相类,而所传各异。但尹吉甫为王朝之臣,韩说犹为可通。”[36](P548)牟应震、王先谦,日本诸葛晃、朝鲜李炳宪等亦证此说为是。
八、念乱说
时乱未艾,故忧念之,深思之。此主旨较合情理,但从者较少。清毛奇龄《国风省篇》说:“《黍离》,念乱也。‘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园有桃,其实之肴’也。‘行迈靡靡,中心摇摇’,‘心之忧矣,歌且谣’也。‘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谁知之’也。‘悠悠苍天,此何人哉’,‘亦勿思’也。”[37](P643)恽敬《大云山房文稿》卷二《黍离说》亦云:“《黍离》作于已乱者也,故其辞哀。虽然,乱未艾也,故其思深。……然而《黍离》之诗人不暇责也,一则曰:‘此何人?’再、三则曰:‘此何人?’此何人盖即指晋文侯、卫武公、郑武公言之。何也?幽王事起仓卒,君灭国残,然四方及畿内诸侯无恙也,三君者皆同心讨贼,灭之绝之,修城池,建社稷宗庙而守之。周可以不东而卒东者,由郑桓公死难,武公内怛,不敢与犬戎抗;晋文侯、卫武公去西都千里,各顾其国,不为王室图久远也。夫皇父、荣夷,斫之于方茂者也,然皆纤才侈欲,容悦之徒而已。若三君者,天下仰望,为圣贤豪杰,王室所倚重,而乃至于此,不重可责邪?此《黍离》诗人之意也。”[29](P458)
九、忧小人酿乱说
清方苞《朱子诗义补正》中说:“此诗似预忧小人酿乱而叹众人之愦愦,故呼天而问之:谓如此之人,何故使当要津以厚其毒也。”[38](P410)与其说相类者是日本皆川愿《诗经绎解》,其云:“此篇言从道者,悠久之业也。其间必不能无时生厌心焉,而其昏惑之际,必又有离贰之言出焉矣,是以预戒令究察以无陷夫邪途也。”[39](P137-138)
十、王室之不振说
胡文英《诗经逢原》曰:“东迁之后,求赙、求车四出不已。诗人因久役而忧王室之不振也,赋《黍离》。”[40](P421)清潘克溥《诗经说铃》中引《印古诗说》曰:“《黍离》,隐然见天下多事,行役不息,以见王政之不纲也,未见宗庙夷毁之意。”[41](P426)姜炳璋《诗序补义》说:“不言悲而言忧,正以朝廷绝少中兴气象,胸中有一叚光复旧物之志而不得舒,非徒下新亭之泪也。”[42](P87)此说显然是从诗中体会而出的意思,并无史实根据。
二 《黍离》主旨旧说辨析
梳理历代《黍离》主旨旧说,可以分为三种情况:一种是秦汉经师相传的旧说,如被认定为毛、鲁、韩三家的观点;二是在《毛诗》“闵宗周”说基础上衍生出来的诸说;三是自创的诸说。
自创之说主要有“请秦归旧都于周”“伤周室不竞”“述迁都之迹”“忧小人酿乱”等诸说。这几种说法一个共同点是:认为此诗与两周之际的某一政治事件相关,但纯是从诗中分析得出的一种可能性,并没有明确的史实作支撑。特别是王质的“请秦归旧都于周”与季本的“伤周室不竞”两说,颇类于小说虚构。故清顾镇《虞东学诗》驳季本说曰:“《序》曰‘闵宗周’,而下言‘大夫行役至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季本谓:‘以事理推之,未必尽然,所见黍离当在野外。’钱天锡亦谓:‘歧周故地,尽以封秦,不应鞠为黍离。’此惑于郑氏《秦谱》横有西都八百里之说,以为秦不应毁废本朝宗庙宫室也。案《史记》:平王赐襄公岐以西之地曰:戎侵夺我岐、丰,秦能逐戎即有其地。是秦封在岐以西,丰镐在岐东,为戎所据,非秦有也。终襄公世不能克戎,至文公十六年,逐戎始得至岐。岐以东仍献之周,是丰镐故都仍隶周境,秦不得过而问焉。特为戎残破,平王视同敝帚,不复加葺,铜驼荆棘,固所不免。史言殷墟城坏生麦,则周墟黍稷理亦有之。”[43](P440)胡承珙引顾说亦云:“虞东之说足破季本谓诗人见黍稷之盛,知秦地广民勤,将以富强雄天下,而伤周室不竞之谬论。”[44](P164)
从《毛诗》“闵宗周”说基础上衍生的观点,如追怨、念乱、王政不纲等说,这些观点与“闵宗周”并不相矛盾,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毛诗》旧说的补充。现在需要关注的是汉代经师的旧说,因其渊源有自,须认真辨析。
首先看被认作《鲁诗》的“卫寿闵兄”说。主此说者中,属康有为最用力。康有为首先把“卫寿作诗”与《韩诗》的伯封作诗,通过考据并为一处,认为“伯封”是“卫寿”的字,鲁韩二说同源。而后否定《韩诗》之说曰:“若吉甫西周贤卿,非同卫宣昏悖,安得伯奇未僭以前,遽以伯字其弟哉?”接着通过驳《毛诗》说,提出三点:一,东周初,镐京故地为戎所占领,大夫不可能出使至此;二,大夫长久滞留戎地,究竟为何呢?史无实据;三,《黍离》表达“隐痛难言”的特征,不合当时“变雅成规”的普遍诗风。[45](P61-63)可以看出康有为所用的是排除法,排除了毛、韩二家,旧说也就只剩《鲁诗》一家了。
康有为对《鲁诗》说的肯定,显然并没有新的证据,而对于《毛诗》的否定,其词亦甚为无力。《史记·秦本纪》对西周覆亡后的史实有具体交代:公元前771年,申侯联合犬戎攻入镐京,洗劫京都,秦襄公等带兵护送周平王迁都洛邑。襄王因此封为诸侯,平王许诺:“戎无道,侵伐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46](P179)公元前766年,秦襄公讨伐西戎,到达岐山,襄公卒。公元前750年,“文公以兵伐戎,戎败走。于是文公遂收周移民有之,地至岐,岐以东献之周”[46](P179)。西周覆亡仅仅二十一年后,部分失地收复,如此大的政治事件周必会郑重对待,派大臣前去举行收复仪式,时间安排也应较为宽裕。至于《黍离》“隐痛难言”与“变雅”诗风相悖之说,笔者以为有机械之嫌。诗风深沉含蓄还是激切直露,固然与时代风气有关,也与作者风格密切关联。况东周初迁都重建,百废待兴,礼乐教化中成长起来的周贵族有忧思,更有励精图治、维护新王朝秩序之公心,因此不直斥在上者也在情理之中。
再看《韩诗》的“伯封思兄”说。胡承珙言:“尹吉甫在宣王时,尚是西周,不应其诗列于东都也。”[44](P164)清龙起涛、民国马其昶、林义光等亦有同说。王先谦曾辨之曰:“盖有传其亡在王城者,及平王东迁,伯封过之,求兄不得,揣其已殁,忧而作诗,情事分明,此不足以难韩说也。”[47](P315)似乎能圆“为何列入《王风》”之疑,但吉甫杀子在西周宣王时,宣王最后一年为公元前783年,距收复镐京失地公元前750年有33年,则伯封如受平王重任复归宗周,在宗周覆亡、东周尚待振兴、秦国壮大等一系列大的政治风云变幻中,心中最深切的悲痛仅为死去至少三十多年前的兄长,于情理相差甚远,其说不通。
下面再来分析《毛诗》之“闵宗周”说。第一,《史记·秦本纪》所载“秦收复镐京失地,还归周”为其说提供了史实印证的可能。诸注家明丰坊、张次仲、胡绍曾,清钱澄之、顾镇、胡承珙等皆以之证。史实较为有力,虽未直接载“作《黍离》事”,然从历史情境上是贴切可通的,周遣使臣归故都,亡国之痛、远离乡土之苦必激荡内心,痛而作《黍离》以抒怀。
第二,纵览历史,王朝更替之际,亡国主题往往是文学创作的主调。历代注家对此文学现象有所揭示,并从不同角度予以分析总结,如李资乾《诗经传注》从君臣大义上解读:“卫受齐德,且欲厚报之。臣子受君恩,当何如报也?故受之以《黍离》。《黍离》之诗,忧周之丘墟,呼苍天而感叹也。”[48](P321)王鸿绪《钦定诗经传说汇纂》引辅广言与此意类:“国家颠覆,在臣子故不能无所忧,此诗人忧之,得其正者也。”[49](P220)新王朝建立之初,一般会出现总结覆亡教训的社会思考潮流,李诒经以此为《黍离》创作动因,《诗经蠹简》说:“此行役大夫慨叹故宫,以警后王之诗也。”[50](P606)当然江山易代、满目疮痍最是痛彻心扉,不吐不快,正如方玉润《诗经原始》说:“文、武、成、康之旧,一旦灰烬,荡然无存。有心斯世者,所为目击心伤,不能无慨于其际焉。”[51](P191)
第三,《黍离》与闵商诗《麦秀之歌》创作风格相似。《史记·宋微子世家》:“箕子朝周,过故殷墟而伤之,作麦秀之诗:‘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46](P1621)宋李樗曰:“箕子闵商之歌曰:‘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既曰麦秀,又曰禾黍,则亦与此同意。”[52](P181)认为《黍离》与之主题相似,皆为亡国主题,后魏了翁、江环、何楷、徐光启、张次仲、王鸿绪、姜文灿、陈大章、胡文英、邓翔、龙起涛、陈继揆、朝鲜朴文镐等皆从是说。但这些论家简略引证居多,详细阐释较少。从二诗文本来看,采用的“禾黍”“黍稷”意象属于同类,行文结构相同,先作物象描写,继之抒怀,且忧伤风格相似,这些应是诸家立论的关键依据。如顾镇所说:“史言殷墟城坏生麦,则周墟黍稷理亦有之。”[43](P440)许伯政阐述得比较透彻:“箕子《麦秀歌》,因见麦秀而作。则黍方布种,而承言禾黍油油,与此之因黍及稷,因苗及穗、实,皆感此以思彼,则知物态日新月异,故宫愈久愈湮,所谓百端交集,一往情深也。”[53](P592)
三 从黍稷意象进一步补证“闵宗周”说
《黍离》中的“黍稷”意象是传达“宗周覆亡”主题的关联点。历代对《黍离》中“黍稷”形象的理解有一个变化过程。孔颖达:“过历故时宗庙宫室,其地民皆垦耕,尽为禾黍。”[15](P5)范处义:“闵周室者,黍、稷莫分;念父母者,莪、蒿莫辨。”[54](P95)刘元城:“初见稷之苗矣,又见稷之穗矣,又见稷之实矣,而所感之心终始如一,不少变而愈深,此则诗人之意也。”[22](P384)这些看法中,“黍稷”形象基本是实物特征。宋朱熹在解读《黍离》时,开始以文学视角切入对“黍稷”形象的分析和对全诗的理解:“稷穗下垂,如心之醉,故以起兴”,“稷之实犹心之噎,故以起兴”,“赋其所见黍之离离与稷之苗,以兴‘行之靡靡,心之摇摇’”。认为黍稷具有比兴义,比兴忧情。到了明顾起元《诗经金丹》,则将黍稷表达的比兴义与“宗周覆亡”主题联结在一起:“总是赋所见以兴闵周之意,因致所叹以致倾周之人。”[55](P367)郝敬《毛诗原解》亦云:“平王东迁,丰镐丘墟,大夫过而伤之,以黍稷比即其所见也。”[56](P297)顾起元等人似更能准确地说明《黍离》的创作宗旨。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从《诗经》中“黍稷”意象入手,做深入分析。
《诗经》中涉及“黍稷”意象的共16篇,其中有“黍稷”联用的,也有单用的,特点有三。一,这些诗在主旨表达上有相对的稳定性,主要是与周重大政事相关的内容:农事、祭祀、战争、政事。二,意象写作手法上,可分为写实和象征两类。一类与农事、祭祀相关者9篇(3)其中一篇《华黍》为笙诗,无辞,但《毛序》述其诗旨为:“时和岁丰宜黍稷也。”且曰:“《华黍》废则蓄积缺。”则其诗应与农事相关。,为写实,如《七月》“黍稷重穋”,《大田》“与其黍稷”,《信南山》“黍稷彧彧”,《甫田》“黍稷薿薿”,《良耜》“黍稷茂止”,《楚茨》“我黍与与”“我艺黍稷”,《丰年》“丰年多黍多稌”等。另一类,与战争、政事题材相关者7篇,“黍稷”皆具有象征意义,展现着重大的政治背景。如《下泉》言:“芃芃黍苗,阴雨膏之。”《毛诗序》说:“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忧而思明王贤伯也。”[15](P12)《黍苗》亦有“芃芃黍苗”之言,三家诗说:“召伯述职,劳来诸侯也。”[15](P806)《出车》言“昔我往矣,黍稷方华”,《鸨羽》言“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此二篇皆与战事相关。《硕鼠》言“无食我黍”,《诗序》言“刺重敛也”[15](P16)。《黄鸟》言“无食我黍”,又言“此邦之人,不可与处。言旋言归,复我诸父”。《毛诗序》:“刺宣王也。”《郑笺》:“刺其以阴礼教亲而不至,联兄弟之不固。”[15](P58)三,运用象征手法的诗中,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出现了“黍稷”意象的重复使用,说明“黍稷”政事象征义在《诗经》中具有的固定化倾向。
关于黍稷的象征意义,古代经学家早有所觉察,如宋蔡卞《毛诗名物解》:“凡言黍、稷者,皆有冀祖考、怀祭祀、念父母之意。”[57](P545)清黄中松亦云: “《说文》《图经》《风俗通义》《尔雅翼》等书皆以稷为五谷之长,毋乃与圣言异乎?将稷与黍皆有益于民生而不可缺者,故古人多以黍稷并言,而皆可为长欤?”[58](P282)黍稷之所以有此特殊的象征意义,主要与周人生活有关。黍、稷是周民族最重要的作物,周之先祖曰后稷,即反映了其以稷发家的历史。据不完全统计,20世纪90年代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周民族祖先稷活动的区域,稷和黍的遗址最多。[59]古以社稷代指国家权力,“社”代表土地,“稷”代表谷物,这种概念正是从周人开始的。正因为黍稷在周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因此其进入歌咏,便有了特殊的意义。
总览“黍稷”意象在《诗经》中的艺术特色,再反观《黍离》文本,诗总三章,将各章前两句摘录在一起,可以看作一首完整的“黍稷”农事歌:彼黍离离,彼稷之苗;彼黍离离,彼稷之穗;彼黍离离,彼稷之实。描写了黍稷的成长、成熟过程。然通读全诗,显然不是农事诗、祭祀诗,故其意不在写实,而为虚写。元刘玉汝:“故都兴亡盛衰之感皆在‘黍离’二语,而有无限悲怆之情矣。”[60](P617)明徐光启言:“不见一‘宗周’字,亦不及一‘宗庙宫室’事,今俱就感黍稷而兴歌。”[61](P182)清牟应震《诗问》:“黍苗小,喻周黎民也”,“稷苗高大,喻秦人茂盛也”。[62](P70)这些意见都看出了“黍稷”意象的国政象征意义。更有甚者,将其中“黍稷”与周族历史作深刻关联,清罗典《凝园读诗管见》:“稷熟最早,为五谷之长而属土,故祠谷神者,以稷配社。五谷不可遍祭,祭其长以该之也。上古以厉山氏之子为稷主,至成汤始易以后稷,皆有功于农事者云。由此言之,则《黍离》之闵宗周,殆思其初开国之后稷也。东迁以后,宗周竟为秦有矣。然有邰之肇基,由来甚远,后之于孙,可无敬念与?《生民》之五章曰: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六章曰:诞降嘉种,维秬维秠,维穈维芑。夫秬、秠、穈、芑,皆黍也,即与稷为一类也。在后稷之先,岂必无此嘉种,特以其穑有相之道,则以为后稷实降之,此所由受封有邰,延及后裔,以大唘宗周也。故作者之闵宗周,因行役而见黍,因黍而念其类之为稷,即因稷而念始生是稷之人之为后稷。其言反复三叹,足使弃宗周者闻之,蹙然无以仰对,思文配天之灵也。”[63](P119)将“黍稷 ”与祀谷神、后稷相联,以致以之象征周之社稷,这个思路是完全可通的。这种联想也赋予了“黍稷”形象的神圣性和庄严性。
以上述结论重新审视《黍离》诸新说,偏颇源于两种情形。一、没有关注到“黍稷”为周诗惯用意象,跳出其地域特征,“贵族破产说”“旧贵族感伤阶级没落说”“流浪者忧思说”“怨战之作”等皆如是。郭晋稀先生以为《黍离》反映了史载卫君黔牟流亡周事。为卫人流寓王城,久行不归而作,是《雄雉》的应答篇。[9](P73)其说较详。然如为卫人表达思国之情,而反复深沉吟诵周之“黍稷”意象,同样有悖情理。(4)又,此说提出的主要证据之一是:“谓我何求”之“求”,与《雄雉》“不忮不求”之“求”,皆“贪求”义。“居人责行者之忮求名利,行人则答以并非封侯念重。”(郭晋稀《诗经蠡测》,巴蜀书社2006年版,73页)然联系“不忮不求”与“谓我何求”两句出处的上下文和语法结构,“求”字义显然不同。“百尔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此处“求”字实省略宾语。该句式与《汉广》“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相同,“求”的对象句子自身有答案;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句式和《臣工》“维莫之春,亦又何求”相同,“何求”即“求何”,“求”的具体内容是未知的。“不知我者,谓我何求”,其句与《园有桃》“心之忧矣,其谁知之”表达的情感内容一致,表达了主人公内心的一种异常复杂的痛苦,无人能深切体会。既知求的内容,何来求何?因此两诗之间无法形成应答连接。二、没有关注到“黍稷”的政事象征特征,诸如“寿思兄”、“尹吉甫思子”、“个体流亡的悲苦”、爱情等说,皆局限于家庭伦理情感、个体情感等,与《诗经》中该意象内涵传达的取向相距甚远。
总之,《诗经》“黍稷”传达的文学意义具有相对稳定性和独特性,神圣性和庄严性,江山社稷是其基本象征义之一,表现周重大政治变动是其基本主题,而《王风·黍离》是《诗经》16首“黍稷”形象相关诗中刻画最详细、精心的,当是《诗经》“黍稷”形象塑造的典型升华。如此郑重的创作态度应与非常重大的政治变动相关,而于周最大的政事莫过于“宗周覆亡”。
然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宗周覆亡”有一个演变的历史过程,非仅指犬戎攻入镐京、平王被迫东迁事。从西周末期,幽王朝政荒唐,国政摇摇欲坠,继而大军日渐压境,大量贵族恐慌、忧虑王城不保,先行匆忙东迁,已为覆亡之肇端。《黍离》诗中未明言创作时间,因此可理解为沉痛缅怀“宗周覆亡”事,也可为深沉预忧。(5)对此清王心敬有敏锐的感受:“《黍离》一诗,周大夫目见西周之沦废而作”,“二南明西周之所以兴,《黍离》志东周之所由衰。其兴也,以化由中壶;其衰也,以衅作艳妻:而皆起宫帏之间者”。(王心敬《丰川诗说》,《四库存全书存目丛书》,齐鲁书社1997年版,126页) 他认为《黍离》为预忧西周覆亡,这也是将该诗编为王风首篇的意义所在,如是当作于西周末。而清崔述则认为该诗作于东迁时:“盖缘说毛诗者,谓王风皆周东迁以后之诗,此篇居王风之首,当为初迁时所作。有此成见在心,故见章首言黍稷,遂以为故宫之禾黍耳。其实王风不必皆在迁后,读者当玩其词以求其意,不得因此遂定以为行役于故国也。曰:然则季札何以谓为周之东也?曰:此不过大概言之耳,非为其必无一二篇在东迁之前也。正如称大雅为文王之德,而大雅岂尽文王之德?称郑风为其细已甚,而有《缁衣》《羔裘》;称唐风为思深忧远,而有《绸缪》《葛生》:其得以是为疑也哉?”(崔述《读风偶识》,《续修四库全书》5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266页) 此说也可通。今人陆侃如、冯沅君,程俊英的“迁都说”与崔说属于一类。又结合诗句“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表达的是一种误解所带来的强烈痛苦,这种痛苦体现的应是情境和作者内心形成的反差。窃以为《黍离》诗的创作可能有三种情形。一是西周覆亡在即,大量贵族为保障家族生命与财富,逃离镐京,仓促东迁。(6)详见杨宽《西周史》第七编第二章中“秦和西戎的战斗以及周避难东迁”。在苟且偷生的时代风气中,作者一腔爱国热情,举步维艰,行路迟缓,途中写作是诗。第二种情形,为东迁时所作,申侯与缯、犬戎攻入镐京,“尽取周赂”,镐京遭到极大的破坏,又有边邻犬戎等的威胁,平王在申侯、晋文公、郑武公的帮助下被迫迁都。途中,离故国渐行渐远,朝廷上下大多为逃离兵灾而庆幸,而作者独忧思故都,不堪承受亡国之痛。第三种情形,当依《史记·秦本纪》所载,作于秦励精图治,收复镐京,将岐以东献周,周派官员赴岐收复失地之时。当他看到故土颓败,想到周权威衰弱,悲从中来,故作此诗以寄忧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