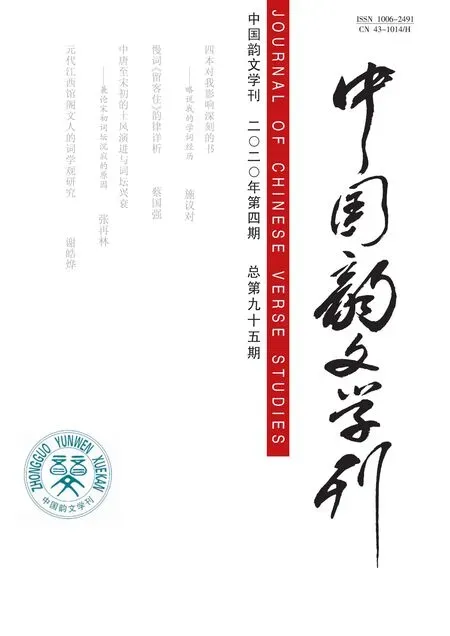南坡之变与元代中期宫廷文人的心灵书写
(香港浸会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系, 香港 00852)
元世祖忽必烈自1271立大元后,文人在朝中地位逐渐提升,仁宗实行儒治,在大都为官的有袁桷、虞集、马祖常等等,由最初出任吏员,到作为朝官参与日常政务,宫廷文人在元代中期逐渐成为蒙元派系间的笼络和针对对象。说是笼络,是因为蒙元上位者需要宫廷文人的写作技能撰写公文;说是针对,是因为蒙古和色目上位者害怕宫廷文人僭越大权。宫廷文人自然不会牵涉入各种权斗里,具体来说,是源自甘麻剌与答剌麻八剌两系的帝位纷争。其中一桩暗杀夺位事件发生于至治三年(1323)八月,英宗被杀,史称“南坡之变”,事涉其继位者晋王也孙铁木耳(泰定帝)以及上述三位宫廷文人。那位策划暗杀夺位的主事者将是宫廷文人侍奉的新主,面对新政时,他们是如何以诗歌言说内乱经验?使用怎样的文学语言表现共同的创伤情绪?其中隐晦的心灵书写如何随着时间推移和时局变迁而沉淀和转化?可以想象围绕这桩内乱的记载非常隐秘,那么通过文学创作治疗创伤是否可能?本文聚焦于这段内乱历史及其周边文本,指出元代中期宫廷文人是以一组联句及三组次韵诗的方式沉淀思绪达至疗伤,由最初激动隐晦的直白至平淡内敛的情词景语,到直斥叛党之非的诗史之笔,最后以大雅正声的宫廷诗回应时政。这时段的几组联作是诗人将创伤经验自我内化的一个过程,并转化为重建道德标准的力量。
一 1323年的南坡之变与元代中期的帝位纷争
蒙元中期以皇太后答己及其党羽铁木迭儿殊为专擅,蒙古派系的争斗造成当时的混乱政局。(1)铁木迭儿于1311和1314年两次被任命为右丞。Hsiao Chi-ching, “Mid-Yuan Politic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 vol.6, Alien Regimes and Border States 907-1368, edited by Herbert Franke and Denis Twitchett.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525~534.马祖常曾弹劾铁木迭儿任意升黜官员,[1](P154)仁宗延祐六年(1319),四十多位御史上书弹劾铁木迭儿,后者因答己的包庇而无罪,御史却被流放或被逼告老归田。英宗于1320年任命拜住为左丞,抗衡答己派系,拜住担任太常礼仪院使时,便与虞集和吴澄为友。[2](P147),[3](P493)英宗和拜住联手保护儒臣免受答己派系的欺凌。[4](P530)宫廷文人及朝臣的经历都使他们后来的创伤经验带来更大的痛苦。
铁木迭儿和答己先后于至治二年(1322)十月去世,拜住于同年十二月被任命为右丞后,[5](P624)立即在集贤院和翰林院起用汉人行儒法,包括王约、吴澄、吴元珪、张珪、王结、宋本。[2](P149), [5](P627)英宗和拜住在儒臣辅助下实行新政,减少皇太后和皇后随从,以免助长派系斗争,继而鼓励御史揭露渎职的官员。[2](P149-150), [4](P531)朝廷命令毁去铁木迭儿石碑,其旧有部属被放逐,以示绝不包庇叛变者。[5](P626-631)当时铁木迭儿的支持者铁失安然无恙,因为他是英宗皇后速哥八剌的兄长。铁失为求自保,与也先帖木儿策划谋害英宗。英宗新政令蒙古贵族的五位宗王年收入锐减,尊贵地位被动摇,他们因之而参与暗杀计划。[2](P152), [6](P291)
至治三年(1323)八月初四日,英宗和拜住自上都回大都,在南坡驿稍做停留。当晚,铁失与阿速卫兵突袭,英宗和拜住被杀,史称南坡之变。(2)关于参与计划的官员名单,见宋濂著《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632~633页。铁失等立即奔赴大都,控制朝臣,夺皇印,拥立身在蒙古的晋王也孙铁木耳(后来的泰定帝)为帝(见虞集《书王贞言事》)。[7](卷39, P12-13)铁失和叛变者在大都命集贤院和翰林院官员随员上都,文官曹元用认为晋王突被拥立异于常态,宁死不从。[5](P4027)晋王即位后,朝臣担心新朝不再以儒治国,许有壬和赵成庆上书弹劾渎职的铁失等人,[2](P155)泰定帝最终同意处死铁失,流放五位宗王。据《元史》记载及萧启庆研究,泰定帝极有可能参与暗杀英宗计划,其王府内史倒剌沙在南坡之变事发前两天告诉他将有叛变,可知泰定帝是在知情下默许刺杀行动。[4](P536),[5](P3305)元代中期宫廷文人见证着这段内乱及其后一连串的政治动荡,是故从他们的文学创作可以一窥其心路历程,以及怎样以一组联句和三组次韵诗的方式沉淀思绪达至疗伤。
二 枪竿岭道中诗——创伤的回响与延宕
这组在枪竿岭撰写的联句诗,是袁桷、虞集、马祖常往上都道中迎接英宗回朝时所作,作品反映了诗人在内乱时的心理恐惧。蒙元皇帝每年夏天由大都往上都避暑,有两条路线可供北上,[8](P149-150)其中一条路线途经不少著名地区,由大都出发,经龙虎台、榆林驿、枪竿岭、李老谷、龙门、赤城、李陵台、桓州,最后至上都,可知枪竿岭位处居庸关北。(3)此路线归纳自不同诗人的记载,基本大同小异。袁桷、迺贤、周伯琦、黄溍,参 《元诗选》初集,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653~656页,第1455~1458页,第1959~1967页; 胡助,《纯白斋类稿》,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26页; 萨都剌,《雁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7~158页;陈衍,《元诗纪事》, 收于钱仲联编《陈衍诗论合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5~1558页。传统上,蒙元皇帝自上都起程回大都,在京的朝官需要在居庸关之北准备内宴恭迎皇帝回京,[8](P153)这是袁、虞、马等等宫廷文人前往枪竿岭之原因。当他们在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于此稍事停留之际,收到事发于十一日前在南坡发生叛变的消息,性格耿直的马祖常便先行发句创作,题为《至治癸亥八月望,同袁伯长、虞伯生过枪竿岭马上联句》。(4)柳贯有和诗一首,《袁伯长侍讲伯生伯庸二待制同赴北都却还夜宿联句归以示予次韵效体发三贤一笑》,见《元诗选》初集,第1127页。
联句以五古三十二句形式出之。(5)联句诗后的名目次序,参《虞集全集》,第39页;《元诗选》,第662页;《石田先生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马石田文集》,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版,593页。此诗独不见于虞集三部文集 (《道园学古录》《道园类稿》《道园遗稿》)。按文意,诗分三部分。第一部分(1至14句)描述枪竿岭兼具陡峭及广漠的环境,与传统以来的记录一致,[9](P166)第二部分(15至22句)写伐木人在此险要之地工作之困境,再次渲染边陲风物,惊叹异域的新奇,这一连串的长篇叙事还没触及内乱。最后部分的第23及24句突转,用上与前此部分不相合的言辞, 描写异域中的想象:
23金桥群仙迎 (虞)
24玉幢百神凿 (马)
金桥指来自冥府的世界,据研究,善者跨越金桥(忠义之士、义士、贞节妇人)或银桥(僧侣或俗世弟子),而桥下为万丈深渊,恶者将行走奈河桥(作惩罚用)。[10](P97)虞集此句似暗喻英宗及拜住,写其仁政、忠诚,故得群仙迎接,而承句的“玉幢”是佛教仪式常见的宝物,二句相合,指英宗及拜住被群仙百神簇拥进入祭祀仪式。这里的想象异常冷静及光明。“迎”本来是臣子在居庸关之北恭迎皇帝回京之谓,现在换成众仙恭迎,生前殁后的巨变, 令人惋惜;后句用“凿”,即知玉幢为石幢,凿上佛像、咒语等护法内容,保护已殁的明君贤臣。接着,诗人以传统历史人物及天上星宿书写这一段共同的创伤经验:
25禽鸣蜀帝魂 (马)
26铁铸石郎错 (袁)
27钩钤挂阑干 (袁)(6)“钩钤”指天子之御,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308页。
28欃枪敛锋锷 (虞)(7)“欃枪”指彗星,乃凶星,不吉,见《汉书》,第1280页。
29属车建前旄 (虞)
30驰道拘严柝 (马)(8)“驰道”即帝王车马行走之道。
31载笔三人行 (马)
32弭节半途却 (马)
先以传统人物蜀帝故事开展异域想象,蜀帝传位鳖灵后离开故土,杜鹃因而啼叫,此后蜀人每次听到杜鹃啼叫便想起先帝;另一文本为蜀帝死后化为杜鹃泣血,此典后来与帝皇之死拉上关系。[11](P61)马句道出英宗之崩殁牵动众人情思,伤痛之余加添泣血之告。
袁桷的第26句有多重含义,结合“铁铸”及“石郎”典。“铁铸”指晚唐天雄节度使罗绍威。906年,他向朱全忠借兵平内乱。为报答朱的帮忙,罗奉上一己镇守之地的珍宝以及生活用品予朱,宴请礼待他停留半年之久,这样必定削弱己方的军事力量以及让对方的资源倍增。之后果然让朱得益,收服北方。最后臣服于朱全忠的罗绍威后悔地说:“合六州四十三县铁,不能为此错也。”“错”语相关,既是“错刀”也指“错误”。朱全忠后来自称梁王,唐哀帝(昭宣)让位于他,建立大梁。[12](P1201-1202)“石郎”指后唐(923—936)将领石敬瑭。935年,石于洛阳收集物资运往其根据地晋阳,向后唐废帝解释此乃军事物资,实为推翻后唐做准备。废帝为打击石,命其将军事力量由河东迁往郸州(今之山东),石拒绝,废帝派兵镇压,石求助于契丹后,大获全胜推翻后唐,于937年称帝建立后晋。石敬瑭称帝后受制于契丹,导致燕云十六州的割让,成为辽的傀儡。
二典说明为了巩固政权而向外借兵之错,《资治通鉴》评罗及石借兵举措都是失误的,以为对方助己,最终变成敌对,并要臣服于他们。[12](P197-221),[13](P13, 64-65)据此,笔者认为第26句的主旨为铁失,作为内乱暗杀事件的始作俑者,得力于也先帖木儿及阿速卫兵,内应于晋王也孙铁木儿,杀害英宗及拜住于南坡。当时铁失赶回大都并控制各派系朝臣,然而袁桷此际预料铁失的计谋终会铸成大“错”,并要臣服于英宗的继任人,如同《资治通鉴》的评定。可见危难中的宫廷文人,也能一针见血道出问题,这是难能可贵的。
袁桷续写第27句,以“钩钤”(喻天子之御)的参差横斜,写所有物事倾侧骤停,英宗已罹难,故诗人失去向前迈进的理由。虞集承句接续星宿意象,以不吉的凶星“欃枪”构句,叛变者造成的灾难已成,故“锋锷”(光芒) 可暂且敛藏。诗对英宗及拜住罹难的震惊以及对当下事情发展的初步判断到此结束,诗人回到当下的枪竿岭,第29句“前旄”指一般行军时,给后面的车马提示前面有危险,虞集据此转写前面南坡驿的政变,而马祖常的承句(第30句)写出枪竿岭道中的紧张气氛,谓当时已被英宗的敌对派系控制整条南北路线了。最后,马祖常以他们在朝中的位置作结:作为宫廷文人的三人既没兵器也没武力,只是一介“载笔”文臣,虽在半途,也得即时回京。
由耿直的马祖常强调“载笔”,此意可圈可点,反映诗人内心的激动与无可奈何。“载笔”回车强调他们没有的能力,即欠缺政治力量和军事武力阻止暗杀的发生,“载笔”同时又隐含载舟和覆舟的效果。这首作品的特殊性在于它是诗人在道中得知南坡之变后的即时回响,此即兴性质的联句在诗人的精心操作下显得激动且隐晦。如上所述,马祖常曾弹劾铁木迭儿,袁桷上书英宗请求任命拜住为右丞,虞集与拜住因为对儒学的推动有共同趋向而有较好的关系,这些曾在英宗朝通过一己之笔表达的正直立场,说明他们与英宗和拜住站在同一阵线,而这些较深的联系,都使三人在枪竿岭道中收到暗杀的讯息时显得仓皇,进而明白已身处险境——英宗拜住被谋害以及敌对派系掌权。诗人熟悉的一切已顿时不存,联句诗32句里只有一句谈及叛变的“错”(第26句),而且是通过两个典故的融合隐晦提出,诗里没有任何肆意批评叛逆者的用词。在知悉危难及领受创伤之间,诗人需要时间沉淀及转化, 要求他们在诗里全面处理创伤经历大概于理不合。再从全首的安排看,首22句写枪竿岭的峭拔与广漠异域,接着的3句(第23—25)以天上星宿及蜀帝典故暗喻英宗及拜住的崩殁,次1句(第26)综合诗人判断,再次4句(第27—30)写枪竿岭道中仓皇情况与紧张气氛,最后2句(第31—32)写中途回京的突转。仓皇书写只有4句,比例上显得突兀,细节极短却是重点,或许有意指出暗杀事件的突袭与恐慌。最后一段的“载笔”或可诠释为三人虽没有军事武力可资帮忙,但仍可运用此笔书写南坡始末。袁、虞、马在内乱后的联句诗,以极短的创伤篇幅对照详细的道中情景,说明他们受制于时局的逼迫而通过隐晦的言语表达激动的情绪。
三 榆林驿对月——创伤经验的沉淀与再现
南坡之变为蒙元中期政局的转折点,有关这桩内乱的诗极其委婉,虞集另有一首触及此次创伤经验,题为《榆林对月》,收录于苏天爵《元文类》卷三。(9)袁桷有和诗《次韵伯生榆林中秋》,见《清容居士集》,《四库全书》本,第1203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69页。《元文类》卷3,第12页。是诗在虞集亲校的《道园学古录》题为《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对月》。[14]( 卷1,P4A)至治壬戌即至治二年(1322),翁方纲将是诗系于此。[15](P451-452)然而,至治二年夏,虞集身处南方。虞诗应系于至治三年(1323),这里从虞集在江南的行踪说明。延祐六年(1319),虞集父亲虞汲去世,集奔丧江西临川。至治二年(1322),于池口与老师吴澄会面,后同往金陵(参虞集《跋吴文正公题朱子写陶诗与刘学古略迹卷》)。[15](P452), [16](卷35,P158)是年,集又往吴郡祭祖 (参《送赵茂元序》)。[16](卷20,P535)集还在吴时,朝廷任命他为国史院一员,拜住遣使者往蜀、江西、吴等地召他回朝,惜未能联系。[5](P4176)至治二年六月,赵孟兆页去世。撰于至治二年八月四日的《题赵子昂书过秦论真迹》提及,赵去世之后的第五十日,集与友人同在吴郡一同欣赏赵书。[3](P464)可见至治二年的夏天,虞集并不在北方,后来亲校《道园学古录》时,大概把《榆林对月》改为《至治壬戌八月十五日榆林对月》,标明年月,以免添乱。(10)增删改写在《道园学古录》并非罕见,关于南坡之变的“密书”就是一例,下述。加上袁桷《秋闱唱和》指出至治三年(1323)八月十五日,他与虞集等人同在榆林驿。准此,本文将虞诗系于至治三年八月十五日,与枪竿岭联句同样是诗人在南坡之变后的反响,分别在于,联句诗是诗人在追赶路程时的道中联句,对月诗是诗人沉淀思绪后作。虞集《榆林对月》全诗如下:
日落次榆林,东望待月出。
大星何煜煜,芒角在昴毕。
草树风不起,蛩蜩绝啁唧。
天高露如霜,客子衣尽白。
羸骖龁余栈,嫠妇泣空室。(11)《道园学古录》作“幽室”,卷1,页4A。
行吟毛骨寒,坐见河汉没。
驿人趣晨征,曈曈晓光发。(12)《道园学古录》作“告晨征”。
与联句诗一样,此诗同样反复使用星宿意象述情。诗的三、四句连用两个星宿意象:“大星”一般指杰出之士,在南坡之变的背景下,此处指拜住;“昴毕”位处冀州上方,即皇城所在,[17](P1278,1288)这里暗寓英宗。两句指英宗和拜住之英明管治就如天上星宿。二人之离世让诗人感到不安,自然界一草一物都为之惋惜而沉寂(五六句),既明且冷的夜星照在露水与衣服上(七八句)(13)虞诗第七句的用字让人联想至《诗经.蒹葭》“白露为霜”的句意。,“白”反映夜色之纯净。接下来,诗人用两个意象写因内乱而引起的心理创伤,失去挚友的哀痛落寞就如羸骖回到破烂之马栈与嫠妇之空叹无助。诗里相关天、地、物、人的意象俱属静态的、缓慢的,意象背景之深广与纵横交错织成悠悠天地的罗网,诗人无法逃离其中,思情积淀继而表现在第十一句“行吟毛骨寒”。诗人无法摆脱伤痛,更无法应对叛逆者的行为,大概只可以“坐见河汉没”,句意既指夜色将尽,也指“大星”和“昴毕”的消逝。相比前述联句诗有大量篇幅勾勒险要异域,《榆林对月》描述了静态的榆林景色和内敛的心理创伤。
对比《至治癸亥八月望,同袁伯长、虞伯生过枪竿岭马上联句》的星宿意象,《榆林对月》措辞典雅,表现一种中正平和的情绪,这是经过沉淀后的思绪整理。前者的“钩钤”与“欃枪”代指皇帝座驾与南坡暗杀之事,借星宿意象书写此地引发的创伤经验,除了是当时对天象的直接印象外,也说明诗人已借广漠天空下的星宿——此地的典型之物——内化为凶残内乱的想象。就用字表意言,“钩钤”与“欃枪”本身塑造了紧张氛围,呈现刺杀行动的刀光剑影,二词自身的感情色彩具象化诗人获得消息后的震惊。当创伤经验再现时,需要以同一系列的文学语言来升华,故《榆林对月》重复出现星宿意象。相对“钩钤”与“欃枪”,《榆林对月》的“昴毕”(出自《汉书》)词性平实,而第七句“天高露如霜”可联系《诗经》“白露为霜”的幽静意境。全诗只用了情词“泣”和景语“寒”道情,余下的皆平实婉转,含蓄地以两条脉络写忧郁,虞集的哀伤化为地 (第1,2,5,6句)、物(第9句)、人(第10句)的情境,把情绪统摄在第十一句。另一条脉络以第三、四句的星宿通过“比”的方式构成:星光(英宗与拜住)照在露水与客子衣服上(七、八句),反照之白色或可喻君臣的纯净无瑕,最后以曙色初现,星光渐褪写二人离世(十二、十四句)。星光的出现与消逝道出英宗与拜住人生之起跌。虞集委婉的述情恰到好处,他在枪竿岭收到消息时的情绪是波动的,及后回京途中,在榆林沉淀思绪后,转向了平淡内敛的表述。[3](P39)
共同的创伤经验唯有以共同的文学语言来抒怀,诗人是以次韵的方式互相慰藉,袁桷《次韵伯生榆林中秋》云:
榆林月中来,今月向此出。
天低鸟翼灭,野净田事毕。
驿马西北鸣,候吏语喧唧。
我行起视夜,炯若积雪白。
昂头望玄宫,耿耿驻营室。
坐令八方澄,不使万景没。
徘徊清影孤,踯躅怅后发。[18](P69)
此诗延续联句诗、虞集诗的星宿意象, 再现共同的创伤经验,第九句“玄宫”代指皇陵[19](P171),承句的“营室”即“室宿”,位处北方玄武,即皇帝夏宫之所在。[20](P36),[21](P133)借两个星宿的配合,指英宗已殁于北方,但其精魂仍使北方澄明。“玄宫”映照又可指英宗过去的保护,袁桷想到现在的孤清,故怀想英宗之澄明。袁诗的星宿意象不再停留于联句诗里的刀光剑影层面,而逐渐从虞集诗闪耀的“大星”和“昴毕”于“河汉没”里抽离,聚焦英宗化为星宿后,仍然照亮万物的一瞬。由同一系列星宿意象的再现可见,袁桷书写创伤后的另一种感受,肯定英宗殁后仍在守护万民,也是回应及安慰虞集“河汉没”的悲痛,想象英宗的精神仍存。那么,是否可以说袁桷借此自我救赎?1326年,袁桷为《秋闱唱和》写的序回顾了这桩榆林往事:
至治三年(1323)八月十五日,乘驿骑抵榆林。于时,善之(邓文原,1259—1328)祭酒仲渊(李仲渊)学士伯生(虞集)伯庸(马祖常)二待制同在驿舍,伤感增怅。今忽同校文于江浙,因述旧怀。[18](P188)
袁桷辞官于1324年,写序之时已不在大都生活,然南坡之变为他带来的创伤一直萦绕不去。
三位诗人虽不在南坡之变的发生现场,事变后数天刚好在北上道中,由于他们与英宗和拜住的密切联系, 可知他们的心理恐惧与压迫。回到大都后,虞集、马祖常仍然在朝,袁桷则在一段时间后辞官。《元史》没有记载袁桷辞官原因,苏费翔(Christian Soffel)指出袁桷于1327年下世后获得不少封号,故他离开翰林院时并非有不愉快的理由,或许因为顽疾而无法侍主。(14)Christian Soffel says “[Yuan Jue] was rewarded several posthumous honours after his death in 1327.Therefore, we can conclude that he left the Hanlin on good terms, maybe because he fell ill and was unable to serve.” “Publishing Strategies in the Early Fourteenth Century: Yuan Jue’s Preface to Wang Yinglin's Kunxue jiwen,” Journal of Song-Yuan Studies,No.35 (2005), 66.笔者提供另一角度思考。袁桷曾赞扬大长公主祥哥剌吉及英宗对汉文化和五经的尊崇,尝试把有益于国家大事的部分移植蒙元内廷,袁为大长公主记述藏品的《鲁国大长公主图画记》云:“至于宫室有图则知夫礼之不可僭。”英宗于1322年按照汉人皇帝习惯,命人把《蚕麦图》挂于上都宫殿,警醒自己无论何时也要念及苍生,[5](P624)这便遥相呼应上文“坐令八方澄,不使万景没”的句意,可以想见英宗和袁桷的君臣契合。后来,默许暗杀行动的晋王继位为泰定帝,同样,袁桷拟说服泰定帝要展示具有道德含义的图画,以重建宫廷秩序、尊卑、礼仪,尤其是袁桷已认定泰定帝摧毁了宗室间的兄弟关系。[18](P600)笔者认为袁桷辞官原因既不满泰定帝继位合法性,又因为年老患病,故萌生退意。
1324年的夏天,南坡之变后的整整一年,虞集又随蒙元传统扈从北上上都,有诗《泰定甲子上京有感次韵马伯庸待制》八句,次韵马祖常诗。(15)《道园学古录》卷1,页4b。原诗八句。马祖常诗待考。此时袁桷已辞官,虞集在上都忆起去年此时此地的经历,唯有再用星宿意象追忆创伤经验:
7我行起视夜,
8星汉非故处。
第7句与上引袁桷第7句“我行起视夜”相同,虞集刻意召唤此前的共同文本记忆(星宿意象及袁桷诗)并直接挪用袁桷句子,意在再次提醒各人的创伤经验,时空已变,创伤依旧,星汉非故处,在诗人眼里其错置更突显时空之无情。但无论它在何处,总使诗人忆起南坡之变带来的伤痛。创伤后的情绪波动反复再现,其重现方式可以是完整、片段式、变形的,或是回环往复的。虞集等人的共同创伤经验和书写是以星宿意象涵义为本, 即由塑造紧张气氛,到叙写平实星光之位置及河汉没落,再至歌颂星光之作用,回到星汉再次出现且错置, 渐次有抒怀开解的作用。诗人联句唱和的回环往复, 次韵诗作的互相提醒和安慰,星宿意象的转化和再现, 皆是三人直面创伤经验的方法。
四 东平王哀诗——以史笔重建新的政治及道德威信
南坡之变的主使者泰定帝继位后,做了一个举动告诉朝臣他对南坡灾难的立场。《元史》拜住传载:“泰定初,中书奏丞相拜住尽忠效节,殒于群凶,乞赐褒崇以光后世。制赠清忠一德佐运功臣、太师、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追封东平王,谥忠献。”[5](P3306)形容南坡之变的逆贼为“群凶”,追封拜住为东平王,泰定帝的允许肯定了忠节之士, 并把自己排除于南坡事变外。那么,大都文人如何面对这样的官方立场突转?虞集及袁桷有一组次韵诗可资参考。
虞诗题为《次韵李侍读东平王哀诗》[14]( 卷2,P10b-11b),袁诗是《至治丞相挽诗次韵李仲渊学士》[18](P194),二诗为古体,各有56句,该写于泰定帝朝及1327年以前(袁桷此年下世)。原诗由李仲渊直学士撰写,已佚。(16)虞集《送李仲渊云南廉访使序》,见《道园学古录》卷6, 页2a-b。柳贯《故相东平忠献王挽歌词》颂扬拜住(1—20句),写南坡灾难(21—44句),反响(45—56句),见《柳贯诗文集》,第76~77页。就虞集哀诗言,他没有使用星宿意象,南坡灾变所受的创伤经验似乎由前一阶段的平淡隐晦化为直接谴责,这里的心理转化或许与官方立场转变有关。诗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用感情激动且波诡云谲的字词追忆南坡之变的突袭与恐慌,“传闻昏白昼,悲愤结全区”(3—4句),“魑魅嫌明镜”(第9句),“笳鸣残夕月,马偾四交衢。所痛仓皇际,将无古昔殊”(19—22句),虞集对南坡暗杀的愤恨叙述至此。第二部分肯定拜住的功勋以及对其离去的无可奈何,“相业今如在,民生实少痡。谁能疵璧玉,唯有泣琼珠”(33—36句)。相比前此两组南坡诗歌,这首重点在第三部分:
37执简书群盗,
38当关欠一夫。
“执简”句指的是监察御史弹劾群盗的责任,那么此次南坡事件为何由李仲渊直学士和虞集以诗来控诉?可从蒙元律法的背景来看。忽必烈于1272年废除金代的太和律,至蒙元1368年退出汉地期间,一直没有颁布适用于蒙古、色目、汉人、南人的律令。(17)终元一世,有两部法律文献曾于1273及1305年提出,包括《大元新律》及《大元律令》,惜最终都没有颁布。Paul Chen Heng-chao, Chinese Legal Tradition under the Mongols: the Code of 1291 as Reconstructed,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3—40, esp.15, 19.当时中央及地方判决有很多矛盾及不合理处,为了判决有所依据,朝臣始编纂判决案例。[22](P94)经过一段相当长的法律制度的讨论,尤其在拜住上书请求建立正式的法律制度及条文后,英宗最终于1321年颁布《大元通制》,但只包括朝廷法令、条格、断例三部分的判决案例,而不及律令。[23](P28)据此,虞集“当关”句并非实指关口,是指英宗一朝除拜住外,缺少监察御史弹劾答己、铁木迭儿、铁失党派、蒙元诸王的恶行。碍于蒙元缺少律令, 无法审判, 虞集故而把南坡事写进诗里,以春秋之笔弹劾叛党。
虞诗前两部分用了不少情感激动的言词,如“悲愤”(第4句),“痛”(第21句),“泣”(第36句),甚至说“危知无复死,恨不奋前诛”(43—44句),“讴吟申感慨,述作惧荒芜”(47—48句),书写愤恨是诗人直面创伤的途径。虞集最后一段称颂拜住:“神还嵩岳峻,气直斗杓孤。陟降先皇侧,回翔造化徒。英灵常会合,瞻想岂虚无。”(51—56句)以《诗经·大雅》尹吉甫《崧高》里对申伯德行的描述,谓拜住的高尚品德如同嵩山。[24](P272)第53句用《大雅·文王》句意(万民得到先祖的保护)颂扬拜住虽殁但仍然保护英宗及其臣民,(18)《大雅·文王》有句:“文王陟降,在帝左右。”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Songs, 227.虞诗末句对英杰再临充满期待。相较前面两组诗歌, 此诗情绪更为愤懑,如此愤愤不平已从最初隐晦的创伤书写、平淡内敛的反应转变为这一首的直接显现,说明官方追封拜住为东平王一事,对大都文人来说,足以让他们放胆在私人领域的书写里畅所欲言,虞集诗的“气粗笔纵”或可由此主题角度理解。(19)清代潘德舆 (1785—1839)评此诗“气粗笔纵”,《养一斋诗话》,收于郭绍虞编《清诗话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040页。
袁桷挽诗约有三部分,第一部分(1—24句)歌颂英宗及拜住纳贤斥佞,“纟熏帛招贤俊,钢金辟佞谀”(11—12句),第二部分(25—40句)再次追忆南坡灾变的突袭,“万骑玄云蔽,群狐黑夜呼”(31—32句),第三部分(41—56句)则是诗人追忆后的当下批判。最为重要的是对南坡之变的责难。如上所述,英宗与拜住在朝时,于朝政改革及律令颁布都有求变之心,袁诗写道:“律成悬象魏,礼缺补鸿都。”(20)“象魏”即阙,用以高悬皇令示民。东汉时的鸿都门设立官学,是图书中心,也是教人写作文、书、画的地方。(17—18句) 纵有敌对派系和诸王的阻挠,拜住仍然“士进三千牍,奸诛十二衢”(19—20句)。(21)这里的“士”指曾上书长篇箴言给武帝的东方朔 (154—93 B.C.),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页3205。袁桷用以代指拜住。与虞集一样,袁诗的后半部表达他对南坡灾难的激动反响,强调书写此段泣血历史之重要,以春秋笔法弹劾叛党:
41杀青谁执简,
42泣血漫成湖。
43史记羮枭赐,
44经簿齿马诛。
除李仲渊外,袁桷把自己也拉进书写历史的责任里。第43句结合《汉书》枭羹赐朝臣事,古代皇帝命朝臣贡献枭(食其母)及貙(食其父)用以祭祀,灭枭及貙因为它们都是不忠不孝之物;[17](P1218)如淳注评此段记载指出, 汉廷命各地呈献枭,在农历五月初五赐朝臣枭羹,示剿灭奸佞之心。[25](P456-457)袁句直指在皇命下,诛灭佞臣。第44句典故来自《礼记·曲礼》“齿路马有诛”,朝臣数皇帝马匹之年并视其齿,非礼法所容,可被诛,此典多指称宫廷内乱。[26](P115)袁桷激动愤懑的言辞指出要有诛灭佞臣的魄力(羮枭),并有完整的礼法秩序和律令阻吓(齿马),才可“邦刑穷剿绝”(第49句)。文明社会需要有政治和道德力量的展示,通过朝廷和儒臣的合作重整律令和礼法制度,“杀青谁执简”的“谁”,除袁桷正在以史笔讨论这段南坡灾难之外,同时肯定及欣赏李仲渊的撰作,而“谁”应可包括任何一个后来者。
由这组追忆南坡事变及悼念拜住的次韵诗可见,大都文人已抛开了最初的巨大创伤,始以反省和提出改革的角度正视现实,这点与泰定帝及其党羽追封拜住为东平王有关。既然朝中已把他视为“尽忠效节”之士,虞集和袁桷便可放心在私人领域的次韵创作提出时政见解。诗里最为核心的观念是以史笔记录之,这缘于当时律令缺失,虞、袁认为叛逆者逃得过法律制裁,但走不出历史判决,进而强调“执简”书写。从两首作品的文学语言看,召唤经史里记载道德力量和威慑佞臣的故事,都可视为儒臣对非礼行为的不满和判断,虞、袁诗里再现这些原典关键词,进一步提供了古代君主断案的方法以及重建道德秩序的事例参考。由南坡之变及泰定帝朝的政治生态切入,虞、袁这组诗歌有巨大的正面价值,它代表了当时对道德力量的要求,而“执简”的史笔意义在于它是当时文人共有的文化背景。蓝德彰(John Langlois )的研究指出,元代专研《春秋》的学者颇多,现存有127种资料,虞集的老师吴澄便有《春秋纂言》,可知当时对“义”的追求是文人共有的想望。(22)Chunqiu, as John Langlois puts it, “could provide a source of norms and laws and precedents which would assist the ruler in restoring order to the world” and provide officials “with guidelines and support in the efforts to advise the rulers in statecraft”.See “Law, Statecraft, and 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in Yuan Political Thought”,119, 127.
五 宫廷诗的劝诫——1326年的经筵后诗
中期的帝位纷争源自不同派系的权力追逐, 虞集是支持答剌麻八剌一系治统的合法性的,这一系包括仁宗、英宗以及后来的文宗,而泰定帝属于甘麻剌一系。泰定帝殁后, 文宗继位,虞集于1328年奉文宗命撰写《即位改元诏》, 严词斥责泰定帝当初继位之不当:
宗亲各授分地,勿敢觊觎。此不易之成规,万世所共守者也。世祖皇帝之后,成宗皇帝、武宗皇帝、仁宗皇帝、英宗皇帝,以公天下之心,以次相传,宗王贵戚,咸遵祖训。至于晋邸,具有盟书,愿守藩服,而与贼臣帖失、也先帖木儿等,潜通阴谋,冒干宝位,使英皇不幸罹于大故。[7](P114), [27]( 第26册, P17)
在文宗的保护下,虞集以“晋邸”称呼泰定帝,在此官方文献里确认其“潜通阴谋”而致南坡之变,否定其继位之合法性。文宗1329年第二次继位,虞集奉命再撰《即位诏》,同样斥责“晋邸”破坏祖宗家训。[27]( 第26册,P18)虞集另一篇宁宗即位诏写于1333年,甚至一字不提“晋邸”,只写答剌麻八剌一脉的英宗(1320—1323)、文宗(1328首次继位)、明宗(1329)、文宗(第二次继位,1329—1332)。[27](第26册,P18-19)
在这背景下看,虞集在泰定帝一朝内心必定充满挣扎及矛盾。这批曾经历南坡灾变后的诗人是如何面对泰定帝呢?1324年,泰定帝命重开经筵,虞集和马祖常俱任讲臣(参虞集《书经筵奏议稿后》)[7](P523),有诗记述讲经之过程,我们以马祖常《大明殿进讲毕侍宴得诗二首》及虞集《进讲后侍宴大明殿和伯庸赞善韵》为例谈谈两位诗人在内乱后的态度。[1](P70), [14](卷3, P4 b)笔者把这组诗系于1326年。1324年,马祖常任左赞善[5](P3412),同年,虞集任国子司业。1326年,虞集升任秘书少监,并于1327年转任翰林直学士。[15](P453-456)柳贯诗《贯草草南归伯生秘监方晨赴经筵驰诗见别舟中次韵俟便答寄兼简伯庸赞善》记录马祖常赞善及虞集秘监同于经筵讲学[28](P6-7)。据马、虞官职,相信此次经筵于1326年举行。 此外,马、虞诗题谓经筵开于大都大明宫[29](P139),翻查史料,1325年的经筵在上都举行[30](P101)。1327年虞集已转任翰林直学士,因此,上述“大明殿进讲”应该在1326年的大都举办。据柳诗记载, 1326年经筵的进讲典籍为班固《白虎通义》,(23)柳贯诗:“讲经白虎论,载笔承明入。”是书重点陈述为君重大的道德责任,以及为臣子的天职应当指出君主错误。(24)Wm.Theodore de Bary says the Baihu tongyi has “a clear reaffirmation of the Confucian emphasis on complementarity, on the heavy moral responsibilities of the ruler, on the minister’s duty to remonstrate with the ruler lest he goes wrong (or leave his service if this is unavailing), and on the son’s duty to remonstrate with his father as well as the wife’s to admonish her husband.” Sources of East Asian Tradition vol. 1,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8, 187~188.如果以上述有关英宗、拜住、南坡事变的各组诗歌书写为讨论脉络,这组宫廷诗虽非专写南坡之变,却是因为深刻的灾难而出现,反映南坡之变后朝廷拟重建和加强道德威信,值得参考。
马祖常《大明殿进讲毕侍宴得诗二首》其二如下:
1汉殿千门饰宝瑶,
2直郎先奏进经朝。(25)直郎是承直郎之谓,属元代的荣誉称号。
3诸儒泥古言虽固,
4明主思贤道已昭。
5饮酒敢同鱼藻赋,(26)《诗经·小雅·鱼藻》,毛诗序认为是篇讽刺幽王只重享乐不重苍生。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Songs, 210.
6制诗真过柏梁朝。(27)指汉武帝柏梁台。
7小臣槖笔词垣侧,(28)词垣代称翰林院。
8白日无翰溯赤霄。
马祖常在五六句书写对经筵的正面看法。第5句用《鱼藻》“王在在镐,饮酒乐岂”句意,(29)据马诗第4句“明主思贤道已昭”,此处暗用《诗经·小雅·鱼藻》篇。 Arthur Waley, The Book of Songs, 144.写泰定帝听讲后满足地与朝臣同乐。第6句写汉武帝柏梁台上的君臣联句,由武帝起句,朝臣承续,例如石庆写“总领天下诚难治”誉武帝治国,咸宣云“三辅盗贼天下危”喻武帝应小心周边地区的各个势力。(30)明代谢榛称誉柏梁台诗:“是时君臣宴乐,相为警诫,犹有二代之风。”见《四溟诗话》,收于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144页。据此, 马诗第6句赞扬泰定帝胸襟广阔,接受朝臣的进讲, 如柏梁台君臣联句一样,看来此次经筵的效果颇佳。虞集和诗(其二)转写泰定帝重视老臣,欣喜有经筵的推行以及宫廷之生气焕发,最后以文臣颂扬上位者作结。有关进讲过程的描述只见于和诗(其一):
1丞相承恩自九重,
2讲臣春殿秩初筵。(31)“初筵”即《诗经·小雅·宾之初筵》诗。 Arthur Waley, Book of Odes,207~209.
3养贤敢谓占颐象,(32)“颐”(Nourishment)象,Van Over Raymond ed., I ching (based on the translation by James Legge). New York: New American Library, c1971, 155~158.
4陈戒犹思诵抑篇。(33)“抑”篇即《诗经·大雅·抑》。Arthur Waley, Book of Odes,263~266.
5既奏虞韶兼善美,
6岂无后稷暨艰鲜。
7愿推余泽均黎庶,
8乐只邦基亿万年。(34)此句用了《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句。Bernhard Karlgren, Book of Odes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0),115~116.
虞集诗用典颇多,典故的共通处在于点出为君为臣的道德行为标准。第1句以丞相(主导经筵)受皇恩起句[7](P523),写君臣和睦。第2句以《小雅·宾之初筵》“宾之初筵,左右秩秩”承接(35)Arthur Waley, Book of Odes, 207~209. 据毛诗,诗刺幽王耽于享乐、宴会和过渡饮酒,虞诗并没有此意。见朱熹《诗集传》,第190~192页.,指出完成经筵后,儒臣往内宴就座后的恭敬形象。第3句引《易经》“颐”象谓:“天地养万物,圣人养贤以及万民,颐之时大矣哉。”[31](P305), [32](P114)这里的类比是“圣人养贤”与“泰定帝养贤”, 皆惠及万民,虞集对泰定帝再开经筵感到恩喜。第4句《抑》篇的典故层次指贤士批评时政的勇气,经筵官向泰定帝进讲,而泰定帝诵《抑》明己志。5和6句为鉴戒,借古乐“虞韶”指出上位者要以虞舜为本,建立道德正义,又以虞舜时的农官后稷为例,元廷要有惠及万民之心。末联回到宫廷诗传统写法,感谢皇恩,并愿意把剩余的惠及平民,再以《诗经》总结邦国再兴且乐的理想境界,原因必定在于朝廷的养贤及惠民政策。
南坡之变三年后,袁桷离场,马祖常和虞集仍在朝中。马、虞于1326年撰写的经筵后诗,重点虽不在创伤经验的追忆,但由于它的主题是暗杀行动的主使者泰定帝,因而可通过此诗看宫廷文人如何周旋于统治不受认可的泰定帝朝。由经筵后诗可见,马和虞对泰定帝是有期许的,这种期许已脱离首两组诗歌的创伤经验,而积极介入朝政的操作,直面泰定帝的统治以及由他引起的创伤。要问的是,泰定帝为何重开经筵?研究指出,他为了表明自己对汉文化的尊崇以及赢得最广泛的支持,故于事变后的1324年立即重开经筵[4](P539),如同武宗于大德十一年(1307)即位时出版蒙文译本《孝经》的目的一致。另一方面,参与经筵的儒臣又是如何看?虞集写于1327年的《书经筵奏议稿后》记载集贤院大学士赵简 (生卒年不详)感叹朝廷没有从经筵获得历史经验推动朝政发展,认为没有一项改革或讨论得益于经筵讲学,虞集安慰赵简,说泰定帝重视经筵,把讲学内容及典籍以金字皮革包裹,虞集进而认为典籍记载的古代经验或许未必切合当今情况,作为儒臣应尽力向上位者讲述儒家要义及经典事例。[7](P523)从1326年的经筵后诗可证,虞集等人非常珍视这些讲学机会,提供美刺并重的经典事例是当时诗人直面泰定帝的共同态度,其心态固然是为了国家秩序和道德力量的重整。
六 虞集的公私撰述及其处世哲学
阅读1323至1327之间有关南坡之变的周边文本,袁桷、虞集、马祖常有着不同程度的情绪显隐,创伤后的激动、平淡隐晦、愤懑,以至直面事实后的反思批判,都与英宗和泰定帝的朝政状况息息相关。从以上四组诗歌来看,诗人是以共同书写、召唤同一文本意象或同一立场来抒怀,并以联句和次韵方式对话疗伤。由于虞集在中期宫廷的政治和文学方面都有重要地位,(36)成宗时虞集任大都路儒学教授(1297年),仁宗时为国子博士(1312年,正七品)、集贤修撰(1318年,正六品)、翰林待制(1319年,正五品),文宗时被召为国子祭酒(从三品),兼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翰林直学士、知制诰、中奉大夫(从二品)。见《元史》,第4173~4227页。本节以他为重心看其在朝中的公、私撰作,探寻其处世哲学, 借此了解为何他对南坡之变的记述特别小心谨慎。
泰定帝1327年离世,1328年文宗在漠北暂时继位,后来恭迎和世(明宗)回汉地为帝,明宗在位数月而薨,文宗于1329年再次登极,崩于1332年8月,其钦点的继任人懿资班伦(宁宗,和世次子)按原定计划继位,惜在位53天便亡。当和世长子妥权贴睦尔(顺帝)于1333年7月继承大统,虞集知其政治生涯即将终结,因为文宗曾命他写诏书诋毁妥权贴睦尔(顺帝),故乞归江西。[30](P104-105,111-113)虞集乃识时务者,学会妥协的生活哲学。有一例值得参考,元代中后期曾讨论宋、辽、金三史编纂,有两种意见,一学南史、北史体例,分别立史,或学晋书体例,以宋史为正史,辽、金入载纪,南方儒者多主此说。[33](P125),[34](P21)当时朝议未决,总修史官脱脱谓:“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37)在修史问题上,中后期文臣态度妥协,对皇帝是华是夷置之不理。可参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龙门书店1977年版,第41页)对杨维桢《正统辨》的讨论。虞集早于修史前十年的《送墨庄刘叔熙远游序》(1334年)便指出:“间与同列议三史之不得成,盖互以分合论正统,莫克有定。今当三家各为书,各尽其言,而核实之,使其不可废,可也,乃若议论,则以俟来者。”[3](P549)所言非常务实,可说是他在朝中的处事原则。另一方面,虞集的创作取向与其展示的公共形象息息相关。欧阳玄为虞集《道园类稿》写的序(1346年)指出:“至治天历(1321—1330),公仕显融,文亦优裕,一时宗庙朝廷之典册、公卿大夫之碑板,咸出公手,粹然自成一家之言。山林之人,逢掖之士,得其赠言,如获拱璧。”[16](P252)虞集文学才能出众,故获朝野肯定,隐士、儒者以得其赠言为荣。[35](P477-480),[36](P460-469)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文章犹作世璠玙”(《题东平王与盛熙明手卷》)[14](卷3,P13a)。虞集背负荣显的公共形象,加上他在文宗的要求下参与诋毁顺帝的诏书写作而被针对,使他未能在朝中的撰作里坦然表达自我意向。顺帝至元六年(1340),虞集已退隐江西六年,友人来访并搜集其散佚作品二百余首,拟成结集。虞集记此事时忆及往日在大都的创作:“早涉笔为文,应事而已,人或以为能,自知其不足也。”又道:“老病自知才思少,应酬长愧语言多。”[14](卷29,P9a)这些话虽是自谦,然不容忽视“应事”“应酬”反映其谨慎的在朝生活。由文宗朝继位的政治纷争看去,更准确地说,虞集是为了明哲保身,这让我们进一步明白为何他以“道园”为号。虞集《道园天藻诗稿序》云:“养亲东南,无躬耕之土。及来京师,僦隙宇以自容。尝读黄庭经,有曰‘寸田尺宅可治生’,是则我固有之,其可为也。又曰‘恬淡无欲道之园’,遂可居有哉!”[16]( 卷19,P505)妥协应事、不冒犯别人、恬淡无欲是他在大都时的处世原则。
自顺帝元统二年(1334)归隐江西后,虞集才放胆写出种种在朝的心灵感受,《次韵陈溪山棕履》(其一)最后数联言:
知君贵贱履,陟降恒有道。
怜我涉世深,垂诫不待造。
兢兢历渊冰,缩缩奉师保。
时行不违矩,庶慊岁年老。(38)《论语》“为政”:“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见刘宝楠《论语正义》,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3页。[14]( 卷27,P4a)
以“历渊冰”总评往日宫廷生活所蒙受的精神压力,虞集在朝中规行矩步,而归隐后的放松心情可以其恒常使用的“素履”为证。《次韵陈溪山椶履》(其二)倒数第二联谓:“感君素履咏,幽贞可长保。”(39)“素履”“幽贞”取自《易经》“履”卦,卦曰:“素履之往,独行愿也。……履道坦坦。幽人贞吉。象曰:幽人贞吉。中不自乱也。”见南怀瑾、徐芹庭注释《周易今注今译》,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90页。虞诗见《道园学古录》卷27,第4a页。“素履”指隐士或幽人,以随心所欲的态度直面生活,故横祸不至,福气随来。“素履”简单直接,表现虞集的个体私情。元统二年虞集已在江西,以眼疾为由婉拒顺帝征召,随后恩准于江西撰作朝廷公文。[15](P464)目前没有资料显示虞集因惧怕权臣而拒赴大都,但至少知道他不欲以“历渊冰”的心情再次进入大都权臣的视野中。相关南坡之变的另一事例值得参考,虞集《平章政事张公墓志铭》写平章政事张珪,此文收录于虞氏亲校的《道园学古录》及苏天爵《元文类》,其中一段约400字的“密书”只见于后者的版本中。[7](卷53,P17-18), [14](卷18,P9A-9B)“密书”重点记载南坡政变、铁失夜扣国门夺取符印、张珪与魏王商略是否应以密书恭迎晋邸为王等内容。虞集于1340年与门生共同审订《道园学古录》时删去“密书”[14]( 卷29,P9A),应考虑到此书会在顺帝朝出版,自己又曾撰写诏书诋毁顺帝,故删除相关宗室派系政变的记载,符合虞集谨慎的政治态度。(40)参见马晓林的观点。他指出虞集考虑到在顺帝一朝,朝野对张珪一家的功过仍没有定评,而且张氏家族之死还是一桩冤案,因而把“密书”一段删去。《张珪墓志铭文本流传研究——兼论〈元史·张珪传〉的史源》,《中国典籍与文化》总第79期(2011.4),第28~33页。据近人研究,元初遗民普遍有“自我审查”,意识到不恰当的言辞会带来严重后果。[37](P603)这观察大致也适用于中期宫廷文人公私两面的书写。南坡之变的历史细节不见于亲校文集,但虞集相对隐晦的创伤经验的再现与评判仍可得见,其隐与显确实与波诡云谲的朝政与个人生活息息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