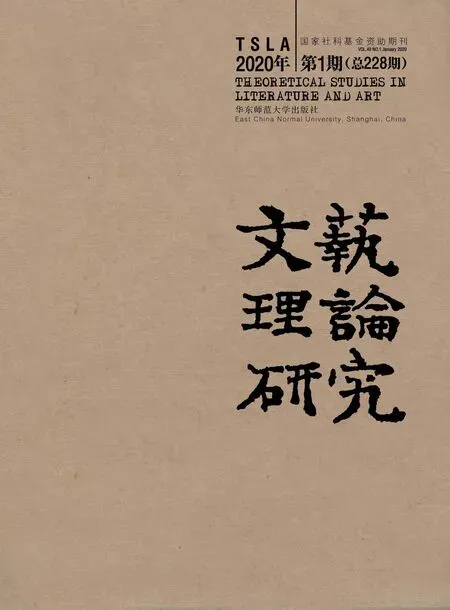注目于“名”: “名物学”的另一条路
鄢 虹
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随着国内“重写”诸史之关注点开始从中心转向边缘,学界对“名物学”的关注也在悄然兴起。(王筱芸190)近二十年间,该学科虽然在扬之水等人的努力下颇有发展,但它的学科性质、研究领域及研究方法等,却仍有待进一步论证,而这种论证,无疑应当从该学科的发展史,尤其是隐匿在既有研究中的问题与潜力出发。整体而言,目前的“名物学”偏重于对“物”的考证,然而它面临的某些问题,以及它上接的传统,却在呼唤它兼顾“名”之面向。
一、 “名物学”的形成: 并非自古有之
“名物”一词,出自《周礼》,名物研究,在中国已有数千年之传统,然而作为现代学科的“名物学”,却发轫于青木正儿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建构。1958年,青木氏将其开设“名物学绪论”等课程的讲义之要旨节录成文,弁于次年出版的《中华名物考》一书之首,是为《名物学序说》,此文初步勾勒了以中国研究为前提的现代“名物学”之框架,允为该学科之首唱。在《序说》当中,青木氏将“名物学”定义为一个“发端于名物之训诂,以名物之考证为其终极目的”的学科,并分四阶段梳理了传统名物研究的发展史: 在他看来,“名物学”在《尔雅》的时代尚与训诂学混杂不分,直至东汉才由《释名》牵出了独立之端绪;此后,该学科在《尔雅》系列续作及《诗经》名物训诂两大系统之外,复于礼学、格古、本草、种树、物产及类书等六方面各有展开,并最终以考证学为依归,在清代得到了长足发展。(10-31)
青木正儿的上述归纳,准确地抓住了传统名物研究的核心方法,同时全面而有条理地爬梳了与“名物学”相关的各类文献,为“名物学”之成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然而遗憾的是,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名物学”并未得到中国学者的关注,而自青木正儿去世以来,该学科在日本亦后继乏力: 数十年间,彼国虽仍有若干种零散、具体的相关研究,但如青木正儿一般站在学科建设的高度上,全面而深入地思考中华“名物学”的学者,却再未出现。
在中国,“名物学”的发展于本世纪初迎来了转机。2004年11月,王强发表《中国古代名物学初论》一文,第一次站在学科建构的立场上对“名物学”展开了系统论述。不过,此文并未利用青木正儿的研究成果,作者对“名物学”之历史及相关文献的梳理,大抵不过重走前人之老路,而他在此基础上对“名物学”作出的定义与展望亦如后人所言,“似乎对中国传统的任何学科都适合,并未真正界定名物学的学科性质与特征”(张桂丽50)。真正接续了“名物学”传统之人,是于同年12月出版了《古诗文名物新证》一书的扬之水: 她在此后十数年间开展“名物新证”的理论基础,即由该书之《后序》初步确立。2012年,《古诗文名物新证》以“合编”的形式再版,弁于书首的《诗中“物”与物中“诗”——关于名物研究》一文,便是对上述《后序》的改写,而其大旨几乎未变。在这两篇文章当中,扬之水回顾了青木正儿的“名物学”,接受了他对我国传统名物研究的总结,而在讨论自己的“名物新证”时,她将“名物研究”定义为“研究与典章制度风俗习惯有关的各种器物的名称和用途”,认为它的研究对象是传世或出土的文物,而其任务则可总结为“定名”与“相知”,即确定器物原有的名称,与明确器物在当日的用途与功能,包括它们承载的文化信息。在研究方法上,扬之水提出“新的名物研究,其基础依然是训诂和考据”,而旧方法革新之关键,是由王国维倡扬的“二重证据法”。除此之外,受其学科背景影响,扬之水还着意追问了名物研究对文学的贡献,并从提示新读法、加深对诗文的理解与开启日常生活描写等三方面给出了自己的阶段性回答(《合编》1-7)。
不管是从持续而广泛的具体名物研究来说,还是从对学科本身的完整而深入之思考来说,抑或是从在学界激起的回应与评价来说,青木正儿与扬之水无疑分别是日本与中国的名物学界之第一人,而扬之水的“名物新证”对青木正儿的“名物学”还颇具传承与发展之功,尽管她本人常常将其学问之源头追溯至沈从文在1961年对“名物新证”的提议。在东亚之外,西方汉学界并未对“名物学”这一概念表现出明显的兴趣,然而他们的某些研究事实上亦以“名物”为对象: 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以及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 唐代舶来品研究》,即为此间之代表。《中国伊朗编》成书于1918年,劳费尔在以中国对伊朗的记载为史料来研究伊朗之前提下,将植物名称视为主要研究对象之一,兼及矿物、纺织品与其他物产。为该书之中译本作序的邵循正指出,劳费尔主要以语言学方法为解决问题的工具,而劳费尔本人则强调,语言现象在他的研究中只是枝节问题,其主要任务乃“探索构成物质文明的一切事物的历史”(8)——如是观之,此书对“名”与“物”的关注,可谓相当明显。《撒马尔罕的金桃》出版于1963年,薛爱华以劳费尔的研究为基础,在时间上将目光集中于中外交流最为频繁的唐朝,而在空间上则将整个旧大陆都纳入视野,同时深化了劳费尔尚未成形的理论,在学界获得了很高的评价。对上述研究的详细分析,将在下文展开,而中日两国之其他学者为“名物学”贡献的零散讨论,以下几节亦将择其善者随文介绍。
二、 “名物学”的理路: 传承与变化
扬之水在介绍青木正儿的“名物学”体系时,仅将其视为对传统名物研究的整理与总结,并未分析其内在理路。事实上,青木正儿虽然在研究方法上忠于古人习用的训诂和考证,但他的研究与传统之间,早已存在本质上的差异。李勇于《名物学与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式》一文中指出,青木“名物学”的理论来源有二,一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清代考据学,一是西方的实证主义,而这种新“名物学”与传统名物研究的关键区别,便是前者在京都学派的学术语境下抛弃了后者恢复“圣人之道”的文化理想(60),自然而然地受到了实证主义精神的感染。的确,传统名物研究与中国的其他旧学一样,大抵以经学为本位,促成此类研究之动机,多为解经、践行圣人之教,或是完善礼制、维护政教秩序等。然而在近代,随着经学之式微与西方学科体系之传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指导学者们开展各类研究的核心思想都在不可避免地发生改变。严绍璗《日本中国学史》有云,“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中,引进实证主义观念,并且使它与中国清代考证学结合,从而架构了从传统汉学到近代中国学的桥梁”(374),是京都学派的整体特点,而青木正儿作为京都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的确符合这一描述: 他虽然视清人考据为“名物学”之大成,但促使他本人展开名物研究的动机却并不是辅翼经学,因此,他的视野并未被框定在经学范围之内,而是很自然地扩大到了往昔难免被视为“小道”的日常饮食、服用、器玩等生活琐物之上,这一点从他为“名物学”指出的主要文献当中即可窥得。
扬之水的“名物新证”,从本质上来说也是实证主义的。她在《诗中“物”与物中“诗”——关于名物研究》一文中讨论名物研究的古今不同时称,就研究对象而言,她与“古”一脉相承,而她继承的“古”,正是被青木正儿整理与建构过的“古”(4)。自《诗经名物新证》出版以来,①她的目光便投向了更为广阔的日常生活领域,殊未受限于经学: 文人香事、金银首饰、《金瓶梅》,皆为其用心用力之处。由上文可知,青木正儿的名物研究视野之扩大,正是实证主义代替经学目的成为指导思想的某种表现,故而继承了这一视野的扬之水,亦可说从一开始便多少接受了实证主义的影响。
在继承传统之余,“新证”之“新”,据扬之水的自述,则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研究方法,即依赖于考古学的“二重证据法”;第二是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二重证据法”并不算是一种新方法,②不过,鉴于青木正儿在开展名物研究时基本依靠文献互证,扬之水强调名物研究应当利用地下之材料与考古学之方法,对“名物学”本身来说,无疑是有益的补充。至于何为“研究层次的深化以及研究内涵的丰富”,扬之水的解释如下: “由单纯对‘物’的关注发展为‘文’、‘物’并重,即注重对‘物’的人文意义的揭示与阐发。也就是说,与作为母体的传统学科相比,今天的名物研究应有着古典趣味之外的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关照。”(《合编》5)“人文”二字,颇为宽泛,传统名物研究的“古典趣味”,也未必不关注“物”的“人文意义”,故而上述解释真正强调的,其实是“对历史事件和社会生活的关照”。应该如何观照历史事件与社会生活?扬之水在得出该总结之前写下的另一段分析,颇可视为其注脚:
作为“名物新证”,它应以一种必须具有的历史的眼光,辨明“文物”的用途、形制、文饰所包含的“古典”和它所属时代的“今典”,认出其底色和添加色,由此揭示“物”中或凝聚或覆盖的层层之“文”。同样是以训诂和考据为基础,新的名物研究与旧日不同者在于,它应该在文献与实物的碰合处,完成一种贴近历史的叙述,而文献与实物的契合中应该显示出发展过程中各个时段的变化,此变化须有从考古学获得的细节的真实与清晰。③(《合编》5)
李勇在解释“实证主义”时曾指出: “实证主义具有清晰的历史意识,既重视‘知识’自身发展演变的历史,又重视‘知识’彼此间始终不断的互动历史。在学术理念上,实证主义力图还原真实可靠的‘知识’形成史,而这恰恰是清代考据学忽略的方面,它几乎否认了‘知识’的累积过程。”(60)从辨明“古典”与“今典”、“认出底色与添加色”等追求来看,上述分析与其说适用于青木正儿,不如说更适用于扬之水。如果说实证主义在青木正儿的“名物学”当中只是不言自明的背景,那么扬之水无疑更加深刻地指出了经学退位之后名物研究在实证主义思想指导下的新目标,这对于进一步明确与完善现代“名物学”之理论体系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上文提到,在现代“名物学”中占据指导地位的实证主义往往被认为源于西方。劳费尔的《中国伊朗编》虽无对“名物学”之建构,却有名物研究之实,而这本颇具实证主义精神的著作问世时,青木正儿的“名物学”尚未成形。不过,依邵循正所言,《中国伊朗编》更像是一种资料汇编: 过于倚重比较语言学方法的劳费尔并未以这批资料为基础提出一套完整的理论(iii),尽管他有野心说明“植物移植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并试图确定伊朗对中国文明的影响(28-29)。当薛爱华以“金桃”为线索接续劳费尔的治学传统时,④青木正儿的《中华名物考》已然出版,但正如劳费尔的研究并未对青木正儿产生直接影响一样,青木正儿与薛爱华的名物研究之间也并无影响关系。尽管如此,薛爱华对劳费尔之思路的深化,却是有目共睹的: 《撒马尔罕的金桃》之译者吴玉贵指出,与劳费尔相比,薛爱华除了在研究视野和深度上都有很大拓展以外,在研究方法上也从比较单一的考据转向了较为深入的社会研究,他通过探讨古代的物质生活内容来分析当时的社会及其文化状况,形成了独特的治学视角(6-7)。更重要的是,在劳费尔与薛爱华之间的传承中,实证主义的指导同样从朴素走向了深入: 薛爱华也更加留意“知识”的形成过程,他不满足于就“物”言“物”,而是格外关注“物”在文字资料中的更新与延续,以此为切入点来展开对社会与文化的讨论(30)。
三、 从“物”到“名”: “名物学”的潜在问题与面向
由上文之梳理可知,自20世纪初以来,“名物学”虽未发展成一门显学,至今亦可称成果颇丰。不过,令人在意的是,现有理论框架当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暴露与讨论。竹内好早在1970年便指出,青木正儿的名物研究多引类书以为据,而类书并不是可靠的资料来源(186),但这一问题并未引起后人的重视: 张桂丽在讨论青木正儿的“名物学观”时亦曾谈到,他征引的材料绝大多数为笔记小说、谱录类书,却对此事并不置疑(49)。
事实上,被青木正儿整理过的“名物学”资料,本就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不可忽视的差异。青木氏对“名物学”的定义,主要是从带有研究性质的训诂、礼学、清人考证类著作当中总结出来的,而被他视为“名物学”之发展的本草、种树、物产类著作与大部分类书,以及常为其在具体研究中所征引的各种小说,其实并不符合他对“名物学”的定义: 它们大多仅因记录下了“物”的性质与状态而被视为“名物学”之资料。对于此类资料,青木正儿并未在训诂与考证以外提出新的处理方法或思路,这无疑是不合适的——与源自经史、在真实性方面有基本保障的研究对象不同,上述五类作品提供的名物记录是否全都当得起严肃的训诂与考证,其实相当值得怀疑: 类书与小说,自是驳杂无伦、饰伪横生,就算是看上去更值得信任的本草、种树与物产类著作,有时也并不那么可靠。举例而言,在本草类著作当中,便存在一批专门记录药物异名的特殊文献,如唐人梅彪的《石药尔雅》《酉阳杂俎·玉格》篇当中的药草异名、《清异录》当中的《药谱》等等。这批文献或与道教修炼相关,或来源于文人之笔墨游戏,与药物性状几乎无涉,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何种文献范围内适用于训诂与考证,便未免有待商榷。
种树类著作当中的某些植物专谱,同样未必即可使人按图索骥。专谱者,专取某一物种(species)而谱之也,为其所记者,实乃各物种之人工培育品种(cultivar)或自然变种(varietas)。因此,这类记录虽多少会涉及性状描写,但各性状之间的差异其实相当有限,有名称而无描述之记录亦复不少,如周师厚《洛阳花木记》⑤收录牡丹品名一百零九种,其间有描述者便只得五十二种。此外,由于牡丹、芍药等流行花种的人工培育品种更替速度极快,被记录在册者有的在十余年后即告湮没无闻,有的甚至在入谱时便已空留其名,《陈州牡丹记》当中的“缕金黄”,便为一例(16)。因此,若要根据此类著作之记载开展精确到品名的考证,将难免流于附会。
至于物产类著作,则更不能使人无疑。被青木正儿在《名物学序说》中挑选出来的《岭表录异》《桂海虞衡志》等书虽大致可信,但据《四库总目》可知,“夸饰土风、附会古事”亦乃常见于此类文献之积习(1896)。就拿同样被青木正儿提到过的《异物志》来说,据今人王晶波之研究,该系列著作当中的“文学性”⑥因素是随着时代之推移而萌发增长的: 在原本反映真实知识水平的记录中,大量传说与附会逐渐掺杂进来,而进入唐代以后,此类著作的“文学性”更是“一举压倒知识性”,成为决定其性质的主要因素(63)。因此,在对各地物产的记录中,有一部分是十分可疑的,它们显然也不能直接成为名物考证之资。
青木正儿想要处理上述材料的心情,或许不难理解: 它们同样是名物之渊薮,且难得地记录了长期为高文大册所忽略的日常饮食、服用、器玩等“小道”,的确弃之可惜。那么,是否有更合适的处理办法呢?其实,从青木正儿的具体研究当中不难看出,训诂与考证并不是他唯一关心的事情。李勇与张桂丽皆曾指出,青木正儿对日常生活的兴趣,与流行于日本大正末年的“中国情趣”紧密相关(李勇61;张桂丽47)。西原大辅在《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一书中提到,所谓“中国情趣”,指的是一种“时髦新型的生活方式”,人们“通过家具、饮食和旅行来体会中国风情的异国情调”(22)。直接感受与模仿文字资料当中的生活方式与审美精神,同样是青木“名物学”不可忽视的面向之一,这一点从《华国风味》《琴棋书画》《抱樽酒话》等书题(皆为青木氏之名物研究著作)当中即可窥得,尽管他本人在《名物学序说》中对此并不强调。附于《华国风味》末尾的《陶然亭》及《花甲寿菜单》两篇文章,或可视为上述面向之集中体现,而与不能保证“物”之实存的棘手材料相发明的是,它们恰好提示了名物研究的另一切入角度——“名”。
《陶然亭》,是青木正儿虚构出来的上下两篇文字,它煞有介事地描述了一家并不存在的酒馆,不厌其烦地详细列举店内的各种陈设。最有意思的是,它收录了一份冗长的《陶然亭酒肴目录》,其中有大量颇具文思之菜名,如“豆棚闲话”“山家清供”“渔樵问答”“补天石”“煮白石”等等,并有说明附于其后,如曰喜荤者与喜素者对酌可用“渔樵问答”,“豆棚闲话”与“田家乐”可使人有鼓腹击壤的田园生活之想云云(347-48)。《花甲寿菜单》之旨趣与《陶然亭》相近,它记录的是青木正儿花甲寿宴上之饮食,菜有“瑞雪脍”“晚霞饭”“梅龙糕”等九种,酒则为“鸾凤玉涎”,其名皆为青木氏所自拟,又各附短文介绍得名由来,如此敷衍成一篇文章——显然,青木正儿在研究中华名物时,对“名”本身委实也抱有不小的兴趣。令人遗憾的是,这种兴趣并未被整合到他的“名物学”理论当中。
无独有偶,薛爱华在开展名物研究时,亦如青木正儿一般,并不刻意避开诗歌、笔记、小说等“不甚可靠”的史料,而尤为可贵的是,他为这种做法贡献了更加深入的理论思考。吴玉贵指出,薛爱华在处理此类史料时,“并没有刻意去追求史料中记载的具体物品的‘真实’与否,而是着眼于史料记载背后所反映的思想观念,以及从这种思想观念中所投射出的当时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10)。薛爱华自己则在导论中写道:“外来物品的生命在这些文字描述的资料中得到了更新和延续,形成了一种理想化的形象,有时甚至当这些物品的物质形体消失之后也同样是如此。体现在文字描述中的外来物品,最终也就成了一种柏拉图式的实体。”(30)这同样是在将人们的视线引向“名”。事实上,《撒马尔罕的金桃》这一书名,便正是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被拟定的。薛爱华称,“金桃”这一名称可以使人产生丰富的联想,如西方传说中的金苹果,以及中国传说中的仙桃,等等(28)。他强调道:
虽然这种桃子曾经是某种“真实的”存在,但是这种水果已经部分地成了一种玄虚神妙的实体。它们仅存的真实的生命是文学的和隐喻的生命。简而言之,与其说它们属于物质世界,倒不如说它们属于精神世界。(30-31)
对谱录、小说、类书等材料当中的名物记录采取搁置“物”而关注“名”之态度,在中国的古人当中其实也是一种常见做法。楼钥《白醉》一诗之小序即云: “陶内翰《清异录》⑦首载开元时高太素隐商山,起六逍遥馆,各制一铭。其三曰《冬日初出铭》,曰: ‘折胶堕指,梦想炙背。金锣腾空,映檐白醉。’余爱其言,取以名阁。”(76)古人若只需从书中撷取好名字,自不必考虑材料之真伪,而“名物学”若能将古人对名称本身的创作与欣赏纳入视野,那么来源不明的小说、类书也自有其真实性: 尽管作者不必确有其人,“物”也或许出自杜撰,但作品总有大体可以确定的问世年代,而充斥于其中的命名行为,是可以体现世风的。换言之,此类著作当中的“物”未必实,“名”却不虚,它们反映的,也是另一种真相。
四、 “好亭子名”: 名物研究与文学研究的桥梁
从青木正儿对文人生活方式的模仿,以及薛爱华对“物”之“文学生命”的关注可知,现代的名物研究,似乎总与文学有某种微妙的联系。上文提到,扬之水从事文学研究的背景,也在时时催促着她追问名物研究能为文学做什么,而对“名”的关注,同样潜藏在她的思考之中。《唐子西文录》里,有东坡轶事一则曰:
东坡赴定武,过京师,馆于城外一园子中。余时年十八,谒之。问余: “观甚书?”余云: “方读《晋书》。”卒问: “其中有甚好亭子名?”余茫然失对,始悟前辈观书用意盖如此。(446)
这则与楼钥《白醉》之小序几乎可以相互发明的轶事,曾多次被扬之水引用。在《古诗文名物新证·后序》及其改写版当中,它被用来说明诗文应当有各种各样的读法,而“只留意其中的‘好亭子名’”,也是其中一种——据2013年《中华读书报》上题为《“记取好亭子名”——扬之水谈名物研究》的一则访谈可知,这也是她最喜欢的一种读法。此外,在谈及《金瓶梅》之好处时,扬之水也借用了“好亭子名”这一说法,称“世俗生活中的种种‘好亭子名’宛转在一支为物画像的笔,不能不教人随着它去追索常常是化身在情境里、情节中的物究竟真身如何”(《合编》7)。据《物色: 金瓶梅读“物”记》一书之后序所称,《金瓶梅》乃扬之水从事名物研究之入口(213),因此,其“名物新证”之肇端,亦不能与赏“名”无涉。
然而,扬之水的名物研究最终也没有落在“名”上。同样关注日常生活的她,多年来一再强调的始终是对具体细微之“物”的关注,并希望从对“物”的了解中寻找某种系统性,寻找“一叶知秋”的契机——《辽宁日报》2017年刊发的另一篇访谈,甚至直接以《扬之水: 我读诗关注的是“物”》为题。只是,面对自己笃行多年的研究方法,扬之水似乎总有某些意难平之处: 一直未能放下“文学”二字的她指出,在自己的研究中,“文学”到底不是主角,“物色”追踪的究竟是“物”,它虽因多存写实成分而可使人窥见时代风俗,对文学来说在很多时候却终究是细枝末节,难免无关大局之讥疑。她还指出,自己唯一一点稍与文学有关的读“物”心得,是“我以为《金瓶梅》开启了从来没有过的对日常生活以及生活中诸般微细之物的描写”,称“它的文字之妙,即在于止以物事的名称排列出句式,便见出好处”,但若按她穷索“物”之原貌的路子对这些物事之名称加以深究,虽可使“文”与“物”在重新聚拢后细节历历地照亮越来越多的生活场景,却又与文学研究渐行渐远了(《物色》214-16)。
有扬之水的自述在前,他人的评介文章,也难免多从“物”入手来分析其研究之妙处。然而,“名”本身的重要性,总是在不经意间被提起: 李旻的《作为诗的物与作为物的诗》一文,是扬之水2008年出版的《终朝采蓝——古名物寻微》之序言,在这篇文章当中,李旻以日本的“茶入”为例,生动地讲述了“名”对于“物”来说不可或缺的作用。他指出,每只茶入的名字,常来自往昔的茶事,如古代的茶人为它作的一首诗;主人取茶时,客人从主人那里知道它的名字,从而得以品味它的诗与它传奇的身世,并最终从主人精心的选择和身体力行中体会对友情的期许和对人生的看法。以美国密歇根大学艺术博物馆收藏的“独寝”茶入为例: “独寝”二字,出自日本著名茶人小堀远州为其创作的一首和歌,并被他亲手题于木盒之上。李旻认为,此间的诗意恰恰寄寓在诗文与茶物微妙而特殊的关系之中: 物与诗,既难以明确显现出各自之始终,亦无法在脱离对方后仍保持自身之完整,而扭合并传递了这一切的,正是木盒上的“独寝”一名。李旻还提到,某些茶入在被西方博物馆收藏时,西人因不解诗情,常将锦囊与题签木盒都当作破旧的“包装”丢弃,而这些丢失了名字的茶人,便也一并丢失了它们的诗意与历史,以及它们承载的层层文化,变成了展厅里一只只无名的“tea caddy”(161-62)。
如果说李旻还只谈到了凝练而富有诗意的名称对诗情与物情的扭合与传递,那么张定浩的某些观点,则更加贴近普遍的“名”之本质,以及它们带来的阅读感受。他在《对具体的激情》一文当中提出,不管是一支玛瑙荷叶簪,还是一颗金累丝镶玉灯笼耳坠,“它们首先都不是作为某种艺术史和造型演变史的材料、某种考古学和历史理论的证据而存在的,它们首先就是自身,就是一个个的名”(146)。在阅读这些名称时,读者仿佛在抚览“无限的清单”,⑧而“这里面真正让普通读者震动的,倒未必是从中获得了某件饰物的鉴赏知识和某个纹样的演变历史,而可能是头脑里对于事物的某种简单固有的符号化认识被无数汹涌而来的具体名称所摧毁,随着这种摧毁所带来的,是个人词汇表的扩展,以及对于事物的重新理解,于是这种词汇表的扩展其实也可视作自我精神领域的扩展”(148)。可以说,张定浩揭示的这种阅读体验,不仅适用于扬之水的《中国古代金银首饰》一书,也适用于上文提到的那些小说、类书与谱录——他本人也指出,“那一个个具体的名,曾被人一笔一画地写出来,隐伏在旧日的典籍、小说、俗本乃至类似《天水冰山录》这样的抄家清单中”。(149)甚至,他对扬之水的文笔之赏鉴,于上述作品而言也具有某种普适性: “这样的白描文字,似易实难,因里面全然都是具体的名词和动词,又因为准确,所以并没有多少饰词和喻词存在的必要,它们始于对具体事物进行的精细研究,又经过作者的反复锤炼。”(146)扬之水称赞《金瓶梅》“止以物事的名称排列出句式,便见出好处”(《物色》215),以上数语,便恰可为之作注。
2017年,张定浩又发表了《文学与名物》一文,从“好亭子名”的轶事切入,站在现代文学的立场上,进一步讨论了名与物在文学当中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文学的基本相对性,在于使人“从观念的重重罗网中挣脱出来,重新透过坚实的万物去观看事件,并被万物和事件所观看”(66)。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单是知道这些事物抽象和普遍的名字还是远远不够的,还要知道它们在彼时彼刻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将那些被湮没的具体的名和同样被湮没的具体的物相连接,如此它们才可能复活,像密码锁的开启,咯哒一声,一个真实存在过的生活世界,而非我们带着今日眼光所以为的那个现实世界,才得以呈现。”(66)
什么是“抽象和普遍的名字”,什么又是“具体的、被唤出来的名”呢?唐宋之际,某种芜杂琐碎的名物记录开始悄然渐增,人们热衷于为寻常事物巧制“文呼”,为已有常名之物另取新名,上文提到过的《清异录》,便忠实地记录了这一风气;⑨至于在北宋兴起,在南宋自成一类的谱录,乃至《金瓶梅》《红楼梦》等热衷于名物记录的小说,则更是风气已开之后的产物了。此类作品对名物的记录,并不以训诂与考证为目的,它们与巧制“文呼”的风气一样,与其说是为了准确指称某物,不如说是出于审美与娱乐之动机。牡丹,有鹤翎红、倒晕檀心、九蕊真珠;砚之形制,有仙桃、玉台、月池;酒,有瑶池、兰芷、千日春……在牡丹、砚、酒等“类名”底下,它们提示的差异微乎其微,就算没有它们,甚至没有这些差异,人们最基本的生存与交流也不会受到影响。
然而,正是它们,能够打破“简单固有的符号化认识”。“抽象和普遍的名字”,是牡丹、砚、酒,而有心人在千百年间孜孜不倦地记录下的九蕊真珠、月池、千日春等繁冗琐碎的“无用之名”,才在当时的生活(而非生存)当中具体地被唤起。此外,张定浩还借苏轼的意见来提醒读者,应当注意“词语的自足”(65),并借金宇澄的小说来说明,“人的真实的活动与感情,需要一个具体的物的世界来安放,并通过那些物的名字来保存”,而“一切的人类,最终都是生活在沉默却有名字的物的怀抱,而非意见和观念的喧嚣中”(68)。
上述围绕“名”展开的意见,其实无不与文学相关。醉心于“物”的扬之水有意在理论层面追问名物研究应当如何与文学发生联系,一种可能的回答或许近在眼前: 通过“名”。首先,像“独寝”这样的名称,本身就是某种最短小的文学创作,它与“物”的形态、质料、功能乃至使用方式一同构筑审美体验,有时还蕴含典故,能以最凝练的方式点化与表达“物”中的诗情,将文学体验引入日常生活;其次,记录、组织与铺陈一般意义上的名称,本身便构成文学手段,它能激发特有的阅读体验,提醒人们注意并总结与之相应的鉴赏观念和方法;最后,对“名”的书写兴趣能标识出一批值得被重新审视的作品,它们此前大多长期处于边缘地位,或被视为“小道”,或与西方传入的“文学”概念格格不入,在文学史中几无地位。若将这条文学脉络清理出来,或许不仅可以为既有的文学研究带来有益的补充,还能与目前偏重于“物”的“名物学”及“物质文化研究”相辅相成,为某些尚待解决或解释的问题或现象提供新的思路。
余论: “名物学”的独立与发展
其实,把对“物”的关注转移一部分到“名”上,不仅有利于弥缝“名物学”内部存在的问题,促进该学科与文学的沟通,还会为它的独立带来更清晰的思路。李勇指出,作为一种“追本溯源的实证主义研究”,目前的“名物学”类似于考古学,它追求对事物本来面貌、状态的还原,而并不重视意义的阐释。李零亦在《奢华之色》恳谈会上指出,扬之水的研究以考古文物为出发点,更接近古器物学,尽管她更加关注器物的意境、审美品格与文化内涵,但这种器物研究层面上的进境,似乎仍可纳入既有的考古学或古器物学之框架中。针对此类质疑,扬之水曾提出以“持名找物”与“持物找名”来区分“名物学”与古器物学的设想,但这一说法未必站得住脚——且不说方法层面的细微不同是否足以标识学科间的本质差异,纯粹的“持名找物”与“持物找名”是否真实存在,首先便使人存疑: 借用日本学者的说法,上述二者指的都是以“名物隔离”为前提的“名物确当”工作,而从实际操作层面上来说,似乎很难通过单向的持此找彼来拼合“名”与“物”——在文献与实物之间往复进行寻找、比对与确认,或许才是更常见而合理的做法。
那么,“名物学”究竟何以独立呢?正如辜承尧在《青木正児とその名物学研究》一文中所言: 不应将“名物”视为一个单独的词,而应将“名”和“物”分开来理解(249): “名物学”,正是在“名”与“物”的交会处独立。考古学者陈星灿称,扬之水做了考古的工作,但在很多方面又“做到我们考古的前面去了”: 以往的考古报告只能“说出这儿有一个人,一条鱼,一只鸟”,而扬之水揭出了“背后的东西”。上述言论,不禁让人联想到扬之水对“满池娇”纹样的精彩分析——如果“名物学”只是“物”的学问,那么她的文章中也只会有零散的荷叶、鸳鸯、鸂鶒: 正是“满池娇”这一名称,为她提供了联结诗与物之枢机,让她的研究区别于传统的器物学与考古学。此外,通过第二、三节之分析可知,对“名”的关注亦与深入发展的实证主义原则相适应。综合以上种种意见与分析来看,或许可以说,在理论层面上关注“名”、重视“名”,实乃为目前的“名物学”打开新局面之良方。
注释[Notes]
① 《诗经名物新证》是扬之水的第一本名物研究著作,出版于2000年,然而据扬之水之自述可知,她在写作此书时“还只是刚刚入门”,其名物研究理论真正成形,要到2004年《古诗文名物新证》一书出版。见扬之水: 《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页。
② 侯书勇在《郭沫若名物新证研究述评》一文中即指出,将传世文献与考古发现互证之做法,早在王肃、刘杳等人以在地下发现的实物材料订正《诗》毛传、郑笺对犠尊、象尊的解释时便已出现。见侯书勇: “郭沫若名物新证研究述评”,《郭沫若学刊》1(2012): 67。
③ 要更清楚地理解所谓“古典”与“今典”,应参看《古诗文名物新证》之《后序》: “关于‘古代’的‘营造’,……它是想象与真实的混淆,理想与现实的合约,不必说,唐人的古,宋人的古,明人的古,都加入了它的当代因素,即以它的当代精神去理解去塑造既真实又虚幻的古典。不断被‘复’着的‘古’或曰被‘营造’着的‘古代’,也因此总是充满生命力和生长力。”见扬之水: 《古诗文名物新证》(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第530页。
④ 《中国伊朗编》中有“金桃”这一词条。
⑤ 此书及下文提到的《陈州牡丹记》皆参见《洛阳牡丹记(外十三种)》(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
⑥ 按: 原文如此,指的大约是凭空虚构之特点。
⑦ 五代宋初人陶榖所撰,体近类书,专录事物之新巧异名,故而青木正儿称此书为“以名物为主进行编纂的类书”。该书自宋代以来常被视为伪书,然而据今人之研究来看,将其视为可反映五代宋初社会“通性之真实”的作品似乎更加合适。
⑧ 该说法乃意大利学者翁贝托·艾柯(Umberto Eco)之书题,他在此书中以大量实例分析了人类在从古至今的作品中对清单绵延不绝的爱好。参见张定浩: “对具体的激情”,《读书》4(2015): 148。
⑨ 《唐阙史》曰: “仲尼云: ‘必也正名乎。’近世缝掖耻呼本字,南省官局则曰版图小绩,春闱秋曹;北省官位则曰紫微貂蝉,侧坡夕拜: 未尝正名其名,岂宣父之本意也?……飞龙庄宅,内园弓箭,皆得以文呼也。”见高彦休: “唐阙史”,《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阳羡生校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32-33页。“文呼”者,“文其名而呼之”也。《清异录》中相关记录甚多,如“小南强”条曰: “世宗遣使入岭,馆接者遗茉莉,文其名曰小南强。”“三无比”条曰: “钟谟嗜菠薐菜,文其名曰雨花菜,又以蒌蒿、莱菔、菠薐为三无比。”此处难以尽举。见陶榖: “清异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孔一校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7、53页。
⑩ 《奢华之色——宋元明金银器研究》是扬之水出版于2010年的著作,此书之恳谈会召开于2011年,有将近20位来自考古、文学、历史、美术等各个领域的学者在会上发言,会议记录之全文见“人文与社会”网站。下文征引的陈星灿之意见,亦发表于该恳谈会上。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陈洁: “‘记取好亭子名’——扬之水谈名物研究”,《中华读书报》,2013年1月2日,第9版。
[Chen, Jie. “On Naming Pavilions: Yang Zhi Shui’s Onomatological Studies of Things.”ChinaReadingWeekly2 Jan. 2013: 9.]
“《奢华之色》恳谈会笔录”,人文与社会网站,2011年4月14日
[“A Seminar Digest ofExtravagantColors.” Humanity and Society 14 Apr. 2011.
高慧斌: “扬之水: 我读诗关注的是‘物’”,《辽宁日报》,2017年9月3日,第3版。
[Gao, Huibin. “Yang Zhi Shui Says “I Focus on ‘Things’ When I Read Poems.”LiaoningDaily3 Sep. 2017: 3.]
高彦休: 《唐阙史》,《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阳羡生校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323-66页。
[Gao, Yanxiu.TheMissingHistoryoftheTangDynasty.ACollectionofLiterarySketchesduringtheTangandFiveDynasties. Ed. Yangxiansheng.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0. 1323-66.]
辜承尧: “青木正児とその名物学研究”,《東アジア文化交渉研究》8(2015): 247-57。
[Gu, Chengyao. “Aoki Masaru and His Onomatological Research on Things.”JournalofEastAsianCulturalInteractionStudies8 (2015): 247-57.]
侯书勇: “郭沫若名物新证研究述评”,《郭沫若学刊》1(2012): 67-71。
[Hou, Shuyong. “A Critical Review of Guo Moruo’s Onomatological Studies of things.”JournalofGuoMoruoStudies1 (2012): 67-71.]
纪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石家庄: 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
[Ji, Yun.TheGeneralCatalogueofThe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Four Treasuries. Shijiazhuang: Hebe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00.]
劳费尔: 《中国伊朗编》,林筠因译。北京: 商务印书馆,1964年。
[Laufer, Berthold.Sino-Iranica. Trans. Lin Yunyin.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1964.]
李旻: “作为诗的物与作为物的诗”,《读书》8(2008): 159-65。
[Li, Min. “Things as Poems and Poems as Things.”Dushu8 (2008): 159-65.]
李勇: “名物学与青木正儿的中国文学研究范式”,《昌吉学院学报》6(2010): 57-63。
[Li, Yong. “Onomatology of Things and the Paradigm of Aoki Masaru’s Study of Chinese Literature.”JournalofChangjiUniversity6 (2010): 57-63.]
楼钥: 《楼钥集》,顾大朋点校。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2010年。
[Lou, Yue.CollectedWorksbyLouYue. Ed. Gu Dapeng. Hangzhou: Zhejiang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2010.]
青木正儿: 《中华名物考(外一种)》,范建明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5年。
[Masaru, Aoki.OnomatologicalStudyofThingsinChina. Trans. Fan Jianming.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西原大辅: 《谷崎润一郎与东方主义——大正日本的中国幻想》,赵怡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5年。
[Nishihara, Daisuke.TanizakiJunichirōandOrientalism:JapaneseIllusionofChinaduringtheTaisyōPeriod. Trans. Zhao Yi.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5.]
欧阳修、周师厚、张邦基等: 《洛阳牡丹记(外十三种)》,王云整理校点。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2017年。
[Ouyang, Xiu, Zhou Shihou, and Zhang Bangji, et al.ARecordofPeoniesinLuoyang(withThirteenOtherWorks). Ed. Wang Yun. Shanghai: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2017.]
薛爱华: 《撒马尔罕的金桃: 唐代舶来品研究》,吴玉贵译。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
[Schafer, Edward Hetzel.TheGoldenPeachesofSamarkand:AStudyofTangExotics. Trans. Wu Yugui.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2016.]
竹内好: “‘餅’と‘餌’”,《竹内好全集(第十卷): 中国を知るために》。东京: 筑摩书房,1981年。第184-89页。
[Takeuchi, Yoshimi. “Cake and Pastry.”TheCompleteWorksofTakeuchiYoshimi:UnderstandingChina. Vol. 10. Tokyo: Chikumashobō, 1981. 184-89.]
唐庚: “唐子西文录”,《历代诗话》,强幼安述。北京: 中华书局,1981年。第441-48页。
[Tang, Geng. “Collected Works by Tang Zixi.”PoetryCommentariesacrossDynasties. Ed. Qiang Youan.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81.441-48.]
陶榖: 《清异录》,《宋元笔记小说大观》,孔一校点。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140页。
[Tao, Gu.ARecordoftheUnusualandthePeculiar.ACollectionofLiterarySketchesduringtheSongandYuanDynasties. Ed. Kong Yi.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1. 1-140.]
王晶波: “从地理博物杂记到志怪传奇——《异物志》的生成演变过程及其与古小说的关系”,《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4(1997): 60-64。
[Wang, Jingbo. “From Geographical Natural History Sketches to Records of the Peculiar and Transformations of the Marvelous: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ARecordofStrangeThingsand Its Relationship with Ancient Novels.”Journalofthe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 4 (1997): 60-64.]
王筱芸: “颠覆与建构: 另一种历史叙述的意义——评《古诗文名物新证》”,《文学评论》3(2005): 190-93。
[Wang, Xiaoyun. “Subvers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Significance of Another Historical Narrative (Book Review ofANewOnomatologicalStudyofAncientPoemsandArticles).”LiteraryReview3 (2005): 190-93.]
严绍璗: 《日本中国学史》。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
[Yan, Shaodang.AHistoryofChineseStudiesinJapan. Nanchang: Jiangx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1.]
扬之水: 《古诗文名物新证》。北京: 紫禁城出版社,2004年。
[Yangzhishui.ANewOnomatologicalStudyofAncientPoemsandArticles. Beijing: Forbidden City Publishing House, 2004.]
——: 《古诗文名物新证合编》。天津: 天津教育出版社,2012年。
[- - -.ACollectionofNewOnomatologicalStudiesofAncientPoemsandArticles. Tianjin: Tianji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2012.]
——: 《物色: 金瓶梅读“物”记》。北京: 中华书局,2018年。
[- - -.ColorsofThings:ReadingNoteson“Things”inThe Plum in the Golden Vase.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18.]
张定浩: “对具体的激情”,《读书》4(2015): 144-51。
[Zhang, Dinghao. “Passion on the Concrete.”Dushu4 (2015): 144-51.]
——: “文学与名物”,《小说评论》6(2017): 65-69。
[- - -. “Literature and Onomatology.”FictionReviews6 (2017): 65-69.]
张桂丽: “青木正儿名物学观述论——兼论名物学的独立”,《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学报》4(2015): 47-50。
[Zhang, Guili. “A Review of Aoki Masaru’s Onomatology of Things with Comments on the Autonomy of Onomatology.”JournalofChongqingUniversityofEducation4 (2015): 47-50.]
——评杜朝晖《敦煌文献名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