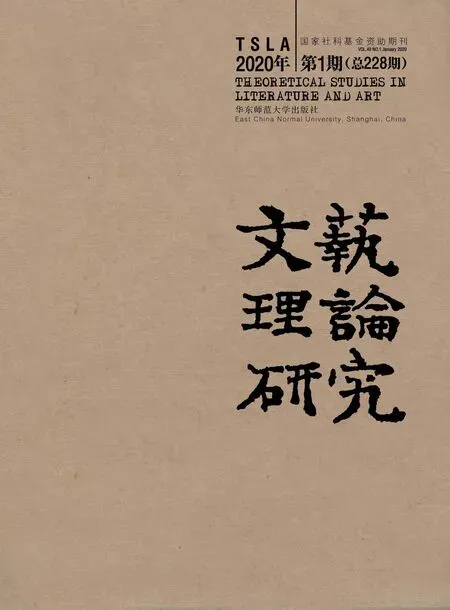叙述可靠性与文学真实性
江守义
在叙事学研究中,叙述可靠性问题一直是一个纠缠不清的问题。大多数研究者从修辞叙事学或认知叙事学的角度出发,对其进行分析,但二者的分析由于立足点不同,很难调和。①如果撇开修辞角度或认知角度的纠缠,从文学效果的角度来看叙述可靠性,它归根结底还是一个涉及文学真实性的问题。只不过,叙述可靠性针对叙事文学而言,它直接关涉的是叙事文学的真实性问题。
一
在《小说修辞学》中论述叙述者“距离的变化”时,布斯提到了叙述可靠性问题:“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亦即隐含的作者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的。”(布斯,《小说修辞学》178)布斯的结论,是在反对现代小说讲究展示和客观性的四个“普遍规律”的基础之上得出的,这意味着,即使是强调展示和客观性的现代小说,不仅无法忽视叙述者的声音,也无法忽视隐含作者的存在,“所有的作者直接叙述也好,间接言说也罢,都是以隐含的形式登场,作为‘处于一切小说体验之中心’的读者的对话伙伴”(布斯,《修辞的复兴》8)。叙述者声音是否可靠,主要看它和隐含作者的意图是否一致,二者一致则为叙述可靠,二者不一致则为叙述不可靠。这看似一个叙事研究的技术问题,但考虑到布斯的研究背景,不难发现技术问题背后还涉及文学观念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初,美国是新批评的天下,新批评重视文本的技术分析,对文本背后的意义相对忽视,布斯对此有所警觉,他重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修辞学传统,采取权宜之计。一方面,修辞讲究修辞格,这与新批评重视的文本“细读”相契合;另一方面,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经典定义,修辞术是“一种能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找出可能的说服方式的功能”(亚里士多德,《修辞学》145),修辞的最终目的是劝别人相信自己说的话,修辞讲究“劝说”效果。从修辞的“劝说”效果出发,柏拉图认为诗人通过修辞将某个事物吹得天花乱坠,用修辞来蛊惑人心,修辞使某个事物听起来像真的一样,但其真实性值得怀疑;亚里士多德认为修辞不仅仅是一种技巧,还应该展示一种劝说的威力,从而将修辞学上升到一种伦理的高度,成为“古希腊第一门知识学科”(《修辞的复兴》4)。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他们表面上观点对立的背后,都意识到修辞的伦理功能。在布斯那里,他显然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观点,并将修辞的伦理力量发挥到极致:“修辞学是发掘正当信仰并在共同话语中改善这些信仰的艺术。”(5)这样看来,布斯从修辞学的角度提出叙述可靠性问题,最终是为其文学的伦理之维服务的。他的“叙述可靠性”是作为“小说中作者的声音”出现的,“作者的声音”是小说和读者交流的重要基础,“小说只有作为某种可以交流的东西才得以存在”,交流的最终目的是让小说中“高人一等的道德”产生影响(《小说修辞学》436—41)。而文学的伦理维度,早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就与文学的真实性联系在一起。《诗学》主张:“喜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坏的人,悲剧总是摹仿比我们今天的人好的人。”(25)诗人通过描述“可能发生的事情”,让诗比历史更有“普遍性”,这里的“普遍性”是因为“可能发生的事情”有其“可然律或必然律”,所以是“可信的”(45),而历史上某些“已发生的事不合乎可然律,是不可能的事”(47),因而是不可信的,换言之,诗比历史更真实。布斯始终强调文学的伦理力量,也是基于文学真实性基础上的伦理力量。
但布斯对文学真实性的用心被其表面的叙述可靠性所掩盖,加上后来的叙事学研究过于关注文本,让叙述可靠性成为一个众说纷纭的叙事学问题,似乎和叙事文学的真实性没有关系。无论是对叙述可靠性的修辞学阐释还是对叙述可靠性的认知性解读,都将焦点放在“可靠性”上。但“可靠性”归根结底又与“真实性”不无关系。从修辞学阐释看,无论布斯还是费伦,都强调隐含作者的作用,至于叙述是否可靠,是修辞策略的结果。所谓可靠不可靠,就是说叙述者的叙述是否能让人相信它是“真的”,从而接受它,叙述可靠性由此成为与文学真实性密切相关的一种手段。布斯的观点很明确: 当叙述者与隐含作者一致时,叙述可靠,反之则不可靠。布斯不像后来的诸多叙事学者用心于不可靠叙述,而是对可靠叙述和不可靠叙述一视同仁。如果说,布斯对不可靠叙述的讨论引发了叙事学中一个长久被关注的话题,他对可靠叙述的关注则体现出他对文学伦理价值和文学真实性传统的继承。布斯始终关注文学的修辞及其伦理功能,它们也是保障文学真实性的条件。要增强文学真实性,叙述可靠性显然是一个重要途径。《小说修辞学》第七章专谈“可靠议论”,列举了提供事实、塑造信念等可靠叙述的方法,在第八章和第九章中也多次提及“可靠叙述者”的具体表现,这和布斯反对“客观作者”的宗旨一致,他认为隐含作者总是会通过叙述者来表达他的意图,叙述者要想传达隐含作者的意图,简便的做法就是和隐含作者保持一致,通过可靠叙述,隐含作者的意图得以传达,文学真实性在叙述层面就可以获得基本保障。或许由于叙述者和作者的“一致”比较直白,可靠叙述没有多少深入挖掘的空间,文学真实性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布斯以后的叙事学家讨论得最多的是不可靠叙述。作为布斯的学生,詹姆斯·费伦基本上继承了老师的叙述可靠性的修辞学观点,但有所发展。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从叙述者和叙述内容的关系入手,将布斯对不可靠叙述的分析从两个维度(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推进到三个维度(增加了知识/感知轴);其二,从叙述者和隐含读者的关系入手,将不可靠性分为“疏远型不可靠”和“契约型不可靠”;其三,对叙述可靠性的谱段分析。就第一个方面看,无论是布斯已经关注的事实/事件轴、伦理/评价轴,还是费伦后来明确的知识/感知轴,都强调了叙述者由于错误或不充分导致的不可靠[“误报,误读,误评,不充分报道,不充分解读,不充分评价”(赫尔曼主编42)],这些不可靠叙述让作品的真实性打了折扣。就第二个方面看,不可靠叙述既可以疏远读者和叙述者的距离,让读者觉得叙述不可靠,也可以拉近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让读者觉得叙述可靠;同样是不可靠叙述,却可以造成不同的真实性感觉,这是费伦对叙述可靠性的新发现。第三个方面是从人物叙述产生的情感和伦理效果出发,在“疏远到亲近之间的一个谱段上”,从左到右,亲近感逐渐增强,依次有六个段位: 错误/不充分报道、错误/不充分评价、错误/不充分阐释、受限制的叙述、交汇叙述、面具叙述,左边三个是不可靠叙述,右边三个是可靠叙述(费伦,“可靠、不可靠”87—92),暗含的意思是,随着亲近感的增强,叙述带来的真实性也随之增强。这也意味着,布斯所说的可靠与不可靠,在费伦这里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随着叙事进程发生变化的。
叙述可靠性的修辞学阐释着眼于隐含作者的修辞策略,从读者认知的角度看,这过于晦涩,因为读者难以了解隐含作者的真实意图。雅克比和A·纽宁由此开启了对叙述可靠性的认知学解读。雅克比从隐含作者的批判入手,认为叙述可靠性不是隐含作者的修辞产物,而是一种“阅读假设”,是“读者依据相关关系临时归属或提取的一种特征”(Phelan等,《当代叙事理论》104),叙述可靠性有赖于读者的“视角机制”,“读者能够将事实、价值观、审美观等方面的各种不一致性解释成叙述者与作者不协调的症候”(106),虽然叙述可靠性最终的依据是叙述者与隐含作者是否一致,但判断二者是否一致又由读者的“假设”来决定。读者从自己的视角出发,心目中形成一个“假设的作者的规范和目标”(121),以此来衡量叙述是否可靠。读者究竟如何来形成自己的“视角机制”,文学真实性的考量可以说是一个潜在的前提。读者阅读一部叙事作品,在理解叙述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想知道叙述者的叙述背后所隐藏的作者意图,作者意图和叙述者叙述的结合成功与否,是作品真实性的基本保障。在这样的前提下,读者可以说是以文学真实性的要求为指引,来形成自己的视角机制。读者相信从自己的视角机制出发,可以对作品加以正确解读,可以发现该作品之所以有文学真实性的内在原因。但问题在于,由于读者的个性化和随意化,如何保证某个读者的视角机制有问题或没有问题,都是很难说清的事情。或许为了解决认知叙事学的这一根本问题,A·纽宁从两个方面对此加以解决。一是就小说与现实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布斯认为小说中的描写最终作用于现实的伦理世界,小说之真指向伦理之善;纽宁则“把小说理解为读者对现实的具体理解”(Hansen238),小说之真缘于读者之思。这样一来,读者的理解决定小说的真实性就有了理论上的支持。二是将个体读者与“框架”联系起来。纽宁援引卡勒的“归化”思想,认为可靠性依赖于两个方面的“归化”,一个是指代框架的归化,另一个是文类框架的归化。②这样,个体读者的主观性和随意性就消融于有公约性的“框架”之中,“框架”的公约性决定了它的可信度,读者可以以“框架”为标准来理解叙述可靠性。这样一来,纽宁的核心问题可归结为“框架”。就指代框架而言,它依据的假设首先是“文本指代真实世界或至少是与所谓的真实世界兼容,使我们能够按照叙述者的行为与真实世界的规范之间的关系来决定可靠性”(Phelan等,《当代叙事理论指南》92),真实世界的规范让作品看起来是否像真的一样,是文学真实性的基本要求,用真实世界的规范来衡量可靠性,也可以理解为将文学真实性作为检验文学可靠性的前提;就文类框架而言,“文学的一般惯例、文学体裁的程式和模式、文本间的参照框架”以及“作品本身建立的结构和规范”都可以作为叙述可靠性的依据(93),同样的叙述在不同的文类规约下,其可靠性会有所不同,读者阅读一个现实主义角度下不真实的故事,在科幻叙事中可能会被认为是真实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一样,都受到文类规约的约束。综观纽宁对框架的理解,不难发现他是以现实社会的价值取向作为框架的基础,文本叙述是否可靠,与读者对作品真实性的感受相伴相随。
但纽宁知道,这个看似“标准”的框架是复杂多变的,因为“按照这一个批评家的道德规范观念去衡量属于非常可靠的叙述者,可能在另一些人眼里是相当不可靠的”(Phelan等,《当代叙事理论指南》91),因此完全用读者的框架来衡量叙述可靠性或许是不可靠的。为此,他接受了费伦“叙事交流”的观点,即叙述可靠性“源于作者(无论隐含与否)、文本现象和读者反应之间循环互动的关系”(100),力图将认知方法和修辞方法综合起来,得出结论:“决定一个叙述者是否可靠,最终要看作品本身建立的、作者动因设计的结构和规范以及读者的知识、心理状况和价值规范系统。”(100)对纽宁的综合,申丹认为是徒劳无功的,因为修辞方法和认知方法的阅读位置难以调和,前者从理想读者出发,后者从真实读者出发,“两者相互之间的排他性”(申丹133),让任何综合两者的努力注定徒劳无功。③但纽宁的综合带来一个启发: 无论是从修辞角度还是认知角度,可靠性都离不开读者这一维度,而真实性则正是从读者角度加以提炼的结果,叙述可靠性与文学真实性之间应该有内在关联。具体说来,无论是修辞方法所主张的理想读者还是认知方法所主张的真实读者,只是具体技术分析层面的问题,它们都属于文学真实性所出发的读者之维。换言之,叙述可靠性是具体的文本分析,文学真实性则是总体的阅读感受,前者只注重文本体验,后者还兼顾到(文本之外的)文学理想。
二
由于叙事学注重从文本出发,对叙述可靠性的分析也立足于文本,真实作者基本上被排除在外。但在实际创作中,真实作者的动机和处境对创作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真实作者的参与,让主要依靠隐含作者修辞或读者认知的叙述可靠性出现了新的情况,这些新情况的出现让文学真实性又表现出多样性。
从修辞的角度看,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一致时,叙述是可靠的,不一致则不可靠,叙述可靠性看起来非常清楚。但当真实作者参与进来后,情况就复杂多了。这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有突出的体现,原因在于古典小说的真实作者有强烈的说教意图。大致有三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隐含作者和叙述者一致,但真实作者创作意图的强烈干预,让叙述显得前后矛盾,而作品总体上又显示出内在的真实性。在《前七国孙庞演义》中,孙膑在学成法术后,由于注重同门情谊,被庞涓玩弄于股掌之间而毫无觉察,即使刖足被囚也仍然相信庞涓,但当别人告诉他一切都是庞涓对他的陷害后,孙膑突然间像换了一个人,他不仅洞悉庞涓一切行为的意图,甚至在庞涓还没有采取行动时,他也能借助自己的法术知晓庞涓将要采取的行动。这样明显的矛盾在小说的叙述情境中却显得非常自然,隐含作者和叙述者并没有产生冲突。但同样是身怀法术的孙膑,前后反差如此巨大,其叙述的可靠性显然是个问题。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况,主要原因就在于真实作者写“孙庞演义”的故事不是为了展示他们之间的较量过程,而是通过较量显示不同人物身上的道德品质和“善恶有报”的说教目的。孙膑的表现前后不一,让叙述显得不可靠,但孙膑始终又是“怀仁尚义”的,小说整体上并没有违背文学真实性的要求。第二种情况,是叙述者和隐含作者不一致,但由于真实作者的介入,这种不一致得到消解,叙述并没有让人产生不可靠的印象,但真实作者明显的价值取向让文学真实性打了折扣。《梼杌闲评》通过魏忠贤的故事来“斥奸扬义”,但在叙述过程中,魏忠贤发迹之前多有“义举”,即使在发迹之后,虽然恶迹斑斑,但对待自己人很有人情味,他和客印月的感情纠葛更让小说透露出浓厚的世情色彩,叙述者还通过小说的果报结构,让魏忠贤等人的恶行成为复前世之仇的结果,这一切让魏忠贤在叙述者看来并不那么可恶,这和隐含作者显然不一致。即使魏忠贤等人在正文的叙述中并没有什么奸恶行为,回目中却不时出现的“斥奸”“大奸”“劾奸”“媚奸”等反复提示,显示出隐含作者先入为主的鲜明倾向。隐含作者和叙述者的不一致,并没有导致叙述不可靠,因为真实作者在一开始的“总论”中就明确了本书“写一个小小阉奴,造出无端罪恶”(《梼杌闲评》2),无论叙述者怎么将魏忠贤等人看作常人,真实作者在写作前的盖棺论定让所有的叙述都笼罩在隐含作者的倾向之中,即使叙述者给魏忠贤等人以理解,但他们的行为早已被认定是“罪恶”的,他们都是梼杌(怪兽),叙述者的叙述成为这些梼杌罪恶的记录,叙述者和隐含作者的不一致被真实作者强扭为一致。这种“强扭”虽然消除了叙述不可靠,却让小说的文学真实性显得模糊。一方面,魏忠贤等人的罪恶是真实的,另一方面,魏忠贤和客印月等人的感情也是真实的,对恶人的抨击和对恶人的理解熔于一炉,再加上整个故事被纳入一个因果报应的大循环框架之中,小说整体上给人呈现出一种万事皆休的虚无感。对写梼杌的作品而言,这种虚无感让读者觉得故事亦真亦假。第三种情况则非常复杂,是真实作者出于某种目的,对真实的故事加以篡改,虚构历史,让叙述历史的故事成为一种“戏说”,在中国古代强大的史传传统中,这样的叙述,虽然隐含作者和叙述者高度一致,但所叙述的故事显然是不可靠的。叙述一个不可靠的故事,对真实作者而言,他可以将其看作游戏之作,只要故事本身经得起逻辑上的推敲,能传达某种人类共有的经验,“戏说”历史的虚构既能是可靠的叙述,也能显示出文学真实性。④他也可以以史家自居,用自己的“戏说”来匡正历史,如果他的“戏说”偏离历史太远,只能被认为是不真实的。酉阳野史编《三国志后传》就体现出这种复杂性。一方面,他编《三国志后传》,是对《三国演义》的结局不满,“是书之编[……]思欲显耀前忠,非借刘汉则不能以显扬后世,以泄万世苍生之大愤”(酉阳野史,“引”)。就这一点看,小说是成功的,其人物刻画、情节布局、结构安排,比单纯叙述同一段历史的《东西晋演义》要出色得多,很好地体现了“仁”在王朝建立和统治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叙述是可靠的,也有其文学真实性,体现了亚里士多德“诗比历史更真实”的思想。⑤另一方面,他有感于陈寿《三国志》“正统未明,权衡未确,其间进退与夺,不无谬戾”(酉阳野史,“序”),似乎他编的《后传》就能弥补这些不足。《三国志》以曹魏为正统,陈寿作为史家,以追求真实为第一要务,“质直”成为《三国志》的显著特色,“质直”的内涵大致包括“内容上力求其真,体例上力求严谨,叙事上力求简要,语言上力求朴实”(周国林229)。相较之下,《后传》中某些重要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杜撰,让稍微了解历史的人都知道,其叙述不可靠。即使是关于历史的文学叙事,历史本身的叙述不可靠,也会影响到其文学真实性。
从认知的角度看,读者对真实作者及其创作状态的了解,直接影响到他对作品叙述可靠性及文学真实性的判断。雅克比从认知角度展开研究时,提出了不可靠叙事的五种机制,最后一种叫“生成机制”,“它将虚构的怪异性和不一致性归于文本的生产。只要存在这些问题,就往往看成作者的问题(譬如踌躇不决、疏忽大意或意识形态狂热)”(Phelan等,《当代叙事理论指南》106—107),这里所说的作者显然指真实作者。真实作者创作时的状况与文本最后的定稿息息相关,很多作家在谈自己的创作经验时都提到反复修改。马尔克斯说自己写《家长的没落》时,1962年写了三百页的初稿,修改时只剩下主人公的名字,1968年重新写的时候,写了半年又卡住了,因为主人公“品格方面的某些特征写得不太清楚”,后来在海明威作序的描写非洲大象的书中找到了灵感,用大象的某些特性来写主人公的品格(马尔克斯 门多萨45)。马尔克斯如此精心写作,无非是想让自己的叙述显得真实可靠,增强故事的真实性。虽然他的作品被公认为“魔幻现实主义”,他本人却坚持认为自己所写的一切“没有任何一行字不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上的”(48)。
真实作者的创作状况除修改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其创作动机。作家具体的创作动机固然是五花八门,但不妨概括为三种: 一是为自己写作,二是为普通读者写作,三是为知音写作。布斯曾列举了“真正的艺术家只为自己写作”的诸多情形(《小说修辞学》101—102),但布斯对此并不认同,他援引莫里亚克的话来表明自己的立场:“一个使你相信他只为自己写作和他不关心是否有人听他的作者,是个吹牛家,不是在自欺,就是在欺人。”(100)事实上,完全为自己写作的作家是极其罕见的。但写作时考虑到读者需求则是普遍存在的,福特甚至认为创作技巧也来自想象中的读者期待:“你必须常常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你的读者身上。这就构成了技巧!”(99)突出的表现是,有些小说采取了开放式的结尾,将故事的结局留给读者来完成,如斯托克顿的《美女还是老虎》。公主暗示情人选择藏有老虎的门还是藏有美女的门,取决于公主对情人的爱恋和对门后美女的嫉妒谁占上风,短短的小说却将结尾抛给读者:“人们无法轻易揣测公主的决定,我也不能擅自回答这个问题。因此,我将问题留给你们: 到底谁走出了那扇门——美女还是老虎?”(斯托克顿43)至于为知音写作,是作家为能理解自己的人写作,马尔克斯曾宣称他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的几个朋友(博尔赫斯5),马尔克斯心目中的朋友不妨看作知音,知音可作为特定读者而存在。综观作家的三种动机,不论作家为谁写作,从认知角度看,作家创作一定要考虑到读者,“需要在读者作者双方心灵之间形成一种艺术上的和谐平衡关系”,优秀的作家集“讲故事的人,教育家和魔法师”于一身,他可以创造自己的读者(纳博科夫89—91)。为了取信于读者,作者就要在两方面下功夫: 一是让叙述者的局部叙述经得起推敲,尽量增强叙述可靠性;二是提高小说的逼真性,让小说读起来像真的一样,这往往借助生动的场面来完成,“对读者来说,除非作者尽可能使得场面生动,否则就没有逼真的东西,而正是为了读者,作者才进行选择,以使这个场面尽可能地打动人”(《小说修辞学》119—20)。
真实作者的人品和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影响到读者对其叙述可靠性和作品真实性的判断。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维·苏·奈保尔的有些作品带有半自传性质,《抵达之谜》把自我身世的迷茫和寻找镶嵌在衰败的乡村场景之中(项静 第3版),既写了当地人的变化,也穿插了自己的写作历程和外出旅行时的心情记录,给人以忧伤的回味。当人们了解到奈保尔几十年来冷落妻子、虐待情人等种种恶迹时,作品中带有自传性的叙述就让人产生疑问: 即使这部分叙述是真实的,也只是有选择的部分真实。虽然读者不能苛求作家在作品中如实展现自己,但在读过《世事如斯: 奈保尔传》的读者看来,传记中的奈保尔形象和《抵达之谜》中“我”的形象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反差,让人有理由怀疑《抵达之谜》中涉及作者自身的叙述是否真的可靠。奇怪的是,或许由于奈保尔的文学成就有目共睹,即使《抵达之谜》中的部分叙述是否可靠值得怀疑,却并不妨碍它成为一部具有真实性的作品。对照现实,其部分叙述不可靠,但作为小说,它还是显示出真实性,尤其是情感的真实性。
从认知的角度看真实作者,在非虚构叙事中有突出的体现。非虚构叙事的基本要求是作家要实录,在此基础上还要做到“内容的真实性”和“呈现的客观性”(龚举善47),但自布斯以来,就证明了文学中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呈现的客观性”,任何呈现都是作者有意选择的结果,这意味着,即使是真实的内容,由于不同的呈现方式,也会给“非虚构”叙事带来不同的面貌,一些新闻报道的倾向性压倒了客观性就是证明。读者如何看待“非虚构”叙事的真实作者,与读者如何解读叙事有关。伊格尔顿说:“一部文稿可能开始时作为历史或哲学,以后又归入文学;或开始时可能作为文学,以后却因其在考古学方面的重要性而受到重视[……]重要的可能不是你来自何处,而是人们如何看待你。”(11)伊格尔顿虽然不是针对“非虚构”叙事而言的,但他的话对“非虚构”叙事同样有效。对一个“非虚构”叙事的作者来说,他从事“非虚构”一定有其动机,既然有动机,他就“不仅仅是叙述,他也解释[……]总有一种为了解释而去选择(史料)的倾向——去选择,更甚或是去捏造”(谢尔斯顿20)。这样一来,读者就会怀疑“非虚构”叙事是否客观真实,“非虚构”叙事的可靠性就成为问题。写过《巴金传》的陈思和对此感触很深:“无论是作者所要努力的还是读者所期望的目标——刻画出一个真实的传主形象,都既是一种渴望,也是一种奢望[……]因为生命的真实是由它所发生的全部细节构成的,而当这些细节本身已经随着时光消失得无影无踪[……]要用文字去‘再现’它的真实又未尝不是天真的神话?”(陈思和1)至于一人多传所显示出不同的传主面貌,自传中为传主辩解或“为本人讳”的意图,⑥在读者看来,都有理由怀疑“非虚构”叙事是否真的可靠。20世纪30年代的沈从文出于真诚的朋友之情,用《记丁玲》写了他心目中真实的丁玲,来纪念误以为已经遇害的朋友,在80年代却遭到丁玲本人的抨击,认为是对她的污蔑之词,二人为此反目成仇。沈从文认为他的传记是真实的,丁玲则认为很多细节不可靠。“非虚构”文学的真实性和可靠性之间的矛盾在此得到突出的表现。
三
上文的分析透露出一点: 无论从修辞角度还是认知角度看,叙述可靠性和文学真实性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尽管它们之间紧密相关。一般说来,叙述可靠性容易提高文学真实性,但由于叙述可靠性主要着眼于具体的叙事策略层面,文学真实性则着眼于宏观的阅读效果层面,二者又可以不一致。不一致的情形无非两种: 叙述可靠但给人感觉不真实,叙述不可靠但给人感觉真实。
叙述可靠的基本前提是叙述的客观性,如何保持叙述的客观性?最好的办法是对话式的实录或对事物的逼真描写。叙述与现实之间的高度一致性往往是文学真实性的重要基础,但文学真实性并不仅仅是对现实的摹仿或复制,更重要的是维特根斯坦所说的“逻辑形式”的相似性,同时,它还要求叙述者在作品中表达出某种情感倾向,使作品在可能世界中成为生活真实和情感真实的统一体。从生活真实和情感真实来看,实录、描写与它们之间都有一定的距离。首先,局部的实录固然是可靠的,但由于其局部性,有时难以发现生活的内在逻辑,无法完成“逻辑形式”的相似性。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中提出“图式表示”理论,其要义是“在描绘性图式与它所描绘的东西之间有种相同的逻辑形式”(朱立元 王文英61)。局部的实录发现不了生活的内在逻辑,自然也无法在作品中“图式”出来,文学真实性由此失去根基。其次,对事物的逼真描写是可靠的,也符合“逻辑形式”的要求,但如果只单纯地描写事物而没有在事物上寄托情感,也无法达到文学真实性的要求。法国新小说派有对事物的精细描写,如《橡皮》对番茄的描写、《弗兰德公路》对赛马场面的描写,都只是为描写而描写,删除它们对作品似乎也没什么影响,可靠性描写与文学真实性之间几乎没有关系。如果通篇作品都充斥这样的精细刻画,就会挤压乃至排斥叙述者的情感流露,反而会影响到文学真实性。从新小说派的作品中,我们很难看出融生活真实与情感真实为一体的文学真实。虽然新小说派有自己的理解,他们要做的就是反对巴尔扎克式的文学世界,“制造出一个更实体、更直观的世界,以代替现有的这种充满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世界”(柳鸣九编63),但一部排斥“心理的、社会的和功能意义”的作品,能有文学真实性可言吗?再次,流水账式的记录是可靠的,但无法给作品带来文学真实性。在后现代小说中,不乏这类作品,加斯《国土中心的中心》可为代表。小说共30章,每章一个标题,标题之间既没有空间布局上的联系,也没有情节逻辑上的联系,整部小说很难串成一个整体,就每个标题下面的内容看,无法说其叙述不可靠,但整部作品则毫无真实性可言。或许如塞奥·德汉所言,“加斯的故事中,什么也无法‘聚合起来’: 的确无情节,无主题,无人物。故事的惟一兴趣想必是在语言本身了”(胡全生95)。显然,文学真实性不能依赖于“无主题”的语言游戏。
叙述可靠性也可以是情感上的可靠性,包括叙述的感情基调和倾向性的评论,它既通过情感和事件的一致来“塑造信念”(《小说修辞学》198),“升华事件的意义”(218),增强文学的真实性,也可以通过情感和事件之间的不协调来削弱文学的真实性。情感的可靠性带来读者感知上的不真实,大致有以下情形: 其一,在叙述的不同阶段,叙述者的情感发生了变化,甚至前后出现抵触。这不是说叙述者随着事件的发展变化而调整自己的情感状态,而是说叙述者在同一小说中没有基本的情感取向。从每个阶段的事件看,叙述者的情感是可靠的,但从整个作品看,叙述者的情感和事件又不尽一致,让作品显得不那么真实。福楼拜的《圣朱利安传奇》叙述了朱利安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最终成为圣徒的故事(福楼拜17—48)。叙述者的情感随着朱利安人生轨迹的变化而随之变化,对他幼年的聪慧流露出赞许,对他打猎训练时的勇敢和嗜杀则是赞许和担忧并存,对他为逃避杀害父母的诅咒而外出建功立业又大加赞赏,对他误杀父母表示同情,对他离家苦行修炼又竭力推崇,就每个阶段的叙述看,叙述者的感情与人物行为是一致的。但从整个作品看,叙述者没有处理好各个阶段之间的联系,让人物的行为在不少时候显得很突兀,朱利安最后成为医院牧师在此前的叙述中更是没一点征兆;小说最后的情感基调固然是一种宗教情怀,但小说主体则是朱利安立志成为圣徒前的反宗教行为,加上叙述者没有否定他的这些行为,这就让小说的宗教情怀显得不那么自然。即使读者相信每个传奇故事的叙述是可靠的,但由于传奇人物自身的不统一,小说的真实性还是让人怀疑。其二,故事流露出的情感姿态和叙述者对故事的评论所显示的情感不一致,故事的叙述是可靠的,故事所显示的情感是可信的,叙述者的评论也是真诚的,故事和评论之间却形成矛盾,“劝百讽一”式的作品往往如此。此外,当一些评论由故事本身生发开来而发表浮泛的感慨时,也可以造成这种矛盾,让作品整体上显得不够真实。许尧佐的《柳氏传》叙述的是诗人韩翊与柳氏在动乱年代里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从叙述看,叙述者对柳氏和韩翊是怀抱着同情和理解的,但最后的议论却说柳氏是“志防闲而不克者”,更由此引申,发出“不入于正[……]盖所偶然也”的感慨(张友鹤24)。叙述者的感慨可以说与故事本身没什么关系,但从当时的正统观念出发,这样的感慨显然是秉持通行的伦理准则。对照故事中流露出来的同情和评论中的倾向,可以说是一个卫道士在叙述一个悖道的爱情故事,矛盾感情的并存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其三,叙述者的情感始终一致,但所叙述的前后不同的事件却反差很大,一般人是不会采取同一种情感来对待反差极大的事件的,叙述者对事件的叙述和情感态度固然是可靠的,但整个作品却让人产生疑问: 面对反差明显的事件,叙述者保持始终如一的情感实在没有理由,作品的真实性由此大打折扣。《甘泽谣·圆观》中的圆观知晓未来,叙述者以崇敬之情叙述他的故事,他在自己托生这一天和李源相约十二年后在杭州天竺寺相见,见面后又告诉李源“与公殊途,慎勿相近[……]勤修不堕,即遂相见”(李昉3090),说完便吟歌而去。叙述者始终以对待得道高人的态度来对待圆观,但圆观离开后,小说就匆促地交代李源五年后就死了,既没有说他是否勤修,也没有提他们再次相见。圆观知晓未来的神通和故事的结局实在反差太大,但叙述者始终对圆观怀有赞赏崇敬之情,实在不合情理。即使是“传奇”,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不值得追究,但故事中叙述者的情感姿态却让人怀疑,这自然会削弱该作品的文学真实性。
和可靠叙述削弱文学真实性相比,不可靠叙述导致文学真实性的情况更为复杂。其一,人物内心和外在表现不一致显示出叙述的不可靠,反而增强了作品的文学真实性。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中的马拉德夫人患有心脏病,在得知丈夫死讯后,外表悲戚,实则内心欢欣,觉得自己终于获得了自由,她装出来的悲伤和号啕大哭显然是在做戏,她躲在房间里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才是她真实的想法;她从房间里出来后不久,丈夫突然回来了,她惊吓而死。人们最终认定她“喜极而亡”(肖邦24)显然是不可靠的,但这种认定非常符合当时的境况。一小时内发生的戏剧性故事非常真实地反映了特定环境下的人物心理,也揭示出生活中的冰山一角,实在是短篇小说中的佳作。其二,由第一人称视角导致的叙述不可靠,这种不可靠只是隐含作者的叙述策略,它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增强了作品的文学真实性。通常从低能儿、儿童等视角形成的叙述往往有不可靠的嫌疑,威廉·里干在《流浪汉、疯子、弃儿、小丑: 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者》中认为一些身份、智力特殊者的叙述往往是不可靠叙述。第一人称的实质是选择某种特定的眼光和某种价值观来进行叙述,由于其视角的局限或价值观取向造成作品的叙述和读者认识之间的差别,其叙述容易被认定为不可靠叙述,如里干所言:“第一人称叙述至少总有可能是不可靠的。”(Riggan19)《哈克贝利·芬历险记》中的哈克贝利通过儿童的视角讲述自己冒险的故事,他的有些讲述显然违背了事实,比如说他认为自己是邪恶的,但作者显然却在背后“默不作声地赞扬他的美德”(《小说修辞学》179),作品正是通过儿童视角写出了社会真相,作者对社会众生相和叙述者的情感态度与哈克贝利的叙述有机地融为一体。《长日留痕》虽然是正常人的视角,但史蒂文斯管家身份的局限让他认不清真相,他对达林顿勋爵的叙述和事实正好相反,他的叙述固然不可靠,但作品正借此形象地展示了他的忠诚和落寞,写出了特定历史阶段英国管家的内心世界和可叹的人生经历。其三,全知视角下叙述者的叙述和事实不一致造成的不可靠,主要有两种情况: 或是叙述者对人物的评价与人物的实际情况不一致,或是叙述者对事实的报道不够充分。就前者看,叙述者对人物有一定的倾向性,这种倾向性与人物的表现不太吻合,叙述者对人物的态度和人物自身的表现之间形成的张力,反而增强了人物的真实性。《红楼梦》中的王夫人,叙述者说她“宽仁慈厚”(曹雪芹 高鹗323),但她却逼死金钏儿,叙述者说她“天真烂漫”“喜怒出于心臆”(837),其实却非常虚伪,且工于心计。叙述者的评价和王夫人行为之间的矛盾,让读者深刻地理解王夫人表面上给人的印象(如叙述者所说)和实际为人之间的差别,写活了人物。就后者看,叙述者有意的省略让叙述由于不充分而显得不那么可靠,但读者仔细推敲后会发现正是省略中让人遐想之处回味无穷。沈从文《阿黑小史》最后,五明由于失去阿黑,由正常人变成“颠子”,但阿黑究竟为什么不见了,小说却留下了空白。叙述者由于没有充分报道事实而让人产生疑问: 从小青梅竹马又真心相爱的两个人怎么能突然分离?但这样的疑问在五明成为“颠子”的映衬下,反而让人唏嘘不已,阿黑是嫁给别人,还是死了?单纯质朴的爱情为什么会最终夭折?这些疑问让人关注到爱情和现实之间的反差,增强了文学的真实性。其四,全知视角叙述者的价值体系有问题。一般读者在阅读时,会遵守社会约定俗成的法则,尤其是在伦理道德方面,所以有人提出叙事中需要恪守“叙事道德底线”(王成军125),一旦叙述者突破叙述的道德底线,其叙述便有可能被认为是不可靠叙述。余华的《现实一种》,写因小孩的玩耍而引发的兄弟之间血淋淋的打杀事件,并细致地渲染血淋淋的场面,实在是突破了“叙事道德底线”,其叙述可靠性值得怀疑。对有特殊经历的人来说,或许会认为其叙述揭示了隐藏在人性深处的恶的一面;但对大多数人来说,这样的叙述是不真实的。换句话说,这种叙述不可靠带了模棱两可的文学真实性。其五,叙述的真幻交织造成不可靠,这种不可靠和前几种叙述不可靠不同,在叙述的过程中,叙述者就对自己的叙述表示怀疑,叙述者的自我怀疑促使读者在真实和虚幻的交织中去复原故事,在复原过程中体验到某种真实。加尔多斯的《电车上的小说》,将在电车里与人交谈、看报、做梦得到的信息,和电车中一些人的实际举动有机结合起来,在叙述者脑海中构成了一个伯爵夫人被谋杀的故事。在叙述过程中,叙述者时而清醒,时而迷糊,有时觉得只是“脑海里编造的故事”,有时却似乎成为“真真切切的事实”(加尔多斯196),但最终认识到这是一种“真正的精神迷醉,是一种暂时的精神失常”(210),意识到自己的叙述是不可靠的。但这个故事对于读者却充满诱惑,不仅幻境和现实的巧合让人惊奇,那种将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结合起来思考的现象在实际生活中也屡见不鲜,叙述者的那种亦真亦幻的体验是人类共有的一种精神状态,它无疑是真实的。
可靠的叙述未必能带来文学真实,不可靠的叙述也可以带来文学真实,这固然是叙述可靠性和文学真实性之间关系复杂性的体现。但通常情况下,叙述可靠容易带来文学真实,反之亦然。如果从历史的角度来衡量“通常情况下”二者之间的一致性,叙述可靠性和文学真实性又呈现出另一种复杂性。在叙述可靠性研究的历史上,认知叙事学曾引导了不可靠叙述研究的“历史文化转向”,茨维克认为,既然对于叙述者不可靠性的判断涉及阐释选择和阐释策略,叙述者的不可靠性就会随着历史文化的变化而发生改变,因而,不可靠叙述既是由文化决定的现象,也是由历史决定的现象(Zerweck157-58),这就给不可靠叙述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也为不可靠叙述和可靠叙述之间的转换提供了基础。V·纽宁认为,不同时代的读者,由于其知识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必然会影响到对文本结构意义的重构,也影响到对叙述可靠性的判断。只有考虑到作品创作时的价值观念和意义建构的历史变化,不可靠叙述的叙事学分析才有价值(Nünning236-48)。汉森说得更直白:“阐释史上有大量的例子,曾经被认为是可靠的叙述者,在以后的阅读中又被认为是不可靠的——不是因为早先的解读有明显的错误,而是因为后来的读者与先前的读者拥有不同的标准和价值观念。”(Hansen240)考虑到叙述可靠性和文学真实性之间的一致性,这意味着,同样一部作品,起初被认为是真实(不真实)的,后来又被认为是不真实(真实)的。伏尔泰从高雅的艺术趣味出发,认为《哈姆雷特》是一个荒唐而又莫名其妙的谋杀故事,尽管其中不乏精彩描写而“光芒四射”,但总体上看,它是“乱七八糟”的。莎士比亚所写的只是闹剧,而不是揭示真实的悲剧(韦勒克49)。歌德从内心的情感出发,和伏尔泰采取截然相反的态度,“他宁可接受一个乱糟糟的剧本也不要冷冰冰的剧本”(267)。在他看来,莎士比亚的剧本“不是为了肉体的眼睛”来看的,而是要“诉诸心灵”,“通过幻想”才能理解《哈姆雷特》的鬼魂和暴力行为(歌德65);他为剧本的每一个细节辩护,即使是奥菲利娅看起来不合时宜的歌唱,也“泄露了她的心思”,“在精神错乱的天真无邪之中[……]用她那没有顾忌而又深受人爱的歌声回荡来宽慰自己”(韦勒克271)。就此而言,《哈姆雷特》的叙述无疑是可靠的,也具有文学真实性。
总之,作为叙事策略的叙述可靠性和作为叙事效果的文学真实性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 通常情况下二者是一致的;但可靠叙述可以导致不真实,不可靠叙述也可以导致真实;随着历史语境的改变,同一作品的可靠性和真实性也可以发生变化。
注释[Notes]
① 按照申丹的说法,“这两种方法实际上涉及两种并行共存、无法调和的阅读位置。一种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读者’的阅读位置,另一种是‘隐含读者’或‘作者的读者’的阅读位置”。见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4(2006): 133—43。
② James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主编: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第92—93页。“归化”在卡勒那里,指“一套产生写作活动的约定俗成的程式”,它是“恢复文学交流功能的过程的第一步”。见乔纳森·卡勒: 《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201—202页。
③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4(2006): 133—43。就申丹的分析看,她说修辞方法的阅读位置是“隐含读者”或“作者的读者”,认知方法的阅读位置是“有血有肉的个体读者”,总体上当然是对的,但纽宁对“文类框架”的重视,说明他意识到个体读者的缺陷,要求个体读者遵从“文类框架”的要求;在隐含作者的心目中,“隐含读者”或“作者的读者”也应该遵从“文类框架”的要求。这说明,两种方法在具有排他性的同时,也为互融性留下了余地。
④ 需要说明的是,此时的文学真实性,有赖于读者对历史的态度,如果对历史较真,这样的叙述就无真实性可言,如果将其看作虚构的文学,则另当别论。
⑤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说:“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见罗念生: 《罗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45页。朱光潜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意思是“诗比历史更真实”。见朱光潜: 《西方美学史》(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679页。
⑥ 自传中的叙述不可靠,按照相关研究,有三种形式的不可靠: 文本世界内不可靠、与真实世界比照时出现的不可靠、互文性不可靠。见许德金:“自传叙事学”,《外国文学》3(2004): 44—51。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亚里士多德: 《修辞学》,《罗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Aristotle.Rhetoric.CompleteWorksofLuoNiansheng. Vol.1.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 《诗学》,《罗念生全集》(第一卷)。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
[- - -.Poetics.CompleteWorksofLuoNiansheng. Vol.1.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2016.]
韦恩·克拉森·布斯: 《修辞的复兴: 韦恩·布斯精粹》,穆雷等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9年。
[Booth, Wayne Clayson.TheEssentialWayneBooth. Trans. Mu Lei, et al. Nanjing: Yilin Press, 2009.]
——: 《小说修辞学》,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
[- - -.TheRhetoricofFiction. Trans. Hua Ming, Hu Xiaosu, and Zhou Xian.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1987.]
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 《博尔赫斯短篇小说集》,王央乐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
[Borges, Jorge Luis.CollectedShortStoriesofBorges. Trans. Wang Yangle.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83.]
曹雪芹 高鹗: 《红楼梦》。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Cao, Xueqin, and Gao E.ADreamofRedMansion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陈思和: 《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Chen, Sihe.TheDevelopmentofPersonality:ABiographyofBaJin. Shanghai: Shanghai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92.]
凯特·肖邦:“一小时的故事”,刘洋译。塞万提斯等: 《骗婚记》,葛凯迪等译。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21—24。
[Chopin, Kate. “The Story of an Hour.” Trans. Liu Yang. Miguel de Cervantes, et al.ASnaredMarriage. Trans. Ge Kaidi, et al.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4.21-24.]
特里·伊格尔顿: 《文学原理引论》,刘峰译。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
[Eagleton, Terry.LiteraryTheory:AnIntroduction. Trans. Liu Feng. Beijing: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87.]
福楼拜:“圣朱利安传奇”,林敏译。菊池宽等: 《不记恩仇》,黄悦生等译。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17—48。
[Flaubert, Gustave. “Legend of Saint Julian.” Trans. Lin Min. Kikuchi Kan, et al.ExcludingHatred. Trans. Huang Yuesheng, et al.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4.17-48.]
佩雷兹·加尔多斯:“电车上的小说”,吴兰译。巴尔扎克等: 《沙漠里的爱情》,年昕彤等译。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187—210。
[Galdós, Pérez. “A Novel on the Tram.” Trans. Wu Lan. Honoré de Balzac, et al.APassionintheDesert. Trans. Nian Xintong, et al.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4.187-210.]
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说不尽的莎士比亚”,《外国文学评论选》(上册),杨业治译,易漱泉、曹让庭、王远泽、张铁夫选编。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63—79。
[Goethe, Johan Wolfgang von. “Boundless Shakespeare.”SelectedReviewsofForeignLiterature. Vol.1. Trans. Yang Yezhi. Eds. Yi Shuquan, et al. Changsha: Hunan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 1982.63-79.]
龚举善:“‘非虚构’叙事的文学伦理及限度”,《文艺研究》5(2013): 43—53。
[Gong, Jushan. “The Literary Ethics and Limitations of Non-fictional Narration.”Literature&ArtStudies5(2013): 43-53.]
Hansen, Per Krogh. “Reconsidering the Unreliable Narrator.”Semiotica165-1/4(2007): 227-46.
戴卫·赫尔曼主编: 《新叙事学》,马海良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Herman, David, ed.Narratologies. Trans. Ma Hailiang.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2.]
胡全生: 《英美后现代主义小说叙述结构研究》。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Hu, Quansheng.OntheNarrativeStructureofBritishandAmericanPostmodernNovels. Shanghai: Fudan University Press, 2002.]
《梼杌闲评》。济南: 齐鲁书社,2008年。
[LegendoftheFierceBeast. Jinan: Qilu Press, 2008.]
李昉编: 《太平广记》(八)。北京: 中华书局,1961年。
[Li, Fang, ed.TaipingExtensiveRecords. Vol.8.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1961.]
柳鸣九编选: 《新小说派研究》。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
[Liu, Mingjiu, ed.StudiesonNouveauRoman.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6.]
加西亚·马尔克斯 P.A.门多萨: 《番石榴飘香》,林一安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优秀读者与优秀作家”,范伟丽译,《世界文学》5(1987): 85—91.
[Nabokov, Vladimir. “Good Readers and Good Writers.” Trans. Fan Weili.WorldLiterature5(1987): 85-91.]
Nünning, Vera. “Unreliable Narr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Variability of Values and Norms:TheVicarofWakefieldas a Test Case of Cultural-Historical Narratology.”Style38.2(2004): 236-52.
詹姆斯·费伦:“可靠、不可靠与不充分叙述——一种修辞诗学”,王浩编译,《思想战线》2(2016): 87—92。
[Phelan, James. “Reliable, Unreliable and Deficient Narration: A Rhetorical Account.” Ed. and Trans. Wang Hao.Thinking2(2016): 87-92.]
James Phelan, Peter J. Rabinowitz主编: 《当代叙事理论指南》,申丹、马海良、宁一中、乔国强、陈永国、周靖波译。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Phelan, James, and Peter J. Rabinowitz, eds.ACompaniontoNarrativeTheory. Trans. Shen Dan, et al. Beijing: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2007.]
Riggan, William.Pícaros,Madmen,Naïfs,andClowns:TheUnreliableFirst-personNarrator. 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81.
艾伦·谢尔斯顿: 《传记》,李永辉、尚伟译。北京: 昆仑出版社,1993年。
[Shelston, Alan.Biography. Trans. Li Yonghui and Shang Wei. Beijing: Kunlun Press, 1993.]
申丹:“何为‘不可靠叙述’?”,《外国文学评论》4(2006): 133—43。
Shen, Dan. “What Is ‘Unreliable Narration’?”ForeignLiteratureReview4(2006): 133-43.
弗兰克·斯托克顿:“美女还是老虎”,屈帮亚译。菲茨杰拉德等: 《重访巴比伦》,刘洋等译。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2014年。37—43。
[Stockton, Frank. “The Lady, or the Tiger?” Trans. Qu Bangya. F. Scott Fitzgerald, et al.BabylonRevisited. Trans. Liu Yang, et al. Nanjing: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2014.37-43.]
王成军:“叙事伦理: 中西小说叙事中的道德安全”,《叙事学的中国之路——全国首届叙事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祖国颂主编。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113—36。
[Wang, Chengjun. “Narrative Ethics: Moral Security i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Fictional Narrations.”TheChineseRouteofNarratology:CollectedEssaysoftheFirstNationalConferenceonNarratology. Ed. Zu Guosong. Beijing: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06.113-36.]
雷纳·韦勒克: 《近代文学批评史》(第一卷),杨岂深、杨自伍译。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年。
[Wellek, René.AHistoryofModernCriticism. Vol.1. Trans. Yang Qishen and Yang Ziwu. Shanghai: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1997.]
项静:“V.S.奈保尔: 自己就是题材”,《文艺报》2014年8月25日第3版。
[Xiang, Jing. “V.S. Naipaul: Self as Subject.”WenyiBao25 August 2014.]
酉阳野史编次: 《三国志后传》。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Youyangyeshi, ed.SequeltoRecordsoftheThreeKingdoms. Shanghai: Shanghai Chinese Classics Publishing House, 2007.]
张友鹤选注: 《唐宋传奇选》。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
[Zhang, Youhe, ed.SelectedLegendsoftheTangandSongDynasties.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64.]
Zerweck, Bruno. “Historicizing Unreliable Narration: Unreliability and Cultural Discourse in Narrative Fiction.”Style35.1(2001): 151-78.
周国林:“试论三国志的质直笔法”,《文献·文献学·文献学家》。长沙: 岳麓书社,2009年。219—35。
[Zhou, Guolin. “On the Straight Pencraft of Records oftheThreeKingdoms.”HistoricalRecords,HistoricalRecordsStudies,andHistoricalRecordsScholars. Changsha: Yuelu Press, 2009.219-35.]
朱立元 王文英:“关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关系的本体论思考”,《复旦学报》6(1987): 60—65。
[Zhu, Liyuan, and Wang Wenying. “An Ontological Reflect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al of Art and the Real of Life.”FudanJournal6(1987): 60-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