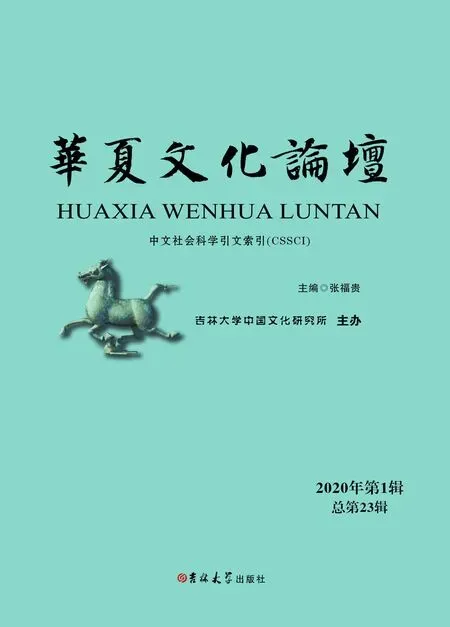意象、氛围、生命
——阿城的诗意书写
冯译萱
【内容提要】在对阿城小说的细读和观念的梳理中,可深切感受到一种上承古典诗学意象、下接世俗诗性人生的诗意美感。他不仅将传统的诗意美学融汇于作品文本,还生发于创作的过程之源,延伸至生命的态度和感知体验中。讨论研究阿城的诗意叙述,有利于使我们在拓宽诗意格局的同时,得到人生美学的启发。
马克思在论述文学批评原则时指出:“文学应当接近真实和实际领域,而不应漫无边际地飞驰遐想;文学应具有形式、尺度和凝练;人们可以从伟大的文学作品里觉出一种真正的诗意。”①[英]柏拉威尔:《马克思和世界文学》,三联书店出版社,1980年,第26页。可见,诗意是伟大的文学作品中必不可缺的素质。在中国这个“诗的国度”,人们更是惯于将“诗意”作为小说评判的艺术标准。陈平原在《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分析道:五四作家、批评家喜欢以“诗意”许人,似乎以此为小说的最高评价。②陈平原:《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25页。正是在那些或明亮、或平淡、或颓废的诗意书写中,铸就了鲁迅、废名、沈从文、张爱玲、郁达夫等一代文学大家所开创的辉煌时代。
所谓诗意,是小说对中国诗歌传统所继承的一种审美特质。不止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表达的性情心态,更在于作品所营造的感觉、氛围,模糊而又无以言表,却能促使人在阅读后产生一种冲击心灵的力量。承袭中国诗歌传统,现当代小说的书写历史中虽有断裂,但仍保留下了这种诗意传统。至20世纪80年代初,诗的意识再次大规模进入小说,“一时之间,小说的传统叙述方式骤然瓦解了。大量诗的观念与诗的技巧有意介入并且改组了作家熟悉已久的‘叙事’,情调、意绪、气韵、意境、瞬间印象,这些诗的臣民大批进驻小说,安营扎寨”③南帆:《冲突的文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95页。。作为八十年代文学的代表人物,阿城始终因自觉的传统文化意识而为人颂声载道。这种传统文化意识不仅表现于作品书写的文化观念,更体现在他作品所蕴含的艺术特征内。基于长久以来对传统诗歌的热爱和研究,阿城在创作中时常自觉地或无意识地流露出浓烈的诗意叙述特征。他以文字编织出一种意象,在营造的氛围中表达感觉、抒发情感、开创意境。这也使他的文章拥有了深刻的带入感和体验感。
与同时期的文学创作者相比,阿城在小说的诗意书写中,显然是道高一筹的——上承古典诗学意象、下接世俗诗性人生。他始终坚守着对于古典文学尽可能的承接和延续,这也是学界普遍将其归纳入“寻根”的原因之一。无论在其创作中,还是在相关文学讨论中,阿城始终秉承不以主观色彩影响他人,尽实的客观展现出一个真实,透过意象的摘取、气氛的烘托,促使人们发生联想或思考,展现出对于古典诗意的完美诠释。于此,本文将探源阿城的诗性观,深入分析其对于意象、氛围、生命意识三个方面的诗意表现,在文本细读和现实考察的交叉映照中,对阿城的“诗意”做出立体研究。
一、诗性的意象表达
在阿城的知识构成中,《诗经》和《史记》是其极重要的组成部分。他曾说:于是凡有关《诗经》的书我都买,历年积有四十多本。①阿城:《脱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35页。而在诸多文章和访谈中,阿城更是谈及自己对于《史记》的理解和偏爱。他在与诺埃尔·迪特莱(法国)的通信中写道:“中国文学传统基于诗,而散文文学传统则基于《史记》,《史记》是具有文学特点的各种描写的开端。”②[法]杜特莱,刘阳:《不可能存在的小说:阿城小说的写作技巧》,《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04期。《史记》在对浩瀚历史长河的鲜活书写中,根植社会生活的繁杂人事,意在传达千百年来传统文化思想的气韵和灵魂,其诗意的表达让后人在千百年的流转中,仍能真切感受到他们充沛的情感,遂才得到鲁迅“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的盛赞。正是这些厚重文化沉淀的濡染,使得阿城在自我创作中愈加注意自己对于感觉、意象的诗意把握。他自己评价《遍地风流》系列短篇:因为是少作,所以“诗”腔外露,做作得不得了。可见阿城自知,并自觉地在书写时埋下诗意。阿城最终选择了笔记体小说的文类表达方式,同时具有诗、散文、随笔和小说的特征,与其阅读影响和诗意的审美追求也不无关系。
阿城不仅将诗意书写进自身的文学创作中,看待其他文学作品时,他也常怀诗意,如他分析《红楼梦》之所以成为古典小说的顶峰,是因“曹雪芹将中国诗的意识引入小说”③阿城:《闲话闲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98页。。对于现当代文学创作的评论,亦是常以诗意为尺:湖南何立伟是最早在小说中有诗的自觉的;山西李锐、北京刘恒则是北方世俗的悲情诗人④阿城:《闲话闲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43页。;南京苏童在《妻妾成群》之前,是诗大于文⑤阿城:《闲话闲说》,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45页。。他评价《受戒》是一种恢复了诗意的散文小说⑥阿城:《脱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62页。,而朱天文的《荒人手记》有点像李贺写诗①阿城:《脱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87页。;孝贤的电影语法是中国诗②阿城:《文化不是味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02页。;而费穆的《小城之春》、张爱玲的《太太万岁》、石挥的《我这一辈子》其实是西方诗和东方诗的混合③阿城:《文化不是味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03页。其中,阿城对何立伟的小说《白色鸟》评论最为细致:“何立伟属于开始发表作品就是成熟的作家之一。他的成熟表现在他的小说有一种诗意,所说的诗意当然不是七八十年代充斥中国小说的文艺腔,他的小说中的诗意属于中国古典诗歌中那些典雅生动的意象的当代表达。这篇小说的诗意人物与环境,隐藏着一个残酷的事实,所以小说结束时,你当可体会为什么小说通篇笼罩在‘正午’这样一个反差强烈的意象中。”④阿城:《脱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64页。如此之高的评价,正是源于阿城对于诗意美学的认同。在其文本创作中,也深刻地蕴含着这种诗性的意象表达。如孔庆东说:“语言上向古诗词中的无我之境靠拢。在这方面,应该肯定,阿城取得了很大的成功,甚至比有意要用唐诗格调来写小说的何立伟还要高出一筹。”⑤孔庆东:《47楼207》,中国文联出版社,2012年,第141页。可见,阿城对传统的诗意表达怀有一种近乎虔诚的钟爱。
1999年冬,阿城与众多知名文坛作家相聚在成都郫县(现为郫都区),开展一场关于“诗意的年代”的讨论,参与者有林白、陈村、徐星、须兰、赵玫、方方、丁天、王朔、马原、棉棉、余华。虽然这次笔会以电影《小说》的拍摄为契机(电影《小说》又名《诗意的年代》,导演吕乐于1999年拍摄后并未上映,2007年入围2007年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单元,2012年第31届香港国际电影节首映),但作家们的讨论交流始终真实地以自我认知为中心,衍生出关于时代、经济、个体生命等众多因素与诗意的关系。对于诗意每个人有不同理解:陈村认为,由虚无的追求变为在破碎混乱的现实中寻找趣味更具诗意;方方将当下生活比喻为打油诗,认为经过岁月的沉淀,可在回忆中品味出更深刻的诗意;丁天认为,物质和金钱的需求似乎将现代生活中的诗意消磨殆尽了,当下拥有一辆车是诗意;王朔则提出,人生沉沦到底打破限制才能看到诗意,才能感受到不同寻常的人生;还有马原无用的人生的诗意、林白个人意识为中心的诗意;等等。相比大家以自我生命体验为依据,畅想出关于生活中诗意的思考,阿城的论述则更具“史”味,旁征博引,展现出别样的诗意。他以古代“歌咏言,诗言志”为依据,说明诗区别于歌,并非直接情感的抒发,而是在行文中产生一种不能用语言表达的东西,即意象。这种无法清楚描述的意象,便是中国诗歌传统中所展现的诗意。以阿城所言,当代诗歌的没落,源于当代小说成为时代新意象的新载体。诗意自清末开始,经五四新文学、新时期文学等阶段,早已融入描写当代生活的小说中,现在任何生活都会产生诗意,且不论它是善、恶、好、坏、有德、非德,终究是存留在我们生活之中的。
在杂文《诗与歌不同》中,阿城对诗和意象的概念做出更为明晰的阐释:“中国很早就对诗另有独特的要求,才产生了歌与诗的本质区别,即诗须产生意象,以至‘诗言志’的传统虽然还在,但对什么是诗的判定已转为‘产生意象的抒情散文才是诗’。”①阿城:《脱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而他所谈及的意象,并非现代汉语中一般所指的物化的艺术形象。“什么是意象?意象就是韵文词句排列后,碰撞出一二不能再用其他语音叙述出来的东西,比一般说的感受、情绪要高的东西,王国维称它为‘境界’。”②阿城:《脱腔》,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6年,第132页。由此而言,意象应是根植内心、发乎情而产生的一种感觉和境界。王昌龄在《诗格》中提出物境、情境、意境三个概念,将对于物、情、意的表现明确指向为相关的境界,即由意象衍生出的诗意。阿城的整体创作意识正是在这种诗性的意象上建构起来的。
在《遍地风流》中,我们可清晰察看到阿城小说对于诗性的意象表达。王德威在北大授课时,曾以阿城的《遍地风流》为例,讨论“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的课题。他诚言:“对我而言,我觉得阿城的成就更在于这一本薄薄的《遍地风流》上。”这本“新时期以来的一本奇书”是“我们讨论中国现代抒情创作的非常重要——而且是一个必要——的部分”③王德威:《抒情传统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00页。。抒情传统于此,便是传统诗学意象的表现。他将感觉融进数百字的短小篇幅,使每一个故事都独具神韵,带来震撼人心的力量。精准节制的语言,几乎不带有主观色彩的描述和任何形容,还现实以真实,却能感受到溢出纸面的情感,隐晦地蕴含着厚重的诗意。如毕飞宇所言:好的短篇应该是“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遍地风流》如是。
“彼时正年轻”和“杂色”两部分中,几乎每篇小说都在描述人们日常中的事物,“大门”“布鞋”“宠物”“提琴”“大风”“白纸”等,这些看似无足轻重的普通意象,却引申出那个年代在人们心中留下的烙印伤痕。地球物理专业的挖煤工,黑脖子黑脸唯有屁眼儿是白的;山气日夕佳的秋天,被批为流氓的农妇却冻得奶头青紫;庄严肃穆的天安门广场,王建国终于站在五星红旗下,却是撒着尿流着泪;一顿饭一斤半的大胃遇得机会到粮库上班,却离不开家里的母牛;养不成宠物的金先生最终与一窝老鼠相互为伴;还有火葬郭处长时烤熟的黄豆、孙仁之收到的莫名其妙的白纸、张武常那张绣着毛主席诗句的被子;等等。阿城以“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的态度,将“风流”二字完全下放到民间,以最鄙俗的意象勾画出世间景象,形成其独特的诗性表达。“这些描述世俗日常生活的小说直至现在仍然保留着当时流行文学无法比拟的诗意。”④潘文峰:《论阿城小说的启示》,《文学评论》,2007年第3期。秉持“天地不仁,各自好自为之”的冷峻,阿城为我们细数了一众平凡如蝼蚁,残喘在伧俗粗粝的世事间的人事。故事中那些不雅的、残暴的、惨烈的场面看似区别于中国传统抒情诗学,但是从文学特质而言,这实则是阿城刻意而为的另一种诗性的意象书写。“他必须要写到这么粗俗,这么狂野,才能用来作为某一种抒情艺术形式的反省,以及对文类本身的批判,以及接之而来的超越。”⑤王德威:《抒情传统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第200页。如王德威所言,故事在这里成为“衍生的抒情美学”中的一种渡口,如《一千零一夜》般为我们讲述一个个寓意深刻的故事,铺就一张张走向不同的支脉,触及世间百态的纷杂人生,归根结底却凝汇于同一根筋骨,诉说着沉痛的哀思,在蔓延的诗意中寻探那个年代留下的印记。
他以直白流水的方式讲述那些普通的故事,却总能在强烈的意象反差中令人猛然警醒。如小说《春梦》:童年时萌动的爱情散发着甜美的味道,顾直安对晓霞青涩朦胧的情感,却在时代的运动中变为侵犯毁灭她的缘由。结尾“晓霞光着的两条腿上是第一次的血,苍蝇飞起来的时候,没有血的地方是安直梦里的白”。现实的残酷血腥与童年梦想般的美好形成强烈的意象反差,红与白的色彩交叠,涂抹出浓烈的悲凉。
鲜明的意象反差引人深思,而某些平淡无奇的意象书写中,亦可窥见厚重的思考。和满街走的女孩子都差不多的小玉准备去插队了,孤身一人的她不愿放弃一直相伴的钢琴,众人费九牛二虎之力将琴拆开托运,最终却因螺钉丢了,钢琴变为一堆废品。“拉弦钢板靠在队部的墙上,村里的小孩子用小石头扔,若打中了,嗡的一声,响好久。”(《小玉》)戛然而止的结尾令人感到意犹未尽。阿城常常在叙述中突然为故事画上句号,然而那层意蕴却如同回荡在山谷的声响,萦绕耳畔,引发回味和深思。钢琴的嗡鸣声最后仿佛回荡在耳边,激荡起人们沉痛的忧思和对于文化断失的遗憾。对于小玉而言,钢琴是她父母离去后与她相伴成长的精神寄托;对于时代而言,钢琴则表现出那个荒诞年代里文化的断裂,一切由古至今人们所传承的文化,都渐渐变为堆砌在角落中的废品,在劳作中变为无用的存在。另一篇小说《大门》中,阿城同样以一座寺庙的大门寄予对文化的思考,伴随着象征中华民族的滔滔黄河,在两种传统文化意象的交织回响中,展露那个时代对于青年思想和古老文化的迫害。
二、诗意的氛围营造
阿城仿若一位内功深厚的绝世高手,云淡风轻地描述出一个故事,却能产生触动心灵的力量。他牵引着读者,在一步步行进间,凝练起一团云雾,聚集起人们的思绪和情感,直到故事结束,好像用一枚无形的针扎破气球,云雾散去,于是人们也在解脱中体味到一种诗意。诗意不仅存在于意象,更融汇于感受的氛围。如同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虽无物可循,却能在言语的氛围中感受到彻骨的悲凉。关于诗意的氛围表达,古人在《诗经》中便早已有运用。《诗经》中所使用的“兴”的表现手法,便是以“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产生一种氛围,为主题服务,如“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或“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借河间啼鸣相伴的雎鸠,营造出柔情的暧昧之意,由艳烈明媚的桃花,烘托出浪漫喜悦的氛围。不同于诗歌的是,杜甫以“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寄喻国破家亡的黍离之悲,阿城在小说中表现出的,则并非某种单一的纯粹的感念,而是糅杂着许多不同的、微妙的、复杂的意象,只能在妙不可言的氛围中体悟诗意的印记。
《树王》是阿城代表作“三王”中诗意最为浓重的一篇。小说通篇笼罩在一种凝重的氛围中,以树、人、生命、良知奠定了主题的基调,运用神秘主义色彩,将树与人之间牵连起无形的羁绊。带着温热脉搏的群山大树,供养着无数飞鸟走兽的生命。信奉革命号召的大好青年们,却不明自然的力量和规律。在那个无法辨别“好树”与“坏树”的年代,似乎也不从区分“好人”与“坏人”的差别。随着以李立为首的知青们大肆砍伐山林,破除迷信,推进新建设,逐渐激化起与肖疙瘩的矛盾,层层铺展开肖疙瘩心怀愧疚的往事,突显出知青们对于革命指令的盲从。最终肖疙瘩用生命为代价的抵抗,唤醒了“我”与读者们的良知。“数万棵大树在火焰中离开大地,升向天空。正以为它们要飞去,却又缓缓飘下来,在空中相互撞击着,断裂开,于是再升起来,升得更高,再飘下来,再升上去,升上去,升上去。”震撼的诗意环境带动出一种沉痛的氛围,仿佛有一种东西也从心底里升腾起来,在胸腔膨胀,沸腾拥堵在喉咙间,几乎喷涌而出。反思着人们所坚持的“正确”,呼唤着那个时代人们内心丢失的空白。小说结尾,肖疙瘩尸骨上生出片片白花,“也能看到那片白花,有如肢体被砍伤,露出白白的骨”。看似苍白实为厚重的寓意,将人与自然在貌似疏离却合二为一的交织中,酿就出各种纠葛的迷茫、惆怅、困惑、苦痛、醒悟,带来解脱并存留下不尽言表的诗意,直到故事戛然而止,凝重的氛围却笼罩心头,久久无法挥散。
《棋王》《孩子王》中对于氛围的诗意营造亦斑驳可见。《棋王》通篇将“我”对于人生意义的思索追寻寄蕴在时代的压迫感和现实的束缚感的裹挟中,隐露着苦闷的氛围,主要表现在人物的刻画和环境的描绘上。与伤痕文学不同,阿城“写文革而不着眼于它所造成的伤痕,而把它们化为一种沉重的时代气氛、艺术氛围”①李星:《搭讪的沟回——读阿城的〈棋王〉〈孩子王〉〈树王〉》,《小说评论》,1985年第12期。。小说通过对“我”和王一生的人物刻画,映照出那个时代语境下人们精神世界的消解。王一生对棋的痴迷反照着时代精神文化生活贫瘠的愁苦,对吃的执着影射着现实生活贫困的悲苦。而小说中的“我”作为一个旁观的讲述者,始终有一种晦暗不明的欲望在心头涌动,“说不清楚,但我大致觉出是关于活着的什么东西”。直至看过王一生棋对九人的一场大战,才顿悟得“衣食是本,自有人类,就是每日在忙这个。可囿在其中,终于还不太像人”的价值感悟。王一生的吃与棋,表现出时代的饥饿和文化的坚守,而“我”的思考则深化出生命价值备受压迫的沉重的时代氛围。在那个充斥着语录和劳作的年代,人们淡却了生活的价值意义,无所谓精神的追求和自由,受困于日复一日的苦闷现实。所以,一盘微小的棋局才能在平淡的日子中掀起轩然大波,而“我”在没有书籍、电影的境况下深切感受到精神的荒芜。
除了人物的刻画,在环境描写中也可感受到这种氛围描述。小说开篇:“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说话。”简单的一句场景描述却充分显现出纷杂错乱的时代背景下,芸芸众生的离别悲欢。混乱的不止车站,更是人心,是当时所处的时代。小说以一个嘈杂的场景蓄势并铺垫出苦闷的时代氛围。而那场著名的九局连环车轮大战是故事的高潮,同时也是“我”对于人生价值追寻的突破。阿城以动静相交的氛围凝聚起饱满的情绪张力,亘古的感受从历史的尘土中苏醒,现实的生活无限延续,动与静映衬碰撞,生发出对于人生价值意义的诗意追寻。中国古典诗学善于以动衬静、化静为动,讲求动静相宜。车轮大战中场外“数千人闹闹嚷嚷,街上像半空响着闷雷”的情境与场内纹丝不动,只有喉结许久才动一下的王一生构成强烈的动静反差,紧张的氛围烘托出这场棋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感念现实和打捞历史的交织中,“我”追念起目瞪口呆的刘邦项羽、尸横遍野的黑脸士兵和提斧野唱的樵夫,生与死的意义得到昭示。
在《孩子王》中,阿城则以一种明暗对比的冲突感表现出感伤的氛围。如阿城所言,《孩子王》是以一位知青教师的授课方式表现了面对强制的要求而不合作的态度。小说中的“我”初到教室,灰暗而简陋的桌椅与孩子们闪烁光亮的眼睛形成鲜明对比,凸显出在那个艰苦的环境中,孩子们对文化知识强烈的渴望之情。在没有任何设备条件的情况下,“我”企图根据自己的理解传授给孩子们最为实用的知识,然而最终却被组织不认同而罢去了教师的职位。离开时,室外暴烈的阳光和教舍门内黑黑的景象再一次形成强烈的明暗冲突,自然的光亮将孩子们的教室突显得更为黑暗,暗喻出教育在那个时代环境中的黯然,孩子们的未来更是缺少了光明和希望。“我”对于孩子未来的生活和体制管理下的教育只能表现出无力和伤感,只有以不合作的态度表明自身的坚守,而这一切也只能在明烈阳光和黑暗教舍的对比中,化为伤感的氛围。
不止《树王》《棋王》《孩子王》,阿城在其他诸多短篇中亦常常通过氛围的营造表达情感的诗意。如《节日》,以孩子们天真烂漫的玩乐营造出轻悦的氛围,却在浪漫星光和凛冽火光的交融中,显现出革命战乱对生命的残忍无情。季红真对短篇《树桩》同样评价道:“作者在这一个个虚与静的氛围中,集结起饱满的情绪张力,像宇宙时空般永恒的生命价值的意识,便从平凡有限的人生具象中缓缓升起,暗示出丰富的语义内容。大有‘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诗学境界。”①季红真:《宇宙·自然·生命·人——阿城笔下的“故事”》,《读书》,1986年01期。他将诗意融于字里行间的氛围,只有酣畅淋漓地畅读至尾,才能在心头升腾起一种感觉,无以言表却感受至深。可见,阿城通过诗意的氛围营造,不仅表达出自身的情感和思考,更构建起小说独特的格调。
三、诗意感觉的生命意识
阿城的小说之所以能给人以震撼的力量,是因为他所讲述的、描绘的,并非刻意造作的故事,而是内心感觉的诗意流露。他早已将诗意情怀融汇于自身生命意识的感觉之中,那些澎湃的情感、厚重的体验、幽深的思考,经由故事散发出来,通过文字链接到读者的内心,产生感同身受般的共鸣。这种饱富诗意感觉的生命意识,不仅存在于他面对万事万物所思考的角度、态度,同样影响了他情感体验的表现方式与写作方法。
文字是情感的表达工具,情感才是小说的内核。关于写作方法,阿城评价自己的创作,就是无关方法,而是将整个的心理现实和心理经验糅和起来,凝练为自己的心理状态,以字词符号的组合流淌而出。读者之所以在阅读后产生了或喜、或怒、或哀、或痛的情感,是因为感受到文章所传达的状态感觉,这种状态感觉的形成正是基于他诗化的生命意识之上。
不同于现代派丰富的技巧性表达,阿城的叙述抛离结构主义、意识流、梦幻等艺术技巧,以最简单直白的线型方式进行表达,顺时推进,始终由状态牵引着故事自己发展,而非自己刻意编造情节环境。“我自己写的时候有种状态……你起先也不知道要写点什么,你也不清楚要说点什么,但是有一种欲望,就像肚子里在练气功,从丹田里开始走气了,走上来走到四肢;或者就像里面的水慢慢满了,到这儿就要流出来,就有状态了。但一切都是比较模糊的,不能用逻辑去把它分解开,那么坐下来把钢笔打足了水,把挺白的纸给摊开,[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就这么写下去吧,基本状态还是写写写,写到气数已尽,气完了,就结束了。”①阿城:《谈谈我的创作》,《香港文学》,1986年第14期。在阿城的文学经验中,写作无关方法,而是文字对于感觉状态的诗意流露。如王晓明所言:“在具体的描写上,他总是注意记述原始的感觉,尽量摒除理智的分析和判断。”②王晓明:《不相信和不愿意相信的——关于三位“寻根”派作家的创作》,《文学评论》,1988年第4期。
反观“彼时正年轻”及“杂色”诸篇可以发现,小说开头几乎都是由人名讲起,敦敦实实,不耍花腔,做出一句真实的介绍。《小玉》开头是:“温小玉,一九六八年的时候十六岁。”《觉悟》的开头是:“觉悟是老俞的释名。”《噩梦》的开头是:“老俞爱笑,没有什么可笑的时候,老俞也是笑笑的。”简短的介绍性文字,如同在宣纸中央落下清晰的一滴墨,随后自然地晕染开来,甚至衍生出一幅壮阔浩瀚的图景。顺延着作者的状态前行,我们看到温小玉在铺着素花被面的钢琴上熟睡的模样,看到觉悟蓄着头发和人解说自己名字的模样,看到老俞几近痴狂的傻笑模样。这一切看似不正常的状态,却都在阿城感觉的书写下,展现出别样的意蕴。小玉的钢琴在上山下乡的过程中,如同任何具有文化印记的事物一样,断裂了意义和价值;觉悟诚心修行后终成高僧,最终却无法理解现世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最浅白的道理;老俞那不合时宜的令人心惊胆战的大笑,原来是“文革”中缓解噩梦,落下的毛病。在作者的感觉状态的牵引下,我们逐渐将故事看似简白的外衣剥离,深入到那些关于时代、关于人性的主题,看似浅显,却蕴含着发人深省的力量。所以才有评论道:“读他的小说,很难把握以因果为序的线性情节,使你不释于怀的,往往是那些难于复述的琐屑之处……恰恰是这些‘闲笔’构成了阿城小说中特有的氛围和境界。”③苏丁,仲呈祥:《论阿城的美学追求》,《文学评论》,1985年06期。所谓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阿城的自然书写总是展现我们以一个真实。他不予置评,不加形容,任由读者根据自身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获得各自的感受,享受一种诗意的阅读。
阿城的诗意书写不仅表达融汇于作品文本之中,发生于创作的过程之源,更延伸至他的生命意识和生活态度里。正是这种秉承着对于生活的诗意情怀,才使得他在创作中展现出一种超脱功利的、充满古典意趣的境界。这种对于生活的诗意情怀,最集中地体现在《威尼斯日记》的书写里。与其说《威尼斯日记》书写的是威尼斯的风貌民俗,不如说它写的是阿城关于人生的态度、意趣之所在,借威尼斯蜿蜒的河流、杂错的街巷、别致的钟楼、华丽的建筑等影射出来,弥漫着艺术的芬芳。在世俗日常的生活中,糅杂进想象性、隐喻性的思考,为客观世界覆盖上一层诗意的色彩。
《威尼斯日记》是阿城受意大利官方邀请,旅居威尼斯三个月中所记录的随感。日记的形式更为真实而细腻地展现出阿城的思维印记和切身感受,让我们更好地体会到他对事物的观察角度、文化心理构成和独特的审美形式。阿城对艺术仿佛具有天生的敏感,他总能将东方的、西方的、古典的、现代的各方艺术融通,寻到关联。例如,“威尼斯像‘赋’,铺陈雕琢,满满当当的一篇文章”,期间掺杂着歌剧、雕像、咖啡、电影、《教坊记》、《红楼梦》,甚至NBA赛事等众多关于艺术和世俗生活的内容。那些独具西方艺术形态的所见所闻总能引发出对于中国古典文化的联想,期间遍布诸多充满趣味的冷知识。虽然看似无章法可循,却能从中感受到一种源自心灵的飘忽的诗意想象。
生活中的诗意情怀不仅体现于阿城丰富的喜好兴趣,更体现在他对事物的观察和捕捉中。在观察中体味生活,在思考中幻想出关于生命的诸多趣味,这种精神自足式的欢乐或许源自知青时期苦中作乐的习惯。年轻气盛的阿城曾游荡在偏远的边境小镇,每日劳作、放牛,现实贫困却换来了相对自由的精神世界。在阿城的回忆中,似乎总能出现一幅他仰望着天空发呆的场景,实则头脑中或许早已展现出一片意趣盎然的景象。在平淡的时光中发现趣味,在闭塞的环境中享受自在,独创一方诗意的世界,阿城将情怀变为习惯,延伸至随后的生活岁月中。在《威尼斯日记》中更随处可拾见他的诗情趣意。“那个倾斜的钟楼,钟敲得很猖狂,音质特别,是预感到自己要倒了吗?我特地穿过小巷寻到它脚下,仰望许久。它就在那里斜着,坚持不说话,只敲钟。它大概是威尼斯最有性格的钟楼。”将威尼斯广场上的钟楼比作一个独特的、猖狂的角色,接连用“预感”“不说话”“性格”拟人化的词汇赋予钟楼以人格色彩,仿佛两个生命在对视交流。他特意穿过小巷寻到钟楼脚下,仰望,观察。对于钟楼的想象,对事物的好奇感,亦是他生活中诗意感觉的展现。诗意不仅限存于生活中对于艺术、文学的多种体验,更深植于灵魂,反射在看待事物的角度和对世界的情绪。还有那生动形象的比喻:“肖邦弹琴的最大音量,是中强(mf),而我们现在从演奏会得来的印象则肖邦是在大声说话。”将通俗的事件加以趣味化的形容,带来忍俊不禁幽默。抛开现实的诸多束缚,阿城总能在头脑中开创出一片属于自己的诗意栖居地。
四、结语
从创作到生活,阿城上承古典诗学意象,下接世俗诗性人生,秉持正统“史”味诗学传统,深入观照到自身文学创作的点滴之中,以“语言的外在律动与作品氛围的内在律动恰到好处地发生了共鸣”①苏丁,仲呈祥:《〈棋王〉与道家美学》,《当代作家评论》,1987年第2期。,传达出他所追求的感觉和境界。无论是感觉流动的自然书写方式,还是生活中无所不在的诗意情怀想象,阿城的“诗意”书写已然根植于生命生活,绽放于文学创作所表达的情绪感觉之中。其文中对于意象氛围的刻画,总能在故事结束后,让人体味到一股撞击心灵的力量。在阿城的脚步中追寻诗意,不仅让诗学传统在当代小说中得以复位,更让我们体味到内心自由、灵魂丰富的人生美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