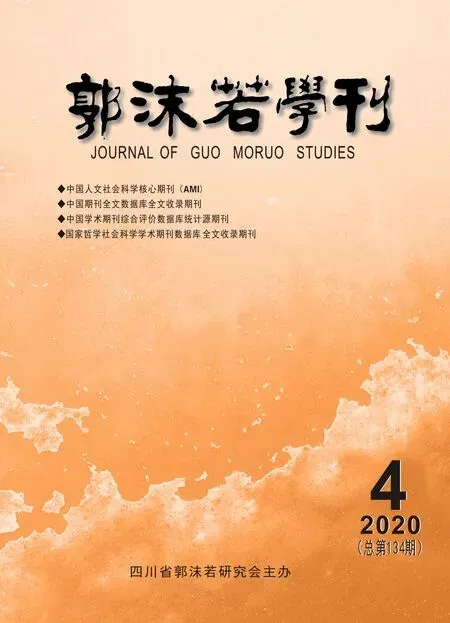郭沫若早期小说与五四“人的文学”
余 玲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郭沫若作为20世纪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其诗歌与历史剧在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影响已经经典化,相比之下,对于郭沫若小说的创作评价,文学史通常是点到为止、寥寥数语,甚至曾一度遭受文坛诟病。但正如杨义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的评价:“他不容抹杀的是小说史上有影响的人物,但影响主要在其开拓者和探索者的历史作用,不在其创造了多少传世不衰的杰作”①杨义:《中国现代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第593页。;又如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写到的:“郭沫若是以诗人著称的,但他写小说也很早。在创造社成立以前,他已经在《学灯》上发表过《鼠灾》,在《新中国》上发表过《牧羊哀话》……其中的情趣尚有令人难于割舍的地方”。②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3页。确如两位学者所言,郭沫若早期小说即使在百年后回望,不仅仍然有难于割舍的“情趣”,并依然有生气,这生气是五四时代的人文启蒙风气,亦是郭沫若鲜明个性在小说中的强烈表达,也是对五四人学观的有力尝试与探索。本文即将郭沫若早期小说放置在现代文学草创时期的文学史大语境下,考察其与五四核心话语“人的文学”的精神契合与呼应,以此探讨郭沫若早期小说在新文学史上的开拓价值与意义。
一
郭沫若从1918年写作《牧羊哀话》到1947年发表《地下的笑声》,期间创作小说计40篇,从内容上看,1927年《一只手》之前的21篇小说多为个人身边小说或浪漫抒情小说,可称作前期创作,此后的小说多为历史小说。从时间上看,前期21篇小说创作时间均在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且最早的《牧羊哀话》发表在1919年11月的《新中国》第七期,但其写作时间据郭沫若记录为1918年的2、3月间,与现代小说奠基人鲁迅1918年5月在《新青年》第四卷上发表的新文学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几乎同时。之前,据《郭沫若自传》记载,郭沫若还曾“火葬”过被退稿的第一篇小说习作《骷髅》,那么由此推断,郭沫若开始小说创作的时间应该更早。而当时新文坛的小说创作局面如茅盾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里的描述:“民国八年(1919年)一月自新潮社杂志发刊以后,小说创作的尝试者渐渐多了,亦不过汪敬熙等三数人,也还没有说得上的成功的作品”。①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页。可见,郭沫若作为现代小说最早的一批尝试者,其开拓之功不容忽视。
不仅如此,郭沫若早期小说更具价值的是——其极具个性化且热烈真挚的叙述极其典型地实践与张扬了五四“人的文学”的精神理念,是五四时期名副其实的新生的“人的文学”。众所周知,晚清民初以来,受西方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中国人也逐渐开始了现代“人”学的觉醒和思考,如严复的“三民说、梁启超的“新民说”、鲁迅的立人-立国思想、胡适“易卜生主义”等都是现代“人学”探索中的重要收获。文学革命中,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道出新文学的实质:“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的非人的文学”。②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93-196页。所谓“人的文学”——即“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③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93-196页。此处的“人道主义”,周作人解释为“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④周作人:《人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193-196页。其随后发表的《平民的文学》进一步提出“人的文学”的两个文体特征,即“普遍与真挚”:“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记普遍的思想与事情”;⑤周作人:《平民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⑥周作人:《平民的文学》,《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在《新文学的要求》《个性的文学》中周作人又多次反复阐述人的文学是以个性主义为基石的文学。自此人的文学遂成为文学革命的旗帜和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核心命题与根本价值追求。在狂飙突进的五四风潮中找到情绪郁积喷火口的郭沫若,其早期小说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五四人学的时代烙印,加之其创作主体偏于主观和情感化的个性特征,以及受到欧洲浪漫主义文学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影响,郭沫若早期小说与五四“人的文学”表现出极大的精神契合,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充分地诠释了现代“人”格品质,为初期的现代文学提供了一种真实可感的现代新人形象。
若将同时期的小说创作做一个横向比较,郭沫若与鲁迅、郁达夫的小说差异还是明显的。作为现代小说之父的鲁迅,其小说多着眼对吃人的“仁义道德”做力透纸背的批判,对于那些“没有吃过人的人”“真的人”并未正面描述和展现,只是寄无限希望于“救救孩子”;又如郁达夫小说在感伤颓废中多散发出封建落魄士子的穷愁羸弱自伤自悼的情调,并未脱尽旧文化的烙痕;与之相比,郭沫若早期小说中的主人公则较少受到旧文化因袭或封建束缚的影响,更多呈现出个性独立、爱恨分明热烈率真的现代人格形象。这个形象显然是在西方人文精神影响下觉醒的一代新人的形象,是五四“人的文学”的重要收获。
二
个性主义是五四人学的核心精髓,也是郭沫若早期小说最为突出的特色,将自我作为小说的表现对象,让小说带上了鲜明的只属于郭沫若的个性色彩。郑伯奇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的导言里将郭沫若这类小说称为“身边小说”:“自己身边的随笔式的小说,就是身边小说。”⑦郑伯奇:《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导言》,《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三集》,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第13页。确如郑伯奇所言,郭沫若早期小说多以第一人称“我”或者“爱牟”作为主人公或叙述者,“爱牟”意即英文“I’AM”之意,是从《残春》开始的多数小说的主人公名字,可视作郭沫若在小说中的自我符号。不仅如此,这个主人公“我”或是“爱牟”的身份、经历、家庭、职业、性格等都与郭沫若本人的情况基本吻合,换言之即是,小说作者与主人公几乎就是同一个人,作者的自我就是小说中的那个主人公,小说不再是虚构的产物,而是自我的描摹与再现。例如,小说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奔波于日本-上海间过着穷困潦倒的家庭生活的留日中国青年,住着“猪狗窝一样的楼房”,娶的是“叫花子一样的妻子,”⑧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70页。还育有三个割他肉吸他血的幼儿。虽然读的是大学医科但弃医从文以卖文为生,日子过得捉襟见肘,经济上很惨伤绝望,这样的小说描写其实就是郭沫若在1920年代前期真实生活的写照。
小说主人公生活穷困漂泊,郭沫若自己其时的生活亦是穷困漂泊:“节省,节省,节省!万事都是钱,钱就是命!”⑨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第170页。被钱折磨、为钱煎熬的家庭生活悲剧堪称这批小说的主要内容:“拢共只有四五百块钱的家资,吃不上两三个月不是便要讨口了吗?固定的收入没有分文,要全靠这做文字来卖钱”;“我全家住在旅馆里,每月的耗费总共六元,我前月得来的稿费还可以支持两个月……生活就在两个月之后逼迫着我,我每个月只要做得上四五万字,便可以从面包堆里浮泛起来。我受着面包的逼迫,不能就贪安闲。”①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206、188、171、28、89、91、147 页。为了节省房租不得不多次举家搬迁:“六岁的大儿……十九次。四岁的二儿……四次。岁半的三儿……七次”;②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206、188、171、28、89、91、147 页。也是为减少开支,不得不忍痛将妻儿送回日本,骨肉离散(《漂流三部曲》)。
日常生活的窘迫心塞在小说主人公与郭沫若的真实生活中是共通的:爱牟在两立方米的亭子间做着译读工作,屋外是剥核桃的妻子和脸冻成紫色的孩子,只能苦中自嘲自己与妻子是“亭子间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亭子间》);“他”在圣诞节前得卖稿费80元,满心欢喜地拿着钱去店里采买东西,却一连遭遇到“哑板”(假钱)和丢钱的悲愤(《后悔》);日间操劳,夜晚久久不能入睡,独自醒着听夜声,无限凄凉(《未央》);这些素材,既无关家国,也不具备重大社会性、时代性,家长里短、柴米油盐,只与“我”个人有关。题材内容的变化意味着文学观念与审美标准的变化,传统的“文以载道”观念、经世致用思想,代圣人立言的道德冲动,均被郭沫若抛弃,作为经过五四人学启蒙的作家,郭沫若创造性地将自我作为小说表现对象,这无疑极大地肯定了自我价值,肯定了个人生活的价值,即使是繁琐细碎看似无意义的生活,但也因是“我”的生活而获得了意义。此外,第一人称叙述视角的大量运用,直接以“我”作为小说主人公和叙述人,在叙述模式的转变中体现了人的主体地位的提高、个体价值的张扬,也是郭沫若五四人学观念在文学上的重要体现。
三
郭沫若早期小说个性化的特征还体现在小说中大量个性化的情感宣泄上。由于其小说主人公个性敏感热烈,极易为生活所触动,内心常常波澜起伏,因此如何处置人物内心这些充盈的情绪,不同的作家呈现出不同的处理方式和小说特色,郭沫若小说的处理方式与其诗歌写作推崇的情感的自然流露的方式基本一致,意即情感的缘起和发展都符合自我内心需要,不做过多的修饰调整,或浓或淡,或喜或悲,均保持情感的本来状态。但情感是否需要自然流露,郭沫若与同时代的鲁迅及文研会作家的理念和旨趣则大异其趣,鲁迅认为情感最烈时不宜作诗,但郭沫若因为受个性主义与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影响,其创作无论是诗歌、小说还是历史剧均以情感的激烈率性、酣畅淋漓而著称,而这种情感“自然流露”的方式也成为郭沫若最与众不同的个性色彩与文体风格。放到五四人学的背景中,如此直面自我,大胆宣泄个人情感,体现出的是现代人对自我的解放,对个体感性生命的肯定,而这正是五四人学的核心精髓。
在郭沫若早期小说中,郭沫若早年生活的多种个人情绪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抒发。经济拮据、家庭受难、社会黑暗、前途无望带来的个人困窘、愤懑、不甘与自责等等情绪抒写比比皆是,如《漂流三部曲》之《歧路》中,爱牟对医学目下无用以及社会贫富乱相的满腹牢骚与抨击:“医学有甚么!能够杀得死寄生虫,能够杀得死微生物,能够把培养这些东西的社会制度灭得掉吗?……医学有甚么!有甚么!教我这样欺天灭理地去弄钱,我宁肯饿死!”③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206、188、171、28、89、91、147 页。在被生活折磨得焦头烂额时,偏遇到儿子啼哭要吃饽馅,爱牟一时气急败坏迁怒于儿子:“你们都是吃人的小魔王,卖人肉的小屠父,你们赤裸裸地把我暴露在血惨惨的现实里,你们割我的肉去卖钱,吸我的血去卖钱,都是为着你们要吃饽馅,饽馅,饽馅!啊,我简直是你们的肉馒头呀!”④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206、188、171、28、89、91、147 页。;《湖心亭》则痛斥了“我”的伪善自私:“我这个把她的爱情滥用的男子哟!我怎么还配乎骂她,和她口角呢?……我究竟有什么权利能够要求她为她百不相干的人再来牺牲呢?啊,你这个无情的伪善者!你不过怕伤你慈惠的假面子罢了!你不过放不下架子去替别人当差罢了!”;⑤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206、188、171、28、89、91、147 页。收到妻子别后自日本寄来的第一封信时,爱牟欣喜若狂:“我们的血简直是不值钱的苋菜水,甚么叫艺术,甚么叫文学,甚么叫名誉,甚么叫事业哟!这些镀金的套狗圈,我是甚么都不要了,我不要丢去了我的人性做个甚么艺术家,我只要赤裸裸的做着一个人。我就是当讨口子也可以,我就死在海外也可以,我是要做我爱人的丈夫,做我爱子的慈父……女人哟,女人哟,女人哟,你是为我而受苦的女人哟,我是你的,我是你的,我永远是你的!”⑥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206、188、171、28、89、91、147 页。
这些血泪文字因为散发着滚烫鲜活的情感和真实的个性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文学魅力。情感作为人类确认自我与存在的重要依据之一,对于情感的挖掘与重视、肯定与展现,体现的是对人性的关怀与抚慰,是人性觉醒的重要表现。郭沫若也正是因为激烈丰沛的情感烈度成为现代文坛不可取代的作家。在叙述功能上,情感使小说人物形象更鲜明,个性更丰满;在接受层面上也更易与读者产生共情。此外,由于小说情感表达在小说主体建构中的强化,小说的抒情性、主观性得以增强,尽管小说的叙事功能因此被弱化,但强化了的情感弥补了小说叙事的不足,一以贯之酣畅淋漓的情感依然较好地维持了小说主体的完整性。现代文学最早的散文化小说即是在创造社郁达夫、郭沫若等的抒情性小说实践中形成的。
四
郭沫若早期小说大胆袒露个人隐私,剖析内心不够“纯洁”的灵魂,也体现出五四人学“以真为美”的美学评价标准。“普遍与真挚”,在周作人看来是贵族文学与平民文学的根本区别所在,认为文学作品“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①周作人:《平民的文学》,第211页。真即美。将人性的真而非道德的善作为新文学表现内容和判断的标准,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在文学上的深刻体现,也体现出五四人学思想对人性复杂多元的巨大包容性。真,注重存在的事实、现象;道德的善,则是对事实和现象的道德判断,它会因价值的合理性而否定事实的存在。若以人性为例,讲真,是尊重人性存在的一切现象和事实,讲善,则可能会从价值结果对人性进行粗暴的选择或切割。诚如“兽性与神性,合起来便只是人性”,②周作人:《人的文学》,第193-196页。兽性、神性、善恶、美丑均是人性,这才是人性最大的“真”,也是文学最高的“美”。
郭沫若的早期小说与郁达夫《沉沦》一起,均在“以真为美”的现代人学审美思潮建立的过程中做出了卓越贡献。郁达夫《沉沦》揭示了现代人灵肉分裂的痛苦,郭沫若小说则更多地表现了现代人婚姻中忠诚与背叛的矛盾。《残春》叙述了爱牟的一段“伤感的情趣”。③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28、89、96、89、84页。爱牟到医院探望友人病,偶遇有处子之美的看护S小姐,于是夜间梦见s小姐袒露出“剥壳荔枝”般的两肩与“蔷薇花蕾”般的双乳向爱牟问诊,正当爱牟心襟摇曳时,友人来报其妻如“美狄亚”般手刃了自己的两个儿子,正提着血淋淋的短刀向爱牟投来,惊得爱牟急忙醒来,第二天赶紧回到妻儿身边,向妻子忏悔自己梦中的荒唐,却也兀自感伤自己赠予S姑娘的红蔷薇片片枯萎。小说以梦的形式暴露了爱牟潜意识的原欲冲动,揭示了一个已婚男子深层的性意识,从一个侧面展现了人性的真与复杂。
《喀尔美萝姑娘》较之《残春》,主人公婚姻内的背叛行为则从梦境变成现实行为。小说叙述了一个工科大学二年生男子有一个圣母玛利亚一样的妻子,“但却是把她爱成母亲一样,爱成姐姐一样。”④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28、89、96、89、84页。当遇到小巷内卖糖饼(喀尔美萝,日语里即用糖熬制的甜食)的一个十六七岁长着浓密睫毛,脸上有着处女红的姑娘时终于“尝着了一种对于异性的爱慕”,于是像一个怀春的处子般追逐起喀尔美萝姑娘,而且“起了一种不可遏抑的淫欲!”,甚至“听她亲自说出我爱你的一声,我便死也心甘情愿!”⑤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28、89、96、89、84页。两年时间里“我”就这般放纵地在婚姻内单恋、意淫、白日梦般地追逐着另一个女人。灵肉分裂的生活让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伪善者”。但是宽容圣洁的妻子崇高的美德无法抵挡来自喀尔美萝姑娘的本能诱惑,他一次次撒谎欺骗背叛,弗洛伊德所谓的本我冲动,快乐原则驱使爱牟在情欲的泥淖里不能自拔。作为人夫,他有忠诚的义务,作为人,他有爱的权利:“我终竟是人,我不是拿撒勒的耶稣,我也不是阿育国的王子,我在这个世界上爱欲的追求,我总不能说我是没有这个权利。”⑥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28、89、96、89、84页。本我的真与道德的善在爱牟身上纠结缠绕,爱牟陷入内心的分裂中。的确,人有爱的本能与权利,也会有错爱的软肋与弱点,一爱一错之间人性的善恶美丑、光明与黑暗、天堂与地狱才暴露无遗。因此,即使是道德不洁,“我”仍然坚持“要把我的内生活赤裸裸的写出来,冒着朋友们唾骂我、不屑我”。⑦郭沫若:《沫若文集(第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第 28、89、96、89、84页。事实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总是以直面人类的痛苦与矛盾而获得经久不衰的文学魅力。
《叶罗提之墓》也是郭沫若早期小说里惊世骇俗,极具先锋气质的一篇。小说叙述了从“他”七岁开始的十年间与“他”的堂嫂叶罗提的忘年恋、不伦恋。小说中细致地描写了一个未成年孩子懵懂隐秘的性体验,比如牵嫂嫂的手,亲吻嫂嫂的手,和酒含下嫂嫂送“他”的顶针,甚至向嫂嫂吐露情肠,这些有违伦常的爱欲体验极大地挑战了当时人们的道德神经,相比《沉沦》揭示的“性爱扭曲”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个题材虽然触犯了某种道德禁忌,但从现代两性关系的研究来看,确也是人性的真实之一。郭沫若该小说创作于1924年,虽然是受到弗洛伊德学说的启发和影响的结果,但也显示了其对人性真相探索的兴趣和勇气,较之30年代有相同趣味的上海新感觉派的心理分析小说而言,郭沫若的小说尝试时间提前了近十年,因此其开拓与探索意义不言而喻。
综上,郭沫若早期小说虽然数量不多,且写作的延续性不长,但其早期已有的21篇小说,显示了郭沫若过人的艺术触觉、大胆尝试的艺术创新精神以及热烈率真的个性,是对五四人的文学浪潮的有力支持与呼应,壮大了五四人的文学的创作实绩。
——《西泠印社社藏名家大系·李叔同卷:印藏》评介
——中国历代绘画大系”先秦汉唐、宋、元画特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