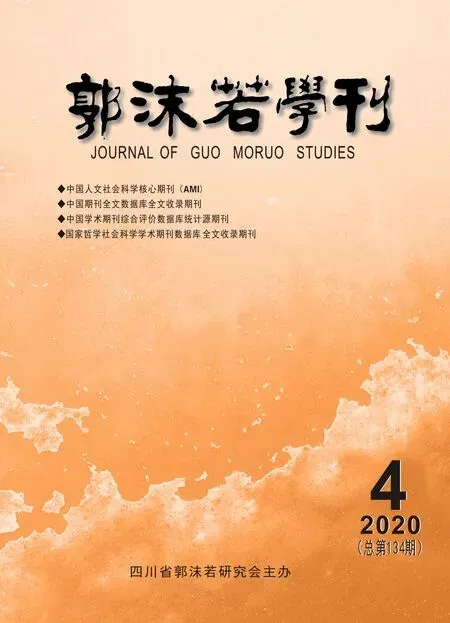郭沫若《题鲁实先〈汉鸿嘉以来气朔表〉》献疑
杨胜宽
(乐山师范学院 文学与新闻学院,四川 乐山 614000)
庆云先生近撰《天才的赞歌——郭沫若赞鲁实先的诗和词》一文,刊于《郭沫若学刊》2020年第2期。笔者身为《学刊》编辑,得以先睹为快。文中提及郭沫若于1942年为鲁实先《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一书所作题诗,围绕该题诗的首次发表及后来收入郭沫若作品集、全集的相关情况,庆云先生重点指出了林甘泉、蔡震主编的《郭沫若年谱长编》第二卷1942年9月1日谱文“诗为赞鲁实先《〈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而作”的事实认定失误等问题,不仅对《长编》日后修订完善具有建设性作用,而且对于郭沫若研究者弄清这一鲜为人知的郭沫若生平事迹中的一段学术因缘,也有助益。因为处理编校过程中的一些知识和技术性问题,笔者上网搜寻一些相关信息,请图书情报专业人士帮助查找原始资料,核对《郭沫若全集》第2卷《汐集》收录《气朔篇》的正文及注释内容,觉得仍然有些疑问难以释怀。故接着庆云先生的话题,就有关疑问逐一提出,希望问题得到感兴趣者,尤其是古代历法研究方面的专家进一步探讨,并最终使之获得圆满解决。
一、关于“鸿嘉”与“阳嘉”
庆云先生的文章提到了郭沫若的题诗1944年在《真理杂志》第一卷第三期刊登的题目是《题鲁实先〈汉鸿嘉以来气朔表〉》,诗中也有“气朔今始鸿嘉年”之句,我们从其提供的影印件看得非常清楚。而在1959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郭沫若的作品集《潮汐集》时,该诗收入《汐集》中,不仅诗题改成了《气朔篇》,而且上述诗句的“鸿嘉”也改成了“阳嘉”。庆云先生文中没有对诗题及诗句中年号的改变进行辨析,只是以列表对照的方式,显示出被改动的情况。
实际上,这个汉代年号的改变,可能是错误的,并且因为诗题改变之后,使后来《郭沫若全集》的编纂者完全发现不了其中是否存在什么问题。由于迄今为止没有找到鲁实先的《汉鸿嘉以来气朔表》原著,新近图情专业人员查到鲁实先之子鲁传先追述其父一生行实及学术研究情况的有关文章,该书被列入其父8种未刊历学著述之一①鲁传先:《国学大师鲁实先先生》,长沙市明德中学百年校庆纪念文集《百年明德 磨血育人》,2003年版,第304页,第303-304页。,看来并未正式出版过,其中涉及的问题只能根据郭沫若题诗显示的信息来进行综合分析判断。
笔者提出诗句将“鸿嘉”改为“阳嘉”可能是一个错误的看法,首先当然是依据郭沫若题诗最早在《真理杂志》发表的初始文献信息。显然,诗题明言鲁实先的《气朔表》是“汉鸿嘉以来”,说明其所制《气朔表》的起始年限是西汉鸿嘉,而非东汉阳嘉。《郭沫若全集》的注释者云:“阳嘉,东汉顺帝年号,公元一三二-一三五年。”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气朔篇》注①,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2页。但注释者可能没有注意到,汉代不仅东汉顺帝有“阳嘉”的年号,西汉成帝还有“鸿嘉”的年号(公元前20-前17)。至于笔者认为“鸿嘉”不误而“阳嘉”误的详细原因,下文再专门进行解析。
其次是笔者所搜寻到的一些佐证材料。鲁实先之子鲁传先,手中保存有其父亲当年与一些学者及研究单位的往来书信,其中涉及到鲁实先该部专著出版的具体内容,其所提供的信息足以证明,鲁实先所著之书,的确为《汉鸿嘉以来气朔表》。其中尤为显著明白的是国立编译馆致鲁实先的两封信函,1942年7月9日的信函内容为:
迳(径)启者:关于大著《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一稿所提示数点,已交供审查人参考,并经审查会议通过。稿拟留馆出版,正呈请教育部核定奖助中。用特函复,即希查照为荷。
此致
鲁实先先生
国立编译馆谨启
(一九四二年)七月九日
1943年2月2日的信函内容为:
迳(径)启者:陈副馆长转来一月十八日台函业已奉悉。尊著《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一稿已经审查,决定留馆出版,并已由教育部照甲种奖助金留稿标准发给奖助金伍仟元。兹遵章寄上著作权让与契约二纸,希即分别填盖,以一份寄掷本馆存执。再台端以此稿尚有空白须待补苴,嘱将原稿发还,俟补苴功竣即行缴回一节,自应遵办。将原稿二册奉上,并希补苴完毕立予掷还,以便办理出版为荷。此致鲁实先先生
国立编译馆启
(一九四三年)二月二日
附《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二册,著作权让与契约二份,空白收据一张。③鲁传先整理:《鲁实先珍藏书信》,湖南省文史研究院:《文史拾遗》2017年第3期。
以上两封书信表明,第一,鲁实先的著作名称是《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书稿为两册;第二,早在1942年上半年,鲁实先就将书稿寄给了国立编译馆,后者留存其书稿,并积极为之争取教育部的出版奖助金;在奖助金争取成功之后,国立编译馆将书稿交由专业人士进行学术审查,并且在1943年初获得通过;对于审查者提出的问题,国立编译馆要求作者进行修改补充,完成以后尽快交还;国立编译馆方面明确告知鲁实先,将争取到教育部甲种奖助金5000元发给作者,作为购买该书出版的版权。还随函附有出版契约二份,空白收据一张,让其完成出版前的必要手续。
似乎书稿出版的事已经万事俱备,水到渠成,不该有任何困难与意外。但不知何故,该书并未在国立编译馆出版。后来由高霁云为其提供一笔“天文奖金”给予特别资助,作为出版费用。而根据其子鲁传先提供的信息,该书依然未获正式出版。据称,包括该书稿在内的一竹箱鲁实先书稿,按照有关方面的指示于1950年运往湖南宁乡县封存,但不知后来的下落。④鲁传先:《国学大师鲁实先先生》,长沙市明德中学百年校庆纪念文集《百年明德 磨血育人》,2003年版,第304页,第303-304页。庆云先生的文章指出,郭沫若的题诗在《真理杂志》发表时没有署明日期,1959年收入《汐集》时才加署为1942年9月1日。显然,《郭沫若年谱长编》正是依据这个时间来撰写1942年9月1日谱文的。如果郭沫若所署日期无误,则其所见似乎只能是鲁实先的手稿而非正式出版物。但直至1943年2月,国立编译馆还在跟鲁实先交涉其专著的出版事宜,其手稿自1942年7月起就一直在国立编译馆方面,郭沫若是什么时候看到手稿的?鲁实先会不会把一部重要手稿交给并无多少交往的郭沫若?不是为了出版又是出于何种目的?这些问题或许得等到郭沫若的全部日记公开出版以后,看是否能寻找到确切答案。
鲁传先所撰《父亲鲁实先行谊》《国学大师鲁实先先生》等文章中,提及该书的书名,也都是《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且谓该书在其父1942年秋到复旦大学任职之前就已写成。①鲁传先:《父亲鲁实先行谊》,网址:http://bbs.gsr.org.tw/cgi-bin/topic.cgi·forum=27&topic=2990。此后因为联系出版遇到一系列原因不明的波折,故始终未能成功。
再次是郭沫若诗中明确提到:“通缠一千五百载,正统偏霸上下篇;上接古史天象表,下与郑著相蝉联”。表明《气朔表》所列的时间跨度为一千五百载,而在时间下限的处理上,是与郑鹤声的《近世中西史日对照表》相衔接的。郑氏的《对照表》,上起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下迄中华民国三十年(1941),总共426年,其书于1936年由国立编译馆出版。显然,鲁实先是看到过此书的,甚至可能在编著体例上都有所借鉴,故不仅在时间的下限上与之衔接,而且书成之后,首先想到也交由国立编译馆出版。国立编译馆之所以很快表示乐于出版该书,并积极为之争取奖助经费,正是因为其书与郑著的“姊妹篇”关系。如果以西汉成帝鸿嘉元年起计算,下至明武宗正德十年(1515),共计为1536年,与郭诗举其成数而言一千五百载正相吻合。而如果从东汉顺帝阳嘉元年(132)起算,时间跨度则只有1383年,尚不足1400年,与诗言“通缠一千五百载”明显不合。
现在回过头来专门讨论前面提到的鲁实先《气朔表》究竟是始于“鸿嘉”还是“阳嘉”的历法相关问题。因为这里面牵涉的,不只是一个年号的对错问题,它实际上跟汉朝的三次修订历法活动有着直接关联。一代王朝获得政权以后,采用什么历法,成为昭示其统治权及其行使权力合法性的一个重要标志。故《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王正月”何休注:“王者受命,必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变牺牲、异器械,明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公羊传注疏》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96页。司马迁《史记·历书》亦云:“王者易姓受命,必慎始初,改正朔,易服色,推本天元,顺承厥意。”司马贞《索引》:“言王者易姓而兴,必当推本天之元气行运所在,以定正朔,以承天意,故云承顺厥意。”③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6页,第1260页。在汉朝统治的四百余年间,重大的修历活动共有三次,分别在西汉武帝、成帝及东汉章帝时。
西汉开国,高祖沿用秦朝的正朔服色,当是未暇顾及新造历法的权宜之计。到文帝时,大臣纷纷上言改正朔、易服色,但因为意见难以取得一致,改历之事始终未成。武帝时,招方士唐都、巴郡落下闳等承担修历之事。《史记·历书》称:“巴落下闳运算转历,然后日辰之度与夏正同。乃改元,更官号,封泰山。”《索引》“姚氏案”引《益都耆旧传》:“闳字长公。明晓天文,隐于落下,武帝征待诏太史,于地中转浑天,改《颛顼历》作《太初历》。”④司马迁:《史记》卷二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256页,第1260页。此历从太初元年开始使用,史称《太初历》。该历确立了一年以正月为岁首,与夏朝的正朔相同,此后数千年均沿用这一正朔,故后世也称农历为夏历。
到汉成帝时,启动了又一次朝廷的修历活动,主其事者,则为刘向、刘歆父子。《汉书·律历志》:“至孝成世,刘向总六历,列是非,作《五纪论》。向子歆究其微眇,作《三统历》及《谱》,以说《春秋》,推法密要。”⑤班固:《汉书》卷二十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79页。看来,刘向将列朝所制的六种历书(指黄帝历、颛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加以对比,比较其中的是非得失,目的是为制作新历做基础性准备工作。所谓《五纪论》,其全文已经不可得见,而在《宋书·天文志》中保存了《五纪说》及《五纪论》的部分文字,后收录于清人严可均所辑的《全汉文》中。观刘向《五纪说》有“此三说,夏历皆违之,迹其意,好异者之所为也”⑥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三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335页。的话,已能见出其不完全赞同以夏正为定准的《太初历》之明确态度。而刘歆继父志而成《三统历》及《谱》,均以班固《律历志》上、下照录原文而得以保存下来。⑦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卷四十一,严氏在《三统历》文末加案语云:“《律历志下》,仅末一条系班固所补,其全卷皆《三统历谱》也。”第351页。此历在孺子居摄2年(公元前7)正式开始使用,此时正王莽专权、刘歆受宠。
东汉唯一的一次朝廷正式修历活动,在汉章帝时。关于此次修历的过程及具体情况,范晔《后汉书·律历志》言之颇详。其中有“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益远,日月宿度相觉浸多”“章帝知有谬错,以问史官”等语①范晔:《后汉书·律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26,3033,3037页。,表明在公元85年,朝廷就把修历问题列入了议事日程。章帝在关于修历的诏书中说:“间者以来,政治不得,阴阳不和,灾异不息,疠疫之气,流伤于牛,农本不播。夫庶征休咎,五事之应,咸在朕躬,信有闕矣,将何以补之?”②范晔:《后汉书·律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26,3033,3037页。治历官员编、李梵、卫承、李崇等人参与了此次新历的修订工作,该历史称《四分历》。根据范晔的说法,“及用《四分》,亦(启)于建武,施于元和,讫于永元,七十余年,然后仪式备立,司候有准”。③范晔:《后汉书·律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26,3033,3037页。则有意于修改刘歆所制的《三统历》,是从汉光武帝取得政权之时就开始动议的,而到了汉章帝时才进入实际制作阶段,直至汉和帝在位时期,《四分历》还在不断修正过程中。
需要特别指出,在汉顺帝时,的确有过一次修历的动议,具载于《后汉书·律历志中》。汉安二年(144),尚书侍郎边诏上书,对章帝所推行之《四分历》提出质疑,太史令虞恭、治历宗为此上书皇帝回应质疑,把《四分历》动议起始点追溯到了西汉文帝时,表明不宜轻易更改的立场。其奏疏言:“自古及今,圣帝明王,莫不取言于羲和、常占之官。定精微于晷仪,正众疑,秘藏中书,改行《四分》之原。及光武帝数下诏书,草创其端,孝明皇帝课校其实,孝章皇帝宣行其法。君更三圣,年历数十,信而征之,举而行之。其元则上统开辟,其数则复古《四分》。”他们的意见得到顺帝的认同。④范晔:《后汉书·律历志中》,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26,3033,3037页。由此看来,顺帝时有过修订历书的官员动议,但最后被顺帝否决了。
综上所述,鲁实先的天文学专著《汉鸿嘉以来气朔表》,其时间起始点应为西汉鸿嘉而非东汉阳嘉;郭沫若最早发表于《真理杂志》的题诗,其题目及诗中关于年号的表述应是正确的。现在无法弄清的问题是,为什么1959年编辑出版郭沫若的《潮汐集》时,从作品题目到诗句文字发生了如此明显的重大改变,且两个年号彼此矛盾,作者和编者均未做出任何说明,究竟在哪个环节出了问题?郭沫若1942年9月初就写成的题诗,何以在1944年才发表出来,这中间有没有其后来追记署时错误的可能性?
二、关于“《气朔表》”与“《气朔篇》”
笔者之所以把郭沫若1944年在《真理杂志》上发表的《题鲁实先〈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一诗,在收录到《汐集》中将诗题改为《气朔篇》称为一个失误,主要基于以下理由:
首先,郭沫若的此首诗作,属于题赠类性质,原题十分清楚地显示了作为题赠诗,必须点明的写作要素:为谁而题,所题何事。这是题赠类作品创作与其他诗歌题材创作不一样的基本特征。显然,这首诗是郭沫若在阅读了鲁实先的《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之后而写的,因为有感于该书的学术价值及社会意义,故专门写了这样一首具有“读后感”意味的题赠诗,表达其对鲁实先的赞佩之意。诚如庆云先生文章所言,郭沫若把鲁实先视为“国内罕见的天才”。这一印象的获得,我们从其题词评价鲁实先的《〈史记会注考证〉驳议》一书完全可以得到印证。郭沫若在该题词的附注里说:“鲁君与余,初无识面,远道将其书见惠,赋以赠之。鲁君之年,闻仅二十有六岁也”。由此可知,郭沫若与鲁实先以前彼此并未蒙面,也不熟悉,并且对于其年龄之类的基本信息,都是靠“闻”之得来。因为对方主动将其书寄给郭沫若,他们两人才算是有了初次学术之缘。在郭沫若看来,鲁实先二十多岁就能够写出如此高水平的学术专著,并且有勇气挑战被日本学界奉为学术权威的泷川龟太郎,是很值得肯定和鼓励的。有了1940年的这段交往经历,1942年前后,鲁实先又将新著《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书稿呈送郭沫若,寻求推介以扩大影响,似乎就是比较自然的事情了。郭沫若读过书稿之后,以题诗的方式作出评价,给予高度推许,这在当时已经属于史学界名流且正在国统区从事文化领导工作的郭沫若来说,是很正常的,也是应该做出的一种必要反馈。因此,初刊时的题目,清晰交代了为鲁实先所著《气朔表》一书而作的写作缘由,其要素信息具有唯一性,不可移用于别人别事别处。
而将该诗改名为《气朔篇》,其弊端显而易见。一般读者,如果不认真阅读全诗,根本不明白该诗题目的含义是什么。因为“气朔”作为一个天文历法术语,恐怕只有专业人士才容易懂得其基本内涵。何谓“气朔”?“百度百科”的解释是:“指显示吉凶的云气和每月的朔日。”南朝齐王融《三月三日曲水诗序》:“絜壶宣夜,辨气朔于灵台。”李善注引郑玄《毛诗笺》曰:“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又引《左氏传》曰:“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①萧统编选,李善注:《文选》卷四十六,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49页。所引郑笺,出于《诗·大雅·灵台》,据说灵台是周文王所筑,用来观察阴阳之气相侵的变化,及由此昭示的吉凶。所引《左传》,出自《左传·僖公五年》,原文云:“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台以望,而书云物,礼也。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为备故也。”杜预注:“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启,立春、立夏;闭,立秋、立冬。云物,气色灾变也。……素察妖祥,逆为之备。”②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794页。周历与鲁历(《春秋》历)都以十一月为岁首,鲁僖公在正月的朔日登台观气象,根据分、至、启、闭的时令节气,来判断是否有什么吉凶的征候,以便早作准备。可见,鲁实先所作的《气朔表》,正是依照一年四季的节气、一月的朔望、一日的时辰等彼此对应关系制成一千五百余载的长历表。其年历的体例或许是参照蔡邕所极力倡导的干支纪年法,此法年、月、日、时均以干支来推算排列,二十四节气是这种历法的重要时令要素,其详细内容具载于《后汉书·律历志下》。③范晔:《后汉书·律历志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077—3079页。《气朔篇》这个名称实际上难以体现这些重要信息。
其次,将《题鲁实先〈汉鸿嘉以来气朔表〉》改名为《气朔篇》,原来不可或缺的关键信息被淹没,而作者对此没有任何解释性说明,是十分令人困惑的。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编辑出版的《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看,《气朔篇》共有六条注释,其中作者自注四条,编者注释二条,而无论作者还是编者,对改换诗题均避而不谈,按照常理是说不过去的。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该卷“说明”云:“《汐集》原为一九五九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潮汐集》中的后半部分,是作者解放前所作部分旧体诗词。……这些诗词编集前大部分没有发表过,其中有些是作者从日记选录出来的,其余均为散见其他著作中而没有编入的作品。现按一九六〇年第二次印刷本出版后作者的校订本编入。”④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卷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2页。照此说来,包括《气朔篇》在内的1960年再版的《汐集》收录的全部旧体诗词,都是经过郭沫若自己亲自校订的,可能其中的四条自注,就是此次校订时所加,但为什么对诗题作了如此明显的改动,却未给出任何说明?照理说,应该特别注明该诗初刊于何时、何种报刊、所用何题,甚至改用现题出于何种考虑,都必须向作者进行交代,以免造成误解或者认识上的困难,尤其是像此篇内容涉及的一般人比较陌生的天文历法内容。郭沫若在校订时理应想到这一点,并作出相应处理。其实,我们从《汐集》中,能够看到作者进行过给出说明处理的例证。比如《牧童与水牛唱和》(西江月)一首,初刊于1946年4月1日上海《文艺》月刊第二期,题目是《风雨归牧》。词的正文前有作者词序云:“(李)可染作《风雨归牧图》,索题,因托牧童与水牛唱和。”收入《汐集》时改为《牧童与水牛唱和》这个题目。⑤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第262页,304页,252页,197页。又如《题画翎毛花卉三首》,初刊于《新蜀报·蜀道》时的诗题为《之佛画展嘱题》,系受工笔画家陈之佛之嘱而作的,编入《汐集》时隐去了嘱托者之名,改用现名。⑥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第262页,304页,252页,197页。而由编辑者加注说明这类情况的例子更多。如《祝新华日报五周年》一诗,就有编者注:“本篇初发于1943年1月18日《新华日报》,原题为《祝新华五周年》。”⑦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第262页,304页,252页,197页。与《气朔篇》改名颇为类似的则是《双十一》一诗,该诗编者注:“本篇最初发表于1945年1月7日《新华日报》,原题《衡老以双十一追忆诗见寄,步韵却酬,兼呈亚子先生》。”⑧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第262页,304页,252页,197页。根据郭沫若的诗序可知,1944年11月11日,柳亚子从桂林来到重庆,郭沫若设宴为之洗尘,参加宴席的沈钧儒(衡老)即席赋诗一首,呈郭沫若、柳亚子二人,郭沫若乃步沈作原韵而作此诗。如果没有其用诗序对作诗背景进行特别说明,必然会给阅读者造成理解上的一定困难。
再次,就诗中的文字改动而言,似乎修改后的诗句并不明显地显得比原来都好,有的甚至改出了问题。按照庆云先生所列对比表,有改动的诗句共九句,主要体现在用词方面的修改。有改后比原来更显精确的,比如把“通缠”改为“通躔”,“躔”字是一个天文术语,《汉书·律历志上》:“日月初躔,星之纪也。”颜师古注引孟康曰:“躔,舍也。二十八舍列在四方,日月行焉,起于星纪,而又周之,犹四声为宫纪也。”①班固:《汉书》卷二十一上,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9965-966页。又如把“国步遘播迁”改为“国步遭播迁”,“闢阖如璣璿”改为“辟阖如玑璇”,比原来稍显通俗易懂。有的属于可改可不改,如把“详密”改为“详核”,“并坤乾”改为“亟坤乾”,各有胜义,不一定有孰优孰劣之分。有的则改得不如原来,如把“青年学士”改为“青年学徒”,“其才其学”改为“追踪司马”,都不如原来用词涵义的庄重与周洽。至于改出问题的,则是把“鸿嘉”改为“阳嘉”,两个年号前后相差一百多年,且后者不仅与鲁实先专著的名称相矛盾,也与作者题诗的题目相矛盾,而出现这样明显的矛盾,作者校订时并未给出任何解释,原因何在?
三、关于郭沫若对鲁实先《气朔表》评价的一些猜想
庆云先生的文章,对于郭沫若《题鲁实先〈汉鸿嘉以来气朔表〉》的初刊、收入其作品集及后来编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的情况有所介绍,重点放在了对《郭沫若年谱长编》的一些失误的驳正上,而其对郭沫若题诗评价《气朔表》的问题没有过多正面涉及。上文已经提出,1959年在交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其《潮汐集》时,郭沫若对所收录的作品是亲自作过校订的,修改诗题及部分诗句的措辞,应该都是郭沫若本人所为,但这种修改,似乎改得并不算高明,甚至还出现了自相矛盾的错误。出现这种情况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它是否与郭沫若在时过境迁之后的评价态度发生某种微妙变化有关?
讨论郭沫若对鲁实先《气朔表》的评价问题,可以把它与其对鲁实先的另一部专著《〈史记会注考证〉驳议》的评价联系起来加以考察。据庆云先生的文章介绍,郭沫若题鲁氏《驳议》一词,发表于1940年7月29日《新民报》,似乎当时的词题应为《奉赞〈史记会注考证驳议〉调寄满江红》,而后来收入《蜩塘集》时才改题《满江红》,今本《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二卷亦沿用此题。根据该卷编纂“说明”,《蜩塘集》收录的是郭沫若1939至1947年创作的作品,初版于1948年,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发行。1957年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沫若文集》时,作者对其中部分作品进行了删增处理。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卷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表明1957年出版的《沫若文集》,同样经过了作者本人的审阅校订。与对《题鲁实先〈汉鸿嘉以来气朔表〉》一诗的处理手法一样,郭沫若的题词也采取了在题目中隐去“本事”(即题赠作品一般必须交代的题赠对象相关信息)的方式,而简化为没有特定对象的“类型”题目,比如《满江红》作为一个旧体词的词牌,在作者的旧体词中数次使用,如解放以后的60年代就曾三次使用过这个词牌,作词七首。③丁茂远:《郭沫若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下编 新中国成立后》,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377页。分别见第371页,第375-376页,第378-379页。这些作品,只有在阅读了其词序和正文之后,才能明白所表达的具体内容。而在《汐集》中,作者使用旧词牌的有如下几例:《鹧鸪天四首—吊杨二妹》《望海潮(挽张曙)》《水调歌头(赠广东艺人)》。④丁茂远:《郭沫若集外散佚诗词考释·下编 新中国成立后》,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14-377页。分别见第371页,第375-376页,第378-379页。所举的这三首词,题目中除用旧词牌外,均有一个提示作品主要内容的副标题,读者一看便知道作品为何而作。但题赠鲁实先的《满江红》词,却连副标题也没有,必须看词序才能明白作品的具体内容。这种细微的不同之处,可能是作者在解放以后的50年代校订其旧作时,已经身居国家领导人高位,鉴于当时大陆与台湾处于紧张的敌对关系之中,而鲁实先此时却身在台湾,可以视为为国民党反动派效力,看待其身份与影响跟40年代的全民抗战形势已然两样,故郭沫若在处理题赠其作品时,显得格外小心谨慎。标题中隐去其名其书,便是这种技巧性处理方式的印证。
对于郭沫若《气朔篇》对鲁实先《气朔表》的评价,全诗由四十句构成。庆云先生的文章说,全诗可作三层意思理解,前22句是“赞颂鲁实先写作的努力,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中间18句是“赞颂霁云老人的慷慨相助,使作品得以面世”;最末2句是“赞颂者的希望”。笔者的理解与庆云先生不尽一致:具体说来,诗的前24句,是对鲁实先《气朔表》一书的正面评价,第23-24句云:“天地低昂入我拳,坐看日月双昭悬”,是对《气朔表》一书赞扬之辞,意谓读者手握一册,则天地日月之运行轨迹,昭彰明白,一查即得,使用起来极为方便。诗意与前面连贯,故当归属第一层。中间的13句可为第二层,是对高霁云慷慨资助《气朔表》一书出版所发挥的社会作用加以肯定和赞美,尤其强调了此书对于延续中华文明的特别意义,所谓“国脉赖之得永延,文化长城万里坚”,即此可见。最容易引起理解分歧的在于诗末6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的标点处理,将“煌煌华夏万古完,终始不绝亟坤乾”点为上下句,故一用逗号,一用句号;接下来“谁能使之可崩骞”句末加问号,则其意当属下,就成了末四句为意。依笔者看,诗的末6句皆三句为意,“终始不绝亟坤乾”句末当用逗号,直贯到“谁能使之可崩骞”,三句的意思是再次强调中华民族历史悠久,坚固不崩,万古不绝,谁也不能改变之。“崩骞”一词,系用《诗经·小雅·天保》“如南山之寿,不骞不崩”的典故。孔颖达谓该诗此章“说(王位)坚固之状,……坚固如南山之寿,不骞亏、不崩坏”。①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毛诗正义》卷九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12页。郭诗这三句实际上是与前面称赞高霁云出资资助行为的作用和意义相连贯的,故宜归入第二层。诗的最末三句为第三层,是诗作者表达的殷切希望,观“尤望继兹次第传”句,此意甚明。希望学术界继续努力,再出佳作。需要说明的是,何以全诗其他都是两句为意,最末6句却变成了三句为意?因为郭沫若这首诗属于旧体诗中的古体诗(与之对应的是近体诗),古体诗在句式、格律、对仗等方面都较近体诗灵活,诗人出于表达的需要,可以不拘于近体之排律诗那样,必须两两为句,且必须上下句对仗工稳。
总体而言,郭沫若对鲁实先《气朔表》的评价是比较高的,特别肯定其在延续华夏文明史方面的作用与意义,故诗中反复提及之。但天文历算毕竟是一个很专门的领域,郭沫若虽然博学多识,但在历算方面似乎着力不多,这在其评价《气朔表》中也体现出不擅此道的某些弱点。除了前面论及的“阳嘉”修改的失误之外,诗中还有一些评价也显得不甚中肯。比如“《通鉴目录》何足数”一句,拿来赞扬鲁实先的历法表,就多少显得有些不伦不类。《通鉴目录》为宋代著名史学家司马光所撰,他因为撰成《资治通鉴》这样的鸿篇巨著,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该书的纲目性内容,所以特撰《通鉴目录》。此书与鲁实先的天文历法专著,其实内容相距甚远,两者没有多少可比性。又如“景烁巧思入神化,厥美难可专于前”二句,郭沫若自注:“景烁乃祖暅字,祖冲之之子。”②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2卷《气朔篇》注⑤,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261页。祖冲之及其子祖暅,均擅长天文历算,祖冲之算出的圆周率,中外皆知,无需赘言;祖暅发明了计算几何体积“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的祖氏原理,其成就主要在于数学领域。但要说在历法方面的成就,祖冲之则远出其子祖暅之上。
祖冲之在《宋书》中无传,但该书《历志》则记载其修历事迹甚详。南北朝刘宋时期,刘裕灭晋夺得南方天下,令何承天制定出了本朝历法,史称《元嘉历》。到宋孝武帝时,南徐州从事史祖冲之上书奏言,指陈《元嘉历》的三大错谬,证据详核,理由充分,同时称自己所制定的新历,则完全纠正了这些错谬。他以此说服皇帝,希望改用其新历。但随即孝武帝崩驾,施行新历之事被搁置了。③沈约:《宋书》卷十三,《二十五史》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35—39页。后来在梁武帝时经过其子祖暅的三次上书争取,终于被颁布采用。因为此历制成于宋孝武帝大明年间,故史称《大明历》,也叫《甲子元历》。《隋书·律历志中》云:“天监三年下诏定历,员外散骑侍郎祖暅奏曰:‘臣先在晋已来,世居此职。……宋大明中,臣先人考古历法,以为正历,垂之于后,事皆符验,不可改张。’八年,暅又上书论之。诏使太史令将匠道秀等,候新旧二历气朔、交会及七曜行度,起八年十一月,讫九年七月,新历密,旧历疏。……至九年正月,用祖冲之所造《甲子元历》颁朔。”④魏征等撰:《隋书》卷十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416—417页。由于祖冲之的新历首次引入“岁差”计算来编制历书,其精确性胜过之前的所有历书。有关资料显示:“《大明历》采用的朔望月长度为29.5309日,这和利用现代天文手段测得的朔望月长度相差不到一秒钟。”⑤《百度百科·大明历》,网址:ttps://baike.baidu.com/item。在一千多年能够准确到这种程度,实在堪称奇迹。
由此可见,在历算方面卓有建树的是祖冲之,而非祖暅。郭沫若却说“景烁巧思入神化”,这要放在祖冲之身上倒恰如其分,而用之于祖暅,则显得有些名实不副。
如果要拿郭沫若赞扬鲁实先两部学术著作所题的诗词来比较一番,显然其评价《〈史记会注考证〉驳议》更加到位些,毕竟郭沫若对于《史记》的了解和研究要内行得多。像庆云先生文章中引述的鲁实先友人廖海廷对郭沫若题词所写的题识,连《驳议》一书通过汉简考定鲁昭公十七年有日蚀天象的细节都被他注意到了,不愧慧眼识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