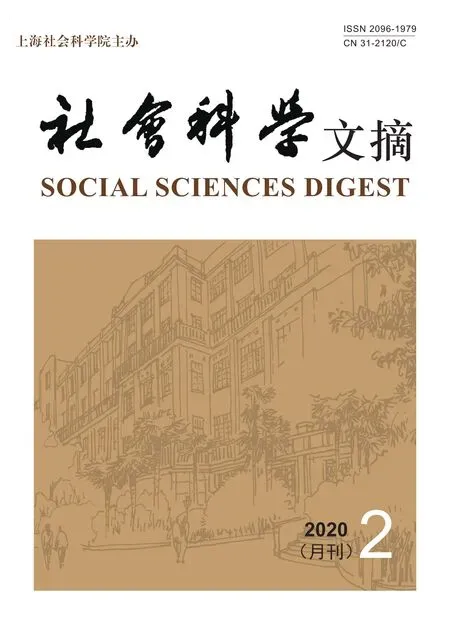民法典物权编规范配置的新思考
文/王轶
作为民法典编纂工作第二步的组成部分,民法典物权编将在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进行适度修订的基础上编纂完成。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配置关注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类型及其配置关系,属于民法典的规范类型及其配置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既事关未来民法典物权编的立法质量,又影响未来民法典物权编的法律适用。服务于妥当判断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效力的目的,依据法律规范协调利益关系的差异,以及法律规范功能的不同,对法律规范进行类型区分,同时完成体系建构,是此次民法典物权编编纂过程中的核心任务之一。
简单规范
民法典物权编编纂的过程中,服务于不同目的,存在着对法律规范进行类型区分和体系建构的不同路径。如果是服务于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妥当判断的目的,民法典物权编规范配置着重需要回答两个问题:其一,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排除民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的适用时,该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如何?其二,当事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民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时,该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如何?这是两个虽有关联,但又相互独立的问题。前者要回答的是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能否被民事法律行为约定排除其适用的问题;后者要回答的是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能否被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问题。对于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而言,这两个问题本身就能够发挥类型区分标准的作用。
一些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既不会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也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一些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可以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但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一些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既可以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又可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一些民法典物权编的规定,有时可以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但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有时既可以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意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又可以成为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违反的对象。
不同类型的法律规范或者协调不同类型的利益关系,或者在协调同一种类型利益关系的过程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发挥不同的作用。民法典物权编作为民法典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民法典其他各编一样,也是通过对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组织之间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设置相应的协调规则,来实现其组织社会秩序的功能。就民法典物权编而言,所谓“特定类型冲突的利益关系”,对应的就是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法律关系,它包括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主体与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还包括因物的归属和利用而产生的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包括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关系。
民法典物权编的范围内,引发民事主体之间利益关系以及民事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原因很多,如果结合民法学说对于民事法律事实所作的类型区分,至少包括:事件、事实行为、准民事法律行为和民事法律行为。其中,事件、事实行为以及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对应着民法法定主义的调控方式;民事法律行为,特别是合同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对应着民法意定主义的调控方式。
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法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律规范,如果调整的是事件引起的利益关系,此类法律规范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排除适用的对象,但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如民法典物权编草案关于因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的规定。物的附合或者混合得基于自然原因发生,此时物的归属问题就是属于事件引起的利益关系。《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第117条确认,“有约定的,按照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依照法律规定;法律没有规定的,按照充分发挥物的效用以及保护无过错的当事人的原则确定”。可见当事人能够借助民事法律行为约定排除该条关于因附合、混合而产生的物的归属的规定;但这一规定确立的是基于自然原因发生物的附合或者混合等特定事件发生,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的规则,因而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服务于妥当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目的,此类法律规范不存在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是否强制性规定类型区分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可称之为简单规范。对于此类法律规范,稳妥的做法是在民法典物权编确立纯粹的裁判规范,即此类裁判规范既不直接发挥行为规范的作用,也不因其反射作用间接发挥行为规范的功能。这与事件自身的特性有关,因为所谓事件,就是指与特定当事人的行为无关的民事法律事实。让此类裁判规范直接或者间接发挥行为规范的功能,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法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律规范,如果调整的是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此类法律规范同样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排除适用的对象,但也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此类法律规范如果协调的是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那就一定不会是《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言的强制性规定;即使此类法律规范协调的是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民事主体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也一定不会是《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所言的强制性规定。因为此类法律规范确立的是实施或者不实施特定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究竟会产生何种法律效果的规则,不可能成为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而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排除此类法律规范适用的约定,能够违反的也一定不是此类法律规范,而应当是法律或者行政法规上禁止约定排除此类法律规范适用的规定。就此而言,服务于妥当判断民事法律行为效力的目的,此类法律规范也不存在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是否为强制性规定类型区分的问题,在这种意义上,亦可称之为简单规范。对于此类法律规范,民法典物权编稳妥的做法应当是直接设置相应的裁判规范,通过该裁判规范对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各种类型的利益关系作出妥当的安排。此类裁判规范,一般并不直接发挥行为规范的功能,但它具有的反射作用,实际上确立了民事主体特定的行为准则,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兼具裁判规范和行为规范的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物权编中的简单规范,有其不简单之处:服务于妥当判断排除此类简单规范适用的约定效力如何的需要,根据此类简单规范能否被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约定排除其适用,可以对此类简单规范作进一步的类型区分。其一,有的协调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能够被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这就是学说上所谓“任意性规范”,排除其适用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其二,有的协调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不能被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这就是学说上与“任意性规范”对立存在的“强制性规范”,排除其适用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损害公共利益,得援引《民法总则》第153条第2款或者《合同法》第52条第4项等认定该行为无效。其三,在能够被约定排除其适用的“任意性规范”和不能被约定排除其适用的“强制性规范”之间,还存在有时能够被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有时不能被当事人约定排除其适用的“混合性规范”。混合性规范有时协调民事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有时协调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排除其适用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视具体情形,判断该行为有效或者无效。
复杂规范
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意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律规范,调整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此类法律规范也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排除适用的对象,与对应法定主义调控方式,调整事件、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的简单规范相同,因而也存在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混合性规范的类型区分。如《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第96条确认,“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以及对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作重大修缮、变更性质或者用途的,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但是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可以借助民事法律行为实施。该条规定明示其确立的法律规则可以经由当事人的约定排除其适用,当然属于任意性规范。
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意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律规范,如果调整的是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引起的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规定的是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协调方案,确立的是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条件,在通常情形下与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法定主义调控方式,调整事件、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的法律规范类似,此类法律规范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排除适用的对象,但不会成为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在这种意义上,也可称之为简单规范。
但民法典物权编对应意定主义调控方式的法律规范,还包含有与简单规范显有不同的法律规范:一是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与特定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以及当事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关系的规范;二是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的利益,但并非确立当事人之间的交易条件,以补充或者明确当事人之间的交易内容,而是确立当事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前置条件或者行为模式的规范。这两种法律规范既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排除适用的对象,又能够成为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因而需要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是否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在这种意义上,可称之为复杂规范。
民法典物权编的复杂规范成为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需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是否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时,可根据复杂规范所协调的利益关系类型的差异,作进一步的类型区分:
首先,是仅涉及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倡导性规范。如《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第141条确认,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应当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但共有人之间另有约定的除外。该规定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确立了当事人实施民事法律行为的前置条件,意在提倡和诱导当事人在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时满足特定的前置条件,以保障物权变动法律效果发生这一交易目标的实现。在共有人之间未作特别约定的情形,处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未经占份额三分之二以上的按份共有人或者全体共有人同意的,该合同效力不受影响,但合同义务的履行存在处分权欠缺的障碍,从而会影响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发生。其次,是涉及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尤其是合同行为当事人与特定第三人利益关系的授权第三人规范。如《民法典·物权编(草案)》第17条第1款确认,“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的协议或者签订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为保障将来实现物权,按照约定可以向登记机构申请预告登记。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的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的,不发生物权效力”。该规定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与特定第三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当事人签订买卖房屋或者其他不动产物权的协议,办理预告登记后,未经预告登记权利人同意,处分该不动产,预告登记权利人有权主张处分该不动产物权的合同相对自己无效。再次,是涉及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当事人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规定,它们属于《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所言强制性规定。
二元规范体系
服务于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作出妥当判断的目的,民法典物权编存在着二元的法律规范体系:其一,围绕着回答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排除民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的适用时,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何,存在着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混合性规范之分;其二,围绕着回答当事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民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时,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何,存在着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规范、强制性规范之别。
这个二元的法律规范体系,既相互关联,又各自独立。第一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任意性规范、强制性规范、混合性规范,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其中并非民事法律行为违反对象的,就不需要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是否“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第二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倡导性规范、授权第三人规范、强制性规范既能够成为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约定排除适用的对象,同时也能够成为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因此需要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作是否为“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
申言之,第一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强制性规范”与第二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强制性规范”尽管都关涉民事主体的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关系的调整,都承担着确认、保障、维护公共利益的使命,都不得被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约定排除其适用,但第一个法律规范体系中一些“强制性规范”对应民法典物权编法定主义的调控方式,协调事件、事实行为或者准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并非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一定不是《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以及《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中所言“强制性规定”。第二个法律规范体系中的“强制性规范”对应民法典物权编意定主义的调控方式,协调民事法律行为引起的利益关系,属于民事法律行为违反的对象,属于《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所言“强制性规定”。至于违反第二类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如何,还需要具体区分被民事法律行为所违反的强制性规定,究竟是要求当事人必须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还是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如果是要求当事人必须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即使被违反,也不导致民事法律行为绝对无效。如果是禁止当事人采用特定行为模式的强制性规定,还要进一步作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类型区分,只有违反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才能被确认为绝对无效。
结语
本文的分析意在说明,当事人借助民事法律行为意图排除民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的适用时,该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如何;与当事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民法典物权编某一规定时,该民事法律行为效力如何,是两个虽有关联,但显有不同的问题。民法典物权编的规范配置应当以这两个问题的类型区分为基础,有序展开,仔细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