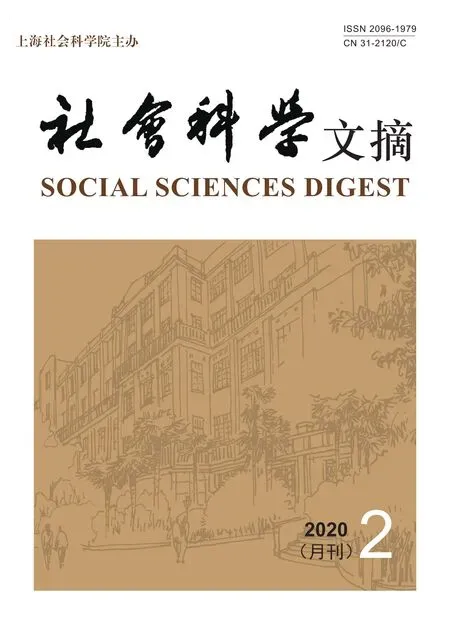“去耕种自己的园地”
——关于回归文学本位和批评传统的思考
文/张伯伟
201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新编了一种出版物——《古代文学前沿与评论》。在第一辑的卷首,刊登了一组总题为“‘十年前瞻’高峰论坛”的笔谈,汇集了当今活跃在学术研究第一线的21位老中青学者的发言稿,在一定程度上,将其视作对当下古代文学反思的代表,也许是合适的。在目前的古代文学研究中,以文献挤压批评,以考据取代分析,以文学外围的论述置换对作品的体悟解读,已是屡见不鲜的现象,究竟应该如何进行“文学”研究,竟成为横亘在古代文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以上反思代表了古代文学学界对当下研究现状与存在问题的某种担忧,但较真起来讲,上述意见不应该是文学研究中的老生常谈吗?而当一个老生常谈变成了研究界普遍纠结的问题时,事情恐怕就不那么简单。有学者指出这种现象与某种“传统偏见”相关,但传统是多元的,有一种传统偏见,往往就会有另一种针对此偏见的传统。又如把文学的艺术性研究看成“软学问”固大谬不然,但这是否也暴露了长期以来文学研究中的某些弊端。由于缺乏对文学本体研究的理论思考和方法探究,“纯文本”研究往往流于印象式批评,即便是人们视为典范的闻一多的“唐诗杂论”,在被敏锐的感觉、精致的表述掩盖下的,依然是“印象主义”的批评方法。而考据与辞章、文学与历史的关系如何,孰重孰轻、孰高孰低,其争论辩驳也由来已久。因此,对上述问题作出清理,以求在一新的起点上明确方向、抖擞精神、重新出发,不能说是没有必要的。本文撰述的宗旨,一方面是对当下古代文学研究的针砭,一方面是对现代学术中某种传统的接续,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中国批评传统的再认识。
从一重公案说起:实证主义文学研究批判
20世纪80年代以来,针对长期存在的僵化和空疏,学术界开始追求学术性和多元化。但到90年代之后,中国的人文学界逐步形成了如李泽厚描绘的图景且愈演愈烈:“九十年代大陆学术时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王国维、陈寅恪被抬上天,陈独秀、胡适、鲁迅则‘退居二线’。”与之密切相关的,就是文学研究中“实证主义”的死灰复燃,并大有燎原之势。近年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的课题指南中,类似“某某文献集成与研究”的名目屡见不鲜,虽然名称上还带了“研究”的尾巴,但往往局限在文献的整理和考据,并且多是一些陈旧的文献汇编影印。这多少反映出学术界的若干现实,也多少代表了学术上的某种导向。
徐公持在总结20世纪最后20年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时,举出当时老一代学者“再现学术雄风,其中钱锺书、程千帆堪为代表”。如果说,21世纪的古代文学研究仍然有对前人“照着讲”“接着讲”甚至“对着讲”的必要,那么,我们最迫切、最需要接续的就是由钱锺书、程千帆为代表的学术传统,并且在理论和实践上向前推进。
从批评实践看文学、史学研究之别
在20世纪中叶,陈寅恪探索和实践了“以诗证史”的研究方法。从文学理论的立场看文学和历史的关系,一种人们熟悉的看法就是认为文学是特定历史时期的反映,因此,理解作品就要将其置于历史背景之中。但文学中展现的历史,与实际发生的历史并不一定吻合,为了研究历史而利用文学材料,就会对文学描写加以纠正,这便属于历史研究。而为了纠正文学描写,就需要对史实(包括时间、人事、地理)作考据,转而轻忽甚至放弃文学批评。即便无需纠正,但如果仅仅将作品看成文献记载,也谈不上是在进行文学研究。当陈寅恪用“以诗证史”的方法去研究历史的时候,他心目中的意义就在于“可以补充和纠正历史记载之不足,最重要是在于纠正”,被他“纠正”的往往不是历史记载,而是作品描写。其为史学研究而非诗学研究,不待细辨即可知。但陈寅恪对文学极为精通,故其论著也时时发表对文学研究的卓见,且深受学者重视。
在文学研究上,钱锺书对陈寅恪没有什么吸收。程千帆则深受陈寅恪的影响,他对陈氏学术方法、宗旨、趣味以及文字表达的理解,远胜一般。但程千帆的学习方式,不是形迹上的亦步亦趋,而是在把握其学术宗旨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研究内容,在学术实践中“有所法”又“有所变”,将重心由“史”转移到“诗”。他们之间的区别,是一个很好的辨析史学研究和诗学研究之差异的个案。如上所说,中国古代诗歌往往包括时间、人事、地理,所谓“人事”,不仅有时事,也有故事,所以在研究工作中就不可避免地需要对史实的考证。若是史学研究,就会判断相关的某一记载(无论是历史文献还是文学作品)是出于“假想”或“虚构”,因而是“错误的”或“不实的”。但若是诗学研究,史实的考证就仅仅是提供理解诗意的背景,而非判断诗人是否实事求是的律条。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程千帆与陈寅恪的差异。如果从作品出发,又回归到作品,就会尊重诗的特性,学习并坚持对诗说话,说属于诗的话。文学批评不排斥甚至有时也需要考证,但仅仅以此为满足,并未能完成文学批评的任务。
关于文学研究中的考据与词章,程千帆还说:“词章者,作家之心迹,读者要须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孟氏之言,实千古不易之论。”其所引孟子云云,见于《孟子·万章上》,以“千古不易之论”为评,似可表明,现代学者的文学批评,也有自觉接续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之某一传统者在。由此重新思考我国两千五百年文学批评之发展,也可以获得一些新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文学批评的另一传统
对中国文学批评作出整体描述,是现代学术形成后的产物。当时人多以19世纪以来的欧美文学观念作为参照系,由此导致了一个被广泛接受的结论,即中国的批评传统以实用的、道德的、伦理的、政治的为主要特征,虽然也含有审美批评,但在整个批评体系中似乎仅仅偏于一隅。在我看来,这是对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简化和僵化,尤其是因为缺乏与西方批评传统的整体对应,因而遮蔽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另一传统——审美批评(包括非常丰富的技术批评)的传统。尽管已有学者对此作出了呼吁和阐发,但仍有进一步呼吁和阐发的必要。面对今日文学研究的困境,如果我们要从中国批评传统中寻找资源,对于这一隐而未彰的传统,有必要予以揭示。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孟子的贡献可谓极大。“文学批评”是一个外来的名词,在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相应的则是由孟子提出的“说诗”的概念,文学批评家也就是“说诗者”。什么是“说”?我们不妨看看中国最古老而权威的解释——许慎的《说文解字》曰:“说,说释也。”段玉裁为我们作了进一步的阐明:“说释即悦怿,说悦、释怿皆古今字,许书无悦、怿二字也。说释者,开解之意,故为喜悦。”因此,西方的“文学批评”形成一种理性判断的传统,而中国的“说诗”是一种由情感伴随的活动。
孟子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贡献,简言之有二:一是提出了“以意逆志”的说诗方法;二是对“说诗”和“论史”作出了区分。这两者也是有联系的。孟子说诗方法的要义在于:首先,要尊重诗的表达法,为了发抒情志,语言上的夸张、修辞中的想象是必不可少的,这是文学的特性;其次,诗歌在语言上往往夸张、变形,诗人之志与文字意义也非一一相应,正确的读诗方法,就是“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读者的意去迎接诗人的志,即“以意逆志”。所以孟子之“说诗”,是以认识诗语的特征为出发点,最终也回到诗歌本身。说诗如此,论史则不然。《孟子·尽心下》曰:“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他认为武王伐纣,是“以至仁伐至不仁”,怎么可能杀人无数,以至于血流漂杵呢?从语言修辞的角度言之,“血流浮杵”只是一种夸张,以形容死者之多。但在孟子看来,作为记载历史的《尚书》,不能也不应有此种修辞。他在实际批评中体现出的说诗和论史的区别,具有重要的意义。张载曾对此作了对比:“‘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意’,此教人读《诗》法也。‘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此教人读《书》法也。”一为诗,一为史,文字性格不同,所以读法也不同。“说诗”与“论史”不同,这是孟子的千古卓见。
中国早期的审美批评至《文心雕龙》作一总结,这就是“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首先是一种感情活动,在获得真知灼见之后,内心也必然充满喜悦,甚得传统“说诗”之髓脑。而经锺嵘《诗品》揭橥的“诗之为技”的观念,到了唐代,衍伸为一系列从诗歌技巧出发的诗学著作,涉及声律、对偶、句法、结构和语义,为分析诗歌的主题、情感等提供了大量的分析工具和评价依据。但自宋代开始,这一情况发生了较大改变。
不识诗语特征,拘泥于史实从而导致对诗歌的误判,在宋代以后屡见不鲜。比如杜牧《赤壁》诗有“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之句,许顗《彦周诗话》讥刺道:“孙氏霸业,系此一战,社稷存亡,生灵涂炭都不问,只恐捉了二乔,可见措大不识好恶。”胡仔也附和其说,认为“牧之于题咏,好异于人”,乃至“好异而叛于理”。他们都自以为熟谙史实、深识道理,便可以高屋建瓴、义正辞严地批评诗人,殊不知正如四库馆臣的反驳:“大乔,孙策妇;小乔,周瑜妇。二人入魏,即吴亡可知。此诗人不欲质言,变其词耳。”“不识好恶”的“措大”正是批评家自己。其共性就是不以文学的眼光看文学,面对着诗却说着非诗的话,尤其是这些议论有时还出于名人之口,这就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古代的说诗传统。从审美(如情感、技巧)出发对诗歌作批评的传统,也就被压抑成一股虽未中断但却易受忽略的潜流。
现代学术传统:理论意识与比较眼光
如果将钱锺书、程千帆的学术传统合观并视,我想举出两点对今日文学批评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遗产。
第一,从作品出发上升到文学理论,以自觉的理论意识去研究作品。钱锺书自述其“原始兴趣所在是文学作品;具体作品引起了一些问题,导使我去探讨文艺理论和文艺史”,其《通感》解决的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程千帆则强调“两条腿走路”的原则:“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后者则是古人所着重从事的,主要是研究作品,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规律和艺术方法来。”虽然两种方法都是需要的,但后者在今天“似乎被忽略了”。为此他探讨了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的问题,试图“在古人已有的理论之外从古代作品中有新的发现”。在对具体作品的研究也就是文学批评中,中国学者往往不太在意理论问题。钱锺书指出:“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几乎是什么理论都不管的。他们或忙于寻章摘句的评点,或从事追究来历、典故的笺注,再不然就去搜罗轶事掌故。”“寻章摘句的评点”最典型的做法就是鉴赏型的喝彩或讥讽,寻求出处或轶事掌故则多半是为“考据”服务的。程千帆对这样的文学批评也有不满:“那就是,没有将考证和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这样,就不免使考据陷入烦琐,批评流为空洞。”而造成这两种现象持久不衰的原因,就是对理论的敌视或轻视。程千帆很重视文学理论。20世纪40年代初,他在任教武汉大学和金陵大学的时候,讲授古代文论,就编为《文学发凡》二卷,具有以中国文论资料建立文学理论系统的雄心。钱锺书同样非常重视文学理论,不仅在他的著作中广泛征引西洋文学理论著作,而且直接翻译过欧美古典和现代理论家的论著,其中较为容易看到的就多达35家。
第二,在文学范围内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批评,使民族文学的特性通过比较而具备文学的共性。同时,揭示了共性也依然保持而不是泯灭了各自的特性。在这一方面,钱锺书表现得更为突出。1945年钱锺书用英语作了一个题为《谈中国诗》的演讲,在结束部分说:“中国诗并没有特特别别‘中国’的地方。中国诗只是诗,它该是诗,比它是‘中国的’更重要。”一般人谈中西文化,因为从外表上看差异大,于是就大谈其差异,钱锺书偏偏能看到其中的“同”。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诗”在文学的框架中发现了“同”,又在各自的文学中保持了“异”。众多的古代文学研究者,在面对西方文学和文学理论的时候,总是强调中国文学的特殊性和差异性,所以只能在古代文学甚至不能在中国文学的范围里讨论问题。
作品层面以外,还有理论层面。1937年钱锺书写了《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里面就谈到,“中国所固有的东西,不必就是中国所特有的或独有的东西”;中西文学理论有差异,但“两种不同的理论,可以根据着同一原则。……虽不相同,可以相当”;最后归结到“这个特点在现象上虽是中国特有,而在应用上能具普遍性和世界性;我们的看法未始不可推广到西洋文艺”。他通过中西文学理论的比较,拈出异同,彰显特色。这是从中国出发看西洋,又从西洋回首望中国。他希望中国文学作品能够走向世界,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和文化修养,抒发的是一个中国书生的梦想。我们需要走出的第一步,就是改变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偏于一隅的状况,这也需要研究者改变自我封闭的心态。
余论
文学家当然有其社会、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诉求,但这一切都要通过文学诉求来实现。所以,文学批评也只能以对其文学诉求的回应为出发点,否则,既证不了史,也谈不了艺。谁能以“白发三千丈”和“飞流直下三千尺”的对比来证明李白的愁发比庐山的瀑布长十倍呢?在今日古代文学研究的再出发时,我们最应接续的是钱锺书、程千帆为代表的学术传统,这不仅因为他们都针对实证主义和印象式批评予以纠偏,坚持面对文学说属于文学的话,而且因为他们的珍贵的学术遗产,也已经为我们在探索之路上的继续前行树立了典范。
文学批评是一门学问,是一门独特的知识体系。抛弃了实证主义,超越了文献考证,文学批评有其自身的知识系统,也需要不断更新自身的知识储蓄。让我们再听听韦勒克的忠告吧:“我们并不是不再那样需要学问和知识,而是需要更多的学问、更明智的学问,这种学问集中研究作为一种艺术和作为我们文明的一种表现的文学的探讨中出现的主要问题。”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两位中外先哲的遗训,一位是中国的孟子,他说:“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放弃自家田地不种,偏偏去耕耘他人之田,在孟夫子看来已经成为某些人的“病”。另一位是法国的伏尔泰,他笔下的“老实人”在历经人间生死荣辱之后,终于在最后幡然醒悟道:“我们还不如去耕种自己的园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