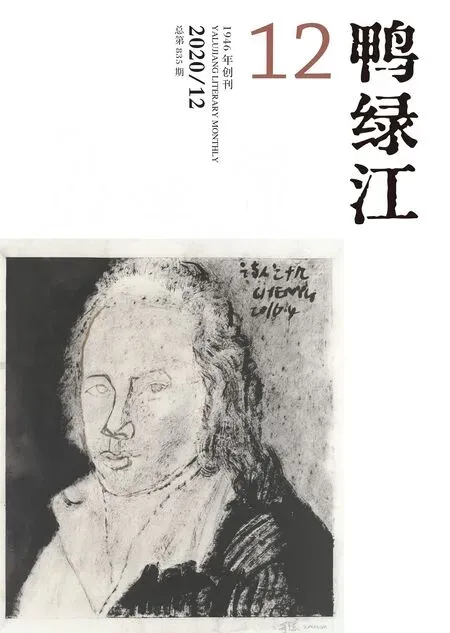故乡,失落的旅程
杨洪波
沿着奈营高速和新鲁高速一路向北,前方就是科尔沁草原,辽阔的原野上,连绵的云阵让秋天的北方格外深远。我手里握着充足的假期,时间变得松弛,行路从容。越来越接近故地,那些熟悉的地名开始涌现,给我的感觉既亲切又疏离,犹如我对故乡的情感。
一路行来,我一直在体验这种复杂的感受。
我搜寻岁月留在乡土上的记忆,希望找到隐藏的人生轨迹,解读命运人生,这成了我踏上这次旅途的目的。
我出生在科尔沁草原边沿一个叫四家子的小村里,村子里只有几十户人家,几乎都是汉族人。后来我知道,我出生的地方是一个蒙汉杂居的地方,周围有很多蒙古族的村庄,标志就是那些奇异的蒙古名字。
故乡是一望无际的田野和连绵起伏的沙坨,村庄和道路切割开深广的大地,在连绵的庄稼和平缓的沙丘覆盖下,村庄显得隐秘而幽静。很多年里我不止一次回到故乡来,想看清村庄的面貌,可我看到的总是村庄的一角,成为交错的光阴留在记忆中的碎片!
总想让故乡的记忆完整起来,这也成了我走回故里的缘由,可每一次来去匆匆,总有种难以言说的疏离感,无法企及心中那份隐蔽的故土乡情。渴望找到此生的原点,找到宿命人生的暗河,可每一次都是枉然。我发现无法走进梦中那个遥远而亲密的故乡。徘徊在乡路上,我常常是一个失途的人,不知道自己缘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
1
北方的大地深广凝重,蓝天白云把秋天的旷野衬托得雄浑、粗犷而豪迈!即便仅仅是为这方风景,此行也令我向往。
高速公路转过通辽市,再转向东北就接近我熟悉的故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开始在一个个路口出现:通辽东、钱家店、大林……这些地名让我备感亲切。在我很小的时候,就从大人的交谈里熟悉这些名字,那时我羡慕大人的丰富经历,这些地名曾经留下亲人的足迹,尽管许多亲人已经不在了,但它们仍然能唤起我温暖的记忆,让我和生活过的村庄联系在一起,这就是血缘的纽带吧!
大林!一个路标映入我的视界,内心一阵兴奋,此行的目的地就在眼前了。
大林的全称是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大林镇。我的出生地四家子,就是大林镇下辖的一个村庄。幼年时我只是懵懂记住了这些地名,当我清晰地知道它们的地理概念和隶属关系时,已是成年。
我的父母来自同一个镇上的两个村庄,两个村庄间相距十多公里,现在的车程不会超过15 分钟。可幼年时,从我家到外祖母家是一段漫长的旅程:一条崎岖难行的乡间小路让所有的通行都显得艰辛,我清晰记得自己骑在一头瘦驴的背上,第一次去外祖母家的情境,每次回想都是痛苦的记忆。坎坷的乡路上,瘦驴的每一步移动都是一次大幅度的颠簸,驴背的硬脊骨硬是磨烂了我屁股上的皮肉,后来结成厚厚的血痂。嶙峋的脊骨的刺痛感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时我急切地渴望旅途的终点,看到一生中最漫长的落日黄昏。当我一边抹着泪水、一边随着那头颠簸的瘦驴走进外祖母的村庄时,我被骑驴的痛苦所折磨,完全忽略了对外祖母的村庄的好奇。
外祖母居住的村庄叫西归力,我一直记得这个蒙古村庄的名字,它让我联想起儿时的玩伴——老发。在我从前某次回乡的途中,在路过的道口看到西归力的名字时,我油然想起那次痛苦的旅途,想起那个叫老发的伙伴。我记得老发一家是外祖母的邻居。
老发年龄比我略长,令我记忆最深的是,老发长着一个与众不同的扁脑袋,这一直是我的疑问。大人的解释是:在老发出生时,老发的父亲每天在屋檐下劈柴,而隔着窗就是襁褓中的老发,老发的扁脑袋就是劈柴声给震的!我知道这种解释是村庄里人对生活习以为常的逻辑,我无法知道老发是不是接受了这个解释,也不记得他对自己与众不同的扁脑袋有过什么疑问,但这些都成了我对老发刻骨铭心般的记忆。
在我记忆里老发家姓德,他的大名叫德发,他家里养着一群牛,那时候所有的牲畜都是生产队的,他们家却自己有牛!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像老发的奇特的扁脑袋一样,我对老发的记忆一直是清晰的。以至于我一回想起幼年时的村庄,我就会想到老发。
幼年的老发既憨厚又幽默,让我喜欢和信赖。想不起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去外祖母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找老发。我们一起玩游戏,他总有办法把游戏带入高潮,或者把陷入绝境的游戏维持下去。
我一直记得我们三个人打扑克的情景,老发不知道从哪里捡来一副残缺的旧扑克牌,扑克牌因丢失一些花色,很难进行一场完整的游戏。记得我很烦恼地扔下那几片纸牌,想放弃这种根本无法进行的游戏。那时我不知道老发是怎么想的,只记得他一脸憨厚地重新收起扑克牌,然后从容不迫地从衣兜里再次掏出另一副,真诚地对我说:“我拿错了,这里才是新的!”于是,我们高高兴兴地投入另一轮扑克牌游戏,可是,很快就发现,我们玩的还是那副旧扑克牌。于是,我再次把扑克牌扔掉,决意不再投入这个无聊的游戏。不知怎么,聪明的老发把这个残缺的扑克牌变成了魔术道具,我俩被老发的新游戏吸引,不再计较缺张断幅的旧扑克牌……我一直没想清楚,老发是怎样用一副旧扑克,把一场寂寞的游戏坚持进行下去。直到晚饭时我一身尘土跑回外祖母家,才知道本来村里来人要接我回村的,可是没能找到我,他们只好先赶路了,老发用这种方式留住我。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除了那个游戏,除了那副残破的扑克牌,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有聪明的老发知道结果,他用自己的方式愉悦我们幼年孤独的时光。以至于我一直记得老发和儿时的那场游戏。
那个午后,我独自开车行在大林镇的路口,当“西归力”的路标投入我的视野时,突然有了去找老发的冲动。此时我53 岁了,和老发一起游戏时不过五六岁,时间隔了近50 年,不知道老发是不是还记得当年,记得我这个伙伴。
我一面被寻找老发的念头鼓舞,一面惴惴不安地揣测着种种可能。不知道老发是不是还住在原来的村庄里?岁月把他改变了多少?是不是还像我一样心里装着那些往事?老发会以什么样的姿态接受我突然的造访?我带着无限的猜想来到村口,在内心的疑虑和不安中悄然把车开进村庄。
到处是翻天覆地的改变,大地和村庄都在不断地翻新我的记忆,从前的村庄早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以至于除了“西归力”这个名字,我再也找不到一点过去的记忆。我在心底搜索关于老发所有的信息,希望沿着一个明确的线索找到他。无论我怎么搜集,关于老发我只记得他的小名叫老发,姓“德”,蒙古族人,家里养牛。因为姥姥常常称呼他老德发,所以他的大名应该叫德发。
正是秋收季,村民在大田里忙着收割最后的庄稼,空落落的村庄少有人迹,虚掩的院门封起的一座座空寂的宅院,让我这个“外乡人”从容窥视,揣想他们展示在我面前的生活原景。沿着无人的空巷,我轻轻推开一户虚掩的院门,穿过整洁的院落,来到屋舍前,隔着塑钢门窗,看到室内陈列的井然有序的现代家电设施,这完全湮灭了过去的痕迹,村庄发生的改变,完全偏离了我对过去的记忆。
眼前的情景让我若有所失:记忆里的村庄不复存在了,村庄没有为我的怀想守着那段古远、破旧的过去时光,一切都改变了,人们过着现在的田园生活,我离开村庄时,他们也离开了过去。
因此注定我们不能回到过去了;更无法走回到过去的村庄,我发现自己离村庄越近,离过去越远!那么我还能找到过去的老发吗?
现在老发怎么样了呢?他怎样面对一个突然出现在眼前的伙伴?而我必须为一个变化了的老发做准备。看起来,所有的答案都在老发那里。那一刻我突然有了一定要见到老发的执念。
我在空落的村巷里辗转,终于从一位乡亲的口中知道了老发的消息,欣喜的是老发还在村子里,只是他的大名叫德继发。他家就在前面的路口西数第五家,门前堆着牛粪,院子里有牛栏和牛群。
于是,按照乡亲的指引,我很顺利地找到老发的家:院门前堆着牛粪,院里的围栏圈着大大小小的牛。打开虚掩的庭院大门,走进老发的家,我看到这是村庄里典型的富裕农民的生活环境,我看着牛栏,看着牛栏里的牛,看到规整干净的院落,看着老发现在的生活,猜想着他的心里是否还有一个过去。
我预感到老发并不在家,他的房门紧闭着,像村庄里所有的农户一样,此时他正在村庄外的大地上收割自己的庄稼。正在我进退的迟疑间,老发的邻居及时发现了我这个不速之客,打过招呼后,我简单说明来意,邻居要我留下姓名,好代为转告,那时我才意识到:离开村庄时,除了乳名,我并没有给老发留下自己的名字,我的名字对老发来说,只是个陌生符号。
探访老发的行程到此搁浅了,尽管有些遗憾,但我已经窥见到老发幸福生活的一面,那些被湮没的过去重新在我眼前复活。现在我要去完成此次回乡的另一个行程,于是我决定把老发未尽的探访留在后面。
2
下一站行程就是我的出生地,科尔沁草原边那个叫四家子的小村庄。我在那里长到八岁,然后随父母迁居到辽河三角洲平原上的另一个村庄。很多年后我发现,我生在辽河边,长在辽河口,我是沿着一条河一路走来。
其实我对村庄的记忆也源于一条河。
幼年时的愿望就是能像大孩子一样,到村庄以外的地方自由玩耍。于是,我就跟着一群大孩子来到村庄外,一个叫干河的地方,干河是流过村庄的古老河床上的一条季节河。正是植物茁壮生长的季节,葱茏的草木和绵延的河床一起切开大地的界限,动物和人都聚拢到河边来,享受河水的滋养。我看到猪群在河边打溺,牲畜也被赶到河滩上吃草和饮水,蝴蝶和蜻蜓在水面飞舞,鸟雀在空中盘旋觅食……大孩子们或者在浅浅的河湾里结网捞鱼,或者在河岸的沙丘下设伏捕鸟。生机勃勃、清爽宜人的河滩也处处有杀机,这也成了我对干河河流记忆的一部分。
幼年关于村庄生活记忆模糊,只有那条小河给我留下有色彩的回忆。那条叫干河的小河,像它的名字一样,在我离开后,在大地上消失了,成了名副其实的干河。以至于在我曾经的寻访中,连村庄里的人都忘了它的存在。
我在落日时分走进村庄,心里依稀装着当年的影子。我站在村口辨认当年的村巷,这里已经没有我熟悉的亲人和邻里,他们或移居他乡或已经离世,我找不到可以寻访的目标,只一个人站在巷口,怀着复杂的心情,像一个偷窥者一样,窥视村庄的人们此时的生活。
同样是秋收季,我知道村里人分散在周围的大地上,寂静的村巷同样空落落。
我在寂静的村巷里徘徊,却无法和记忆中的村庄对接,这个既亲切又陌生的村庄,它完全覆盖了我从前的记忆,如果眼前的村庄是现实,那么从前的岁月就是遥远的梦境。
面对陌生的故地我恋恋不舍,总希望找到什么,一个人或者一段往事,在这个黄昏,我想找到有关故乡的记忆!
我看见有人从村路上走来,有人走出庭院向我询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含糊其词,说自己是路过的外乡人。这是我能找到的最简单的身份,我只是这个村庄的过客,是他们生活的旁观者。
直到我看到一缕炊烟静静地升起,我有了抑制不住的感动,我那么想走进那个农院,看一眼他们围坐在餐桌前吃晚餐的场景,我想留下对这个村庄最后的记忆。
于是,我情不自禁走进那户农院,一位老乡和他的子女们围拢在餐桌前准备就餐,我这个贸然“入侵”的不速之客,显然打扰到了他们。这也正是他们心中的疑惑,一个想看别人晚餐的外乡人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也许出于善良和矜持,他们满足了我的好奇心,以开放的心态向我展示了他们一家的晚餐,却没有追问为什么。我怀着感激的心情,用随身带的相机匆忙拍下一家的晚餐后,心满意足地离开。
我以这种方式走进了故里,这也可能是故乡留给我的最后记忆。
沧海桑田,物是人非,这是许多人眷眷乡情中重复的体验。我渴望一次重回故里的旅行,除了乡土情结,半生归来,我还带着一个追问:渴望在人生的原点找到命运人生的答案,我缘何而来?为何而去?
3
不知从何时开始我喜欢大地上的风景,田野、树木、河流、村庄……不知这些平常的景物,最初是怎样映入我的视野,并触动我的心结,因何感动我,以至于我追逐着大地上的风景一路走来。特别是站在秋天的大地上,旷野、树木、远天、白云,大地用它最朴实的风物,在我眼前铺陈出无限风华,吸引我一次次驻足,去品读大地的语言。
我没有走错!那个早上,沿着那条古老的河床的遗迹,凭着感觉就找到记忆中的那片神秘土地——白沙坨。白沙坨是村庄的一个地标,也是我心中抹不去的记忆。
白沙坨是一片开阔平缓的沙坨地带,位于距村子东北方不足2 公里的地方,就是记忆里那条其乐融融的干河流过的地方。沿着当年干河浅浅的流水溯流而上,沿着河床切开的平缓的沙丘上行,呈现在我面前的是一片碑碣林立、坟茔森然的墓地。这是村庄里祖祖辈辈先民的长眠之所,也是村庄里无数鬼故事传说的原发地。我依稀记得,当年和村里的仨孩子在大地上剜野菜,就是沿着这条河道,懵懵懂懂地撞到白沙坨上的墓地上来,看到丛丛荒草下,半遮半掩间森然矗立的坟茔,一股肃杀之气油然而起。对坟墓本能的畏惧,源于我们对死亡的恐惧。就在我们胆战心惊之际,一股旋风从远处悠悠地旋转飘来,我们再也抑制不住恐怖的压迫了,拼命地朝村庄的方向跑去,那是我幼年时跑过的最远的距离……这也是我在许多有关村庄的记述中描绘过的情景。为此,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村里人把最好的土地留作坟地?让白沙坨这片草木丰盈、景色宜人的美景的另一侧,卧着森然的亡灵,让人对这片土地充满矛盾的记忆,仿佛一条浅浅的水线划开了生死之间的界限。
多年以后干河消失了,干河上的风景也消失了,人们把从前的沙坨直接变成田园,那条隔开墓地的界限显得模糊了。在放倒成片的青纱帐屏障后,白沙坨上的墓茔更加逼仄地呈现在我面前。
我沿着河床的遗迹摸索着来到白沙坨的墓地时,才发现这是村庄的最高点,如果没有一望无际的玉米秸遮挡视线,站在这片墓地上,就能清晰地看到小村的面貌。这里阳光明媚,开阔的墓地脚下就是干河留下的宽广的河床遗迹。那里已经变成了新开垦的园地,稀疏的树木间留下陈年耕作的痕迹,除了一片待收获的向日葵,还有一捆捆干枯的豆秸。明亮的阳光下,墓园没有了记忆里的森然。我一直想为什么村民把墓地放到最好的水土上。很多年后,我理解了,把最好的土地留给先祖,除了沿袭古老的风水习俗,更源于对逝者的崇敬。
这次归来我终于探查清楚,干河只是古老的大河最后的子孙。这里原是西辽河的一段故道,它在我出生前,就流淌在村庄的大地上,干河的名字就是村民对这条古河道形象的称呼。而我就是沿着它的遗迹一路追踪而来,站在古老的河床上,我想起帕斯卡尔那句名言:“河流就是前进着的道路,它把人们带到他们想要去的方向。是河流把无边的大地联系起来,在人们视野之外,为你指向海的方向。”我相信沿着这条古老的河床,一直可以走到几天前我出发的地方,那就是我的第二故乡——辽河入海口处的渤海湾。我发现我走过的岁月就是一条河流的方向,人生岁月何尝不是一条河。
这也许是我回到这片土地找到的最好的答案!
4
视野中一群玄色的鸟群不知从什么方向,突然聚拢在我眼前深邃幽蓝的天空中,在我的头顶略作盘旋后,又谜一样消失。我知道那是鸦群。它们只在北方的大地上神奇地出没,如图腾一样神秘,是注解这片大地古远而神奇的存在。
金风萧瑟,野旷天蓝,我在深秋的大地上流连,深广粗犷的北方,有种与生俱来的悲怆,也许这就是我面对的人生境遇。
余下的时间,短暂地探访还住在近乡的两位嫡亲之后,在一个黄昏时分,我再次来到西归力老发的家。因为轻车熟路,没费周折,径直来到老发家门前。
走进已经熟悉的庭院,首先发现我的是老发的爱人,一个白皙、俊俏的女人。当老发应声从屋里走出来,我们站在庭前彼此打量的瞬间,立刻在心底湮没了过去的记忆。没有预想的那种矜持,老发,站在我面前的依然是那个憨厚的老发,久别重逢后悠然间跨越彼此心中那段模糊的岁月,很自然地在心底接受生活改造后的彼此,几句问候过后,老发突然叫出一个陌生的名字,这是我幼年时只有很少的人知道,后来从没有用过的名字,他居然记得我最初的名字!这让我心里一热,所有的疏离瞬间消散了。看着他憨厚的笑容,我内心也涌动起温情,庆幸自己此时的选择。
我特意留意老发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扁脑袋,已经没有记忆里那么夸张。交谈中知道,他原来长我三岁,一个标准的蒙古汉子,这样的年纪,居然一头密实的黑发,这让老发看上去很年轻,否则也不会娶到一个如此俊俏的媳妇!老发的爱人很自豪地告诉我,老发比她大五岁。
还记得老发亲热地把我让进客厅时,愉快地对他爱人嚷道:“快给我换一套新衣服,我要陪‘大孩儿’好好唠唠!”这一次,他自然地叫出了我的乳名,很多年没有人这样呼唤我,这声呼唤让我从心里感到亲切。我们愉快地回忆起幼年时那些往事,他快乐地数出另一些我记忆中似曾相识的伙伴,他帮我回忆起更多往事,我发现他不但没有忘记,甚至还记得更多细节!我们很快就聊过一大截的时间,最后,我谢绝了老发的挽留,我感到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于是,我向老发一家辞行。
夕阳西下时我走出了老发的庭院,记得当年,我第一次骑在驴背走进村庄时也是这样的黄昏。那时我走进的是隔壁的外祖母家……这是多么有象征意义的巧合。
离开村庄时,我看到三个正在游戏的孩子,他们正处于我来到这个村庄时的年龄。我不由自主停下车,看着三个孩子的游戏浮想联翩,我想起,那些落日时分正是我们准备结束游戏的时刻,总有一个孩子恋恋不舍地说:
“咱们再玩最后一次吧!”
不知道是哪一个黄昏,离开了老发和伙伴们的最后一次游戏。从此,我离开了故里,也离开了童年。
如果人生就是一次远行,也许这一次返乡,我是在寻找内心那些失落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