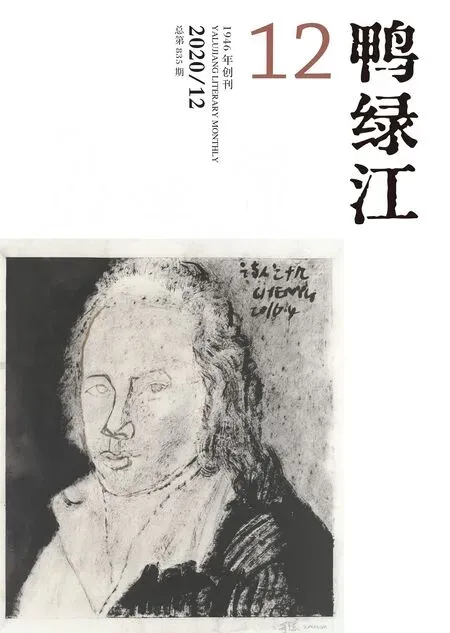边门旧事
万冰峰
惊蛰天的晌午,日头出奇地好,把初春的马鞍山,包括山北面残存的冰雪,都照得软乎乎的。填仓靠在福兴寺的墙角,抄着袖子,眯起眼睛,让暖暖的光晒进身上的每处骨头缝里,啧……真舒坦。填仓每天天不亮就让师父赶起来扎马步、走木桩、打沙袋,晒太阳这样的时候太少了。他想,世上最舒坦的事儿,应该就是吃饱喝得了,靠在墙根儿晒太阳……
山门吱嘎嘎地响了,他慵懒地支棱起耳朵听了一下,随后赶紧一纵身跳上梅花桩。他心里偷偷念叨:“真悬,差点叫师父堵住。可话说回来,师父今天的脚步咋这么慢,这么重?要不,凭他以往那走路速度,肯定能堵住我。”
宫道长在院子当中停下脚步,甩了下拂尘:“别在那儿装相了,再站半炷香,站完进大殿里来。”然后,风似的走进二层殿。填仓伸了下舌头,瞅这出,师父又要讲法了。
宫道长原本只是边门县一个庄稼院的孩子,后来跟随一个游方的道长上了武当山修行。几十年后,他回到老家,就在这胜宝山的道观里挂单修行。宫道长道学高深,方圆几百里的许多信徒慕名而来,或听道,或学武,聚集了近百人。
师父不要求填仓听道,可填仓挺愿意听,练完功就在旁边跟着听。师傅讲法不玄、不飘,谁都能听明白。师傅讲:“这道啊,是一种信仰,啥叫信仰啊?就是人活着的一个奔头。人只有为了信仰活着,才有精、气、神。人世间的所有东西,包括咱们人在内,都在五行之中,凡事都要顺其自然,这世道才能平平安安,要不就会出天灾人祸。”
有师兄就问他:“山底下的日本人,不在自己国家老实待着,跑到咱这地界成天咋咋呼呼的,他们是顺着五行不?”师傅捋一捋胡子说:“他们这就是反天道而行之,是魔道,必遭天道所谴。”
另一个师兄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人家有枪有炮的,这个魔,现在压着咱这道呢。”师傅重重地叹一声:“国家积贫天道孱弱,必然被魔道所欺。”
有个漂亮的师姐就叹气道:“那些东北军都撤到关里去了,咱们化外之人,除了静心为百姓求安,恐怕也干不了别的。”邻村那个叫二壮的师兄站起来,用拳头捶了下柱子:“俺就不信那个邪。师父,您带俺们成立这个白刀会,不能光是讲道吧?咱得做点啥。”师傅忙摆手,示意他压低声音,又轻声轻语地说:“咱们成立白刀会,就是要除魔卫道,不过你们要想好了,包括师父我在内,咱们修为尚浅,要是真刀真枪地拼起来,估计都免不了一死,你们打怵不?”一屋子人就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异口同声地低吼:“为国尽忠,驱邪除魔,死而不悔……”
填仓走进大殿的时候,师兄师姐们都已经一身缟素地聚齐了。宫道长正大声地吼着:“昨儿个,小日本的征粮队说大伙交粮不积极,存心对抗皇军,把靠山屯整个村子的男女老幼一个没留……咱们的衣食、香火,都是这一方百姓在供养。百姓就是咱们的衣食父母,有人杀了你们父母,你们该咋办?”屋里的人似乎被一团火点燃了,喊出来的声音都带着炽热:“斧正天道,替乡亲报仇!”
宫道长喊填仓过来,填仓擦了擦鼻涕,慢慢地蹭过来,他不懂发生了什么,但是心里沉沉的。宫道长把他领口裂开的纽襻系上,轻声问他:“知道你为啥叫填仓不?”填仓点点头:“知道,师父把我从山底下捡回来那天,正好是填仓节。”宫道长摸了摸他的后脑勺:“这名字还有另外一层深意,你以后长大了自己参悟吧。孩子啊,你今年十三了,可连自己姓啥都不知道,师父这些年忙忙活活的,也没能照看好你。”填仓听出了一丝歉意和哀伤,心一沉,忙拽紧师父的道袍袖子:“师傅你说啥呢!要是没有师傅,我估摸着早就叫野狼叼跑了。师父,我有姓,我姓宫,你就是我亲爹。”
宫道长平日里参透生死般平静的脸似乎动容了,眼角渗出一点晶莹。他从条案上拿起一个包裹,替填仓背上:“师父仔细看过你的九宫天格,你此生注定驰骋疆场,所以从小开始,我只教你习武,不领你悟道……其实,除魔何尝不是修道呢?”宫道长摸着填仓的头顶低语,填仓扬起头,似懂非懂地盯着师父。
宫道长拉着他的手慢慢走到山门前,指着西北方向对他说:“记住师父的话,一直朝那个方向走,找个叫延安的地方,那里有支队伍,师父听几个从那边来的人说,那是一支仁义之师,你去投奔他们,将来一定会有番作为。”填仓听得蒙头蒙脑的,忙给师父跪下:“师父,你为啥撵我走啊?是不是我哪儿做得不对惹你生气啦?”宫道长轻笑一声,把他扶起来:“师父和你师兄师姐们要去做件大事,估摸一时半会儿回不来,你先去,要是……师父还能回来,就去那儿找你,听话。”填仓不敢和师父顶嘴,瞅了瞅师父和身后过来送他的师兄师姐,一步三回头地走下山坡,向着师父指的方向走去。
1937 年3 月上旬,在日占区出版的《奉天日报》头条刊发了一条新闻:“今法库边门地区福兴寺,有匪首宫良栋,纠集反日分子百余人,秘立反逆组织‘白洋法’,呼口号‘驱邪魔护天道’,突袭东科尔沁前旗警察分所,此股匪患虽手执刀枪并无火器,然凶悍异常,致我士兵及皇协军二十余人玉碎,捣毁分所后,旋进军旗公署驻地后新秋镇。前旗参事官浅野良三中佐率队拦截,激战于彰武平顶山。后匪帮被我大军所围。然百余匪众竟无一人肯降,被尽皆诛戮……”
1946 年初春,秀水河子战役的前几天,东北联军进入法库地区。在一个轻雪飘扬的早晨,边门西部山区的一片荒冢前,一个身着戎装的年轻人在脱帽默立。警卫员跑过来:“营长,老乡们都说,当时尸骨遍地,小鬼子又催得紧,来不及辨认谁是谁了,就稀里糊涂地埋在这儿,实在认不清到底哪个是宫道长的墓了。”年轻军官点点头:“算了,神州无处不青山,十四年的抗战,牺牲的烈士何止几千几万,有多少人都埋身荒野了。最起码我还能有个凭吊的地方,知足了。我想,有师兄师姐们陪着,老人家无论睡在哪儿都不会寂寞的。”
说完,他飞身上马,对警卫员说:“师父曾给我起了个小名叫填仓,我现在终于明白了,就是祈求老天风调雨顺,天下的百姓能够五谷满仓的意思。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我们的事业,都是在为和平而战。我想,虽然我与他的信仰不同,但是,咱们所做的与老人家所奉行的‘天之道应顺于民’的道家理念,是殊途同归的。”说完,他催动战马,迎着雪花,踏着广袤的东北大平原,向目的地疾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