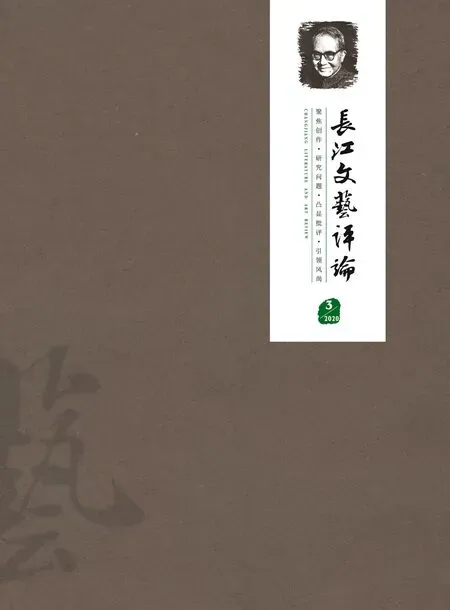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启蒙式”批评与“志业式”批评
◆梅兰
近日,编辑部转来牛学智先生《“主持人化”恐怕难以拯救批评》(以下简称牛文)一文,经细读,产生了不得不发声的想法。牛文虽然指向当前文学批评期刊的栏目制和主持人现象,实际上是从期刊的栏目制谈到了两种批评的现状:学院里的专家批评占据了各大文学研究期刊的版面,而原来相当活跃的“作协派”“自由评论”等从人员、文体到发表阵地都受到严重挤压。牛文不仅对这两种批评的此消彼长提出质疑,而且认为这导致了当下批评的窄化和脱离现实,换句话说,批评的专业化带来了公共性的减弱甚至消失。
之所以出现两种批评,这要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机制说起,建国后到20世纪80年代,文学艺术皆属于社会思想战线,作家和批评家当然就是新中国思想战线的战士,批评者的身份、言论影响力以及文学批评导致的各种始料未及的后果,都非今日所能想象。20世纪90年代以后,文学不再是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作家很大程度上恢复为一种自由职业,文学批评的规模和影响力也相应改变,批评的学院化、专业化成为近30年来的大趋势。牛文所列举的“主持人化”的特点,比如主题化、片面专业化、急切经典化甚至某种程度的门阀化,可以说都是批评的专业化带来的。这其中最大的不同是身份及批评观念的差异。“作协派”批评代表的是培育、指导、帮助作家进行创作的官方力量,可以以集体名义开展批评,代表了官方的政策、方针、意图导向等。同时,作为一种直接介入社会生活的宣传方式,“作协派”批评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比起“学院派”批评,“作协派”更为强调文学与现实的关系,看重作品体现出来的社会价值及意义。“作协派”批评,体现为快速有力的文学社会学批评范式,具有强烈的启蒙现代性特点,可以称之为“启蒙式”批评。在传统媒体时代,“启蒙式”批评的价值判断和各种大讨论曾经发挥很大作用。近30年来,一方面社会公共空间受到压缩,另一方面批评的专业门槛越来越高,这两方面共同造成了“作协派”等“非学院派”批评的困窘。但是“启蒙式”批评并不仅限于“作协派”等“非学院派”批评,“学院派”批评中同样有“启蒙式”批评身影。以“启蒙式”批评来命名,所根据的不是从业者的现实身份,而是其所持的批评立场及方法。
相对于“启蒙式”批评的意识形态特色,一部分“学院派”批评立足于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把自己限定为一种学术活动,侧重事实判断,聚焦于文学作品的阐释和分析,追求对文学作品及现象的学术问题的发现与解答,套用韦伯的说法,可以称之为“志业式”批评。“非学院派”批评里面也存在“志业式”批评。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很多“非学院派”批评受到了“志业式”批评的影响。
牛文认为,当下批评表现出现代性的主体性缺失、规避现实等问题,很大程度是因为栏目“主持人化”体现的“志业式”批评占据了优势地位。牛文指出的批评危机,比如批评的集体失联、被终结、被背叛等,应该说也是从“启蒙式”批评的立场出发的。“启蒙式”批评的核心是价值评判,它有着悠久的中外批评传统,传统的文学批评基本上都侧重于道德功能和认识功能。儒家“兴观群怨”的诗教,从人格修养、认识社会、凝聚群族到宣泄怨愤,囊括了文学的大部分现实功效;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诗学,都着眼于诗的认识功能和道德功能,其中后者更为重要。贺拉斯、布瓦洛等后世批评家继承了批评的寓教于乐的道德目标,直到19世纪、20世纪的阿诺德、利维斯,文学批评仍捍卫着文化传统的道德标尺。但是文学批评传统并不能解释“启蒙式”批评的现代性立场,甚至这种立场与文化传统刚好是批判关系,“启蒙式”批评的现代性起源意味着对传统批评的重新审视甚至断裂。17世纪之前,欧洲的文学批评从属于文法和修辞学。17世纪批评(criticism)这一术语及批评活动才得到承认并传播起来,“这个过程与一种普遍的批评精神及其传播有关,这种精神包含了一种逐渐增长的怀疑主义,对权威和陈规的不信任……这一过去被严格限制在对古典作家进行词句批评这种意义之内的术语,后来则逐渐与对作家的解释、判断这一总体问题,甚至与知识和认知的理论等同起来。”[1]显然,新的文学批评凸显了建立现代性线性时间秩序中的批判精神,正如浪漫主义运动中的雨果对原始时代、古代、近代的三阶段区分,每个时代都有它相应的文类及审美原则。如果说17世纪、18世纪的批评活动涵盖了作家作品的校勘、判断、阐释、说明,以及报刊评论,还在哲学、美学、历史学、心理学等学科外徘徊,那么“启蒙式”文学批评的出现则要归功于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与历史、哲学的结合。伴随着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19世纪的文学批评从一种文学趣味的判断和表达,成为担负起民族国家精神建设重任的角色,俄国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批评家将“启蒙式”批评推到了巅峰,别林斯基以及他气势磅礴的“年鉴式”批评,给20世纪的现当代中国批评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启蒙式”批评从根本上来说,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以人的主体性为核心,有着极强的现实政治关怀的意识形态批评理论与实践。在20世纪的中国语境中,“启蒙式”批评是从对自我消遣式的传统诗文小说批评,到启迪民智推动社会变革的功能巨变,是从传统文人到知识分子的批评家身份的改变,也是文类等级剧烈变化后的现实主义文学及批评的一路披荆斩棘。在“启蒙式”批评看来,作家、文学和社会是一个互相影响的有机整体,文学批评即是直击社会现实的公共性批评。“启蒙式”批评主体往往具有集体主体的特点,通过把自己与批评精神等同,构建起不容置疑的批评伦理,批评因此具有崇高风格。“启蒙式”批评因为它的价值评判而建立合法性,“启蒙式”批评的价值评判来自于现代理性个体对文学的生活时间与历史时间的双重感知,后者决定了“启蒙式”批评的高度。但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已宣告现代理性个体与历史时间的失败,20世纪的大部分西方批评流派或思潮都建立在非历史主义或反历史主义基础上,比如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神话—原型批评、精神分析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后结构主义批评等。“启蒙式”批评所依赖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类型都来源于19世纪的欧洲,“启蒙式”批评的信念源自思维与存在、主体与社会生活之间的同一性逻辑,表现为物质决定论(或主体决定论)、文学反映论、本质主义文学观等,这决定了它难以回应当下非同一性的文学现象和问题,只能频频回到19世纪文学和批评中找寻思想动力和典范文本。但是,通过这种回溯活动,“启蒙式”批评也仅保持着对当代文学及批评的批判姿态,无论是可疑的批评主体、陈旧的文学观念、高度雷同的批评模式,还是苍白的道德评价、避实就虚的批判锋芒,都显示出其合法性危机。
“志业式”批评去掉了“启蒙式”批评的意识形态立场,批评成为一种科学研究,而不是作为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或社会学家的分析、预言活动。牛文称“志业式”批评为价值共同体,但事实上,“志业式”批评并不存在价值共同体,单一的价值观恰恰被学院的考核制度所忽略,甚至学术生产机制所反对的——学术期刊组织学术问题讨论时,尤其鼓励价值立场相互论辩。牛文还认为,“学院派”批评的主题化、专业化等特点来自学院的科研考核制度,从经济角度考察“志业式”批评的成因当然有其根据,但并不能解释“志业式”批评的非功利性特点,比如审美立场、问题意识、跨学科研究方法等。这种评价忽略了“志业式”批评的批评立场的合理性,而且把批评的专业化与公共性立场完全对立起来,也颇为狭隘。
不管是就某些学术问题组织讨论,进行文学史史料的整理和发现,开展作家作品批评,还是回顾新时期40周年的文学研究成果,研究当代著名批评家或推出青年批评家,当下的“志业式”批评构成了一个学术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学术规范而不是现实关怀构成其道德底线,知识生产而不是思想批判成为它的主流,比如文学史的发现与重新阐释。“志业式”批评的研究立场来源于20世纪文学批评的几个转变:
第一就是批评由哲学、美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附庸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变化。如果说“启蒙式”批评与政治、哲学、历史更为契合,政治激情、历史意识、批判立场和辩证法构成了“启蒙式”批评的独断论模式。那么,“志业式”批评则更类似科学研究,研究对象的观察描述、批评对象的选择、问题的提炼论证和解答,这些是“志业式”批评的常规活动。相对于“启蒙式”批评对普遍真理的追求和捍卫,“志业式”批评对真理的谱系、话语及运作机制更感兴趣,它致力于对文学的客观分析、阐释。20世纪被称为“批评的世纪”,这很大程度体现在批评成为了一门独立的学科。20世纪文学批评引人注目的是其自律性追求,批评甚至可以切断文学与作者、读者等外界事物的联系,把文学批评作为一门科学对待。文学观、文学文本、文学语言、批评方法、文类、文学史、文学制度等被重新勘测,这些批评活动完全改变了人们对文学的理解方式。
第二,文学批评的审美建制。虽然这一特点现在饱受批评,但批评的审美建制并不是当代文学批评的成就,而是启蒙主义时代以来随着宗教信仰的衰落,艺术救赎功能被逐渐放大的结果。另一方面,审美批评一直伴随着启蒙现代性的发展,是批判启蒙现代性的同一性思维的对立面,它排斥普遍性、主体性、中心、确定性、同质性等,努力彰显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异质性特点,比如现代主义及后现代主义文学对现代性的批判。文学批评审美建制的问题在于自身的僵化,可以通过重新激活其价值批判维度来解决,审美实践本身包含意识形态内涵,而且20世纪文学批评的人文主义和形式主义思潮构成了审美自律性与政治功利性的对话与融合。
第三,文学批评的理论化和超学科方法。后现代主义思潮拥抱差异和异质性,几乎在文学批评的每个环节,都出现了决然不同的概念和路径。文学批评研究他者、反讽、含混、话语、外位性、身份、梦境、规训、编码、仿真、互文、狂欢、身体、欲望、社会性别等等。在一些哲学家看来,文学批评已经取代了哲学,成为一种综合性的跨越多个学科的理论,卡勒称其可以解答阳光下一切现象和问题,“为意义提供了新的和有说服力的说明”[2]。文学批评的理论化背后是对同一性逻辑的分解,范畴概念的更新意味着批评思想的重新建构,大量的人文甚至自然科学术语的涌入改变了文学批评与历史哲学的紧密联系。批评不再与现代民族国家、社会现实、主体精神休戚相关,背负过重的功利性内涵与功能,而成为各有特色的“片面的真理”的对话场域。可以说20世纪文学批评本身即是非同一性思维的成就。文学批评的理论化不仅仅表明20世纪文学批评对哲学、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语言学等学科的广泛借鉴,而且也充分证明20世纪是一个泛文学时代,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都注意到了文学的价值,它们的跨学科研究从各个角度扩展了文学批评的领域。
知识体系的变化决定了批评的学科化和专业化,同时,对同一性思维及其一元论后果的反思也促使了批评的转向,“志业式”批评是新时期以来西学东渐和学术思想反思的结果。当下中国的“志业式”批评也并不缺乏牛文所忧心的批评公共性,批评公共性的萎缩很多时候并不能仅靠指责“志业式”批评就能解决。“志业式”批评是文学批评脱离政治话语的结果,也是批评从神坛走向职业化的结果,批评者不再承担政治任务和思想导师的职责,而是回到学术工作本身。但“志业式”批评是不是去政治化、去公共性,要看如何定义政治。倘若政治指的是权力的分配和斗争,“志业式”批评当然远离政治。但朗西埃认为,文学的政治指的是感性的分割,是对空间和时间、地位和身份、言语和噪声、可见物与不可见物等进行的再分配,当文本立足于感性的实践与分配,它就在历史、词语和事物之间建立了自己的政治领域。[3]由此看来,专注于文学研究的“志业式”批评同样含有政治性和道德性,只不过不是充满道德优越感的“启蒙式”批评的政治与道德立场。
注释:
[1]【美】勒内·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罗钢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3-34页。
[2]转引自【美】彼得·基维主编:《美学指南》,彭锋等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8页。
[3]参见【法】雅克·朗西埃:《文学的政治》,张新木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