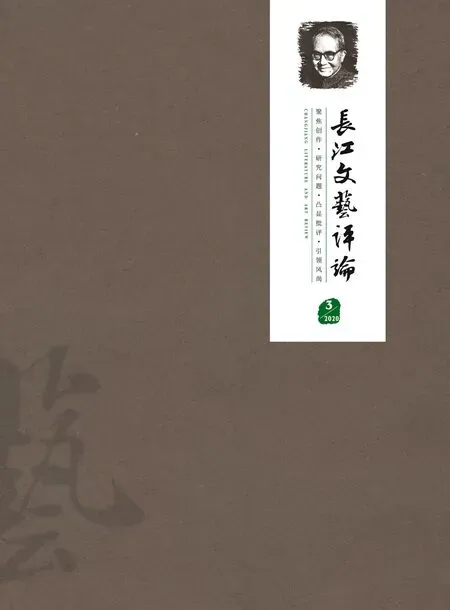我看见了我正在看着的一切
——林东林和他的诗
◆魏天无
在诗集《三餐四季》自序中,作为诗人的林东林开宗明义提出“诗言我”,作为他诗歌写作的主张,也是他阅读诗歌的趣味。这里的“言”更接近于“说”:他提醒正拿起诗集的读者,他将以“说话”的方式来表达,和他们的惯常表达没有太大差异。这里的“我”是“小我”或“个我”,是与大写的、集体的“我”相对立或对抗的写作者的投影:“作为一个诗人我们要写出的是个体表达和个体感受,因为最小的个体中也始终隐含着最大的集体。一个人就是人类。”[1]
除了“我们”这个“集合名词”夹在文字间给人有点怪的感觉,“诗言我”算不上新鲜见解。从诗歌的源头,到晚清黄遵宪“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再到朦胧诗时期顾城对父亲(诗人顾工)说:“我是用我的眼睛,人的眼睛来看,来观察,”“表现世界的目的,是表现‘我’。你们那一代有时也写‘我’,但总是把‘我’写成‘铺路的石子’‘齿轮’‘螺丝钉’。这个‘我’,是人吗?不是,只是机械!”[2]……概言之,“小我”与“大我”,“个我”与“集体的我”的往复循环,可视为现代汉语诗歌发展的主线之一。不过,诗立足于个体这一常识被年轻诗人林东林再次郑重提出,原因在于个体言语的丧失与集体表达的崛起的状况如果确实存在,不是因为个体与集体是截然分开的——如林东林所言:“一个人就是人类”——因而诗人被迫要做出另一种选择。集体表达的驱动力的强大表现在,许多诗人把集体经验当作个体经验,或者说,集体经验被内置为个体经验:在远离历史情境的局外人看来是集体经验者,被彼时的局内人顽强地视为个体经验;局内人的真心实意被后来的局外人视为荒诞。而看起来我们并没有从中走出,只不过黏附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集体经验,今天已被名为“日常生活”的集体经验所取代。日常生活中的“我”自然可视为全新的“我”,就像当年顾城坚信他所写的“我”是与其父辈完全不一样的,“打碎了迫使他异化的躯壳,在并没有多少花香的风中伸展着自己的躯体。他相信自己的伤疤,相信自己的大脑和神经,相信自己应作为自己的主人走来走去”;[3]但没有人能保证未来的诗人不会把今天主动领受或归化日常生活中的“我”称为“集体的我”,就像第三代以降的诗人把顾城诗中的“我”称为“代言人”。
很明显,诗人林东林正走在书写日常生活的道路上;至少,他希望读者相信《三餐四季》写的是一个普通人的平凡生活,或者,一个平凡人的普通生活。自序中的这一段话被置于诗集封底:“没有什么是不能入诗的,跟其他文体一样,诗歌并不需要特别的题材和内容。如果愿意,我完全可以写一个沐浴中的女人、你家的狗死了、我父亲二十二岁时的照片、在克拉马斯河附近或者铁匠铺和长柄大镰刀——就像卡佛那样;也可以写酩酊大醉的酒鬼生活、应召而来的摩登女郎、一辆红色保时捷、在窗外读圣经的超短裙少女——就像布考斯基那样。然而问题在于,我既不是卡佛,也不是布考斯基,同时也不是我不能成为的任何一位诗人。换句话说,我只能成为我自己这样的诗人,而你也一样。”[4]但是,诗人也许没有意识到,在他以及其他写作者如此反复强调“没有什么是不能入诗的”时候,日常生活已成为诗歌“特别的题材和内容”;每个人的生活当然不一样,但共同的是“日常”,是他所认为的对“非日常”的纠正或抗议:“‘日常’已成为具有原型意味的诗学神话,写作的目的——如果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是‘用简单的语言去发现、接近和抵达我的日常以及日常的我’”[5]。他相信用“日常”可以打通横亘在写作者与读者之间的大山,不过,此时的诗已不是原有意义上人的内心的幽暗隧道,而是连接两座看似相像却有不同的山峰的桥梁。
诗人林东林特别的地方,是他所强调的“诗言我”、走上“有我之路”的这个“我”,是世界的旁观者、倾听者和描摹者;他在世界之中,但往往不在他所观察、倾听和描摹的那个世界之中。就好像日常中他随时举起莱卡相机,闭上左眼,耐心对焦于世间交织的光与影:他倾心于复现“我”与世界、“我”与他人、他人与他人、物与物、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之间”构成一个个场域,在其间“我”分身为无数个“我”,但很难捏合为一个完整的“我”。《二十楼的雨》这首诗看似单调的重复,但巧妙暗示了日常生活确实是碎片,如一阵阵雨声;但那每一个碎片(雨声)都是一个不可取代也不可混淆的场域。每个人都在其间,因此也都是“另一种人”:
临近傍晚的时候下雨了
我听到一阵阵雨声飘过来
我听到了这是我的雨
这是二十楼的雨
二十楼的雨落到十九楼
那就成了十九楼的雨
十九楼的人听着十九楼的雨
接下来落到十八楼
那就又成了十八楼的雨
十八楼的人听着十八楼的雨
一楼的那些雨是另一种雨
它们会直接落在叶子上
雨棚上或者地面上
发出清脆的一声又一声
住在一楼的人会听见那些声音
住在一楼的人是另一种人
而《秩序》一诗中的“秩序”一词,只是对“我”与物、物与物、物与自然(光线)之间关系的另一种表述:
一整个下午我都在归置客厅
我把那张废弃的桌子移到阳台上
把两只木头沙发靠墙摆着
把小茶几摆在它们中间
把布艺沙发摆在它们对面
把地毯铺在木头沙发和布艺沙发
之间的一小块空地中央
把几盆绿植摆在墙角和茶几上
我在客厅里走过来走过去
微调着它们之间的间距和空隙
傍晚的光线从窗外撒进来
让它们呈现出了它们该有的样子
我满意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它们对应着我内心深处的某种秩序
看上去,林东林的诗具有某种现象学意味,即“面向/回到事物/事实本身”,而悬置“意义”;存在各种关系的“事物/事实”在文字中的显现,本身就是诗人意识活动的结果,其中含有情感活动,只是大多数时候被有意屏蔽。所有涉及日常生活的诗歌都有“事物/事实”的显现,并且它们常常居于文本的核心位置;只不过这种显现往往被“另一种”诗人视为“奇迹”,被当作神迹般的启示,因而穿透事物揭示启示被这类诗人看作“抒情诗”的使命。自称深受第三代诗歌影响的林东林,自然是“抒情的放逐”的拥趸。他热心于还原事物,因此需要在错综交织的关系网中为事物定位,确定秩序,也调谐万物的节奏、韵律;但他并不希望读者将诗中的事物看作是对日常的“还原”,而是想让他们心甘情愿地承认这就是日常事物本身。就像《一个吹笛子的男孩》中的“我”凝视着那个“永远地走在去库斯科的路上”的男孩时,一开始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看的是一张年代久远的著名照片:
戴着一顶毡帽
穿着一双草鞋
背着一口沉甸甸的布袋子
他的身后是高山、梯田与河流
他正在路过一株植物
早逝的瑞士摄影家比肖夫,用镜头凝固了现实世界中行走在原野中的男孩的瞬间,而诗人现在要用流动的文字让那已逝的现实重现。正是在这种白描式的、“简单的”文字中,在人物与远景、近景的层叠中,男孩仿若现身于读者眼前:“他正在路过一株植物”。精于摄影的林东林或许赞同苏珊·桑塔格对照片与现实之间关系的阐述:“现实被理解为难以驾驭、不可获得,而照片则是把现实禁锢起来、使现实处于静止状态的一种方式。或者,现实被理解成是收缩的、空心的、易消亡的、遥远的,而照片可把现实扩大。”[6]致力于还原事物的诗歌,同样也具有“把现实扩大”的功能。摄影凝固了现实世界中“决定性的瞬间”[7],诗歌则是诗人从记忆中提取他所凝视的瞬间。这一瞬间是否具有“决定性”意味,取决于他在语言中能否重新发明记忆并取代已消逝的现实:
傍晚时分我从景区出来
跟着一队游人汇入了街头
穿过密密麻麻的店铺
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
我来到空旷的长江边上
我远远看到
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
独自坐在那条长躺椅的一头
这一下子让我觉得
整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我慢慢走过去
看见了她脱掉的粉红色塑料凉鞋
她低头拨弄的小马
我走得越来越近
甚至看见了她脚背上的一小块疤痕
她后颈上淡黄色的绒毛
我已经走到她身边了
她也没抬起头来
还是在拨弄着那只小马
我的到来是为了确认
整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
(《傍晚时分穿过三斗坪》)
对一位诗人来说,记忆不是简单的回忆,是用语言重新发明那个场景并覆盖掉意识深处的它。林东林对诗歌道路的选择与其偏爱的摄影风格之间有着同构关系;甚至可以说,对摄影艺术的理解直接影响了其诗歌写作的审美取向。林东林会同意如下关于摄影的观点:“在摄影中,最微小的东西也能成为伟大的主题。人间渺小的琐事能变成乐曲中的主调。我们观察我们周围的世界,并且把它表现出来,这些事物本身具有形式上各种各样的有机的韵律。”[8]在此意义上,诗歌里的日常亦即摄影中“最微小的东西”“渺小的琐事”;从事物本身发现“有机的韵律”而不是从其背后去挖掘本质或启示,成为林东林诗歌的主调。与静止状态的照片不同的是,无论对于写还是读,诗歌是语言符号的连缀,是流动的活物;读者跟随着语言之流实际上是跟随着诗人活跃的思绪;他用语言发明记忆的过程也就是重新组装记忆的过程;他可以前后相续地交代事物,并把“决定性的瞬间”置放于诗尾,就像《傍晚时分穿过三斗坪》所展示的那样:“整个世界上只有她一个人”——整个世界在此瞬间只为一个穿红裙子的小女孩而存在。而在“粉红色塑料凉鞋”“脚背上的一小块疤痕”“后颈上淡黄色的绒毛”这些最微小的细节中,一种坚不可摧的真实,一种不可名状的巨大的幸福感从诗中涌现出来。
也许人们会说,世间万物本无所谓渺小与伟大,也就不存在非要将两者翻转过来的文字游戏。这种刻意的区别其实起于人心的偏私,更可能源自一个人丧失了爱这个世界的能力,却抱怨这世界是冷漠的、麻木的、乏味的。美国诗人杰克·吉尔伯特谈到他的诗《试图让某些东西留下》时说:“这是我想写的诗。不是因为它悲伤,而是因为有所谓。如今人们写那么多的诗,都是不需要写的。我不理解那种对在纸上排列单词的技巧或新方式的需要。你可以这么做。你可以写各种诗,但外面有一个完整的世界。”[9]诗人是“有所谓”的人,既对这个世界也指那个“我”;诗歌复现的是世界微小的局部,但它并不是微不足道的,并且要能让人感受到“完整的世界”的存在;也可以说,每一首诗都是一个“完整的世界”。第三代诗歌中诗人韩东提出的“诗到语言为止”,并不只具有新批评式的、强调文本语义与结构的意义,它是对更真实、更具活力、更有包容性的诗歌世界的召唤;它首先需要的是一颗真诚面对世界、也面对“自我”的心。将第三代诗歌认作通往未来道路上“过去的灯塔”的林东林,其诗中的“我”虽然也是以冷静的旁观者面目现身,然而,与静物画和静止的照片不同,诗人处于文本的“内部”。当他的意识活动启动,事物按照一种通常是缓慢、稳定的节奏渐次出现;他无从控制语言在流动中的自我生长,诗歌在抵达它的终点时会出现“偏移”现象,就像《两只柠檬》中的“上一次,你念起那些好听的名字/是在云南山中的墓碑前”,《桉树的气息》中的“也许我们还年轻/它们散发出的桉树的气息/要等到很多年之后/才能抵达我们”,《另一个世界》中的“不能看见的,虽然还有很多/比如另一个世界的父亲/比如究竟有没有另一个世界”,《湖边》的“在松软的泥沙上/这些垃圾脱离了具体生活/而存在着/存在着/并散发出一种新鲜而亲切的光”,《昨日一幕》中的“那光亮映在餐桌前一家人的脸上/直到来电很久后也没有消失”,以及《贴梗海棠》的最后一节:
我走到外面去
走在人群之中
揣着那盆贴梗海棠传递过来的一振
明晃晃的有一个点
从我心间向四周扩散
有的人接收到了
而有的人没有
诗歌写作正像诗中描绘的那样:“我”感应到了世界的“明晃晃的”一个点,“我”用文字复现并扩散它,给那些心还在温热跳动的人。它只能抵达它可以抵达的人,就像诗歌只能帮助那些值得帮助的人。
因此,林东林诗中有不经意流露出的温情的一面,那种基于某种诗歌理念想竭力隐藏但其实无法压制的一面;它并不比客观、冷静珍贵,但很可能,诗人的倔强,与他想从文字中芟除却无能为力的属于诗文体——诗歌语言编织物——的倔强,是平等的:
一只土狗对我摇晃着尾巴
就像对它的主人那样
我蹲下来
然后它就跑过来蹭啊蹭的
也像对它的主人那样
这是春天的一个雨夜
许多人正在山上的一间房子里喝酒
就在几分钟之前
我也是那许多人之中的一员
雨水窸窸窣窣地落下来
不断刷亮窗前微光中的那些树叶
房子里传出的一阵阵劝酒声
把雨声压得很低很低
后来我又出来了两趟
那只狗就瑟缩着挨到我的脚边呆会儿
雨还在继续下
天很冷
远处很黑
我们都感受到了这一点
(《雨夜》)
这是典型的“有我之诗”,典型的林东林的写作风格:任何人都具有外部的和内部的两个世界,诗人可以无碍穿梭于两个世界。不过作为写作者,如耶胡达·阿米亥所言:“诗人总是得在外面,在世界中……他的车间在他脑中,他必须对文字敏感,必须对如何在现实中运用文字敏感”。[10]林东林的文字方式是白描外部世界,在那个世界中,事物渐次出现形成一个特定场域:土狗、春天、雨夜、许多人、雨声、劝酒声、寒冷……“我们”在这个场域中出现并拥有相同感受——当“我们”于诗中最后现身,诗人不仅跨越了“我”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也同时贯通了“我”的世界与土狗的世界:这是同一个世界,“我们”一同感受到寒冷、黑暗、孤独和莫可名状的忧心。或者说,这种并非复杂也不新颖却令人心动的感受是被文字召唤出来,它改变了外在于诗人的日常世界。诗人,按照耶胡达·阿米亥的说法,是以自己的心境,以一种“两次曝光法”来看世界,来看“世界的本来面目”。[11]在林东林的诗中,“两次曝光法”清晰显示了一个人的两个世界,“我”与他者的两个世界,是如何安静地汇流;而实际上,我们和诗人所共同看到的所谓“世界的本来面目”,只存在于文本中,只存在于那些被挑选出来呈现给读者眼睛的事物本身。这就是诗人韩东的“诗到语言为止”,林东林迫切希望的反身之处:“诗到语言为止”即“诗到事物为止”,亦即“诗到世界为止”。
林东林是诚实的,他毫不避讳他在诗歌观念和实践上得益于第三代诗人韩东、杨黎,也不会顾忌在今天提出返回第三代诗歌奠定的基础有何不合时宜:诗歌是不合时宜的,第三代诗歌的杰出代表已表明此点,却总是被人遗忘;一部诗歌史差不多就是一部“遗忘史”。一位诗人的诚实最终可能表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他不是“大自然的搬运工”,诗里的“完整的世界”不可能与诗外那个孕育了“我”和“我的诗”的“完整的世界”一一对应;所谓复现、再现,是创造艺术的方式之一,与表现、与强力的“抒情”方式并无二致。唯一需要警觉的是布列松指出的“舞台式的安排”,那种唯我独尊的感觉,那种自以为“世界的本来面目”没有潜在之意和弦外之音,因而要“消灭”文字的引申义、暗示义、隐喻义、象征义——以一己之私欲挟持语言,并控制读者对诗歌语言的接受和阐释权力的妄念。对林东林以及对那些自称诗歌直接取材于“我”的日常生活的诗人来说,明智的选择也许是在文本中让出“我”的世界——只有让出“我”才有“我”;只有让出“我”才能得到梦想中“完整的世界”:
一个苍老的女人坐在草坡上
坐在铺着垫子的草坡上
望向远处
她的身边没有他
也没有年龄相仿的女伴或者
环绕而欢闹的儿孙
他们今天没来
还是正在不远处准备野炊的食物
她一动不动地坐着
并保持着那个一动不动的姿势
孤弱的样子就像多年之前
少女时代的一天
风和日丽
她也坐在这儿
或者一处跟这儿差不多的草坡上
——没有垫子,青草就是垫子
她也一动不动地坐着
并保持着那个一动不动的姿势
在漫长无助的年月里
她沿着自己的躯壳旅行
突然之间就抵达了
外部的女人
就此成为内部的女人
但她并不为此感到追悔、痛惜
苍老使她变得平静了
空茫的眼神望向远处,多么干净
(《春日一幕》)
如前所述,两个不同的世界在这“决定性的瞬间”——“一个苍老的女人坐在草坡上”——安静地汇流:当然有“我”的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否则就不会有这首诗;但更重要的是“苍老的女人”“外部的”和“内部的”世界的交汇,在诗人的观察(外部)和冥想(内部)之中。未现身的“我”把全部世界让给了陌生的他者,是因为只有通过借助他者和他者的世界,才有可能认识“我”、更新“我”。这就是林东林在《致林东林》一诗中表达的:“我一遍一遍默念这个熟悉的名字/同时想象着那个陌生的你/在对你一遍一遍的想象之中/我反复确认着自己”。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我”是不同的,但每一个“我”意识到“我”的成长、成熟的路径并无本质差异。林东林确实不可能成为卡佛、布考斯基,不可能成为韩东、杨黎或其他任何诗人,但对诗人来说,世界是“有所谓”的,世界是有意义的,无论他怎样去理解这个意义。而对读者来说,好的诗歌是一个他者的世界,读者也正是借助诗人建构的“完整的世界”,来审视、辨认既在现实世界之中,又在文本世界之外的属于他的“我”,并最终确认:这是一首“有我之诗”。
注释:
[1][4][5]林东林:《自序·诗言我》,《三餐四季》,文化艺术出版社2019年版,第10页,7-8页。
[2]顾工:《两代人——从诗的“不懂”谈起》,《诗刊》,1980年第10期。
[3]顾城:《请听我们的声音》,《诗探索》创刊号,1980年9月。
[6]【美】苏珊·桑塔格:《影像世界》,《论摄影》,黄灿然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7][8][12]【法】亨利·卡蒂埃·布列松:《〈决定性的瞬间〉序言》,孙京涛译,“影像中国”网站:http://www.cpa net.cn/detail_news_61004.html。
[9]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诗人访谈》,柳向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449页。
[10][11]美国《巴黎评论》编辑部编:《巴黎评论·诗人访谈》,欧阳昱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第244页。耶胡达·阿米亥原话如下:“我在内部世界和外部世界之间,从未感到任何区别,我现在都没有这种感觉。真正的诗人,我认为,能将内部世界变成外部世界,反之亦然。诗人总是得在外面,在世界中——诗人不能把自己封闭在他的工作室里。他的车间在他脑中,他必须对文字敏感,必须对如何在现实中运用文字敏感。这是一种心境。诗人的心境,就是以一种两次曝光法来看世界,看潜在意思和弦外之音,看世界的本来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