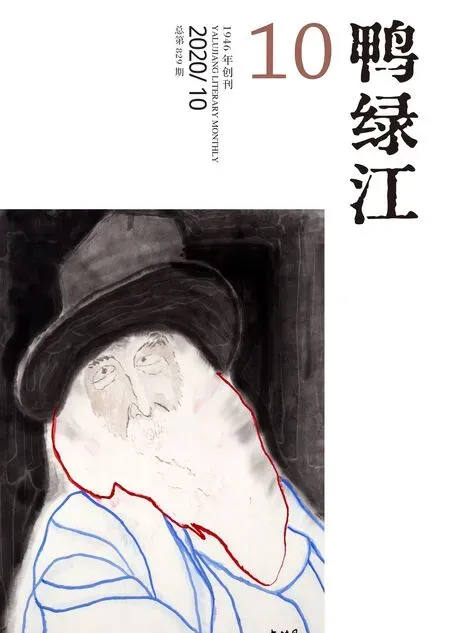游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
——辛酉中短篇小说论
张立军
小说集《闻烟》是辛酉短篇小说的代表作,其中的短篇小说《闻烟》一经发表便得到了业内高度的评价,于2019 年10 月获得了第十届辽宁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小说《闻烟》给读者营造了一种传统与现代间的纠合感,这种扭结似乎也成为辛酉其他短篇小说的一种基调或底色。无论从故事本身还是讲述方式来看,辛酉的中短篇小说总是显得那么古朴平实却又暗藏玄机,暗暗地潜隐着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纠葛。
1
辛酉小说的人物是带有传统的底色的,不管是处于小说中心的主人公,还是依故事发展出场的次要人物,不论是来自历史,还是来自当下,他们身上都流淌着某些善于延续和传承的基因,抑或是某种集体无意识的留存。从小说人物的职业设定来看,这种古朴性的遗存以一种传统技艺的方式显现于小说中。在《闻烟》(《闻烟》,作家出版社,2016)中,一个具有一百六十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同顺祥”定格了“我”和“父亲”作为冰晶糕技艺传承人的角色,而中篇小说《过霜》(《鸭绿江》2019 年第10 期)中的老邹为了获得救命龙菇展开了艰难的周旋,却也因此勾画出一个身怀绝技又心存大爱仁心的胡神医来。在今天的文化语境中,他们是传统技艺与文化的传承者,从事的职业神秘而且光鲜。《闻烟》在开篇即亮出了“我”所从事的特殊职业和身份,“我叫柳见三,是同顺祥的第八代传人”(《闻烟》)。传承人的身份造就了“我”对自己职业的热爱和自傲感,“临溪镇有很多卖冰晶糕的店铺,同顺祥的名气最大,历史最悠久。准确地说,其他冰晶糕店都是同顺祥的仿版。”(《闻烟》)而《过霜》中的胡神医更是有着累代从医的世家身份,谦和严谨的行医态度与漠视金钱名利的人生信条,令他远近闻名且备受尊敬。
在小说中,辛酉对传统技艺的描述堪称精彩。《闻烟》中有一段对冰晶糕制作工艺的描写,对冰晶糕的整个制作过程,如选料、搅拌、“拍面”、灌模、蒸糕以及磨粉、榨油等,都进行了细致的介绍,这不单单增强了故事的真实性,更加深了读者对制作冰晶糕这一传统工艺的认知。《过霜》中,胡神医治疗老邹肺癌的过程被作者捕捉,“胡神医的药很特别,是一种贴在后背上的外用药。由多种药材打磨成粉末状,再配上五十五度的玉米酒搅拌在一起,最后像贴饼子一样贴到患者的后背上固定好。三个小时后等药饼里的酒精蒸发干净了,就把药饼解下来再重新倒入一定比例的五十五度玉米酒搅拌。患者要每隔三个小时换一次药,而且一天24 小时都要将药饼贴在后背上,十分遭罪。”(《过霜》)事实上,这两篇小说在工艺方面的描述,均源自于推动故事发展的“祖传秘方”,不同处只在于一边是一张药方,一边是一道神秘工序。作者将类似的描述和介绍融于整个故事中,就像晕染和浸没,直至向整个故事铺陈,不甚刻意,不留凿痕。其中作者讲述得有板有眼,有一种举重若轻的自如。
在辛酉的其他小说中,主人公的职业称得上五花八门,其共通之处在于这些职业将随着社会的迁移而被时代封存,《她和他》(《闻烟》,作家出版社,2016)中追随黑影发现“师父”利用墓地做毒品交易并卷入其中的墓园更夫,《王进的自行车》中那些在起重机厂里扯线、弹线、打铳子的20 世纪60 年代的国营工厂学徒工,《三颗痣》(《闻烟》,作家出版社,2016)中话不多、但却心存刻骨初恋的理发师阿霞等,他们所从事的职业连同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都在悄然发生着变化,他们是蜷缩在小说中的时代的缩影,也是在急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冲击下的无奈。《过霜》中胡神医有三次程度不同的无奈,第一次是接到药材商王厂长的电话,传统药材的逐渐消失、涨价,让胡神医忧心忡忡;第二次是在自知无力拯救病人,对青年夫妇即将面临丧子之痛时胡神医那貌似认命的无力劝说,“世上哪有什么神医,也没有能包治百病的药,人各有命,你们认命吧”(《过霜》);第三次是胡神医内心平静却无奈地献出药方。三次无奈的程度显然在不断递增,然而这种无奈的背后却掩藏着现代社会对传统的弃置,正如胡神医所担忧的,“因为这张宣纸很快就是一张废纸了。你们只知道龙菇现在已经基本绝迹,但面临灭绝危险的药材可不止它一个。不出五年,方子里的好多药材都将消失。”(《过霜》)《闻烟》似乎也存在着这样一个传统技艺在现代社会如何持存的问题,它面对的是更加激烈的两难问题,在传承人和技艺无法并存的时候当做何选择?在现代社会的步调和语境中确实很难找到适中的平衡点。
2
如果说《闻烟》和《过霜》这类的小说是从传统窥探现代,透过对传统技艺和人物的身份的构筑来呈示现代与传统之间的罅隙的话,那么辛酉还有一部分作品则是从现代去窥探和触摸传统,意欲找到两者的契合点,并试图将现代与传统进行勾连和接续。
如《第四十九天》《路灯》《走夜路》《相亲》等短篇小说,其描写的尽管是现代生活中的点滴或者片段,但从讲述方式和萃取的内容来看,却有着中国传统志怪志人小说的缩影和叙述逻辑。《第四十九天》从儿子半夜不住的啼哭声开始讲起,其中嵌套了两个具有民间传说意味的故事,不知来路的“周阿姨”与啼哭孩童的某种默契,使生者与死者之间的神秘关联在故事的讲述中得到延展,“你们不知道吧,在孩子出生后的第四十九天,他的前世会来看他的,人鬼相逢一定会有异常的”(《第四十九天》)。这使得民间传说与现实之间产生了若即若离的对位关系。
《路灯》和《走夜路》乍一看来不觉有些恐怖,“我忍不住又往刚才烧纸的方向瞅了一眼,发现那个老太太还立在原地,一动不动。不知为何,眼前的情景让我心里一激灵。我赶紧转身就走,在回家的路上,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太反常了……”(《路灯》)“后来,有一天晚上下起了大暴雨。张老师想,如果在这种天气下还能见到那对男女,他们就一定是非人类。于是,张老师穿着水鞋和雨衣,又来到松树林,躲在一棵树后环视……就在张老师转身的一瞬间,他看到那对全身赤裸的男女,静静地并肩站在他面前,身上没有一丝一毫被雨水淋湿的地方。那个男人用一种近乎磁带走调的声音说道:‘你在等人吗?’”(《走夜路》)故事读到这里时竟令人有些不寒而栗,而在故事的收束处,作者却将故事引向了另一种路径。面对行为乖张的“赵婶”,“我伫立在寂寞的街头,望着他们两个人远去。……低头看着那个还没有完全燃尽的火堆和静静躺在地上的一小摞报纸,之前准备好的忏悔不由自主地从我嘴里冒了出来:‘妈妈,对不起,儿子没能给您尽孝……’”(《路灯》)而春梅给“我”讲恐怖故事,吃假“狼肉”之后,“我就再没那么胆小了,也可能那块狼肉真的有效果吧,我常这样想”《走夜路》)。这不仅让恐怖气息烟消云散,甚至让整个故事变得温馨起来。
从结构故事的方式看,我们似乎可以从辛酉的许多小说中看到《聊斋志异》的古怪精灵和冯梦龙“三言”中某些谐趣的缩影,《宿命》巧妙地把院长竞聘会上临时加的业务测试和过去的错恶联系在一起,并使其成为一种具有宿命性的惩罚措施,天理昭彰,为恶者终究无处遁形,《喻世明言》的味道也便由此而生。《相亲》中“小伙子”发来的一条道歉信息,让整个故事蒙上了古朴的诡异感,但故事走向却充满了温馨和悲慨,不禁令人想起陈陶的《陇西行》来,那种“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的千古悲悼在相亲的故事中复燃,读后不是落泪,而是心中的酸楚。
值得一提的是,辛酉的这些小说,尽管是立足于现代生活立场,却是以一种传统谐趣去讲述故事,让整个故事蒙上了俚语传说的色彩。这些故事的主干和背景大多发生在现代都市,但在整个讲述中却始终没有离开民间传说的叙事逻辑。这种在讲述的过程中让传统奇幻甚至灵异故事干预情节的发展,并使其成为故事的重要构成的组织方式强化了现代与传统的关联,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作者站在现代生活中对传统,特别是对那些即将遗失的记忆的回望或者致敬。在辛酉看来,现代社会的迷失,似乎源自于对传统的遗失,而寻求拯救的方式正是以叙事的方式有意从现代朝传统进行回溯。这种回溯更多的是一种试探性的尝试,就像某些神秘的“配方”很难掌控此间的配比一样。
3
辛酉小说的讲述方式简单而淳朴,他常常以第一人称“我”作为叙事的主视角,在他的小说集《闻烟》中,这种叙事视角较为普遍,如《闻烟》《谎言识别器》《她和他》《三颗痣》等,均属于此。这种叙事视角增强了故事的亲和力,使故事给人以一种亲历感,读者的视野和阅读体验会随着主人公的起起伏伏不断地迁移。但这种叙事也是具有限制性的,它无法像全知视角那样充分和面面俱到,所以辛酉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使用了对举和嵌套的方式,对叙事视角进行转换和调整,以便于扩大小说的容量,强化故事性。
《她和他》分别以第一人称讲述了佳佳和乔风之间,从彼此相识到消失在各自视野之外,再到相见并且袒露心声的过程。《三颗痣》分别以第一人称讲述了理发过程中理发师阿霞和顾客吴凡那懵懂的初恋体验。这种叙事模式使故事的主人公分裂成了两个“我”,而当故事结束时,两个“我”又相融为一,这样以两条独立的线索接续故事,使故事呈现出一种传统的线性发展模式,故事性也在两个独立的故事线的碰撞中得到填充与完成。在一个故事中嵌入其他子故事的复调形态,在辛酉的小说中也很常见,像《三颗痣》中程栋写给吴凡的信,《走夜路》里春梅给“我”讲的恐怖故事,以及《第四十九天》和《相亲》等插入的其他故事等,这种写作方式使故事之间相互交错,加紧了表层故事与潜层故事之间的紧密度,强化了小说的恐怖或悬疑效果。《创可贴》中,作者将老板对暗恋者的寻找与“我”充斥着人到中年渴求外遇的故事相融合,将那种情感的流动与抑制的心理展现得淋漓尽致。结尾处,一个人怅然若失,另一个人却在生活与爱情产生的矛盾中经受住了考验,回归家庭,两个故事的交织无疑增加了个中复杂情感的浓度和容量。
尽管辛酉小说总体是平实和充沛的,读来貌似平淡却并不索然无味,这主要在于他的讲述过程并没有脱离对生命意志和意识的探寻。从内容上看,其中饱含了对人性和人心的描摹。其中有觊觎和明争暗斗,像《闻烟》中那些无时无刻不在觊望同顺祥冰晶糕制作秘方的竞争者和族人,他们构成了夺权派和正统派之间的咄咄逼人与钩心斗角;《过霜》中为争夺“龙菇”“药方”展开的欺骗与欺诈,让人心在本心中不断地扭曲复位,再扭曲再复位;《宿命》中,“我”为了仕途,不惜将妻子和孩子隐藏起来,与周副院长之间展开的明争暗斗最终都归于对一个类似诅咒的专业测试的恐惧和胆怯。
这些中短篇小说中也不乏人性光辉的闪现和脉脉温情的流露。《闻烟》中,父亲始终隐藏着冰晶糕最后一道工序的诀窍,给自己的孙女取名“闻烟”,其实质是为了减少这道工序对儿子的损伤,意在延长自己儿子的生命,其良苦用心可见一斑;《第三种可能》中,在得知那位定期定时向“我”借火的大叔,是出于对儿子的思念的时候,在得知那个对“我”施暴的文倩正是帮助“我”解围、暗恋“我”的女孩的时候,“我”原本被激起的浮想联翩和恨意也随之烟消云散了,在这样的结尾处,给读者留下的是温馨和些微遗憾。
辛酉中短篇小说的谋篇有精到之处,叙事过程中对结局和结尾的揭示使得故事摆脱了悬疑和恐怖,不落入民间故事的“小道”,令故事变得圆润闭合,具有可延展性。这种叙事模式同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它平稳低沉,缺少了些许变化和起伏。原本第一人称叙事的代入感较强,能够让读者身临其境并随之起伏。然而辛酉的叙述又偏于冷静,仿如以旁观者的姿态叙述“我”的故事,又给读者一种若即若离的跳脱感。与此同时,对故事特殊时代背景的构筑和特殊职业的捕捉也很可能会削弱作品的故事性,大篇幅的介绍性文字也很可能妨碍故事叙述的节奏感,弱化冲突,让故事缺少应有的跌宕起伏的曲线。此外,在嵌套故事的过程中,也应注意适当调配,一方面不能影响主线故事的发展,另一方面嵌套故事还需注重推动情节的功能性问题。
总体而言,辛酉用他的作品为我们敞开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他的故事涉猎的行业众多,主人公职业各异,然而他的作品所触及的重点并不止于这种横向的丰富性,更多在于他有意无意间做出的一种现代与传统之间纵向的勾连。在过往诸多探讨现代性与传统问题的小说中,多见的是构述它们之间的矛盾与裂隙,或是透显出现代所背负的历史的沉重。而在辛酉的系列中短篇小说中,给读者带来的却是更多的寻找,无论是通过对传统的追溯去追踪现代生活所遗失的元素,还是透过现代去窥探和触摸传统,他的目的都是在寻找一种完美的契合点。也许正是由此,他的小说薪传古朴又熨帖现代,涵载现代又绾合传统,其间隐藏着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冲突与纠葛。在传统渐行渐远的现代生活中,人逐渐被工具和技术所掌控,遗失传统的同时仿佛也在遗失人自身,介于此,如何唤回人情感的丰富性和生命的真实性,让人最大效用地享用技术带来的幸福感,而不是被技术钳制?对这一问题的求解途径是多元的,而作为小说家的辛酉的答案,则是回到传统,试图通过寻回传统,弥补遗失,来抵消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那些负面因素。所以,他在叙事时,总是在现代和传统之间摇摆,试图将现代与传统进行勾连和接续,意欲找到两者的契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