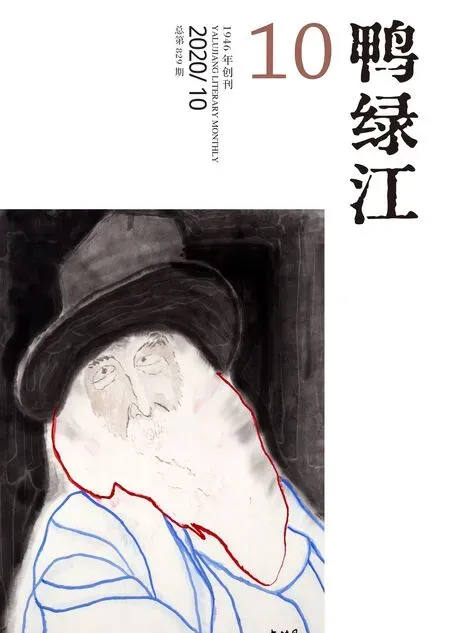小小说七题
盖氏无双
伊本多情
掐指一算,小娇今年也已三十有七。离开沈阳十余年,已经是上海市民了。
我们的友谊始于上20世纪90年代。那时,我们正是心高气盛,把青春年华当成爆米花,一把一把随意咀嚼的时候。
小娇的脸当时看还算不上漂亮,就是觉得有点另类。不久就开始黄头发当道黑头发靠边儿,文眉、画眼儿、漂唇等等面部深加工的手艺遍地开花了。于是,人们的审美便有了翻天覆地的改变,欧式眉眼儿大行其道。那些街上走动着的美女,那些橱窗里固定着的模特,通通眉毛高挑,眼窝深陷,红唇热烈。再看小娇时,不由得羡慕人家长得那叫自然美,加上她走路时习惯的“猫步”,伴着精细的小蛮腰,红色的长摆裙裙角飞扬,充满了波西米亚风情。
走在这样一个风情万种、妖娆多姿的女人身边,我是很自卑的。从她那里总结的经验就是:作为一个长相一般、走路僵硬的女人,尽可能不要和比自己漂亮又摇曳的的女人并肩同行。
那时候,我正在一个据说能够孕育作家的“摇篮”里,做着一个叫作“文学”的美梦。小娇常来找我。她会让男同学觉得眼前一亮,也会让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女同学心生嫉妒。我很高兴她来。
我一直觉得,她比我更适合待在那个“摇篮”里,做一个“文艺女青年”。她对人生有比我更美的憧憬,对生活有比我更曼妙的期待。她说,她能听到梦想开花的声音。这语言多诗意啊!在我那个四面漏风的寝室里,她倚在我的床头,长睫毛下的大眼睛对着上铺的床板忽闪着,散发着迷人的光芒。我坐在冰凉的木头凳子上,脚搭在床沿上,一颗接一颗地嗑着瓜子,只听到了咔嚓咔嚓的声音。
小娇比我先参加工作,先后换了很多种类的工作,都不如愿。总觉得有更好的事情在等着她去做,当然,在做那些愿意做的事情时,一定还会遇到一个喜欢的人。于是,在更换工作的同时,那个人也在替换中。
一晃,便过去了许多年。我已婚多年,脸色渐黄。她多年未婚,神采依然。她像她的爱情一样,一直在路上。
最近一次来电话,说从沈阳返上海的火车上遇一男子,英俊挺拔,玉树临风,成熟稳重,资产雄厚,不仅待她温柔体贴,还至今未婚。更值得一提的是,该男子一点也不像传说中的上海男人,很东北。目前两人已经同进同出,你侬我侬,忒煞情多。
如此艳遇,符合她的浪漫情怀。
一个人的战争
2012 年元旦,祝福的信息呼啸而至。在那些喜庆温暖的文字里,夹杂着小蕙的一条短信,三个字一个符号:祝福我!对于我这样一个思维走直线的人来说,这几个字充满了莫名其妙的味道。有些疑惑发信息是说不清楚的。一个电话过去,茅塞顿开:截止到2011 年12 月31 日,小蕙的丈夫长达9 年的任期结束,从此此夫正式卸任,改称号为前夫。而小蕙从2012 年元月1 日起,恢复单身。这事儿,对于小蕙,的确可喜可贺。
我发自肺腑地对她说:“祝贺你啊,终于胜利了!”这样说,是因为我目睹了小蕙九年的婚姻生活里,有长达八年的时间在为离婚抗战。当然,她的战斗是间歇性的。一般来说,每个月会爆发一次,其余时间还是可以和平共处的。爆发的原因很多,比如她在餐桌脚下发现一块橘子皮,观察了一周之后,它依然大大咧咧地待在那里,从柔软到坚硬,兀自躺着,而老公竟一直熟视无睹,遂勃然大怒。比如她老公的烟屁股不小心把那套米黄色的沙发烫出了个小洞后,竟用透明胶给粘上了,欲盖弥彰,遂火冒三丈。比如老公夏天的那条休闲裤,因为穿得过于频繁,屁股后面已经被磨得松松垮垮,膝盖处已明显突兀,却仍然钟爱有加,遂怒不可遏,于是被卷巴卷巴一扔了之,后怒骂一番。比如冬天出入有车,她老公却仍然要把自己穿成个企鹅状,整天窝窝囊囊,像个移动的棉花包,她看不上却又无法阻止,遂气得咬牙切齿……如此种种,使得小蕙整天像个大气包,说不定哪天会被扎个眼儿,冒出些许愤怒来。
小蕙每次发火,都是忍无可忍,自然会上升到一定高度,一番怒吼后以宣布离婚为口号,以她老公懒得迎战收场。
暂且不论小蕙如何,单说她老公,我其实是满心佩服的。他能在如此频繁的战火硝烟中保持温和的心态,足以见得其心胸的宽广,以及对婚姻的容忍,对琐碎的宽容。
实际上,这是小蕙一个人的战争。她老公是战争的始作俑者,但却从不参战,更不恋战。小蕙长剑在手,却四顾茫然。她有点累,还有点悲壮。退出战争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离开战争的导火索。痛定思痛,口号变成实践。
在没成定局之前,我还是试图劝和不劝离。我说:“其实,你老公的那些缺点是大多男人的共性,你不去计较,自然就不算什么大事儿。仔细想想,你嚷嚷了这么多年离婚,你老公依然对你不离不弃,那还不是因为真的爱你吗……”未及说完,小蕙拦腰打断:“不要和我说爱,爱就是个屁,听得见声,摸不着影!只有那些乱七八糟的日子才是真实的,再不斩断,我都快崩溃了!”我一时无语。
都说婚姻是需要经营的,但有人愿意经营,有人懒得经营。还有人想经营时,却发现没什么值得经营。于是,黄铺儿。
我们都是玻璃花
快下班的时候,手机“汪汪”地叫起来。那是小语打来的电话。
小语属狗,她亲自在我的手机里把属于她的来电铃声设计成如此,导致我的生活中随处可闻狗吠之声。她自己听不见,就不觉得烦。
“亲爱的,请我吃个饭呗!”她懒懒地说。我没犹豫,说好,找个地儿吧。“泰山路上,檀香楼,二楼,我就在这儿呢,等你!”我想说,还没见过像你这么积极的被请的主儿呢!但没等我说出来,她就把电话挂了。
天热。郁闷。我也懒得回家。
十五分钟以后,我见到了掩映在淡紫色珠帘后面的小语。她手举一杯香茶,做思考状。看见我,龇牙一笑,淑女风范荡然无存。
“铁子,你可来了!快点菜。”我不喜欢她这样叫我“铁子”。那是东北地区十几年前流行的一个词儿,可褒可贬。同性之间这样叫是表现朋友关系“杠杠的”,那是一个结实!异性之间这样叫,用北京话说,那就是个“情儿”,容易让当事人心生荒凉。如今这个称谓早已被各种名词替代,但小语偶尔还是会冒出来。相比之下,我倒宁愿她喊我“亲爱的”,虽然从她嘴里说出来,会让我有毛毛虫缓慢爬过肌肤之感。
点了两菜一汤。小语说,咱俩喝点酒吧,我想喝酒。
那就喝吧。
服务员连忙把酒水单递上来,开始介绍那些提成高的酒水。我最讨厌这种强加于人的方式,摆摆手说我自己看吧。
白酒性烈,红酒做作,啤酒轻薄,还是喝花雕吧,比较温和。有三年有五载的,年头越久价格越好。这年头儿,只有女人才越老越不值钱。于是,满怀愤恨点了一瓶二十年的。贵就贵点吧,解恨!
菜上齐全,酒也温过。
开始吧。
两个长发披肩、身材尚且不很臃肿、皮肤还算白皙、多少还有些姿色的中年女人,在临街的玻璃窗后,手擎花雕,自斟自饮,把自己当成一幅风景。
红晕浮霞一样涌上来。再温和也是酒啊。
小语说,铁子你知道不,我最近老惨了。上回朋友透露个消息,让我买那只蓝筹股票,一个金融危机,把我赔了个稀里哗啦。现在到处都说金融危机已经过去了,可它还潜伏在那儿,自个儿危机呢!什么狗屁股票!我们家老范不知道我买,这要是知道了,还不得哭死啊!
小语说,我儿子九月份就得上小学了,找了一大圈人儿,绕了八百道弯弯,可算是给塞到市实验了!我的妈呀,你知道扒了我几层皮吗?离吃糠咽菜的日子不远了。早知道整个孩子这么难,当初就应该学你,丁克到底。有时候真想捏死他得了,我们家老范是啥也指望不上,我当初怎么就嫁了那样一个人呢?你说,我那时候是不是长了个玻璃花眼睛?是不是啊?
我笑。有多少人都怨恨自己当初的眼睛是玻璃花状态啊!就算是后天治愈了,可当初因为“玻璃花”而犯下的错误却已经成了难以改变的事实,空留一声叹息。
小语说,跟你说个事儿啊。我们老板让我过几天和他飞一趟广州。说有一笔业务要谈,其实我就一出纳,公司谈业务的事儿跟我没什么关系,我知道老板是对我有点儿意思,他都说好几回要带我出去转转了。上回从香港回来,他还特意给我带一个腕表,是蒂芙尼的。我没敢要,怕老范看见,说不清楚。
我不知道“蒂芙尼”是个什么牌子,也没有人送我那玩意儿。
小语说,我现在老是失眠,也不知道为啥。活了三十多年,终于知道什么叫胡思乱想。越想睡越睡不着,就开始找理由。就觉得我们家老范那呼噜,呼哧呼哧的,像个破火车,真想一脚把他踹地下去。我现在听见他喘气都烦得慌,老范说我是更年期,你说咱是不是离更年期还有段距离呢,不能这么早就更了吧?
话多,酒喝得就多。二十年的花雕变成大红花,贴在小语的脸颊上。小语醉眼迷离,一点儿也看不出有玻璃花。
二十年的花雕啊,破费了我一把银子,却没机会喝上几口。
把小语从饭店架出来时,正值月色撩人。
我在出租车上给老范打电话,说你媳妇掉酒缸里了,赶紧下楼接她。
车拐进制药厂破旧的家属楼,明亮的车灯打在老范被困意纠结的脸上,像似照见了一场不堪的生活。
不谈爱情
小美总会让我心疼。她坐在那里,像旧上海歌舞升平后遗落的一张宣传海报,喧嚣之后的寂寞都被她捡拾了去,注入精致的高脚杯里,一点一点啜饮。
她抬起头看我,眼神说,陪我坐一会儿吧。
我们坐在午后斜阳懒散的余晖里。不说话。各自想着心事。
没有什么能比时间走得从容。它漫不经心地走着,走成两行清泪,沿着小美的面颊无声无息地滚落下来。
“姐,我还要等吗?”小美终于说。
“你说呢?”我不知道该怎样回答。
五年。一段绚烂的年华。一枚种子,即使不能结果,也该开花了。只是一个人的浇灌,等不来绽放。
“他什么时候回来?”我问
“应该等他岳母过完生日吧!他订的是下月的机票。”
让那个长着翅膀的男人,飞着飞着就掉到山涧里吧。我在心里恶狠狠地诅咒着。表情尽量平静。
毕竟,那是小美的爱情。只是,她想给予的缠绵已经变成了他想摆脱的纠缠。
一个多么俗套的故事,整天在我眼皮子底下悲情上演。我郁闷、愤怒、烦躁,却无力改变。我只是一个观众。他们的剧情并不需要我。
我想告诉她,所谓爱情,具有多少欺骗性。那些被许多人如获至宝、自以为是的爱情,一旦彻底铺展的时候,涂满怎样冷漠的色彩。听说一座高山可以在转瞬被夷为平地,听说一条河流着流着就会枯竭,听说即便冬雷阵阵夏雨雪,仍然有君绝……世道变幻不堪,还有什么可以相信?当女人把爱情看作生命全部的时候,它不过是男人手中的一个标签,随意地撕扯下一张,粘贴在任何一张需要的脸上。那些蜜语甜言不过是男人对于爱情的简单说明,和其他雷同的拥抱一样,在不同的地方反复演练。
女人习惯在自我陶醉中以爱情面对寡情,男人喜欢女人卖弄风情而不讨论爱情。在爱情面前,男人和女人是相向而行的两列火车,轰轰隆隆而来,却总是擦肩而过。女人们高唱着“为爱痴狂”,呼啸而去,男人们则轻扬唇角,一丝冷笑映在了冰冷的玻璃窗上。
然而,我不能。我不能像个“愤青”似的,面对一张为情所困的忧伤的脸庞。
她不经历,就不会相信。
所有人都一样。
商君择友进行时
商君是一个王老五,但级别差点,算不上钻石。前几日几个朋友凑在一起,专门为商君清算了一下个人资产,明细如下:1.1升排气量的夏利一辆(八成新);闹市区四十平方米的商住房和二环外八十平方米的回迁楼共两套;股票账户有资金二十万(缩水前),现有剩余八万零四百,等待解套;银行账户存款十万(包括建行、工行、招商行、农业银行等各个户头),透支卡两张忽略不计;如果单位不亏损自己不下岗还能保证月收入四千到五千元。此种经济状态,基本可以将商君定性为铜板级王老五,大小也叫个金属,属于稀缺资源。结论出来,商君并无喜色,仍然郁郁不乐。
他也的确乐不起来。他是被老妈的一只拖鞋给甩到门外,有家不能归的人。想归也行,先带个媳妇回来。
事实上,商君的个人问题,已经是我们这些朋友的共同问题。大家伙儿为了商君的终身大事,都快成媒婆了,到处替他寻觅二八佳人,却一一无果。商君今年三十八岁,这个年龄还没个固定对象,就恨不得往下再减两岁。遥想当年,他也是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白面小生,正儿八经地年少轻狂了一阵,那些亲戚朋友介绍来的、自己个儿凑上前来的年轻貌美、窈窕多姿的小女子也是若干,一段相处过后,自然都会期待婚姻,于是最终都被商君无情地PASS 掉了。那时候,他还不想过早地身陷婚姻的囹圄,被禁锢成一棵日渐干巴的老树。到如今,商君一手拽着而立之年的尾巴,一手搭着不惑之年的脑袋,深切地感受到了光阴真是一把利剑,咔嚓一下就把他的美好年华给砍掉了,忽忽悠悠就到了一个上不讨巧下不待见的老光棍儿状态。老爸老妈都已到了古稀之年,别说抱上大孙子,就连儿媳妇的影儿也没摸着啊,老人家得是何种心情,怎还能容得这个不孝之子继续逍遥!逐出家门,算是轻的了。
其实,商君心里的火苗,也开始像那个叫“穿天猴儿”的炮仗,噌噌地往上蹿。早在三两年前,看别人这岁数都已经是娇妻在侧,儿女撒娇,其乐融融了,也心生艳羡。于是和当任女友正襟危坐,想要谈婚论嫁。万万没想到的是,女友一听结婚二字,就当场宣告“白白”了。原因很简单:以商君目前的状态,不足以为她的婚姻提供足够的经济基础和物质保障。商君只知道此种打击是空前的,却不知道,那绝非绝后。此后的日子里,商君身边虽美女不断,但只入得商场、酒店、影院,却拒入婚姻的大门,其态度之坚决,让商君痛如天涯的那个断肠人。
商君就不明白了,这些个女子,怎么看了施华洛世奇的胸针,就撇了周大福的项坠?怎么摸了LV 的包包,就扔了袋鼠的手袋?怎么两万八的彩貂也买了,“如家”的房间也开了,却仍然,腰枝一扭,转身就说分手呢?早些年与他相处的小女子,如今被他一一回忆着,竟个个让他留恋。只可惜都已嫁作他人妇。
今夕何夕啊!商君仰天长叹,一叹情何以堪,二叹世道变迁。
近日,商君致电各亲戚朋友,说自己从此不再追求美女,择女友条件一次性放宽:年龄不限,只要不比自己年长;长相不限,只要晚上可以开灯相见;工作不限,只要做的是正经营生;家庭状况不限,只要能够确定生父生母。唯一需要限制的是:此女必须得生来就是女性。
谁为董小六的爱情买单
董小六要结婚了。准确地说是又要结婚了。
在过去的六年时间里,董小六结了三次婚,离了三次婚。现在是他人生的又一个新阶段。人都说事不过三,董小六在向我发出婚礼邀请的时候,这样说道:“哥们儿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准确坐标,不容易啊!大家也都看到了,我这是经历了多少爱情的磨难才终成正果啊!哥们儿保准是最后一回了。结婚这活儿,他妈的也够累人的啊!”从董小六第二次结婚开始,他的婚礼邀请就从请帖改为电话通知了,省钱,省事,又让接到邀请的人无法拒绝。他说别的,我们都不相信,但说结婚累人,这话我们都信。当然,就算是把他累成王八样儿,和我们都没关系,但我们这些无法把他甩开的同学,是委实觉得很累了。掐指一算,我花在他婚礼上的份子钱,已经有两千五百大元了。对于我这个还活在中等生活水平以下的平民来说,这哪里是个小数啊!董小六第一次结婚,我刚有个稳定的工作。作为一个盆里洗脚、一个碗里喝粥的同学,我一咬牙,硬是挤出五张大钞,盖了个“哥们儿够意思”的大戳,递了过去。不想,这家伙没几天离了。据说是因为他老婆觉得距离没了,美也没了。离婚那天,董小六请我们哥儿几个喝酒,边喝边涕泪横流,直到卧倒在椅子旁边,人事不省。一个当小头目的同学给董小六的饭局买了单,就当为一场爱情的结束搞了场悲伤的葬礼。那段时间,董小六的脑袋始终和地面保持垂直,一副活不起的熊样。我们这几个有家的没家的地块,都成了他小子的免费宿舍和食堂。
好了伤疤忘了疼,一年后这小子就意气风发地宣布,他在人生的拐角处撞到了一份真挚的爱情,这是上天对他的眷顾,是生活馈赠给他的礼物。他要结婚了。第一次结的不对,咱再重新结。这怎么说也是个好事啊!为了庆祝他终于结束了混乱的单身生活,以及因为他的单身带给我们无尽骚扰的结束,也为了表示对他新爱情新生活的肯定和祝贺,哥儿几个一商量,决定每人表示一千元。董小六开始了生活的新篇章,我们也走入了生活的正常轨道,一时间感觉生活轻松而美好。
是谁说的好景不常在,好花不常开?真对。不到两年光景,他又离了。据说是当年生活馈赠给她的那份礼物,打了太多层的包装。董小六在过去的六百多天里,有大半的时间为一层层揭开那花里胡哨的包装纸而忙碌,直到他看到了礼物的真实面貌时,基本上已经崩溃了。还得喝酒,好在他没醉,但却提前退场了,说是情绪一直在超低空飞行,压抑过度,挺不住,得先走一步。这次,有个买卖做大了的同学买的单。董小六一走,我们也离开了饭馆,另外寻了个喝酒的地儿,天南海北瞎聊一阵散去。
这之后很长时间,董小六一阵风似的消失了,好像大概也许是去了南方,淘金去了。打他手机,一直说关机,请稍后再拨。这一稍后,就稍了一年半以后,他又一阵风似的出现了,一通电话把几个老同学都拘到某酒店。再见董小六,脸明显见大,肚子明显见圆,脖子上多了条粗大的金项链,腕表也锃亮。身边还多了个一脑袋羊毛卷儿的年轻女孩,不停地撒着娇发着嗲,弄得哥儿几个坐卧不安,寒暄一阵便纷纷告退。不多日,我们的电话依次响起,内容一致:董小六的婚礼庆典于6 月18 日下午五点在新大地酒店举行,恭候光临。为了董小六的婚礼事宜,我们几个老同学专程小聚,当然,不包括董小六。大致议题是:董小六的第三次婚礼,我们该随多少礼钱比较合适。考虑到目前社会经济状态和生活消费已是水涨船高,另外大家多年同学加哥们儿一场,即便不涨价,也不能降价啊!研究来,探讨去,最后决定,还是参照第二次结婚,依然随一千元的礼钱吧!决定一出,几个至今未婚的人明显有些面色铁青,我是其中之一。那顿婚宴,让我们哥儿几个吃得杯盘狼藉,依然觉得不大够本。
董小六再次离婚的消息传来,我们都不觉得惊奇。那女孩分走了他一半家当,出国去了。好在董小六已经今非昔比,不差那一杯羹。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用一点金钱买回了自由,而自由是无价的。他说的真轻松啊,他怎么就不想想,他用来买自由的那“一点钱”,可是有我们哥儿几个吃饭穿衣的血汗钱在内啊!这只蠢猪!
现在,他居然又要结婚了。撂下他的电话,我就觉得血往头顶上涌,一时竟不知道如何是好。他董小六走马灯似的娶了四个女人,我却依旧孤家寡人,这是什么年头儿啊!社会分配也太他妈的不平均了!我用颤抖的手分头给几个哥们儿打电话,想问问他们都是如何感想,也借以抚慰一下自己失落或者愤怒的心,更想了解一下,这一次的礼,该怎么随啊?
谁解风情
刚到家,正在灶台边发愁晚餐鼓捣点什么出来的时候,小春来了。我习惯了她的突然造访,但我不习惯她出现在我将要做饭的时候。因为她每次瞧见我在做饭,就会为此愤愤不平。以她对我的认知,我是不可以围在灶台边儿做家庭妇女状的。但这是事实,我的事实。
还是说说她吧。小春芳龄三十六,仍然待字闺中。整天愁眉不展,东掐西算,寻婚问嫁。苦闷至极时,她总会想方设法找到我,发泄她的郁闷心情。我历来是个杰出的听筒,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摆出倾听的姿势。在她无数次的宣泄面前,我的劝慰已经苍白如纸了。实践证明,她并不需要我的开导、安慰或者鼓励,她只是想找个可以倾诉的对象,而这个人要了解她、理解她、同情她,还不会讽刺、嘲笑和打击她。我是最佳人选。
在来我家之前二十分钟,小春刚和那个超市小老板分手。
“哎,让你说,我们俩喝杯茶能花几毛钱啊,他竟然要和我AA!你要是只‘海龟’我也就认了,咱也算往高层次上靠靠。你就是个开小卖店儿的,你和我扯这个,不就是一小心眼儿吗?就这样的,我还指望嫁他过上阳光灿烂的日子,那不是脑袋被门挤抽抽了吗?”
我点点头,没吱声。上次那个4S 店的老板倒是大方,见两面就答应送她一辆“甲壳虫”,连我听着都羡慕,没几天,不也吹了吗?好像是嫌人家土包子开花,装大,没品位,不懂情调。
的确,那些都不是小春心仪的爱情。在她心里,那个人是物质与精神兼具的。他可以让小春不必餐风露宿地去寻找爱的阳光雨露,他有足够的能力给小春一个硕大的水晶宫,让她生活在爱和惊喜中。当她需要依靠的时候,只要身子一歪歪,就会有一个温暖的胸膛。当她需要拥抱的时候,只要呶呶嘴儿,就会有一双坚实的臂膀。当她想要吃大餐的时候,那个人就是她的顶级厨房。当她想要购物的时候,那个人就是她的豪华商场。那个人,应该是她的天堂。
我目睹小春在寻找爱情的途中,只有风雨,不见彩虹。红颜渐老,但她却依旧脚步铿锵。
我不能告诉她,那些想象不过是婚姻之前的假象,是恋爱的台词,不是婚姻的实质。我也不能告诉她,不是所有的爱情都会开硕大的玫瑰,还有可能长成狗尾巴花。与其将来在婚姻里哭泣,不如现在一个人独自美丽。用一句市井的话说,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容易遭致人身攻击。我也不能提那些有关城里城外的话题,都老掉牙了。我只能眼看着朋友去撞南墙,但是,我最怕的是,她就算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控诉的环节已过。
小春说,我刚才只喝茶了,没吃东西,给我做点吃的吧。挑省事儿的。
我转了一圈,说,热汤面怎么样。
行。哦,别忘了卧个鸡蛋啊!
感谢上帝,她还身在红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