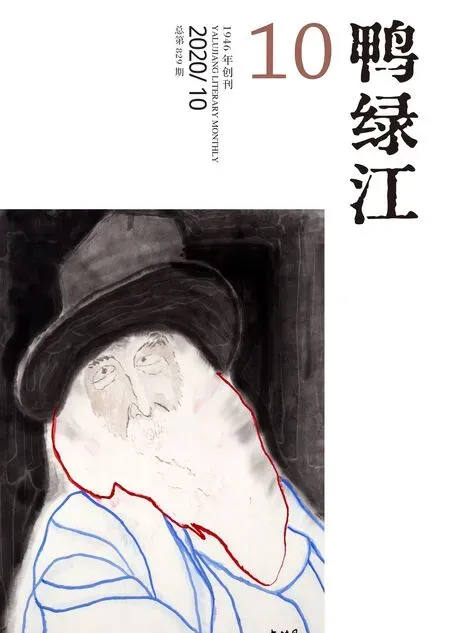画廊
王梅芳
老话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话对星红轩画廊老板胡砚泉来说,一年之间就完成了河东河西之间的转变,他的经营状态由日进斗金到日不见分文。
拐点
时光快闪回2019 年。
进入12 月份了,2019 年就要过去了,这一年的冬季好像特别寒冷。当然这种寒冷不仅是室外的气温,还有星红轩画廊,已经连续一周,没有客人进来了。何止一周,已经一年多,基本没有什么人来了。偶尔进来个人,问问画的价位就走了。
轩主胡砚泉抱着手机胡乱看,在朋友圈里发降价处理画和书法的信息和图片,发完等着反馈,没有信息的时候他在朋友圈里挨个儿点赞。微信时代,点赞就相当于四十年前拎一包蛋糕走亲朋,是情感的润滑剂,点了可能不顶蛋糕,但不点赞早晚会被朋友拉黑。
最近一两年,他有时间了,每天都看手机五六个小时,可是,在离开手机屏幕的那一刻,就彻底地忘记了自己都看了什么,不知道是自己年已半百,记忆力减退,还是网上的碎片都是过眼即忘,一股惆怅从心里涌出。
胡砚泉放下手机,摘下花镜,走到门口,向大街上望去,看手机的后遗症是眼睛雾蒙蒙的,这时,一辆宝马在他的门店前戛然而止,漂亮!胡砚泉的心情此刻像一轮初升的太阳,从宝马车停下的位置升腾起来。
胡砚泉太高兴了,这宝马车主王学林是胡砚泉的铁哥们儿,这么多年来,每年从胡砚泉手里买走的画都有几千万元,有时候是他自己买的,有时候也是给他朋友买的。总之,王学林是胡砚泉的大金主,只要来找他,就是一个事儿:买画,而且从来不讲价。但是今年一整年了,王学林却一张也没买,胡砚泉请他喝了好几回酒,洗了好几回桑拿,一起自驾去了内蒙大草原、大兴安岭的森林,明里暗里提醒他好几回,他也没买一张画。此时此刻,这哥们儿来了,让胡砚泉如何不在心中且歌且舞呢?
来了不一定买画,但是,不来,那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他赶紧迎出去,替王学林开了车门。
高大健壮的王学林并没马上跟他进屋,而是从后备厢里给他拎出一扇排骨,说:“今年猪肉贵,送谁猪肉就是跟谁铁,我从乡下给你整来的笨猪肉哈,这还有两瓶法国红酒,送给你欢度新年。”
胡砚泉赶紧顺杆就爬:“是啊,哥你跟我是真铁,你说这画也不走道儿,我哪儿舍得买猪肉啊!正馋着呢,哥就来了,你是及时雨哈哈。”
王学林笑着把这些东西递给胡砚泉,胡砚泉脚步轻盈地走在前面,王学林跟着他进了星红轩。
上了二楼,在茶台前落座,胡砚泉赶紧烧水泡茶,一边忙活一边打趣王学林:“这猪是乡下的小嫂子养的?你别说,你的眼光就是好,相比于大的,小嫂子的那股野劲儿还是别有魅力啊!”
王学林说:“没时间跟你扯淡哈,说正事儿,前年我不是从你手里买了三幅佟曾的六尺整纸吗,每幅一百万,这三幅三百万,对吧?”
胡砚泉说:“对啊,这十来年,你每年都买得比这多哈,不止这三幅啊,你承揽工程什么的,不全指望佟曾给你开路吗?说到底,这佟曾也是咱俩的福星,有他,你做工程发得噼里啪啦,我做画廊也奔了大康。咱俩是铁哥们儿,今天你要拿,算捡了大便宜啊,如今市场不好,佟曾的画,同样尺寸、同样质量的,五十万一幅,你拿走,我是赔本赚人气。”
王学林吸了一口烟,长长地吐出来:“腰斩了?”
胡砚泉说:“这家伙是咱们省的美协主席,才腰斩的,其他没有官职的画家,大部分都车裂了,稀碎。”
王学林把手里吸了半截的南京煊赫门细支狠狠地掐灭在烟灰缸里,说:“我认了。”
胡砚泉听了,心中一喜,说:“哥,我也认了,我这就给你取画去,给你看看,你一看就知道,自己今天占了多大便宜。相当于中一张彩票的大奖。”
王学林一把拽住他:“你坐下。今天我不买画了,今天我卖画。”
胡砚泉一听,心凉半截,疑惑不解地说:“哥,你做你的工程呗,卖什么画啊?你没看老弟我今年一年就赚了个‘球儿’,你还来捣什么乱啊。”
王学林说:“你赚了个‘球儿’,我赚了个‘毛儿’,彼此彼此哈。当初你卖给我这三张画的时候,你跟我说,‘你留着,将来指不定咋回事儿呢。’我当时的脑子里就往涨价上合计,就留着了,既没送礼,也没转手,没想到才三年过去,就腰斩了。都是你当年忽悠我的。今天,我把这三张画拿来了,我也是讲义气的人,不要求你按原价给我,现在按市场价,你得给我收回去,哥现在缺钱。我做工程都是我自己垫的钱,甲方得工程验收合格后再给我工程款,如今到年底了,我得给工人发工资啊。所以,腰斩了,我也认。这回,我按腰斩的价格给你,你也相当于彩票中了大奖。”说着,王学林从茶桌下面拎出了画筒,把画芯掏了出来。
胡砚泉一下子傻眼了,王学林什么时候把画拿来的,他都不知道,他只惦记着今天如何能从王学林的口袋里再掏点钱,而且,这几张画,当时为了卖高价,胡砚泉特意给配上了高级的金丝楠木画框,可谓好马配好鞍。配上高级画框的画,果然像化了妆、着了华服的姑娘,让人亮眼,也像过度包装的月饼,让人看着高端大气上档次,贵重。
当时王学林都没讲价,回头就让会计给他转了钱。王学林的工程非常广泛,建楼、修高速公路、建市政管网,自己还有建材公司,自己的建筑用自己的建材。他买画通常是给主管审批这些工程的人送礼,佟曾这大名头的画家,就充当了钱的功能。官员收画,也不是喜欢和热爱艺术,就是因为佟曾的画有市场价值,前脚收了,后脚就派个人送画廊来。胡砚泉曾经把佟曾的一幅画反复地卖出去十多回,赚了个满坑满谷。可是,今天,王老板却把画框卸掉了,直接拿画芯过来,他都懒得找个大车拉过来,可见他的急迫和坚定。
这让胡砚泉一时反应不过来,看来真是变天了。
暴富
那年月,胡砚泉觉得这世界上再也没有比卖画更赚钱的职业了。他觉得是自己幸运,命好,当初他爸爸爱画画,自己没画出什么名堂,给儿子取名“砚泉”,希望儿子在绘画上有点出息。可是,砚泉一点也不爱画画,甚至不爱学习,所以,考美术学院学画的道路就不通了,高中读了职高,毕业就被安置在一家国有企业做木型——铸造的前一个工序,就是工厂里的木匠。上班十二年,单位黄了,给他发了十个月的失业金就不管了。他在社会上游荡,找不到正经工作。他爸爸是中学美术教师,社会资源异常稀薄,画画的名气是没有的。想当名家的行动是有的,年年在家画大画参加画展,他把齐白石的虾临摹到一张两米多的大纸上,对砚泉妈说:“这么大的虾,连齐白石都没画过,到了展厅,绝对震撼,绝对颠覆,绝对抢眼,今年获奖没跑儿!”结果一公布,却没有颠覆评委,没评上。来年又画了徐渭的葡萄,画成那么大尺幅,仍然落选。如此整了几年,他就认定入选需要认识评委。在等待认识评委的过程中,他仍然异常勤奋。其实胡砚泉也是看见老爸累得像狗一样也赚不到钱,画的画顶多换顿酒喝,换包茶叶,换条烟抽,胡砚泉才不想像老爹那么活,才不画画的。但是,他的命运也一辈子没与画分开,这份关联也是老爸带来的。
老爸经常派他到街角的裱画店给自己裱画,裱画店的店主是位姑娘,砚泉一看就喜欢上了,更乐意为老爸去裱画了。虽然去得勤,但那女孩忙得根本不抬眼看他,只是简单地问答,来送画的时候姑娘问:你裱轴还是裱框?要什么颜色、什么材质的画框?想什么时候要?取画的时候更是取出来画、收了钱、把画交给他就忙去了,把胡砚泉的心整得像一百只猫爪儿在挠他。
胡砚泉总说自己命好,他不是瞎说的,在他人生最重要的情感问题上,老天就来帮他了,并且一直帮他成了大富翁,所以,他总是感念老天的成全。
机会是这么来的,毫无征兆。那天,胡砚泉又想去看那姑娘,可是,他爸爸又不老裱画,怎么办?怎么办?正在裱画店门口徘徊,他一下看见裱画店在招裱画工人,要男性。
机会来了。
胡砚泉毫无悬念地被取用了,他为了获得姑娘的芳心,干活儿特别能吃苦,特别有耐心。他在工厂做过木模,钉个画框什么的,手到擒来。20 世纪60 年代初出生的人,是挨过饿、吃过苦的,多干点活儿又不能少块肉,那根本就不叫事儿。
来了画廊一年,他就以诚实、肯干、脾气好、手巧、会说话的光辉形象,娶了姑娘回家。夫妻二人继续干裱画店。要说他该发家,谁也挡不住。
这一天,佟曾也来裱画了,当然他经常来裱画,砚泉俩口子手工裱画的手艺在盛京城里首屈一指,所以,名头大的人来也不足为奇。他裱画,也跟别人一样,交钱取画。如果还按这个程序往下走,这个发财的机遇也不会停留在胡砚泉的身上。
缝合这个大机遇的人是砚泉爸爸老胡。
无巧不成书。
同一时刻,佟曾来了,老胡也来了,砚泉发财的机遇就来了。
佟曾当时也不是省美协主席,但是多次获得国家展览的大奖。老胡对佟曾佩服得五体投地,可是不管怎么努力,就是撵不上老佟,他早就惦记着跟老佟拉拉关系,打探一下参加全国美展能获奖的门路儿,毕竟老佟是获过两回国家大奖的人了,一定知道路数,也认识评委。老胡不希望获大奖,只要能入展三回,他就能加入中国美协,这是他的目标。老胡一看老佟来裱那么多画,就问他干吗,佟曾说要办个展,但是,经费也紧张。当时中国的艺术市场还没有形成,佟曾的画自然也没有市场,他最牛的画被国家最高收藏机构收藏,八平尺也只给他八百元一张的收藏费,这都把同行的眼珠子惊掉了。老胡说:“这样的话,这批活儿,我就让孩子们给你干了,过后,你给拿几张画来就行了。”
佟曾感激地握住老胡的手,连连说:“你真是我亲弟弟。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就说话。”
老胡说:“就是请你指点指点我的画。”
老佟说:“这是小菜一碟,你拿来吧。”
老胡连忙拿出来他这次要参展的作品,也是刚刚裱完,这回他画的仍然是齐派,齐白石的大鸡冠花,也是两米多的尺寸。
老佟看完,没吱声,问:“你这么画,是怎么想的?”
老胡说:“我这是超越齐白石啊,齐白石也没有画过这么大的画,所以,我认为这样能震撼评委。”
老佟说:“你是在尺寸上超越了齐白石,内容上没有超越。另一方面,最近几年的美展喜欢工笔,写意的画很难评上,我劝你这样的写意就别拿了,不好上。拿了也几乎白拿。”
老胡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不甘心地留老佟喝酒,想在喝酒的时候问问老佟认识评委的事儿,老佟说改天就走了。
佟曾虽然不帮他评画,但也是讲究人,来取画的时候,就给胡砚泉家带来六张斗方、一张四尺整张,一共七张画,若按当时国家收藏他画的价格算,三千两百元。胡家没亏。但是,画毕竟不是钱,在需要钱的时候,不能扯一块儿拿去买肉吧。小两口在老佟走了之后就埋怨老胡。
老胡说:“换他的画,咱亏不着,暂时出不去,我还能学习学习他在笔墨方面的功夫。学齐白石我上不去,我先学老佟。画我拿走。过后我把这笔钱给你俩。”
从此,老佟来裱画,就不再出钱了,拿画置换。砚泉也觉得就孝敬老爸了吧,毕竟自己的儿子还在老爸家里养着,白吃白喝白挑眼儿,媳妇也不好说什么。
换得多了,也裱好挂在店里,偶尔也有人买几张,裱画店也兼画廊。待到又过了八年,老佟当上了省美协主席,中国的艺术市场也形成了,这时候,胡家手里已经有了三十多幅老佟的画,都是通过裱画换来的。这一天,老佟又来裱画店了,砚泉迎上去说:“佟大爷又裱画来了。”
老佟说:“今儿个我不裱画。以前我撂你家的画还在吗?”
胡砚泉说:“在啊,胡大爷,我爸成天学习你的画呢。”
老佟说:“好事儿,斗方我按三千元一张收回来,这一来,裱画费翻得不止一倍。”
胡砚泉说:“这是好事儿,画在我爸爸手里,他在学校上课,打电话也不方便,你先回去,我爸爸回来,我跟我爸要来画,到你家换钱去。”那时候是千禧年了,但是也不是人人都有手机的,老胡就没有。
胡砚泉知道现在有画廊收老佟的画,精品的斗方给五千元一张,应酬的也给三千元一张,他家的都是精品,这佟主席往回收,必有大涨的势头,所以,他拿老爹打哈哈。晚上跟老爹说了。老胡说:“不能卖,这事儿像养孩子,养小孩花钱,养大了才能赚钱,现在卖画刚刚成风,买他画的人还会多,咱们等风大了再顺风出手。从此,凡是画家当官的,来裱自己的作品,不要钱,要作品;凡是美术学院的教授、国家画院的专业画家来裱自己的作品,不要钱,要作品。画家,书法家都按这个路子干。”
小胡遵守了这两个规矩,发了大财若干年后,回想老胡的这一决定,觉得不可思议。老胡在画画上那么笨,怎么勤奋也获不了奖,喜欢徐渭,喜欢齐白石,一辈子就跟在徐渭、齐白石的屁股后面画写意花鸟,怎么也没有自己的创造,后来又临摹一段佟曾,怎么临也找不到要领,就放弃了。他看见中国历届美展获奖的工笔画比例高,就改行画工笔花鸟,可是他怎么画怎么匠气,当然老百姓看不出来,都夸他画得真像,颜色真好看。他的工笔花鸟虽能换点小钱了,可是在抓住商机这件事儿上,老胡却无比精明。
可能这就是老天的平衡法则,好事儿不能全让一个平凡的人全占了。
又过了两年,老胡说:“时机成熟了,砚泉可以去租个房子干大点的画廊了,裱画店再雇个人跟你媳妇做。无论什么时候,裱画店必须留着,这是与画家、书法家对接的窗口,也是养家糊口的好营生。”
的确是这样。这些年,经济发展了,专业的画家、书法家各种展览层出不穷,只要展览,就裱画。另一方面,老年大学异军突起,遍地开花,那些退休后不差钱的人都进老年大学了,学画画,学书法,期末,老年大学也搞结业展览,展览,就得装裱作品,平时能画几笔的,也都把自己画的东西拿出来装裱。这就成全了胡砚泉家的裱画店,不断地扩大规模,招收员工,赚钱也不少。
小胡于是放心地听爹的话,准备外出开画廊。正到处踅摸房子开画廊呢,老天又来帮他了,他的一个高中同学李易在大酒店做经理,得知小胡租房子,就说到我这里来,房租优惠。
小胡说:“净扯,酒店是吃饭、住宿的地方,谁来买画?”
李易说:“这你就不知道了,我的酒店是五星级,全省乃至全国的会议都在这里开,来开会的非富即贵,不是你的商机吗?你到我这里,你卖画需要发票,我还能给你开发票,餐费、住宿费、会务费,都给你开,你交点税就好了。又没有人找你麻烦,多好。”
小胡回家跟老胡一商量,老胡对这个地点叫绝,说:“大隐隐于世。闷头发大财。”
于是小胡就在盛京大酒店租下了一处一百平的房子,原来的底子是个咖啡店,装修得挺好,小胡不准备在装修上投入,吧台正好当收银台,就准备开业了。
小胡的画廊起名字的时候,小胡想,自己的名字叫砚泉,那得跟墨汁有点关联,有一款墨汁叫红星,那就叫红星轩。
老胡说:“立意不错,就是咬嘴,不如倒过来,叫星红轩,咱也图个买卖红火。”
这名起着了,小胡的星红轩还没正式开业,正在屋里挂画,就有人来溜达。小胡也没理他们,继续指挥工人挂画,其中一个人问了一幅佟曾画的价格,小胡看着这俩人不像买画的,心里嗔他进来捣乱,就张口把市场上价值三万的这幅画说成五万,只想打发他们走了,自己好整整屋里的东西,准备明天开业。
那人不但没恼,反倒说:“这画不错!”
说完俩人就走了。小胡心说,果然是棒槌,不买瞎问。
傍晚的时候,其中的一个人又来了,还问那幅画的价格,胡砚泉就咬死五万元,因为他怎么看那人都不像买画的。那人说:“你这人真黑,这人的画,一个斗方外面就卖三万,你卖五万。”
胡砚泉:“什么黑的白的,我就这价。”
那人说:“包上吧。”
胡砚泉愣了,这就卖出去了?但见那人砸出五万元的时候,心像一根点了火的钻天猴,噌地一下上天了。
但是他还是绷着脸说:“我这里保真,如假包换。嫌贵你就到外面去买。”说这话的时候,心还在突突地跳着,生怕他反悔。
那时他还没有卖画的预期,心里还有白交三个月房租的准备,画廊里也没有什么包装的东西,只好到酒店前台整几张报纸,用胶带给粘上了。他想:这是条大鱼啊!既然是大鱼,已经上钩,就不能让他跑了。
这是生活在底层的胡砚泉在生活里强化出的生存本领,遇到一点小机会都像水蛭一样叮上去,直到把自己吸得肚圆。
于是他笑着说:“哥,给弟弟留张哥的名片呗,我有好画好通知你。”
那人说:“我没有名片,你也不用通知我。赶紧地给我开发票,我着急走。”
显然,那人并不想成为他的哥。
胡砚泉自己内心有多狂喜,那个人内心就有多崩溃。
小胡看出来了,马上拎出一幅老胡的工笔荷花画,八平尺,比佟曾的画大一倍,他也延续老爹的创作思想,在规模上超越。拽那人胳膊:“哥,别着急,你买一小的,我送一大的,友谊长在。”
那人这才笑了,说:“我看这幅比那幅还好看呢!那幅怎么那么贵?黑乎乎的,墨用得太多,我就看不出有什么好来。”
小胡说:“那人卖的名,这幅绝对不比那幅画差,这是画家胡春贵的作品,现在名气差点,将来也会值大钱,你也是赚了。”
那人说:“哦,那是不是得等这个胡春贵死了,画就更值钱了?”
小胡一听这话硌耳朵,但是看在他是个冤大头的份儿上,就不跟他较真了,毕竟现在小胡觉得钱比爹被咒更实在,说:“画家还年轻,不用那么久,过几年就值钱了。”那人高兴地掏出名片送给了胡砚泉说:“我这一摸,还真剩了一张,弟弟是讲究人。”
胡砚泉一看:大林建筑工程队队长:王学林。胡砚泉心说:没想到一个小包工头儿居然出手这么大方。这跟他在裱画店所见的人是不一样的,他现在顾不上琢磨他,把名片往抽屉里一放,赶紧找李易给开发票,只是发票并不写单位的名头,只写金额。
李易领他到前台开了发票,交给王学林。待他走了,听胡砚泉说完这件事儿说:“夸你画好的人是领导,掏钱的人是求领导办事儿的人,领导钦点了这张画,他不敢不买,多贵他都得认。这是开会之后溜达的结果。所以,我这里好吧?多亏我吧?明天我赶紧给你找银行的人来给你安装pos 机,以后,卖画的数量多了,你给他们提供刷卡机也方便。免得他们到处找银行提款给你,你还得再存银行去,而且,你晚上也得开店,因为他们都散会了,晚饭吃完的时候溜达,才能来买。”
砚泉立刻数出来两千元塞到李易的口袋里,抱拳说:“李哥是我的贵人!多谢多谢!”
李易也不推辞,喜滋滋地走了。
直到李易走远,砚泉才从狂喜中醒过神来,赶紧打电话给媳妇分享自己巨大的喜悦。这张口就多出来的两万块钱,他得在裱画店裱多少张画才能赚出来?开门红啊,开门红,好兆头。
胡砚泉就这样开始了在画廊里“捡钱”的生涯。最狠的一次,一张画赚一百万,那是一个人送来地佟曾的丈二大山水画,画面上有水湿过的痕迹。胡砚泉在给佟曾裱画的过程中熟悉了佟曾的用笔风格,认得这是真的,早期的,艺术风格还没有成熟。胡砚泉正在心里盘算出多少钱收下合适,那人以为他不想要,之前他走过许多家画廊,都没有人敢要,说看不准是不是佟曾地真品。到这里,他绷不住了,说:“这绝对是真品,佟曾早年送给我爸爸的,就是楼上发水淹了这画,这样,痛快点,我也是白来的,十万给你。”
胡砚泉假装勉强地掩饰着内心的狂喜收下了这张画,回头与老婆重新装裱一下,洗去了被水淋过的痕迹,转年卖了一百二十万。
以后王学林也经常来,而且不讲价,胡砚泉要多少他给多少。
一次酒后,王学林告诉了胡砚泉他不讲价的秘密:“舍得,有舍才有得,就是因为他第一次从胡砚泉这里买了画,没讲价,送出去了,就击败了很多竞争对手,拿下了一个大工程,现在成为跨好几个行业的公司董事长。在外面做事儿的男人嘛,就不能小气。”
一年过去了,胡砚泉富了,买了本田大吉普,买了五套大房子,自己一套,儿子一套,给他爸爸整了一个大画室,给老丈人也整一套,三家人住在一个楼里,有事儿好照应。他爸爸安心在家画画,他在画廊给老胡卖,他爸爸的作品也由最初的给名画家作品添秤,变成了“著名”画家之一,这都是胡砚泉的主意。
胡砚泉在画廊认识的人多了,给他老爹买了几个头衔,跟《围城》里方鸿渐买的美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学位差不多。他给胡春贵改名胡春归,又买了一个联合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一个中国水墨画家协会副主席两个艺术家的头衔,中外占全。这两个协会都是子虚乌有的,胡春归开始不好意思用,但是,胡砚泉说:“俗话说,满城贴告示,还有不识字的,谁知道这俩协会是什么东西?你要坚信:你就是国际级别的艺术家。”
儿子一说,胡春归马上认可,原本他就对自己没有什么清醒的认知,画的虾个头儿比齐白石的虾大十几倍,就认为自己能颠覆齐白石。他甚至也认为齐白石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炒作嘛,是毛主席家乡人,就起来了嘛。所以,一直以来,他都认为自己是绘画的天才,只不过时运不济、怀才不遇而已,现在儿子这一整,他也觉得自己是国际级的艺术家了,走路的时候都摆脱了中学教师的走法,变成有财有富的步伐了。
为了实现老胡的国际化,胡砚泉留心来盛京大酒店住宿的外国人,只要来星红轩溜达的,他都送一把扇子,这扇子是胡春归画了画的,然后请他们与胡春归的作品合张影。不到一个月,胡砚泉就收集到了十几张与白人的、黑人的,还有日本人、韩国人的合影十多张,然后洗出大照片,说这些外国人收藏了胡春归的画作。
胡砚泉给他爹做了一个半小时的电视宣传片,把这些与外国人合影的照片悉数收录进去,再找当地的名人分别夸胡春归的画在学术上如何好。这宣传片在画廊的大电视里反复播放,画廊重点宣传他爹,因为他爹的产品一则是自家产的,没有太大的成本;二则父子同心,连盗墓贼的最佳搭档都是父子。不像那些画家,一旦画卖得快了,就涨价,小胡去买画还经常跟他们装孙子。为了全方位立体地宣传老胡,小胡还做了个大大的易拉宝,把胡春归留着长胡子的美颜头像印上去,艺术家的范儿十足,把那些吓人的头衔印上去,当然,盛京城里中学美术教师的头衔是坚决不提了,光看这些印在简介里的文字,除了照片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其他的信息读完都觉得老胡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来处。下面印的是胡春归在一些公共场合与明星、官员、大艺术家、外国人的合影,好像这些人都是他的亲兄弟一样。胡春归的工笔花鸟一幅画卖个三万两万的,也是常事儿了,而且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状。胡春归就雇了四个美院的大学生,到他的画室流水作业,他打印出来画稿,孩子们就把宣纸铺在透台上,照着画稿在上面勾线填色,胡春归就设计图样,题款盖章,忙得充实而富有。
小胡回味自己发财的现状,越发佩服他老爸的高瞻远瞩,用自己裱画的手艺换来这些画,随着艺术市场的洪流,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钞票。胡砚泉已成为画廊界一代富豪,成为嘉士德等世界级拍卖行的贵宾。老胡自己也在小胡的运作下成为富人,一年卖上个一百来万,轻飘飘的。
每当这时,胡春归越发觉得自己是个世界级的大画家了,这么说也不是空穴来风,他是有依据的,他想:像凡·高,生前只卖出去一幅画,还是他弟弟买的;高更画的“大溪地”系列,别看现在贵得离谱,当时在巴黎展览的时候,遭到的也不是赞誉,甚至也一张画卖不出去;明朝的徐渭,死的时候甚至连埋自己的席子都没有。古今中外的穷画家不胜枚举。这么一想,胡春归更加得意,自己已超越古今中外的画家,自己百年之后,也可能像凡·高、高更、徐渭一样,价格贵得吓人,如今谁买了自己的画,谁划算。这么一想,越发觉得自己画的价格太低了。
老胡这想法跟小胡一说,小胡说:“这好办,我给你上拍卖会把价格做起来。”
第二天就拿了一张老胡的画送拍卖行去了,他找了六个朋友在拍卖会现场轮番叫价,一直把老胡的一张八平尺的画叫到了一百万的价格,为此,胡砚泉也拿出了十五万的佣金给拍卖行。之后这个胡春归的工笔画《清晨》拍出百万高价的消息,由拍卖行做成了文章链接,发在自家的公众号上。只要一百度,这件事儿就出来了,《胡春归的工笔画<清晨>拍出百万高价》。胡砚泉除了发动所有人在微信朋友圈里反复推送,还请了地方电视台、报纸、电台的记者,进行了全方位立体报道。这个消息用老胡自己的话来说,绝对颠覆、绝对超越。
但是,老胡的画价并没有因为这次运作而涨起来,贵了就没有人买了。倒是小胡的妈妈说话了:“别扛价,你爸的破画也不当饭吃,饭,人家吃完了再吃,你爸的画更不当钱花,钱花了再出来赚,谁买了第一张还回来买第二张,有人买,你就赶紧卖吧,还要啥自行车,忘了以前一百元一张都没有人要的时候啊,那时候给你一百元一张,你得乐屁颠儿的。”
这么一说,老胡不服气:“今非昔比,你的老爷们儿如今厉害了,不懂吗?老娘们儿别搭茬。”
干了这么多年画廊,胡砚泉看的画多了,自己也明白了,他太知道他爹画的画就是装饰画,属于工艺品类别。佟曾的山水画真是吸收了中国古代传统,又吸收了西方的意识理念,的确有自己的创造性、颠覆性,跟认不认识评委没有绝对的关系,有些时候,可能有点关系,但是,要是作品本身不行,认识评委也不行。老胡的画就是认识每个评委,也不能让每个人都给他投票。
胡砚泉就对他爹说:“我觉得妈的话有道理,该炒作炒作,该卖多钱还卖多钱。”
老胡不敢吱声,因为只有他儿子才能把他的画卖出去,他自己是卖不出去的。
当然,胡家也是没忘本的,胡家的幸福都是艺术品给的,于是,胡砚泉为报答艺术品的恩德,给自己的儿子请来美院的教授,亲自辅导他画画,想让儿子考入美术学院,学绘画专业。这也是为了胡家的画廊成为百年基业,甚至千年基业,但是,儿子对绘画不感兴趣,画得不勤奋,也就没考上美院,而是考了一个职业高中,功课不多,在网上玩起了抖音,说要当网红。
锦上添花
胡砚泉在盛京大酒店干了五年之后,大酒店提前一个月以合同期满不再出租为由,赶胡砚泉离开。酒店是从胡砚泉开发票的金额上看见画廊赚钱太快,准备用胡砚泉的地方自己干。
此时的胡砚泉早已不是当年的裱画匠,而是腰缠万贯的老板,外人都叫他胡总。其实酒店就是不撵他,他也早就想自己出去了,毕竟一年交给酒店六十万元的房租,他也是心疼的,而且自己要做百年老店,岂能总寄居在别人的屋檐下?
只不过胡砚泉觉得自己已经人模狗样了,自尊心爆棚,被人驱逐,心里相当不爽,觉得只能我淘汰你,你怎么能赶我走?
酒店宣布解除合同的第二天,胡总就用现金在酒店对面买了一处底商,上下三层,一共一千多平米,两千多万元。一个月后,装修也结束了,胡砚泉就乐呵呵地搬到自己的房子里,那一刻,他觉得星红轩三个字在盛京城里熠熠闪光,再也不用隐于大酒店里了。
也多亏了酒店这次不续约,胡砚泉看着自己的大房子,吃咸菜都香,他是不怕酒店再开一家画廊的,他通过五年的运转知道,那些固定客户,他走哪儿都会跟他去的。
胡砚泉把大房子的一层作为一个小型美术馆,大约能展六十幅画,他有针对性地选了三个画家签约,出低价买他们的作品,给他们出画册,办展览,找报纸、电视、网络的媒体宣传,同时在画廊卖他们的画。
这件事标志着胡砚泉已经从倒买倒卖的画贩子,蜕变成画家的经纪人,当然,包装自己老爸也算是经纪人的萌芽阶段。对外也不叫胡总了,叫策展人。胡砚泉觉得策展人这个称谓好极了,一般人不知道策展人是干什么的,自己觉得有文化,先锋。相比策展人,“胡总”这个称谓就太土了,满街都是这总那总的。
这回他在大楼上安装了LED 电子屏,反复播放那三个签约画家加上他爹,一共四个人的宣传片。
二楼悬挂画廊出售的作品。还备了一张大画案子,书画家来了,可以挥毫泼墨,开个小型笔会,没有问题。另外还间壁出了两个包间、一个小型厨房,朋友来了,十几二十个的,就不用到外面吃饭,请对面酒店的厨师来做,省钱又安全。茶台就安放在二楼,朋友来了喝茶、聊天,顺便选画。
三楼他给老婆的裱画店搬来了,在三楼裱画,这样,原来裱画店的房租每年十多万元也省了下来。现在画廊要装裱这些东西也方便,工人还可以重合使用,楼下挂画布展,就下来干活儿;楼下没活儿,就上楼装裱;朋友来多了,工人还可以外出买菜,回来在厨房做下手。胡砚泉觉得这是老天又一次帮他。不算房子本身的增值,画廊加裱画店的租金,一年合起来七十万省了,十多年这门市就回本了。
于是,这回乔迁开业,他是大宴宾朋,鞭炮齐鸣,微信朋友圈更是重要的事情发十遍。他的朋友多,那几天的微信朋友圈都被星红轩乔迁刷屏了。那些在他画廊里卖画的画家、书法家都来了,每人送他一件作品,祝贺他乔迁之喜。人多,胡砚泉把午宴安排在盛京大酒店,十二桌,人气爆棚,像娶媳妇一样,胡砚泉越瞅越高兴。
虽然盛京大酒店驱赶他,然后又在他原地开一家画廊,令他不爽,但是,毕竟盛京大酒店是他的发迹地,是带给他人生巨大财富的地方,他还是恨不起来的。
新址开业后,并没有影响胡砚泉卖画,因为房子大了,又临街,更奢华的是门口有十几个停车位,免费的,许多人顺脚就来了,一度比在酒店里更加热闹。
胡砚泉以为这样的日子会延续到老,再延续给他的子女,没想到,三年以后,官方出台了“八项规定”,买画的人就日渐稀少了。他以为这规定会是一阵风,刮一阵子就过去了。但是,过了三阵子,这风也没有过去,仍然霜风凄紧。
逐渐地,胡家的星红轩门前冷落马鞍稀。胡砚泉闹心的时候,就四处打电话让老主顾来喝茶,来喝酒。这些人来了,喝茶的喝茶,喝酒的喝酒,喝完都走了,画也买得少了。
老胡的画价已经从一幅三万降到一幅三千了,也走不动道。老胡还是相信自己的实力,仍然雇用那四个大学生,加班加点地生产胡派画作,以期待市场回暖的时候,以原来的价格抢购一空,也希望自己多给这个世界留下一笔文化遗产。
老胡坚信:机遇是留给有准备之人的,所以,自己得时刻准备着。
花谢
到了2019 年,星红轩再也不红了。
有一天,胡砚泉的画廊一天一个人也没来,他想起了门可罗雀这个词儿,继而又想到,自己的门也不可锣雀,因为门前的大街上,汽车的洪流只多不少,容不得麻雀上当。
今天,听完王学林的来意,胡砚泉后背的冷汗唰唰地流,此时此刻,他才明白过来,日本电影《罗生门》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刚才王学林所说的“我认”是什么意思,而在卖画心切的胡砚泉心里,错误地理解为王学林认可了画的价格。实际这张画是他三十万收来的,本想在这“我认”的喜悦里,每张画收获这二十万,没想到,反过来,王学林要五十万一张卖给他,这三张画里外里坐地就赔六十万,事已至此,还不能说实话,这如何不叫他冒汗?
很多时候,即使是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同一方向,不同的眼睛看出去,同一句话,不同的耳朵听进来,就可能是天壤之别!年岁越大,这样的体会就越多。
他当年的确是这个价钱卖给王学林的,在这三张画上,胡砚泉赚了也不止六十万,可是,要把到手的钱,不,已经转化成自己血肉、神经的那份钱,再撕扯下去,胡砚泉感觉撕心裂肺。
胡砚泉心乱如麻,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这么多年来,他没少从王学林手里赚钱,他心里也想保留这个客户,万一以后市场复兴了,他还是那个一掷千金的大客户,而且如果今天不答应,他也怕王学林到处说他坏话。世界好像很大,可是,画廊的圈子就这么大,放个屁都能臭到整个圈子里。这王学林也不是好惹的主儿,可答应他,就得吃这个哑巴亏,掏出六十万来,相当于打了水漂,王学林不但不能领情,还会理所当然,因为王学林自己也亏了一百五十万,要细算三百万这三年的利息收益,亏的还不止这个数。
此时,这笔买卖不是双赢,而是双输。所以,他既不能一口回绝,也不能一口答应。
这时候,老胡来电话了,小胡心中一喜,老爸是他的福神,最少也能因为这个电话给自己一点时间和空间,想着怎么答复王学林。
小胡接了电话:“爸,你有事儿啊?”
老胡说:“这样啊,今年学校给我们退休人员订阅的报刊放开了,他们不再统一给我们订了,让我们自己订,然后,让我们拿发票给我们报销,我和你妈一个人一百九十八元。我俩都不爱看报纸了,我画画没时间看,你妈看手机,你看看能不能找人给我们俩开了发票来,报纸就不订了。”
胡砚泉一听,被王学林整乱了的心更乱了,有点不耐烦地说:“不要了,多点钱啊,我哪有时间给你整那玩意儿。”
王学林在旁边听到了,说:“这太容易了,我给你办。我朋友的孩子在邮局上班,前几天还找我,要我帮忙卖纪念币,你买两套纪念币,他就给开了报刊订阅的发票,纪念币还是钱,愿意留就留,不愿意留,过几天还可以再卖出去,里外里还是你合适。”
说完就给邮局的朋友打电话,又用微信把老胡夫妻的名字发过去了。半小时后,那孩子就给送来了,胡砚泉也只好把纪念币的钱微信转给了那小孩。
胡砚泉也看出来了,今天他要是不给王学林转钱,晚上他还得请人家喝酒,问题是,他现在哪有喝酒的心情?借酒消愁,可是他的愁就是从王学林身上来的,怎么可能再跟王学林俩人消?
想到这里,胡砚泉仍然不甘心,说:“哥,你把这画还像以前一样送出去换大工程呗。”
王学林说:“今非昔比,给谁谁也不敢要,所以,我也陷入困境,有俩钱都填工程里了,不到万不得一,我怎么会来卖画?”
胡砚泉一看实在没有逆转的可能,就招呼王学林到楼下银行给王学林转账去。银行的柜员一看转款单子上转一百五十万,就把大堂经理叫来了。经理跟胡砚泉很熟,说:“胡总,干吗转这么多钱啊,不是被骗了?给谁啊?”
胡砚泉说:“给我哥们儿,这不在这里吗,骗什么,净说笑话。”
经理说:“胡哥,到年底了,我也有揽储的任务,你这大笔转出去,还能转回来不?”
胡砚泉说:“短时期内回不来啦。办吧。”
于是转了,三人都是一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模样。
王学林也没上楼,开车走了。
胡砚泉上了三楼,跟媳妇细说了王学林来了这戏剧的一幕。媳妇说:“你做得对,王学林跟你也不是一年两年了,这么多年过来了,你吃亏这一回,说不定他还能给你带来别的效益呢,这快过春节了,还会有很多人来买画送礼呢!”
胡砚泉听了媳妇的话,也平息了内心的躁动,跟媳妇去厨房炖了排骨。
笨猪肉果然很香。
两口子在期待庚子春节的心情中也香香地睡去。
庚子春节很快在胡砚泉夫妇的期盼中来了。但是,夫妻俩期盼来的不是买画的客户,而是新冠肺炎,武汉封城,盛京自然也严禁市民走动,连拜年都改为网络和电话拜年了,全市的企事业单位实行弹性办公,街上真的可以罗雀了。
胡砚泉夫妇这二十年来,第一次这么清闲,工人没来上班,店里没有裱画的,没有买画的,也没有来喝茶喝酒的,更没有闲逛扯闲篇的。
只有胡砚泉的儿子不消停,成天在家关着门用手机录段子,像脱口秀,气得两口子饭都懒得做,但是儿子自己可以叫外卖。
胡砚泉夫妇在画廊待着,没事儿干,只能成天玩手机。
于是,一家人比任何人都盼望疫情赶紧过去,一切好恢复正常。
胡砚泉在微信朋友圈上降价拍卖手里的存画,无人问津。一年前,他还觉得干画廊比干企业都好,一转眼,过了一个冬天,一切都变了。所以,当儿子得知老爹的画廊生意萧条的时候说:“爸,不要紧,风水轮流转,我给你在线上开个店铺,卖画。我给你打造成线上品牌,将来让全国人民知道你。我们的口号是:买电器,到京东,买书画,到星红轩。”
胡砚泉两口子听了儿子话,觉得儿子不靠谱,并不往心里去。顺嘴骂了几句:“你都快三十了,不搞对象,不上班,你能不能干点正事儿?还线上卖画,八成是陷阱吧。”
儿子嬉皮笑脸地说:“老爸,不要以为你干的都是正经事儿,我看你就是运气好,稀里糊涂地赚了钱。你要是真有本事,你还是你,而且经验更加丰富,现在怎么不灵了?这年代,你拒绝互联网,你就要被世界淘汰,什么时候想通了,什么时候来找我。”
说完关上房门对着手机喊:“姐妹们,喜欢的话,call 六个六啊!Call 起来——”
这话听得胡砚泉心都要碎了,对于大人来说,孩子只有按照父母的愿望成长,大人才能够安心。
他听不懂儿子在喊什么,更要命的是儿子的话打击了他,他多年来被金钱构筑起来的骄傲被儿子打碎了。可是,儿子说得也对,自己几十年经营画廊的经验毫无用处,他无法以自己的方式去延续画廊的辉煌,一股巨大的空虚包围了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