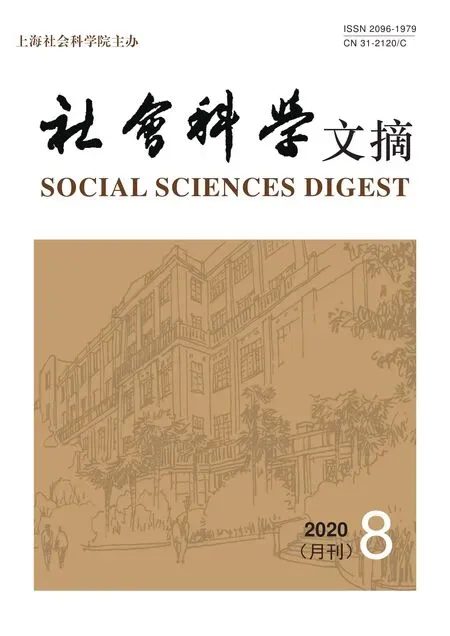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元影响因素析论
文/于春洋 陈奥博
保有和增进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是当代多民族国家面临的普遍问题。相对于多民族国家的主体民族而言,少数民族在历史记忆、文化传统、利益诉求、信仰关怀等诸多方面更容易表现出与多民族国家的“国家特性”异质性的特点。这些异质性特点有助于少数民族关注自己的民族身份并由此维持较高水平的民族认同,但也容易成为保有和增进少数民族国家认同的阻力,而且也不排除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和特定群体中出现民族认同消解国家认同的压力。本文尝试就当代世界影响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多元因素进行分析,为保有和增进基于公民身份的少数民族国家认同提供参考和借鉴。
全球化影响公民身份认同的三个维度
全球化的影响全面而深刻。事实上,本文所分析的诸多影响因素都与全球化密不可分——它们或是在全球化的场域中出现的,或因全球化的赋能而得以实现,或者直接就是作为全球化的具体实现途径而存在。综而观之,全球化对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影响表现在三个维度。
第一,全球化导致良莠不齐的信息跨越地理空间和政治边界不断流动扩展,影响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互联网在提供即时性、交互性、共享性信息的同时,也让信息维护监管难度指数级增加,给国内分裂势力与国外敌对势力提供了制作传播诋毁国家正面形象、破坏民族团结虚假信息的舞台,导致少数民族难辨信息真伪、易受蛊惑利用,增加与国家的隔阂,削弱公民身份认同。
第二,全球化的“马太效应”放大不同群体/区域贫富分化的落差,而当这种落差与不同民族群体/民族地区重叠时,会影响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居住区域整体经济发展水平相对主体民族聚居区域为低。而全球化增加了利益分配的标准差,主体民族聚居区域较之于少数民族居住区域往往能获得更多的资金、人才、技术、机会等社会资源,从而让少数民族“相对剥夺感”增加,甚至出现“绝对剥夺”事实。这种态势会让少数民族对于本国政府的满意度下降、信任度衰减,危及公民身份认同。
第三,全球化让传统社会个体成员相对简单的一元身份变得日益复杂多样,少数民族个体身份的多元化发展也带来了身份认同的多元取向。社会实体组织身份认同、网络虚拟社群身份认同、家族身份认同、民族身份认同、公民身份认同、宗教身份认同等等,当多元身份认同集中存在于少数民族个体成员身上时,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势必遭遇多元身份认同取向的稀释。
作为“逆全球化”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
在“逆全球化”的诸多表现中,尤以“族性张扬”为特征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对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影响最为明显。
一方面,族性的“内聚”特点使得少数民族个体成员内部的民族身份认同得以加强,国家公民的身份属性则被有意无意地忽略甚至回避。通常意义上,人们是以国家公民这一社会个体政治身份来维护自身利益的,而经由族性动员的少数民族在参与政治的时候,往往会以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为基础,所要实现的更多也是群体利益而非个体利益。此外,也不排除在发生敏感事件、有人或组织蓄意煽动破坏等极端情况下,族裔民族主义甚至可以引领少数民族走向对于获得民族独立、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追求。
另一方面,族性的“外斥”特点也使得少数民族个体对于“外部化”的公民身份产生疏离,进而影响对于多民族国家的认同。全球化深入发展的后果之一是导致主权国家的权力遭遇挑战,这一挑战使得作为一种“外部化”的公民身份背后的国家影响力也在弱化。与此同时,族性“外斥”的特点在国家间关系与区域合作领域也有明显表现,这种局面更是增加了“去中心化”的复杂度和影响面,强化和助长了族裔民族主义意识,少数民族的公民身份认同进一步被疏离。
国家自主性的削弱
国家自主性的削弱及其对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分析。
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威胁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对于这类问题的解决需要各国通力合作。2019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在世界范围快速蔓延所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就是一个典型且紧迫的全球性问题。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世界各国在医疗、数据、技术、航空等方面的共享、互信与合作。不论是否情愿,国家都需要通过让渡权力的方式来赢得国际合作的机会。国家自主性的削弱是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而必须付出的代价,这一代价背后也隐含国家对国内少数民族影响力的衰减。
另一方面,在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劳动力、商品、信息等资源的全球化流动,使得互赖型全球统一市场体系趋于成熟。这种态势势必会对多民族国家的国内资源分配以及宏观经济调控能力产生冲击和影响。由于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相对滞后、生态环境较为脆弱、市场发育程度不够充分,在互赖型全球统一市场网络之中,整体处于缺乏竞争优势的生态位。这种局面既会进一步扩大少数民族的“相对剥夺感”,也让多民族国家普遍缺乏提振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有效资源。
民族地方治理的兴起
对于大多数多民族国家而言,民族自治是处理国内民族关系的基本政治制度,也是实现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途径。同时,民族自治作为多民族国家政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是在国家政治结构内部运行的一种次级政治形态。民族地方治理的兴起是多民族国家的民族自治在全球化时代的重要表现。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多民族国家的政府治理模式发生深刻变革,民族自治走向民族治理进而导致民族地方治理的兴起,就是这场变革的典型反映。民族地方治理的兴起意味着更具回应能力的民族地方行政组织体系得到长足发展,也预示着因地制宜解决民族地方公共服务问题的可能性。然而也要看到,民族地方治理的兴起也给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带来隐性的负面影响。这是因为,民族地方治理的成效有利于少数民族建立对于国家的信任感,但也存在基于对自己民族身份的认同而将民族地方的治理成效仅仅归结于本地民族精英个体或群体,从而激发少数民族对于本民族精英个体或群体的信任乃至崇拜之情,公民身份认同有被削弱和淡化的可能;与此同时,民族地方治理的兴起亦会导致本地民族精英在为地方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同时,更倾向于以维护本地少数民族的利益作为各项治理工作的出发点,并且以维持民族地方社会的团结与稳定作为筹码来争取中央政府更多的政策与财政扶持。
凡此种种,传统意义上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赋权与被赋权、领导与被领导的科层关系转变为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平等博弈关系。这种转变使得多民族国家主体民族与少数民族之间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国族共同体意识遭遇挑战,少数民族的公民意识以及公民身份认同也可能在这种关系转换之中被慢慢消损。
地缘政治局势
对于多民族国家而言,有相当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区位于国家的边疆。根据地缘政治理论,边疆的人文地理因素与国家的政治行为以及边疆区域范围内的政治格局关系密切。地缘政治局势对于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影响包括两方面。其一,由于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多地处边疆,远离国家政治经济中心,国家的权力触角难以精确高效地抵达边疆,容易导致各项方针政策在边疆地区的实施过程中出现偏差,在国家的价值追求与具体的政策实施之间产生落差,使得少数民族对于国家政策产生误解甚至怨恨,影响少数民族对于所属国家的信任感,进而消解公民身份认同。其二,在边疆存在邻国的情况下,如果邻国是富裕发达国家,这些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物质生活水平本身就会对身居边疆的少数民族产生吸引力,加之发达国家出于维护自身安全、左右地缘政治走向的考虑,会选择经常性地与边疆少数民族保持多种连结,进而通过强化少数民族的民族身份认同、破坏民族团结关系甚至煽动民族冲突等方式,削弱边疆少数民族与其所属国家之间的认同关系;如果邻国是贫穷发展中国家,则可能出现偷渡、洗钱、贩毒、走私等容易危及边疆社会秩序稳定的状况,导致边疆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边疆治理能力产生怀疑,同样不利于公民身份认同的确立。
民族分裂势力
当今世界,民族分裂势力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之间有着密切关联,日益成为危及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目前,影响中国的民族分裂势力主要有新疆的“东突”势力、西藏的达赖集团以及海外的“台独”势力。新疆的“东突”势力坚持制造与散布“疆独”分裂舆论,不断挑拨和激化少数民族与汉族之间的民族对立情绪,怂恿少数民族的族裔民族主义意识;达赖集团不断把西藏问题推向国际舞台,使得西方敌对势力有机可乘,粗暴干涉中国内政,蓄意挑拨民族关系,甚至不惜利用宗教问题掀起有组织有预谋的暴力活动,制造社会动乱;以民进党为代表的“台独”势力有机会通过参与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的手段离间台湾与大陆之间的情感联系,破坏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妄图通过举行非法的公民投票方式达到“台湾独立”的目的。凡此种种,这些民族分裂势力的活动会削弱利益关切民族成员的公民身份认同。
跨界民族问题
跨界民族的存在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该民族主体成员的聚居区跨越两个或多个国家政治边界(狭义的跨界民族),另一种是该民族的主体成员跨越不同国家政治边界,同时该民族的聚居区也是分散的,并未在不同国家政治边界附近聚集(广义的跨界民族)。跨界民族是影响地缘政治走向、邻国外交关系、边疆治理成效的重要变量。同时,跨界民族问题也会对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产生重要影响——跨界民族的身份认同明显要比其他民族复杂。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成员具有双重身份,分别是文化-心理维度的民族身份和政治-法律维度的公民身份。前者是个性身份,后者是共性身份。而对于跨界民族而言,民族身份是所有跨界民族个体都具有的共性身份,公民身份则变成跨界民族个体的个性身份。并且,跨界民族与多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多重性和模糊性,使得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更为复杂与多元。由于跨界民族生活在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相邻国家,其公民身份认同既受到本国内部民族关系状况好坏、社会治理水平高低的影响,也深受邻国同族生存状态的影响;既接受本民族历史、文化与记忆的规制,又经受世界范围内的族裔民族主义浪潮的干扰。
社会结构转型
社会结构转型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进程,包括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乃至社会信仰价值观层面发生的一系列结构变迁。这种转型在中国发生在改革开放以后,尤其是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在印度尼西亚开启于1998年以来“后苏哈托时代”的民主化转型之时;在尼日利亚则出现在以1999年阿布巴卡尔军政府将国家政权移交给奥巴桑乔文官政府为标志的“还政于民”以来。
以中国为例,中国的社会结构转型是以经济转型带动社会转型的方式推进的。改革开放40多年来,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革,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改革开放的红利让当代中国的社会财富总量激增。2010年,中国的经济总量首次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国。然而我们也要看到,由于在改革开放之初到世纪之交,中国经济转型的重点是从逐步加大市场调节力度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则主要是推动东部地区优先发展的非均衡性发展战略,致使民族地区的市场经济发育较之于东部地区乃至全国平均水平为低,市场经济基础薄弱、市场主体成长缓慢,计划经济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体制惯性较为浓厚。新世纪以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兴边富民”行动、“对口支援”计划和扶持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等一系列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的战略/政策纷纷出台,民族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大规模兴起,经济结构得以优化,居民生活水平获得较大程度提升。但也出现了诸如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的利益分配问题、经济社会转型发展中的民生问题、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保护的矛盾冲突问题等等。
对于中国社会结构转型所带来的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长期处于劣势的问题,有学者用“发展进程中的社会排挤”来加以描述。面对这种梯次发展、非均衡发展所带来的社会排挤问题,生活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往往会在认知和行动层面通过“抱团取暖”的方式来对其进行“外部化”,在这一过程中,公民身份被淡化,民族身份被强化。
区域发展失衡
还是以中国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并且实现了与东部地区发展速度差距的相对缩小。然而,民族地区相对发展速度的提高并不能消除它与东部地区乃至全国绝对发展落差的扩大。区域发展失衡问题导致处于事实上的落后状态的少数民族内心深处长期存在一种“相对剥夺感”,这种被边缘化、受到剥夺的身份焦虑会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他们主观幸福感的匮乏和对国家及政府满意度的下降,也阻碍了他们对自身公民身份作出肯定性评价。
当代世界影响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的因素是多元的。既有外显因素也有内隐因素;既有国内因素也有国外因素;既有全球化深入发展所带来的普遍因素,也有特定时空背景和独特地缘政治所赋予的特殊因素;既有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也有社会信仰价值观等多方面因素;既有绝对发展落差导致的因素,也有相对剥夺感派生的因素。唯一可以确认的是,所有这些因素都无法忽视,任何或大或小、或外显或内隐、或普遍或特殊的因素一旦处理不好,就容易带给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以负面影响,进而危及到少数民族对于国家的认同。必须承认,当代世界政治结构体系及其运行规则与隐含在其中的社会个体/群体身份认同网络已然形成一个高度复杂的生态系统,那种试图通过局部突围的方式一劳永逸解决少数民族公民身份认同问题的努力只能是徒劳的。不断透过现象探求影响因素背后的底层逻辑,在动态的、不确定的和充满未知的真实场景中不断调整和应对来自不同维度和层面的挑战,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才有可能让公民身份成为少数民族身份认同谱系中的主导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