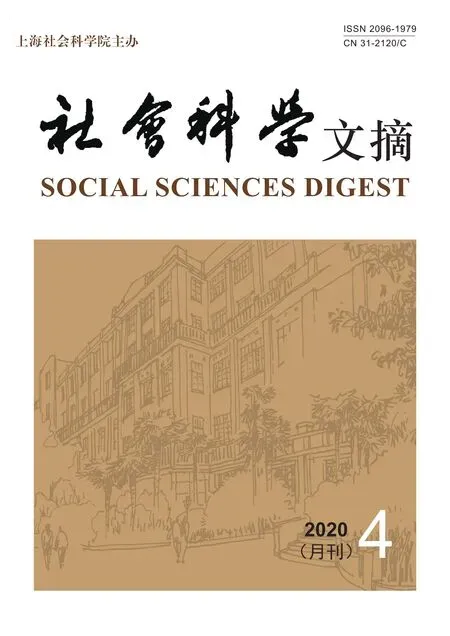“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文/张城
数千年来,中华民族走着一条不同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明发展道路。我们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非偶然,是由我国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
引言:一脉相承的经史问题意识
清代中叶,面对经学训诂学之兴起与挑战,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这是其历史哲学之核心。他从重建经史关系之视角,力求为“史”正名,同时给予“经”应有之地位。浙东后辈章太炎承继“六经皆史”说,师从章门高足黄侃的范文澜,对“六经皆史”亦有批判继承。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开展了影响深远的“整风运动”。其核心问题是处理共产党党内的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经”)与中国历史实践(“史”)之关系。
在毛泽东看来,共产党人无论对待马克思主义、历史文化传统,还是当前的革命实践,都须从理论上给出准确阐释,关键就在于史观之重建。如没有一套成熟系统的史观贯穿其中,历史即是一堆杂乱无章之史料。正因有范文澜这样既受过经史训练,有深厚经史功底,又经历革命实践,真诚服膺于唯物史观的历史学家之援助,毛泽东在处理党内经史关系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之“经”与中国革命实践之“史”的关系时便得心应手,为中国共产党人成功建构起了一套中国革命的历史合法性叙事,占领了意识形态与道义制高点,进而带领人民成功实现了百年来的革命建国夙愿。
“六经皆史”:章学诚的经史观
欲与“经学即理学”针锋相对,章学诚必须自立一套从本体到方法的更为彻底的经史理论,“六经皆史”说应运而生。
(一)章学诚的经史论
“六经皆史”乃章学诚经史观之本体论。若想理解其经史观,则须先释“经”“史”之义。何为经?“六经初不为尊称,义取经纶为世法耳,六艺皆周公之政典,故立为经。”尊经一方面是因有传而始有经,另一方面乃因诸子之兴而尊经。何谓史?章学诚所言史学,非四部之史部,亦非史料,而须具史德,乃“著书者之心术也”。
“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章学诚重史之地位毫无疑义,但说其抑经却非如此。他非疑经之人,对孔子赞赏有加,推崇备至。与其说尊史抑经,不如说是尊经之下,纳史入经,尊史为经。由此,章学诚其实经史并治,经史并重。
(二)章学诚的认识论
章学诚提出“六经皆史”,要义即指出何谓道,进而何以求道、明道。何谓道?“道之大原出于天”,道即社会发展之必然趋势,与圣人无关。他常叹世人“不知六经皆器”。道虽不可见,但“道器合一”。圣人“即器而明道”。故道于器中方能求之。
何为求道之方?“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六经只能明三代之道,而“事变之出于后者”则须随时撰述,不断揭示道之恢宏全体。因此,必须与时俱进,经世为本,以时为大,此即“六经皆史”论之精髓所在。
(三)章学诚的实践论
“学于众人,斯为圣人。非众可学也,求道必于一阴一阳之迹也。”此乃章学诚方法论之真谛,看似主张圣人史观,但章学诚遵循的是群众路线,坚守群众史观。章学诚的认识论亦即实践论如下:圣人必须学于众人,道之迹(众人之感性材料)——道之作(圣人经纶制作)——道之器(编辑为经典)——道之理(变为指导实践的思想),由实践之深入随时撰述以究大道。
在章学诚看来,既不能误器以为道,更不能离器而言道,离事而言理,舍今而言古。秉承浙东史学经世传统的章学诚“六经皆史”之经史观,核心即道器合一之本体论、即器明道之认识论、学于众人之方法论,宗旨为知行合一之实践论。
思想之榫卯:从章太炎到范文澜的经史观
(一)章太炎之经史观
被誉为“有学问的革命家”的章太炎,深受章学诚影响。对于二章之思想传承,思想界早有共识。但基于反清革命之需要,章太炎已对“六经皆史”作出新诠释。
首先,章太炎承继了“古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之经史观。章太炎明确指出,六经虽不能言事变之出于后者,虽非道之恢宏全体,但有精义在,忽略粗迹,发挥精义,随时推阐,必能有功于当代。
其次,章太炎对经之范围的界定,超出章学诚之定义。在章太炎看来,不能以官书为标准,认为“经之所该至广”。他纳史入经,经史不分,看似将经之外延扩大,实质却已触及经史关系之根本,经史著述由官学渐变为私学,为私学之繁荣奠定了正当性之基础。
再次,章太炎指出,六经非为万世立法,力图还原经学之历史本色。章太炎力图突破经学之神圣性,既不像今文经学家神乎其神地尊经,亦不能如疑古派怀疑经之价值,其意图在于还原经学本色,给予经以史之恰当地位。
最后,对于“六经皆史”内含之知行观,章太炎承继其精神实质。章太炎强调随时变化,注重从实干中积累经验,以“六经皆史”为基,重建经史关系之方法论,反对教条,注重经典中所内蕴之民族意识与家国情怀。
(二)范文澜之经史观
范文澜与二章同为浙东人,对二章“六经皆史”论演变脉络了然于心。到达延安后,范文澜备受礼遇,毛泽东亲笔去信鼓励其用马克思主义史观清算经学。
首先,范文澜继承“六经皆史”之基本内涵,强调六经皆古史。“五四”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思潮影响颇大。范文澜也受到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影响,曾明确提出“经本身是古代史料”。将经视为史料,可用唯物史观作为方法进行甄别,创造性转化,即能从经学所保存的丰富史料中汲取营养,丰富共产党人所需之精神信仰。
其次,范文澜让“经”获得了新生——“变经学为史学”。贬经为史料,经之神圣性瓦解,经学之价值崩塌。“五四”后之新时代,经学发展“新的康庄大道”即是“变经学为史学”。由此,经学虽走下神圣宝座,范文澜却纳经入史,使经学在历史实践中走向新生。
再次,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经学之态度。第一,范文澜运用唯物史观系统研究经学。第二,范文澜对清末民初的经学家进行了严肃批评。第三,范文澜认为,共产党人须用历史唯物主义对待经学。面对近代中国深重之民族危机,范文澜虽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但因深受浙东史学传统影响,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年代,他把马克思主义与传统经史论融会贯通,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理论进程,最终把它落实于抗战建国的革命实践之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的“经史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彻底实现,既需要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理论素养,又需要中国传统经史之深厚功底,以及对国情之切实把握,而这三者在毛泽东身上无疑是兼备的。
(一)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的“经学观”
首先,毛泽东尊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他在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信仰后,终生不渝。其次,毛泽东并未把马克思捧上神坛,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他始终把马克思当成历史人物看待,不是造神似地把马克思神化,而是实事求是地评价其历史地位。再次,毛泽东认为不可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具体字句结论,而要知晓贯彻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学懂弄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不能公式化地背诵词句,要从立场与方法着眼,马克思主义之精髓即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最后,毛泽东指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并未结束真理,而是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是行动的指南。“马克思主义是空前而不绝后。”社会实践过程无穷决定认识过程也无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任何伟人都身处特定时代,都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只能是认识绝对真理过程中的一部分、一环节。经史并重,强调实践才能不断出真知,这即是毛泽东之真理观。
(二)以中国问题为中心——毛泽东的“史学观”
首先,中国问题意识是毛泽东唯物史观的中心。毛泽东异常清醒,请马克思主义到中国来就是要解决中国问题。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之于中国问题就是一种工具。“要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其次,毛泽东善于从实践中总结新理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创造了一系列(包括农村包围城市、武装斗争、统一战线等在内)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总纲的中国理论。毛泽东对此十分自觉,认为必须从中国实践中产生出中国理论,再以此进一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再次,毛泽东把中华文明作为方法,纳入社会主义之内容。毛泽东深受列宁、斯大林关于民族解放斗争理论的影响,突出表现在新民主主义理论中。但他对内容+形式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始终不满,力图有所突破。在毛泽东的思想理论库中,两个“老祖宗”都是共产党人思想体系的重要来源,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当然是马克思主义,但中华历史文化与中国社会实践本身即具有一种方法论意义,能够以此丰富和发展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三)向群众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
首先,毛泽东注重实践与调查研究。毛泽东通过系列调查研究,逐步形成了一套解决中国革命的方针策略。学习不只是读书,实践是更重要的学习。“从战争学习战争——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其次,毛泽东指出,人民是历史创造者,要以小学生的态度向群众学习。毛泽东一生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主人,必须先当学生,再当先生。毛泽东曾这样与全党同志共勉:“和全党同志共同一起向群众学习,继续当一个小学生,这就是我的志愿。”作为人民领袖的毛泽东,始终把老百姓当成力量之源,甘拜百姓为师,甘作百姓的“小学生”。再次,毛泽东与时俱进,以国情为一切革命问题之根据。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路线,亦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在毛泽东看来,不论是认识中国之前提,还是改造中国之目的,其主体自然都是中国,必须立足于国情。
尊经重史:经史观之方法论启示
诞生于中国历史文化土壤中的中国共产党当然不能照搬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文化进行艰难的思想性创造,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必须按照中国特点去应用它。“六经皆史”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二者同样面临处置自身经史的关系问题,其内在的经史思维逻辑具有某种程度的相似性,极具方法论启示。
(一)反对教条主义:尊经之地位,重史之作用
章学诚认为六经并非道之恢宏全体,体道、识道、弘道须以经世为本,以时势为大,纳史入经,尊史为经。章太炎亦指出:“古之作者,创制而已,后生依其式法条例则是,畔其式法条例则非。”范文澜将其与学习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相结合,达到了炉火纯青之境界。
毛泽东深知要使马克思主义得以彻底中国化,必须既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把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提炼出来指导革命,不至于犯教条主义之错误;又能根据中国革命实践之史,不断总结提炼新规律,纳史入经,使得中国革命在经史关系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不断发展过程中,彻底解决中国革命问题。
(二)经世致用,注重实践
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宗旨即知行合一之实践论。章太炎曾言:“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可见,深受浙东史学经世传统影响之二章,皆颇重视实践之作用。
毛泽东特别看重把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与中国哲学知行合一观深度融会贯通而成的《实践论》。正是因为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与中国古典经世致用的经史传统融会贯通,内化为革命理论,并外化于革命实践,才从根本上解决了近代以来中国人的理论求索,在精神上从被动转为主动,在革命斗争实践中实现了建国夙愿。
(三)向群众学习,走群众路线
章学诚高度重视经典谱系之传承,明确指出“学于众人,斯为圣人”,否认圣人史观,走的就是群众路线。此思想谱系亦为章太炎、范文澜一以贯之。章太炎倾向大众之道德价值观,对知识人道德品格甚不满。范文澜继承发展了人民史观,他之所以得到毛泽东赏识,与在其著作中贯穿群众路线的人民史观甚相关。
毛泽东始终坚持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立志还原历史舞台上的真正主人。其方法就是马克思主义史观与“学于众人”文明传统相结合,此即共产党人的群众路线。知识分子要想真正向群众学习,必须走群众路线。如未具备群众感情、工农立场,便学不好也掌握不了真正的马列主义。这鲜明体现了毛泽东的人民史观与群众立场。
(四)以时为大,与时俱进的真理观
章学诚认为不能抱守残缺、舍今求古,须以时为大,经世为本,这即“六经皆史”之要义。章太炎把六经视为可征信的古史材料,而非为万世立法之经,消解其神圣性。在范文澜看来,“经”不能当成神圣教条,经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五四”后之新时代,经学发展“新的康庄大道”即是“变经学为史学”。
毛泽东虽然强调要尊重历史,但不是颂古非今,而是用唯物史观给予历史以科学解释。社会实践过程无穷,决定了认识过程之无穷,包括马克思在内的任何伟人都身处特定时代中,不可能掌握绝对真理,只能是认识绝对真理过程中的一部分、一环节。毛泽东深知追求真理的过程无穷无尽,共产党人如不能坚持与时俱进的真理观,那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
余论:道事之间——经史关系中的历史与信仰
无论是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经史问题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都要面对自身经史关系中的事与道即历史与信仰。章学诚的“六经皆史”,六经来自于有制度实践支撑之古史;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亦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立基于丰富的中国革命实践之中。二者的确都是经史一体,以事载道,以史释经,历史与信仰就在实践发展之中成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
毛泽东一生最为重视的就是史观问题,问题意识即马克思主义必须与中国历史文化、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实现本土化。马克思主义作为“经”,已经过中国革命实践之史的检验,通过历史沉淀,信仰已变得清晰。有了真实历史支撑的信仰就不再空洞,丰富的历史过程本身,经过“随时撰述”,其自身就已凝练成为新的信仰;有了坚定信仰指引的历史就不再迷失方向,科学的信仰本身就是一种历史进程的客观反映。“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由此,在丰富的实践发展过程中,历史被提升为一种历史哲学,事即道,史即经,历史化为了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