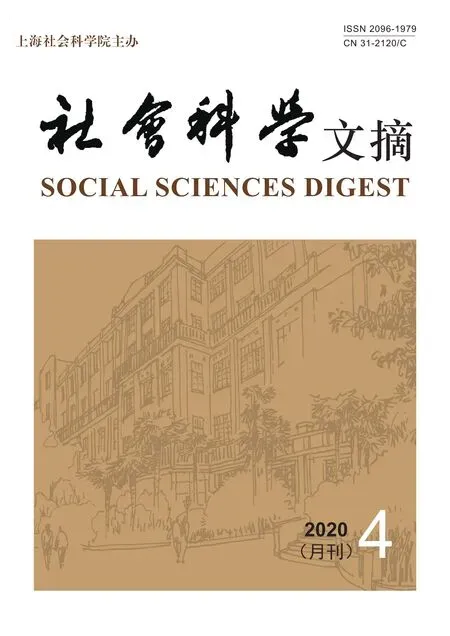立法扩张与司法限缩:刑法谦抑性的展开
文/田宏杰
刑事立法的犯罪化扩张与刑法的谦抑性之间究竟什么关系?践行刑法的谦抑性,是否必须收缩刑法规制的疆域而以非犯罪化为努力方向?刑法现代化的推进与现代刑法的建构,应与传统刑法观逐渐决裂还是坚守不变?笔者拟以我国法律体系为主要研究语境,通过对上述问题的研究,提出对于现代刑法的谦抑性内涵及其实现路径的思考。
内涵与厘定:象征性刑法论对谦抑性的现实误判
象征性刑法是指立法者为回应公众舆论对于犯罪治理的呼吁和压力,将不应当且实际上也难以有效进行刑事规制的行为,以象征性或者宣示性的姿态予以刑事规制而制定的刑法。中国晚近20年的刑法修正之路,具有明显的象征性立法趋势,尤其恐怖犯罪、网络犯罪和环境犯罪的个罪修改和增设,不仅恐怖犯罪和网络犯罪的罪名适用率极低,而且严重的环境污染并未减少,立法实效乏力,因而是象征性立法的体现。但是,立法对民众期待的回应就意味着立法的象征性姿态吗?判决中的罪名适用率低就表明立法效果欠佳吗?笔者以为,恐不能如此简单等同视之。
事实上,无论在英美法系、大陆法系还是中国法律体系,法律都不可避免地与政治、伦理、道德和民意有着十分紧密的关系。这是因为,法律既是百姓行为的准则,更是最低限度的道德。如果说,法律关系中的权利义务的设定,是法律以正面形式对社会政治、民众舆论、伦理道德所做的回应、确立和宣示,那么,包括刑事责任在内的法律责任的设立和实现,则无疑是法律以负面形式对社会政治、民众舆论、伦理道德进行的回应、宣示和保障。因而象征性是所有法律普遍具备的功能,而非象征性刑法的专利。可以说,没有刑法的象征性,也就没有刑法的政治性和道德性。刑法应当具有也必须具有象征性,但刑法象征性的具备并不等于就是象征性刑法。
至于判决中的罪名适用数量高低,无论与案件实际发生的数量多少还是与法律的实效性状态之间,均非简单的线性对应关系。“如果‘实效’意味着一项规范某种行为的法律规则大部分时候都会被遵守,那么很清楚地,任何规则的‘效力’与其‘实效’之间实在没有必然的关系。”刑法乃“必要的恶”,故而刑法的实效性与刑法的有效性之间,往往呈现出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刑法的效力已如此深植于百姓心中而为百姓忠诚、恪守,践踏刑法而犯罪者属于社会少见反常现象,刑法较少实际动用,以致实质有效的刑法似乎实效性不强;二是刑法的效力如此为公众拒斥漠视,既不为百姓所信守,亦不为司法所适用,徒为一纸空文,以致刑法仅具形式的效力,并无实质的效力和实效;三是刑法的效力刚刚产生,公众对于刑法的忠诚或拒斥尚未在心里生根,以身犯法者屡屡有之,刑法既具有形式上的效力,又具有较强的实效性,至于实质上的效力,则有待于时间的检验沉淀和价值文化的评判演变。
外延与层次:积极刑法观对谦抑性的理论误解
由于前置法中的调整性规则和第一保护性规则乃刑罚权发动的必要条件,刑法两次定量的独立判断和选择建构,才是刑罚权发动的充分条件,从而不仅形成了刑法有别于前置法的基本原理和制度,而且决定了前置法不备,刑罚权不动;刑事立法不规,刑事司法不治,既是刑法谦抑性的形式内涵,更是刑法形式合法性的规范要求;而前置法虽备,但在只有法益之刑法保护必要时,刑罚权方用;刑事立法虽规,但在只有实际动用刑罚权方能实现法益之刑法保护任务时,刑事司法方治,才是刑法谦抑性的实质精义,更是刑法实质合法性的正当根基。如果说形式意义的谦抑确保了刑法的不越位,实质意义的谦抑则确保了刑法的不失职,二者有机结合的关键,在于刑事立法备而刑事司法少用或者不用。
由此决定,在前置法中的第一保护性规则及其调整的第一保护性法益不断拓展,前置法规范中的“法律责任”条文和内容不断丰满,实际动用的前置法制裁力量不断增强以至逐渐接近其上限的情况下,刑法上的犯罪圈如果较之前置法上的不法行为圈过于骨感,这样的刑法是不可能有效发挥保障法作用的。而对于刑事立法没有定型为犯罪加以规制的行为,刑事司法之不用刑,并非刑事司法的谦抑之举,而是刑事司法的守土之责,否则,就是刑事司法对刑事立法的僭越和对体系批判的法益理论之否定。只有在刑事立法之制刑规定和刑事立法之用刑授权的疆域内,刑事司法的谦抑才有闪转腾挪的空间。其结果,或者司法出罪,或者司法定罪,却绝无将立法未予规定为犯罪的行为自行予以司法上的犯罪化处理即司法制刑的可能。
所以,刑事立法谦抑的实现,既不能超越前置法之第一保护性规则划定的第一保护性法益和一般不法行为的范围,又必须通过犯罪化的立法制刑为刑事司法谦抑的实现奠定基础,为刑罚权的实际动用提供规则,二者的有机结合,就是刑事立法制刑之谦抑性必须恪守的规范边界。故而笔者以为,我国晚近刑事立法犯罪化的扩张,既不是背离谦抑性的象征性立法之态,亦非放弃传统刑法观转向积极刑法观的告白檄文;既不是刑法法益日呈稀薄化、活性化的危险征兆,更不是刑法法益作为立法限制批判机能的日薄西山。相反,实乃坚守传统刑法观、担负刑法法益保护使命的刑法现代化的谦抑之道。
扩张与限缩:通往谦抑的刑法现代化之路
与公法的私法化和私法的公法化等现代法治变革潮流相应,我国刑事法治坚守传统刑法观、践行谦抑性的现代化之路,在于立法扩张和司法限缩的并行不悖、张弛有度,即在刑事立法层面,以刑法修正的形式,对犯罪圈进行静态理性扩张和刑罚强度的结构性减弱;在刑事司法层面,通过恢复性司法改革,进行动态适度限缩,从而与前置行政法、民商法以及其他非法律的社会治理方式一起,构建政府掌舵-社会共治-公民自律的多元社会治理体系,助推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一)刑事立法的谦抑之道:犯罪化的静态扩张
遵循法益保护原则和比例原则,以刑罚权发动的空间为纬度,科学增设行政犯,适度扩大重大刑法法益的抽象危险犯设置;以刑罚权发动的强度为经度,扩大非监禁刑配置,降低刑罚制裁的刚性和严苛,应当成为我国刑事立法现代化前行的方向。
其中,行政犯增设的类型,即作为行政犯成立标准的刑法分则中的基础犯罪构成,应视刑法法益的宪法价值位阶高低区别设置:侵犯一般刑法法益的行政犯应以侵害犯或具体危险犯为基础类型;而对于侵犯重大刑法法益的行政犯,则应以抽象危险犯为基础类型,并配以侵害犯或具体危险犯作为加重的犯罪构成,即情节加重犯或结果加重犯,从而形成轻重比例得当、罪责刑相适应的罪刑阶梯,正如《刑法修正案(八)》对污染环境罪的修订。
而刑罚结构调整尤其是非监禁刑的配置,则应成为刑事立法纵向减弱的着力点,并在总则和分则中分别展开。总则层面的调整包括:(1)建立管制和短期自由刑的易科或转处制度;(2)建立形式多样性与后果层次性兼具的现代缓刑制度,增加规定暂缓起诉和暂缓宣告两种缓刑形式,引入罚金缓刑和法人缓刑制度,对于一些过失犯、初犯、轻微偶犯、未成年犯,在缓刑考验期内如尽到法定义务,符合各项监督考察规定,可在缓刑期满时宣告不以犯罪人论处。分则层面的调整重点,则在于罚金刑适用的扩大,一是扩大至所有故意类行政犯,二是扩大至部分过失类行政犯。
(二)刑事司法的谦抑之路:犯罪化的动态限缩
1.在刑法规范的司法适用上,倡导前置法定性与刑事法定量相统一的刑法适用解释规则。对于刑法条文、术语的解释,应当坚守法秩序统一的宪法基本价值要求和部门法之间的结构性、功能性、比例性规范关系,并遵循以下解释进路:(1)按照刑法自身基本原理,立足于刑法规范条文用语的文义进行行为定性的形式解释;(2)延伸至该刑法条文致力于保障的前置民商法或前置行政法所确立的调整性法益和第一保护性法益的本质、前置法之第一保护性规则即“法律责任”规制的不法行为类型、配置的法律制裁方式及其制裁强度综合考量,对刑法规范进行行为定性的实质解释;(3)按照行为的法益侵害程度和刑事制裁必要性,结合刑法第13条但书进行行为定量解释,确定行为入罪的追诉标准。
2.在刑事案件的办案机制上,构建前置法优先处理为原则与刑事法优先处理为例外相统一的刑事案件处理模式。对于“前置法优先处理”机制的构建,笔者建议,当发现正在办理的行政案件或民事案件涉嫌刑事犯罪时,行政执法部门或民事审判部门应在继续行政处理或民事诉讼的同时,将案件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或其他适格的侦查机关,以便侦查机关开展刑事案件立案前的初查,同时将相应案件信息报送检察机关,以实现与检察机关的信息共享,确保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作用的发挥。
至于“以刑事先理为例外”,是指案件涉嫌行政犯罪或民事犯罪并由侦查机关先行发现,侦查机关可自行立案,同时与行政执法机关或民事审判部门实现信息共享,以同步展开案件所涉之行政处理或民事诉讼程序。当然,民事诉讼程序的进行必须恪守民事诉讼基本原则。
结语
法律家的事业在于明察面前的特殊事实与整体结构之间的关系。只有将刑法置于宪法秩序视野下的法律体系中,在宪法价值秩序和比例原则的指引下,在具体法律语境下的部门法规范结构及其相互关系中,探求刑法保障法的真谛,刑法学才能完成知识转型和理论再造,实现对自身的超越。唯此,刑法才能与其他部门法以及非法律的社会治理力量一起,完整而协调地向着宪法的价值目标行进。